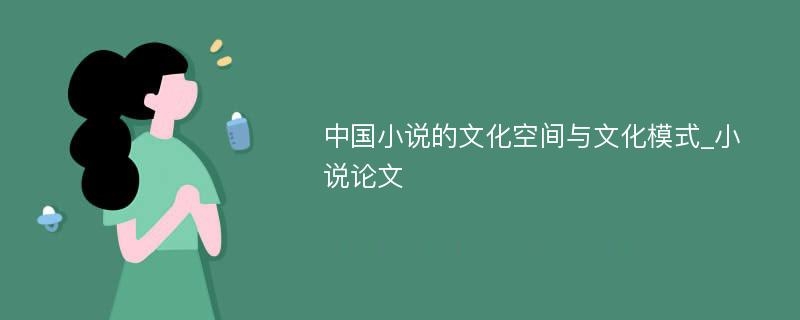
中国小说的文化空间和文化格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中国论文,格局论文,小说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G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3)03-0095-06
中国传统小说历来存在两大系统,一是历史传记系统,对后代小说的叙事时间、结构方式和写作方式影响深远;二是地理志系统,包括地理书、地方志、博物志、风俗志等书籍,对后世小说的自然意识、空间描写及空间思维方式影响深远。前者源远流长自不必说,后者也同样可以追溯到古代神话地理奇书《山海经》,南北朝时期更有炫耀地理博物的《神异经》、《十洲记》,以及记录岁时节日风俗的风俗志《荆楚岁时记》等,至唐宋又出现了《酉阳杂俎》、《东京梦华录》、《梦梁录》等记载市井招商字号、饮食酒点、服饰风貌的作品,以及大批论香(《香谱》)、论石(《云林石谱》)、论酒(《北山酒经》)的博物志。
受此影响,小说方面出现许多带有展示异域风土人情、山川自然景观,特别是奇风异俗的作品,使各种秀美奇特的自然风光与民风民俗,以及寓有象征意味的自然意象在作品中大量涌现,像《西游记》、《镜花缘》、《三宝太监下西洋记》之类作品,更直接以大肆铺陈渲染异域风光为乐事;现代文学史上则出现大批描绘异国风光的留学生文学,如向恺然的《留东外史》、郁达夫的《沉沦》等;当代更是掀起了留学生文学热,著名的小说有《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我在美国当律师》、《我的财富在澳洲》、《上海人在东京》、《陪读夫人》等。它们浓墨重彩地渲染了异域风情和异国他乡的风光。而寻根小说则发掘国内异乡僻壤之地的奇异风俗,如李杭育的葛川江风光、贾平凹的秦地风俗、张承志的草原风景等。
古代神话《山海经》还以山川走向、江河湖泊分布、山岛洞穴等地理方位,作为全书的结构方式,并以此总领起千奇百怪的奇异幻想,将它们纳入一个整体框架。它的叙事特征近于空间艺术,即按照东西南北四面八方的方位和顺序展开叙事,将许许多多神话片断连缀组合成一个宏大的叙事体系。全书分成“海内经”、“海外经”、“大荒经”等,描绘了“大人国”、“小人国”、“丈夫国”、“女子国”等地的风俗、物产及人的奇形怪状。但这个神话体系是不同于古希腊神话体系的,正像杨义所说的:“在这种神话与神话的多方域聚合和历史的代代层积中,中国神话形成了迥异于西方史诗神话的非情节性和多义性的基本特征。”(注: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7页。)这成了后世小说的空间描写、世界视野和空间思维方式的滥觞。
这种空间思维与汉大赋的思维及写作方式也有一定的亲缘关系,典型的汉大赋就是按照四面八方的方位和顺序展开穷形尽相的描绘,如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就是顺着东西南北的次序进行描绘的。这一特点与西方小说理
论家爱·缪尔所说的人物小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将小说分成人物小说与戏剧性小说两类,并认为二者的区别是:“在伟大的人物小说中有无比充塞的空间感觉,正如戏剧性小说中紧凑的时间感觉一样奇特。狄更斯笔下伦敦近乎梦魇的浮华生活;他的书里如此熙熙攘攘的一大群人物,以至场面似乎拥塞到了饱和点;这种只能在人物小说中得到的强烈的空间现实感,同《呼啸山庄》主要场景和《白鲸》结尾中强烈的时间感恰成对照。”(注:爱·缪尔:《小说美学经典三种》,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387页。)
一、中国小说中的虚拟空间
中国小说中还开拓了或者更确切地说臆造了一个幻想的、虚妄的鬼神世界。这是一个神奇、神秘的世界,是一个想像或幻想的空间,同时也是一个文化的空间或符号的空间。它与人世构成了相互对立、比照、对抗、互补等多重关系。它一般由四部分组成:一是所谓地狱世界,又称阴曹地府或冥府;二是天堂世界(含西天极乐世界),又称天宫;三是地上的神仙府第或精灵魔怪生活的地方,它们多在山上、岛上或洞中,像昆仑山、终南山、峨眉山、青城山、蓬莱三山、天台山都是有名的仙山;四是龙宫或水府,一个栖息于江海湖泊的水底世界。
与西方小说不同,中国小说中的鬼神世界与人间的现实世界是相通的,人在偶然或某种机遇的情况下是可以走进这个鬼神世界,做一次逍遥游的,而鬼神更是成天在人间游荡来游荡去,即人与鬼、人与神仙都是可以相交相通的。如志怪小说、唐传奇小说以及《聊斋志异》等小说中,都包含着大量世人漫游地府,漫游仙山神府,以及鬼神来到人间,帮助、谋害凡人或干预人间之事的故事,这显然不同于西方文化中人与神之间存在着天然不可逾越的鸿沟的观念。方士幻想和神仙道教的兴起,使幻想世界的描写日趋系统化和神异化,神仙家的空间幻想逐渐渗入到志怪小说写作中,使志怪小说“在空间形态上,它除了幽明杂陈这种真实空间和虚幻空间的交错之外,还别开生面地寻找非人们所能亲历的殊域空间和洞穴空间”,(注: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第117页。)出现一大批着力描绘或夸饰神仙境地的神异之作。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鬼怪、鬼神小说还摈弃了恐怖、恐惧的美感,充满着缠绵优美的抒情和人性、人情的人间情调,被世俗化了,鬼神世界成了世人熟悉而又陌生的异乡。因此,从文化精神的角度来说,鬼神世界为中国作家提供了一个自由的文化空间,一个可以恣意泼洒才情的地方。中国作家可以借助鬼神世界表达自己的带有异端色彩的思想,或在非现实的面罩掩护下,淋漓尽致地表达对现实的挞伐,发泄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像《聊斋志异》就是典型的一例。
如果说鬼神世界是一个超人间的文化空间,那么武侠小说的江湖世界则是一个超现实的文化空间。作为官府的比照,它是一个法外世界,也是一个化外世界,有着自己的行为规矩和生活方式,带有否定官府世界及其合法性、合理性的色彩;作为现实世界的对立面,它又是一个理想的世界,一个近乎乌托邦的世界。它与现实生活世界相对隔绝独立,并且分庭抗礼;相对于现实世界的拘束限制,它又是一个自由平等、逍遥自在、不受任何王法拘束的世界,是一块净土和乐土,多处在荒山野岭、悬崖山洞、大漠密林之中,散发着天然野趣。
从原型角度来说,它是中国人古老的精神家园——桃花源的投射和变形,有着鲜明的象征色彩。“在至高无上的‘王法’之外,另建作为准法律的‘江湖义气’、‘绿林规矩’;在贪官当道贫富悬殊的‘朝廷’之外,另建损有余以奉不足的合乎天道的‘江湖’,这无疑寄托了芸芸众生对公道和正义的希望。”(注: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2页。)江湖上讲究的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赞扬的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讴歌的是救危济贫、仗义疏财,江湖因此成了公道和正义的象征,成了中国人精神自由超脱的寄托,不再是地域概念或自然概念,而是一个文化的概念、符号的概念。
才子佳人小说中不可缺少的是“后花园”这一文化空间。这里即使不是正统文化的“空白之地”,至少也是薄弱地区,或者说是正统文化的一块飞地,一处“化外之地”。它意味着正统文化的鞭长莫及,也因此能为青年男女的相爱提供了一方热土。《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实际上也属于此类。
二、中国小说的文化格局:南北之争和东西之争
中国小说还存在着地域差别。一是中国小说中存在着南北文化的差异问题,即南北存在着不同的文化精神传承。法国著名文艺理论家斯达尔夫人在《论文学》一书中,将欧洲文学分为南北两大文化区域,并探讨了由于南北环境、气候、土壤等方面的差异所造成的不同文学风貌。南方气候清新,丛林溪流众多,因此,南方人性格开朗活泼,感情细腻柔和,生活富于情趣,且兴趣广泛。北方土地贫瘠,气候阴沉多云,因此,北方人容易滋生生命的忧郁感和哲理的沉思,但同时也造就他们独立坚忍的意志和豪爽慷慨的性格。南北自然条件的不同,又造成文学的不同:南方文学注重人的日常生活,喜欢铺陈刻画大自然的美;而北方文学则更多地将目光投向民族的自豪感和个人意识,这样就使南方文学追求世俗,北方文学张扬崇高。
她的这种观点虽带有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色彩,但用来分析中国文学却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深刻性。中国北方地域辽阔,“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但气候寒冷,自然环境恶劣,或是莽莽林海或是大漠孤烟,或为高原峻岭或为戈壁黄沙,而且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特别是中原更成了逐鹿之地,大规模的征战杀伐连绵不断。而南方气候湿润,遍布江河湖泊,触目皆是茂林修竹和崇山峻岭,山清水秀,风和日丽,“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
北方属于麦菽文化,南方属于稻作文化。前者标榜儒学,儒家的理想在于社稷钟鼎,注重人与社会的协调,滋生伦理道德规范和内省模式;后者以道家及其巫鬼文化著称,道家志在山林,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崇尚自然,耽于幻想,孕育审美人生论和宗教观念。北方有朴实无华的《诗经》,南方有奇幻瑰丽、神秘狂放的《楚辞》。儒道互补,北方朴实的理性光华与南方奇丽的浪漫色彩相伴共生,一同构成中华文化的两大源头。南北文化在美学上存在着几乎相反的风貌:南方是“杏花春雨江南”;北方则是“铁马秋风塞北”。南方优美,妩媚婉约,充满阴柔之气;北方壮美,豪放刚劲,具有阳刚之气。南方明丽如画,秀丽动人;北方沧桑如歌,悲怆感人。南方“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寥廓。其于人也,漻乎其如叹,邈乎其如有思,暖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北方“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镠铁;其于人也,如冯高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姚鼐《复鲁絜非书》)。南方文学笔调柔和舒缓,从容不迫,荡漾着纡徐轻松的旋律,于细波微澜中点染出一幅幅生机盎然、风光旖旎的“清明上河图”,洋溢着喜剧精神;北方文学粗犷豪迈,昂扬激越,喧腾着英雄史诗般的悲壮格调,于大气磅礴中谱写出一部部高亢雄浑的交响曲,响彻着悲剧精神。南方文学犹如清澈见底的山涧溪流,泉声淙淙,韵味悠长,加以两岸翠色葱茏如画,令人赏心悦目,精神获得愉悦慰藉;北方文学则挟着电闪雷鸣,如雪崩冰裂,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击着文坛,使人震惊,给人力量,激励人们勇猛向前。
中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在北方,在长期的南北文化相互影响、渗透融合中,北方占据优势地位。明代中后期随着资本主义在江南萌芽,“在苏州、松江等南方的大都市中,以经济的繁荣为基础,对北方中央文化的批判精神,从明初开始便兴旺流行。市隐,就是以这种情况为背景的一种彻底自由的人群。沈周、祝允明、唐寅、文征明、徐祯卿等这些人,可视为其代表。没有历来权威的一切束缚,自由奔放地生活,他们的共同姿态,就是对于当时士大夫官僚的批判,而且他们时而显得奇矫的行为,却正因此而被民众的趣味爱好所接纳。”(注:内田道夫编:《中国小说世界》,上诲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87页。)南方商业文化开始表现出对北方政治文化的挑战。到了20世纪,先是世纪初的北伐战争,代表的是政治“北伐”,寓意革命的火种从南方撒向北方;后有世纪末港台的通俗文学、大众文化的大举北进,掀起文化上的“北伐战争”。这种北伐随着珠江三角洲经济的崛起和城市群的扩张进一步深入。
具体到文学领域,南北之争还表现为20世纪文坛上的“京派”与“海派”之争。而“京派”和“海派”之争并不仅仅意味着南北文化的对立,同时还标志着一系列文化上的二元对立组合:乡土/城市、乡村文明/都市文明、农业文明/工商业文明、政治型文化/经济型文化、黄河文明/长江文明、传统文化/现代文化、东方文明/西方文明、农民/市民、海派/内陆等。樊星在《北方文化的复兴》中呼唤道:“北方文化中源远流长的刚烈之魂、豪放之气、壮美之情也深深融入一代又一代北方人的血液中——在政治动荡的年代里,它异化为造神的酷热、党同伐异的褊狭,到了思想解放的岁月,它升华为生命的呐喊、创造的激情、慷慨的壮歌。”北方作家的笔下多是叱咤风云、气吞山河具有英雄主义气概的人物,在他们身上闪现着理想主义的光彩。“北方的自然条件比南方严酷,中国历代的战乱又主要集中在北方。因此,北方比南方多苦多难。苦难消磨了多少生命热情,同时又砥砺出多少英雄豪气。”(注:《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2期。)北方造就的多是热血男儿、慷慨之士,泼洒出一腔豪情,写就生命的颂歌、命运的膜拜、人生的礼赞以及苦难的悲歌,格调遒劲挺拔,刚健雄浑,浓烈深沉。
除了南北之争以外,中国文化上还存在着东西之争,在20世纪表现为东南沿海与西北内陆之争。东西部有经济和地理方面的差异,也有文化领域的差异,甚至世纪末还有了“陕军东征”的说法。当然,东西之争不像南北之争那样明显,也不像南北之争那样激烈。
西部多是尚未开发的荒漠之地,幅员辽阔,地老天荒,人烟稀少,是迁客逐臣流放贬谪之地、发配充军之所。西部大自然是奇异瑰丽的,雄奇苍凉,充满着崇高和壮美,如一望无垠的大草原和大沙漠、荒凉冷寂的山谷等。它们有时难免带有恐怖感和神秘感,对人不太友好,给予人的是折磨和痛苦。狂风肆虐时一片飞沙走石,“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绝然不同于内地的和畅蕙风;大雪狂舞时则是:“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犁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翰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此外,还有“空中白雪遥旋灭,蒸沙烁石燃虏云,沸浪炎波煎汉月”的热海以及“火云满山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的火山。既令人不寒而栗,又令人豪情万丈!既有长河落日,大漠孤烟这样壮观美景,以及高山峡谷、森林草原这样独特的地形地貌,又有西风瘦马、古道侠肠的人格精神。对东部中原来说,这些无疑都带有异域蛮荒色彩。
西部潜藏着人和自然的奥秘,西部文学的基调就是人与自然冲突,体现着鲜明的自然意识,色彩浓烈,情调粗犷,有着浓厚的西部情结。西部文学描绘着西部风情,展示着西部人的风采,捕捉着西部地域的神韵。西部文学的大旗在文坛上猎猎作响,迎风飘舞,独领风骚。文坛上的西北风强劲悲凉,展示出边塞的奇异壮丽;高原风则悲壮忧愤,想象奇特,充满着奔腾的激情和磅礴的气势。
到了20世纪末,西部经济落后了,文化也受到挤压,趋于保守、封闭、压抑,但西部不甘于自己的衰落,于是在世纪末演奏了一出“陕军东征”的悲喜剧。之所以说其是悲壮的,是因为带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献身精神,凝重雄奇,表现了西部人勇于挑战东南沿海以发达的商品经济为特征的现代文明;说其是喜剧是因为它打着“纯文学”和反商品经济的旗号,却有效地利用了商业运作手段,给人以不伦不类的滑稽之感,或者说就像堂·吉诃德在那里大战风车。
三、中国小说的文化空间
受地理人文环境的影响,即古人所说的“钟灵毓秀”,山川之美钟于人物,一个地方的地形地貌、山水景观滋养着那里的人,形成这一地域独有的文化传统、文化心理和文化性格,并进而形成多种多样的小说地域流派,如“山药蛋派”、“荷花淀派”,90年代出现的“京味小说”、“津味小说”、“汉味小说”、“苏味小说”概念,以及“晋军”、“湘军”、“鲁军”、“陕军”、“豫军”说法。古代更不用说了,像《越绝书》、《吴越春秋》、《燕丹子》都打上了鲜明的地域文化烙印。中国地域广袤辽阔,无论山川水土自然地貌,还是语言、风俗、信仰、生活方式,都差别很大,地域文化特征始终以隐性传承的方式存在,如古人经常称道的“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关中风土淳厚,民质直而尚义”。
乡土小说中更描绘了许多带有地理标志的“故乡”,构成小说的文化空间坐标,如鲁迅的绍兴、沈从文的湘西、老舍的北平、萧红的呼兰河、师陀的果园城、孙犁的白洋淀、张承志的金牧场、贾平凹的商州、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等,特别是沈从文笔下的湘西风情有着地方志般的精细。再者,小说家们还往往选择一个具有特色的地方进行充分挖掘,并进而创造出典型的意象空间,如鲁迅的“未庄”、王安忆的“小鲍庄”、韩少功的“鸡头寨”、马原的“西藏”、古华的“芙蓉镇”等。那些世界著名作家更是通过发掘某一地方的文化意义而写出著名作品的,如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的马孔多小镇、巴尔扎克《高老头》中的伏尔盖公寓、福克纳的约克帕塔法县。这些小说,不仅写出当地的自然风景和风尚习俗,而且写出其地的生活基调和精神特征,充满诗情画意,令人情不自禁地沉醉在一幅幅散发着乡土气息的风俗画中。茅盾就曾称赞孙犁的小说“既能以金钲羯鼓写风云变色的壮丽,又能以锦瑟银筝传花前月下的清雅”。
山东作家则极力张扬传统儒家的入世精神和重义轻利的人格风貌,像张炜《古船》、矫健《天良》、王润滋《鲁班的子孙》等;湖南作家韩少功有意发掘楚文化精髓,如《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等;浙江作家李杭育则致力于追寻吴越文化神韵,如他的“葛川江”系列小说;陕西的贾平凹、路遥、陈忠实等试图接续三秦文化的“根”;郑万隆的“异乡异闻”刻意张扬关外黑土地的文化精神;张承志则开掘塞外蒙古大草原的文化意蕴。
四、中国小说中的大自然及自然观
古代山水诗和山水散文发达,从六朝模山范水的山水诗和山水美文中就可以领略到古人对自然的亲近和由衷的喜爱,古人还善于将自然人化,人与自然心心相印,其乐融融,体现了古人徜徉山光水色之间的悠闲自在的气度。但罕见展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小说,或者说大自然没能进入小说家的审美视野,仅有的《西游记》、《镜花缘》等几部作品,也没有深入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使偶尔出现描绘大自然风光的段落,也多是套话、熟语,充满了陈词滥调,很少来自作家真正富有个性的、独到的观察,对此夏志清在《中国古典小说导论》曾大加挞伐。
新文学革命后,才开始有了较大改观,出现在小说中的自然景物有了鲜明特色和个性,如鲁迅、郁达夫、萧红等人的小说中,都有十分出色传神的景物描写片断。但真正集束式展现自然风光,当推80年代的寻根派小说。它们集中描绘自然风光,展现大自然性情,发掘大自然情调和内在旋律,甚至可称为“空间小说”、“自然小说”。
他们有的用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细腻笔触,刻画山水、人情,犹如一幅幅工笔山水画,达到了出神入化、浑然一体的境界,写出了人与大自然之间的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关系,深化了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文化观念,像沈从文的《边城》就是表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亲密关系的代表作。小说主人公翠翠与竹林建立了天然的联系,竹林成了翠翠的避难所和安全屏障。那里的青山绿水还净化了人的灵魂心地,使人全无尘世的俗念,像翠翠就犹如出水的芙蓉,犹如活脱脱的自然之子或自然精灵。有的用如椽巨笔泼洒写意山水,写出大自然的神秘、野性,乃至不无恐怖的壮美景观,并浓墨重彩地渲染大自然的种种魔力及对人类生活的支配性作用,写出人们生活环境的恶劣险峻,以至艰苦卓绝。如叶蔚林的《酒殇》、《蓝蓝的木兰溪》等作品,就描画了作为人的绝域、动物乐园的菇母山深处的恶劣自然环境。在这里,人的房屋竟然建在悬崖峭壁之上。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雾界山传奇》、《浮屠岭》等作品描绘了深山密林之中护林人家的生活,荒凉、遥远、封闭、孤独是他们生活环境的主色调。
另一方面有些小说还深入开掘了人与自然冲突主题,这是西方文化观念输入的结果,或表现人与自然的抗争搏斗,表现人在自然的重压下的优雅风度,表达了人要战胜自然、征服自然的决心,尤其是浓墨重彩地渲染了人在凶险野蛮的大自然背景下,进发出的强悍、粗砺和原始的生命力,膜拜礼赞生命的强力;或者刻意宣扬人由于破坏自然,不爱惜自然,从而受到大自然的强烈报复和惩罚。如孔捷生的《大林莽》,就通过人力和自然的神力的冲突,展示了大自然的凛然不可侵犯。“大林莽”的神秘莫测,已经超越了人与自然的生态平衡的意义,俨然成为威严的象征。古华的《浮屠岭》等一系列以林场为背景的小说则着力谴责了极“左”时期人对自然的种种灾难性破坏之举,以前郁郁葱葱、生机盎然的青山翠岭被砍伐殆尽之后,成了贫困瘐瘠的荒山秃岭。人破坏了自然,必将受到自然的惩罚和报复。叶蔚林的《天鹅岭林涛》更是发出了“救救森林、救救大自然”的呼吁。莫应丰的《麂山之谜》不仅以拟人化的手法讲述了黄麂的悲剧,展现了一幅令人触目惊心的人对动物赶尽杀绝的景象,用动物的悲剧隐喻了人类的悲剧,同时小说中还表现出人对大自然的极度敬畏之感。
而出现在这些小说中的大自然还具有不同于古代诗文中的自然风景的美学风貌,特别是有别于唐诗宋词里的婉约娇媚而又优美和谐的自然山水,而表现出大自然的野性、蛮荒、神秘和不驯服,气概恢弘,呈现出的是力的美,是野蛮的美,大自然透露出其雄性气势和阳刚的壮美。这在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邓刚的《迷人的海》和孔捷生的《大林莽》等作品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在他们笔下,大自然被人格化了,仿佛有了自己的生命和灵魂。无论是“北方的河”、南方的“大林莽’、东部“迷人的海”,还是火红火红的红高粱,欢蹦乱跳的黑骏马,仿佛都燃烧着生命的火焰,秉有了生命的灵性和活力。大自然在那里或奔腾跳跃或呻吟呼号,或喃喃细语或咆哮暴虐,或汹涌澎湃或狂放不羁,显示出一种久违的野性雄风,一种大自然本身的强力和自由蓬勃的生命活力,同时也写出了人对自然的亲近和热爱。张承志《北方的河》中的“河”是养育主人公的一方水土,是主人公的血脉和生命的精灵。六条滔滔奔腾的江河,一个个雄奇的自然景观,给读者造成强烈的视觉冲击。阿来的《尘埃落定》则将带有“异域”色彩的西藏风光描画得震撼人心,为岷江、大渡河、嘉陵江上游的康巴高原、河谷、草地、森林涂上一层浓浓的诗意的、梦幻般的光晕,使他笔下的高山、峡谷、森林和绿草都从大地上升腾起来,以一种新的文化视角去观照和探索生养他的藏族的历史、文化和人的心灵,乃至人与自然及宇宙万物的交流感应。
90年代又出现环保小说、生态文学,体现出较强的生态意识。在这些小说中,不仅描绘了一种新的自然景观,展示了一幅幅壮美的图画,更主要的是深入探讨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或者说重新思考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特别是立足于可持续发展,呼吁人们重视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地球及人类的家园。它们不仅抨击人与自然对立冲突的观念,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更反对人对自然的破坏,特别是掠夺性开发,对种种破坏生态平衡之举进行猛烈鞭挞,并站在新的立场上思考环境污染、城市垃圾处理、野生动物保护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