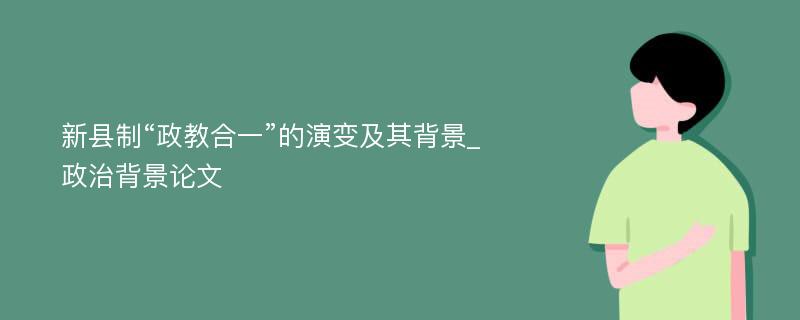
新县制“政教合一”的演进和背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县论文,背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教合一”作为一个专有名词,人们熟知的是指政治与宗教的关系,宗教凌驾于政治之上。但在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政教合一”作为当时特有的称呼,还有另外一个鲜为人知的含义,那就是政治与教育的关系,尤其是指基层政治与基础教育的关系。因此,抗战时期新县制语境下的“政教合一”,是指由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义务教育与成人民众教育组成的国民教育,分别与乡镇、村街保两级基层政治,在人事和制度上的合流、冲突及其互动关系。
政治与教育的关系,古来有之,一般而言,二者关系比较正常。在古代中国,儒家大一统思想独尊,天地君师一体,政治与教化同一,二者关系和谐。在近代西方,普及教育被视作民主政治的基石,各国政府多加重视,教育从属政治。然而,在近代中国,由于新式教育源自域外工业社会,与以农立国的中国国情相扜格,教育与社会、政治分家;加上党派政治势力的插手和干扰,“教育独立”一度甚嚣尘上。政教分离,结果双方均受其累:“一、失却教育即生活之意,二、政治制度和民智不能调和,三、政治不能清明。”① 就是说,政治因为没有教育的能动配合难以清明,民主进程步履蹒跚;教育由于没有政治作为动力,进展缓慢,也未能有效发挥其揭橥的救国功能。这种情形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尤为明显。因此,自20世纪20年代起,民间和官方都有如何妥善处理政教二者关系的诉求。② 1939年9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了《县各级组织纲要》,标志着新县制开始实行。它号称是中国近代甚至秦汉以来重大的政治制度变革,不仅意味着中国传统统治重心由上层移向基层,而且是蒋介石就任国民党总裁,登上权力颠峰后重新调整党、政、民、教,尤其是政治与教育关系的重要举措。
新县制的基本精神“为党,政,民,三位一体之通力合作,其特色为管(政治——笔者注,下同)、教(教育)、养(经济)、卫(军事)四大政术连环运用”③。这是抗战时期新县制推行结束后的1946年的概括。事实上,新县制实施期间④,党政具体关系处于秘密状态⑤,政教关系也比较抽象、隐晦。这种情况影响了时人对它的记载,也制约了后人对它的研究。因而已有相关研究,主要着重于新县制推行的原因目的、法规条文、内容特点、实施经过、得失评价和对基层社会的控制等方面⑥;而对作为其中重要方面的政治与教育纠葛关系——从“政教合长”到“政教分长”,从“政教分长”再到“政教不分家”或“政教相连”的变化过程及其背景动因,尚未进行详细、深入的研究。本文拟通过对新县制中政教一波三折关系的考察,加强对理论上视为天经地义和今天习以为常的政教合作,在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实际运作时,所呈现出来的复杂面相和艰难性的认知。
一、从“政教合长”到“政教分长”
在《县各级组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中,体现了新县制“管教养卫合一”的基本精神和特色。在乡镇方面,第32条规定“乡(镇)公所设民政、警卫、经济、文化四股,各股设主任一人,干事若干人,须有一人专办户籍,由副乡(镇)长及乡(镇)中心学校教员分别担任,并应得酌设专任之事务员”;第34条规定“乡(镇)长、乡镇中心学校校长及乡镇壮丁队队长,暂以一人兼任之。在经济、教育发达之区域,乡镇中心学校校长以专任为原则。”在保甲方面,第49条规定“保长、保国民学校校长、保壮丁队长,暂以一人兼任之。在经济、教育发达之区域,国民学校校长以专任为原则”;第50条规定“保办公处设干事二人至四人,分掌民政、警卫、经济、文化等事务,由副保长及国民学校教员分别担任之”。⑦ 根据时人的解释,进一步发掘上述这些抽象条文背后深层的含义可知,至少有三方面的内容值得注意:第一,在管教养卫四者之中,以政教为重心;第二,政与教之间关系密切;第三,政教合长有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
依新县制重要参与者、四川省民政厅长胡次威的见解,“管教”之所以成为管教养卫的“重心所在”,是因为“‘养’‘卫’的推行,均须先有‘管’‘教’的设施。‘管’的目的在‘教’‘养’‘卫’的机构组织与人事的健全;‘教’的目的在‘管’‘养’‘卫’的人才和方法的训练与充实。‘管’‘教’能联系推进,‘养’‘卫’自亦顺利完成。”⑧ 一人兼三长、政教合长制主要由广西、江西的“管、教、养”三位一体制演变而来。⑨ 如广西省自1934年开始实行三位一体制度,到新县制实施之前,在内涵上已比较固定。“从人事方面说,就是一人三长的制度,即乡(镇)长兼任中心国民基础学校校长、民团后备队大队长;村(街)长兼任国民基础学校校长、民团后备队队长。从事务方面说:就是乡(镇)公所,中心国民基础学校,民团大队部三机关合并办公。人员互助工作,办公设备,互为应用;再从工作的性能方面说,则是以乡(镇)村(街)公所为中心领导机构,运用民团的组织力量推动建设,以基础学校实施教育,以教育的力量,辅助建设工作的进行,而统一于乡(镇)村(街)长的掌握之下。”⑩ 这里有两点需要指出,一为以行政为主导的政治、教育和军事的综合一体制,政教关系紧密;二是一人兼三职,兼职不支薪,三个办公机关“一屋三用”。这样做的原因,用省主席黄旭初的话来说是因“地方财政困难”,旨在“节省经费”。(11) 这是三位一体制实施的经济基础。
1939年6月,蒋介石在被称为《纲要》蓝本的《确定县各级组织问题》讲演中说:“为解决最重要的经费与人才问题,所有乡(镇)及保(或村街)的干事,均由学校教师分别担任。所有乡(镇)保长、学校校长及壮丁队长均暂由一人兼任,以收管、教、养卫合一之效。但在经济、教育发达的区域,自治事务纷繁,乡(镇)中心学校校长及保的国民学校校长,仍以专任为原则,期集中职责,而免兼顾困难。”(12) 这显然借鉴了广西的三位一体制度,而又有所不同。“借鉴”就是人事上“一人兼三长”,目的还是为了解决“最重要的”经费与人才问题;“不同”即并没有明确提出由乡镇保长兼任两级校长。
《纲要》中的第34、49条,对蒋介石《确定县各级组织问题》讲演中的有关提法,既有继承,也有变通。“继承”,即在政治与教育关系上,以组织人事为纽带,在干部负责人层面,仍然没有规定“一人兼三长”以谁为主导;在一般教师层面,通过兼任镇保干事办法,佐理地方事务,使“政教两方面人与事之相互沟通”。(13) 产自长期与南京国民政府对立之广西地方的三位一体制度,这时之所以能够上升为国策,是因为全面抗战爆发后,富庶的东南沿海先后沦陷,“中国的经济重心”由东南向“内地”和比较落后的农村转移(14),经费、人才奇缺,迫切需要节约型的基层政治制度。而没有明确规定由谁来兼任三长,实与《纲要》制定过程中出现以管(保甲)为主,还是教育为主的分歧有关。在双方相持不下的情况下,只好折中、妥协和模糊处理,不作明确规定。“变通”体现在一人兼三长的规定趋向弹性。若将《纲要》有关规定,与《确定县各级组织问题》演讲中的相关内容——“所有乡(镇)保长、学校校长及壮丁队长均暂由一人兼任……但在经济、教育发达的区域,自治事务纷繁,乡(镇)中心学校校长及保的国民学校校长,仍以专任为原则”进行比对,可知“所有……均”三字被删掉,“但……以专任为原则”继续沿用。依据姜书阁的看法,这实际上是将蒋介石演讲中的乡镇保“‘政教合长’之绝对性,变成以校长专任为原则,而以暂时兼任为过渡”的相对性和弹性制。换言之,“一人兼三长”的政教合长制或校长兼任制是暂时和过渡的,“一人一长”的校长专任制才是最终目的。这是《纲要》较蒋氏演讲的变化和改进之处,为“极有价值极可宝贵的一个特点”。(15) 而合长制向专任制的转化和过渡,何时、何地完成,纯以“经济、教育发达”与否为前提条件,再一次说明经济以及教育水平,是政教由合长制转向分长制的最大制约因素。
可见,在新县制推行之初的1940年,各方对《县各级组织纲要》有关条文的解释,以政教为主;而在以人事为纽带的政治与教育关系中,一人兼三长的负责人兼职的领导关系,自然要比以一般教员为媒介的政与教互动关系受到人们的关注。政教合长制或兼任制,向校长专任制的变化趋势,取决于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这也表明立法者在重视政教合长制综合方面优长的同时,已开始意识到它在分工和专业上的不足。
专治新县制的粟显运认为,“三位一体”符合中国基层经济落后、社会分工不发达的国情,因之对地方行政而言,至少有四方面的优点:减少摩擦、增进效能、节省经费、利用人力。仅以“增进效能”为例,在基层推行政令,“各部门的工作需要密切配合,才(能)够增进行政效率”。如办理国民学校,必须将全保失学儿童和成年人调查清楚方能着手;宣布政令可以运用学校做工具,并且能令学生参加实践工作,使理论与实践完全合一、教学做打成一片。又如编练壮丁,必须将户籍编制完整,壮丁调查清楚;同时在文化方面又必须使民众了解组训壮丁的意义。“诸如此类,只有实行三位一体制,才能做得到,才能增进行政效能。”(16) 关于“三位一体”、“一人三长”的作用,从前一般的看法多以加强思想控制一言以蔽之,加以否定。(17) 如果从上述社会综合的角度来看,它对地方行政的进步仍有不少可取之处。
关于三位一体、政教合长的不足,据蒋介石的概括,主要有两点:“其困难在人才难得,其流弊恐专权害公。”(18) 围绕着对这些缺点的认识、讨论和克服解决,出现两种不同的思路和方法。
“人才难得”,主要是从专业和分工方面而言,指术业有专攻,一人三长,实难得此种同时拥有管教养卫各项技能的全才。姜书阁正是从教育专业化和政教性质不同的角度,批评“政教合长”制不足为训。从专业化来说,“现在教育学术已成一种极繁难的专科,毕生从事犹恐不及,岂可以一知半解之人,而随便付以代管之责”。从政教性质而论,“教育毕竟与行政殊科,一般乡镇保长多属门外,付以办学之任,实有不妥。故以地方行政的立场遴选的乡镇保长,大抵均不适于充任学校校长。若令兼任,自不免有许多困难之处,但若站在教育立场遴选适当校长而令其兼任乡镇保长,亦不免对地方行政有许多隔膜之处。所以政教合长确是不可为训的办法。”(19)
事实上也是如此。在基层社会负责人中,有的对教育有研究,而无政治经验;有的政治、军事颇有基础,而缺乏教育程度。曾有某县原任小学校长数人,因考取了乡镇长,经受训后很想在任上有一番作为,但履职不到两个月,便以“我只后(原文如此,‘后’疑为‘会’之误——笔者)教书,办不了乡镇各项事务,更乏应付环境之能力”而请求辞职。(20) 这是会当校长并不一定能做好乡镇长的典型例证。而对政治有兴趣而教育资格和程度不够者,实际上主要是指乡镇保长兼校长的制度。这种以行政为主体和本位,教育为兼职的做法,为时人、特别是教育界所诟病。在新县制实施以后,虽然《纲要》并未明确规定由谁兼谁,但各省市政府借口地方人才和经费缺乏,“一律以乡镇长兼任中心学校校长,保长兼任国民学校校长”。而乡镇长保长多数“不但缺乏常识,根本不懂教育,甚至有不识之无的”。对教育,他们挪用经费,支配人事,挂名支取干薪,流弊甚多。结果,原任校长、教职员“纷纷离职而去”,小学教育遭受重创。(21) 原教育部国民教育司司长顾树森的这一事后回忆,对乡镇保长兼任校长制几乎全盘否定,未免以偏概全和渗入后来观念。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对教育质量的提高无疑有影响,但并不等于说“三位一体制”对教育有害而无益。至少在行政力量的强制作用之下,国民教育短期内在量上的普及能有较快推进,因而不能像顾树森和有些学人那样,笼统地说“三位一体”对教育一无是处,尤其是在中国普及教育尚未发达的历史条件下。否则,就很难解释新县制实施仅一年后,国民教育“在量的方面,已有飞跃之进展”这一被誉为新县制“最大之收获”的事实。(22) 教育因此受损和亏空一面,当然也毋庸置疑。
在乡镇长、保长兼任校长制下,为防止教育成为附庸,教育理论界提出许多补救的办法。其中的关键是,除校长逐渐专任外,主要是增设协助校长、专门负责教育的教导主任和提高行政负责人兼任校长的教育程度和资格。1940年6月,罗廷光提出三个主张:第一,“实行分工合作”。对于教育应指定专人,如教导主任负责,校长只总其成,加以督促指导而已;第二,多镇长、保长人选,应“具有小学校长的合法资格”,即应系师范毕业生;第三,最好能实行“校长专任”。(23) 同年11月,广西国民基础教育的开创者雷沛鸿结合本省的情形,发表《广西省三位一体制度运用问题》一文。该文指出:乡(镇)、村(街)长政务纷繁,“顾此失彼”;在教育方面,不但无暇担任教课,而且未遑兼顾校务,非但不足以省人才、经费,反而产生了教育“有名无实”,教师“荒废教课”以及随乡村长“调动频繁”等弊端。既然政教合长制节省经费和人才这一赖以生存的基础已动摇,且给教育带来那么多的负面影响,那么它的改变就势在必行。为此,雷沛鸿提出以下解决办法:各校设校务主任一人,协助校长主持教务,并经县政府委任;副乡镇村街长不兼教师,以期各专职责;学校协助地方政务之推行,“应以不妨碍教课为原则”;兼任校长逐渐改设为专任;确定教育为地方自治事业。该文因“确有独到见解”发表在教育部的权威机关刊物《教育通讯》上。(24) 设校务主任、校长专任、学校不能无原则地迁就地方政务等主张,与前述罗廷光的办法一脉相承而又有明显的发展,且对下文论及的国民参政会有关议案的通过,产生指向性和案例性的影响。
关于补救乡镇保长兼校长造成的“专权害公”的办法,蒋介石建议“加重副乡镇长之权限,充实民乡(乡民)代表会之监督权”(25)。在外充实和加强该代表会监督权的设想,在人治发达、法制欠健全的条件下,操作起来并非易事,倒是内部分权的办法与舆论界的主张有不少相通之处。对三位一体制,与教育界极力谋求改变不同,舆论界多主张加以修正和完善。1940年2月30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批评全才难得的观点,是“不知乡镇保长中尚有副乡镇长保长之规定”,主张借重和增加副乡镇保长职权,变成“三位一体两干部制度,灵活运用”。主张学校校长须合于一定资格方可胜任;若正职不合,副职可以使之适应,则问题“即可得到适当的解决”。(26) 几乎在同时,赵海金在与中央日报社关系密切的《中央周刊》发表文章,坚持乡镇保长兼任校长制。至于由此带来一人多职、无暇他顾的缺点,他建议可藉增设“有给职之副校长”加以解决;并认为此举有利于利用国人“作之君,作之师”的传统心理,“以利政务之推行”,以及使乡镇保长“无兼顾不暇之虞”等好处。(27) 同年9月,曾做过实验县县长的张鸿钧,则主张采用各级壮丁队长分别隶属于区长、乡长、保长之下的“辖而不兼”制,以解决军事人才难得的三长制问题。(28) 这些作者与政界有或多或少的瓜葛,因而他们的主张,采取或提高副职权力,或增设专业负责人进行分工,或放弃部分权力的做法,旨在维护和完善以政治为本位的兼任制,属于制度内的修补。相反,教育界,尤其是教育行政部门,侧重在制度和行动上采取以教育为本位的校长专任制,或者有条件限制的行政负责人为本职的校长兼职制,涉及整个制度的变动。因而,政教双方在解决政教合长问题的取向上,泾渭分明。
政治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是人事问题;而人事的解决有赖于组织制度和法规的明确和理顺。曾长期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1938年1月改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深谙“希望人事上不摩擦,必须在制度上办法不摩擦,否则无济于事”之道。(29) 于是设法重新强调或明确原来模糊不清的有关政教合长的规定。1941年12月,教育部国民教育司通过“私人”关系,在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大会上,提出了篇幅颇长的《凡中心国民学校、国民学校校长,应尽量改为专任案》。这里,“私人”主要是指与顾树森有旧的参政员,包括中华职业教育社成员江恒源、黄炎培、冷通,以及反对县政中废局设科、边缘化教育的北大派傅斯年(30)、钱端升、陶孟和等人。提案联署者还有陈启天、李廉方、王云五、褚辅成、耿毅等,一共23人,多数为教育文化界知名人士或态度比较中立的国民党元老、社会贤达。议案最后获得了通过,要点可概括为:第一,各地乡镇长保长之人选均未能达到教育理想的标准,以致办教非人,教育成为附属机关,甚至动摇原来小学教育的基础;第二,地方教育向由地方教育行政机关直接负责管理,今改为从属于国民政府管辖的乡镇长兼长学校行政,势必造成地方教育行政机关因无权任免校长而无法监管地方教育;第三,地方自治以教育为基础,理应借重校长、教员,今反而利用不具资格的乡镇保长政府官员长教,实与新县制立法用意相矛盾;第四,最早实施新县制、推行“一人三长”的广西已承认乡镇保长兼任校长使教育失败,今已将校长一律改为专任,已有前车之鉴。解决问题的主要办法为:中心国民学校、保国民学校校长尽量改为专任;或以校长兼任镇长、保长为第一原则;而不具备师范毕业等资格的乡镇保长绝对不能兼校长。也就是说,在政教关系上,提高了教育地位;在管理上,提高县教育行政机关的地位,使有权任免校长。(31) 其中心内容是抨击各地一律以乡镇长或保长兼任国民学校校长的做法,揭露其给教育造成的弊端,并提出了解决办法,多少反映了以教育界为主的意志。
对此,盼望已久的教育部积极跟进。除转发行政院通过的国民参政会上述“洞中时弊”的提案,要求各省照办外,很快就在烽火连天的1942年2月召开全国性国民教育大会,通过了《乡镇中心学校保国民学校校长专任兼任问题案》。议案的内容主要有三大方面:其一,中心学校及国民学校校长应以专任为原则;其二,经费不足、教育不发达之区域,因人才不足暂时无法专任者,“应以校长兼任乡镇保长为第一原则,而以合于小学校长资格之乡镇保长之兼校长为第二原则”,但均应依照下列规定办理:(1)中心学校及国民学校校长应以兼任副乡镇长副保长为原则;(2)无论校长兼乡镇保长或乡镇保长兼校长,学校应设教导主任,以便协助主持校务;(3)乡镇保长兼校长一律由县政府核委;(4)兼任系暂时性质,一俟经费筹足,师资造就后,仍应改为专任;其三,乡镇保长兼校长资格,应于乡镇组织暂行条例规定资格以外,另行规定以兹补救。(32) 议案最后一方面的内容过于简单,令人费解。原来在此前的1941年8月9日,国民政府公布了《乡镇组织暂行条例》。其中的第28、29、53、54条,关于乡镇保长兼任中心校、国民学校校长资格,只是将“师范学校毕业”等列为担任上述两种职务的四或五个条件之一,而没有规定为兼任两类校长资格必备的专门限制条件。(33) 这与前述国民参政会提案有关规定相左,显然对乡镇保长兼校长教育资格的要求过低,故需“另行规定以兹补救”。
按照贵州教育界人士张英的解读,在国民参政会提案基础上产生的教育部的议案,实际上提出了次序有先后、限制程度有不同的三个原则:“中心及国民学校校长应以专任为第一原则,以校长兼任乡保长或副乡保长为第二原则,而以具有校长资格之乡保长兼任校长为第三原则。”(34) 校长专任本是《纲要》法定,先由国民参政会重提为“尽量改为专任”;进而变成教育部的“应以专任为原则”,最后上升为“第一原则”。对乡、镇、保长兼任校长的做法来说,这实际上是一种逐步加强的否定。第二原则强调了以教育为本职、行政为兼职,与原来各地事实上以行政为本职、教育为兼职的做法,重心正好发生逆转,可谓针锋相对。第三原则提高了行政兼任校长的资格和门槛,并以校长兼任副乡镇保长或设教导主任加以牵制和分权。总之,在解决政教合长问题上,政教双方明显具有各为本位、争夺权力的考虑。
有意思的是,正当教育与行政两个官方行政系统为基层行政、教育负责人谁兼谁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民间教育学术团体则提出,解决问题的重点应该放在比较超然和相对现实可行的校长专任上,而不应纠缠在双方各走极端的兼任制上。1942年7月,中华儿童教育社在第九届年会上发表宣言,称:保甲长兼任学校行政或教职,会动摇或破坏原本完整的学校教育基础,“此实国民教育之最大危机”;反之,“在目前师资缺乏,尚不能达到以校长兼任保甲长施行以教育为中心之政治时,应厉行国民学校中心学校专任制,以期巩固国民教育之基础”。(35) 校长专任本是法定,又可以暂时游离于政教本位之争的漩涡之外,而且符合教育界自身力不从心的实际,应是较为平实之论。
新县制中政教合长以及校长专任、兼任之争,在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大会和全国国民教育大会后似乎得到了解决。然而,在现实中,由于政治主宰和行政权力独大的作用,各省市并没有切实依照无实权的国民参政会的决议和鞭长莫及的教育部的命令行事,以致教育部长陈立夫也哀叹“地方教育更困难了”。
总之,尽管《县各级组织纲要》没有明文规定一人兼三长究竟以谁为本位,但由于经费和人才两缺,以行政为本职、教育为兼职的政教合长制,还是一度成为主流。这比较符合抗战时期中国基层社会经济欠发达和战时权力高度集中的现实,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不宜简单以加强思想控制予以否定。但从分工和专业化的角度论,则有权力过于集中和教育被边缘化的弊病,这决定了政教必然由合长制过渡到分长制。在这一过渡和转化过程中,与行政界试图修正和完善以自己为中心的合长制明显不同,也与民间教育界倾向于校长专任的政教分长制有所区别,教育官方极力争取向以教育为本职、行政为兼职制的改变,遂与行政方面形成冲突的焦点。
二、从“政教分长”到“政教相连”
由于新县制重要发源地以及“三位一体”的原产地广西,在行动上首先进行政教分长的改革,加上国民参政会、行政院和教育部的呼吁,各地开始逐渐实行校长专任制。政教双方似乎可以相安无事了。岂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校长专任后,尽管有“人才物色,教育易于开展”,“办学者心意专一,专心致志”和“较能分工合作”等优点,但由此造成的缺点也显而易见,“各自为政,政教易于脱节”,“乡镇保长与校长间,往往发生摩擦,摧残教育”。(36) 即政教突出分工后,又走向另一极端,产生了新的政教分离和不合作,甚至出现了取消三位一体制的论调。这意味着有重蹈以前政教分离覆辙的危险。这显然是一种倒退,也再度表明政教合一问题的棘手和复杂。如前所述,《县各级组织纲要》在组织与人事上,规定了一人兼三长和明确教师参与地方行政两个主次层面分明的政与教之间的关系;但政教分长之后,为了克服新的政教分离带来的问题,原先处于次要层面的教育与地方行政联系的重要性开始凸显,并逐渐上升为主要方面。这表明原有的政教合一和“三位一体”制已无法适应实际情况变化,需要进行新的理论解释和论证。
这种情况在广西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以先行一步、问题暴露较早的广西为主,结合全国教育界以及实行新县制的一些重要省份(如四川),能够非常典型地剖析这一问题。此前学界先后分别从军事和现代化、综合、基层社会控制的角度,对广西的三位一体制作了研究,时间多限于1940年之前的广西本地情况(37);但对1941年校长专任后,政教之间的摩擦、政教分长而不分家和政教相连的重新强调,甚少涉及,也没有置于全国范围内考虑。而这些问题对研究三位一体的变通、新解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校长专任后,政教分离造成了两败俱伤的严重后果。校长改为专任,这是对“一人三长”的一大改变,其影响立竿见影。1941年11月,梁上燕转引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在一次省府纪念周上的原话,说“目前有一种不良现象,就是专任校长,往往看不起乡镇长,以致两方面不能密切联系合作,甚至两方面所用器具,界限亦分得很清楚,毫无通融之处。”(38) 政教关系重趋紧张,双方均蒙受损失,两败俱伤,教育尤甚。“现在我们看到各处的乡村公所与中心国民学校在工作上能彼此的经常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的有多少呢?真是凤毛麟角,大多彼此不相闻问,相互歧视,甚至尚有对立起来,互相牵制阻碍,这种现象,尤以学校自设立专任校长以来表现的最为显著。”(39) 为解决这一新问题,教育学术界对三位一体制的变化进行了理论探究。广西教育界多认为校长专任,旨在使政教更好分工与合作,并非对三位一体制的取消,而是一种保持和变通。“一人三长”的主要问题是违反分工的原则。因此,梁上燕在肯定政教分长的分工意义的同时,注意到政教之间的合作和联系,强调这是对三位一体的保持、变通。因为“乡镇公所内部设置的民政、警卫、经济、文化等股,各股主任与干事,仍由中心校教员分担,这就是保持了三位一体的精神,实施管教养卫打成一片的办法。所以,政教分长,我们应该看作三位一体制办法的变通、演进,而不是三位一体制的取消。”又因为基层管教养卫四大建设,原则上需要由乡村长统筹计划,并妥善分配给四大部门工作人员分担。这种“人力分工,事业合一的方法,是可以保证政教分长后,各项建设事业的均衡发展”。(40) 1942年2月,卢显能认为校长专任,适应了政教分工合作的事实需要。基层建设事业的变化,由简而繁;基层人员的分工,也由粗而精。因此,专任校长的设置,即适应这些“事实的需要”。他还特别点醒,在“三位一体”制度之下,专任校长的设置,“只是‘政教分长’,而不是‘政教分家’”;政教分长的作用,“在加强政教的合一”。(41)
而在理论上有明显的创新,将政教分长而不分家说得最为清楚者,当推1941年3月浙江大学教授李相勗提出的“三位一体”制的含义“有广狭之分”说。广义即“把教育和地方建设打成一片……实施‘管、教、养、卫’合一的教育”;狭义“就是‘一人三长制’”。他断言:一般人所诟病者,实为“狭义的三位一体制”;而对广义三位一体制,“军政教打成一片,任何人不能怀疑的”。此说的意义在于,不但在含义上和评价上剥离出三位一体的两种内容,较笼统地说一人三长制弊多利少要准确、深入,而且突出了以往多注意政教一元化和分工,而有所忽略的两者联系这一更重要的内容,独具匠心和慧眼。(42) 事实上,教育界对“三位一体”一直都有政教联系区别甚至重于政教合长的看法,只是被淹没在外观上抢眼的政教合长的形式上,而没有引起注意而已。在新县制实施前的1935年8月,朱智贤就已注意到“政富教合一”“是事业的策略与路线的合一,而技术的研究与改进却不应合一”。具体而言,合一是“单指教育和政治经济呼应合作以达到真实的建设的目的这一点而言,而不是把三件事自始至终混而为一,或把教育和政治经济完全并到一块,因为教育政治经济各有其专门的技术,这些技术需要有详细的精密的分工,才能进步,才得正确”。(43) 这一政治、经济、教育三者事业上应合作联系,专业技术上要分工的观点的提出,颇富前瞻性。在新县制开始不久的1940年6月,罗廷光已清醒地预见“校长纵然专任,但与普通行政(民政、财政、建设、警卫——原注)及军事仍是息息相关,毫无隔阂的”(44)。与此同时,广西三位一体制的重要创造者之一雷沛鸿也明确指出,“一人三长”或“一所三用”并不等于三位一体制;相反,“教育要以政治经济军事的需要为中心,教育要靠政治军事去推进,而政治军事又靠教育做它的方法,才能展开与发展。这是运用三位一体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45) 雷氏的看法,不仅认识到“一人三长”与“三位一体”的区别,而且摆正了政治与教育之间的主与次、体和用的关系,在当时政教纠纷过程中容易沉溺于自身本位而不自知的情况下,为教育界少见的一种理性认识。同为抗战时期一度播迁在广西的浙江大学任教授的雷沛鸿,将“三位一体”的主要精神放在联系而非一人三长上的看法,这对其同事李相勗来说应该不陌生。换言之,李相勗的三位一体制有广义、狭义说,实为对当时教育界开始重视三位一体制中联系重于或优于行政合长的一种概括和提高。
在论证校长专任后并没有违背三位一体制的同时,还出现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广西“三位一体”由于缺乏或不够重视实际上更加重要的“养”——经济建设,与新县制管教养卫在内容上,未能一一对应和扣合。不少省外学者批评这是广西本制“最大的缺点”。原因是“管教养卫是政治的四大部分,等于桌子的四个足,缺一不可的,三位一体的制度,缺了养的一个足,因而推行其它三部分的工作,就要发生很大的阻碍”。故必须在三位一体的制度基础上,再加入“养”这个部分而变为“四位一体”。(46) 尽管早在5年前,时任广西教育厅长的雷沛鸿已注意及此,但这时也不得不重申:桂省要“发扬三位一体制的精神,使管教养卫更密切地联系,更进一步地推行四大(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建设,在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建设,务须全力以赴,努力增加生产,并要求分配的合理化,以改善民众生活”(47)。三位一体制在全国视野之下,加入并强调了最重要的经济建设,真正成为“四位一体”,并在《广西省基层经济建设纲领》中得到体现和落实,在内容上更加匹配新县制管教养卫的精神。这是广西三位一体制在内容上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也是在全国抗战的大背景下,此前长期与中央对立的广西与全国在制度上对接和统一的一种表现。
除理论上进行新的论证外,广西教育界还对政教分长后如何保持和加强两者之间的关系,献计出策。其中,既有集体的建言,也有个人的主张。
1941年3月21日,桂林市第廿三次基础教育座谈会就《校长专任后与政教联系问题》进行专题研讨。与会教育界人士叶昌歧、郭资厚、金开山、李文圃、陆静山、丘奕焕等作了发言,提出不少建设性的主张。如郭资厚首先批评政教分家的错误,认为校长专任是为了更好的分工,并提出政教应如何“适当”地进行合作:“在以前镇校合一的时候,为了处理镇方面的事体,常把功课停着,以致学生家庭常发生反感,今后如遇政务较小的事体,校长及各主任教师,应作部分协助,较大的事体,应作全体动员之协助,以达到政令之完成,这才是适当的处理。”李文圃自信,如能做到下面各点,政教联系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一)怎能使学校教师乡镇长能互相认识清楚自己职责。(二)在同一地点办公。(三)应具有真诚的态度。(四)双方互助。(五)校镇两方开会应互相邀约出席。(六)我们应认清事务是共同的,工作进行是分工的。”这未免过于乐观。况且,当天会议只有教方人员参加,没有镇、街方的人士出席,不无一厢情愿之憾。(48)
广西省政府曾颁布过《广西各县(市)乡(镇)村(街)公所与设置专任校长之基础学校联系办法》。1941年11月,梁上燕据此认为校长专任后,政教工作联系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49) 第一,“隶属问题”。上述《联系办法》曾规定“学校对于乡村公所,视为上级机关,行文对公所用呈”。但后来乡镇教育权收归县、市上级机关管辖后,公所对学校行政权限,只限于筹措经费和使用民力,其他学校行政事务不必向公所分呈转呈,而可“径呈县(市)政府核办”。结果,乡镇长就不再与校长合作,声称“以后学校要修理,学生不上课这一类事,都不要再问我”。(50) 这使校长办事很感困难,教育与行政明显脱节。不少县长甚至提出废除校长专任制,退回原来的三位一体制。对此,梁上燕主张乡镇长与专任校长应该认真讨论,订定某一事项,须呈由公所转呈,做出详细的规定,既“可以使行政处理迅速,而又可以免去种种误会与纠纷”。第二、第三分别为“场所问题”和“合作问题”。关于场所,由于原来的“一人三长”、“一所三用”,无论工役、房舍、器具多属政教双方共同使用,现在政教已分长,场所使用时,“必须订定办法”。关于合作,《联系办法》规定:公所应运用行政力量,积极推行教育事业;学校应协助公所,推行乡村政务。要想实现两者之间的合作,双方“工作计划与实施办法,应该容纳彼此的互助办法”。此外,村长、校长彼此之间,应共同出席各自有关会议,双方待遇一致、奖励均沾。
在解决校长专任后政教如何联系问题上,与桂林教育界单方面集体提出的建议相比,供职于县教育行政机关的梁上燕所提的办法较为具体,可操作性应该说要强一些。但与实施新县制最重要地区之一的四川省各县自实际工作第一线、由行政方面总结出来的经验相比,仍不免相形见绌。这些浓缩的经验包括:“专任校长人选,由乡镇保长遴选合格教师二人至三人,报请县政府择优核委,不随乡镇保长去留,以求人事之协调与健全”;“所有学校筹募基金、建筑校舍、充实设备、督催入学等必须用行政力量推行之事务,由乡镇保长负责,其余校内人事及教务训育事项,由专任校长负责办理”;“办理乡镇保教育及其它文化事业,应规定其分层负责,专任校长者由校长负第一层责任,乡镇保长负第二层责任,不致因校长之是否兼任而有畸轻畸重之现象”;“政教合一之真义,固不拘形式之‘兼任’与否?而重在政教力量之相互为用,以发挥‘藉政治力量实施教育,以教育方法改进政治’之功效”。(51) 纸上得来终觉浅。专任校长人选的规定和流动过频对教育影响的修正,行政、学校负责人事务划分,以及层级负责制的明细化等实际经验,较广西主要是从教育界和理论上得来的办法,显然更胜一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全国各地政教之间的合作联系已无懈可击。直到1943年5月,仍存在不少问题,如乡镇中心校、保国民学校布点不合理,校址多数与乡保不相邻,乡保各股干事由学校教员兼任,因距离遥远,等于有名无实。学校筹款招生,强迫入学等工作,也无法获得乡保的帮助。(52)
总之,针对校长专任后出现的政教重新分离的现象和后果,广西、四川两省的教育部门和行政部门,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解决问题的创新性设想,着重发掘和彰显政与教之间的互动联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置于“一人三长”人事之上,从而使政教相连关系调整、校正在一种比较适度的位置和程度上。这无论对保证新县制政教合一制度在全国的运行和逐步完善,还是妥善处理政治与教育的关系,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意义。
三、政教冲突的背景
乡(镇)长、保长,壮丁队长,中心学校、保国民学校校长,均以一人兼任为原则,最初用意之一在于使政教兼顾,保持平衡。这一并非完全侧重行政,而是便于政教双方互动和联系、不分轩轾的良好愿望,何以在实际运行中造成双方关系紧张,走向反面?究其原因,主观上与国民党政府各有关方面利益博弈分不开;客观上则是近代中国引进分工发达背景下的西方教育,与中国社会分工欠发达的国情相枘凿的结果。
国民党政府各有关方面利益博弈,由浅入深,包括受其管辖的行政、教育两界本位思想,管理机关教育部与内政部矛盾,以及掌控教育部的CC派积极扩张和与内政部关系密切的政学系互相排挤等方面。这几层的利益又时常缠绕在一起,难以分割,使得政教冲突问题变得格外复杂。
研究新县制不能仅仅满足于法规条文的罗列,而应深究条文制定的经过及其背后动因。任何法规的制定,都是各种学说、理论和各派意见,甚至利益的一种结晶或妥协。《县各级组织纲要》主要起草人和参加者有张群(主持人)、熊式辉(中央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甘乃光(曾任内政部次长,时为中央设计局秘书长)、雷殷(原为广西民政厅长,后任内政部常务次长)、王先强(浙江民政厅长、内政部民政司长)、蒋经国(江西赣南专员)、李宗黄(中央党部地方自治委员会主任委员)等,既有张群、熊式辉、甘乃光等新政学系头面人物以及与其接近的行政要员,也有李宗黄等CC系骨干分子。(53) 这一起草班子中,中央与地方、党与政、不同派系都有,构成复杂,播下以后纷争的种子。
作为一个集大成的制度,新县制吸收了广西、江西、浙江等省地方自治的经验。(54) 如前所述,它在条文制度形成过程中,就已出现教育和政治究竟以谁为中心和本位的争论。教育界以平教会为代表,认为新县制的基本建设“应以教为中心”。理由为中国之所以贫弱,其病在愚,因此普及教育,开发民智,为地方自治当务之急。政方以推行保甲为本位的江西等地为代表,主张新县制“应以管为主”。理由是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要管理,权力就得集中,因而保甲应为新县制建设的主要任务。(55) 与此同时,教育界为改变弱势处境和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在推波助澜。一就在《县各级组织纲要》出台前夕,针对此前偏重民众组织和训练、忽略教育效用的“保甲合一”做法造成乡村教育退化的现状,陕西教育界有人建议,政府应该另订“保教合一”的办法。即“将保甲附着于教育以行,以教育来运用保甲”;保长必须听命于保学的教师,并不得“兼任保学校长”。(56) 在争取教育与保甲地位平等的同时,以教育为本位的倾向十分明显。
其实上述这两种意见都各有所偏,而且还杂有政、教主管机关——内政部与教育部的权力之争。据做过县长和内政部科长的汪振国回忆,“有一次召集内政、教育两部讨论乡镇中心小学校长是专任好、还是兼任好,如果兼任则应由谁来兼这一问题”,教育部认为,“乡镇中心小学校长应以专任为原则,如果兼任,以校长兼乡镇长,不宜以乡镇长兼校长”;内政部也认为“中心小学校长以专任为好,如果兼任则应以乡镇长兼校长,实行政教合一”。两者虽各有所见,未可全非,“但实际上是内政、教育两部对于乡镇行政教育领导权之争”。由此可知,校长专任、政教分长,教育、内政两部均无大异,唯分歧的焦点在于校长兼任制中,究竟是以校长兼乡镇保长,还是以乡镇保长兼校长的领导权力之争。讨论结果,在《县各级组织纲要》中不作硬性规定,校长可以兼乡镇长,乡镇长也可以兼校长,由县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决定。(57) 明眼人一看即知是一种妥协。这就是《纲要》规定一人兼三长,但不明确规定由谁兼谁的缘由,从而造成政教两界人士在解释和运用这些条文内涵时,各取所需,出现本位分歧之结果。
教育界主张“一人三长”要以教育为主体;相反,政界坚持应以政治为中心。1940年6月,教育名家高践四十分肯定地说“新县制完全是教育的”(58)。这一观点为教育界争相转引,互为奥援。1941年10月,政治学博士、广西民政厅长邱昌谓强调,“一人三长”的三位一体制是“以政治为中心的一种行政体系,中国近四十年来,在教育方面,是以欧美教育为教育的思想,并且养成一种以教育为全能的观念,这是错误的”(59)。邱氏在强调政治中心作用的同时,其笔锋也不忘扫及教育万能论,政教两界不和由此可见一斑。
不仅如此,这种界域本位和分歧的言行,也反映在新县制实施过程中的主管和监督机关上。在管教养卫打成一片的精神下,教育部和各省都负有领导新县制之责,但在解释《县各级组织纲要》和制定本地和本部门的实施具体法规时,往往各存利益本位,“大有出入”。比如,在有实施新县制“模范省”之称的四川,1940年11月,威远县县长程厚之注意到,该省制定的法规有《县各级组织纲要与实施计划》、《乡镇公所组织规程》和《保长办公处组织规程》;而CC系控制的教育部制定的是《乡镇中心学校、保国民学校设施要则》等。程县长在列举、对照双方有关一人兼三长制的条文规定后,结果发现川省的法规,“总是以乡镇保长的身份为主体,而以校长为兼职”;相反,教育部“是以校长为主体,而以乡镇保长为兼职”。需要指出的是,教育部为CC首领陈立夫所掌控,四川省主席张群、秘书长李肇甫、民政厅长胡次威均属政学系。由此看来,行政部门的利益主体分歧的背后,也不乏派系竞逐的因素。程氏因此颇生感慨:“这个法规上的矛盾,因为立法机关的不同,固属难免,但是到县府拿来实施时,民政教育两科各有所本,便发生争辩,实有莫知所从之苦。”(60) 政教本位之争,一媳二婆之苦跃然纸上。同样,在上级多头监管新县制的各行政部门中,由于利益立场的不同,引起摩擦。1941年6月,研究新县制颇有心得的陈柏心指出,管教养卫各级行政分级掌理,中央有各部、会,省为各厅、处,各家职权和利益范围不同,“往往坚持本身的观点,固守自己的立场,对监督权的行使,发生无谓的摩擦。如教育厅主张以乡镇中心学校校长兼乡镇长,保国民学校校长兼保长;但民政厅则主张以乡镇长兼中心学校校长,保长兼国民学校校长,各以其本身职务为主体,各欲在人事方面取得较大的控制权或任用权。”(61) 可见,在新县制法规的制定、解释和实施过程中,无论在教育学与政治学两界,还是教育部与省政府、内政部,以及教育、内政两部管辖的教育厅、民政厅,在基层乡、镇、校长谁兼谁的问题上,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态度却截然不同,存在明显的界域本位、管理权之争,甚至派系角力,以致政教合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在校长兼任的争论中,如果前引高践四的说法,有教育系统本位之嫌,那么身为CC骨干分子、新县制设计的主持者之一李宗黄所强调的“现在新县制的实施,就是以教育为中心”的动机和用意又当如何解释?(62) 李氏鼓吹新县制以教育为中心,并非真正重视教育,而是与其背后深层的政治党派利益之争有关。国民党内部党派林立,主要有三大派,素有黄埔系主军、CC系主党、新政学系主政之说,各派时有倾轧。CC系以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为首,长期盘踞国民党党部和各级组织部门,特点是排他性极强。陈立夫由组织部调长教育部后,组织部长由与二陈分道扬镳的朱家骅接任。丢失了组织部这一老据点后,CC派势力不仅随之大规模渗入教育领域,而且更加积极进行活动和扩张,不容他人染指。新政学系主要代表有黄郛、杨永泰、张群、熊式辉、蒋作宾、吴鼎昌、黄绍竑等,多为有能量的行政和技术官僚,虽没有组织和纲领,但志同道合,互相援引,如影随形。它与CC系既有历史积怨,又有现实利益矛盾,形同水火,长期恶斗。在新县制“政教合一”实施过程中,CC系主动出击,与以政学系为代表的行政界,在保甲与自治、党与政方面,进行明竞暗争,并逐渐占据上风。
保甲与自治何者为主的明争。1932年以来,国民党政府在地方上实行强调官治的保甲和主张民治的自治两种互相矛盾的制度,表面上好像在实验两种不同的地方制度,实际上是新政学系与CC派互相缠斗的一种反映。CC系首领之一的陈果夫,在该系势力范围江苏江宁、浙江兰溪“办自治不办保甲”,试验地方自治实验县,欲待经验成熟后推向全国。这与以杨永泰和张群为首的新政学系,在江西、湖北、河南、福建等省一律“停止自治,改为保甲”,使全国地方行政归入该派囊中的野心,发生尖锐的冲突,并在1935年12月第一次“全国最高行政会议”上达到高潮,双方剑拔弩张,互不相让。为打破僵局,最后由内政部长蒋作宾提出了一项“寓保甲于自治之中”折衷方案,大家均觉得有颜面,且得到行政院长蒋介石的认可。“寓保甲于自治”这一办法为后来的新县制打下了根基。(63) 又因为教育一向被目为地方自治的基础,而“南昌行营”在新政学系首脑杨永泰、张群的策划下,为解决政教系统脱节的问题,提出在省进行合署办公,在县设置实验县,废局设科——将原来的民政、财政、教育、建设、社会等各局缩小为各科,甚至有将教育与建设合为一科者。平心而论,应该说这有助于集中权责,节约经费,提高行政的效率,但对分工逐渐发达、日益复杂的教育,则是一大挤压。当时教育界上下纷纷谋求抵制,掀起一场旷日持久的要求恢复教育局的运动。教育界名流、CC分子杨亮公以“难以应付复杂之教育事业”、“人选不易”、“轻视教育”、“教育经费无保障”等理由进行反驳,并断言县教育局终归要恢复。(64) 但在当时于事无补。
随着保甲和自治成为新县制的基本内容,两派的矛盾也随之转移。实验县中废局设科的做法为新县制所继承,教育仍旧受到挤压。在三位一体制中,乡镇村、保长分别兼中心校、国民学校校长,在人事上有“宾主之分”,在工作中必然有畸轻畸重之别。(65) 这种重行政而轻教育的规定,在当时被视为事关国民教育成败的关键,自然为握有教育界的CC派难以容忍。于是,双方矛盾再度爆发和公开。占据教育界的CC骨干分子群起而攻之。1940年3月,程时煃对“一人三长”的规定,主张慎重试办,强调兼任校长者必须具备师范毕业生资格条件,“否则仍以不兼为是”。(66) 态度十分明确。陈立夫则亲自上阵,公开指责一人三长制“试行以来,由于职责不专,及乡镇保甲长流品不齐,弊多利少……校长务须专任,以免影响基本教育之发展,必要时或以其分别兼任副乡(镇)长或副保长,以符合政教合一之精神。”(67) 旁人的记载则说,陈氏“特别反对乡保长兼校长的制度”,曾扬言:“如果争不下来,就可不必办。”没有任何商量余地。(68) 要重视教育,除人事权上争取外,从根本上说还是要恢复教育局的组织建制。为此,教育部国民教育司再三力争;又依靠私人关系,借助国民参政会开会之机,通过了“调整地方教育行政机构加强地方教育行政应恢复县教育局”的决议,经行政院转饬教育部核办。此后,县教育局才逐渐得以恢复。(69) 这说明杨亮公预言的准确,也反证了废局设科对教育的失误。自治以教育为基础,保甲是行政的要项,以新县制为界,之前的自治与保甲之争,演变为教育与行政的冲突。这固然是政治统制与现代教育分工的冲突在行政制度上的一种客观反映,但无疑也打上了CC系与包括新政学系在内的行政系统方面的利益争斗的烙印。
党、政、教关系的紧张和暗斗。这涉及新县制推行中不公开于《县各级组织纲要》中,但更值得关注的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以及国民党内部党政关系如何处理的重大“秘密”问题。因而当事人之一的胡次威在一次纪念周上说,新县制第一个精神就是“实现县以下的各级党政关系彻底打成一片。至于怎样的打成一片,因为这是本党新的决策,有暂守秘密的必要,恕我不能向诸位公开报告。”(70) 正因为这一“秘密”,该问题很少引起新县制研究者的重视或讳莫如深。即使到了新县制结束后的1946年,参与其事的陈之迈,对这一“秘密”在惋惜未能深论的同时,也只是闪烁其辞地透露,党通过党员人事布控、“以党透政”方式、加强对政府工作的监督与联系的大体思路。(71) 1991年,忻平注意的也主要是党政关系处理的分工合作等原则性的问题。(72) 直到2003年,王奇生才从国民党组织形态的新角度,出彩地揭示了县党政联合的情形和成效不佳的许多具体秘密。(73) 这里还可以进一步补揭另外一些重要的“秘密”:
首先,这时正处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时期,党政关系,除国民党内部党政关系外,更多的是指外部对中共的防范和反制;特别是为将来抗战胜利后实施宪政时,拟与中共展开选举战而争取主动的一种深谋远虑。1940年6月16日,唐纵对“中统”负责人陈立夫所拟防共对策,认为过于消极,特地增加了“省县以下各级党部,均应改用秘密方式,深入群众,领导人民,从事于地方自治,督促政府,完成新县制”一项,且为蒋介石采纳。(74) 回忆资料也佐证了这一点:“为了在战时取得维护国民党在中央与地方的优势,限制其它党派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势力的渗透,有必要对县政制度作一次改革。县是政权的基本单位,是直接掌握群众、控制选举的场所。能控制各县,就能控制各省,能控制各省,就能控制中央,因此对县制县政的改革必须在抗战胜利、宪政开始以前完成。”(75) 因此,这一秘密,如果仅仅理解为国民党防止中共的短期渗透,而没有注意到其以“县为政治据点”(76),在抗战后争取政治选战主动的未雨绸缪长远政略,是不全面的。在皖南事变善后政治攻防过程中,国民党坚持要求中共敌后抗日政权“须照新县制设置和组织”。(77) 因此,新县制成为国共两党当前和长远利益争夺的重要阵地和环节。
其次,国民党内部党政紧张关系,以政教之争的间接形式反映出来。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抗战期间,CC系势力大量从组织部转到了教育部,党与教紧密结合,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造成了党即教的态势。原组织部长陈立夫起初调任没有实权的国防最高委员会下辖的三个政治部副部长之一,后才转任教育部长。虽说CC系丢掉经营多年的老巢组织部,但却将在该部编织起来的势力转移到教育部,以图固守和扩张。这是CC系由党界大规模挤入、侵占行政界的重要一步,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1938年2月8日,深知内幕的王子壮在日记中云:陈立夫“转陈蒋(介石)先生一电,大意为党部同志一律可使其参加教育工作,是证明蒋之所以任立夫为教育部长其原意实在此……目前接近民众之工作实最所需要也,而立夫一向对于民众工作,实所隔阂,于此时期乃不能不使其别有所发展。”(78) 可证陈立夫出掌教育部乃出其主动,意在借机抢占新地盘,安置部下。1943年8月21日,在国民党内部态度相对中立的王子壮,又在日记中批评陈立夫粉饰办理国民教育的成绩,为了安排亲信张廷休做校长,增设没有必要的贵州大学(贵州已有办理未善的大夏大学):“外人以为党的力量普遍教界,殊不知教育界正复弥漫着封建势力……言念及此,衷心怫然。”(79) 说明这一时期,CC派大量涌入教育界,内党势外教育,党与教两股势力结合甚至重合;并以此为势力范围,结党营私,不仅主张如前所述的国民学校校长专任,而且力争以校长兼任乡(镇)、村(街)长,插手教育以外的基层行政,引起有识之士的不满,自然也不为新政学系等其他利益相关的行政力量所容。
再次,CC系与政学系在新一轮的党与政竞逐中占据上风。CC系与政学系争斗由来已久,互有胜负。在1930年代前中期的湖北、江西等省的剧烈较量中,政学系赢得胜利。(80) 但在十年后的交锋中,因CC系得蒋介石的支持,结果迥异。这可从基层和上层两方面来看。在基层,这是全面抗战前政学系“融党于政军”与CC系“融政于党”争斗的一种余绪。前者是指政学系首脑杨永泰强以蒋介石的名义,结纳黄埔系,将豫、皖、鄂、赣省市国民党组织变更,省、市党部设主任委员,由该地军政大员兼任;主任委员之下,设多由其亲信担任的省、市、县书记长,以取代原来由CC系把持的上述三个级别的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后者是指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为抵制政学系的进攻,多方“设法把他们认为CC的骨干打进行政部门和教育部门。同时他们暗中发动喽罗们掀起所谓护党运动,实际就是护CC集团运动。”CC系处心积虑夺取民政和教育两部门,原因在于民政部门既可安置每年由陈氏兄弟掌握的中央政治学校毕业生,又可和省、市、县、区各级党部配合起来;教育部门既可和党部中的宣传、训练、特务工作呼应,复可扩大本派力量。但此举“受到政学系的抵抗”。(81) 新县制推行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调整党政之间的紧张关系。蒋介石规定国民党党政关系处理的原则为,在中央“党高于政”,以党统政(因蒋是国民党总裁);在省“党政平行”,加强联系;在县“融党于政”,党政融化。根据“CC即党,党即CC”以及国民党“在全国性的政治派系中,只有政学系主要以政界为依托”的说法(82),新县制时期的党政融化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此前CC系以党为主体的“融政于党”和政学系以政为主体的“融党于政”争斗的一种平衡和调和。蒋介石所规定的“融党于政”与政学系所说的名同而实异,并且根据县以下党政关系“应注重使党员尽量参加下层工作,从工作中发生领导作用”等秘密规定(83),其倾向于重党。也就是说,此举有利于CC系而不利于政学系。加以政学系没有组织依托,在基层根基不牢,在地方竞争中难敌CC系。
在上层,蒋介石当上国民党总裁后,为巩固自己的权位,采取重党轻政、弱省强县的政策,支持CC派打压政学系。蒋在性格上为“最实际之军事政治家”(84);在用人方面,有为“防止他某个部下的系统发展得太快太大,形成尾大不掉之势,经常扶甲抑乙,提丙压丁”的一贯作风(85)。这时为提高党的地位和领导力,如同他做行政院长时重用政学系一样,在1942年底极力擢拔CC党人。张厉生为行政院秘书长、张道藩任宣传部长、曾养甫当铁道部长、程天放作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李宗黄则“因其研究新县制”而升任内政部次长。所以,知情人以为,此为蒋介石“重用党人之表现,尤以(陈)果夫先生之部下为最得计也”(86)。相反,当张群发动各省省主席向蒋介石提出“确定省与县之地位”议案,要求“增进省政府之地位,一切由省府民财建教各厅负责,在中央不必直接在各省设立机关,县亦确定其地位,勿使担负事物太多”时,却未得到支持。张的提议一方面固然有与孔祥熙为首的中央行政争权之意,另一方面则试图削弱新县制的权势,但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占多数的CC系反对下,张群这一议案以及其他系列提议“均告失败”。对此,王子壮评道:“果夫先生方面以会场多敢言之士,尽力批评,颇获成功,总裁亦采纳若干。”(87) 通过自治与保甲、党与政关系的明争暗斗可知,这时的CC系党人,由于有蒋介石的重用和支持做后盾,积极抢占,上下结合,在与新政学系争斗过程中处于上风,从而也使新县制政教冲突披上党派角力的色彩。
1935年3月,雷沛鸿鉴于中国近代以来普及教育失败原因之一,是教育没有其社会基础,以及照搬西方教育制度,主张重估中国社会发展的水平。他认为,中国与西方分工发达的产业社会相比,仍处于“农业社会、乡村社会、宗法社会”。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经济不发展、社会分工不发达的前现代化社会。在这种社会基础上产生的教育制度,其设施“要综合,要简单,要有效,并且使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打成一片。”(88) 次年8月,曾参观过广西教育并对此赞赏有加的河南洛阳乡村建设负责者陈大白认为,中国“还是滞留于自给社会,甚难有经济政治教育军事之划分”;假使教育与政治、经济、军事分了家,教育本身就会分别缺少了推进的原动力、丧失了建设的立足点和严密的组织力,其实效也因此不能显现。所以,“政治,教育,经济,军事,四者应该由联络而合一”。(89) 从中国社会结构和分工不发达的国情,寻找“三位一体”存在的社会基础与合理性,较之于单纯地从政治统制或经济落后上寻找其原因,自当更为深刻。这显然受雷氏的启发并有所发挥。
试图将在西方分工发达的工业化社会基础上产生的教育,简单嫁接在以农业为主、分工不发达的中国社会土壤上,这是近代中国域外与本土教育长期冲突的根本原因;也是制约新县制三位一体从“政教合长”到“政教分长”变化的一大关键。关于近代中国教育史上,外来与本土两种不同教育冲突的根本原因这一抽象、重要结论,今人鲜有对其进行深入的思考,并清楚地给出有说服力的答案。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少从社会分工和社会结构方面进行的探究。到了1940年代末,曾与雷沛鸿共过事、思想深受其影响的教育名家董渭川,在批判和总结从前中国教育失败原因时,说过一段发人深思的话:西洋“课程之注重纵的系统,是有其意义的,并且是能综合应用到其分工的生活上的。而我们呢,不光是没有工业革命,而且变成了列强的半殖民地,民族工业无由发展,大多数人还在经营着近乎原始的‘自耕而食,自足而衣’的农业和手工业;学了人家那许多东西,除掉换取身份地位以外,根本与生活无涉,更无从应用到生活上去。因为中国人的生活,还是一套又一套的综合性的横的单元。例如种田,是一人一家从耕种致收获整套包办下来的,从来无所谓分工。由此一个例,可见那些分析得专精的纵的系统根本无法综合到横的单元上去;况且是一套洋的材料呢……这问题,小而言之,是和一人一家的各种生活不相干;大而言之,是和国家社会的建设事业不相干。”(90) 所谓“纵的系统”是指西洋每一门课程,上下都单独自成一体,各自独立,彼此不发生关系,很符合分工发达的工业社会生活需要。“横的单元”说的是,中国以农业、手工业为主的社会生活,前后左右彼此关系密切,综合性和整体性都很强。因此,西洋教育引入中国后,“纵”“横”扞格,结果害人误国。
由此观之,外来教育欲中国化,根本上就是由分工的、纵的教育,向综合的、横的中国社会进行结构性调整、转型和适应。于是,一个悖论出现了,没有综合的社会基础,产生不了“三位一体”、“一人三长制”;而综合的社会基础,又满足不了原本来自域外,且分工日益发达的中国教育的要求。对此,有人直言不讳地指出:一人三长制“有背分工原则”(91)。这样,三位一体的“一人三长”合长制与校长专任制发生矛盾,以及从前者向后者转变,就成为必然。这有助于理解和阐释以下关于近代中国教育成效不佳原因的经典表述的深刻含义:“中国‘新教育’的迟迟不上轨道,以我们见到的,中西文化的冲突,找不到一个合适互让点,是其中最大的原因。”(92) 或者说,新县制中政教合长及其向政教分长的过渡,正是官方在吸收民间教育家们集体智慧的基础上,为中西教育乃至文化冲突寻找一个“合适互让点”的一次重要尝试。仅此而言,政教从合长到分长制问题的研究,其学术意义实已超出新县制范畴。
新县制基本精神为管教养卫合一,四者之间本应平衡发展,但在实际上则有所侧重,以管教为主;而且将党务、政治、教育、经济、军事等诸多相异的目的和要求,简单地糅合在一起实行,存在难以克服的麻烦和矛盾。这些矛盾自然又集中表现在政治与教育人事的纠葛和紧张上。二者关系经历了从“政教合长”到“政教分长”;从“政教分长”,再到“政教不分家”和“政教相连”的一波三折变化。其中隐含着综合与分工的社会客观矛盾和政教系统、部门各为本位,以及党派政治利益的主观冲突。教育要与政治结合,在理论上似不成问题,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两者之间性质本不相同,一属软性教化,一为硬性强制;一着眼目前,一关心将来,既互补又矛盾,加上权益本位的作用,遂大成问题。在新县制实施之前的1937年6月,舆论界就有这样的担忧:近代以来中国教育,因为脱离现实生活,“能不能”与政治结合,以及政治总处于主动、进攻的态势,“肯不肯”与教育合作。并不无先见之明地指出:“政教合作,就理论言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就事实言,才是极成问题的问题。”(93) 从而提醒人们:在理论上习以为常的事情,实际上可能存在异常复杂、多维的面相。这对妥善处理有时仍棘手的政治与教育之间动态的平衡关系,也有借鉴作用。
注释:
① 陈一:《政教合一之理论与实际》,《建国月刊》第13卷第6期,1935年12月10日,第2页。
② 有人对民间关于教与政关系由分离到结合的过程作过概括,首先是“教育生活化”和“学校社会化”;其次是“平民教育”、“社会教育”等;再次是“政教合一”。姜书阁:《新县制下的国民教育》,重庆,中国政治建设学会1940年印行,第8—9页。
③ 刘中南编:《新县制地方行政事业推进方法》,锦州,东北文化服务社1946年版,第5页。
④ 抗战时期新县制实施期间原定5年,后改3年,通常称为第一期,坊间一般所说的新县制主要是指这一阶段。基于此,本文主要研究这一时期新县制中的政教合一情况。有研究表明,从1946年到1949年间,新县制仍继续推行。见忻平《论新县制》,《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2期,第199—202页。
⑤ 1939年6月,蒋介石发表为新县制定调的《确定县各级组织问题》公开演讲,内分甲、乙、丙和说明四个部分。其中,甲为“县各级党政关系调整办法”,但有目无文,并注有“密”字,故在相当时期内,局外人对其基本精神明白,但具体的内容无从知晓。《新四川月刊》第1卷第7期,1939年11月30日,第4页。
⑥ 这方面代表性的成果有张俊显《新县制之研究》,台北,正中书局1988年版;魏光奇《官治与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12—255页。从社会控制角度研究新县制的最新成果有曹成建《地方自治与县政改革》(1920—1949),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⑦ 徐秀丽编:《中国近代乡村自治法规选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19、221页。
⑧ 胡次威:《半年来的川省民政》,《政教旬刊》第4期,1940年11月1日,第10页。
⑨ 常导直:《新县制下之地方教育行政问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中央周刊》影印版,第41册(第2卷第27期,1940年1月21日),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324页。
⑩ 亢真化:《广西乡村三位一体制之检讨》,《建设研究月刊》第2卷第1期,1939年9月15日,第22页。
(11) 黄旭初:《广西建设之理论与实施》,李宗仁等:《广西之建设》(合订本),桂林建设书店1939年版,第187页。
(12) 蒋介石:《确定县各级组织问题》,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中华学术院1984年编印,第1321页。
(13) 姜书阁:《新县制下的国民教育》,第11页。
(14) 刘试读:《新县制的研究》,《建设研究月刊》第5卷第1期,1941年3月15日,第61页。
(15) 姜书阁:《新县制下的国民教育》,第10页。
(16) 粟显运:《新县制的实施》,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1年版,第34—36页。
(17) 譬如说“一人三长”目的是“一方面利用政治的力量统制教育思想,另一方面利用教育和宣传来麻痹民众意识”。顾树森:《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反共教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50页。
(18) 李鸿音:《对新县制实施之意见》(二),《行政评论月刊·新县制特辑》第2卷第1期,1941年1月,第5页。
(19) 姜书阁:《新县制中“政教合一”之理论》,《政治建设月刊》第2卷第3期,1940年3月1日,第38页。
(20) 陈一:《在新县制实施中所感到的九大问题及其解决之道》,《行政评论月刊》第2卷第1期,1941年1月,第2页。
(21) 顾树森:《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反共教育》,《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151页。
(22) 胡昭华:《新县制概论》,重庆,商务印书馆1942年版,第173页。
(23) 罗廷光:《今后之国民教育》,《教育通讯周刊》第3卷第23期,1940年6月15日,第3页。
(24) 雷宾南(沛鸿):《广西省三位一体制度运用问题》,《教育通讯周刊》第3卷第45期,1940年11月23日,第11—12、16页。
(25) 李鸿音:《对新县制实施之意见》(二),《行政评论月刊》第2卷第1期,1941年1月,第5页。
(26) 社论:《新县制实施诸问题》,1940年2月30日重庆《中央日报》,第2版。
(27) 赵海金:《新县制的研究》,《中央周刊》影印版,第41册(第2卷第35期,1940年3月28日),第460页。
(28) 张鸿钧:《对新县制实施之意见》,《行政评论月刊》第1卷第4期,1940年6月,第30页。
(29) 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第200页。
(30) 在1930年代的实验县改制时,将原来县政中财政、民政、公安等各局,降改为科,教育局取消,并入建设科,挤压教育,为文化教育界所反对。如傅斯年曾说,“教育,本是全省齐一的,而其行政性质又与普通民政不同,这一局是不便裁的”。《地方制度改革之感想》,1935年2月3日《大公报》,第2版。
(31) 江参议员恒源等二十三人提:《请政府明令规定凡中心学校国民学校校长应尽量改为专任以重教育而符新县制之精神案》,《国民教育指导月刊》(湖南)第1卷第6期,1941年12月31日,第78—79页。
(32) 《国内教育重要消息·国民教育大会决议案摘录》,《广西教育研究月刊》第3卷第2期,1942年2月25日,第82页。
(33) 徐秀丽编:《中国近代乡村自治法规选编》,第235—236、239—240页。
(34) 张英:《本省目前实施国民教育应有之认识及努力》,《国民教育指导月刊》(贵州)第2卷第1期,1943年1月,第11页。
(35) 《中华儿童教育社在第九届年会宣言》,《良师月刊》第1卷第2期,第1—2页。该刊附在《国民教育指导月刊》(福建)第2卷第1期中发行,1942年7月31日。
(36) 沈朋主编:《县实际问题研究》,正中书局1943年版,第22页。
(37) 朱浤源:《从变乱到军省——广西的初期现代化,1860—1937》,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年版;曹天忠:《教育与社会改造——雷沛鸿与近代广西教育及社会》,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30—235页;张伟:《民团、学校与公所:1930年代新桂系对广西乡村社会的控制》,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79—92页。
(38) 梁上燕:《论三位一体制的演进与政教分长》,《建设研究月刊》第6卷第3期,1941年11月15日,第63页。
(39) 罗善屏:《当前国民教育之严重问题及其解决方法》,《国民教育指导月刊》(广西)第2卷第10期,1943年12月15日,第38页。
(40) 梁上燕:《论三位一体制的演进与政教分长》,《建设研究月刊》第6卷第3期,1941年11月15日,第65、67页。
(41) 卢显能:《县教育行政的根本问题》,《广西教育研究月刊》第3卷第2期,1942年2月25日,第18页。
(42) 李相勗:《国民教育制度中的三位一体制问题》,《教育通讯周刊》第4卷第10期,1941年3月15日,第2、5页。
(43) 朱智贤:《政富教合一之途径与设施》,《山东民众教育月刊》第6卷第6期,1935年8月25日,第26页。
(44) 罗廷光:《今后之国民教育》,《教育通讯周刊》第3卷第23期,1940年6月15日,第3页。
(45) 雷沛鸿:《三位一体制的运用问题》,韦善美、马清和主编:《雷沛鸿文集》(续编),广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89、94页。
(46) 张平洲:《四位一体与推行合作》,《现代读物月刊》第5卷第5期,1940年5月,第19页。
(47) 雷沛鸿:《三位一体制的运用问题》,《雷沛鸿文集》(续编),第94页。
(48) 何与仁记录:《校长专任后与政教联系问题》,《教育与文化月刊》第2卷第7期,1941年4月15日,第8—9页。
(49) 粱上燕:《论三位一体制的演进与政教分长》,《建设研究月刊》第6卷第3期,1941年11月15日,第68—69页。
(50) 黄旭初:《各级行政人员在工作上应如何联系》,《建设研究月刊》第6卷第4期,1941年12月15日,第125页。
(51) 沈朋主编:《县实际问题研究》,第25页。
(52) 余森文:《三年来的新县制》,《中央周刊》影印版,第46册(第5卷第39期,1943年5月13日),第247—248页。
(53) 杨君劢:《对于县各级组织纲要应有之认识》,《政治建设月刊》第1卷第6期,1939年12月1日,第14页;胡次威:《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的“新县制”》,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总第129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01页。
(54) 新县制其实并不“新”,只不过是“集我国推行地方自治经验之大成”。陈之迈:《中国政府》第3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96页。
(55) 汪振国:《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地方政府》,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12册,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547页。
(56) 由少蕴:《“保教合一”的商讨》,《抗建三日刊》第27期,1939年9月16日,第1页。
(57) 汪振国:《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地方政府》,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12册,第548页。
(58) 高践四:《教育和新县制关系的分析》,《教育通讯周刊》第3卷第22期,1940年6月8日,第8页。
(59) 邱昌谓:《广西县政》,桂林文化供应社1941年印行,第281页。
(60) 程厚之:《乡镇保长兼校长纷争之平议》上,《政教旬刊》第5期,1940年11月11日,第9—10页。
(61) 陈柏心:《新县制实施的检讨》,《建设研究月刊》第5卷第4期,1941年6月15日,第10—11页。
(62) 李宗黄:《新县制与教育》,《教育通讯周刊》第3卷第13期,1940年4月6日,第9页。
(63) 胡次威:《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的“新县制”》,《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总第129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98、200页。
(64) 杨亮公:《论裁局归科》,《政问周刊》第38号,1936年9月16日,第5—6页。
(65) 董渭川:《发挥国民教育功能之先决问题》,《教育通讯周刊》第3卷第18期,1940年5月11日,第4页。
(66) 程时煃:《新县制推行下之教育问题》,《教育通讯周刊》第3卷第15期,1940年4月25日,第2页。
(67) 陈立夫:《九中全会对于教育的指示》,《中央周刊》影印版,第44册(第4卷第22、23期合刊,1942年1月15日),第188页。
(68) 梁尚彝:《乡镇保长兼理校长问题之商榷》,《国民教育指导月刊》(湖南)第l卷第6期,1941年12月31日,第34页。
(69) 顾树森:《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反共教育》,《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151页。
(70) 胡次威:《一个新的政治方案——确立县各级组织问题》,《新四川月刊》第1卷第7期,1939年11月30日,第29页。
(71) 陈之迈:《中国政府》第3册,第104页。
(72) 忻平:《论新县制》,《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2期,第191页。
(73)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289—292页。
(74) 《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第134页。
(75) 汪振国:《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地方政府》,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12册,第547页。
(76) 楼桐孙:《县各级组织纲要释论》,1939年9月30日重庆《中央日报》,第3版。
(77) 杨奎松:《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45页。
(78) 《王子壮日记》(手稿本)第4册(1937—1938年),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编印,第398页。
(79) 《王子壮日记》第8册(1943年),第328页。
(80) 孙彩霞:《新旧政学系》,华夏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第222—225页。
(81) 刘不同:《国民党的魔影——“CC”团》,《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4年版,第249—250、239页。
(82)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第216页。
(83) 《县各级党政关系调整办法》,《新县制参考资料》,第2页,编辑、出版单位和出版年月不详,南宁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藏。
(84) 《王子壮日记》第4册(1937—1938年),第540页。
(85) 此为蒋介石的心腹康泽所语,见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政治》第3卷,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3页。
(86) 《王子壮日记》第7册(1941—1942年),第554页。
(87) 《王子壮日记》第7册(1941—1942年),第548、551页。
(88) 雷沛鸿:《国民基础教育的产生》,韦善美、马清和主编:《雷沛鸿文集》下册,广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34页。
(89) 陈大白:《新兴民众学校运动之动向》,《民间半月刊》第3卷第8期,1936年8月25日,第2页。
(90) 董渭川:《旧教育批判》,中华书局1949年版,第23—24页。
(91) 沈忱农:《论县各级组织纲要》,《中央周刊》影印版,第41册(第2卷第35期,1940年3月28日),第457页。
(92) 廖泰初:《动变中的中国农村教育:山东省汶上县教育研究》,1936年12月著者自印,第2页。
(93) 阮雁鸣:《政教如何合作》,1937年5月17日天津《大公报》,第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