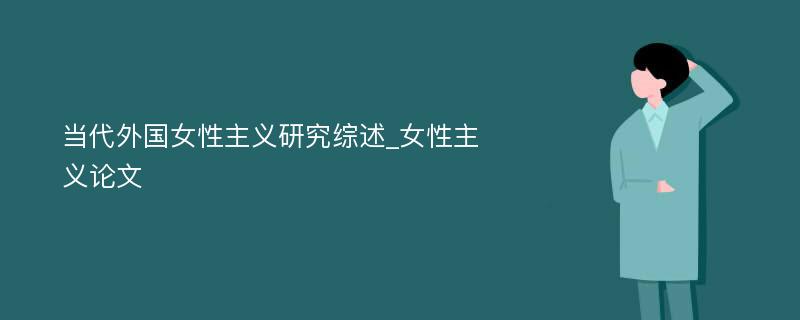
当代国外女性学概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性学论文,当代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旨在争取男女平等的妇女运动已有200多年的历史, 正是这一运动造就了女性学。女性学与妇女运动实践紧密结合,为改变妇女社会地位提供了理论武器。它经历了由表及里、由浅入深、从边缘到主流、从西方到全球、从政治到经济到社会到文化的多元化发展的进程,从白人中上层人士到有色人种妇女的各阶层参与的变化。从语言用词上的变化亦可见一斑:早年称之为女权主义(feminism ), 而后称为女性主义(womanism)〔1〕,80年代末又以社会性别(Genoler)研究对学术界进行冲击,进而提出超性别模式的新观点。女性学的各种流派的形成、发展大致也体现了这些变化。本文试就这些变化作一概述。
历史回顾
世界妇女运动发展可分三个时期。第一阶段是从18世纪妇女运动的兴起到二战结束,主要争取妇女的外在权益。其间英国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于1792年出版了《女权拥护论》,强调妇女应拥有个人权利。19世纪中叶美国妇女运动如火如荼,诞生了三八国际妇女节。
第二阶段为二战后至本世纪70年代初。在追寻“女子为何不如男”及如何改变妇女“二等公民”地位的探索中,法国著名女作家西蒙·波娃的《第二性》喊出了“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环境的产物”的口号,主张女人要与男人一样承担社会责任,成为社会的人来实现妇女的解放。1963年美国女记者、作家贝蒂·弗里丹发表《女性的奥秘》,更是道出了妇女的心声——走出家庭,在社会和事业中寻找真正的自我价值。
第三阶段是70年代至今。由于科技进步,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妇女进入社会,在各行各业担当起越来越重要的责任。女性学研究也由此进入了一个全新发展的阶段。这20年来它经历了填补(清除学科中男性为主的偏见,把妇女包括进来,填补知识的空缺)——分离(创立新的理论)——更新观念(对长达2000年的父系文化圈重新整理),女性学逐步走上正规化、科学化、系统化的道路,从边缘地位向主流地位上升。经过女性学界几代人的努力,女性学以其跨国界的研究计划,深入的文化内容使该学科成为一门综合的多元的动态性的学科。特别是90年代以来女性学研究出色的学术成果,使学术界的态度以尊敬取代了抑制。西方已出现了一些学生们象钻研文学、经济学之类那样去专修女性学,很多男士也参加到女性学的教学研究中来(当然有的是认为从事女性学研究可以很快在学术界取得成就)。
研究机构
一个学科的成熟的标志之一,是研究领域的机构化。1960年在美国建立了第一个女性学研究中心——瑞克利夫研究所(RadeliffeInsfifufe)〔2〕,到80年代早期这类中心发展到50多个。这些研究机构依托于政府机构、大学和妇女组织,经费来源多样,研究也各具特色。美国协调和支持女性学研究的全国组织是成立于1982年的“妇女研究全国委员会”(NCRW )和成立于 1977 年的“全国妇女研究协会”(NWSA)〔3〕。
在欧洲,根据欧共体妇女研究数据库(GRACE)的不完全统计, 到1988年已有332个中心进入该数据库〔4〕。北欧妇女在就业、参政等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妇女研究得到政府的支持。如挪威社科人文研究委员会(NAVA)和芬兰议会中男女平等委员会均设立国家协调人的职位,他们的职责是建立网络、负责出版、组织讨论会,以各种途径支持妇女研究。北欧国与国之间合作也很有成效,已成立了“北欧论坛”,旨在交流信息和推动北欧研究基金组织对妇女研究给予更多的支持。女性研究在荷兰已成为卓有成效的全方位的学术活动。1976年格罗宁根大学设置第一个女性学教授职位,到如今,各大学中已有13个教授职位。所有的大学都有女性研究项目,女性研究并得到国家的支持。法国女性主义者由于其排拒集体性和不与政府为伍的原则,导致研究机构化滞后于理论建设。1982年法国召开了首届女性研究会议, 而后在全国建立了5个分会;1983年法国科学院设立了“关于妇女和女性主义的研究项目”;1984年才在法国大学中设立了女性研究的职位。在德国,直到1992年才成立女性研究机构联邦联合会,宗旨是开创大学内外女性主义研究者合作的机会。但德国所有大学均有女性学的教学与研究活动,1983年建立“女性学研究跨学科研究小组”(IFF); 民间有“女性主义跨学科研究所”(FIF)。
80年代后亚洲各国也掀起了妇女研究热潮,日本、韩国、印度等国都有从事女性学研究的组织和机构。联合国妇女十年的活动从1975年起召开了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对女性学研究起了很大作用。1980年“妇女研究国际网络”(Women's Studies In ternational)〔4〕在哥本哈根第二届世妇会非政府论坛上产生,旨在加强各国妇女的联系,提供服务,促进研究,并致力于促进有利于妇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女性学的主要流派
一、自由主义女性学(Liberal Feminism)
女性学首先探索的是妇女受压迫的起源。其理论认为两性不平等的关系经历了三个段:首先从生理差异向社会差异转变,然后因社会差异产生了一系列价值关系,由此引出了不平等观念。这种不平等即男性所承担的社会分工被认为是更重要的,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得到了回报,而女性所承担的社会分工被认为是次要的、附属的,往往是没有相应回报的。其斗争目标就是进入男性世界,争取平等权利。这是经典女性主义又称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代表作除了上述西蒙·波娃的《第二性》、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外,还有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的《自己的房间》和《三个畿尼亚》,(美)凯特·米丽特1970年发表的《性政治学》〔5〕等。
二、第三世界女性主义(Third Worlod Feminism)
不同的阶级阶层、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国家的妇女的利益是不同的,价值观也不尽相同。80年代产生了由第三世界和发达国家中(主要是美国)的有色人种妇女及赞成这一观点学者构成的第三世界女性主义。他们批判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狭隘性,反对将白人文化强加于人。他们认为,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以及第三世界中不平等的权力结构是妇女受压迫和歧视的根源。妇女的地位是双重边缘地位。美国的彻丽·墨拉哥和格拉瑞·安萨尔杜阿主编并于1981年发表的《我的背是座桥》,是该流派的第一部专著。 美国黑人女性主义者贝尔·胡克斯1984年出版了《女性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 可视为该流派的经典。他们提出的妇女解放的目标在于致力于使妇女摆脱各种类型的压迫,并为各国妇女提供联合团结的基础。他们提出各个民族的妇女要根据自己特定的文化及社会经济条件来制定自己的首要战略和目标。争取男女平等的斗争是与反对种族主义、经济压迫的斗争紧紧相连的。美国黑人女作家艾丽斯·沃尔克在1983年提出抛弃女权主义一词代之为女性主义(womanism),其女性主义的定义是:“献身于实现所有人民的,包括男人和女人的生存和完美的主义”。
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学者对一些传统的理论进行了批评,如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批评。对于第三世界的人口控制与社会发展问题,一般认为只要广泛使用避孕知识和技术,控制妇女生育就能解决贫困问题,把妇女当成单纯的控制人口增长的机器,导致损害妇女身心健康和取消妇女自主生育权的恶果,使控制人口的项目成效甚少。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还对西方中心思潮的“现代化理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认为这是西方中心的偏见,忽视了当代第三世界国家是在世界不平等经济结构及秩序下求发展的事实;这种“现代化”对妇女的冲击,使妇女的社会地位并不象预想的那样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提高,而是下降了。这一批判迎来了“妇女与发展”(Women And Development)新学科的确立, 主张把社会性别分析运用到发展计划的制定与实施中去。
三、马克思主义女性学(Marxist Feminism)
这一流派不完全是指引经据典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关于妇女问题的观点,而泛指持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结构影响女性的理论学派,其中甚至包括了对马克思,特别是对恩格斯妇女思想的批判。
该学派认为压迫妇女是私有制的直接后果,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解放妇女。因此妇女运动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妇女的利益与工人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在阶级社会中,妇女除受到阶级压迫外,在家庭中还受到男人的压迫,由于养生送死的持家工作未纳入社会生产领域,造成了妇女的卑微处境。1971年英国的朱丽叶·米切尔发表《妇女等级》一书,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妇女状况。1975年美国的戈尔·卢宾出版了《交换女人》一书,提出“性别制度”说,从人类发展和个人发展的初级阶段中寻找女性受压迫的渊源。美国律师凯瑟琳·麦金农主张在女性主义原则基础上建立国家法律体系,1989年发表专著《建立女性主义的国家理论》。经过以其为代表的女性主义者积极奋斗,使美国联邦法和各州法作了修订,把婚内强行性行为定为强奸罪。美国女性主义者还首次提出“性骚扰”一词,并努力通过建立法规对施行性骚扰者予以制裁。
四、激进派女性主义(Radical Femimism)
该派最著名的著作有:舒勒密斯·费尔斯通的《第二年笔记:激进女权主义重要著作》,罗宾·摩根主编的《姐妹情谊就是力量》,维维安·戈尼克和芭芭拉·莫兰主编的《性别歧视社会中的妇女》,安·凯德特等主编的《激进女权主义》,凯西·萨拉查尔德的《女权主义革命》〔6〕等。与自由派女权主义者不同的是, 激进派女性主义者不仅谋求国家在法律上承认妇女之权利,而且力图在一切领域、一切社会体制中改变男女间的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包括家庭、婚姻、性生活。她们的著作矛头指向父权制,批判男性对女性在生育能力上的控制及在意识形态上对女性的压迫。他们对广大妇女进行教育,“提高觉悟”,使之从蒙昧状态中走出来,并采取各种行动攻击性别歧视的社会制度。她们的组织绝对排斥男性,行动有时甚为戏剧性的过激,如命令《花花公子》杂志男代理人当众脱衣以体验模特儿处境之类。
该派争取妇女对自身主权的活动有两个方面:一是把妇女从不情愿的生育活动中解放出来;二是反对男性暴力行为和黄色作品。她们在美国各地成立了强奸危机中心和收容所来帮助受害妇女,至今仍使受妇女同胞们受惠。
五、社会主义女性主义(Socialist Feminism)
这是70年代中叶发展起来的女性主义思潮。该学派认为,尽管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但性别歧视仍可能继续存在,因此除了改变经济基础外,还必须借助文化活动来发展女性意识;妇女不仅参与社会生产,还应担负更具权威,更加光彩的有实权的职务;强调国家政策的改变应有利于改善最底层妇女的生活,应该给干家务劳动的个人支付工资,提高家庭妇女地位。此外他们强调“主观因素”在革命变革中的重要性,否定传统马克思主义所持有的经济决定论。1979年美国的第一部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文集《资本主义父权制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状况》出版,编者齐拉·爱森斯坦申言他们超越了单一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和孤立的激进女性主义理论,反对把个人发展作为妇女运动的最终目标,而是要解放整个社会。
六、后现代派女性主义(Postmodernist Feminism)
女性主义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受到80年代、90年代西方后现代主义各种思想的浸淫,包括福柯的后结构主义、拉肯的心理分析、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以及各种新马克思主义等。后现代派女性主义否定“男性”和“女性”的观念,认为两性平等观是一种误解,是男权思维逻辑的延续,不能从本质上认识女性受压迫的问题。丹尼斯·赖利的《我叫那个名字吗?女性主义和“女人”的范畴》就代表了这一论点。朱迪思·巴特勒的《性别麻烦》(1990)认为性别角色及特征是靠表现决定的,服装、举止都是表现的道具,社会又将此固定成性别模式。因此要打破男权制度最为有效的方法是“男女混装”,因为当人们不能确定自己的社会性别时,性别差异乃至性压迫就有可能消失。唐娜·哈拉威的《赛勃克宣言,20世纪80年代的科学、技术以及社会主义女性主义》(1990),把改造历史男权社会的希望寄托在人类与科技结合的产物“赛勃克”(一个殉职的优秀警察的大脑植入机械人体后形成的高于人类与机械的机器人)身上。也就在这一年,苏珊·博尔多的《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及性别怀疑主义》和南希·哈特萨克的《福柯论权力,为女人服务的理论?》对构造论的极端理论提出了异议,认为不应脱离了历史苛求前人,不应忽视女性受岐视的社会现实,不应瓦解自己,而应进一步加强社会性别论的研究,制定更有效的斗争策略。对构造论批评最烈的是坦尼亚·莫迪莱斯基,她认为解构“女人”观念就是颠覆女性主义政治(《没有女人的女人主义》1991)。还有相当多的人持中间观点。英国不者克里斯·威顿的《女性主义实践与后结构主义理论》(1987)认为,各种观点相差甚远,但 是有共同之处。女性主义是对现存文化权力结构明显不平衡状态的反抗。我们所处的朝代已经意识到人的局限性、理论的局限性,承认并接受差异更有利于女性解放。
三位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海伦娜·西索、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和露西·依利加芮均在美国思想界有广泛影响。她们对女性的身体、欲望、情感进行探索,歌颂女性和女性文化,70年代中叶创立了“女性写作”(L' Eeriture Feminine)理论。依利加芮在1985年发表《另一个女人的窥镜》一书,对弗罗伊德的《论女性特征》(1933)中男性性征崇拜理论进行质疑,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男权文化的产物是无法准确、合理再现妇女心理的。
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反本质主义立场超脱了以往一切争论,开启了一个理解性别问题的新天地。他们认为每个男性个体与每个女性个体都千差万别,千姿百态。因此,我们既不要男尊女卑也不要女尊男卑对立的二元结构,而要建立一个两性特质的多元的,包含一系列间色的色谱体系。
由于分类的立场、视角不同,女性主义中还有诸如文化女性主义、心理分析女性主义、存在主义女性主义、女性主义人类学、同性恋女性主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女性主义美学、女性主义民族志研究、生态女性主义等等,本文从略。
结束语
近年来的女性学已从妇女运动的理论武器发展到正在进入主流文化中的一门学科,是由于它突破了由男性或根据男性经验来阐释人类文明的知识框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来研究自然、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女性学的研究成果纠正和补充了学术界以往将片面有限的经验夸大人类的普遍经验而造成的谬误、偏颇和疏漏。在创造一个东西方平衡、物质与精神生活平衡、男女平衡的21世纪新世界中,女性学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注释:
①苏红军:《第三世界妇女与女性主义政治》,见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价》第21页,三联书店1995版。
②③④闵冬潮:《妇女研究在美国、西欧的历史、现状与发展》,见《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价》。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77页、196、212页。
⑤文摘(沪)1995年第6期第11页。
⑥王政:《女性的崛起》,当代中国出版社1955版,第132页。
上海社会科学院改革与开放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