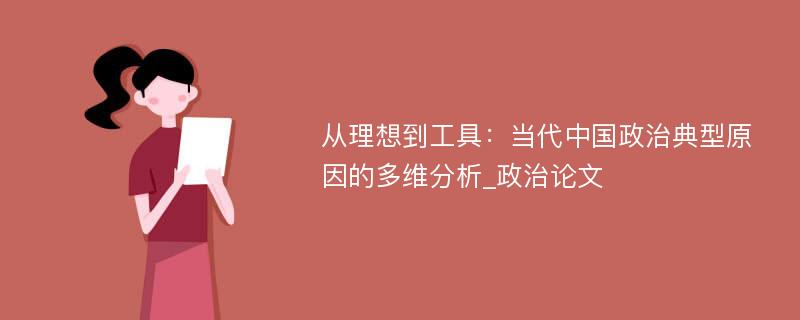
从理想性到工具性:当代中国政治典型产生原因的多维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维论文,当代中国论文,典型论文,理想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文艺学和哲学等学科对典型理论意兴阑珊的时候,重提典型似乎相当不合时宜,有炒冷饭之嫌。不过这里要研究的是政治典型,因为目前关于政治典型的学术研究是很不够的,而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又显著地存在着浓厚的“典型情结”。关注当代中国政治生活的人轻易即可发现,每隔一段时期,各类主流媒体总会推出某一先进典型的连篇累牍的宣传报道,并借助层层下发的红头文件在机关学校等单位掀起学习典型的运动。这些典型由于得到官方媒体和文件的认可,具有政治属性,是名副其实的政治典型。如果自共产党执政算起,从具有全国影响的国家级典型到仅具地方影响的基层典型,可谓不计其数。政治典型在中国是如此的司空见惯,以致成为建构公共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和镶嵌在政治景观中的连续不断的亮点,进而衍化为中国共产党治理国家与社会的得心应手的工具,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我们知道,建国前曾树立过白求恩、张思德等无数典型,据此可以认为,树典型、学典型是中国共产党治理国家和社会的一项有生命力的传统,而“一切有生命力的传统都是一种现实的力量,任何创新活动都无法抛弃或割断传统,即令创造历史的人们在主观上多么希望彻底地摆脱历史传统的纠缠”①。
所以,当我们今天希望进一步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对既往的政治传统进行反思。树立典型的政治传统当是我们反思的对象之一。本文姑且先探察政治典型产生的原因。从革命遗产和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的角度能够部分解释典型产生的原因②,或许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占据中国艺术主流地位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弘扬的典型理论对政治典型的产生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下拟从政治典型产生之理想性维度及工具性维度来解读政治典型产生的原因。
一、传统文化为政治典型的产生提供了有力的背景支持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辉煌灿烂。虽然清末以来,中国文化的主流对于传统文化基本抱持一种拒斥的态度,1949年后更是欲对传统文化给予彻底的颠覆,但传统文化仍为政治典型的产生提供了有力的背景支持。这种支持既包括可资借鉴的理想层次,也包括可直接使用的工具手段。首先,中国传统时代在追求成仁成圣的道德理想主义的支配下,就有通过树典型进行社会教化的传统,以使社会进化为人皆圣贤的个人之集合,即所谓大同社会。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是儒家学说,其施政理想是德治,要求统治者“为政以德”,特别强调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明君的楷模作用,希望统治者通过施仁政,成为天下人的学习榜样,获得“其身正,不令而行”的施政效果。而对于普通百姓,统治者在“政教合一”的传统下为了实现道德教化,维持封建统治,就通过树立各种类型的道德典型来推行德政。各种史籍和各地方志中就记载了数不胜数的“孝子”、“节妇”和“烈女”等道德典型,而且在传统社会受到了统治者的大力宣扬。典型在此既是实现封建政治统治的工具,也是封建统治者梦寐以求的理想社会状态。可见树典型在中国具有深厚的历史传统,使得国人养成了接纳典型的习惯。即使二十世纪以来,儒家文化的整体结构遭到了全面的破坏,但人人高尚的社会才是合理的传统思维仍主导着整个社会的价值追求,共产主义成为中国人的奋斗目标。因而,新社会政治典型的产生既有来自传统社会的参照启发,也有来自新社会的坚实基础。此外,中国自传统社会以来一脉相承的权威主义的政治文化传统也使得具有权威特征的典型在新社会仍有生命力。由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强调从群体本位到国家本位,个人在社会和国家中无从获得主体性地位,不可避免形成依附性人格,只得本能认同外部规定,当然也就难以对典型进行实质性的怀疑与批判。而权威主义的政治文化传统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必以其历史惯性攫取一定的生存空间,甚或可以说政治典型就是这种权威主义的一种体现。政治典型作为意识形态的象征物,由政党和政府确认而不能自封,因而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以树典型和学典型为中心的政治运动在以其权威性扫荡旧的权威主义文化的同时,又很自然地将政治典型升级为新的社会政治符号,不但容不得说三道四,而且其运作逻辑还或多或少带有强制性。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中突出存在的类比思维方式与树典型的思维方式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是政治典型产生的直接智力支持。中国古代哲学家在认识人类世界的过程中不像西方哲学家喜欢运用演绎推理的原则,而更习惯于用类比的方法,从已知达到未知,逐渐获得关于对象世界的总体性认识。因而,总的来说,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偏重于形象思维和类比思维,如高晨阳所说,“一方面,它通过形象性的概念与符号去理解对象世界的抽象意义;另一方面,它又通过带有直观性的类比推理形式去把握和认识对象世界的联系。感性、形象之中具理性、抽象,理性、抽象之中又夹杂着感性、形象,二者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相互凝融,保持着有机的统一,这是中国传统哲学所特有的一种把握和理解事物的思维方式。”③孔子就曾要而不繁地指出:“能取近譬,可谓仁之方也。”所谓“取譬”就是通过举出具体事例来说明抽象且不太容易理解的事物,使所要说明的事物形象可感,以便人们理解,在孔子看来这甚至“可推导出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把握宇宙人生之道。”④中国古代哲学家的著作中运用类比方法说明事理可谓比比皆是,以致汉代大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精华》中概括说:“得一端而多连之,见一众而博贯之,则天下尽矣。”这也如同我们常说的由此及彼、触类旁通的思维方法,虽难免牵强附会的缺点。显然,典型作为类的代表的认识论作用与中国人所习用的类比思维传统非常契合,同类则易于比较,也易于学习模仿。按照塔尔德在《模仿的定律》中的说法,“社会存在,实质上都是模仿……社会上的一切东西,不是发明就是模仿”⑤。而且合乎逻辑的是,模仿式的学典型能造成类似格式化的趋同效果,这种“尚同”似又宜于集体主义意识的生成,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则是多多益善了。
二、马克思主义为政治典型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前提
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在两个方面对政治典型的产生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首先,从功能指向上说,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根本指导思想,作为一元化意识形态的生存逻辑与典型本义所指示的功能具有一致性。典型的希腊文为Tupos,原义是铸造用的模具,并派生出英文单词type。但Tupos的衍生义“典型”、“模范”、“规范”、“模式”等已上升为主要意义。在古汉语里,典型也有相同的内涵,“……《说文解字》:‘典,五帝之书也’,‘型,铸器之法也’。段玉裁注:‘以木为之曰模,以竹曰范,以土曰型,引申之为典型。’”⑥典型作为“模子”之原义,很显然意味着一个模子只能铸造出无数同样的东西。但“典型”这一术语最终进入政治实践领域,与其所具有的“规范”、“代表”和“理想”等特有内涵是密不可分的。政治就必然意味着统治、管理、治理、规训和教化,也必然包含着政治家的政治理想,在这一点上与工匠打造出完美器具可以说是一致的。实际上,在对词源的追溯中,我们就会隐然感觉到“典型”概念的原义所寓有的这种普遍力量。所以,树立政治典型不再是“铸器之法”,而是示范引领社会。政治典型的产生过程就是政治家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外在化、客体化的过程。在现代汉语中,典型的核心涵义是“代表性”⑦,也就是作为典型个体的“一”代表无数的“多”。一元化意识形态的生存逻辑必然希望这世上无数的“多”能归于“一”,就像一个模子铸造出来的东西,不再是杂乱无章,而是整齐划一,多元归于一统,以致消除差异纷争,从而社会也就安宁易控。以典型为风向标,万众一心沿着同一方向前进,是一元化意识形态希望构建的社会图景。在这个意义上,一元化的意识形态和典型的原义遵循着相同的运作机理,而政治典型又是一元化意识形态的模范响应者和积极行动者,所以,欲实现对社会之一元化整合而树立典型,将一元化的理念落实到一元化的物质载体“典型”上,则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其次,从内在逻辑来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典型理论促成了政治典型的产生。虽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的典型理论主要是关于艺术创作的,但由于他们作为社会哲学家的本色,决定了他们的最终追求还是要落实到政治实践层面,所以,他们对文学典型的主要评价标准是看其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他们的理论立足点不在于一般文学理论的研究,而是从特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出发,按照时代的政治要求对文艺作品提出批评,具有鲜明的阶级和政治指向。当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成为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时,典型理论就逐渐转化为一种促成政治行动的知识论述,参与推动历史的进步,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典型理论就如前苏联时期一样明确要求艺术领域能够创作出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主体和神圣内涵的“新人”典型,并“为政治服务”,以演绎时代精神并体现巨大的历史潮流。但从改造世界的角度来看,直接反映社会本质和规律的现实政治典型无疑较之间接反映现实生活的艺术典型具有更大的冲击力和说服力,既有助于建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更有助于发挥精神激励和思想引导的示范效应,以实现动员、控制和整合社会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艺术典型和现实典型有时是纠缠不清的,艺术典型是现实政治典型的观念预演和行动纲领,而现实政治典型则是艺术典型政治诉求的世俗呼应与积极践行。如果说艺术典型是以特殊形象形态存在的、具有审美认识功能的艺术中介,那么政治典型就是以鲜活形象存在、具有社会认识功能的政治中介。艺术典型与政治典型的内涵的联结和同构既模糊了二者的话语边界,也模糊了二者的功能边界。因此,新的艺术典型的创造也同时预示着新政治典型的创生。
三、理想主义精神为政治典型的产生提供了内在精神动力
在历史上人们一般把乌托邦理解为与“科学”相对立的不切实际的“空想”,是并不存在的好地方,此种乌托邦的政治追求在现实世界应该遭到拒斥。但是,人存在的自然性和超自然性的二重化结构决定了人之为人必然具有乌托邦精神。乌托邦精神是对当下现实生活的关怀,使人们意识到现实的有限性和局限性,“就是立足于当下可感境界又超越当下现存状况的对真善美价值理想的不懈追求精神。它的重大使命……在于克服人的自然惰性和对现实事实的消极默认,为人和社会走向新境界提供新的可能性。”⑧乌托邦精神在批判性和超越性的意义上与树立典型是具有共同指向的。树立典型也显然是政党和政府不满足于社会的既定现实或当下给定的存在状态,欲以之改造社会,造就新人。依据“取法乎上,得乎其中”之理,如果不学习追求先进,我们得到的只有落后。而如果一个社会中不只存在着若干被树立的典型,且通过学典型把典型的要素播种到社会的每个个体身上,以致达到“人皆为尧舜”的理想境界,那么,这样的社会与古人所描绘的大同世界应该是没有什么区别了,与共产主义的距离恐怕也不过半步之遥。回顾政治典型的传播史,我们当然知道,典型的示范性再强、学典型的力度再大,也不可能使学习者都转化为典型,但至少令学习者知道努力的方向,因而有同化为典型的可能性。典型政治的逻辑寓于此则是不言自明的。所以,典型政治的运作过程中也多少体现了乌托邦精神——这种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一种精神状态,激励人们战胜惰性并打破对现实的消极默认以超越现实世界,实现“对现实的批判”,并在批判现实中追求未来。
乌托邦精神实质上也就是一种理想主义精神。中国作为外生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极其落后,在此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需要理想的事业。没有对理想的渴望来克服落后现实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描述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差距给人们带来的沮丧感,就难以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就缺少发展的动力,可能如莫里斯·迈斯纳所说,“历史的动力(而且的确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动力),不是乌托邦的实现,而是对它的奋力追求。正如韦伯曾经指出的:‘人们必须一再为不可能的东西而奋斗,否则他就不可能得到可能的东西了。’”⑨所以我们特别强调理想教育,因为理想既超越已有的人类文明,也超越人本身,促进人类发展和个体进步。“理想是目标,也是向导。因此,现实和理想虽有很大差距,但我们知道,除非有一个崇高的理想树立在它的面前,现实是不会有长足进步的”⑩。理想教育需要典型这样的物质载体,以通过真实可感的先进典型展示理想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典型既是现实的,也是未来的,是展示未来理想图景的现实存在,能起到连接理想与现实的桥梁作用,并能以之克服理想和现实的距离及其所表现出的当下的不可能性。典型的卓越性还能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能教育那些对实现社会主义之可能性将信将疑的人,令其以更大信心面对现实,面向未来。因而,通过典型的宣传动员能够满足人们对理想主义精神的期待,激发满足社会和精神的种种需要的共鸣,唤起群众的极大热情,从而引导社会整体以激情燃烧的状态投身具有理想主义性质的社会实践,促成一个处于潜在状态的美好世界的出现。
四、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需要政治典型的“在场”
典型的“在场”有助于社会主义思想的社会化。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和私有制社会根本不同,典型的政治象征功能有助于具有超越性追求的社会主义政治价值和道德理想的社会化,为社会主义的政治合法性提供论证和辩护,因为“一个政权并不是通过暴力和强制,而是通过它型塑我们的世界观的能力来维持自身的”(11)。可1949年前,中国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主要是源于传统的封建思想和来自西方的资产阶级思想。社会主义思想虽然声势渐壮,但共产党的地下身份使得社会主义思想不能得到名正言顺的宣传以获得统治地位。而传统的封建思想历史悠久,又长于家庭政治社会化方式,资产阶级思想则倡导自由主义的政治社会化方式。传统封建家庭的教育内容往往与社会主义理想教育格格不入,同时,自由主义的多元追求也与有特定追求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社会化方式相冲突。因而1949年前,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和政治社会化方式显然都不适合社会主义的需要。
最主要的是,在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匮乏的情况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能从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旧社会机体中自动生长出来,只能是基于建构主义逻辑而建立,借助革命从社会的外部强行楔入社会肌体。而革命又往往必然导致由于制度上的颠覆所带来的政治文化上的断裂,因此,新的社会主义政治秩序和政治结构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既陌生也不太容易理解和接受的新鲜事物。因而,虽然通过艰苦卓绝的革命取得政权,勉强跳跃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但在物质资料的极大丰富这一基本条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使得新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为大多数中国人理解、接受和认同,将这陌生而又先进的理论和宏伟的理想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实现,是共产党人亟待解决的问题。可以说,我们要在私有制的社会机体上建立要求公而忘私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和道德要求,尤其在社会生产力极为落后且不能摆脱具有私有制特性的家庭束缚时,更是一种艰难的政治和道德实践。因而在建国初,社会主义的框架已经搭就的时候,打磨适合需要的“砖瓦”成为了当务之急,所以特别强调“关键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之类话语。
可如果仅是对社会主义思想进行理论宣传则既枯燥又抽象,亦难以理解。而典型的“在场”则至少在形式上实现了把社会主义的抽象思想转换成形象可感的“物”的存在,并落实到具体可视的“点”上。这种可视性更符合大多数人的知识水平和认知习惯,切合中国人“见贤思齐”的传统,而且沃拉斯也说,“认识往往附属于所认识事物的某些特征(无论是天然发生的,还是人为制造的)”(12)。所以,可以理解,“点”并不是随便圈定的,而是经过精心选择才得以产生并最终上升为典型,以近乎完美的形象成为意识形态的表征。如果再经过精心建构的魅力型话语的夸张渲染,就可以使得“典型在观看者那里不再是模糊的图景,而是清晰的展现;不再仅仅牵动某种神秘的情愫,而且既为个人指明了如何把这种情愫与切己的修炼结合起来的法门,也给各个具体单位勾画了把政党伦理贯彻在日常治理实践中的要点。”(13)说得简单一点,树典型就是把典型建构成包含一系列生动感人故事的意识形态实例,而用实例进行统治甚至在西方也有此不自觉的传统。曼斯菲尔德在为马基雅维里的《论李维》写的导言中就提到,“教会哲学用实例说话,正像政治中的统治者要用实例而不仅仅是用法律进行统治一样”(14)。当我们动员大多数群众学习典型时,就是希望借助典型这样的实例能产生“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效果,既能克服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国人文化素质不高的局限性,又能实现以先进带后进,教育和动员人民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把追求美好生活的潜在动力上升为推动行动产生的现实动力,努力把多数政治冷漠的群众从听众和旁观者变成行动者和参与者。甚至,群众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产生了问题,也能通过对先进经验的参观学习,“到实地一看就解决了”(15)。不止于此,典型的普遍存在还充分昭示,无论是超凡脱俗的道德实践,还是宏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目标,都能够通过努力达到,不是高不可攀的。
五、“鲶鱼效应”是政治典型大量产生的工具性原因
建国后,我们的政治理想决定了我们只能建立一元化的意识形态。一元化的意识形态虽易于社会控制,但也易致社会僵化。尤其是改革开放前,学习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典型建立起一元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并辅以高度统一的意识形态及经过过滤的舆论表达,就社会整体而言,在改革前各种表面喧嚣的政治运动背后迹近万马齐喑。高度一元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由于单薄而孱弱,由于高度集中而僵化,只有通过不断强调阶级斗争的政治压力来获得人们的服从、遵守、忠诚和执行。文革中流行过一句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就特别明确地宣示了这一点。因此,没有给人们留出多少独立思考的空间。况且,独立思考动辄得咎,因而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大行其道,社会日趋僵化,缺乏生机和活力,经济效率低下,这又是领导人所不愿见到的,需要某种“鲶鱼”来激活日益僵化的社会。
而这样的“鲶鱼”本来就存在。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和地理大国,实际情况是,即使在一元化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下,必然由于地理历史因素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以及由于自我图式的不同界定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自然难免所谓先进与落后之分,社会不可能由于一元化追求而完全同质。树立典型的本意是要消灭差异,达致统一,但换个角度来看却是凸显这种差异的政治切割术,展示出一种试图打破一潭死水式的均衡僵局的努力,并建构起国家主导与掌控的从落后到先进的不同经济、政治和道德等发展系列,目的是要以这种人为制造的差异来激活管理僵化缺乏活力的一体化社会。虽然很多典型与非典型之间的差距只是国家动用各种经济、政治和文化资源进行差异性支持的结果,但体现了政治偏好的先进典型在政治权威的支持下被推至社会之巅,甚至由于舆论宣传的不断升级而超凡脱俗,直至成为圣物,散发出克里斯玛式的摄人光芒,升格为社会行为的榜样甚至标准,从而明确具体地对社会行为产生指向和调节作用,“使行为沿着既定目标发展,从而完成某种任务,达到预定目的”(16),并能产生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的“合力作用”。
另一方面,毋庸讳言,典型政治在其表面的耀眼光环之下无疑充斥着利益的考量。成为典型能使典型及其相关者都成为利益的获得者,不但可以获得社会声誉,还可以获得物质奖励,甚至个人的升官晋爵,显然形成了对于典型较为张扬的正向激励功能。换个角度来看,也似对非典型施加了一种潜在的负向惩罚功能。因此,成为典型的过程中必然充满竞争。这种竞争也许不是树立典型的初衷,但却是价值极大的副产品,因而被大力提倡。在竞争情境下,竞争的参与者“都有争取达到有限目标的强烈愿望和动机,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压力,促使人们你追我赶,争取好的工作成绩”(17)。由于典型是由国家树立,体现了国家的价值准则和目标追求,甚至可以说其即为意识形态的物化形式,学习典型成为典型所产生的竞争,其显性效果是营造了一种大张旗鼓实现国家政治经济目标的态势,而隐性效果则是施加了无处不在的规训,对参与者的言语和行为产生约束力,并导致了迎合意识形态需要的竞争。而且,人们学习典型的行动能出乎意料地带来态度的转变,能使那些对社会主义将信将疑的人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因为有时候“行为决定态度……社会心理学理论中大多数的研究都为这个结论奠定了基础,”(18)从而巧妙地增强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合法性。
从以上五个方面的简略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无论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中,还是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确实广泛存在着对于完美典型的理想性期待和借助典型示范社会的工具性利用,这种理想性期待本是出于对更加真善生活的追求,但亦似为当代中国政治实践中产生大量典型营造了能被普遍认同的社会心理氛围。只是,当我们利用人们的这种理想性期待,过于急迫地把典型用作意识形态建设和经济建设等的政治工具,并赋予典型过多的功能,以致典型产生的工具性色彩遮蔽了理想性光辉的时候,促使典型产生的理想性追求与工具性利用必然构成典型产生的悖论。这种难以调和的矛盾更会激发人们对典型的反思,必然打破笼罩在典型身上的耀眼光环,从而弱化政治典型所承载的理想目标的吸引力,还会因此消解政治典型存在的必要性。这确实是当前许多政治典型处境尴尬的内在原因。
注释:
①曹锦清、陈中亚:《走出理想城堡》,海天出版社1997年版,第81页。
②冯仕政:《典型:一个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学海》2003年第3期。
③④高晨阳:《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203页。
⑤E·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6页。
⑥李衍柱:《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概述》,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352~353页。
⑦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7月修订第3版,第280页。
⑧贺来:《乌托邦精神:人与哲学的根本精神》,《学术月刊》1997年第9期。
⑨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⑩乔·奥·赫茨勒:《乌托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66~267页。
(11)艾尔东·莫里斯,卡洛尔·麦克拉吉·缪勒主编:《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6页。
(12)沃拉斯:《政治中的人性》,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0页。
(13)魏沂:《中国新德治论析》,《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2期。
(14)哈维·曼斯菲尔德:《导言》,尼科洛·马基雅维里:《论李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页。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一九五六年一月——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9页。
(16)(17)赵中天编著:《社会心理学》,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第150、155页。
(18)戴维·迈尔斯:《社会心理学》,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年版,第102页。
标签:政治论文; 理想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