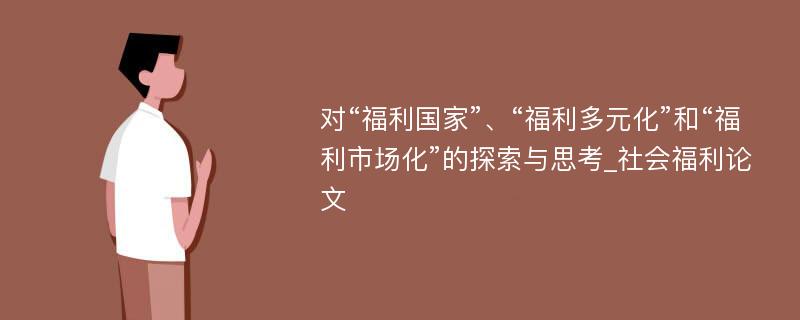
“福利国”、“福利多元主义”和“福利市场化”探索与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福利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的目的是重新探索(revisit )一些近代社会福利理念以及福利发展道路的选择和背景,从而以历史的视角反思当今我们面对的困扰和可能走进的误区。
首先让我们回顾历史。传统的社会福利方式是什么?背后的理念为何?在人类社会未进入工业化和现代化之前,传统的福利工作就是家庭、社区、教会、行会和慈善团体为其成员在日常生活上给予的照顾和遭逢危困时提出的特殊帮助,政府绝少对其子民提供直接的生活补助。在华人社会,家族、乡里的互济功能尤其显著。一个公认的说法是:传统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就是家庭福利制度。政府对老百姓的救援只在大规模灾荒及饥馑的情况下发挥作用。
工业化和现代化改变了上述的状态。由于个人和传统组织承受风险和解决困难的能力日渐减弱,以社会力量共同筹组的支援工程变得重要和迫切,制度性的社会福利设施得以确立。特别是在二次大战之后,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都各自对其福利制度进行了拓展和完善,巩固了以政府力量为主导的公共社会服务系统。
在西方,政府为国民提供基本生活需要(basic needs guarantees)和负上生存风险最终保证的做法称为“福利国”模式(welfare state model)。 这是相对于早期强调个人与市场为满足生活需要的主要渠道、慈善团体作为补充来源、政府只作低度介入的“剩余福利模式”(residual welfare model)而言的。 “福利国”亦有人称为“制度型福利”(institutional welfare model)(Titmuss,1974)。理念假设是,大部分的社会问题, 包括生活困难的产生, 都是由社会结构变型和异化所导致,单凭私人、民间社团和志愿组织的能力无法妥善解决,需要政府的高度承担和投入,以其权力、威信、动员能量、资源,解决有关的困难和满足社会需要。具体的做法是政府把大量公众资源用于社会建设,为国民提供高水平和全民性的服务,以集体干预调整市场分配不公,抗衡因市场运作失调(market failure)而产生的社会矛盾。后果是公平、有效和人人受惠的社会福利制度发挥了作为资本主义市场制度纠正和补充的作用,使后者变得更人性化和更具合法性,避免了资本主义跨台的危机。可以说是用怀柔手段巩固与强化了资本主义,使其在与社会主义阵营的竞赛中取得优势。
在同一时间,社会主义国家推行了比西方福利国家更彻底的社会革命。社会主义相信人人平等、按需分配、公财共享和社会公平。由于推崇公有制,取消了市场,实行计划经济,以党和国家的力量规管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在民生方面,实行了保证就业、福利与工作制度相结合、国家与集体提供文化教育设施和生活资料平均供应等手段,造成一个史无前例由国家集体包揽人民需要的局面。这种福利制度给予人民很大的安全感,分配方面亦比市场经济更为公平。虽然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使用“福利国家”来形容他们的福利制度,实际上,他们走的全民福利型模式更为彻底。
Mishra 把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福利模式定名为“结构性福利”(structural welfare model)(Mishra,1981)。特点是把福利制度溶合在社会基本结构之中,由国家保障人民全部的需要,体现最大程度的公平、提供最高水平的服务。不过,在实践经验中发现,要落实这种理想的制度很不容易。
70年代石油危机引发世界经济发展放缓,西方社会亦发现“福利国”的制度不如期望中的完美,政府对国民作出生活承诺的代价不轻。针对“福利国”制度的批评此起彼落,出现所谓“福利国”危机这个说法(Mishra,1984;Offe,1984)。综合各方面的意见,“福利国”的弊端可以归纳为几方面(King,1975;Brittan,1977;Offe,1984):
(1)政府办的服务素质欠佳,效率低落,太官僚化;
(2)国民习惯依赖福利金和政府服务,工作意欲弱化, 自力更生精神从而受损;
(3)削弱了家庭和社区的责任;
(4)政客、压力团体和官僚为了讨好选民, 不断扩张福利和作出不切实际的承诺,终于做造成政府功能超负荷;
(5)政府负担过重,触发财务危机,公营部门规模过大, 浪费社会资源,不利经济发展,亦减低了竞争能力。
值得补充的是“福利国”危机背后的因素。工业社会进入后现代时期,社会、人口、经济、政治环境起了重要变化,包括人口老化、离婚率上升、家庭核心化、失业问题严重、经济竞争激烈、政府威信下降等等,过度慷慨的福利制度恐怕难以持续。普遍提出的问题是:社会福利究竟是谁的责任?公办福利是否唯一的选择?什么类型的福利制度最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当然,基于大家的信念不同,每个社会的文化、环境、条件和政治情况不一样,所得出来的结论也不尽相同。主流的看法是福利不一定要由国家包揽,民间社会也应该参与,福利产品的供应可以来自四方面:国家、家庭、商营部门和志愿机构,而且来源是越多越好。这种模式学术界概括为“福利多元主义”(welfare pluralism), 亦称为混合福利经济(mixed economy of welfare)( Rose , 1986 ;Johnson,1987,1999)。在肯定福利多元论的同时, 大家亦重新发现一个事实:民间社会,尤其是家庭与社区,从来都是提供个人福祉的主体,而且他们的角色是不能被其他部门,比如政府服务,完全替代。至此,大家发现以前迷信“福利国”、相信政府万能,实在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上述的教训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一种由国家“包”的福利制度,必然造成所有人极度依赖国家,国家集体的负担变得越来越重,在经济不发达、物质短缺的大前提下,极其量只能提供低层次的生存条件。而且,公有制的生产和分配方式较难调动人的积极性,结果是国民经济缺乏活力,发展落后,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无法提高。于是,大家都意识到政府不是万能,迷信全包型的保障制度实在是一个误区。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首先就要打破“大锅饭”和“铁饭碗”的制度,提出人民不要依赖国家集体,福利照顾不单只是政府份内的事,而是人人有责。做法是福利提供、融资、管理采用多层次和多渠道的方式,让社会大众齐来参与(张德江,1990)。我个人认为“社会福利社会化”和“福利多元化”的理念非常接近,两者都反对国家单独包揽福利,肯定政府与非政府部门的责任,主张采用多元化和多来源的方法来解决福利问题。
八十年代后期,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加快,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更白热化,很多国家都进行了公有部门的改革(public sector reform )(Gilbert and Gilbert,1989 ; Osborne
and Gaebler , 1992 ;Deacon and Walsh,1996)。方向是缩小政府的规模,节省公共预算,尤其是尽量控制社会开支,在公共部门的运作引入商业化的营运方法,提升前者的效率。上述的方向可以称为“市场化”(marketization)。“市场化”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内容是“私营化”或“私有化”。一种方式是把国有工业或公有事业的产权改变,如出售和拍卖,以后用商业原则经营。更普遍的做法是削减政府的角色,从直接提供、财务承担和业务监管的层面后撤( reduction
in
provision, funding andregulation)(Walker,1984)。踏进九十年代,市场化和私营化可以说已经演变成为一股大潮。冲击遍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国家,其中转型经济(transitional economies),包括前苏联、东欧,甚至中国承受的压力尤其显著。
自然,我们最关心的是在福利领域发生的事。很多国家的福利制度随着经济、人口、社会变化加剧,加上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冲击,分别采取了相应对策。
西方福利国家普遍采纳的应变措施有几方面:严格控制社会福利膨胀,把受助标准定得更严,援助水平冻结或封顶,撤销一些服务,鼓励供应机构竞争,把部分公营服务外判或交给民间社团甚至市场承办,广泛推行服务收费等等。当然,在发达国家之中会有做法与侧重点的差异。 比如在劳工和劳工福利问题方面, “社会民主型”国家(SocialDemocratic States )(如瑞典)倾向尽量保持高就业和在维持现有公共福利的基础上控制社会开支; “自由主义福利型”国家( LiberalCountries)(如英国、美国)采取了开放劳动市场、 降低工资和劳动成本以及福利市场化、私营化策略;“保守共责体系”国家(Conservative Corporatist Regimes )(如德国)选择的是容忍在夕阳行业中的高失业, 给予失业者经济补偿和加强再培训工作( Esping-Andersen,1996)。
在香港,我们的福利制度没有走“福利国”路线。在基本服务方面,政府提供了免费九年义务教育,象征式收费、全民性的公办医疗,和为百分之五十的市民提供了公屋(包括出租公房和优惠价房屋)。不过,在经济援助方面只提供一种比较吝啬的社会援助(综合社会保障援助)。在服务提供环节,政府相当依赖志愿机构,大概超过一半以上的服务都是由社会机构办理。需要补充的是,民间团体绝大部分都接受政府资助,政府拨款占他们收入之百分八十以上。从理论角度来看,香港的福利模式很难归类,既不属单纯的“剩余式”,亦不是“制度型”。较为适当的叫法应该是“混合模式”,因为参与的部门遍及全社会,政府、志愿机构、家庭、慈善社团和市场经营者都各司其职,互相配合。当中,政府扮演了政策制定、资源提供和服务监管的角色。同时,由于民间机构对政府资助的依赖越来越重,除了部分有独立经济来源的福利组织,大部分已经变为听命于政府的“非政府机构”( non- governmentor-ganization or NGO)。可以说,香港的社会福利基本是由政府主导。
近年,香港社会福利的发展方向亦渐渐朝向市场化、私营化。政府为了节省开支,开始把部分服务外判,鼓励成本回收或用者自付,对志愿机构的拨款方法变相削减。再者,因为担心综合社会援助金上升速度太快和市民养成依赖政府的习惯,把部分受助家庭(三口和四口家庭)的援助金额降低,要求有工作能力的人接受培训和做义务工作。在其他社会服务领域,市场化的做法也趋于明显。比如,公屋政策的基本原则是鼓励家庭置业,以至近年来出租公房的数量下降,最近,政府还计划把公屋管理私营化。此外,医疗融资也要进行改革,改变政府单方面负担的局面,措施包括要市民缴纳医疗储蓄金、购买医疗保险或增加医疗收费。在高等教育环节,考虑分科收费,有市场价值的学科政府可能减少补贴,修念这些课程的学生要付较高学费。
在内地,近年由职业单位提供的福利有缩减的现象。城镇社会保障已经放弃过去由单位独立承担的做法,变成由企业和工人一同供款。在社会福利和救济的范围,“社会化”或“私营化”的倾向亦十分明显。这种势头我在1994年已经指出。主要表征是国家办的服务增长放缓,九十年代初民政部门开办的服务已经被社会办或社区办的设施所超越(无论在单位数量、收容人口或服务支出方面)(Wong,1994、1998)。现在,私人或市场经营的社会服务已经冒出头来,在一些地区(如广州、上海)的发展更为蓬勃。在这种背景下,政府部门提出了要大力发展第三部门,即鼓励非盈利性、民办非企业单位多办社会服务(杨团,2000;熊跃根,2000),长远而言,甚至设想把服务推行的工作交给第三部门。此外,在医疗、教育和住房制度改革方面,同样倾向扩大收费空间,节省政府开支,以前内地居民享受的社会福利权利慢慢弱化,导致个人负担日重,很多人享受不到保障。展望将来,市场化和私营化的步伐可能比现在更快。
检视上述趋势,我有几点感受。第一,福利多元化发展到市场化和私营化的地步,已经纠正了以前盲目崇拜政府力量的弊端,走出一条符合实际和尊重社会价值观的发展道路。
第二,过分肯定市场能量,本身也是一种迷信,慢慢地,市场化变成泛市场主义,与以前迷信“福利国”同样是走进误区。
第三,政府、民间与理论界没有充分了解市场化和私营化的危险和代价。现在,越来越多人发现国家福利功能后撤往往造成非常严重的社会后果。比如,贫穷问题恶化,边缘群体的生存条件受到威胁;竞争失利者生活困苦,难免感到愤慨和失望,容易作出反社会行为,危及社会安定。
第四,政府没有认清本身的责任,为了尽快把负担放开,倾向把社会责任外移,对民间团体能力估计也过分乐观。
其实,民间社会,包括家庭、社区和社会团体,面对的压力很大,可是,他们承受风险的能力是有限的。一个具体的例子是就业,现代人失业的风险是越来越高,一旦丧失工作,家庭很快就会陷入困境。到现在为止,世界大部分的国家仍然找不到出路。同样,人口老龄化也是一个全球性的挑战,加上家庭功能弱化,现在人们需要的不是更少而是更多的社会支援。
最后,我相信现在是重新思考政府和公民社会的福利责任的时候,透过广泛的讨论和详细的论证,理清哪些是政府职能,什么属于个人家庭义务,哪些工作由市场和第三部门办理更有效益,只有这样做,才可以确保社会不同部门各司其职,协调合作,人的需要和尊严受到应有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