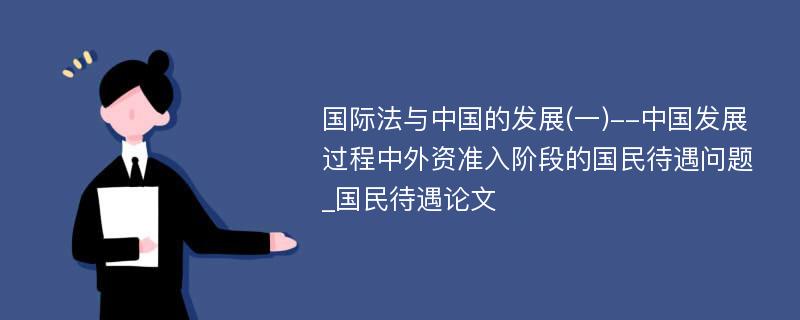
国际法与中国发展(上)——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外资准入阶段国民待遇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国际法论文,过程中论文,外资论文,国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最引人注目的动向之一,是区域性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的发展。例如,美国已与一些国家达成了FTA协议,其与南美洲国家进行的美洲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 of American,简称FTAA)的谈判也预期于2005年结束,届时美洲自由贸易区将成为包括34个国家在内、具有8亿人口的最大的自由贸易区。这些自由贸易协定,有的已经不限于区域性的了,而是一种跨地区的安排。(注:例如,美国与澳大利亚、摩洛哥、新加坡、约旦等国已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与南非关税同盟国家(包括博茨瓦纳、纳米比亚、莱索托、斯威士兰、南非)的FTA谈判正在进行。See http://www.ustr.gov/Trade-Agreements/section-Index.html)在亚洲,东南亚联盟近年来一方面加强区域内的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也在以FTA方式谋求与其他国家、包括中国、日本、韩国进行合作。
这种区域一体化或自由贸易区制度发展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其内容已不单是贸易自由化方面的安排,而是包括贸易、投资、服务、劳动、环境、竞争等诸多因素在内的综合性制度安排。其中,投资自由化是重要内容之一。
中国近年来也在与有关国家及东南亚联盟进行FTA谈判,因此也必然要应对国际上FTA所涉的问题。其中投资自由化是最令人瞩目的问题。投资自由化就是放松投资准入的限制,包括投资准入的领域和投资准入的条件方面的限制。实行投资自由化最关键的措施是在准入阶段实行开放,给予外国投资者以国民待遇。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在外资准入阶段实行国民待遇是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必须考虑到各种相关因素及潜在的影响,采取适当的政策和措施。本文拟就准入阶段国民待遇问题及中国的对策进行探讨。
一、国际上关于国民待遇的条约实践
在国际条约实践上,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对国民待遇采取了不同的规定。有些国家的投资条约无国民待遇的规定,以便保留其对国内企业或对外资提供优惠待遇的自由。不过,国际上大多数投资条约均规定了国民待遇,但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对国民待遇的适用范围采取了不同的规定。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研究,主要可分为准入后(post-establishment)国民待遇和准入前(preestablishment)国民待遇两大类。(注:See UNCTAD,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Flexibility for Development,pp.94-103,UNCTAD/ITE/IIT/18,UN,New York & Geneva,2000.Establishment是设立商业机构或场所的意思,是否允许设立就是外资准入问题,为便于理解,这里简单称之为准入前或准入后国民待遇。)
准入后国民待遇有两种类型:(1)有限的准入后国民待遇。即在准入后阶段给予外国投资者以国民待遇的同时,东道国保留着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例如,中日1988年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可以说是属于有限的准入后国民待遇,它将准入阶段排除在外,并在其议定书中规定,若因“公共秩序、国家安全或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所必需,可以采取差别待遇。(2)全面的准入后国民待遇。这种做法包括以下某些特点:仅适用于准入后待遇;对国家经济至为重要的特定产业或幼稚产业予以例外保护;实体标准采用“类似情况”和“不低于”这样的表述;没有地方政府措施的例外;适用法律上和事实上的国民待遇;国民待遇条款与其他待遇条款并存。近些年由德国、英国、法国、瑞士等国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大都采取这种类型。
准入前国民待遇是在全面的准入后国民待遇的基础上再加上准入前的国民待遇。它也有两种形式:
1.有限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即将国民待遇扩及到准入后和准入前阶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东道国关于外资准入的自由裁量权,但是东道国对于自由化的程度和步伐以及准入的条件仍保留着某种程度的控制权。在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研究看来,这种方式对那些希望以渐进的方式对外资准入实行自由化的国家比较适合。其具体做法是:(1)使用WTO《服务贸易总协定》第16条采用的“选择准入”(opt-in)、“由下至上”(bottom up)、“肯定式清单”(positive list)方法。除非经东道国特别同意,其产业和活动在准入前阶段不适用国民待遇。(2)使用“尽最大努力”(best endeavours)这样的表述,就像APEC无拘束力的《投资原则》所使用的一样。(注:该《投资原则》关于国民待遇的规定是:除国内法律、规章和政策规定的例外以外,成员国在关于投资的设立、扩大、经营以及保护方面,将给予外国投资者不低于国内投资者在类似情况下所获得的待遇。转引自UNCTAD,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Flexibility for Development,p.101,UNCTAD/ITE/IIT/18,UN,New York & Geneva,2000.)这样,发展中国家在法律上就不受准入阶段给予国民待遇的约束。这种方法可以为发展中国家在向准入前国民待遇的过渡阶段使用。
2.全面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即除通过“否定式清单”(negative list)方式来保护某些产业及活动外,在准入阶段给予国民待遇的承诺原则上扩及所有的外国投资者。这种方法缩小了东道国的自由裁量权,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东道国控制外资准入的传统的权利。
例如,2002年日本与韩国间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第2条第1款规定:在投资的设立、获得、扩大、经营、管理、维持、使用、享有、出售及其他处分等方面,每一缔约方在其境内须给予缔约另一方投资者及其投资以不低于其本国投资者及其投资在类似情况下所享有的待遇。
同时,日韩协定既列出不适用于国民待遇的行业以及相关措施的清单(否定式清单),又对不同的例外产业规定了“停止”(Stand-Still)和“回转”(Roll-Back)机制,以将产业高度自由化与国家发展政策相结合。(注:See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Japan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for the Liberalisation,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Investment,Article 2,4,5,Annex Ⅰ,and Annex Ⅱ.)
(1)例外产业或措施。根据日韩协定的规定,例外清单有两类,附录一列举的产业例外清单主要涉及国防、国家安全、公用事业、政府垄断、国有企业等关系重要产业。附录二列举的产业例外清单主要是应受保护的一些产业,包括农、林、牧、渔业、资源产业(石油、采矿业)以及某些服务业(如运输业、电讯业、金融服务等)。
(2)“停止”和“回转”机制。日韩协定对附录一和附录二的产业采取不同的措施。对于附录一清单中所列的产业,缔约国可以采取或维持与国民待遇原则不一致的措施,没有必须“停止”(或维持现状)或“回转”方面的要求。对于附录二清单所列产业,缔约国可以维持协定生效之日已存在的例外措施,同时还附有“停止”和“回转”方面的限制。所谓“停止”机制是指将现有的缔约各方的不符合投资协定的措施锁定,禁止制定新的或者限制性更强的不符合双边投资协定规定的国民待遇的义务的措施。“回转”机制是以前述锁定的不符合投资协定的措施为起点,逐步减少或消除该限制措施的自由化过程。缔约方只能努力逐步减少或取消这些措施,而不得采取新的例外措施。
美国是最早采取全面的准入前国民待遇的国家。从1980年起,美国开始与发展中国家谈判和缔结促进与保护投资的双边条约,要求在投资准入阶段实行国民待遇,这在当时是惟一的要求缔约国在准入和开业阶段将外国投资与内国投资同等对待的双边投资条约。(注:See Patricia Mckinsty Robin,The BIT Won't Bite,The American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Program,33 Am.U.L.Rev.931,949(1984).)从此后,投资准入前的国民待遇就成为美国式双边投资条约的重要内容之一。(注:不过,考虑到不同国情,美国与某些国家(如波兰、俄罗斯等前苏联东欧国家)的条约在此问题上后来也作出了一定的妥协。See Kenneth J.Vandevelde,U.S.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The Second Wave,14 Mich.J.Int'l L.621.)截至2004年9月15日,美国已与46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条约。(注:U.S.Department of State,U.S.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y Program,Sept.15,2004,http://www.state.gov/e/eb/rls/fs/22422.htm(last visited October 1,2004).)此外,自1992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第11章专门对投资作了规定后,美国在此后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中也对投资问题采取了类似的规定。2004年2月,美国国务院颁布了2004年更新了的双边投资条约范本,以替代1994年的条约范本,并使其结构和内容与美国FTA中的投资章节相协调一致。(注:See U.S.Department of State,Update of U.S.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Feb.5,2004),http://www.state.gov/e/eb/rls/prsrl/2004/28923.htm(Last visited October 1,2004).)这样,美国通过双边投资条约和自由贸易协定两种协定方式,达到促进投资自由化和强化投资保护的目的,而且这两种协定关于投资问题的规定也协调一致起来了。
除美国外,日本近年来也紧跟在美国之后,在条约实践上采取准入阶段的国民待遇。上述日本与韩国(2002)以及与越南(2003)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均将国民待遇适用于投资准入阶段。
二、关于外资准入阶段国民待遇的政策考虑
从国际法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传统上,外资准入问题属于国内管辖事项,国家有权决定外资准入的程度和条件。近年来随着投资自由化的发展,在发达国家的推动下,有的条约已将国民待遇扩及到投资准入阶段。但是,从东道国的角度看,能否在投资准入阶段采取国民待遇取决于其本国国情及其政策考虑。这通常涉及以下因素:
1.外资的引进与保护
对外资采取全面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可以起到改善投资环境的作用,更有利于吸引和保护外国投资者。因为,此种待遇具有如下特点:(1)市场准入。将国民待遇适用于外资准入阶段,就是在准予投资的领域、投资准入的条件以及投资审批方面给予外国投资者与内国投资者同等的待遇。其核心或实质意义,是使外国投资者能在市场准入环节与内国投资者居于平等的地位,从一开始就能与内国投资者平等竞争。(2)透明度。将国民待遇作为一个原则,而将例外产业以清单的方式列举出来,可以增强透明度,使投资者在进入东道国之前就能清楚地知悉自己能在哪些领域投资,有何限制性条件,增强投资决策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这无疑对外资的进入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2.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
对外资给予准入前国民待遇也涉及到国家的管理权问题。根据国家对其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原则,每个国家都有权决定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条件,有权管理外国投资和跨国公司,管理领域内的一切经济活动。(注:参见联合国大会1974年12月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第2条的规定。)若给予外资全面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就可能限制甚至排除东道国对外国投资进入领域和进入条件的全面审查权,东道国只能对经双方同意的少数产业领域限制外资进入。这会对发展中东道国主权的行使构成限制,并会损害其利益。
3.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及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一般来说,对外资能否给予国民待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及企业的竞争力。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间实行国民待遇,可以通过平等竞争,相互获益。但在经济实力相差悬殊的国家间在投资领域实行国民待遇,即使是互惠的,对弱国一方也是不利的,因为在实力不对等的基础上的竞争,必然导致弱者一方处于劣势或从属地位,造成实质上的不平等。(注:参见余劲松主编:《国际投资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27页。)
目前发达国家间在投资领域相互给予国民待遇已基本没有异议,经济合作发展组织草拟的《多边投资协议》关于国民待遇的规定就包括投资准入后和准入前阶段。但是,对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关系来说,投资准入阶段的国民待遇仍是一个敏感问题。由于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的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内资企业大多处于弱势地位,不具有国际竞争力或竞争力不强,而发达国家的企业具有资金、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若允许外资在准入阶段就享有国民待遇,则在竞争力悬殊的情况下,会使外资从一开始就处于优势,本国民族工业难以得到有效的保护。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权衡外资竞争力对本国经济和企业发展的影响,确保本国经济和民族工业能得以健康发展。
不过,在实践上,也有些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实行准入阶段国民待遇,这通常是基于其国情和有关政策考虑所采取的。例如,有些发展中国家与美国间的双边投资条约就采取了准入阶段的国民待遇,越南最近与日本间的投资条约也对此作了规定。这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接受准入阶段国民待遇,有的是希望藉此形成良好的投资气候,吸引外资来发展经济;有的国家国内产业薄弱或本身不发达,需要予以特殊保护的本国产业较少;还有的国家政府认为,采取准入阶段国民待遇,可以使其国内产业从逐步开放中受益、从更具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中受益。
中国在国民待遇的问题上,无疑也应仔细考虑和权衡上述因素,既要考虑投资环境的改善问题,也要考虑本国产业的保护和国家对外资的管理权问题,并在此基础上采取相应的对内对外措施。
三、中国应对准入阶段国民待遇的国内法措施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客观发展趋势。经济全球化必然要求经济自由化,因此,投资自由化也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中国入世,承担了WTO《服务贸易总协定》关于服务贸易逐步自由化的义务,这实际上在投资自由化方面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今后中国会继续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向经济自由化的方向迈进。
但是,在经济自由化的进程中,中国必须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在维护本国主权和利益的基础上,采取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法和道路。具体说来,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应该把发展作为自己的根本目标,应该采取逐步自由化的措施,循序渐进。
因此,在国民待遇的问题上,首先要做到逐步给予外资全面的准入后国民待遇;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的逐步成熟,可以逐步提高市场准入的程度,采取有限的准入阶段国民待遇;待市场经济发展成熟后,再可采取全面的准入阶段的国民待遇。为此,中国目前在国内政策和法律方面应考虑采取以下措施:
(一)统一内外资政策,实行全面的准入后国民待遇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逐步扩大了对外资的国民待遇的适用范围。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在中国进行经营活动时基本上已经享受了国民待遇,而且在税收方面还享受着优惠待遇。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要改善投资环境,对外商投资实行国民待遇。
实行全面的准入后国民待遇,就要统一内外资政策,消除内外资企业间的差别待遇。这样,一方面要防止和消除对外资实行的各种法律上和事实上的歧视,另一方面也要平等地对待内外资企业。目前颇为引人关注的,是外商投资企业享有税收优惠,有人称之为“超国民待遇”。这种内外差别待遇使内资企业的税收负担重于外商投资企业,不利于其在平等的基础上竞争。因此,将有关的鼓励和优惠措施同等地适用于内外资企业,使它们在平等的基础上公平竞争,是国民待遇本身的要求。
(二)实行产业逐步自由化措施
中国如果要进一步实行准入阶段国民待遇,最重要的是解决国内产业的保护问题。中国目前正在处于经济转型期。国有企业正在实行改制和改革,许多国营企业正处于一种体制过渡的不稳定的状态。民营企业正在发展过程中,许多企业规模小、国际竞争能力低。因此,与发达国家相比,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数量不多,若实行准入阶段国民待遇,可能相当多的内资企业会受到影响。
因此,中国必须根据产业发展水平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并采取不同的措施。
在这方面,可以借鉴日本在加入OECD、承担《资本移动自由化法典》义务时的做法,根据实际情况,对产业部门进行分类。例如,将那些完全可以与外国投资者竞争的产业列为第一类自由化产业,可以予以开放;将虽具有一定的竞争力但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竞争力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的产业列为第二类自由化产业,实行一定程度的保护;将没有竞争力的产业列为第三类自由化产业,提供相应的保护;将不对外开放的产业部门列为非自由化产业。
当然,关于国内企业的保护方面,也必须考虑到问题的另一方面,即防止以市场准入限制来保护落后产业。对于应由市场调节的企业来说,市场准入限制应该是个过渡措施,不应无限制的使用,否则,过度的保护会使其丧失发展的动力,导致不进则退,从而丧失竞争力。
至今为止,中国还没有一部可以统一适用于内外资的产业目录。因此中国政府有关部门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必须对各门各类产业进行梳理或清理,仔细考虑分析以下几种情况:(1)哪些行业应保留给政府或国有企业的;(2)哪些产业是应保留给内资企业的;(3)哪些产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4)哪些产业需要过渡保护期的。
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就必须开拓和形成一种机制和渠道,使企业和行业的意见能有机会得到表达和反映,使政府有关部门能及时了解企业的信息,了解各行各业的发展状况和需求。否则,产业政策不符合实际,就会产生严重的副作用。这就必须发挥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三方面的作用,尤其要使行业协会与政府真正分离,使其能真正代表行业企业的意志与利益。
(三)逐步放松外资审批制
与产业自由化密切相联的是外资审批制的逐步放松。对于那些具有国际竞争力、可以实行自由化的产业,在法律上也应采取相应的措施,放松其审批制度。中国目前采取严格的投资审批制,每一个投资项目都必须逐个审批。在以后的产业逐步自由化的过程中,可以考虑采取审批与登记相结合的制度,凡属自由化的产业,只需登记,毋需审批。
四、中国应对准入阶段国民待遇的国际法措施
由于实行全面的准入阶段国民待遇的时机尚不成熟,因此,中国目前原则上不应通过条约来承担会导致普遍性的准入阶段国民待遇义务。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采取准入阶段国民待遇。例如,在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的情况下,由于该种协定可以构成WTO和其他双边投资协定的例外,缔约国间相互给与准入阶段国民待遇不会通过最惠国条款扩及到其他国家,因此,在这种特殊安排下,准入阶段国民待遇应是可予考虑的。
当然,这种区域性或双边安排的对象不同,也应采取不同的对策。例如,若此安排发生在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间,那么,由于其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同,采取准入阶段国民待遇对缔约方不会产生太大的副作用。若是在中国与发达国家间,那么,对准入阶段国民待遇就必须采取更为审慎的态度。
无论是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达成区域性或双边安排,如果实行准入阶段国民待遇,仍然应该考虑到各方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采取各方能够接受的灵活的安排。这些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一)“发展”例外问题
对国民待遇的例外、特别是一般例外如何规定是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发达国家之间对于一般例外也存有分歧。因此,在此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利用。例如日韩投资协定实行高度投资自由化措施,但它也规定,在例外的金融情况、经济情况或工业情况下,可以采取例外的限制性措施。
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中,也有的将“发展”列为国民待遇的一般例外。中日1988年的投资协定就有关于“经济的健康发展”的例外规定,但那是针对准入后国民待遇而言的,若实行准入阶段国民待遇,采取此种例外也是可以考虑的一个选择。
(二)采取有限制的准入阶段国民待遇
采取这种做法,东道国对投资自由化的程度和步伐以及准入的条件可以保留某种程度的控制。因此,这种方法对于那些希望对投资准入采取逐步自由化的国家来说较为适合。
具体做法可以采取“肯定式清单”方法。除非经东道国特别同意,其产业和活动在准入前阶段不适用国民待遇。中国目前不应接受发达国家所主张的“自上而下”、“否定式清单”的做法。因为采取这种方法,需要对产业进行艰难的评估,这在目前中国一下子还难以做到。同时采取否定式清单法时,某一产业如果没有列入例外清单,会导致其潜在地受到来自外国投资者的损害性的竞争,特别是当协定中规定有“停止”义务时情况更是如此,这就可能导致该产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三)特殊的和差别的待遇
若是在与发达国家间的投资安排中采取准入阶段国民待遇,就必须对中国采取特殊的和差别的待遇。这种特殊的和差别待遇除体现在上述有限的准入阶段国民待遇外,还包括应对中国不适用“停止”和“回转”机制。
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期,一是产业发展处于不稳定不成熟状态,产业政策也处于不稳定不成熟状态;二是在此期间为改变产业和经济结构,政府必须进行宏观调控。政府的宏观调控必然会对产业发生影响,有的产业会逐步放开,但也不排除会对某些产业施加限制。这种宏观调控不仅可能使所列举的例外产业难以锁定,而且也有可能由于出现新的敏感部门或新的经济活动领域而需增加新的须予限制的产业。因此,发达国家协定中所规定的“停止”和“回转”机制应不适用于中国,应允许中国政府为经济宏观调控目的而实行限制,包括新增受限产业。
总的来说,在如何规定准入阶段国民待遇时,应在投资者保护与促进东道国发展间达到平衡。发达国家要求实行准入阶段国民待遇所强调的是投资者的保护,而发展中国家所强调的是本国主权和经济利益。由于利害冲突严重,双方关于国民待遇的分歧在国际投资领域一直难以消解,这也是国际上长期以来未能达成多边国际投资协定的原因之一。因此,在条约谈判中要就国民待遇问题达成一致,就不能只是片面地考虑单方的意愿和利益,必须将当事各方的意志和利益协调起来。片面地强调投资者的保护或东道国的主权和利益,都不是好的办法。合理的解决办法是在二者间达到平衡,既要保护投资者的投资安全和利益,也要维护东道国的主权和利益,促进东道国经济和民族工业的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