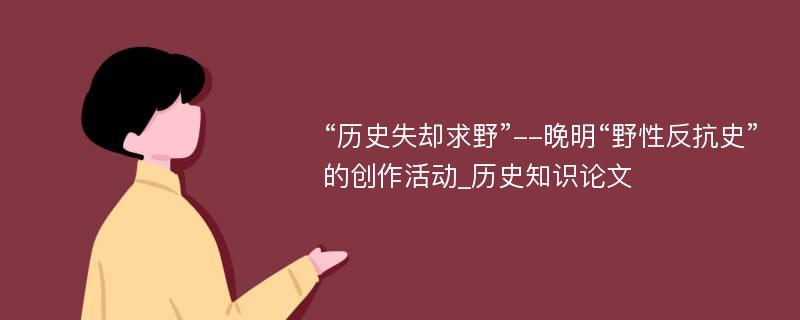
“史失则求诸野”:晚明在野力量的野史撰述活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撰述论文,野史论文,力量论文,史失则求诸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晚明野史笔记恢宏旷达、跌宕奇崛、躁急奔竞,种类之繁多、题材之广泛、叙事之详尽、笔法之恣肆、评论之任情,一时蔚为大观,历代罕见。何谓野史笔记?谢国桢先生早有明确定义:“凡不是官修的史籍,而是由在野的文人学士以及贫士寒儒所写的历史纪闻,都可以说是野史笔记,也可以说是稗乘杂家。”①这一界定大体抓住了野史笔记的核心特征:野史笔记与官修史籍相对应,撰述主体多为在野知识群体,记载内容多是历史纪闻。不过,应当指出的是,晚明野史笔记并非全为在野知识群体撰写,不少当政的士大夫也参与其中,只是他们的撰述活动属于私家修史,而非代表官方行使史权。 以撰述主体的社会身份为标准界定野史笔记难以反映出“官史—民史”格局及其此消彼长的内在理路,也难以确定野史笔记在晚明史学生态系统中的历史坐标,因而,并不十分允当。按历史书写主体、对象、内容、风格的不同,可以粗略地将历史分为“大历史”和“小历史”两种史学形态:“大历史”多由朝廷组织、史官书写,记载对象多为帝王贵胄、卿士将相,内容多关涉军国大事、典章制度,撰述风格表现为“宏大叙事”;“小历史”则多由在野知识者书写,记载对象多为乡野鄙夫、市井百姓,内容极其庞杂,举凡山川鸟兽、乡野见闻、民风教化、灵异灾象,无所不包,撰述风格表现为“微观叙事”。“大历史”与“小历史”囊括各种形态的史学群落,这些史学群落共同构成一定的史学生态。作为民史的一种,野史笔记属于“小历史”的范畴,在晚明史学生态中处于与国史对应的地位。 野史撰述真正成熟当于晚明。这一时期野史成书种类极多,数量极繁,私人撰述热情极高,表现形式富于前瞻性,史学思想富于创造性。晚明以降,野史命运几经沉浮。清代野史虽为数不少,却被视为被官方史学流放的史学形态。20世纪前半期,伴随新史学之风盛行,正史被斥为“废铜”②而不为人重视,野史反倒成为一些史学家著述取材的大宗③。在一批开明学者的引领下,野史研究成为一种学术风尚。④近几十年来,学界对野史有一定关注。⑤不过,许多问题依然有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的空间,一些成说尚有商榷的余地。笔者曾撰文探讨过晚明野史笔记繁盛的历史合理性⑥,却未能诠解“史失则求诸野”的内在理路,因而犹觉言之不足。“史失则求诸野”究竟为何在晚明发生?这种史学现象到底蕴含着怎样的史学逻辑?又面临着怎样的历史命运?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一番考察。 一 平民化趋势加剧与在野知识群体壮大 自“唐宋变革”以来,中国社会逐渐步入平民化的轨道,这突出地表现为阀阅观念淡薄、等级秩序趋于瓦解、平民力量持续增强。在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迁的晚明时代,等级秩序的松动和民间力量的上升表现得尤为显著。 在等级社会中,衣饰冠带是考察社会秩序的重要外物,扮演“区别各种不同的地位和阶级”⑦的角色,具有识尊卑、别贵贱的身份象征意义。人们运用“执简驭繁之术”,“以劝善惩恶之心,寓于寻常日用之事”,作为“治天下之具”的衣冠承担着“辨等威而定秩序”的功能。⑧承绪蒙元、衔接清朝的明朝对衣冠隐喻格外重视。大明律对服饰规格有明确区分,目的是“望衣冠而知士庶”。明中叶以后,这种等级规制受到撼动。嘉靖时,“诡异之徒,竟为奇服以乱典章”,“衣服诡异,上下无辨”⑨,“妇人之衣如文官,其裙如武职”⑩。衣冠秩序受到挑战反映的是社会等级秩序松动和民间力量上升。明中叶以后,种种逾制行为屡禁而不止,深刻地反映出层级壁垒坍塌和社会流动加剧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强大洪流。 明廷一系列进步举措对平民化趋势加剧、在野知识群体壮大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1.明廷对人权问题非常重视。开国君臣多起自社会底层,建基皇明后打压豪族显贵,为平民阶层崛起创造了良好条件;通过主佃关系的调整,基本废止了佃农的人身依附关系,将具有奴隶色彩的佃农提升至平民层级,且为平民入仕提供了种种便利;英宗朝废除人殉制度,生命的尊严得以彰显;神宗朝张居正改革进一步缓解了人身依附关系。人权受到尊重反映出人的觉醒,人的价值受到重视。 2.明廷对民间教育的发展不遗余力。有明一代,朝廷非常重视文教事业,各府、州、县遍立学堂,广施教化。一时间,“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崖,此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11)。民间教育的发展普及了知识,提升了草野俊彦的文化素养。 3.朝廷为寒门子弟求学问道提供了种种便利:明代继承了传统的“士子免役”政策,并且通过各种途径向寒门士子提供资助;朝廷对书籍征税额度较低,“不鬻于市”的书籍可以免征赋税(12);“国子监及各州军郡学,皆有官书以供众读”(13)。官方的右文举措促进了民间知识群体的孕育和成长。 4.科举制度僵化,饱学之士借科考入仕之途逼仄,客观上造成了在野知识群体的形成。约占当时全国人口0.46%的60余万生员(14)和约占全国人口3.5%的180余万童生(15)因无法步入仕途而滞留民间,连同大量游离于“科举—仕途”之外粗通笔墨的村社塾师、店铺掌柜、寺观僧道和城乡居民,构成了庞大的民间知识群体。 来自民间的积极因素同样推动了平民化巨轮,促进了在野在知识群体的形成和壮大。 1.心学勃兴燃起了在野知识群体的道德担纲意识。心学使得民众摆脱了士大夫以“德”和“知”为依托对民众施行教化而民众只能被动地接受教化的模式。伴随良贱秩序颠覆、四民界限模糊,愚夫愚妇赢得了与士大夫同等的地位,这就“把道德的承担者从士大夫、官僚、地主扩大到商人、农民、劳动者,亦即所谓自父老、布衣至田父、野老以及市井庶民”(16)。 2.狂者精神在晚明的复归增强了在野知识者的群体认同感和历史使命感。狂者精神是在深沉的责任感和自觉的使命感基础上表现出的勇于担纲、舍我其谁的宏远器识、孤绝格调、雄伟气魄以及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切关怀。中晚明占据狂者精神的制高点,是中华文化狂狷传统的集大成时期,各阶层、各群体、各领域几乎都被“狂”风浸染,“狂”成了全社会普遍的文化情致和生活韵致。(17)大批狂者放浪形骸、意气横厉,充满着对平等、自由、独立的向往。在狂者精神的冲击下,禁锢人心的理学受到鞭挞,人的自我意识觉醒,人的个体性和主体性得以弘扬,人的欲望、尊严、价值得到尊重。这些文化品格对在野知识群体认同感的形成和对历史使命感的激发大有裨益。 3.植根于民间的泰州学派掀起的儒学平民化运动为在野知识群体的形成和壮大做了思想和理论铺垫。与朝廷的右文理念相呼应的是,民间设坛讲学之风十分浓郁。泰州学派一扫士大夫阶层垄断教化的困局,广纳乡野鄙夫为徒,授以知识,晓以大义,开启民智,可谓“述通效劳于草莽,牖开盲聋于四海”(18)。席卷知识界的儒学平民化运动实质上是一场把儒教道德“广泛扩散到民间、使民众主体性地承担乡村秩序的精神革新运动”(19)。随着这场运动的深入开展,愚夫愚妇的平民意识得以彰显,平民诉求得以表达,在野知识群体趁势而起。 4.出版技术改良引发的民间刻书、藏书热潮促进了在野知识群体的形成和壮大。晚明私刻书籍之盛令叶德辉慨叹:“使有史家好事,当援货殖传之例增书林传矣。”(20)书籍大量刊刻催生了一大批藏书量极大的民间藏书家。由是,图书收藏格局发生变动。诚如时人所论:“汉、唐、宋开国之际,皆尝博求遗书,故其时内府之藏,尽天下之有,若史籍所志,何其富也,本朝则不及远矣。……乃今秘阁之藏,不及士人积书之半,天禄石渠之奥,空虚等此,亦大缺典也。”(21)书籍不仅是知识的载体,反映社会和文化的“理性程度”和“开放程度”(22),还是知识群落得以形成的物质承载者,不仅扮演着信息传递的角色,还是“自我和身份的象征。正如我们确定穿着风格不单单是为了实用,我们选择书也要能‘恰当地’反映我们以及我们所加盟群体的形象”(23)。在民间刻书、藏书的风潮中,在野知识群体得以便捷地汲取文化营养而迅速壮大。 5.“超越前代”和“立言不朽”思潮盛行激发了一批在野知识者自觉从事历史书写,形成在野史家群体。明中叶后出现一股勇于肯定当代、褒扬本朝的“超越前代”思潮。(24)借此思潮,明人的时代自豪感显著增强,希冀明代史学能够“跨唐、宋而上之”(25)。“立言不朽”思潮则为困顿中的草野之士实现人生价值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途径。他们不再言必称《史》《汉》,而皆望成马、班。怀揣“超越前代”理想和“立言不朽”情结,民间史家在艰苦的环境下饱满激情地致力于历史书写,形成规模庞大的在野史家群体。 大批知识精英滞留民间,势必引起朝野文化格局的变动。原本高居庙堂的史学散落民间,社会上出现“诸生修史”(26)和“布衣修史”(27)的现象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二 官方史学式微与民间史学勃兴 (一)“无史”、“实录不实”:官史不振 1.“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史官失职,国史失修 明代官史乏善可陈,日录、起居注粗陋,处于一种“无史”的状态。郎瑛表达对“无史”的看法: 古人左史纪言、右史纪事,宫中又有起居注,善恶直书,故后世读之如亲见者也。今史官虽设而不使目录,一朝宴驾则取诸司奏牍而以年月编次,且不全也,复收拾于四方,名目而已,且爱恶窜改,于二三大臣三品以上方得立传,但纪历官而已,是可以得其实乎?今日是无史矣。(28) 按古之定制,国史编修通常采择日录、起居注等一手资料,如此方能“读之如亲见”,明代史馆制度粗陋且执行不力,史书编修往往依据事后回忆信手落墨。史官形同虚设,多随个人好恶肆意窜改,只为高官显贵立传,记载内容多局限于皇帝、大臣言论,以至于王世贞慨叹:“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也。”(29) 当代正史阙如,各朝实录通常被视为“国史”,却多出现记载失实和评价不当的现象。李维桢叹息道:“本朝无史,而遂以实录为史,有识者病之。”(30)沈德符认为“本朝无国史,以列帝实录为史,已属纰漏”,更何况“实录难据”。(31)清人也猛烈抨击“实录不实”的现象。四库馆臣曾指出:“盖明自永乐间改修《太祖实录》,诬妄尤甚,其后累朝所修实录,类皆缺漏疏芜。”(32)夏燮也说: 正史之多本于《实录》,明人恩怨纠缠,往往藉代言以侈怼笔。如《宪宗实录》,邱浚修郗于吴、陈;《孝宗实录》,焦芳修郗于刘、谢;《武宗实录》,董玘修郗于二王。而正史之受其欺者遂不少,弇州所辩,十之一二耳。至如《洪武实录》再改而其失也诬,《光宗实录》重修而其失也秽。(33) 近人邓之诚在《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序》中批评明代实录不及唐、宋实录,并深刻分析了其中因由: 尝谓有明实录之修,其乱如绳。发凡起例,未见其人。褒贬无闻,徒多篇幅。以视唐宋,迥然有上下床之别。盖实录之作,本以编年之体示其褒贬,备修史削稿,犹有所凭。唐累修国史,宋有三朝四朝之史,而明以实录为史,遂废笔削,一也。唐修实录,本于起居注,宋则本于日历时政记,虽取材不广,要有所本。明代惟凭章奏成书,二也。唐宋实录,多出名手。韩愈之于顺宗,王安石之于英宗,固无论矣,宋尤慎选史官。而有明宣德以后,例以修撰编检修史,非翰林不得与一代纪载,三也。宋之秦桧,可谓专横,而其尚言曰,实录当以实示人。乃明代实录多由大臣操纵。焦芳之于何乔新彭韶谢迁辈,辄肆丑诋,颠倒是非。世穆两朝实录皆出张居正之手,最称严核,然世宗实录于郭希颜胡宗宪唐顺之多有贬辞,未挟舆论,而穆宗实录特著高拱之不善以见恩怨,四也。……故钱谦益《太祖实录辨证》、潘柽章《国史考异》批穴导覆,历举忌讳之失,史官之驽下。即万斯同笃信实录,然其读洪武实录则诋其详于细而略于巨,读弘治实录谓其最为颠倒,而后知有明实录之未可尽信。(34) 明代实录在体例上很不整,褒贬上有失允当,在采择上少有依凭,在修撰上过于冗杂,编修者少有良史之材,柄权者多为奸佞之臣,明实录不及唐、宋实录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国史失职深深地刺痛了柄权者的自尊心,开明的柄权者认识到这些问题并试图“亡羊补牢”。翰林院编修张位疏言: 臣备员纂修,窃见先朝政事,自非出于诏令,形诸章疏,悉湮没无考。鸿猷茂烈,郁而未章,徒使野史流传,用伪乱真。今史官充位,无以自效。宜日分数人入直,凡诏旨起居,朝端政务,皆据见闻书之,待内阁裁定,为他年实录之助。(35)起居注本应由史官随时记录,史官却玩忽职守。张位为此忧心忡忡,遂出谋划策,希冀起居注完备,待编修实录时采择。张居正也意识到,明中后期朝廷失去了朝记夕注之规,以致累朝以来史文阙略,纂修《实录》不过总集诸司奏章,章疏所不及者无凭增入,欲采录诸野史稗乘又恐失真,“凡此皆由史臣之职废而不讲之所致也”(36)。 万历二十一年(1591),陈于陛上疏请修国史,对当朝史学做了深刻检讨: 我朝兴造功业,建立法制。事事超越,而史书独有列圣《实录》藏之金匮石室,似只仿宋世编年《日历》之体,但可谓之备史,未可谓之正史。至于《大明会典》屡修颁布,凡六曹政体因革损益之宜虽已该载,而庙堂之谟、谋、册、诰,臣工之论议、文章不与焉,但可谓之国有典制、百司遵行之书,而非史家之体。(37) 后来,他又惊呼:“实录宝训秘在金匮,而会典职掌又涣而不属,野史诸家更秕而不典。苟不及此,时修正史,何以昭一代之盛?”(38)在“事事超越”的大背景下,作为“国之重器”的史学事业岂能自甘落后? 陈于陛请修国史令无数士人兴奋不已,然而短视的统治者视修史大业如同儿戏,虽几经努力,但最终以失败告终。(39)一时间熙熙攘攘,再回首满目疮痍,终明一代,官修史书始终没能逃脱失败的命运。 2.“不得其人,不专其任”:史馆制度僵化与众人分纂没落 明代“无史”和“实录不实”的史学困局是史权受制于治权、史馆制度僵化及众人分纂没落造成的。 历史学家时常哀叹史权之衰微,痛心于史书难以彰善瘅恶。综观整个中国史学文化,史权与君权关系异常微妙。当史权依附君权或被君权胁迫时,史权虽得以伸张,却扮演着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的不光彩角色,这是尚有一丝良知和独立意识的历史学家不甘心的。当史权对君权表现出离心倾向时,往往会遭受君权压制甚至毁灭性打击而致史权式微,这又是历史学家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上,无论史权大张还是史权式微,都是史权的异化。前者表现为史权受制于治权、是非曲直取决于“圣裁”等隐性的史学暴力;后者表现为“焚书坑儒”、“文字狱”等显性的史学暴力。晚明现代性因素固然大幅增长,但专制制度无所不在,专制思想无孔不入。伴随君臣矛盾、党派矛盾和史官矛盾,史书编修往往被当做政治斗争的工具,自然难以求实征信。在帝制时代,将史家之褒贬系于帝王之裁断,史学堕为专制主义的奴婢,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自南北朝设置史馆以来,官修史书得到长足发展,许多重要史籍出自史馆。但是,史馆修史制度本身因其难以克服的弊病饱受垢议。唐以前的史书多为私人著述,自设史馆众人分纂以来,史家精神堕落已是无可挽回,“既不是私家著述也不是家学,而是奉天子之命,经多人之手,按照分纂方法编纂”的《晋书》是“治史堕落的开始”。(40)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几亲身体验史馆制度之苦,列举史馆修史之“五不可”,其中提到众人分纂之弊:“古之国史,皆出自一家……咸能立言不朽,藏诸名山。未闻藉以众功,方云绝笔。唯后汉东观,大集群儒,著述无主,条章靡立。……今者史司取士,有倍东京。人自以为荀、袁,家自称为政、骏。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41)中国古代史馆修史之弊,讫清末犹未革除,刘知几所谓的“五不可”即隋唐以降官修之史不及私修之史之总因。(42) 到了明代,史馆修史制度之弊更是暴露无遗。王鏊认识到成化之后史馆修史的程序繁琐且难以取信后世: 前代修史,左史纪言,右史纪动,宫中有起居注,如晋董狐、齐南史皆以死守职,司马迁、班固皆世史官,故通知典故,亲见在廷君臣言动而书之,后世读之,如亲见当时之事。我朝翰林皆史官,立班虽近螭头,亦远在殿下。成化以来,人君不复与臣下接,朝事亦无可纪。凡修史则取诸司前后奏牍,分为吏、户、礼、兵、刑、工为十馆,事繁者为二馆,分派诸人以年月编次杂合成之,副总裁删削之,内阁大臣总裁润色。其三品以上乃得立传,亦多纪出身、官阶、迁擢而已,间有褒贬,亦未必尽公,后世何所取信乎?(43) 官方以冗繁的行政手段操纵史馆修史,导致官史生命力大为减退。官方组织的史馆集体纂修效率低下,而史馆众人分纂之流弊很大程度上是执笔操觚者不得其人、不专其任所致。纂修国史对史家素养要求很高,然而明代史馆选拔史官往往不得其人。谈迁注意到: 明初史馆,布衣亦尚与坛坫之末,其后非公车不敢望。又其后馆阁有专属,即公车之隽,或才如班范,未始以概进也。噫!明之于功令龂龂甚矣,故史日益以偷。垂三百载而无敢以左足应者。(44) 明前期尚能以史学素养作为准绳选拔史官,甚至出现布衣史官;后来选拔史官更多地考虑政治需要,德才兼备的良史未必能进入史馆。入清后,有名流荐举谈迁入馆阁修史,遭到拒绝。谈迁对史馆集众人分纂不抱好感,不无气愤地说:“国初布衣预史馆时,略势分,广采集。今进贤冠载笔尚论崇卑,一措大厕其间,仰望鼻息,不过呈翰吮墨,等于门下牛马走。”(45)朝廷既不能选拔优秀人才,又不尊重人才。曾参与修撰国史的焦竑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 史之职重矣,不得其人,不可以语史;得其人不专其任,不可以语史。故修史而不得其人,如兵无将,何以禀令?得人而不专其任,如将中制,何以成功?苏子谓史之权,与天与君并,诚重之也。……自二史虚员。起居阙注,衣冠百家罕通述作,求风俗于郡县,讨沿革于台阁,著作无主,条章靡立,人自以为荀、袁,家自以为政、骏矣。(46) 得其人、专其任是修史的先决条件,明代史馆修史做得还远远不够。朝廷屡屡开馆修史却次次以失败告终,激起了天启帝的怒火: 史官无他官业,专以纂修为事。皇祖实录,开馆至今,已经五年,尚未告成,虚糜廪禄,各官职守何在?以后俱着入史馆编摩,不许私寓逍遥宴饮,亦不得给假乞差,以致出入无常,稽误大典。仍先按月送稿;其修成实录,一年两次进呈,务在早完。(47) 散漫的史官修史效率极低,连平庸的天启帝都不得不严加斥责、敦促再三。然而,直到天启帝驾崩,完成“昭一代之盛”的修史夙愿依然遥遥无期。史官之失职、修史效率之低下由此可窥一斑。 时人对史馆假众人之手分纂史书颇为不满,对此做了深刻检讨。焦兹提到众人分纂之弊: 盖古之国史,皆出一人,故能藏诸名山,传之百代。而欲以乌集之人,勒鸿钜之典,何以胜之?故一班固也,于《汉书》则工,于《白虎通》则拙;一欧阳修也,于《新唐书》则劣,于《五代史》则优,此其证也。今之开局成书,虽藉众手,顾茂才雅士,得与馆阁之选者,非如古之朝领史职而夕迁之也。多者三十年,少者不下二十年,出为公卿,而犹兼翰林之职,此即终其身以史为官也。自非遴有志与才者充之,默然采其曲直是非于中外雷同之外,以待他日分曹而书之所不及,吾不知奚以举其职哉?(48) 班固、欧阳修这样的良史独立修史则成经典,参与众人分纂则拙劣无比,更何况明代史官选拔机制僵化、缺少可堪大任的良史呢?谈迁也认识到欧阳修独撰《五代史》则卓著,集众人之手撰修《新唐书》则不太理想,慨叹:“天下事成于独而散于同,比比是也。明作者非一人,繁简予夺之间,得失相半。”(49)祝世禄认识到:“馆阁作者如林,寥寥未竣,曷故哉?古之史者有专任而无分曹,有独裁而无乱笔,故史于今者难且百倍古。”(50)明以后亦有不少有识史家持此观点,说明明人对此问题的认识是清醒而深刻的,并非情绪化使然。万斯同诟病设馆分纂:“昔迁、固才既杰出,又承父学,故事信而言文,其后专家之书,才虽不逮,犹未至如官修者之杂乱也。……官修之史,仓卒而成于众人,不暇择其材料之宜与事之习,是犹招市人而与谋室中之事也。”(51)章学诚也以唐代官修诸史行而私门著述废为由慨叹“史学亡于唐,而史法亦莫具于唐”(52)。晚清民国的刘咸炘也认识到:“夫史文之瘠,生于史体之坏。史体之坏,则由史任之变专家为官修。”(53) 设馆分纂不可能产生传世名作,根源在于其不符合学术创造的规律。古今中外,经典史书多为独著,集体修史鲜有值得称道者,因为史书编纂和史学研究是个性化很强的活动,极富创见的史学思想往往源于学者内心深处的独立思考,“是学者个体的心灵体验……古往今来,任何学术名作,都有着作者对历史的独到见解,有着对历史内在精神的天才猜测,而这些是集体编书无论如何无法达到的”(54)。学术事业的繁荣和进步往往以官(势)、师(道)分离为前导。“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礼失而求诸野”,引发了春秋战国时期学术思想的勃兴。20世纪二三十年代,如雨后春笋般崛起的民间学术团体和自办学术期刊大大推进了中国学术思想的进步;六七十年代意识形态严厉控制学术事业导致了学术思想的贫瘠。这些无可争辩的事实昭示:官方话语旁落,政治为学术松绑,学术回归民间才是学术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 (二)“美哉,彬彬乎可以观矣”:民史崛兴 1.“学士大夫之辱”:明人对本朝史学的反思与批判 明人对本朝史学的反思是至为深刻的,批判是不遗余力的。 首先是对“实录不实”的反思和批判。 起初,《实录》虽严重失实,但秘藏宫禁,鲜为人知;万历中叶后,历朝实录由宫禁相继外传,“其病态遂大著于世”(55),遂引起朝野上下同声斥责。李建泰严厉批评道: 国家历祀几三百年迄今,成史无闻。问其所用传信者,不过曰累朝之《实录》。至《实录》所纪,止书美而不书刺,书利而不书弊,书朝而不书野,书显而不书微。且也,序爵而不复序贤,避功而巧为避罪。文献之不足征久矣!(56) 史馆修史制度僵化,史官玩忽职守,根据个人好恶和政治形势率尔操觚,势必导致记载失实、评论失当。谈迁指出: 史之所凭者,实录耳。实录见其表,其在里者,已不可见。况革除之事,杨文贞未免失实;泰陵之盛,焦泌阳又多丑;正、神、熹之裁笔者,皆逆奄之舍人。至于思陵十七年之忧勤惕厉,而太史逐荒,皇宬烈焰,国灭而史亦随灭,普天心痛,莫甚于此!(57) 《实录》纂修受政治形势干扰,十分令人痛心。无论在朝士大夫,还是在野知识者,对这一弊病的看法都是清醒而一致的,说明“实录不实”已经到了朝野共愤的地步。 其次是对史学乱象的反思和批判。 有明一代,史学一途堪忧。斯文丧尽、追名逐利者有之,率尔操觚、粗制滥造者有之,此因彼袭、拾人牙慧者有之,厚颜无耻、抄袭剽窃者有之,可谓百弊丛生。“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俨然是“一诬妄之世界”。(58)凡此种种对明代史学造成严重创伤。首先,学风极差,“未免风光狼藉,学者徒增见解,不作切实工夫”(59);其次,率尔操觚者甚众,优秀史家极少。黄端伯坦承:“我明作者如林,然良史之才尚阙。”(60)第三,史书数量多而质量劣。“著书之人几满天下,则有盗前人之书而为自作者矣,故得明人书百卷,不若得宋人书一卷”。(61)明代史学乱象横生,引起有识之士的愤恨,激起了他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有些开明的史学家认识到当代史学相对于前代史学尚有许多不足,转而冷静审视当代史学的真正价值,重新定位当代史学的历史坐标。李维桢感叹明代史学不如宋代史学成就高: 余复窃叹宋人议论多而成功少,国因不振。今议论烦嚣殆甚于宋,然宋犹能使正史编年成功。倾诏修国史,筑室道旁,三年不成。宋能以议论成其议论,而本朝议论亦付之亡是,乌有其有三长如弇州先生,徒令以文士成其名,可不为长太息哉!(62) 宋人虽喜好议论,尚能取得不俗的史学成就。明人议论多驰骋空谈,史学成就粗鄙,徒令王世贞之辈以文士博得史家名分,令人不胜感慨。面对扰攘纷繁的史学乱象,有识者扼腕而叹。钱谦益说:“国家重熙累洽,度越汉、唐,而史事阙如,此亦学士大夫之辱也。”(63)当朝各项事务都超迈前古,唯独明代史学如此粗鄙,不足以垂范后世,真是文士大夫的莫大耻辱。 历史召唤着新型史学形态走向历史前台。 2.“史氏失职,以故野史甚多”:官史与民史此消彼长 “史失则求诸野”是对修史权力由庙堂向民间转移最为精当的表述。喻应益疾呼:“史失则求诸野,则野史之不可已也久矣。殆亦天之所必存,以留是非之权于万世者也。三代而后,国家之盛、是非之明,未有隆比我明者,故野史之繁,亦未有多于今日者。”(64)明代史学呈现出一种官史不振、民史崛兴的特征,表现在史权下移,“是非之权”散落民间:从史书的视角看,反映世风民情的野史笔记繁盛;从史家的视角看,涌现于民间的贫士寒儒纷纷执笔操简,以史职自任。 官史废失为民史崛兴提供了机遇。沈德符认为:“本朝史氏失职,以故野史甚多。”(65)王世贞也认为:“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也……当笔之士或有私好恶焉,则有所考无所避而不欲书,即书,故无当也。史失求诸野乎?”(66)文震孟同样意识到:“实录间亦有未实者,于是野史竞作。”(67)顾炎武不仅认清这一点,还做了更加翔实的诠释: 国初人朴厚,不敢言朝廷事,而史学因以废失。正德以后,始有纂为一书附于野史者,大抵草泽之所闻,与事实绝远,而反行于世,世之不见实录者从而信之。万历中,天子荡然无讳,于是实录稍稍传写流布,至于光宗而十六朝之事具全。然其卷帙重大,非士大夫累数千金之家不能购,以是野史日盛,而谬悠之谈遍于海内。(68) 官史与民史是此消彼长、尔强我弱的。崛起于山野市井之间的民史趁官史不振而表现出勃勃生机,反过来又对官史造成强烈冲击。“野史日盛”导致“谬悠之谈遍于海内”只是顾炎武的价值评判,姑且置之不论,但官史废失、实录流布民间给民史崛兴创造了条件,当是确凿无疑的。相比之下,作为文士的祝允明对民史的评价更为公允,他说: 盖史之初为专官,事不以朝野,申劝惩则书。以后,官乃自局,事必属朝署出章牒则书。格格著令式,劝惩必衰。又以后,野者不胜,欲救之,乃自附于稗虞,史以野名出焉。又以后,复渐弛,国初殆绝。中叶又渐作,美哉,彬彬乎可以观矣。(69) 官史繁文缛节、劝惩不力束缚了史学发展,民间史家十分忧虑,做出不懈努力且甘愿被边缘化。民史适应了史学生态,表现出勃勃生机,此自然之理。晚清民国的刘咸炘曾论:“国史取详年月,野史取当是非”,“真治史者欲贯串一代之风,势必更旁求他书。若徒执正史,非独不足,即所有者,亦晦而不明。吾尝言读《明史》不如读《野获编》,非激论也。”(70)钱锺书也认为,民间史家“自具识见,不为朝报所惑”,民间史著“觇人情而征人心”、“光未申之义”,民间史学繁盛恰恰是“史失而求诸野之意,所谓‘路上行人口似碑’也”。(71) 在晚明史学生态中,野史固然不能取代国史作为“大历史”的地位,却以其强劲的生命力捍卫着民间知识群体的史学话语权。晚明史学生态以国史为主、野史为次的观点或可勉强成立,来自政府档案典册的国史比来自民间传闻的野史可信得多的观点却有待商榷。至于以国史“秘之金匮玉函,以传万世之信,所重在于尊藏”,“天下臣民无由得见”(72)为由认为国史秘而不宣是导致野史乘虚疯长的主要原因的看法,并不符合事实,也未看清中国史学发展大势,忽视了野史崛兴的深层动因。 晚明史学具有野史化的特点。野史并非只有“补正史之阙”(73)的作用,还是一种可以独立存在的史学形态,甚至可以凌驾于颇富政治意味的正史之上。事实上,野史比正史出现的更早,生命力更强。民史繁盛、草野寒士分割在朝史官的史权,与史权由庙堂之上转移到草野之间的趋势是一致的,具有深刻的历史合理性。早在衰周之际,就出现了史权由天子而盟主继而列国的现象,秦汉以后部分地流落民间。其实,具有卓识的明人已经隐约意识到这一史学发展趋势。王世贞说:“周衰而天子之史不在周,而寄于齐、晋之盟主。盟主衰而又分寄于列国,国自为史,人自为笔。至秦务师吏斥百家,而史亦随烬矣。”(74)焦竑也认识到:“古天子诸侯皆有史官,自秦汉罢黜封建,独天子之史存,然或曲而阿世与贪而曲笔,虚美隐恶,失其常守者有之。于是岩处奇士,偏部短记,随时有作,冀以信己志而矫史官之失者多矣。”(75)唐、宋以后,伴随着平民化趋势加剧,史学发展也开启了平民化之路。野史笔记在晚明崛兴实际上是对史学平民化的适应,因而生命力强劲。而没有顺应这一趋势势必导致是非多出:“周秦以来,史臣有专职,亦有专述,故其官与业交相劝也。明之史臣夥矣,大概备经筵侍从,既夺名山之晷,而前后有所编摩,俱奉尺一,其官如聚偶,其议如筑舍,非正三公而埒入座者,不得秉如椽焉。”(76)史权下移,官史让位于民史,史学的官方性格演变为民间性格,实乃史学发展内在理路使然,势不可挡。 三 余论 不少晚明野史家往往把野史撰述视作为朝廷修纂国史做准备。他们希冀朝廷重视野史保存的史料,并企盼由朝廷出面组织编修国史。王稚登评价《戒庵老人漫笔》:“足以代董狐之笔……异时天子开石渠、虎观,诏诸儒撰一代正史,是编宁能舍旃?”(77)陈文烛为《弇山堂别集》作序时即称:“异日有裨于国史者最其大也,耆儒考证其次也,宾筵以资谈谑特其余耳。”(78)浓烈的国史情结直到明清易鼎仍未消退。号称“古藏室史臣”的遗民史家抱着“国史既亡,则野史即国史”(79)的理念,在艰险环境下不避斧钺,保存史料,以备有朝一日修纂国史者采择。倘若明廷处理得当,官方史学大器晚成,或未易量。遗憾的是,不断恶化的形势并未给在野史家群体更大的施展抱负的空间。由于缺乏一种人人皆可俯仰于恢阔之境的自由空气,史家凛然于政治的严酷而不敢奋笔写史,“史学天才,如燕居危巢之中,鱼游沸鼎之上,从容写史,势不可能”(80)。 清初野史一仍其惯性得以秉承晚明余烈,这当与鼎革之际民族情绪高涨息息相关。明清易鼎之后,清统治者为文饰太平而设馆修书,广纳博学硕儒入其彀中,包揽浩大的文化工程“以笼络才智之士,广其卷帙,厚其廪饩,使卒老于文字间耳”(81),甚至暴力推行“文字狱”。这是对唐宋以来史学进步趋势的倒行逆施,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知识者的思维路向,也操控了人们的历史记忆,更误导了未来数百年间中国史学的走向。随着文化专制近乎恐怖的强化,史学平民化趋势遭到阻滞,史家主体意识淡化,这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史学的发展路径。明季野史泛滥在为自己掘墓的同时又为随后的乾嘉考据之风奠基。之后学术几乎一切皆是模拟、复古,缺乏明之前那种创造精神,后来“在西洋科学的影响下,中国学术界不论是经、史学,或文、哲学,都被披上了一件科学的外衣,究其实际,仍然不能脱离清代考据学的窠臼”(82)晚明野史笔记的现实性、批判性和进步性品格突出地表现在“举刺予夺”的特征上。这一特征延续宋代以来注重褒贬的史学风气,有助于彰显史家主体意识,最终却因保守因素的桎梏而跌入低谷,反映出传统史学“巫魅”之深重,中国史学现代转型依然任重而道远。(83) 注释: ①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82页。 ②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1《叙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页。 ③孟森:《心史丛刊·序》,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页。 ④梁启超、朱希祖、鲁迅、邓之诚、孟森、谢国桢等前辈学人贡献较大。其中,用力最勤、成就最大者当推谢国桢。他早年即开始整理、研究晚明野史,相关著作除《明末清初的学风》外还有《增订晚明史籍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明清笔记谈丛》(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等。 ⑤有关晚明野史笔记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姜胜利:《明代野史述论》,《南开学报》,1987年第2期;王树民:《从史学谈明清小说野史的价值》,《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谢贵安:《论明代国史与野史的生态关系》,《学术月刊》,2000年第5期;孟德楷、于瑞桓:《简论实学思潮对明清野史的影响》,《东岳论丛》,2012年第12期。关于野史的综论性研究成果主要有:瞿林东:《杂谈正史和野史》,《江淮论坛》,1982年第3期;陈力:《中国史学史上的正史与野史》,《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瞿林东:《说野史》,《齐鲁学刊》,2000年第1期;雷戈:《史失求诸野——中国古代野史观念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⑥单磊:《晚明野史笔记繁盛的历史合理性》,《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0期。 ⑦[德]格罗塞著,蔡慕晖译:《艺术的起源》,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81页。 ⑧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版,第63页。 ⑨[清]张廷玉等:《明史》卷67《舆服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40页。 ⑩[明]郎瑛:《七修类稿》卷10《国事类》,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97页。 (11)[清]张廷玉等:《明史》卷69《选举志一》,第1687页。 (12)[清]张廷玉等:《明史》卷81《食货志五》,第1975页。 (13)[清]叶德辉:《书林清话》卷8《宋元明官书许士子借读》,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23页。 (14)陈宝良:《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5页。 (15)赵子富:《明代学校与科举制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第294页。 (16)[日]沟口雄三著,索介然、龚颖译:《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9页。 (17)刘梦溪:《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81-82页。 (18)[明]颜钧:《颜钧集》卷4《道坛志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1页。 (19)[日]沟口雄三:《俯瞰近代中国》,《读书》,2001年第9期。 (20)[清]叶德辉:《书林清话》卷5《明人私刻坊刻书》,第142页。 (21)[明]于慎行:《谷山笔麈》,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1页。 (22)[德]G.弗兰克著,刘北城译:《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页。 (23)[美]约书亚·梅罗维茨著,肖志军译:《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7页。 (24)“超越前代”是明中后期一股重要的思潮,董谷、刘仕仪、谢铎、陆容、张燧、王世贞、陈继儒、谈迁等皆有相关言论。详见郑克晟:《论董谷刘仕义之明朝超越前代说》,见《明清史探实》,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6-344页;杨联陞:《朝代间的比赛》,见《中国语文札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2-155页;吴士勇:《制度、琐节与反思:明代文人笔下的国朝胜事》,《历史教学问题》,2012年第5期。 (25)[清]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90《制科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869页。 (26)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83页。 (27)单磊:《晚明布衣修史现象研究》,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28)[明]郎瑛:《七修类稿》卷13《国事类》,第136页。 (29)[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20《史乘考误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61页。 (30)[明]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8《史料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31)[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实录难据》,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1页。 (32)[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51《史部·杂史类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33)[清]夏燮:《明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页。 (34)邓之诚:《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序》,见董其昌辑:《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卷首,燕京大学图书馆藏清钞本1937年影印本。本条史料蒙同门师兄王呈样博士提供,谨此致谢! (35)[清]张廷玉等:《明史》卷219《张位传》,第5777页。 (36)[清]夏燮:《明通鉴》,第2579-2580页。 (37)《神宗实录》卷264“万历二十一年九月乙卯”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 (38)《神宗实录》卷305“万历二十四年十二月乙亥”条。 (39)详见李小林:《万历官修本朝正史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0)[日]内藤湖南著,马彪译:《中国史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15-117页。 (41)[唐]刘知几著,[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90页。 (42)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11页。 (43)[明]王鏊:《震泽长语》卷上《官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7页。 (44)[清]谈迁:《国榷·自序》,见《国榷》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 (45)[清]谈迁:《枣林杂俎》,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26页。 (46)[明]焦竑:《澹园集》卷4《论史》,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9页。 (47)《熹宗实录》卷55“天启五年正月癸酉”条。 (48)[明]焦兹:《澹园集》卷4《论史》,第19-20页。 (49)[清]谈迁:《国榷》,第5页。 (50)[明]祝世禄:《序一》,见黄光异:《昭代典则》卷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51)[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38《万先生斯同传》,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87页。 (52)[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14页。 (53)刘咸炘:《刘咸炘论史学》,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15页。 (54)李振宏、刘克辉:《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6-122页。 (55)苏同炳:《明史偶笔》,台北:“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87页。 (56)[明]李建泰:《名山藏序》,见何乔远:《名山藏》卷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57)赵尔巽等:《清史稿》卷501《谈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863页。 (58)[明]张岱:《石匮书自序》,见《石匮书》卷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59)[明]黄宗羲:《明儒学案·发凡》,见《明儒学案》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60)[明]黄端伯:《瑶光阁集》卷6《函史序》,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版。 (61)[明]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亭林文集》卷2《钞书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0页。 (62)[明]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8《皇明琬琰录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63)[清]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90《制科三》,第849页。 (64)[明]喻应益:《国榷·喻序》,见[清]谈迁:《国榷》卷首。 (65)[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5《私史》,第631页。 (66)[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第361页。 (67)[明]文震孟:《傃庵野钞序》,见[明]蔡士顺:《傃庵野钞》卷首,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 (68)[明]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亭林文集》卷5《书吴潘二子事》,第114-115页。 (69)[明]祝允明:《寓园杂记序》,见[明]王锜:《寓园杂记》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 (70)刘咸炘:《刘咸炘论史学》,第211-213页。 (71)钱锺书:《管锥编》第1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443页。 (72)谢贵安:《论明代国史与野史的生态关系》,《学术月刊》,2000年第5期。 (73)[明]杨慎:《升庵集》卷47《野史不可尽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4)[明]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116《国史册》,万历五年(1570)世经堂刻本。 (75)[明]焦竑:《国史经籍志》卷3《史类·杂史》,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76)[清]谈迁:《国榷·自序》,《国榷》卷首。 (77)[明]王稚登:《王稚登序》,见[明]李诩:《戒痷老人漫笔》,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54-355页。 (78)[明]陈文烛:《弁山堂别集序》,见[明]王世贞:《弁山堂别集》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79)[清]古藏室史臣:《弘光实录钞》,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75页。 (80)杜维运:《中国史学史》(第3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669-671页。 (81)张舜徽:《广校雠略》,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 (82)蒙文通:《中国史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8页。 (83)单磊:《“举刺予夺”:明季野史笔记的重要特征》,《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标签:历史知识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历史论文; 历史书籍论文; 明朝论文; 野史论文; 读书论文; 历史学论文; 晋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