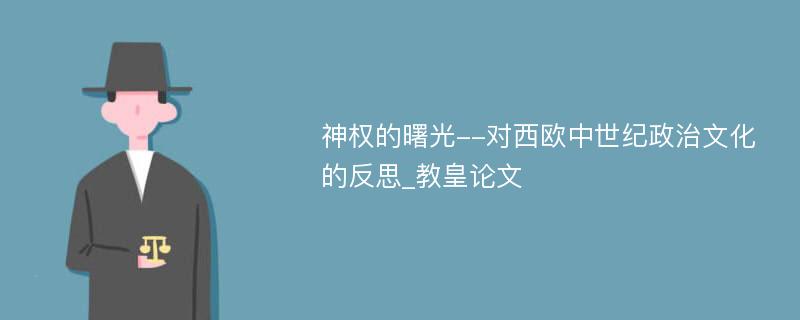
神权政治中的民权曙光——对西欧中世纪政治文化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欧论文,政治论文,曙光论文,神权论文,民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13文件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7712(2001)02—007—05
西方中世纪是上帝统治的时代,也就是说,“上帝,作为绝对的唯一,先于并高于世界上所有的多,他是一切存在的唯一源泉和唯一目的。”[1](P9 )一切权力,包括教会权力和国王乃至皇帝的权力,都源于上帝。关于这一点,在《圣经》中多有隐喻。耶稣曾对彼得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2](第16章第18 节)作为中世纪社会的思维范式和基本话语的圣经影响的程度之深和范围之广,都说明人们对权力源于上帝这一基本观念的普遍认同。神权政治在中世纪有着不可挑战的地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尽管如此,我们却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中世纪神权政治是一种纯而又纯、不掺拌任何“杂质”的政治观念。因为,无论是从中世纪文化的多元性、中世纪社会组织的复杂性,还是从处于整合之中的中世纪政治思想的矛盾性来审视,神权政治观无论是在逻辑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不是无懈可击的,也就是说,中世纪的神权观念中涵蕴着自我否定的矛盾因素。或者说,在中世纪神权政治的外衣下,还包藏着其他权力观念,这些观念随着教会圣光在教、俗冲突中的退去,逐渐“露出水面”,并成为预示西方近代人民主权思想的曙光。可以说,在中世纪政治文化的地平线上,近代民主政治思想的曙光已依稀可辨。
西欧封建社会政治关系蕴涵着民权观念的原始“胚胎”
西欧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是从日耳曼人侵入罗马帝国的版图开始的。美国著名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家汤普逊指出,中世纪西欧封建制度的主要性质是由罗马人所贡献的财产关系和日耳曼人所贡献的人身关系混合而成的。正是具有这种特质的封建制度使早期过度的、野蛮的个人主义转化为服从法律和秩序的精神,具体化为宗主权、附庸地位、忠诚、服务和契约的权力与义务的制度。[3](下,P325~327)其中,契约观念乃是“蛮族”注入中世纪社会肌体的最重要的“激素”之一。这一观念不仅成为西欧中世纪封建社会政治关系中所特有的文化内涵,同时,它还随着西欧封建化运动向纵深展开而在西欧基督教世界普遍流行和广泛传播。在这一运动中,土地的封授过程包含着两种逆向性关系:不动产——土地的使用权自上而下的移交关系和附庸自我保护权自下而上的转移关系。也就是说,土地封授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处于这种关系之中的“上级与下级”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性界定过程。在西欧社会的封建关系中,“领主的主要职能是提供每个社会必须生产的公共产品——保护和公正,而佃农和农奴则部分靠他们自己的财产、部分靠领主的财产提供劳动作为交换。”[4](P39)可以说,领主的保护义务与附庸的服从及其他义务具有对等性。这种保护与服从的关系是受“具有无上权力的惯例”所强制规范的。这一点在一度盛行的“请求让地”的协定中也十分清楚地表现了出来——土地的转让以获得人身安全和其它权利的保护为前提。可见,在西欧中世纪,人们对领主的服从是有条件的,这一条件本质上蕴涵着领主的管辖权受托于被管理者的观念。总之,权利和义务共生对等的观念潜在地否定了绝对专制权力的可能性。即使在神权政治思想甚嚣尘上的时期,权力以被统治者的“普遍同意”为基础这一集体“无意识”始终存在。西欧封建社会的这种统治与服从关系中的文化内涵不仅自始至终以习惯法作为其载体,而且有相应的强制措施为其后盾。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在西欧封建社会的“语境”中,根深蒂固的契约观念涵蕴着如下思想倾向:(一)权利与义务是不可分的,只享受权利而不承担义务,或只承担义务而不享受权利对日耳曼人乃至整个西欧中世纪社会来说,大概是陌生的。尽管西欧的封建领主享有行政、司法乃至铸币权,但是,中世纪的法律却尚未被当作人们主观意志的表达,它被看作是一种只能被发现、而不能被制定的客观存在。人们普遍遵循的习惯法具有不可变动性,因此,封建领主也就不可能为所欲为,因为任何践踏法律的尝试往往意味着损失财产的风险。(二)自上而下的统治权的行使是有条件的,即:对处于这种封建关系中的被统治者人身安全及其他权利的保护。那么,反过来讲,对人身安全等基本权利的破坏便意味着统治权力的丧失。如此一来,一种强制性的权力似乎原本存在于社会个体成员的手中。(三)任何契约都是以对契约主体双方的某种平等权利的理念设定为前提的,因此可以说,西欧封建关系中的契约原则本质上就蕴涵了中世纪社会对人与人的某种自然平等关系的普遍承认。从这一视角来透视,任何权力的存在及其行使都是以民众的同意为基础的。换句话说,统治者的统治权是民众所赋予的。当然,这只是我们对涵蕴于西欧封建“语境”中契约观念的内容进行历史和逻辑的解析所得出的结论,至于这一观念内涵在社会主体意识中的清晰程度以及人们将其从观念的形态转化为实践形态的广度、深度及其自觉性则由于具体历史时空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但是,作为近代民主政治的原始“胚胎”的民权观念早就存在于中世纪社会的契约观念之中当是无可置疑的。
古罗马文化中涵蕴着民权观念的“基因”
罗马法是古代社会留给中世纪的文化遗产之一。在中世纪社会的后期,不少王权派思想家大量援引古罗马法为国王独立于教会的权力进行论证。然而,对罗马法的研究表明,这一庞大的文化遗产,犹如一个巨大的“采石场”,可从中提取的原则和原理各种各样,五花八门。那些为着绝然不同政治观点辩护的人都能从中找到所需要的支持性证据。[5](P47)英国学者梅因指出:“在西方世界中每一个国家的平民成分都成功地击溃了寡头政治的垄断,几乎普遍地在‘共和政治’史的初期就获得了一个法典”。[6](P10)这一结论对罗马帝国是适用的。古代罗马法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从共和国到帝国的漫长岁月,其构成成分因而也就十分复杂:其间既积淀着共和国时期的民主文化,又包容着罗马帝国时期的专制主义原则。罗马安托宁时代的法学专家就指出,“每一个人自然是平等的”[6](P53)。这一观念在共和国宪法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那个时代,“平民会决议与法律相等同”[7](P191 )。在查士丁尼的《法律编纂》(Justiniun's cofidition)中记录着“关涉众人之事须经众人赞同”的立法原则。这些共和国时期的思想虽然曾经一度被帝国时期的皇帝专制思想所淹没,但是,在教、俗论战中,随着罗马法研究的复兴,“人人平等”的思想又一次被法学家们所“开发利用”。涵蕴于罗马法中的平等观念在政治思维中具有这样的逻辑推导结论:既然人人都是平等的,那么,一切针对人的统治权力就只能来自被统治者的授与。这一点,我们还能从罗马法学家的如下观点中得到印证,即:“皇帝的意旨具有法律效力,因为人民通过《国王法》中的一段话把他们自己的全部权力授予了他。”[8](上,P213 )尽管这一论断是对皇帝的至高无上权力的辩护,但是,皇权源于民众的观念却是异常清晰的。古罗马法学中这一要素之所以能最终以文化的形式而长期存在,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作为古希腊文化之末流的斯多葛主义中的自然法和自然平等观念在罗马的政治实践中为社会所认同;其二是在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政治实践中,这一观念借助元老院和公民大会的形式得以制度化、法律化。从以上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古代罗马传统与日耳曼文化有着某种“默契”,彼此之间存在着“对话”的基础。在政治社会中,这种自然平等观逻辑上蕴涵着主权在民的思想。在西欧社会政治生活中,无论是世俗权力的极端专制主义主张,还是教皇专制主义的要求,都因缺乏文化根基,往往仅如一阵“孤鸿哀鸣”,而难以得到社会的“和声”,因而专制主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只能是昙花一现。究其原因,我们很难不诉之于中世纪文化中深厚的民权意识积淀。
基督教文化中也涵蕴着某种民权观念的特质
从正统基督教的教义来看,一切权力都来源于上帝,人是上帝创造的,他们所具有的一切,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都是上帝所赋予的,当然,其权力只能是“二手货”。但是,基督教文化中却有两大因素为民权观念的存续提供了牢固的基础。其一是圣经中关于信众平等的思想,其二是早期基督教会的宗教实践史。《马可福音》第3章第31 节向人们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耶稣的母亲和兄弟来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兄弟在外边找你。 ’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 谁是我的兄弟?’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兄弟。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弟兄姐妹和母亲了。’”难怪,耶稣把他说话的对象称为兄弟姐妹,还要求他的门徒把他们传道的对象当作与其平等的弟兄姐妹。在原始基督教中,使徒与门徒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是一种帮助与被帮助、代表与被代表的关系。 [9](P147~148)在记录着圣灵启示的《圣经》中, 弥漫着一种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宗教气息,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人是作为上帝之子的平等,还是因为同犯原罪而平等,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的平等观念获得了一个稳定的神学前提。换句话说,在西欧中世纪的封建等级制普遍盛行的时期,基督教为人们的平等观念提供了某种栖息之所,在西方教皇大分裂之时,这种平等意识开始在教会生活中首先复苏,宗教大会运动就曾以其特有的形式展露过这种由平等观念所派生出的主权在民的朦胧意识。古代基督教史的研究表明,原始的基督教是“在主耶稣面前彼此相爱平等如弟兄的教会”[9](P169)。 在早期的基督教生活中,“信徒们过集体生活, 实行财物公有制……社团成员一律平等”[10](P38),“初期教会继承了基督教徒社团的组织形式……通过自然形成或公众推举逐步产生了一批有一定权威或某种特殊身份的教会领袖”[10](P50)。尽管在国教化以后, 以罗马教廷为首的教会开始逐渐走向腐化堕落,教皇也不断地尝试走向极权专制,但是,早期教会的宗教实践曾充分地贯彻过基督教的平等原则,而且,根据教会的制度,教皇从来都是由红衣主教选举产生的。这种存在于历史和现实中的基督教文化,足以启发人们思考上帝之外的另一种权力。这一“情结”在中世纪社会晚期人们抵抗教皇专制主义的时候曾表现为披着宗教外衣的民权意识。不仅宗教大会理论在神权政治的框架内对此曾予以较为全面的论证,在西方教皇大分裂(the papal schism)的历史关头,这种民权意识还通过教会代表大会的实践充分地表达了出来。
诚然,平等意识并不直接等同于民权意识,也不能无条件地转化为民权意识,尤其是在西方中世纪一切权力被认为是来源于上帝的神权政治时代。在神权政治的主流意识形态中,逻辑地涵蕴于人们平等观念中的民权意识往往处于一种朦胧的“自在”状态,它的觉醒及其从“自在”向“自为”的转化还有待于某种现实条件的刺激。而西欧社会的发展却戏剧性地为此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契机,从而使蕴藏在平等观念之中的民权意识终于获得了一发不可收拾的自我展示机遇。
这一历史性机遇是同教会与国家摩擦和冲突中的教、俗大论战以及西方教皇大分裂相关联的。在旷日持久的唇枪舌剑中,教权派和俗权派围绕着世俗权力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教权派中的一些思想家为了避开罗马教会这一在权力来源过程中的中间环节,他们把其目光从天国下移至凡世,在承认一切权力是上帝之权的“流射”这一神学命题的前提下,他们又在“此岸世界”的大众之中设定了一个与教会相对峙的“批准环节”。
研究西方政治哲学的著名学者奥托吉尔克曾经指出,在中世纪的观念中,无论是教皇还是皇帝都只是作为一个法人团体的首脑代表着团体的目标。皇帝不等于帝国,教皇也不是教会本身。作为一个共同体,教会或帝国都有与之不可分割的主权,这一主权由共同体“集体地”而不是“分散地”行使。到中世纪晚期,人们便逐渐开始认识到共同体的主权应该以正式组织起来的大会形式来行使。[1](P62~64)巴黎的约翰在为王权进行辩护时曾经这样写道:“王权的存在和行使都早于教皇的权力,法兰西国王的出现早于基督信徒。所以无论是王权还是王权的行使均不是源于教皇,而是源于上帝和通过选择一个人或一个皇室来选举一个国王的人民。”[11](P208)他认为,教会与国家之间并无联系,因为王权乃是通过人民的选举直接来源于上帝。他还特别强调,国王掌权是经过人民的意志所批准的。值得注意的是,巴黎的约翰不仅认为,国王的权力以人民作为其直接的源泉,就是教会的权力也不例外。他认为,教会的高级教士是从选举和通过人民的同意而取得其权力的,教皇的统治权可以由人民免除,因为教皇权力中的实质性成分是信徒的同意,这种同意在教皇愚蠢、无能和无用,或者他们认为有任何与此相关的原因之时,是可以收回的。[12](P203)根据研究西方中世纪政治思想的著名学者乌尔曼的意见,大致从14世纪上半叶起,这种自下而上的权力理论已经再也不是作为辩护性的措施被提出,而是作为一种能够为当时或后来困扰思想家们的问题提供积极的和具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案而出现的。[12](P218)
在西方教皇大分裂时期,为解决教皇的合法人选问题,教会以其实践的形式显示了人们民权意识的本能冲动,与此同时,思想家则为这一选举教皇的行为予以了理论上的论证,从而这种潜伏于整个漫长中世纪的民权意识在神权政治的框架之内得以昭示于众。
1303年,卜尼法斯八世去世。自此以后,在长时期内,教皇都不得不听命于法国国王。1305年在腓力四世的压力下当选为教皇的克雷门五世使教会法国化的努力,以及法国国王使基督教会服务于法国王权的企图引起了西欧基督世界的反感,加速了其他政治体民族国家意识的发育。从1318年到1417年,由法国和意大利争夺对罗马教廷的控制, 从1378年到1409年,在罗马和阿维农同时存在两个教皇;到1409年, 在意大利比萨举行的基督教大会上,又选出一个教皇,于是形成了1409 —1417年间,三个教皇同时并存的局面。1414年, 德意志皇帝西吉斯孟会同约翰二十三世召开宗教大会,这一持续四年的康士坦斯宗教会议废黜了既存的三个教皇,另选出新教皇马丁五世,结束了大分裂的局面。对教会史的这一简要回顾为我们提供了两个有用的信息:其一是国王们使基督教国家化或民族化的企图逐渐成为一种不可遏制的趋势;其二是教皇选举客观上意味着具体的教皇人选至少必须经过其下级教士的批准。诚然,根据正统的基督教教义,教皇是彼得的直接继承人,但是决定由谁来充当彼得的继承人的权力则在下级教职人员手中。可以设想,当神权政治的迷雾散尽后,主权在民的近代民主真谛就会自然而然的显露出来。一些思想家借助罗马法的社团法人概念以及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对民选教皇以及其权力做了较为系统的论证,其间也自然闪耀着民权理论的光芒。
“信徒的同意”自从早期教会起就被当作信条来引用,宗教法也规定主教必须由牧师经俗众的同意选出,基督教团体的某些活动应该得到其成员的同意。另外,罗马法文本中关于“关涉众人之事须经众人赞同”的原则都被用来为宗教大会运动的实践进行论证。中世纪晚期最具原创性的哲学神学家之一库萨的尼古拉(Nicolas of Cusa )的宗教大会理论就是建立在教会法学家关于“同意”的概念与基督教—新柏拉图主义关于宇宙“和谐的一致”相结合的基础之上的。这位思想家把教会与帝国的关系比喻为心灵和身体的关系,视教会与帝国、教士与俗人为基督社会中相互关联的不同部分,并把基督社会的理论基础建立在教会法、宇宙论和自然权利之上。他认为,无论是基督教的法律、世俗社会的活动,还是宗教大会的权威和所有的统治权力,都是立基于“同意”之上的,正是“同意”把自愿服从的臣民与合法的统治者结合了起来。他提出了三个重要观点:第一,法律的效力只能在它所施恩的对象的主观同意中才能继续存在下去……教会法植根于人们的自然权利。第二,制定教会法的权力在于宗教大会的“共同同意”:“违反这一结论,任何法令和习惯都不具有比违反这一结论所源出的神圣和自然的正义具有更大的效力”。第三,教会管辖权部分是由信众的主观同意并经神的权威的确认而设置的。在他看来,神的权威和公众的同意相互依存。主持圣事的权力和世俗事务的统治权力都是上帝所恩赐的,然而,行使这些权力的人必须由选举产生;公职是由上帝设定的,但是,由谁占有这些职务者必须由其臣民决定。[5](P583~584)
显然,在这位中世纪晚期的思想家的理论中,在统治者和上帝之间,存在一个中介环节,这一环节是民众而不是教会,更不是教皇。不仅如此,彼得与教皇之间不能直接地进行权力的交接,为此,宗教大会的理论家们在二者之间又安装了一个“中介程序”。这一中介环节的“插入”得到了上述三个因素的支持:日耳曼文化、罗马文化以及基督教文化。因此,从文化自身的逻辑来审视,我们能清晰地看到,整个中世纪的意识形态中始终渗透着以平等精神为基础的民权意识,随着教权与俗权的摩擦和冲突的不断展开与深化,这种意识逐渐从朦胧走向清晰;随着亚里士多德理论的传入,这种意识逐渐从一种零散肤浅的感性形态走向一种系统深刻的理性形态;随着市民社会的形成和不断发育,这种意识逐渐从一种模糊、“自在”的观念形态走向“自为”而生动的实践形态。如果说,这一概括基本正确,那么,神权政治中蕴涵着民权意识就是我们在以上分析中得到的逻辑结论。如果说这一结论基本正确,那么,我们同样有理由说,西方近代民主政治的曙光早在中世纪就已经出现在了历史的地平线上。在宗教改革运动和文艺复兴运动的洗礼中,随着基督教神权思想的迷雾在理性之光的驱逐之下逐渐从“此岸世界”的消逝,民权观念就自然而然的成为市民社会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一个重要武器,并由此而构成了西方近代民主政治观的前奏。
收稿日期:2000—7—21
标签:教皇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西欧中世纪论文; 政治论文; 中世纪论文; 基督教教义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民权运动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