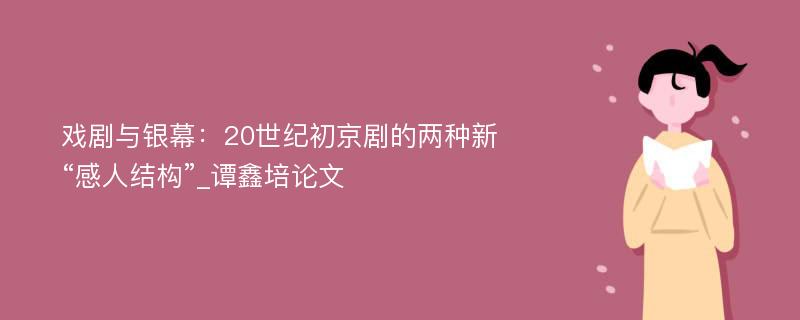
剧院与银幕——20世纪早期京剧两种新的“感触结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京剧论文,银幕论文,剧院论文,感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视点并不等同于历史叙述。历史叙述的工作是史料的搜集、印证和重组,追踪过去事情的来龙去脉,是大规模的研究工程;历史视角固然也以认真的态度去对待史料,但目的在于为过去某个事件建立一种历史感,以历史叙述为基础,把过去的事情放置回到历史潮流之中加以观照、诠释,发掘事情与当时社会之间的历史性关系。本文的规模无法作历史叙述,而是尝试采取某种历史视点,给京剧在20世纪早期的两个重要现象(由茶园入剧院、从舞台至银幕)建立一种历史感。本文引用的历史资料包括20世纪早期中国社会史及该时期的京剧发展史,这两方面,不少前辈已作了严谨的研究和精辟的分析,本文有幸以为基础。
一、主导理论
戏剧形式和内容的关系这一命题从来就让不少理论家大感困扰,但英国文化、戏剧、媒体理论家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他的著作《戏剧自易卜生至布莱希特》(Drama from Ibsen to Brecht)短短二十多页的引言中,便解决了这问题。他认为关键在于,形式与内容两者均由社会生活派生出来,但形式多了一个维度,就是“传统”。汉语“传统”是个含义很广的词,英语则分别用两个字指涉这丰富的意思,一是“tradition”,二是“convention”,两者含义很相近,但前者强调价值观念及行为模式代代相传的延续性,后者则着重群体对事情达成共识而产生的行为准则,特别指艺术及文化创作上形式的规范性①。威廉斯认为剧场的形式传统(convention)亦有着时间维度,因此每个创作行为也是面对整个传统(tradition)的行为,个中关系十分多样,可以是规管、反叛、改革等。
威廉斯认为,支配每次创作行为的,有很多不同因素,形式传统固然先给内容的处理和发挥定下一个框架,但同时影响创作人的还有很多因素,威廉斯把这些因素的总和形容为“感触结构”(stucture of feeling)②。“感触结构”是人每天对社会现实生活的感官触觉和思考内容,以及在个人意识中形成的总体经验结构,这结构又根据生活体验不断改变。强调经验是结构的,目的在于凸显它既在个人意识中结成总体,同时又保持内部的多元,甚至可能潜藏矛盾。在艺术作品中,每一笔、每一字、每一音、每一视、每一动都来自当下的“感触结构”,每次创作行为都牵涉创作人当下的经验结构的内部整合,新体验被纳入使得已有的“感触结构”更加丰富,但也可能与形式传统中某些成分所暗示的经验或价值不吻合,造成“感触结构”的内部矛盾。一些精湛的艺术形式,建立了几乎天衣无缝的美学程式,它的规范性亦来得强而有力,往往把与创作当下的那一“感触结构”中不吻合的成分压抑住,久而久之,发展成一个超稳定的系统。可是,假如“感触结构”中越来越多的东西被超稳定的形式压抑,换句话说,就是生活中越来越多的经验未能在这些作品中表达出来,那么,不管这一形式有多精湛,也逃不过与当代社会现实相脱离、被观众离弃的命运。当然,并非所有精湛的艺术都这样,有些艺术形式虽然拥有精细微妙的美学系统,不断受到不同作品创作当下的“感触结构”中新成分的冲击,但是这些美学系统具有弹性,能够做出自我调整,不断更新,于是成功地表达了当下的“感触结构”,与当代观众产生了强大的深入心灵的共鸣。芭蕾舞就是一个好例子,它的形式有清晰的架构规条,但又不断吸纳20世纪对身体的思考潮流,于是能够产生前卫的杰作,表达两次大战及其后人们对脆弱可朽肉身的思考,震撼世界舞台。另一个好例子是莎士比亚戏剧,莎剧的结构与当时的表演形式结合无缝,我们今天只读剧本,也可粗略感受到作品的剧场性,从而理解这戏剧系统中剧本与演出之间统一完整的关系;莎剧之所以能代代更新,永远赢得当代观众同理心的亲近,除了因为剧本主题具有普世性、对人性的发掘极为深刻之外,更重要的是因为伊丽莎白时期的戏剧表演美学系统十分开放,因此,莎士比亚的剧本虽然盛载着这独特的戏剧程式,但每代每位导演几乎都能在这系统之内找到空间,加入创作者当下的“感触结构”,与剧本内部的传统因子进行互动,碰激出奇异的艺术火花。
20世纪早期的京剧就享有相当优势,它承继了徽调、汉调、昆曲等传统戏形式以及戏曲作为一个戏剧体系的表演程式,因此,它的美学系统丰富、复杂、多样、紧凑、完整。同时,自徽班晋京,几种地方戏杂交形成京剧,它自身的程式和美学系统开始慢慢稳定下来,但它的美学体系仍然是开放的。因此,在20世纪早期中国翻天覆地的“西潮”之中,它毫不犹豫地与当下社会的生活经验进行互动,做出内部的美学调整,有效地表达当下的“感触结构”,所以能够感动观众,成为颇受欢迎的文化娱乐节目。
二、由茶园至舞台
西方剧场建筑传入中国以前,京城里京剧的主要演出场地为酒馆、茶园及会馆。直至19世纪中期,戏曲演出场地几乎在八百年内保持了基本的面貌——勾栏的基本空间关系③。茶园舞台光光,观众出入走动自如,演出时除了台上的戏外,还有其他茶客谈笑吃糕点、小二沏茶答应,看戏经验的不仅是表演内容,简直是声色味的万花筒,戏里戏外的官感经验不断渗透、交错,演出本身难以隔绝在演出环境之外。虽然19世纪以后,演出场地继续演变,茶园在演出时已不再设宴,但仍侍奉茶水糕点;到了19世纪中叶,桌子横排,与舞台平行,椅子设在桌的三面;有些戏院设长方桌,对面长条板凳,座位价钱根据与舞台的距离而定④。这些设施上的改变固然使观众更舒服,也有利观戏,显示了观看表演在整个观剧活动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但观众的参与模式基本不变,还是走动自如,看、吃、喝、讲,观剧的感官经验与旧日分别不大。
开始给观剧经验带来改变的,是20世纪初的科技发展,首先是灯光和音响的改变。灯光对演出场地的空间及距离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旧式茶园夜间照明全用煤油灯,台上台下一致,光度一样,空间感也如出一辙。音响方面,茶园内活动繁多,人声喧杂,也没有规矩要求观众静音观戏,演员歌声、乐声混在台下各种声响之中。总的来说,茶园的演出并不是一种隔离的、纯粹的美学客体,而是混合了日常生活衣食住行各种官感经验,看戏与谈生意,与吃、喝、会朋友等活动在同一时空内进行,观众在这些不同方面的体验也在意识中共时发生。这主流的观剧经验由勾栏到茶馆一直基本不变,直至1908年上海老生演员潘月樵、演员武生夏月润、夏月珊等,得到同盟会的爱国银行商人沈缦云支持,建成了中国第一座西方剧院建筑的京剧表演场地“新舞台”。
西方剧院在19世纪晚期进入中国,1874年,居沪的英国人为侨民建成剧院,内设镜框式舞台,观众席为三层,观众守则已与现时无大分别,包括购票划位、准时入座等。上海的一些京剧戏院跟风,采取了相似措施,从前最靠近舞台的坐位票价最低,此时改成票价最高,长条板凳从前与舞台成直角排列,此时改成平行排开,但这些措施未从根本上改变观众的观剧经验。可是,“新舞台”却给京剧定下了新的接收框架,彻底改变了京戏的观剧经验。戏院以混凝土建成,与传统木建茶园、会馆有极大分别,隔音和传音的效果都很不同。传统戏台上两条支撑大柱不复再见,“新舞台”设镜框式舞台,前有一小副台突出,又设旋转舞台,以电灯照明,而且采用地灯,打面光,强调台上演员的身体和面部表情,放大了舞台上的人物和物件,缩短了舞台上下的视觉距离,改变了观众对戏院空间结构的主观感觉。这样,从前京剧观众熟悉的空间感完全改变了。前台的改变也很惊人,设售票处,观众划位凭票入座,场内不卖小食、饮品等⑤,入场纯粹观戏。上海不少戏院纷纷根据“新舞台”改装,尤其是舞台技术部分;在其他主要城市,也有新建的新式剧院,或旧院改装。在北京,直至1921年,才落成第一所新京剧剧院,剧院既演京剧,也播放电影,因此,院内可全暗,完全隔绝光线,采用电灯照明。
这样一来,京剧完全给置于西方观剧模式之中,这模式与茶园、会馆大不相同。首先,观剧环境净化了,没有吃、喝或其他丰富的人事及活动,观众的注意力被提炼得更集中,同时,演出与观众的其他方面活动完全分隔开来。观众在大堂或门外买票,划好位子,做好心理准备,手拿着票走过剧院大门,有些剧院甚至设走廊甬道,观众走过,心理上放下剧院外的世界和纷扰,就像一个净化仪式,准备投入演出的世界里。在旧式茶园、会馆里,观众不仅五官感受大调和,戏里戏外的世界也不用分明。因此,现代剧场建筑可说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京剧观众的观剧意识和经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舞台”的原意是以国资企业抗衡当时在上海日渐强势的外资力量,可是让京剧从此进入西方剧院建筑的美学框架,本来为了抗衡西方势力在中国的扩张,反而成了催化剂,使中国观众的观剧意识受到西方模式的同化。
其实西方戏剧也不是从来如此。16、17世纪莎士比亚的“环球剧院”无论结构和习惯都与中国的茶园有点相似,但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工业资本主义进一步要求劳动力大规模分工,中产阶级在数量上和社会地位上都变得越来越重要,剧场提供指定的人工环境,把生活其他方面分隔开去,作为工余的消遣娱乐。到了19世纪,欧洲工业革命把工业资本主义推至高峰,人力资源的分工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社会上各种活动的模式进一步服务这样的秩序,剧场也不例外,高度人工化的剧场环境把观众的感官世界完全掌握,更吻合劳动力高度分工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秩序。这当然不是说西方所有剧场作品都单一地为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秩序服务,我们熟悉的左拉、易卜生,甚至布莱希特,就是利用了这样的剧场条件,以剧场手段,把观众的注意力调校到预设的地方上,强调社会某些现象,引导观众做出反省。但这种批判性的剧场需要其他配套才能生存,包括观众层面的多样化,有足够数目的知识分子重视剧场的社会及政治功能,以及政治体制能够容忍艺术对社会做出批判等等。
传入中国的,就是在这劳动力高度分工制度下产生的剧场建筑,任何建筑作为内里活动的载体,必定在结构和设施上与这些活动有所互动,互相改变。剧院建筑是剧场体制中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现代剧场盛载的戏剧作品诉说着人力高度分工的“感触结构”,建筑上固然也引起观众的官感高度分工。可是,京剧的观赏习惯原本不是这样,怎么会接受这样的改变,而且渐渐变成主流呢?
原来19世纪末西方剧场传入中国这现象,必须放置在整个中西关系上去观照。在当时国势强弱悬殊的情况下,中国先企图输入西方的坚船利炮,后来在学习西方政治和社会模式的过程中,也不得已改变生产体制,农村的农耕并小规模手工业自给自足经济破产以后,流入城市的人口从事低技术工作,这样的劳动力在初期的制造业中也渐渐形成高度分工,生产力的分配及运用与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模式逐渐接近;人们的思考方式,以及他们的官能意识也逐渐改变,有些思想及官能活动属于工作以内,有些则属于工作以外,白天上班赚钱,晚上到新式剧院看戏。在剧院外街道上走过,小贩叫卖,小食茶香刺激着他们的嗅觉、味觉;进入剧院大堂,在售票处购票划位,心理上作好准备,走过甬道,进入观众席,人工灯光和隔音设施把外面的世界隔绝,大幕一启,台灯一亮,观众席灯光虽不全灭,却也暗了下去,足以把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到舞台上去;刚才活跃的味觉、嗅觉此时钝了下去,视觉、听觉取而代之。看毕了戏,三五知己走在街上,谈笑议论刚才角儿的风姿,才大大启动了社交意识。这种意识活动的分工、分类和分时,配合了中国城市在20世纪初急起的工业资本主义系统重新调配及整合劳力资源、塑造人力的模式。京剧进入西式剧院,观众的思考和官能高度分工,应和着当时社会生活的“感触结构”。亦由于这样的剧场内与剧场外观众经验的“感触结构”相似,这种新的剧场建筑和观剧习惯便显得顺理成章,渐渐变成主流。
除了观剧过程中的官能分工外,京剧在其他方面也向这新的社会秩序靠近,在整个戏行里,不同方位也看到相应的改变。以戏班内部分工为例,由于新式舞台的创作空间宽松,舞台机器又容许多样式的尝试,京剧舞台设计便变得复杂,“新舞台”就聘请了日本舞台设计师负责,这样的舞台已不是习惯了处理一桌两椅的班中师傅能够照顾的。此外,剧院的运作规模和方法与茶园、会馆不可同日而语,与剧院合作,可以想象戏班中的行政、财政、宣传等工作也变得复杂。前台的工作程序和方法也与旧式演出场地不同,在这种西式剧院,售票处卖票的售票员小姐可能从不进场看戏。从前比较自足圆满的班子运作模式,此时已不再可能。
更根本的改变在于训练模式的转变。欧阳予倩1918年在日本发表文章,提出戏曲训练体制的改革⑥;1930年,焦菊隐任中国专业戏曲训练学校第一任校长,改革课程,设专业及文化教育两大科目,首先在意识上把专业知识生活及其他个人发展所需的知识分开,换句话说,就是工作和生活二分。在不少其他类似的戏曲训练学校,也禁止要求学生从事与专业训练无关的粗重工作。这些课程和规则,固然是为了改善学员的生活和素质,杜绝旧戏班学徒制可能出现的剥削、甚至虐待的情况,而采取的手段是“专业化”,就是在意识上把专业与生活分开。而且以后学院分科日渐变得专门,与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力高度分工完全吻合。总结来说,20世纪初期京剧业的内部分工,及在西式剧院内观剧经验的官能分工,实在是当时中国城市迈进西式工业资本主义体制的一环,是人力作为生产力变得高度分工这整体过程中的一部分,无论是训练、制作、观赏等各方位的京剧活动,都表达了人们在高度分工的生活状态下的“感触结构”。
三、戏曲电影
随着西方文化传入中国,改变观众观剧经验的,不仅是西式剧场建筑,电影传入中国,也给了中国民众一种新的戏剧载体,成为他们新的世界观的一部分,改变了他们观看故事叙述的方法和习惯。人们一旦适应了电影语言,对被观客体情景的空间、时间、速度,都有了新的期望;换言之,京剧电影与西方剧场建筑里演京剧一样,反映了同时亦影响了20世纪早期京剧观众的“感触结构”。
电影源于摄影技术,而摄影美学则延伸了现实主义绘画美学,因此早期人们对电影的思考一般循视觉艺术的路径,无怪电影一开始便企图制造现实主义效果,镜头内的景物充斥着生活中熟悉的物质细节,有时甚至以现实主义的手段表现超现实主义的内容。因此,电影故事与当时西方已成主流的现实主义戏剧在反映现实的思维上非常吻合。这实在并非巧合,19世纪西方自然科学的长足发展,使西方文明全盘倾向现实主义,主宰着视觉艺术、表演艺术、文学及其他文艺思维,这其实是当时西方的主流“感触结构”。
有记录的中国第一次电影上演为1896年8月11日在上海徐园茶楼,播出的是法国摄制的短片,此后在中国城市放映的欧洲短片越来越多,经常有魔术、烟花及民间艺术同场表演;1897年美国短片也进入中国市场,电影成为廉宜新颖的娱乐方式。第一个尝试在中国电影市场上分一杯羹的华商是北京丰泰照相馆的东主任庆泰;与建筑第一间西式建筑京剧院的沈缦云一样,任庆泰的初衷也是使“中国人用中国货”,制造国产货品,建立国产企业,以平衡当时中外之间严重的贸易差额,结果也与前者一样,反使中国观众的观剧文化更靠拢西方模式。
任庆泰最初拍摄的短片取材与西方早期短片极为不同,西片故事往往是日常生活琐碎趣事,如胖子在花园绊倒、美女在厨房熏得一脸黑等。任庆泰最初拍摄的,却是1905年谭鑫培在京剧《定军山》及《长板坡》中的一段表演;翌年他继续拍了另外六段短片,均为京剧选段。这批短片当然是黑白默片,最初在北京大观楼戏院播放,也属任庆泰产业,后来复制拷贝给东安、甚至江苏及福建一些戏院播放⑦。1909年,丰泰照相馆起火烧毁,任庆泰破产,他的京剧电影事业告一段落。至于同期是否有其他京剧电影及京剧表演纪录片,至本文完成之时,未发现有记录。
任庆泰以京剧选段为拍摄主题,显然是一个商业考虑,当时京剧是最受欢迎的娱乐艺术,谭鑫培又是名角,拥趸很多,影片拍了出来,不愁没有观众。影片的质素以电影美学的角度看来,似乎不怎么样;影片现已看不到,但根据资料,影片在丰泰照相馆的花园拍摄,照明全靠日光,演员身后挂一条白布为幕,摄影机架在演员正前方,一个长镜头贯穿全片,片中有中断接片的地方,乃是拍完一卷胶卷更换新卷之处。据看过影片的人忆述,片中人物的影像起初尚算清晰,可是随着他大刀舞动,画面却有时只见大刀不见人,另一些时候则只见靴子或靴子上袍甲的底部⑧。
在拍摄电影之前,谭鑫培已为法国百代公司的中国分公司灌制过唱片,因此在全国其他城市,有些没看过他演出的观众,不仅在新闻纸或娱乐杂志上看过他的新闻和照片,也听过他的录音。而且自19世纪后期,中国有了铁路,交通发达,京剧班子巡回演出,也不仅是京、津、沪等大城市之间的事,角儿到其他地方演出,或是观众到京、津、沪旅游观剧,已属常见;京剧实在是当时发展最蓬勃、流传最广的戏种,谭鑫培等角儿,拥有支持者遍及南北城市。
除了丰泰与谭鑫培合作的短片外,早期的中国电影不少是娱乐性短片,但较为重要、又有系统制作的,则要算是新闻短片和纪录短片。当时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文化机构商务印书馆也拍摄了许多新闻片和纪录片,而且在1920年,与梅兰芳合作,拍摄了戏曲短片。首先拍摄的是《牡丹亭》中“春香闹学”一折。根据梅兰芳忆述⑨,春香出现第一个镜头是特写,他先以扇子掩面,镜头拉出,他才放下扇子,露出脸孔。而且他与导演先商量了镜头细节,才开始拍摄;为了使镜头更有效地捕捉他表演的精髓,他改变了不少舞台调度的位置。由此可见,由1905年至1920年,由谭鑫培至梅兰芳,戏曲电影已逐渐兼顾电影语言的要求,尝试寻找两者美学共存、甚至共融的方法。
1924年,梅兰芳再拍了五部短片,分别是《西施》、《霸王别姬》、《上元夫人》、《木兰从军》中走边一场,及《黛玉葬花》,其中《黛玉葬花》在北京一旧式大宅花园取实景拍摄,取其与《红楼梦》大观园相似之意。到了20年代梅兰芳替商务印书馆拍短片时,毕竟电影在中国已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在电影语言的运用上,当然胜过《定军山》;可是,这两批作品最核心的美学现象还是相同的,因为它们都以记录表演为主。比较后来发展的叙事电影,便可凸显这两批短片的特色:叙事电影指涉的是电影院外某个现实世界,假如电影院里观众身处的环境是第一度现实,那么,电影里显示的那个在某时某处的世界就是第二度现实。谭鑫培与梅兰芳这批短片的主要内容是他们的表演、拍摄现场就是第二度现实,那么,故事里说的,不管是黄忠还是黛玉的故事,不过是再隔一重的第三度现实。因此,戏曲片的重点,还是表演,不是叙事。有趣的是,在白布前和花园里进行的表演,制造了从现场抽离出来的错觉,似乎不属于任何时空之内,凝结在胶卷上,变成了可重复的、可复印的、几乎是永存的东西,脱离于时、空,甚至不再依附于演员本身。
本来,表演艺术是空间的艺术,亦是时间的艺术,而作品与观众的关系,最刺激的,莫过于台上台下在同一空间、同一时间之内共同“在场”,剧情和演员的表演要带动观众在三小时内经历情感起伏,观众在三小时内经历感情起伏的连贯性,亦靠现场实况在这三小时内、在这剧场空间里无间断的演出中产生。可是,电影语言的本质,却不是“续”,而是“断”。首先,银幕上的与银幕下的空间本属两个世界,拍摄和演戏的地点不是观赏的现场,拍摄和演戏的时间不是观赏的时间,拍摄过程也是断断续续的,每个镜头分开拍摄,加上剪接及蒙太奇等电影语言的运用,影片基本上形成了一段不住断裂的视觉叙述,观众的认知习惯也必须随着这认知客体的特性而做出调整,这与强调“连贯”的剧院现场观剧经验有很大差别。
电影在西方本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谈到电影的始祖——摄影——与传统绘画艺术的分别。他认为两者在观赏经验上的不同,正显示出在现代社会里,人们接受艺术的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每幅画作都是独一无二的,观画的人长时间站在画前凝视,思考画的细节,细细感受作品的情感内涵;相反,照片可以大量复印,没有所谓的原作、副本之分;而且拍照不同绘画,拍摄现实世界,不能完全控制出入画面的东西,进入画面的东西很多,比如拍摄街景,就有数不清的东西收入镜头,因此照片的观赏模式也不一样,人们不会在照片前凝视细赏,通常只会速速浏览,根本看不尽照片里的内容。照片尚且如是,电影的视觉内容更复杂,20世纪的观众面对这样繁复的画面,没有觉得欠缺秩序、不够精致而排斥它,是因为这样的杂乱无章,根本就是现代都市生活的秩序。而且交通发达,人们对时间和空间的感觉跟从前很不一样,过去未能触及的远处国度,在20世纪变得近在咫尺;由于科技进步,过去需要很长时间成就的工作,现在眨眼间就可完成;知识和技能高度分工,人们越来越不能够完全理解身边事物的来龙去脉,断裂的认知模式已成了人们生活的日常状况。电影这媒体表达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触结构”。
中国20世纪早期在城市生活的戏曲观众,无论来自什么背景、持怎样的政治和文化立场,都生活在现代化的都市内,同样面对因交通和科技在短时间急剧大规模发展而突然改变的生活习惯、感官经验及认知模式。《定军山》给他们带来的是一种复印的文化,外省观众在影片上看见“谭鑫培”,不是供拥趸慰情聊胜于无的次货,而是一件把谭鑫培的表演非个人化了的作品⑩,即以科技把谭鑫培的表演与他分离,他的表演不再依附于他个人,他不在,他的表演也在。这与他在之前灌录的唱片或是本雅明形容的摄影,在本质上基本相同,因此它表达的,基本上就是现代化社会复印文化的“感触结构”。
梅兰芳那批电影与20世纪早期中国城市生活“感触结构”的关系更明显。《闹学》开始时的特写镜头、他与导演商量后决定的分镜和调度等,充分利用了电影语言的美学潜能,同时亦极度吻合现代化社会里断裂的认知模式。因此,电影语言越丰富,就越能表达这种属于现代化社会的“感触结构”,而这种打从本质上就是断裂的、不连贯的美学经验,与传统剧院里那连贯的、台上台下同时临在、即时即场交流的美学经验,相距越来越远。
本文审视了20世纪早期京剧创作和接受模式的两个重要的转变,论述这两个新的模式怎样吻合当时急剧转变的中国城市的“感触结构”:由茶园至剧院、由舞台至银幕,这两个改变不仅意味着艺术外部硬件配套的现代化,而且改变了观剧经验中一个最核心的、牵涉形式与时代关系的美学原则。
注释:
①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
②Raymond Williams,Drama from Ibsen to Brecht,London:The Hogarth Press,1993,p.18.
③《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226页。
④这里对茶园环境的描述,基本上是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卷》和廖奔的《中国古代剧场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的资料,再整合而成。
⑤廖奔:《中国古代剧场史》,第162—165页。
⑥转引自于江上行《六十年京剧见闻》,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第164页。
⑦资料散见于郦苏元、胡菊彬《中国无声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
⑧郦苏元、胡菊彬:《中国无声电影史》,第15页。
⑨资料散见于梅兰芳《我的电影生活》,中国电影出版社1984年版。
⑩更确切地说,是把他的表演意念化,因为影片似乎因拍摄技术问题,根本没有真正把他的表演好好记录下来,观众其实没有在片中看到他完整的表演,但票房成功,就说明了观众不介意看到多少和多好的表演,“看谭鑫培表演”这事本身就是目的。
标签:谭鑫培论文; 京剧论文; 京剧演出论文; 剧院论文; 京剧摄影论文; 艺术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戏剧论文; 剧场论文; 定军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