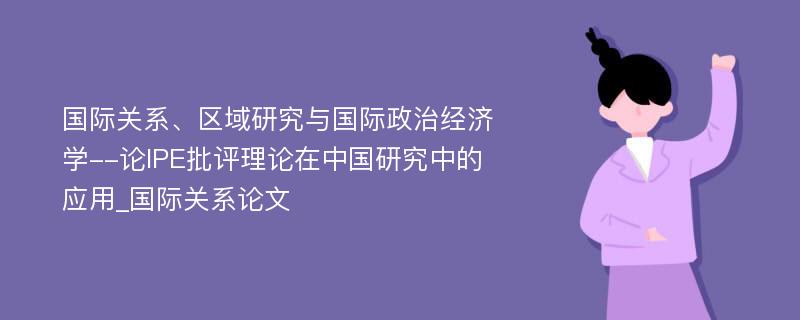
国际关系学、区域研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使用IPE批评理论研究中国的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系学论文,国际论文,政治经济学论文,理论研究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导论
回顾汗牛充栋般的西方有关研究中国的文献,它们中的多数没有强调把国内与国际、 政治与经济分开的分析方法带来的问题,在方法论上仍然过分强调国家中心主义与现实 主义。
我们可以使用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方法来检讨这一基本失败。许多IPE与全球化研 究的东西存在方法论问题。这些著述主要依据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各种理论,或者它们试 图发现一种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关于国家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或者把民族国家仍作为 分析的基本单元(这些情况有时同时存在)。同时,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就方法而言, 对全球化与国家之间关系的IPE研究已经变得更加“多元化”(注:For a good recent
account of the literature on globalisation and the state,see Hobson,J.and Ramesh,M.(2002)‘Globalisation Makes of States What States Make of It:Between Agency and Structure in the State/Globalisation Debate’New Political Economy,7(1)2002:5-22.)与更精细化,不过,多数方法仍然未有目的地转 向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
本文认为,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IPE要对区域(国别)研究更加敏感。要做到这点,就 要有更多的区域研究,从而丰富IPE理论。这些区域研究建立在个案的特定详细知识上 ,有助于为真正的IPE理论发展提供比较基础。同时,靠使用IPE工具来考虑全球化下的 中国政治经济,也将促进对中国问题的研究。
在考克斯传统(Coxian Tradition)的意义上,选择此种折中的混合与阶级形成的理解 ,特别是与佩恩和葛布有关的“新政治经济学”,(注:Payne,A.and Gamble,A.(1996) ‘Introducti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and World Order’in A.Gamble and A.Payne(eds).,Regionalism and World Order.Basingstoke:Macmillan:1 -20.)我们就能提供一个关于政策制定的分析架构,而且考虑到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政 治经济中的力量以及全球因素已深入于国内政策制定中。区域研究与IPE的联姻,既促 进分析架构的发展,又为未来的中国研究提供一系列的问题和假定。
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
本文的一个论点是,占主流地位的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的方法太过于强调民族国家(中央 权威)以及层次分析方法,这些都是建立在国际关系的国家主义与现实主义基础上的东 西。在展开本文前,想强调指出的是,我并没有做大前研一式(Kenichi Ohmaeesque)( 注:Ohmae,K.(1995),The End of the Nation State.London:Harper Collins.)的论断 ,即民族国家已“死亡”。是的,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时如果不承认正式的外交与政府 间关系的重要性,就是毫无意义的。否认了国家是中国国际关系的重要行为体也一样是 毫无意义的。不过,中国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关键动力是,中国地方性的国家行为体(地 方政府)与国际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
我认为,只集中在中央一级的双边关系已经忽视了决定中国国际关系的一些关键因素 以及外部力量在部分意义上塑造中国政治经济演化的方式。第一,主流的国际关系研究 忽略了经济因素的显著作用——特别是非国家经济发挥的角色。第二,对中央一级的理 解忽略了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及其政治含义的地区与部门分布的不均衡性。(注:Breslin ,S.(2000)‘Decentralisation,Globalisation and China’s Partial Re-engagement
with the Global Economy ’,New Political Economy,5(2):205-226.)
本文的任务是考虑这些“经济”问题的政治以及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深入于地区与全球 进程中。我考虑到国内政治、国内经济、国际关系和国际经济之间的联系。地区化产生 了地方化和国际化的关系网络。在研究双边关系的同时,考虑这些关系网络有助于我们 更好地理论化当代中国的国际关系。
在中国内部,作为一个学科的国际关系学(IR)现已有了一些相对成熟的文献,并且中 国人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也得到发展。(注:For a recent example,see,Geeraerts,G. and Men Jing(2001),‘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China’,Global Society,15(3):251-276.)IR在中国仍然是个相对来说很新的学科,不少中国学者对此 做了很好的评估。说所有的中国IR文献知识使用现实主义的方法论是错误的。张勇进就 注意到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对英国学派作为一种方法工具的日益增长的兴趣。(注:Zhang
Yongjin(2000),The‘English School’in China:A Story Of How Ideas Travel And
Are Trans-planted’.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SPAS,ANU:Working
Paper No.2000/4.)建构主义的观念,特别是与瑞思(Thomas Risse)相关的著作开始影 响一些中国学者,如复旦大学的陈志敏与苏长和就在探索国际结构如何影响中国的对外 政策选择。也许值得指出的是,从古典现实主义到建构主义的转化并不是个漫长与艰苦 的过程。(注:Knudsen argues that both Ruggie and Wendt‘accept more or less
implicitly the main tenets of realism’,and that the gap between a social constructivistreading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mainstream traditionalism seems smaller than the argumentative rhetoric would lead us to expect……I have very little problem with anything set forth by either Ruggie or Wendt in these two solid books,except that the specifications they
advocate seem to add little of consequence to the theories they want to improve.See,Knudsen,O.(2001),‘Transcending a Fruitless Debate:Towards a Delimitation of Competing Paradigms’.http://www.sh.se/statsvetenskap/files/ knudsen.doc.)国内与国际的关系也是这些考虑全球化对中国影响的学者探讨的问题。 王逸舟是最早涉及这个问题的中国学者。中国学者对IPE的兴趣也在日益增长,一些大 学已经开设IPE的课程,并编辑出来一些有关的中文教材。不过,这些著作只是描述西 方的方法,而非应用这些方法去分析中国政治与对外关系。
如同20世纪70年代末与80年代中国对“西方”国际关系学的早期研究一样,上述最近 的研究著作承认和考虑(西方的)方法,但并没有广泛使用它们。不过,国际关系学在中 国不是一成不变的,新观念与新方法正在讨论中。公平地说,中国IR学科的发展仍存在 着一系列障碍。在全球化条件下,这些障碍可以得到有效克服。
第一个问题是过分集中于研究与美国的关系,这已作为“条件”因素强加在了中国国 际关系学身上。对中国、中国政策制定者以及研究者来说,美国比任何其他国家与国家 集团(比如欧盟以及单个的欧洲国家)都更重要。在政策层面上,这种(中国学者的)美国 中心主义(American-centricism)是可以理解的,但本文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 提供奖学金与资助、在美国呆一段时间仍然是有意在西方从事研究的中国学者最可能与 最吸引人的选择,通过这一渠道,在国际关系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美国观点已部分地传播 到正在兴起的中国IR共同体中。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大多数IR文献仍然是关于国家主权与国家地位之类的问题,它们的 方法当然是现实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宋新宁认为,“制约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主要 障碍是结构性的,也就是在中国搞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社会环境”,具体来说是三大国 内制约:与政策相关的研究的统治地位、残留的旧观念以及在中国话语背景下国家本身 的重要性。(注:Song Xinning(2001),‘Buil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0(26):61-74,p. 71.)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IPE)方面,中国的IPE深受美国的影响。朱文莉有关中国IPE的论文 就是很国家主义的。她的观点属于对作为分析工具的美国IPE——特别是“霸权稳定论 ”的某种回应。“全球问题的出现被描绘为外交舞台的扩展”。(注:Zhu Wenli(2001)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from a Chinese Angle’,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10(26):45-54.)
再如,宋新宁与陈智宏认为,在中国,人们强烈地认为以下就是IPE:“在IPE研究中 西方学者使用的方法,例如理性选择、博弈理论,数学以及统计方法”。(注:Song Xinning and Chan,G(2000),‘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China’in Weixing Hu,Gerald Chan and Daojiong Zha(2000)China’ 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Dynamics of Paradigm Shift.Lanham: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这再次显示出来,在观念来源上,中国IR占压倒一切地依赖美国同 行——即使一些美国观念是为中国IR与IPE学科所排斥的也不例外。如同我们在后面要 谈到的区域研究中提到的,美国的许多人也关心理性选择方法作为国际关系研究中方法 论的“科学”性。我认为,IPE作为一个分析架构的总体概念(范式)如果超越美国方法 的主导性,就能有助于把理论建设真正向前推进一步。
非国家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批评理论(The Critical IPE)并没有对中国的国际关系 研究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中国学者很少注意到独立行动的经济力量已使单个国家内部受 益,也较少关注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例如,那些被斯特兰奇所称的“国际商业文明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ivilization),(注:Strange,S.(1990),‘The Name of
the Game’in Nicholas Rizopoulos(ed.)Sea-Changes: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a World Transformed.New York: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或者考克斯所形容 的“跨国经理阶层”(transnational managerial class)。(注:Cox,R.(1990),Power, Production and World Orde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Press.)
上面所说的问题并不是有意“垃圾化”(to ‘rubbish’ Chinese academia)中国学者 ——情况远不是这样。我们知道,美国主流的IR期刊一般都由理性选择和现实主义方法 主导。中国不是把学术与政策制定联系在一起而导致方法论上近视的惟一国家。确实, 在今天的时代,很难知道有的学者是否只是研究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或者还是试图写这 样的政策本身。再者,许多美国关于中国IR的文献也忽视了欧洲学者对中国的研究。约 翰斯顿与罗斯编辑的文集《与中国接触》中没有一章是有关欧洲的。(注:Johnston,A. and Ross,R.(eds)(1999),En 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London:Routledge.)中国之外,各学科之间的门户之界线也是泾渭分明的。(注:The requirement to publish within disciplinary journals for career enhancement provide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xplanation here.)如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的大量 文献中,经济学、国际关系、政治与经济地理仍然是各说各的、分立门户。
我建议,为了用理论模式来分析中国的国际关系,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无需更进一步 只集中在美国。
区域研究与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
最近几年,美国一直在争论有关区域(国别)研究与作为学科的IR、IPE之间的关系。美 国政治科学中理性选择理论的统治地位确实为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研究带来很大的问题。
这里我不想讨论IPE中关于政治学与经济学相互关系的老问题。经济学方法一直主导着 很多的IPE研究,并且非常不合理地对政策制定的方法论产生了影响。在有理由对作为 解释工具与方法的理性选择、经济理论的有效性进行怀疑的同时,不能重新回到那种认 为区域研究可以不要所有理论方法的老路上去。二战后,在美国,作为一个研究计划的 区域研究是与冷战分不开的。库明斯对此做出了经典的评论:“二战后的整整一代,莫 斯科与华盛顿的两极冲突、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霸主地位使得学术的界线泾渭分明:受 慷慨的公私资源的支持,‘区域研究’和‘国际研究’有着清楚的地点、问题和进程而 变得重要起来。这里所谓地点一般就是指有关各国:日本作为发展的成功范例而受到青 睐,中国则作为失败的不可接受的发展范例而受到持续关注。关键的过程一般指的是诸 如现代化,或者多少年来一直讲的走向明显的或者隐含的自由民主之‘政治发展’。” (注:Cumings,B.(1997),‘Boundary Displacement:Area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during and after the Cold War’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29(1):6-26.)
在一些方面,区域研究不仅是为了研究中国,而且是为了适应变化中的地缘战略环境 。今天,导致库明斯认为的、使区域研究与国际研究界线分明的冷战背景不复存在,世 界不再是基于安全考虑的地缘战略矛盾,而是基于日益增加的经济相互依存(尽管是不 对称的相互依存)的地缘经济矛盾。而这意味着国内与国际的界线变得更加模糊。于是 ,人们要求一种说明这两者如何互动的解析:“全球与地方的划分不再成立,因为新的 全球经济等级结构切割了地区与国家的边界”。(注:Gamble,A.,Payne,A.,Hoogvelt,A ,Dietrich,M.and Kenny,M.(1996)‘Editorial:New Political Economy’New
Political Economy 1(1):5-11.)这又反过来要求一种对外部环境、行为体与过程的正 确理解。
就“中国研究”而言,冷战的终结与中国自给自足时期的终结正好相一致。也许直到1 992年已故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南巡”,(西方)关于中国政治的研究几乎完全依据中 国的国内状况。我认为,这种“国内主义”(Domesticism)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就不再 有效,至于中国的后WTO政治经济就更不能说没有外部因素在内了。
有关区域研究与IPE的有效性与未来的辩论不能仅仅局限在美国学术以及以经济学与理 性选择理论为代表的霸权方法的范围内。如同卡萨巴主张的那样,(注:Kasaba,R.(199 8),‘Towards a New International Studies’,http://jsis.artsci.Washington.edu /programs/is/toanewis.html)区域研究要求把对特殊性文化的研究与宽广的学科之一 般性理解结合起来,以期产生一种“复合”效应——不是理性选择的“科学”,而是其 他学科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世界的地方—全球关系(The local-global)。我同意卡 萨巴的一个后现代主义基本理论:不要用新的横亘于“区域研究”与“国际关系学”之 间的壁垒取代旧的:“为了不因使用这种方法而导致分离,我们应该从下面的基础出发 :现代是一个生产它自己的综合世界观的时代,这些世界观包罗了所有地点与互动着的 集团。”(注:Kasaba,R.(1998),‘Towards a New International Studies’.See
http://jsis.artsci.Washington.edu/programs/is/toanewis.html)
如果远离与美国学者之间的无谓论战,我们可以找到区域研究与IPE相互促进的方式。 在“全球化”这个大题目下,我们可以通过承认几乎大多数国家(如果不是所有国家的 话)都要面对着一系列的国际因素来做到这点(即两个研究的结合)。但是,我们也要承 认这些全球因素在不同国家起作用的方式不同,原因在于每个国家固有的国内背景不同 。(注:See,for example,Gills and Philip(1996),-a special issue of The Third
World Quarterly,which assessed how different embedded historical,political,social and‘cultural’contexts led to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outcomes in developing states notwithstanding similar internationalising contexts.In particular,see Gills and Philip(1996b)for a conceptual overview,and Breslin( 1996)for a conceptual overview,and Breslin (1996)for a case study of China.) 我们需要IPE去理解前者,而区域研究去理解后者。
如上所述,世界上不只存在一种对IPE的理解。我认为只有“IPE批评理论”才能为区 域研究与全球化下的IPE研究提供方法论与存在论工具。IPE批评理论从这样的假定出发 ,国内与国际、经济与政治的部门划分应该被打破。IPE批评理论的核心是关注结构与 能动者(structure and agency)之间的关系(虽然并非坚持这两者的分家,(注:Wood,E .(1981),‘The Separation of the Economic and the Political in Capitalism’,New Left Review(127).)但这却是在试图重塑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精神。)(注:Gamble,A .(1995),‘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Political Studies,43(3):516-30.)
人们可以从IPE批评理论所反对的东西上来理解它。顾名思义,IPE批评理论反对的东 西远比它代表的东西多。我认为,这种IPE可以定义为反对纯经济解释、反对理性选择 理论、反对国家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学。对于各种IPE批评理论学者来说,大家 的共性是都多多少少同意此种拒绝主义(rejectionism)。在所有这些拒绝的领域,值得 指出的是拒绝霸权的与傲慢的“科学”方法。
全球主义IPE的隐患
在强调使用IPE批评理论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方面,我并不主张IPE拥有对所有问题的 答案。相反,本文的一个出发点是,通过一种更加具有比较性质、意识到不同国家(特 别是那些处于全球政治经济非核心区域的国家)的不同背景,我们能够促进IPE的真正发 展。
这里不是讨论整个IPE对全球化的不同解释的地方。很明显,任何对全球化性质的评论 以及关于它的IPE研究,都冒着(把一个概念)大规模地过分一般化的风险。然而,就如 同使用占主导地位的方法论去研究全球化时代的中国IR要发生的潜在危险一样,在IPE 文献中,也存在着潜在的方法论危险。目前,大多数IPE研究是普遍主义的、是以发达 的民族国家(OECD国家)为中心的。
(一)普遍主义
第一个危险来自于试图做包含普遍真理的定义式陈述。用一个发现回答所有问题是基 本的误导。例如,谁拥有权力,是国家还是市场?真正的质疑应该是两方面:首先是发 现国际政治经济中的不同层次——一种非常适合华语文献中有关单一的全球化世界力量 分布不均衡性质的论断。简单地说,不同国家在全球化中的能力以及对全球化力量做出 的反应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本文同意那些认为全球化是一种不均衡(平等)进程的观点, 而不是认为全球化一定导致和谐化与集中化。“既存的不平等性使得全球化更可能导致 日益增加的核心国家与边缘化国家之间的尖锐分化,核心国家分享着一种叫做全球性世 界经济的价值、益处以及政体。”(注:Hurrell,A.and Woods,N.(1995),‘Globalisation and Inequality’,Millenium 24(3),p.149.)
第二个危险是接受差异,布局区域研究的考察,考虑国家与权力、结构与能动者关系 是怎样由个别国家(区域)的具体情况决定的。IPE不仅应该允许多样性,而且确实要强 调没有单一答案、没有单一理解、没有单一关系组合这个事实。研究者应该考虑,特别 是通过比较方法,不同的关系组合是如何在不同的权力平衡下,在不同的特定历史、地 理、社会与政治的背景下出现的。
这是一个不导致简单化的方法。世界是复杂的,这比那种只服务于方法论或者意识形 态之偏爱而截断现实(truncating reality)的做法要好许多。(注:Hettne,B and S?Derbaum,F.(2000),‘Theorising the Rise of Regionness’New Political Economy, 5(3):457-473.)
(二)所谓全球主义的IPE其实只是一种对发达国家的研究
佩恩认为,(注:Payne,A.(1998),‘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Area Studies’ Millennium,27(2):253-273.)过去,关于霸权的各种理论大多建构在对美国经验的观察 上,当然,有时也以历史上欧洲的情况进行类比。我们偶然见到的霸权概念不过建构在 一个狭隘的若干例子基础上而已。更进一步,这个概念只是这样一种(或者几种)特别情 况,也许离开这个情景以后就不相关了。同理,对许多IPE方法而言,也是建立在特别 情况的基础上的。一旦我们离开建立理论所依据的个案研究情景,理论的适用性就成了 问题。
对IPE学者最重要的一个研究问题是考虑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这方面的英语文献已有大 约至少百多本。(注:There are around 100 published books in English alone where the main focus is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in one way or another,but the classic remains strange(1994a).)不过,这些文献的多数都是对现代世界中 “国家作用”的理解,主要以先进的工业化民主国家的经验为基础。然而,如此支持了 许多西方的区分国家与市场的IPE方法并不总是在非西方的情景下是真的。比如,沃尔 芬恩一直主张,来自“西方”的分析并没有很好地理解日本,因为这些分析从一些错误 的假定出发。(注:Van Wolferen,K.(1990),The Enigma of Japanese Power(New York :Vintage).)对丁裴烈来说,这是一种对“东亚的所谓‘经济’与市场经济建立方式的 传统理解”的后果。(注:Deans,P.(1997),Japan-Taiwan Relations,1972-1992:Virtual Diplomacy and the Separation of Politics and Economics.University of
Newcastle upon Tyne:PhD thesis.)在某些方面,波拉伊(注:Polanyi,K.(1994),The
Great Transformation.Rinehart & Company.)以来,确实,日本资本主义与欧洲、美 国资本主义并没有多大的不同。
这里又有两个问题。首先是对先进工业化经济之研究的主导性。即使在那些非常出色 的比较资本主义著作中,其强调的重点仍是先进工业化经济。如考茨就集中于比较美国 、瑞典、德国和英国的资本主义,(注:Coates,D.(2000),Models of Capitalism:Growth and Stagnation in the Modern Era.Oxford:Blackwell.)而克鲁齐和斯垂克则 考虑意大利、瑞典、英国、法国、美国与日本的资本主义。(注:Crouch,C.and Streeck,W.(eds)(1997),Political Economy of Modern Capitalism:Mapping Convergence and Diversity.London:Sage.)薄格与多尔的著述则集中在资本主义三角 欧洲、美国与日本。(注:Berger,S.and Dore,R.(eds)(1996),National Diversity and Global Capitalism.Cornell University Press.)这些著作服务于暴露工业化社会 内部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目的,但它们缺少对不发达经济的研究。
在美国,没有多少学者使用IPE的视角研究发展中区域。一些比较好的文章出现在研究 发展问题与专业的“区域研究”期刊。
其次是概念延伸的潜在性。如果沃尔芬恩是正确的,那么,用来理解事物的西方总体 概念(范式)在日本应该是适用的,但当我们把视线转向如中国那样的国家,问题就出来 了。当中国是个“不同的”国家——国家做计划的经济——时候,相对而言很容易分析 这个国家。那时,我们知道它是不同的,并这样对待它。当中国已经改革并且远离了传 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我们也许日益觉得很难把它与其他那些国家列入一类。对付差异 性总是相对容易一些,困难在于问题的相似性。新兴的中国市场经济中,国家固有的权 力意味着,在使用那些专门为个案研究而设计的分析模式时,我们要格外慎重。
(三)仅以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元
与大量经济学与IR的文献一样,IPE的一个危险趋势是仅把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元。即 使是研究全球化,一般也是考虑全球化是如何影响国家的,而不是把国家分解为几个分 析单元。在最简单层次上,我们不要忘记了政治学的头号问题——谁获得什么?我们不 应问中国是否从加入WTO中获益、而应问谁从中获益、谁将从中不获益这样有意义的问 题。中国问题专家都知道,改革已经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城乡差别只是其 中之一例,我们还可以加上现存精英层与普通工人层、农村人口以及其他集团获益的不 同。
中国内部各个地区差别很大,一些地区已深入进国际化生产网络,与全球经济高度一 体化;而另一些地区,即使最好的情况,也只不过是边缘化地参与全球经济。这不是说 这些地区不受全球化的影响,而是说,它们并未与国际经济一体化。这种情况往往被解 释为沿海与内地之间的两极化。这种方法对认识中国国际化的差别性是有帮助的,但只 是在部分意义上。内地也有从国际化中受益很大的部分。在研究全球化与一体化IR文献 中,只有很小一部分考虑到民族国家内部各个部分所受到的不同影响,已有了一些好的 讨论世界各地国家之下(次国家)和跨国的地区一体化的研究。(注:For example,Mittleman(1999),Hettne(1999),Hettne and S?derbaum(2000),Breslin and Higgott( 2000),and Schultz,S?derbaum,and?jendal(2001).)尽管如此,对于微观地区主义(micro-regionalism),也就是全球化导致的民族国家政治与新兴的跨国经济空间之间的 分离,仍然是一个没有很好研究的课题。
目的论(Teleology)和政治:什么驱使全球化?
目前,已有大量试图理解全球化的文献。大前研一、赫斯特与汤普森(注:Hirst,P.and Thompson,G.(1999),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Cambridge:Polity.)分别代表了 对全球化认识的两个极端。赫斯特与汤普森甚至质疑,全球化是否真的发生了。如同泰 勒指出的那样,“没有别的词汇像‘全球化’这样一直被使用和滥用。可是,对于所有 这些围绕着全球化而来的夸大其词,全球化的确切含义仍然是模糊、难解,代表着对不 同人来说不同的一系列事情。”(注:Taylor,I.‘Globalisation’in Nicola Phillips(ed)Globalising IPE(Palgrave forthcoming).)赫利尔持同样的看法,“虽 然很少与任何清晰明白的理论相关,全球化一词已经成为最有力的用来说明一系列正在 发生的普遍进程的比喻,这些进程产生了国家之间、社会之间日益增加的相互关系与相 互依存。”(注:Hurrell,A.(1995),‘Explaining the Resurgence of Regionalism
In World Politic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1),p.345.)所以,我避免给 全球化下定义,而代之以考虑通过全球化的棱镜研究国际关系学存在的方法论隐患。
我认为,一个主要潜在隐患是可能的目的论理解。公平地说,西方的IPE话语中并没有 很突出的目的论解释。然而,在讨论中国的全球化时,我总是遭遇到所谓全球化是一个 经济而非政治现象的观点。在广泛的关于全球化的解释文献中,这种依据经济与政治分 离而得出的观点很显著。
批评者可能抱怨这不过是中国人关于全球化的描绘,他们会指出一个事实,一些研究 全球化的中国学者确实在思考国家如何对全球化做出回应、如何与全球化共存以及如何 处理参与全球化的经济带来的政治问题。比如王逸舟就承认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影响以 及全球化渗透进入各种社会问题。他认为,全球化不仅仅是个发生的问题,全球化也取 决于各国政府的决策和政策。(注:Wang Yizhou(2000),‘Political Stabil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lobalisation’.)但问题是 ,他的观点似乎光考虑到经济全球化的政治方面,却没有指出经济全球化本身就具有的 固有的政治性质。
在考虑建立一个IPE架构来研究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国际关系时,有必要从对全球化不只 是发生这一理解出发。全球化是一种由技术进步、生产组织形式的改变驱动的现象,它 也是由主要国际金融机构的政策偏爱与主导观念驱动的。在这方面,全球化具有意识形 态的含义。综合上述,如同博纳德和拉沃海尔在研究东亚政治经济时认为的那样:“我 们争论的东亚新兴政治经济应该根据政治经济的全球化、各国政治经济的变化与生产组 织形式变化之间的关系来理解。”(注:Bernard,M and Ravenhill,J.(1995),‘Beyond Product Cycles and Flying Geese:Regionalization,Hierarchy,and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East Asia’,World Politics(47):171-209.)
所以,建立在考克斯(注:Specifically,Cox,R.(1981),‘Social Forces,States and
World Orders: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in Millennium(10),Cox,R .(1983)‘Gramsci,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n Essay in Method’in
Millennium(12) and Cox,R.(1990),Power,Production and World Orde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著作基础上、与葛布和佩恩以及其他学者有联系的“新 政治经济学”方法认为,以国民经济之间的交换关系为特征的布雷顿森林时代已经由生 产与金融为基础的全球经济所取代。“新全球政治经济的形成与国际流动资本的结构性 权力相关。国家现在不仅不得不承认其他国家与国际组织的权力,而且承认国际资本、 银行以及外汇市场的权力。”(注:Payne,A.and Gamble,A.(1996),‘Introducti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and World Order’in A.Gamble and A.Payne(eds)Regiona lism and World Order.Basingstoke:Macmillan:1-20,p.15.)这是 非国家行为体在形成金融与商品流动上扮演重大作用的一个体系,然而,在这个体系中 的国家为全球化提供许多便利。
在某些方面,我们必须后退一步,考虑全球政治经济中非国家行为体日益增加的权力 背后的政治方面。首先,我们要考虑非国家行为体如何拥有了这种权力。斯特兰奇声称 跨国公司是促进全球化生产的关键角色,“这不是偶然的。权威从国家转移到市场在很 大程度上一直是各个国家政策的结果。这不是说跨国公司偷了国家政府的权力,而是政 府以所谓‘国家的理由’(Reasons of state)拱手把权力交给跨国公司。”斯特兰奇继 续论述到,即使是美国也不能控制跨国公司的巨大力量,反而,世界上最强有力的政府 发现自己已受跨国公司的限制。尽管如此,事实是,经济结构最初的自由化却是建立在 政治选择与决策基础上的。(注:Strange,S.(1996),The Retreat of the Stat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44-45.)
也许这里应该区分全球主义(Globalism)与全球化。全球主义是过去历届美国政府热烈 追求的、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其他政府在新自由主义日程下支持的一项计划。它寻求在 全球范围扩散特定的政治、经济、安全和社会互动与理解的形式,特别是以努力推广市 场经济、促进新自由经济战略的里根—撒切尔主义以及主要国际金融机构的相应政策为 标志。相比之下,全球化则是受这些不同方面驱使而日益增长的相互联系性,非国家行 为体利用了政治精英为之建立起来的经济与法律结构。一句话,全球主义是为全球化进 程得以进行的一项政治计划。
我们也需考虑发展中国家中全球化的政治动力。今天,全球化的政治动力很不同。“2 0世纪90年代初,目的不再是对一个更加独立的全球经济的许诺,而是作为一种措施去 确保持续地参与到这一进程中。发展中国家的担心不再是依附全球经济,而是作为一种 措施确保持续地参与到这一进程中。”(注:Bowles,P.(1997),‘ASEAN,AFTA and the
New Regionalism’,Pacific Affairs 70(2):219-233.Though in light of the financial crises of 1997,a feature of the new‘new regionalism’is an attempt to moderate to excesses of unrestrained capitalism.See Breslin,S.,Hughes,C.,Phillips,N.and Rosamond,B.(eds)(2002)New Regionalisms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Theories and Cases.London:Routledge.)如果说全球化是 一种新的依附理论,那么大部分地,它是一种国内自我强加的依附——依附作为达到增 长目标的最佳方式。
这里有两个关键问题需要考虑。一是“意识形态”或者“观念”的变化。发展中国家 的精英改变了他们的政策偏好,接受新自由主义计划作为实现增长的最佳方法。二是如 何为全球化提供方便。因特网与电信设施增加了信息传播的速度,但货物、人员仍然要 通过各种交通工具来运输。所以,人们就需要通过国家投资建设而非私人部门融资的必 要“硬件”基础设施。
总之,这种变化的内部进程已受到斯克莱尔所说的“全球化中的国家官僚”(Globalising State Bureaucrats)的促进。(注:Sklair,L.(1995),Sociology of the
Global System.Baltimore: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pp.135-136.)政府的政策 是使中国的投资制度越来越自由化,对国际资本更有“吸引力”,改革国内经济结构以 减少国内保护主义,使更多的新自由主义总体概念机制化。这里,我们通过考克斯的分 析架构来理解这点:“有权势的公司经济力量与它们在政府和各界的网络组成了可叫做 是‘初始的历史集团’(Nascent Historic Bloc),它们使得政策演变并为全球的意识 形态化做宣传。一般来说,国家只不过扮演全球经济的代理人角色,其主要任务是适应 全球经济自由主义的急迫需要而调整经济政策与实践。这种权力结构受到内外的支持, 外国的支持来自一种所谓全球政策一致(“华盛顿共识”),内部的支持主要来自那些从 全球化中受益的社会力量。……新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和政策上是霸权的。”(注:Cox,R.(1999),‘Civil Society at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Prospects for an
Alternative’,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5(1),p.12.)
建立一种新的分析架构
就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而言,本文建议远离IR的双边与国家主义解释,特别是注意各 层次的中国精英与外部非国家角色的互动。一些非常好的研究已经指出中国沿海省份正 在与全球经济一体化。本文主要强调这种一体化的部分国家性质。
第一,使笔者感到困惑的是,这些研究(是否)与对中国IR的整体分析相符合。一些人 可能反对这点,因为调查的关系仅是纯经济的,不符合前述的政治与经济之间相互联系 的(原则)。日本的情况表明,地方政府的角色是很重要的。罗斯曼与胡克就对日本地方 政府在与日本的邻国建立经济联系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注:Hook(2000),‘Building Yellow Sea Bridges:Kyushu’s role in Sino-Japanese Relations’Conference Paper cited with author’s permission and Rozman,G.(1998)‘Flawed
Regionalism:Reconceptualizing Northeast Asia in the 1990s’The Pacific Review,11(1).)确实,地方对地方的关系已经是中日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 些联系不仅是建立在地方政府之间对话基础上的。地方政府是关键的方便提供者,其他 角色包括地方的通产省分支机构、日本驻中国代表,各个公司以及它们的关联企业、运 输业者、甚至从日本留学回到中国的学生,等等。地方政府由于充当了促进非国家行为 体利益的(主要是日本方面)机构而特别引人注目。
第二,让人感到困惑的是,不密切关注特定的此种关系的地方化表现。现在已经产生 了讨论“大中国”崛起的大量文献,其中有的文献(好的范例包括诺顿与汉密尔顿的著 作)(注:Naughton,B.(ed)(1997),The China Circle:Economics and Electronics in
the PRC,Taiwan,and Hong Kong.Washington:Brookings.Hamilton,G.(ed)(2000)Cosmopolitan Capitalist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是对此种关 系的复杂性的理解,超越了简单的双边关系分析架构,考虑到广泛的地区与全球进程。 一种对“大中国”经济空间的理解低估了日本与美国在塑造这个资本主义进程(地方化 的关系形式存在其中)中的重要性。
我们需要超越这种以国家为基础的分析,即使这种分析本身有时超越了双边主义。我 们应该思考特定的地方化如何与更广泛的地区或国际的分析方法相适应。但是,这些地 方化关系并不是孤立存在的。确实,海外华人网络故意利用他们与中国的文化联系来立 足中国,但是,这些地方化的关系是以一个更加广泛的地区与全球经济结构的存在为前 提的。所以,我同意司马特的下述分析:“许多资本主义的实践深嵌于地方结构中,这 种情景能够产生新的、有活力的资本主义变种。全球化产生了多种多样的地方结果。” (注:Smart,A.(2000),‘The Emergence of Local Capitalisms in China:Overseas ChineseInvestment and Pattern of Development’in Si-Ming Liand Wing-Shing Tang(eds)China’s Regions,Polity,& Economy:A Study of Spat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Post-Reform Era.Hong Kong:UHKP,P.74.)
地区性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远比人们希望的双边层次分析能提供更深入的解释。我 们需要布置一种跨越政治切割出来的边界、依据生产网络和(或)阶级联盟的分析方法。
IPE的一个基本教条即国内与国际的区分已被打破。作为方法的IPE批评理论,不仅对 研究IR,而且对研究中国国内政治经济都有效。未来几年,中国的法律结构将继续变得 符合WTO的要求,全球对于中国国内的重要性将日益明显。我认为,不承认北京的改革 者、美国与别的地方那些想促进中国按照国际规则与“国际社会”的利益进行改革的力 量,就不能分析中国加入WTO的决策。
经济学与政治学的藩篱也需打破。我认为,金融体系内部结构调整的主要制约是政治 意志。对政治稳定的最大挑战取决于中国领导层如何处理经济调整。把这一点放到上面 提到的国家—国际联系的背景下,IPE研究就大有作为。值得强调的是,我并没有否定 国家仍然是重要的。我所主张的对中国内部力量进程的理解需要修正。这种修正认为主 权(至少在经济领域)已经被“穿刺”了,而现在外部行为体确实对中国政治经济的运转 产生了影响。用萨森的话说,全球化已经扎根在国家中。她认为,经济全球化的诸种效 应总是到了国家那里才得以成为现实。“全球化进程所依赖的战略空间总是民族国家的 ;那些通过有利于全球化的、通过贯彻新法律形式而形成的机制,常常是民族国家机构 的一部分。”(注:Sassen,S.(1999),‘Embedding the Global in the National:Implications for the Role of the State’in David Smith,Dorothy Solinger and
Steven Topik(eds)States and Sovereignty in the Global Economy.London:Routledge,p.167.)
在全球化对中国政府结构中权力平衡的影响方面,萨森的着眼点是权力平衡在政府各 部门之间的转移——金融机构可能获得权力与影响,而其他机构则可能失去。全国人大 常委会负责改革法律结构以符合WTO的要求,这将使它在塑造中国国内权力基础上发挥 越来越大的作用。由于党政分开在中国是很难做到的,WTO成员国资格将加强国家机构 的作用。在这个方面,中国基本的政治改革将受到激励,或者也许更正确地说,由于国 际经济协定,为政治改革提供了方便。
我们需要考虑意识形态或者观念的变化。如果新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是霸权的,在 政策上,我们需要考虑新自由主义变成霸权的机制。这是中心国家运用直接的权力工具 促进发展中国家变化的部分结果。盖尔提出“戒律性新自由主义”(disciplinary neo- liberalism)的概念,“美国政府把别的国家要接近的广大市场当做权力杠杆来使用, 把这一杠杆与国际商业环境的形成联系起来,当然,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并不适用于美国 。”(注:Gill,S.(1995),‘Globalisation,Market Civilisation,and Disciplinary
Neoliberalism’,Millennium24(3),p.415.)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别的更直接方法, 教育交流、培训计划的提供、因特网的崛起、对外部世界的日益接触,能使中国官员、 学者、官方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成为“WTO规则遵守者”。商业人士也可通过“社会 学习”和“产业学习”来发展与实践新概念。
结论
我与海冈特曾呼吁:“各种各样的区域研究学者组成的学术共同体,需要在学科研究 的架构下多发表看法,以便提供彼此对话与比较的基础。”(注:Breslin,S.and Higgott,R.(2000),‘Studying Regions:Learning from the Old,Constructing the New’,New Political Economy,5(3):333-352,p.343.)这一愿望(区域研究使用更多的 学科方法,而接受更多的对非核心国家的分析也能促进学科本身)也是佩恩关于区域研 究与IPE重要论文的核心。本文也是探讨区域问题专家与理论专家如何结合起来以改进 各自研究的。
中国对全球化的“接受”或“反应”已深入进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的特定历史、政治与 文化背景中,我的讨论就是从这一理解开始的。但是,仅仅考虑中国内部的变化进程是 不够的。通过深思熟虑的决定,中国领导层已经选择让中国,或者至少是中国的一部分 ,与全球政治经济完全一体化。在这个进程中,他们已经允许,至少在经济范围内,中 国主权向世界“洞开”(perforated),在政策范围增加了一系列诸如地方的别的行为体 。“醒醒吧……世界已变了”,(注:Susan Strange(1994b),‘Wake up Krasner!The
World has changed’RIPE,1(2):209-219.)我们既需要关于国家的知识,又需要学科的 知识来真正理解这个变化中的进程。
在发展当代中国的IPE架构方面,我们能够对超越只以全球政治经济的中心地带与IPE 学术的中心地带为重点的学科发展有所贡献。这样,未来的区域研究与IPE研究也许能 够很好地彼此借鉴、扬长避短,为全球化下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研究提供一些更 综合的文献。
注释:
(53)Hook(2000),‘Building Yellow Sea Bridges:Kyushu’s role in Sino-Japanese Relations’Conference Paper cited with author’s permission and Rozman,G.(1998)‘Flawed Regionalism:Reconceptualizing Northeast Asia in the
1990s’The Pacific Review,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