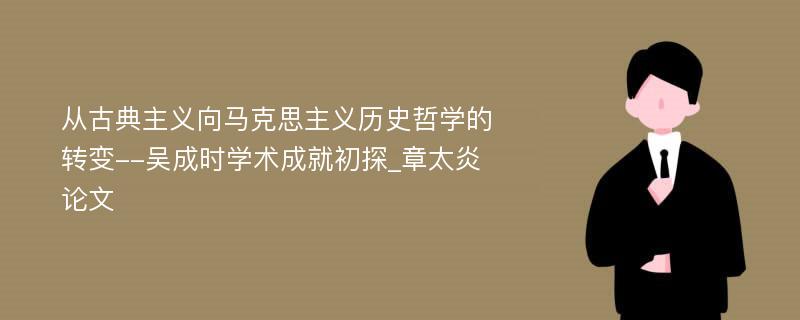
由旧经学向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转变——吴承仕学术成就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学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哲学论文,成就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吴承仕,字检斋,号展成,又号济安,安徽歙县人,生于1884 年3月20日,卒于1939年9月21日。他与黄季刚同是章太炎的得意门生, 三十年代曾以“南黄北吴”并称于世。黄季刚继承了章太炎的“小学”,竭尽整理提高之功,为旧的文字训诂学走上现代科学的道路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吴承仕超越章、黄之处,是他在晚年能够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观点重新研究经学和中国古代历史,成为我国第一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从事经学研究的学者。因之,探讨、研究吴承仕的学术成就,揭示其由旧经学到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发展过程,无疑是有意义的。
一
吴承仕的治学道路,以他三十年代初接受马克思主义为标志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他受业章太炎致力于旧经学的研究;后一阶段则是他晚年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力图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分析研究我国的古代经籍,特别是对《三礼》和《说文》等书发表了不少篇观点内容不同于前代和当代学者的论文,为后学开辟了研究古礼制和古文字学的新途径。现在先叙吴承仕前一阶段的学述成就。
吴承仕生长在一个富有家学传统的士大夫家庭。曾祖父吴道隆国学生出身,曾受封朝议大夫;祖父吴景桓亦出身国学生,曾任布政司理问,受封奉政大夫;父亲吴恩绶长期担任京师歙县会馆(位于今北京宣武门外)馆长,是位饱有学识的爱国志士;母亲汪氏亦为书香世家女子,深谙启蒙教育的道理。这使吴承仕有条件较早地接触中国历代古籍,诸如经史子集、典章名物、文字音韵之类,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养和熏陶。
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刚满5岁的吴承仕, 就被家人送入村里私塾。在启蒙老师的循循善诱之下,他循序渐进,为后来专门从事国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清光绪二十七年,17岁的吴承仕与其父同榜中秀才。父亲为纪念这次“恩科取中”的机遇,特意将原名“绍绶”改为“恩绶”,不久出任歙县知事,之后便长期寓居京都了。翌年,吴承仕又应试中举人。及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清廷举行举贡会考,吴承仕参加廷试,获第一名(注: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录》,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73页。),被授大理院主事(注:民国(歙县县志》。),时年23岁。从现在尚存留于“墨卷”(原件存安徽歙县政协)中的《汉文帝减租除税而物力充羡,武帝算舟车、榷盐铁、置军输,而财用不足论》、《中外刑律互有异同,自各口通商,日繁交涉,应如何参酌损益妥定章程,令收回治外法权策》和《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三篇论、策、义的文章来看:吴承仕在论中痛陈“理财者私其利于国,不能公其利于民”之非;于策中主张“讲论变通之道,为长治久安之谋”;于义中则纵论“莫难于知人,莫难于化恶。知用人之难,则朝无倖位;知化恶之难,则野无莠人”。可以看出他在青年时期,不但举业功深,而且具有非凡的学问和识见。
吴承仕青少年时期,旧中国正处于逐渐衰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动乱年代。目睹祖国山河破碎,民生凋敝,他激发起爱国热情,拥护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民国初年,出任司法部佥事,但与部中官吏意见每多不合。他对当局的政治腐败十分愤懑,任内工作只是应付而已。从此时起,他开始了对历代典章制度、三礼名物比较系统地涉猎,并把注意力投向当代著名的大学者章太炎。
章太炎不仅是学者,而且是有着很高声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1914年1月7日,章太炎大闹总统府,痛斥袁世凯包藏祸心,窃取辛亥革命果实,被袁贼软禁。吴承仕对章太炎不畏奸佞、敢作敢为的精神异常佩服,毅然独往章氏被囚禁的地方探视,送衣送饭,执弟子礼恭。章氏则将自己的一些学术见解口授于吴,这就是后来印行的《菿汉微言》。章太炎《自定年谱》里记载了与吴承仕的这段经历:“三月(按:1915年),歙吴承仕检斋时为司法部佥司,好说内典,来就余学,每发一义,检斋录为《菿汉微言》,时袁氏帝制萌芽已二岁矣。(注:《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11页。 )”从此章吴师生情谊得到忠诚而长久地发展。吴承仕对于章太炎,无论在反对权势、伸张正义的革命性方面,还是在钻研学问、勤思勉力的治学方法上,都是有所继承和借鉴的。
这一阶段,吴承仕主要师从章太炎致力于旧经学的研究。吴承仕深深懂得,“小学”是经学的工具。所以,在文字、音韵、训诂上,他是很下了一番功夫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是浸淫于所谓‘正统派经学小学’的很小范围中费时甚多而心得较少的一人。”(注:吴承仕:《竹帛上的周代的封建制与井田制》,载《文史》一卷三号,1934年。)其实,“心得较少”是自谦之词,“费时甚多”却不足以形容他苦心钻研的精神。他的主要音韵训诂学著作《经籍旧音辨证》,成书前作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材料准备工作。他搜检群书,把旧存的各家音切分别抄录,又依次将各音系一一整理出来,最后参之典籍原文纵横比较,作出辨证。光是抄出的材料就有好几尺厚。这是一部研究经学的工具书,也是一部音义互证的音韵训诂专书。黄季刚对这部书极为重视,不但通观了全书的文字,而且专门为之作了《笺识》。章太炎为该书撰写了《经籍旧音题辞》,表明了对吴承仕学术成就的赞赏。
吴承仕的经学也有很深的造诣。他的经学著述甚多,其中以《经学通论》、《经典释文序录疏证》及《国故概要》三书成就最高,均为指导研究古代学术的门径之作。而三书之中,尤以《经典释文序录疏证》为最突出。该书是为南朝末年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序录》所作的注。吴承仕在对本书所作的批注中指出,《经典释文序录》产生于经学史上承前启后的时代,借助它,可以了解唐以前经学发展沿革的基本线索。本此目的,他在本书中详征博引,叙述和考证了群经的兴衰以及经学史上这个重要时期的重大事件和主要人物、著作,其中不乏精辟的议论。本书可看作是一部唐以前的经学发展史,以其论述的深入和资料的详博,在为数不多的经学论著中独具特色。
吴承仕是以研究“三礼”著称的。在《三礼名物》一书中,他对《仪礼》、《周礼》、《大戴礼》及《小戴礼》的相互关系,剖析至为精确,并提出了“礼之事类有四:曰礼意、曰礼制、曰礼器、曰礼节”的见解。
章太炎对吴承仕的“三礼”成就是十分赞赏的,说他“能明三礼名物,最为核实。”(注:拙编:《吴承仕研究资料集》,黄山书社1990年版,第234页。 )陆宗达先生称颂道:“检斋先生遵循古文经学家实事求是的精神,从文字训诂上来考订名物,又通过名物来说明古代制度;在方法上重证据、重发展,实在是近代礼学不可多得者”。(注:《吴承仕诞生百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8页。)皆非溢美之词。
吴承仕对我国古代学术的研究极为广博。在经学、小学、史学、诸子、《三礼》、《春秋》、《论语》、《尚书》、《诗经》、道藏、佛经、诗文以及戏曲小说诸方面,都有很大建树,特别是对于经学及小学研究的成就尤为显著。他先后撰写著述150余种,计约200万言。其中重要的有《经学通论》、《经典释文序录疏证》、《国故概要》、《周易提要》、《淮南旧注校理》、《尚书三考》、《三礼名物略例》、《六书条例》、《公羊徐疏考》、《蜀石经考异叙录》、《说文讲疏》、《历代尺度表》、《读南北史札记》、《论衡校释》、《初学因明处》等数十种(注:关于吴承仕的著作,黄寿祺先生曾作文介绍,参见《吴承仕诞生百周年纪念文集》,第126—139页。)。在经学、文字学研究方面,已可以说是得心应手,所著非凡了。章太炎称许吴承仕之书,谓其“于学术既能缜密严理,所得已多”;“校正《释文》,极为精当,视臧氏《经义杂记》有其过之,无不及也”、“……此类精审之处,皆昔人所未到”[按:《释文》指《经典释文》,臧氏指清经学家臧琳]、“仆于《石经》古文所不解者数事,得君发明,此一事涣若冰解矣”、“得《经籍旧音辨证》、《论衡举正》二种,足下于旧音用功完密,所发正五百余事,洵为精善”、“及吾门得辩声音训诂者,其惟检斋乎!”章太炎晚年所著《新出三体石经考证》中,其他人均未提及,唯独引用了吴承仕、黄侃之说。章氏对吴承仕学术成就的推崇由此可见一斑了。
二
作为一位硕学鸿儒,吴承仕接受马克思主义新思想,始于30年代初。起初由范文澜介绍他读《共产党宣言》。“九·一八”以后又在进步学生齐燕铭、张致祥等人的帮助下,更广泛更系统地阅读了大量的马列主义著作,如《资本论》、《哲学的贫困》、《德意志意识形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谈谈辩证法》等,努力去寻求真理,从中接受新的思想,汲取力量的源泉。这位钻研古籍数十年,蜚声海内的经学大师,读这些新书,如读中国的古经典一样,也是眉批旁注,丹黄满目。此外,还涉猎了莎士比亚、歌德、高尔基等人的著作。他在总结自己的学习心得时写道:“一直到19世纪中叶的某哲人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说以后,才把政治、经济、历史等等研究部门,奠定下科学的基石。”(注:《吴承仕文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 243页。)
吴承仕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以后,他力图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哲学来重新研究经学和中国古代历史,他说:“我企图着将旧来研究所得的材料,用一元论的历史哲学,从事于中国社会发展史中之某一部分工作,以实践来证明理论,这当然是我们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注:吴承仕:《竹帛上的周代的封建制与井田制》,载《文史》一卷三号,1934年。)。吴承仕所承担的这一历史任务,显然是旧的国学未曾涉及又不可企及的。他在国学方面原有极为深厚的素养,如今有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他的学术研究便闪发出新的光辉。
吴承仕接受马列主义思想的这段时间,正是国民党反动派日益趋于腐朽没落的时期,也正是日本侵略者由蚕食中国进而企图灭亡中国,妄想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时期,故他以抗日救亡为职志。他在《启蒙学会宣言》中写道:“现当民族危机迫于眉睫的时候,只有集中一切力量,作抗敌救亡的决死战,才是我们的唯一出路。”(注:《吴承仕文录》,第249页。)所以,吴承仕在这段时间里, 除了满腔热情地投身到抗日救亡斗争中去以外,还积极帮助进步青年学生出版书籍,创办刊物。自1934至1936年,他和他的同事、学生一道,创办过《文史》、《盍旦》、《时代文化》三个进步学术刊物,除担任繁重的组稿、编辑、校对、印刷、发行等事务工作外,还先后用黄学甫、虞廷、汪少白、少白、大白、非白、绍伯、孙之桓、夏雍、白、记者等十多个笔名,撰写过数十篇文章,有时一期杂志上有他不同笔名的文章三、四篇。此外,如《经济学报》、《文化动向》以及《时代周刊》等刊物上,也都发表有吴承仕的文章。吴承仕这一时期的文章,概括起来,其特点有五个方面:
第一、力图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观点研究古代经学、礼制、哲学和语言文字。吴承仕接受前人“六经皆史”的观点,但他和许多唯物主义的历史学家一样,不只是消极地保留历史资料,而且要通过这些资料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证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史,从而说明科学社会主义实现的必然性。他在经学中特别重视研究《三礼》,准备将三礼名物的材料整理出来,考订真伪,作成系统的论述,名之为文献检讨篇;再比较异同,确定中国历史某时期的经济形态相当于哪一社会发展阶段,名之为史实审定篇。(注:《吴承仕文录》,第72页。)他认为在古代典籍中,“礼”是直接表现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的,因而也就足以反映当时的经济基础。他更认为研究《三礼》应自丧服始。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者对于丧服应认识的几个根本观念》一文中说:“丧服的整个表现,无疑的是某时代某种经济社会的一个意识形态,换言之,丧服中诸条理,是宗法封建社会中一种表现人伦分际的尺度,同时即是后来研究古代亲属伦理的一个最适用的钥匙。”(注:《吴承仕文录》,第13页。)在讲解《丧服传》时,他说:“服制是一方面表现为嫡庶贵贱,亲疏远近,另一方面从服制的升降隆替,能寻绎得社会阶段的演变和权位财产继承权之所本。”(注:《文史》创刊号,1934年。)他对于《孟子》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说也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在《五伦说之历史观》一文中他指出:古代宗法制度、纲常名教以及对于五伦宣传说教的先秦旧说汉儒新义都是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是那一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几千年来“古今中外如出一辙的支配者对于被支配者的最好的麻醉作用”,要用“变的观点”即科学的方法“研究它的缘起、演进、变迁种种过程以及它与当时社会适应的缘故”(注:《吴承仕文录》, 第227页。)。这些说法无疑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也正是吴承仕由旧经学向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跃进的一个明证。
第二、针对现实,抨击国民党反动派。他在《国歌改造运动从国语须别四声谈起》一文中,讽刺国民党的党歌,唱的是“三民主以误荡搜宗”,“无一时一处不表现它的低能,低到打鼓书、蹦蹦戏以下百千万倍”,是“无聊的歌词,倒字的野调”。在《语言文字之演进过程与社会意识形态》一文中,在议及古代社会从“以贝计财”到“废贝为钱”时,揭露国民党政府官吏“总难免有‘行贿’、‘受赂’、‘贪脏枉法’的事情。”(注:《文史》第一卷第二期,1934年。)由此观之,吴承仕所写的这些文章,已经发挥了为现实斗争服务的作用。
第三、宣传抗日救亡。他在《一二·一二的示威游行与学运》一文中,高度评价爱国学生的示威游行运动:“手无寸铁的学生们,全凭着白的心,赤的血,显示出忠勇坚决的举动,作为全国民众的代言人,这至少不得不使敌人和准敌人在我们面前发抖!”(注:吴承仕:《一二·一二的示威游行与学运》,载《时代文化》一创刊号,1936年。)在《北平文化界最近的动态》一文中,他认为:“当侵略者加紧进攻的时候,只有侵略者是我们唯一的敌人。除敌人外,自然都是我们同生死共患难的弟兄朋友。”他完全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指出:“联合广大群众结成抗战救亡的统一战线是我们民族解放的唯一出路。”(注:《时代文化》创刊号,1936年8月。 )吴承仕的这些文章,如同匕首和投枪,刺向反动势力,尤其给站在爱国斗争第一线的青年们以鼓舞和力量。
第四,倡导教学改革。当时吴承仕任中国大学国学系主任,在新思想的指导下,开始改造国学系。首先在国学系的方向上,他明确指出,随着社会的进化发展,“我们现在研究国学,当然不能抱残守缺,尽在故纸堆里讨生活”,所培养的学生应当懂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任务,将来能够“为社会服务”(注:吴承仕:《本系的检讨与展望》,载《中大周刊》第56期,1934年。)。其次在课程设置上,也提出了他的创见,主张“废除经院化的词章考据校勘学,御用化的政治经济学,宗教化的神学、形而上学等。这些历史资料,不妨留待将来的专门家去整理和批判,暂时只有束之高阁罢了”(注:吴承仕:《关于华北的非常时期教育问题》,载《盍旦》一卷四期(署名汪少白),1936年。)。认为“一切科学皆是史学,于是欲治史学,必须先有历史观,欲有正确的历史观,必须先有进步的世界观。”因此,在原来所有的课目之外,必须“创设《社会科学概论》一必修科,作为认识的基本知识”(注:《吴承仕文录》,第227页。)。 他在强调学习《社会科学概论》时特意解释了文学、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我们所托以生存的社会,纵看起来,就是历史,横看起来,就是社会”,“在今日的社会上研究文学、史学,文学、史学便都是社会科学的一方面”,研究、学习的目的在于“为了明了社会各方面体系。”此外,他主张除研究国学外,还要“兼习外国语文,看东、西书籍,融合贯通,自然是无可置议的必由之路了。”(注:《吴承仕文录》,第237页。 )吴承仕所倡导的教学改革,改变了国学系长期安于现状、囿于旧法的状况,给国学系带来了生气,从而形成了良好的学风和浓厚的学术气氛。(注:参见胡云富等:《吴承仕传略》,载《吴承仕诞生百周年纪念文集》,第196—197页。)
第五、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本质。他在《从毒化谈到游街》一文中写道:“租界,是帝国主义对于半殖民地的一个特殊机构,这机构是他们发动政治经济的剥削掠夺以及挑拨操纵等等的策源地。尤其是东方帝国主义对于我们所实施的最惨酷最阴险的毒化政策,这机构更展开它极大的作用和效能。”(注:《盍旦》第一卷第五期,1936年。)他用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点,分析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意识形态中宗教意识对于人民的麻醉欺骗作用。他在《圣诞节——半殖民地国家的宗教意识》一文中写道:帝国主义的传教士“作为侵略的先遣队”,“确实的为资本主义国家执行了调查、开辟、向导、侦探种种的职务”,他们“勾结当地的土豪劣绅,上以交通官府,下以鱼肉乡民,形成一个广大和深入的社会基础,”辛丑条约的签订,“达到了加深整个中国半殖民地化的最高阶段”。伴随着帝国主义入侵,而传入了西方宗教,如中国出现的“圣诞节”,便是适应帝国主义商品掠夺的需要,而形成的“半殖民地化的意识形态之一”,它“是帝国主义者用枪刺沾上弱小民族的血写成的。”“帝国主义者对半殖民地,一面施行毒化政策,一面又榨取商品利润。”(注:《时代文化》第一卷第四号(署名孙之桓),1937年。)吴承仕的这类文章,以犀利的笔锋,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作了无情的揭露,表现出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著名国学研究者陆宗达先生说得好:“检斋先生深入国故而又能超出国故的治学态度,他钻研经学小学而又用马列主义哲学统帅的正确方法,他不忘遗产而又能立足当今的批判精神,他忠于科学并用来为党的事业服务的革命思想,不只在当时,即使在今天,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三
吴承仕的学术研究已形成了自己的鲜明风格和特点,概而言之,约有以下数端:
1、集学者和战士的品格于一身。 吴承仕作为学比乾嘉的经学大师、北平高等教育界的知名教授,对于治学和授业,从来一丝不苟,锲而不舍。他为了校勘辨伪,广查资料,撰写论著,可以整天整天地埋头书房,或伏案默读,或挥笔疾书。但是,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他放眼于“民族”和“人类”的大我,毅然走出那安静舒适的小小书房,以年近花甲的高龄,积极投入挽救祖国危亡的革命洪流。他创办进步刊物,以笔代戈,批判敌人,批判旧社会,用以激励人民的爱国热情,鼓舞人民的抗日斗志;在军警刺刀、警棍、水龙的镇压下,他大义凛然,亲自参加“一二·九”的学生游行队伍,还和青年们一起步行到西山露营;学生运动发展起来了,他联系大学的教授,组成教育界抗日救国会;反动当局逮捕了进步人士和学生,他不顾安危,千方百计地奔走营救;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他以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更加严格要求自己,自觉地进行战斗;北平沦陷后,他又去天津坚持抗日救亡斗争,不断为天津的地下抗日刊物《时代周刊》撰写文章,传播民族革命的吼声,因受日本侵略者的迫害,不幸染病逝世。人们只要回顾一下,在他的同时代的名流学者中间,有的人提倡国故,有的人公开阻挠学生运动,有的人沉湎于明清小品和苦茶随笔,其情形正如鲁迅所说的,“‘功成,名遂,身退’者有之,‘身隐’者有之,‘身升’者更有之。”相形之下,在吴承仕身上无疑体现了最可珍贵的精神品质。
2、治学先从继承入手。吴承仕非常推重章太炎的学术成就, 认为章氏“对于语言文字学、经学、诸子学有绝大开发绝大贡献”,所以自己虽年过四十,仍“钦念本师章君之所喾敕”(注:《国学论衡》卷二。)。时人评他“笃守师说,翼戴绪论,罔敢或替”(注:参见吴承仕逝世时他家所发讣文中的《哀启》、《行述》,原件存安徽歙县政协。)。然可贵之处还在于他从来没有墨守成规。如在汉语音韵的研究上师生两人的途径和方法就不同。章主要是从王念孙父子、孔广森、黄以周那里接受的理论(这和其师俞樾是大有关系的)。而吴则是从徽州学派江永、戴震、金榜、凌廷堪诸乡先哲这里受到启发。此外,吴对章还有过具体的批评,如对章的《文始》,有不少问题他不同意,曾对学生说《文始》中4/10可以商榷。对《新方言》亦有不同看法。尤为可贵的是,在他接受了马列主义新思想以后,“他再不以其业师章太炎的衣钵为满足”(注:吕振羽:《悼吴检斋先生》,载重庆《新蜀报》1940年1 月20日第四版。),而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重新研究经学和古代历史,成为我国第一位用马列主义观点从事经学研究的学者。由此可见,先从继承入手,然后批判发展,走出自己的路来,这是他对待学术遗产的基本态度。
3、博大宽厚之风。吴承仕虽是学界名宿,但为人很谦虚, 从不以学问骄人。他从来反对称他为“某某大师”,为此他在课堂上向同学们解释说:“太炎先生人称国学大师,但他从来是否认的。所谓国学本分“朴”“质”两学,太炎先生对我们朴学是有精湛研究和新建树的,太炎学识渊博,我只是从他学得一点东西,当听到人称我‘大师’或称我为“王”时压力很大,又无法解释,希望同学们免称尊号为好。”作为学者,谦虚主要表现在对待学术批语和不同的学术见解方面。他很乐意人们对他的著作提意见,作好文章总请三种人看:请专家看,请同辈朋友看,请学生看。他的学生回忆说:“吴先生常让我看他的稿子。读他的文稿,是有要求的,要从内容到文字提出意见,意见不怕多,但偏偏不许说捧场的话。正因为他热情的鼓励,我也就敢于畅所欲言地提出问题;即使是极不成熟的意见,甚至吹毛求疵以不误为误,他也从不计较。他这种虚怀若谷的精神,永远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