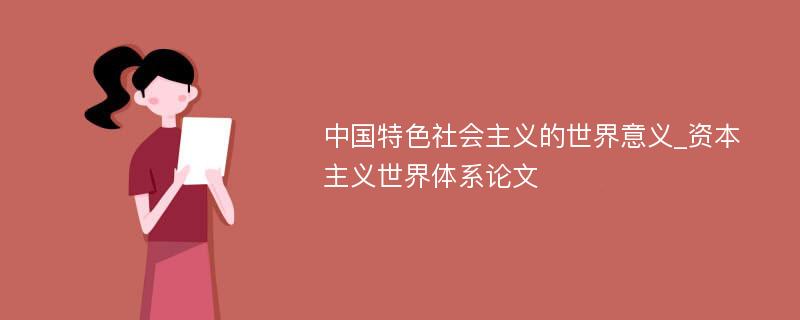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意义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苏东演变之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对于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而且对于冷战后各种社会制度共存(既有矛盾又求合作)的世界来讲, 都具有了某种示范意义。 80 年代末, 美国学者德里克( Arif Dirlik)发表了一篇题为《后社会主义? 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章,载于德里克和迈斯纳(M·Meisner)编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1989年英文版)一书。德里克虽然讲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用“后社会主义”作为某种前置的定性,其实正是从世界范围的社会制度变化来讨论这个问题的。所以,他的一些看法,对我们理解中国今天的事情多少有一些视角上的启发。
首先,德里克说他使用“后社会主义”这个术语是受到文化研究中一个相似的术语“后现代主义”的启发。德里克引用了列奥塔(J·F·Lyotard)的一个看法, 即把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特征看做一种“对于共同叙述的怀疑。”在同样的意义上,德里克说,今天的社会主义之所以是后社会主义,其特征正在于它丧失了把社会主义当成“有着连贯的现在和确定的未来的一种社会和政治理论”的信念。当然,这里有一种变化的意思,即是指社会主义也在发展变化。列奥塔明确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比现代主义更具有现代性的状况,它的变化在于它更真实地揭示了“规则与现实之间的两难处境”。比较而言,德里克似乎有一种方法论的考虑。他针对当前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改革现实,认为再沿用过去的社会主义概念,就会造成一种“歧途”或“误选”意义上的“概念化桎梏”,而“后社会主义”一说,正是他找到的打破这种桎梏的一个“切题方式”。
第二,德里克在这里并不是在概念上钻牛角尖,更不是搞文字游戏。他是从现状和历史两个方面来谈中国的后社会主义的。
从现状来讲,德里克指出了意识形态在中国社会制度中的重大作用,所以在改革开放中,中国社会的转型性质是在一种不停地“论争”(discourses )中来确定的。 我不能肯定德里克是不是在福科(MichelFoucault)的意义上来使用“论争”的,但他确实把此当做一种知识状态,特别是它表达了某些具有社会力量的观点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样一来,“论争”的支撑其实是对改革开放持不同主张的各种政治和社会力量,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论争中就成了各种主张的参照标准和价值取向。因此,“论争”所体现的,其实正是社会主义作为国家实体和观念体系之间的矛盾,而对此如果没有一个切题的理论表述,就不可能摆脱现实与观念的两难处境。在此意义上讲,“后社会主义”正是用来表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各种“概念化桎梏”所不同的含义特征的。
德里克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从其本原(origins )来讲就是“后社会主义的”。当然,德里克这样讲有一层意思是指中国社会主义一开始就和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社会主义理论以及苏联的社会主义首创模式都不一样,而且他也确实提到了中、苏之间矛盾分歧的历史原因。但是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他认为后社会主义本来就是一种历史状况,而不仅仅是今天才产生的状况。社会主义选择是针对资本主义而言的,中国从革命战争年代直到今天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改革时期,一直明确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是不道德的(在此意义上讲,也许德里克会同意,古巴更是一种后社会主义),而“后社会主义”在今日中国之所以比以往格外地突出出来,是由于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中国的经济先决条件和它的政治及社会期望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为了消除这个差距,同时又要保持政治理念的延续性,改革开放的中国才提出要建设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
第三,作为后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得不采取的一个务实步骤,就是同资本主义的“接轨”。事实上,德里克曾说过:“我并不认为我的意思是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任何严肃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德里克给笔者的信)当然,如果我们承认当今世界主要的游戏规则(至少在经济方面)是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主导而历史地形成的,那么所谓各个领域中的“与国际规则(或惯例)接轨”,显然只能是和资本主义接轨。但是,不管德里克在什么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总之他明确指出,这种“接轨”并不必定表示一种向资本主义的倒退或者对“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放弃。
其实,“倒退”这个词在德里克上面那句话中倒是没有在“任何严肃意义上”来使用的,而仅仅指一种时间上的习惯说法:因为先有资本主义,后有社会主义。作为后社会主义的中国社会主义自动向资本主义接轨,并不是对政治理念和理想价值的放弃,这一事实的历史根据,在于社会主义本来就是和资本主义平行的两种现代化模式。既然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按经典理论从资本主义变革而来,又既然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了的国家变成了社会主义,那么,中国所说的“接轨”,其真实根据只能在于不同主义的政治理念与社会实际的价值体现之间是不尽吻合的。换句话说,至少在今天,世界上其实既不存在经典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也不存在经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更为真实的情况是,体现不同政治理念的社会制度已经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程度上同时存在于一个国家之中。所以,德里克认为戈登·怀特(Gordon White)所说的“社会资本主义”(social capitalism )的意思最为贴近后社会主义的真实含义。我想,德里克之所以这样讲,在于把这种“社会主义”当成一种生产方式,避免了作为一种转型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解释,由此也避免了与现实妥协。
第四,德里克认为,和资本主义“接轨”并不仅仅是中国的事,同时也是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要解决的问题。但是,这不仅不表示对社会主义理念的放弃,甚至也谈不上是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的承认,而只是出于后社会主义对于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关联域(context )的考虑。当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尤其是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占据了的在资源配置和利用方面的优势,同资本主义“接轨”事实上已经成了社会主义在国际竞争中发展自己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然而,不管资本主义发展方式是否真的不道德,总之它所存在的种种弊端和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对此,德里克列举了一些状况,比如民族、种族,以及性别中的压迫;阶级压迫;生态学意义上的毁灭;世界范围的黩武主义;“消费文化”(culture of consumption)的异化;由劳动的技术分裂造成的不平等;等等。当然,这些状况作为世界性问题,也许并不能简单地全部归咎于资本主义,但是德里克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后社会主义,其世界意义还在于它实际上成了救治这些弊端和问题的“监护人”。
这种“监护人”的含义,根据德里克的分析,在中国后社会主义的各个阶段都得到了体现。首先,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前夕,就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的前途,这样,社会主义就暂时成了发展进程的一种监护人,它从资本主义中抽取经济活力,并允许其存在直到中国具备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其次,在改革开放中,社会主义的坚持并不真的指向某种确定的理想前景,而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监护人,用以抑制滑向资本主义的可能。第三,这种监护人在今天尤其是同时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两方面的:一方面,中国以对社会主义的坚持来抵制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展;另一方面,它保留了一种可能的选择权,以便根据情况决定如何在某些方面“退向”资本主义”(比如“接轨”)。
显然,德里克所讲的“监护人”并不是法定意义上的真实角色,而更多的是在行为方式和价值选择上的一种示范。然而正由于此,中国后社会主义的世界意义,就在于它在尝试人类共同文明的发展模式方面具有更大的包容量。对此,德里克在文中指出:“对于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来讲,向资本主义开放已经创造了新的可能,其中可以包括对经济选择的更大开放以及比以前更大的民主可能,因为它已经放弃了一种对强制的乌托邦主义的直接可能的信仰,并且,伴随着对于全球文化多样性的承认,它还产生了更为丰富的文化可能,而这在仍把进步当成是整个人类命运的一种直线运动的情况下当然是不可能的。”
也许,德里克对中国的事情的看法过于乐观,但更可能的是,他这种乐观恰恰来自于中国向资本主义的“接轨”。然而不管怎么说,德里克把中国的后社会主义实践看成是具有世界意义的“紧迫工作”,因为这是“对整个发展问题的考虑”。所以,后社会主义可以看做是一种“社会的重新概念化”,以区别于流行的概念。
为了适应变化了的情况而创设新的概念和术语,这当然是必要的,而且事情历来就是如此。用“后社会主义”这个词来表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固然是很有意义的。不过我认为,德里克过于看重社会主义的经典表述和苏联的首创模式,尤其对中国向资本主义的“接轨”有过多的乐观,所以把中国的社会主义从一开始直到今天都看成是一种后社会主义,而我认为后社会主义指的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然而就这方面的现实意义来讲,我想德里克的分析和我有一个实质性的相同之处,这就是说,后社会主义并不是社会主义的某个变种和发展,而是指它表明了一种可能的状态,使得某些代表人类共同进步的承诺可以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以及它们的合作)中得到真实的兑现。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那么德里克所说的在中国和其他地方的社会主义的“合法性危机”也就失去意义了。
标签: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