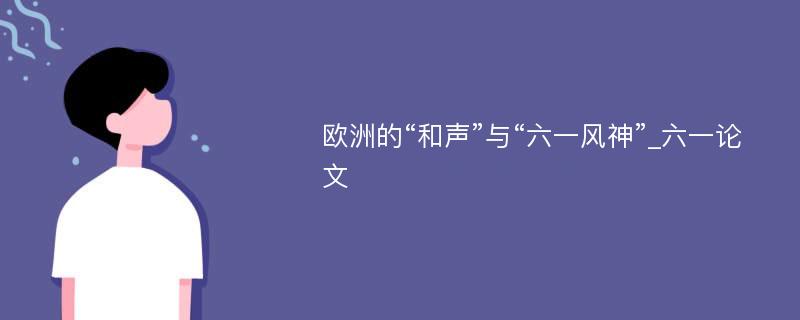
歐陽修的“和氣”與“六一風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歐陽修论文,六一風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從上世紀90年代起,隨著歐陽修研究的深入,“六一風神”引來許多學者的關注:或對“六一風神”稱謂的來源詳加考查①,或謂“六一風神”是“對歐陽修散文審美特質最準確的概括”②,或稱“六一居士的人格是六一風神的內在主體精神”③,或强調“茅坤對‘風神’的討論主要針對叙事文而發,與議論文無涉”。④此外,尚有不少真知灼見,恕不贅述。學者們從不同方面闡述自己對“六一風神”豐富內涵的理解,共同深化了“六一風神”的研究。可以說,在迄今爲止近二十年的探討中,大家對如下觀點是趨于認同的,即“六一風神”最早見于茅坤、歸有光的論述,並上承“史遷風神”;它是抒情範疇的産物,于一唱三嘆中見悠長的韻味;與韓文的陽剛之美截然不同,“六一風神”是歐文獨特的陰柔之美的體現;就文體而言,它見于叙事文,而與議論文無關。
“六一風神”之稱謂因獨具魅力的歐陽修散文而生,因此,對六一風神的探究,離不開歐陽修這個人物,特別是離不開他與衆不同的個性氣質。拙文《略論“六一風神”》⑤,在論述“散文詩化:六一風神的標誌”,“情感外顯:六一風神的本質”,“陰柔之美:六一風神的屬歸”之同時,强調“身兼三任:六一居士之特點”,指出政治鬥争、修史經歷、古文運動給歐陽修帶來的憂患意識、深沉思考和情感波瀾,賦予其創作以巨大的能量,成爲其作品所藴含感人的藝術魅力的無盡源泉。今天看來,這些論述尚有不足,還必須結合歐陽修本人的秉性,考察其特有的“和氣”的强化,即氣質、性致、涵養的完善,探討這種强化與完善與六一風神形成的關係。
蘇洵評歐文云:“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⑥曾鞏稱歐文“深純温厚,與孟子、韓吏部之書爲相唱和”。⑦蘇轍《歐陽文忠公神道碑》云:“公之于文,天材有餘,豐約中度,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⑧與歐公同時代而關係密切的這三位大家,深有所感地評價歐文,其用語雖异,而精神實質卻是一致的。所謂“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深純温厚”及“豐約中度,雍容俯仰”,都形象地道出了歐公的氣質素養和歐文獨特的藝術風貌。
後世,又有宋人邵博引人注目地指出:“歐陽公之文和氣多,英氣少。”⑨羅大經引楊東山語稱歐公“温雅純正,藹然爲仁人之言”。⑩金元人評歐文,延續宋人的論析。趙秉文云:“亡宋百餘年間,惟歐陽公之文不爲尖新艱險之語,而有從容閑雅之態,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11)劉壎云:“歐公文體,温潤和平,雖無豪健勁峭之氣,而于人情物理,深婉至到,其味悠然以長,則非他人所及也。”(12)
至明代前期,方孝孺仍沿襲前人“和氣”之說,稱“永叔厚重淵潔,故其文委曲平和,不爲斬絶詭怪之狀,而穆穆有餘韻”。(13)而歸有光的評說已由“和氣”轉到“風神”,稱歐公“風神機軸逼真太史公”。(14)茅坤云:“西京以來,獨稱太史公遷,以其馳驟跌宕,悲慨嗚咽,而風神所注,往往于點綴指次外,獨得妙解……累數百年而得韓昌黎,然彼固別開門戶也。又三百年而得歐陽子……而其姿態橫生,別爲韻折,令人讀之,一唱三嘆,餘音不絶。予所以獨愛其文,妄謂世之文人學士得太史公之逸者,獨歐陽子一人而已。”(15)又云:“《五代史》……往往點次如畫,風神燁然。”(16)到了清代,桐城派方苞繼承歸有光、茅坤的論述,曰:“永叔摹《史記》之格調,而曲得其風神。”(17)顯而易見的是,在歸、茅二氏提出“風神”的概念以前,兩宋、金、元、明之人,皆以“和氣”之類的言辭描述歐公的氣質與文風。當“六一風神”已然成爲歐文風格的核心概念深入人心的今天,我們有必要追根溯源到諸多有關“和氣”的表述,探究一下它與“六一風神”的關係。
當然,以“和氣”爲代表的歐公這種氣質並非固有的,而是在步入仕途和文壇後逐步形成的。所謂“和氣多,英氣少”,自然不是針對早期的歐公而言,而是指爲人與爲文、從政與創作趨于成熟時的歐公說的。我們不妨從邵博的話入手,探究歐陽修一生英氣與和氣的消長及其對創作的影響。
首先,要明確英氣與和氣的概念。所謂英氣,指銳氣、豪氣、英武之氣、剛明秀發之氣。陳壽評孫策時云:“策英氣杰濟,猛銳冠世。覽奇取异,志陵中夏。”(18)和氣,指温和、温柔、温潤之氣,多含蓄與涵容。和,有和順、和諧、寬和、平和等意思。人問伊川先生程頤“橫渠之書有迫切處否”,程頤答曰:
子厚謹嚴,纔謹嚴便有迫切氣象,無寬舒之氣。孟子卻寬舒,只是中間有些英氣。纔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顔子便渾厚不同……或問:“氣象于甚處見?”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見。如冰與水精雖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温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19)
上述“氣象于甚處見”的“氣象”,即指英氣。程氏以爲,如將孔、孟之言加以比較,孟子“有些英氣”,似玉;而孔子“如冰與水精”,雖無“許多光耀”,但顯得“温潤含蓄”。確實較形象地道出了英氣與和氣的不同。故人言孟子善辯,文有氣勢,有光焰;而孔子德性寬大,氣象從容,即之也温,如飲醇醪,如沐春風。
回顧歐陽修由天聖入仕至熙寧致仕的經歷,其英氣與和氣的消長,大致可以分爲五個階段:
(一)初仕西京及任職館閣時期:英氣甚强,和氣甚弱。
天聖末,以國子監試、國學解試與禮部試三個第一步入仕途的歐陽修,英姿焕發,豪氣干雲,在錢惟演的西京幕府,與尹洙、梅堯臣等切磋詩文,漸以文章知名天下。《答梅聖俞寺丞見寄》云:
憶昔識君初,我少君方壯。風期一相許,意氣曾誰讓。交游盛京洛,樽俎陪丞相。騄驥日相追,鸞鳳志高颺。詞章盡崔、蔡,議論皆歆、向。文會忝餘盟,詩壇推子將。(20)
早年的歐陽修責無旁貸地以文會的主盟者自居,以飛馳的騄驥與高颺的鸞鳳自喻,以古時盡人皆知的著名文士自比,這是何等的意氣風發、何等的英氣逼人啊!
明道元年(1032),因修建遭焚毁的大內,洛陽竹林被砍伐至“地榛園禿”,如此“斂取無藝”,令歐陽修忍無可忍而痛斥之,呼籲“不作無益害有益”。(21)初入官場,便以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勇氣,怒斥時弊,矛頭直指“天子有司”,真是放膽直言,銳氣可嘉。同年,又作《非非堂記》云:“是是近乎諂,非非近乎訕。不幸而過,寧訕無諂。”(22)英銳之氣,盡顯于短章之中,見批判錯誤的無比堅决及嚴以律己的高度自覺與自信。
至于深爲敬佩的人物,歐陽修亦以責賢者備的態度待之,不稍寬貸。明道二年(1033)四月,范仲淹自陳州被召赴闕,歐上書激勵鞭策之,稱“拜命以來,翹首企足,佇乎有聞而卒未也”,謂仲淹當“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23)景祐二年(1035),在石介因上書論不當録用五代及諸國後嗣,惹怒仁宗,被罷去即將擔任的御史臺主簿一職時,歐陽修毅然上書御史中丞杜衍,責備其“爲天子司直之臣”,未能堅持初衷,推薦石介,不主持公道而屈服于威權。(24)
與朋友論事,歐有不同的觀點,亦坦誠相告。批評對方錯誤,從不輕描淡寫,不留一點情面。景祐二年,歐作《與石推官第一書》,直言不諱地指責石介“端然居乎學舍,以教人爲師,而反率然以自异”;(25)在石介不聽勸告,强詞辯解之後,又作《第二書》,謂石介曰:
今足下以其直者爲斜,以其方者爲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饌于案,加帽于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爾。若其納足于帽,反衣而衣,坐乎案上,以飯實酒卮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者,以此之于世可乎?不可也。(26)
言辭不可謂不辛辣,語氣不可謂不尖銳,批評不可謂不有力。
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專權,忤權相,落職貶知饒州。歐陽修致書司諫高若訥,斥其詆誚范仲淹,而不能辯仲淹非辜,痛駡若訥“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27)愛新覺羅·弘曆曰:“是歲修甫三十歲,年少激昂慷慨,其事之中節與否雖未知,孔、顔處此當何如?然而凜凜正氣,可薄日月也。時修筮仕纔五年,爲京職纔一年餘,未熟中朝大官老于事之情態語言大抵如此,千古一轍,于是少所見多所怪,而有是書。”(28)這段評語頗爲生動地道出了官場的情狀和歐陽修凜然無畏之英氣。
英氣甚强,則和氣甚弱。《歐集·書簡》有天聖明道間致富弼書一通,寫于富弼離西京赴絳州後,歐“獨怪彥國了無一書”,又回憶分手時曾有“通相思,知動静”的約定而寫道:
當時相顧切切,用要約如此,謂今別後,宜馬朝西而書夕東也。不意足下自執牛耳登壇先歃,降壇而吐之,何邪?平生與足下語,思欲力行者事何限,此尺寸紙爲俗累牽之,不能勉强,向所云云,使僕何望哉?洛陽去京爲僻遠,孰與絳之去京師也?今尚爾,至絳又可知矣。(29)
年輕氣盛的歐陽修咄咄逼人地指責富弼未踐行好友間的約定,篤于友情固然是修書的動因,但“何邪”、“何限”、“何望”等一連串的詰問亦見少了和氣,無後時容與閑易之態也。
(二)貶官夷陵及參與新政時期:英氣依然,和氣不足。
景祐三年的夷陵之貶並未能使歐陽修屈服。甫抵夷陵,歐即作《黄楊樹子賦》,序云:“江行,過絶險處,時時從舟中望見之,鬱鬱山際,有可愛之色。獨念此樹生窮僻,不得依君子封殖,備愛賞。”賦云:“日薄雲昏,烟霏露滴。負勁節以誰賞,抱孤心而誰識……節既晚而愈茂,歲已寒而不易。”(30)顯然,歐以樹自比,托物言志,抒堅貞不屈之情懷,英氣未嘗稍減。致尹洙書云:“往時砧釜鼎鑊皆是烹斬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之,與幾席枕藉之無异。”(31)一賦一書,异曲同工。歐陽修依然鬥志高昂,豪氣淩霄。同年,歐作《讀李翱文》,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家胸中之塊壘:
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嘆老嗟卑之心,爲翱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翱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其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嘆也夫!(32)
貶謫中的歐陽修銳氣未減而和氣未增。
康定元年(1040)返京後即有《通進司上書》,縱論國是,獻可替否。慶曆二年(1042)又有《准詔言事上書》,采當世急務爲三弊五事,謂“天下之勢,歲危于一歲”(33),極力呼籲變革。此前一年,樞密使晏殊置酒西園,邀歐前往飲酒賞雪,歐即席賦詩云:“主人與國共休戚,不唯喜悅將豐登。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34)歐心有所感,口無遮攔,以詩進諫,惹惱恩師,雖經一度貶謫,英氣仍舊强盛,和氣依然未長。
慶曆四年(1044),在新政人士橫遭污蔑與攻擊之時,歐不避“朋黨”之嫌,斷然作《朋黨論》呈進,籲請仁宗“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35),剛烈之性可見。何焯謂“此歐文之近蘇者”,“少和氣”。(36)
慶曆五年(1045),在范仲淹罷參知政事、富弼罷樞密副使之後,杜衍罷樞密使,韓琦罷樞密副使,新政領導人紛紛被趕出了京都。面對新政已然夭折的嚴酷局面,志强氣盛的歐陽修,在河北都轉運按察使任上,呈進《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言杜、范等乃可用之賢,無可罷之罪:
臣聞士不忘身不爲忠,言不逆耳不爲諫,故臣不避群邪切齒之禍,敢干一人難犯之顔,惟賴聖明幸加審察……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群邪相賀于內,四夷相賀于外,此臣所爲陛下惜之也……今群邪争進讒巧,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秋,豈可緘言而避罪?敢竭愚瞽,惟陛下擇之。(37)
明知局勢已難挽回,但骨鯁在喉,不吐不快,歐陽修還是要作最後的抗争。奏狀充滿了革新者無私無畏的勇氣、嬰逆麟而直言的正氣和久郁于胸中的憤懣之氣。同時,歐陽修作《班班林間鳩寄內》詩,向夫人薛氏闡明形勢之嚴峻和抗争到底的决心;
孤身一許國,家事豈復恤?橫身當衆怒,見者旁可栗。近日讀除書,朝廷更輔弼。君恩憂大臣,進退禮有秩。小人妄希旨,論議争操筆。又聞說朋黨,次第推甲乙。而我豈敢逃,不若先自劾……苟能因謫去,引分思藏密。(38)
寧折不彎的歐陽修,最終爲自己的抗争付出了橫遭污蔑而貶往滁州的代價,但這一時期所展現出的不屈的鬥志和磅礴的英氣,深受後人的褒揚和欽仰。
(三)貶滁徙揚至潁州居喪時期:英氣消減,和氣漸長。
歐陽修慶曆五年(1045)貶謫滁州,八年徙知揚州;皇祐元年(1049)移知潁州,二年改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四年丁母憂,歸潁守制;至和元年(1054)返京,這就是所謂“十年困風波,九死出檻阱”(39)時期。在新政夭折和貶滁的沉重打擊下,歐陽修的挫折感油然而生,不再像早先那樣無所顧忌,不懼後果,他仍思進取,但有些猶豫和彷徨了。慶曆六年(1046)作《新霜二首》,其一云:
林枯山瘦失顔色,我意豈能無寂寞。衰顔得酒猶强發,可醉豈須嫌酒濁?泉傍菊花方爛漫,短日寒輝相照灼。無情木石尚須老,有酒人生何不樂?
“林枯山瘦”之景,映襯著失意寂寞之人,木石無情,尚且老去,何况有情之人生?無奈的詩人也只能以酒澆愁,愁中取樂了。
荒城草樹多陰暗,日夕霜雲意濃淡……蘭枯蕙死誰復吊,殘菊籬根争艷艷。青松守節見臨危,正色凜凜不可犯……惟有壯士獨悲歌,拂拭塵埃磨古劍。(40)
這裏展現的是詩人情感的另一面:與枯死的蘭蕙和籬根的殘菊截然不同,青松傲然挺立,凜然不可侵犯,壯士磨礪古劍,引吭悲歌,這是何等的壯烈與不屈,何等的莊嚴與豪邁!
歐陽修矛盾的兩種心態的交織,真實地反映了他的苦悶,反映了他的豪氣、銳氣、英邁之氣遭到嚴重的消磨。這與他第一次被貶的時候大不一樣,那時他對政局的革新還充滿期待,閱讀夷陵架閣陳年公案,爲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而慨嘆,仰天誓心,仍欲大有作爲。如今,新政的失敗如同當頭痛擊,他的內心實在難以平静。《重讀徂徠集》爲受誣蒙冤的石介鳴不平,實際上也是在爲夭折的新政鳴不平:
人生一世中,長短無百年。無窮在其後,萬世在其先。得長多幾何,得短未足憐。惟彼不可朽,名聲文行然。讒誣不須辨,亦止百年間。百年後來者,憎愛不相緣。公議然後出,自然見媸妍。孔孟困一生,毁逐遭百端。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我欲犯衆怒,爲子記此冤。下紓冥冥忿,仰叫昭昭天。書于蒼翠石,立彼崔嵬巔。(41)
在憤懣不已的同時,歐陽修也開始自我調適,讓滁州的山水撫慰他那受傷的心靈,留下了《游琅琊山》、《琅琊山六題》、《題滁州醉翁亭》、《豐樂亭小飲》、《豐樂亭游春》及《醉翁亭記》、《豐樂亭記》等詩文,著意描寫滁地的安閑、豐樂和醉翁的逍遙、瀟灑。我們看到,在英氣消減之時,歐陽修的和氣明顯增長。
慶曆八年(1048),徙知揚州,歐爲郡寬簡,公餘携客往游平山堂,傳花飲酒;中秋宴飲梅堯臣,請許元、王琪作陪,賦詩爲樂。皇祐元年(1049),移知潁州,爲西湖風光之美所吸引,嘆“柳絮已將春去遠,海棠應恨我來遲”;(42)二年改知應天府,爲杜衍等設慶老公宴……這裏,我們看到的是從政事紛擾中脫身的自在平和的歐公。而皇祐四年(1052),范仲淹逝世,歐有《祭資政范公文》,懷念頌美范仲淹,並嚴詞厲色地痛斥誣陷仲淹的邪佞小人:
嗚呼公乎!學古居今,持方入圓。丘、軻之艱,其道則然。公曰彼惡,公爲好訐;公曰彼善,公爲樹朋;公所勇爲,公則躁進;公有退讓,公爲近名:讒人之言,其何可聽!(43)
“公曰”領起的四句排比,盛贊范仲淹的美德,無情地揭露與批判污蔑仲淹的小人的醜惡行徑。這裏,我們又看到了一個正氣凜然、愛憎强烈、銳不可擋的歐公。
(四)逐步高升而歷任要職時期:英氣猶在,和氣大增。
至和元年(1054),歐陽修已四十八歲。服除返京,權判吏部流內銓,即請抑制豪門貴族子弟優先入仕的特權,又遭人中傷,出知外州,幸得吳充、范鎮等保護,留京修《唐書》。旋遷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與“壯年猶勇爲,刺口論時政”相比,他感到力單勢薄,因無所作爲而苦悶:
丹心皎雖存,白髮生已迸。慚無羽毛彩,來與鸞皇並。鎩翮追群翔,孤唳驚衆聽。嚴嚴玉堂署,清禁肅而静。職業愧論思,文章慚誥命。厚顔難久居,歸計無荒徑……何日早收身,江湖一漁艇。(44)
在惶惑和不安中,歐陽修已流露出收身歸田的念頭。
嘉祐二年(1057)權知貢舉,力革文弊,擢拔蘇軾等英才,使慶曆時已執文壇牛耳的歐公聲譽日隆,但身陷宦海,身體衰疲,難有革新作爲,令其情緒不佳。嘉祐三年,致書王素云:
歲月不覺又添一歲,目日益昏,聽日益重,其情悰則又可知……群賢在外,皆當召歸,而議者不及。衰病思去,又亦未得。守常不變,其弊乃爾。(45)
歐公向慶曆時同爲諫官支持新政的摯友敞開了心扉:群賢未至,事業難期,“守常不變”,內心不寧。這是壯志尚未完全消泯而對現實又無可奈何的表白。他已作好歸田的準備,《歸田四時樂春夏二首》之一稱:“吾已買田清潁上,更欲臨流作釣磯。”(46)對于前時與今日環境及心態的變化,歐公有切身的感受,《謝觀文王尚書惠西京牡丹》云:“心衰力懶難勉强,與昔一何殊勇怯。”(47)于是,翌年遂有《秋聲賦》問世,直抒百憂感心萬事勞形之抑鬱。在“砭人肌骨”的秋氣中,我們明顯感覺到歐公的英氣已大大消磨。
嘉祐五年(1060),歐擢爲樞密副使;六年,任參知政事。官職的榮升,並未給他帶來什麽欣喜,昔日的英邁之氣,罕見于筆端,而時起歸田之念,常有思潁之作。致吳充書云:“某以孤拙之姿,不求合世,加以衰病,心在江湖久矣。”(48)八年,仁宗崩,英宗繼位,與皇太后成隙,歐陽修與韓琦竭力彌縫母子,鎮安內外。他們的努力促使政局趨于和緩,而避免了動亂的發生。
治平年間,濮議之争起,歐陽修在紛擾中益增衰暮之感,歸田之念益加迫切。治平二年(1065)作《秋陰》云:“國恩慚未報,歲晚念餘生。”(49)《秋懷》云:“鹿車終自駕,歸去潁東田。”(50)四年,作《謝提刑張郎中寄筇竹拄杖》,以“玉光瑩潤錦斕斑,霜雪經多節愈堅”(51),自喻剛正之節操,仍見英邁之氣。《歸田録序》云:“既不能因時奮身,遇時發憤,有所建明,以爲補益,又不能依阿取容,以徇世俗,使怨嫉謗怒叢于一生,以受侮于群小。”(52)宣洩憤慨與牢騷,見銳氣不盡消失,但此時歐公胸中更多的卻是平和之氣。熙寧元年(1068),歐作《端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四庫館臣云:“(蔡襄)爲秘閣校勘時,以《四賢一不肖詩》得名,《宋史》載之本傳,以爲美談……歐陽修作襄墓誌,削此一事不書,其自編《居士集》亦削去《與高司諫書》不載,豈非晚年客氣漸平,知其過當歟?”(53)確實,與早年的英氣遠勝于和氣不同,致仕前的歐公,和氣遠勝于英氣,心態十分平和,看問題全面而客觀。與這種心態相適應,他愛潁州“民淳訟簡而物産美,土厚水甘而風氣和”(54),迫不及待,急欲歸田,終老潁州,“其進退出處,顧無所繫于事矣”。(55)
(五)六一居士致仕歸田時期:英氣甚弱,和氣甚强。
熙寧三年(1070),歐公更號六一居士,作《六一居士傳》,感嘆“軒裳珪組,勞吾形于外;憂患思慮,勞吾心于內”(56),渴望早日退休。又撰《續思潁詩序》,自稱“年益加老,病亦加衰,其日漸短,其心漸迫”(57),故思潁之詩愈多,仍以告老歸田爲言。同年,作著名的《峴山亭記》,云: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于荆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于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己而名著也。元凱銘功于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爲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58)
此記是因襄陽守史中煇“欲記其事于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于久遠”而作的。歐公以古說今,以彼喻此,借言羊祜雖爲仁者,但好名之心未泯,杜預聲名顯赫,猶不忘銘功于石,委婉地勸說史中煇勿“汲汲于後世之名”,也抒發了自己無比謙恭曠達的情懷,尤見晚年歐公的博大心胸與寬厚平和之氣。
熙寧四年(1071),歐公終于如願以償地致仕歸潁,時有《答資政邵諫議見寄二首》,其一云:
豪橫當年氣吐虹,蕭條晚節鬢如蓬。欲知潁水新居士,即是滁山舊醉翁。所樂藩籬追尺鷃,敢言寥廓逐冥鴻。期公歸輔岩廊上,顧我無忘畎畝中。(59)
從當年豪氣衝天的館閣校勘,到貶滁時銳氣漸次消磨的醉翁,再到退居潁州逍遙自在平和自如的六一居士,在歐陽修自述中,我們不難察覺他那和氣漸長直至主導整個身心的歷程。
熙寧五年(1072),歐公與世長辭。此前,所作《退居述懷寄北京韓侍中二首》之一云:
悠悠身世比浮雲,白首歸來潁水濆。曾看元臣調鼎鼐,卻尋田叟問耕耘。一生勤苦書千卷,萬事銷磨酒百分。放浪豈無方外士,尚思親友念離群。(60)
詩中寫到自己仕宦漂泊的一生和晚年如願的致仕歸潁,寫到在朝時參與國家大事和退老後安逸自在的田園生活,寫到畢生的勤學與奮鬥和如今的逍遙與解脫,也寫到了自己對人間真情的珍惜和感悟于老莊的情懷。這是對自身漫長而豐富的經歷的心平氣和的總結。
綜觀上述五個階段,歐陽修貶官滁州前的兩段生涯,英氣甚盛而和氣不足,而貶官滁州後的三段生涯,和氣漸增,並成爲其氣質之主導。歐文中所見到特有的風采、情韻、意態,即“六一風神”,正源于其以和氣爲主導的人格修養。因此,“六一風神”在貶滁以前的作品中不是没有,但主要還是見于以和氣爲主導的貶滁後的生涯中。由于“六一風神”是歐陽修以和氣爲主導的精神産物,自然非一般所說的委婉紆徐之歐文皆有;屬于抒情範疇的“六一風神”,亦非見于歐公的所有文體,而僅見于叙事的文體。歷代古文評家争相選録的膾炙人口的佳作,多具備“六一風神”以沉吟往復、抑揚吞吐、唱嘆不盡、韻味無窮爲要素的美感,爲讀者反復吟誦,珍愛有加。如此精品,有序體文,如《蘇氏文集序》、《江鄰幾文集序》、《釋秘演詩集序》、《梅聖俞詩集序》、《五代史伶官傳叙》、《五代史一行傳叙》等;有贈序文,如《送徐無党南歸序》、《送楊置序》等;有記體文,如《豐樂亭記》、《醉翁亭記》、《峴山亭記》等;有墓誌文,如《張子野墓誌銘》、《黄夢升墓誌銘》、《瀧岡阡表》等;還有哀祭文,如《祭石曼卿文》(治平四年)、《祭尹師魯文》(慶曆八年)等。其中,僅有少數作品,如《釋秘演詩集序》、《張子野墓誌銘》、《黄夢升墓誌銘》等寫于貶滁的慶曆五年之前。
歸有光和茅坤是最早就歐文提出“風神”這一概念的文評家,“六一風神”見于序、贈序、記三體者尤多,以下謹列茅、歸兩家各自所編歐公文選中三體文之題目,考其作年,加括弧標示于作品之後,並略作分析。先看茅坤的《歐陽文忠公文鈔》,其選録之三體文如下:
序:《外制集序》(慶曆五年)、《內制集序》(嘉祐六年)、《薛簡肅公文集序》(熙寧四年)、《蘇氏文集序》(皇祐三年)、《廖氏文集序》(嘉祐六年)、《江鄰幾文集序》(熙寧四年)、《仲氏文集序》(熙寧元年)、《梅聖俞詩集序》(慶曆六年)、《謝氏詩序》(景祐四年)、《釋惟儼文集序》(慶曆元年)、《釋秘演詩集序》(慶曆二年)、《傳易圖序》(作年不詳)、《詩譜補亡後序》(熙寧三年)、《韻總序》(作年不詳)、《孫子後序》(康定元年)、《續思潁詩序》(熙寧三年)、《禮部唱和詩序》(嘉祐二年)、《集古録目序》(嘉祐七年)。上文除《傳易圖序》外,全選自《居士集》。
贈序:《送王陶序》(慶曆二年)、《送徐無党南歸序》(至和元年)、《送楊置序》(慶曆七年)、《送秘書丞宋君歸太學序》(皇祐元年)、《送梅聖俞歸河陽序》(明道元年)、《送廖倚歸衡山序》(明道二年)、《送曾鞏秀才序》(慶曆二年)、《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景祐四年)。上文除送梅聖俞、廖倚二序外,均選自《居士集》。
記:《相州晝錦堂記》(治平二年)、《有美堂記》(嘉祐四年)、《峴山亭記》(熙寧三年)、《李秀才東園亭記》(明道二年)、《泗州先春亭記》(景祐三年)、《真州東園記》(皇祐三年)、《海陵許氏南園記》(慶曆八年)、《菱溪石記》(慶曆六年)、《浮槎山水記》(嘉祐三年)、《游儵亭記》(景祐五年)、《伐樹記》(天聖九年)、《吉州學記》(慶曆四年)、《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寶元元年)、《豐樂亭記》(慶曆六年)、《醉翁亭記》(慶曆六年)、《畫舫齋記》(慶曆二年)、《峽州至喜亭記》(景祐四年)、《夷陵縣至喜堂記》(景祐三年)、《偃虹隄記》(慶曆六年)、《王彥章畫像記》(慶曆三年)、《樊侯廟灾記》(明道二年)《明因大師塔記》(景祐元年)。以上有“李秀才東園亭”、“游儵亭”、“伐樹”、“偃虹隄”、“樊侯廟灾”、“明因大師塔”六記選自《居士外集》,餘皆出自《居士集》。
茅坤所選序、贈序、記三體文凡四十八篇,僅九篇出自《居士外集》,《外集》篇目尚不及總數的二成。這說明歐公晚年親手編纂的《居士集》,確實彙集了其畢生散文創作的精品,爲後人所青睞。如按作品的創作年份來區分,作年不詳的《傳易圖序》、《韻總序》不計,三體文共四十六篇,其中作于前兩段生涯,即慶曆五年歐公貶滁之前的作品,計22篇,而貶滁之後的作品有二十四篇,尚多出二篇。
相較于茅坤,歸有光是明代杰出的散文大家,有很强的創作和鑒賞能力,選文更爲精當,其所編《歐陽文忠公文選》中選收三體文如下:
序:《外制集序》(慶曆五年)、《蘇氏文集序》(皇祐三年)、《廖氏文集序》(嘉祐六年)、《江鄰幾文集序》(熙寧四年)、《釋惟儼文集序》(慶曆元年)、《釋秘演詩集序》(慶曆二年)、《詩譜補亡後序》(熙寧三年)、《孫子後序》(康定元年)、《集古録目序》(嘉祐七年)。
贈序:《送徐無党南歸序》(至和元年)、《送楊置序》(慶曆七年)、《送秘書丞宋君歸太學序》(皇祐元年)、《送梅聖俞歸河陽序》(明道元年)、《送廖倚歸衡山序》(明道二年)。
記:《御書閣記》(慶曆二年)、《相州晝錦堂記》(治平二年)、《峴山亭記》(熙寧三年)、《豐樂亭記》(慶曆六年)、《畫舫齋記》(慶曆二年)、《真州東園記》(皇祐三年)、《浮槎山水記》(嘉祐三年)、《伐樹記》(天聖九年)、《王彥章畫像記》(慶曆三年)。
歸氏選三體文凡二十三篇,只有送梅聖俞、廖倚二序和《伐樹記》計三篇出自《外集》,僅占總數的百分之十三,餘皆選自《居士集》。歐公貶滁之前的作品僅十篇,貶滁之後的作品有十三篇。需要說明的是,包括《居士集》和《居士外集》在內的《歐集》,共收三體文八十三篇,內作于貶滁前的有四十六篇,而作于貶滁後的只有三十七篇,少于前者九篇,但歸氏選入其《文選》者,貶滁後作品反多出貶滁前作品三篇。可見,歸氏與茅坤一樣,更偏重于選收貶滁之後的歐文。因爲隨著年齡的增長、學識的豐富和仕宦歷練的增多,歐陽修涵養也不斷提升,襟抱更爲闊大,思慮更爲周全,處事更爲在理,創作亦更爲成熟,貶滁後以“和氣”爲主導的歐陽修,其作品的藝術魅力自是非此前可比,給讀者帶來更大的震撼是理所當然的。
特別要指出的是,景祐後期,歐貶夷陵,潜心鑽研經學,延至康定及慶曆初,在《易》理的探究上,深有創獲,成就斐然。在追求中正之道上,他甚有心得,看問題更爲全面。這對他品格的提升、修養的完善都有很大的幫助。他指出:“事無不利于正,未有不正而利者。”(61)視中正之道爲自己從政處世務必遵循的價值取向和修身爲人務必時刻秉持不可偏離的道德準則。又指出:“必合乎大中,不可以小過也。蓋人過乎愛,患之所生也;刑過乎威,亂之所起也。推是可以知之矣。”(62)他强調,要符合大中至正之道,且須實事求是,不能意氣用事,應該說,獲得這些認識,對貶滁之後歐陽修“和氣”的增長有莫大的幫助。如在從政上,他避免偏激,講求中道,完全肯定范仲淹與呂夷簡的釋憾解仇;(63)晚年編《居士集》,不收早年所寫影響極大而未免過火的《與高司諫書》,等等。其實,在貶滁之前任河北都轉運按察使時,歐就拒絶在鎮壓保州兵變之後,富弼欲殺降以斬草除根免卻後患的謬見(64),已表露出他堅守中道,不走極端,嚴防過猶不及的思想。
六一風神的本質是情感的外顯,是淋漓盡致的抒情。以“和氣”爲主導的歐陽修,在貶滁以後,“和氣”日增,在情感領域裏,則表現爲温情、柔情、深情、濃情的强化。藉助賓主相形、俯仰今昔的手法,追懷逝去的風雲歲月和長眠地下的親密友人,一篇篇可見梅堯臣、蘇舜欽、石延年等至愛友朋身影的以“追”字訣聞名的動人心魄的佳作,一唱三嘆,情韻不盡,極致的抒情充滿陰柔的美感,無限的風神溢出于字裏行間。《豐樂亭記》與《峴山亭記》則是充滿“和氣”的中、老年歐公書寫憂國愛民和謙恭博大情懷的杰作,最見令人心馳神往的“六一風神”。歐公從容的氣度、寬闊的胸襟,見諸兩篇文字;歐文之藴蓄吞吐、亦盡顯于兩篇文中。紆徐的情致、蕩漾的筆調,古今的俯仰,無窮的韻味,令此二篇無愧于歷代評家所給予的高度贊譽。這一切都離不開歐公極爲真摯闊大的情懷,自然,也離不開歐公那“和氣”主導的令人崇敬的人生。
①參見黄一權:《“六一風神”稱謂的來源及其闡釋》,《中國文學研究》1998年第4期。
②參見周明:《論“六一風神”——歐陽修散文的審美特質》,《江蘇教育學院學報》(社科版)1999年第3期。
③參見馬茂軍:《廬陵學與六一風神》,《東南大學學報》(哲社版)2004年第4期。
④參見劉寧:《叙事與“六一風神”——由茅坤“風神”觀切入》,《文學遺産》2011年第2期。
⑤參見拙文:《略論“六一風神”》,《文學遺産》1996年第1期。
⑥蘇洵:《上歐陽內翰第一書》,《嘉祐集》卷十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⑦曾鞏:《上歐陽學士第一書》,《元豐類稿》卷十五,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⑧蘇轍:《歐陽文忠公神道碑》,《欒城集·後集》卷二十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⑨邵博:《邵氏聞見後録》卷十四,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⑩羅大經:《鶴林玉露》丙編卷二,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11)趙秉文:《竹溪先生文集引》,《閑閑老人滏水文集》卷十四,四部叢刊本。
(12)劉壎:《隱居通議》卷十三文章,叢書集成本。
(13)方孝孺:《張彥輝文集序》,《遜志齋集》卷十二,四部叢刊本。
(14)歸有光:《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五《新唐書·兵志論》評語,清刊本。
(15)茅坤:《歐陽文忠公文鈔引》,《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三十一,明刊本。
(16)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歐陽公史鈔》卷首,皖省聚文堂重校刊本。
(17)方苞:《古文約選序例》,清同治乙巳望三益齋重刊本。
(18)陳壽:《三國志·吳志》卷一《孫策傳評》,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9)朱熹編:《二程遺書》卷十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0)歐陽修:《歐陽文忠公文集·居士外集》卷三,四部叢刊本。《歐陽文忠公文集》,以下簡稱《歐集》。
(21)《戕竹記》,《歐集·居士外集》卷十三。
(22)《非非堂記》,同上。
(23)《上范司諫書》,《歐集·居士外集》卷十六。
(24)《上杜中丞論舉官書》,《歐集·居士集》卷四十七。
(25)《與石推官第一書》,《歐集·居士外集》卷十六。
(26)《與石推官第二書》,同上。
(27)《與高司諫書》,《歐集·居士外集》卷十六。
(28)《與高司諫書》評語,《唐宋文醇》卷二十二,清光緒三年浙江書局重刊本。
(29)《與富文忠公》《歐集·書簡》卷一。
(30)《黄楊樹子賦》,《歐集·居士集》卷十五。
(31)《與尹師魯第一書》,《歐集·居士外集》卷十七。
(32)《讀李翱文》,《歐集·居士外集》卷二十三。
(33)《准詔言事上書》,《歐集·居士集》卷四十六。
(34)《晏太尉西園賀雪歌》,《歐集·居士外集》卷三。
(35)《朋黨論》,《歐集·居士集》卷十七。
(36)《朋黨論》評語,《義門讀書記·歐陽文忠公文》上卷,清乾隆三十四年刊本。
(37)《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歐集·奏議集》卷十一。
(38)《班班林間鳩寄內》,《歐集·居士集》卷二。
(39)《述懷》,《歐集·居士集》卷五。
(40)《新霜二首》,《歐集·居士集》卷三。
(41)《重讀徂徠集》,同上。
(42)《初至潁州西湖種瑞蓮黄楊寄淮南轉運呂度支發運許主客》,《歐集·居士集》卷十一。
(43)《祭資政范公文》,《歐集·居士集》卷五十。
(44)《述懷》,《歐集·居士集》卷五。
(45)《與王懿敏公》,《歐集·書簡》卷三。
(46)《歸田四時樂春夏二首》,《歐集·居士集》卷八。
(47)《謝觀文王尚書惠西京牡丹》,《歐集·居士集》卷七。
(48)《與吳正獻公》,《歐集·書簡》卷二。
(49)《秋陰》,《歐集·居士集》卷十四。
(50)《秋懷》,同上。
(51)《謝提刑張郎中寄筇竹拄杖》,同上。
(52)《歸田録序》,《歐集·居士集》卷四十四。
(53)《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五十二《蔡忠惠集》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
(54)《思潁詩後序》,《歐集·居士集》卷四十四。
(55)同上。
(56)《六一居士傳》,《歐集·居士集》卷四十四。
(57)《續思潁詩序》,同上。
(58)《峴山亭記》,《歐集·居士集》卷四十。
(59)《答資政邵諫議見寄二首》,《歐集·居士集》卷十四。
(60)《退居述懷寄北京韓侍中二首》,《歐集·居士外集》卷七。
(61)《歐集·易童子問》卷一。
(62)同上卷二。
(63)《文正范公神道碑銘》云:“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于是二公歡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見《歐集·居士集》卷二十。范家子弟否認范、呂釋憾,擅改《范碑》,爲親歷其事、尊重史實的歐公所不能容忍。此事邵博載入《邵氏聞見後録》卷二十一,《避暑録話》卷上、《墨莊漫録》卷八等亦有記載。
(64)參見蘇轍:《歐陽文忠公神道碑》“會保州兵亂”一段記叙,載《欒城集·後集》卷二十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