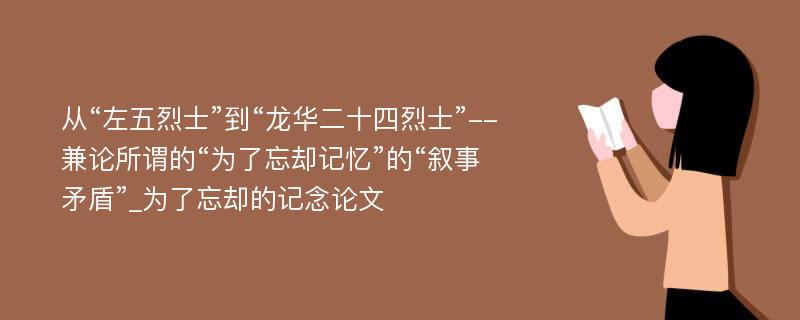
关于从“左联五烈士”向“龙华二十四烈士”的还原——兼谈所谓《为了忘却的记念》的“叙述矛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烈士论文,二十四论文,记念论文,矛盾论文,左联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鲁迅晚年的生活和创作深受“左联五烈士事件”的影响,《为了忘却的记念》则是解读“左联五烈士事件”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如果能够对《为了忘却的记念》的相关史实进行历史的辨别和澄清,则无论对《为了忘却的记念》的解读,还是对“左联五烈士事件”的认识,甚至是对鲁迅晚年思想的理解都将是有益的。许锡强先生的论文《“‘左联’五烈士”案情新探》(下称许文)①对“左联五烈士事件”作了多层次、多侧面的分析,并对“左联五烈士事件”与“龙华二十四烈士事件”的相互关系作了新的阐释,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从“左联五烈士”向“龙华二十四烈士”还原的问题。总体上看,许文在综合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左联五烈士”与“龙华二十四烈士”的关系所作的辨别和分析,较之以往的同类研究有一定的拓展。但令人惋惜的是,许文的全部论述是从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存在“叙述矛盾”这一论断出发的,以确认《为了忘却的记念》存在“叙述矛盾”为基点,许文的主要观点不但否定《为了忘却的记念》关于“左联五烈士事件”的叙述和结论,而且通过对“龙华二十四烈士事件”的还原而在某种意义上否定“左联五烈士事件”本身。然而,许文关于《为了忘却的记念》中存在“叙述矛盾”的论断是不准确的,因而导致该文对“左联五烈士事件”和“龙华二十四烈士事件”的历史认识存在误读与误导之处。对此,笔者试就许文相关论点略陈管见。
一、《为了忘却的记念》并不存在“叙述矛盾”
许文认为,鲁迅的散文名篇《为了忘却的记念》关于左联五烈士遇害后,“当时上海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件事,或者也许是不愿,或不屑载这件事,只在《文艺新闻》上有一点隐约其辞的文章”,与“可是在中国,那时是确无写处的,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等处文字存在“叙述矛盾”。理由是:一方面,“左联五烈士案件”影响到了鲁迅的生活,使鲁迅一家不得不外出避难,“但就是在这样的避居生活中,鲁迅也并没有隔断与外界的联系”;另一方面,柔石等人被捕后,当时上海的外文报纸、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中共中央机关报都对“左联五烈士案件”作过报道,因此,“国民党政权并未能将中国‘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
《为了忘却的记念》是鲁迅为纪念柔石等人遇难两周年而写的,其中相关叙述是以两年前柔石等人被捕被杀的实地背景为参照的。为了认证以上许文所说的“叙述矛盾”,首先要回到《为了忘却的记念》的叙述现场,确认文中所述“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指的是什么。通观《为了忘却的记念》全文,其中对左联五烈士案情及其影响的叙述共有三处,②照录如下:
第一处:“一九三一年的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是我们的五个青年作家同时遇害的时候。当时上海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件事,或者也许是不愿,或不屑载这件事,只在《文艺新闻》上有一点隐约其辞的文章。”(着重号为引者加,下同)
第二处:“这一夜,我烧掉了朋友的旧信札,就和女人抱着孩子走在一个客栈里。不几天,即听得外面纷纷传我被捕,或是被杀了,柔石的消息却很少。有的说,他曾经被巡捕带到明日书店里,问是否是编辑;有的说,他曾经被巡捕带往北新书局去,问是否是柔石,手上上了铐,可见案情是重的。但怎样的案情,却谁也不明白。”
第三处:“第二封信(指柔石从狱中发出的第二封信——引者注)就很不同,措词非常惨苦,且说冯女士的面目都浮肿了,可惜我没有抄下这封信。其时传说也更加纷繁,说他可以赎出的也有,说他解往南京的也有,毫无确信;而用函电来探问我的消息的也多起来……但忽然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说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弹。”
以上三处文字的背景是:柔石等人被捕被杀后,关于这件事的报道和传言很多,而且一些报道和传言涉及到鲁迅。上海《社会日报》于1931年1月20日登载了《惊人的重要新闻》造谣称“鲁迅被捕”,天津《大公报》1931年1月21日也发表文章散布“鲁迅在福州路被捕”的谣言,但当时上海的大报并没有就柔石等人被捕被杀事件发表确切的消息,也没有对关于鲁迅的谣传进行澄清,致使外界对事件真相不得而知。鲁迅本人虽然对柔石等人被捕被杀事件有所了解,但对于整个事件的背景和过程并不清楚。因此,面对外界的种种谣传,鲁迅只好一一写信向关心自己安全的亲友们解释自己的境况。在2月2日致韦素园的信中说:“上月十七日,上海确似曾拘捕数十人,但我并不详知,此地的大报,也至今未曾登载。后看见小报,才知道有我被拘在内,这时已在数日之后了。然而通信社却已通电全国,使我也成了被拘的人。”③在2月4日致李秉中的信中说:“上月中旬,此间捕青年数十人,其中之一,是我之学生。(或云有一人自言姓鲁)飞短流长之徒,因盛传我已被捕。通讯社员发电全国,小报记者盛造谰言,或载我之罪状,或叙我之住址,意在讽喻当局,加以搜捕。”④鲁迅特别指出当时上海的大报没有发表相关消息,是希望有关媒体能够公布事实真相,以便于澄清外界的种种谣传,但当时的大报上却看不到确切的消息。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忘却的记念》中说当时的报章或者“不敢”、“不愿”、“不屑”载这件事,或者“隐约其辞”,“毫无确信”,“怎样的案情,却谁也不明白”。
根据许文中所提供的线索,当时上海的外文报纸、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中共中央机关报确实都发表过关于左联五烈士案件相关的报道,但实际上,这些报道的叙述不但“隐约其辞”,而且相互矛盾。夏衍就当时的外文报纸和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报道回忆说:“不久,中文报上都发表了国民党中央社统发的消息,说共产党在东方旅社开会,被巡警查悉,逮捕了共党四十六人,但没有发表被捕者的身份和名字。同时,上海的英、法、俄、日文都发表了这一事件,所报道的内容互不一致,有的说被捕者为三十六人,其中有中共中央委员;也有的说这一事件是共党内讧,有人向工部局告发而发生的。”⑤不难看出,在外界已经众说纷纭的情况下,这类隐约其辞、互相矛盾的报道对于了解事件真相没有任何帮助。
另一方面,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在2月12日以“二七纪念日龙华司令部秘密枪杀廿三名战士”为题发了消息,该消息全文是:“确息,龙华卫戍司令部于二七纪念日晚七时,秘密枪杀二十三名被拘的革命战士,其中最后一个被枪杀时,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等口号,使行刑的士兵都掉下眼泪。”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是当时上海国民党当局拘押或处决政治犯的主要据点,在这里处决政治犯是一种“例行公事”(包括向忠发、陈延年、赵世炎等中共重要领导人都是在这里被杀害的),因此,在没有说明被害人的确切身份和背景的情况下,仅仅报道“龙华司令部秘密枪杀廿三名战士”并不会引起舆论的特别关注。况且,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当时是秘密出版发行,这刊物本身就是被禁锢之物。何况,《红旗日报》的报道既没有透露枪杀事件中遇难者的真实身份,也没有说明枪杀事件的相关背景,从这一报道中难以判断遇难者的真实情况。相反,《红旗日报》的报道证实了柔石等人是被“秘密枪杀”的,这恰恰证明《为了忘却的记念》中所述柔石等人被捕被杀的真相被“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是准确无误的。
从以上史实可以看出,《为了忘却的记念》中所谓“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既不是指鲁迅与外界隔断联系,也不是指当时媒体没有对左联作家被捕被杀案作过报道,而是指当时国民党当局对这一事件的真相严密封锁消息,致使外界对于被捕者的真实身份,以及对于相关案情的真实背景和过程始终得不到确认。从这个意义上看来,《为了忘却的记念》对柔石等人被捕被杀事件的叙述以及“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的结论与当时外界对案情真相不得而知的实际状况是一致的,文中对“左联五烈士事件”及其影响的叙述与当时鲁迅所了解的案情状况之间并不存在“叙述矛盾”。许文根据鲁迅“没有隔断与外界的联系”和当时报章“隐约其辞”的报道,得出与“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相反的结论是对鲁迅文本的一种误读。
二、关于历史上的“左联五烈士事件”
基于对《为了忘却的记念》中的“叙述矛盾”的认定,许文认为,历史上并无鲁迅他们所宣传的“左联五烈士案件”,有的只是当时新闻媒介作过报道的“龙华二十四烈士案件”;以鲁迅为首的左联,却在这一事件发生之后,即从“龙华二十四烈士”中抽出五位青年作家,进行所谓的“左联五烈士”纪念活动,从而造成了从“龙华二十四烈士”向“左联五烈士”的转换。如果说许文对《为了忘却的记念》存在“叙述矛盾”的认定是对鲁迅文本的一种误读,那么,建立在这一误读基础上的上述论点则是对鲁迅与“左联五烈士事件”的一种歪曲。
勿庸质疑,从总体上看,“左联五烈士事件”是“龙华二十四烈士”事件的一部分,但历史地看来,“龙华二十四烈士案件”是一个历史悬案,这一事件的真相长期处于“禁锢”状态,其在历史上并没有产生明显的反响。相反,作为“龙华二十四烈士案件”的一部分,“左联五烈士事件”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而且长期以来一直是“龙华二十四烈士事件”的一个历史性标志。如果没有对“左联五烈士事件”的广泛、持久的关注,那么,“龙华二十四烈士事件”不过是中共党史上的一桩被悬置的历史公案。在这个意义上说,确认“左联五烈士事件”与“龙华二十四烈士案件”之间的关系,不应该表面地着眼于二者之间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而应该着眼于二者之间“外在”与“内在”的关系,“左联五烈士事件”的“外在”定位是历史的选择,而“龙华二十四烈士事件”作为“左联五烈士事件”的“内幕”只是事后“追认”的一个结果,二者之间不是不同性质的两个事件,而是同一个事件的不同程度的历史呈现。鲁迅与左联宣传“左联五烈士事件”,实质上也是以当时唯一可能的方式纪念“龙华二十四烈士”,宣传“左联五烈士事件”与纪念“龙华二十四烈士事件”之间并不矛盾。
从历史上看,“左联五烈士事件”或“龙华二十四烈士事件”真相之所以长期被“禁锢”,与这一案件的特殊背景和涉案人员的特殊身份有关。左联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团体,而是一个“半政党”性质的组织。相应地,柔石等人并不是一般的作家,而是从事“地下工作”的革命作家。1930年初期,左联的活动不仅受到国民党文化围剿的压迫,而且受到中共党内宗派斗争的影响。左联五作家是1931年1月17日被捕的,此前的1月7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解除了李立三的领导权,确立了王明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王明的上台激化了中共中央的内部矛盾——以何孟雄、林育南、罗章龙为代表的“实力派”领导人在反对李立三路线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王明上台后他们却被排除在中共中央之外,何孟雄等人因此对六届四中全会强烈不满,他们当即采取了与王明集团决裂的行动,宣布另行成立以何孟雄、王克全等为领导的江苏省委。1月17日,何孟雄、林育南等人分头在东方旅社等地秘密开会,讨论反对王明的领导,但由于有人告密,包括柔石等左联作家在内的全体入会者悉数被捕(史称“东方旅社事件”),最终导致包括柔石等人在内的23位革命者在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集体遇难,这就是后来中共党史上所称的“龙华二十四烈士事件”(后经研究确认遇难者为23人,这里暂从许文中的“龙华二十四烈士”说)。
以“东方旅社事件”和“龙华二十四烈士事件”为背景,关于“左联五烈士事件”的历史叙事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作为政治事件
在国民党方面,“东方旅社事件”从逮捕到屠杀都是秘密进行的,国民党当局始终没有公布这一案件当事人的身份和罪状,也没有对案情结果作确切报道,整个过程中都严密封锁消息。在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判决死刑的犯人,有两种执行方式。公开判决的,就公开执行,在外面贴布告,在看守所上绑,上汽车,在外面田间枪毙的。……另一种方式,则是秘密判决,秘密枪毙的。”⑥后一种方式不贴布告,不公开执行,行刑的时候甚至对当事人也要隐瞒实情。通常的方式是:看守喊他们收拾东西,说要解南京,实际上是将他们押赴刑场。柔石等人的处决方式是秘密执行:“二月七日晚点名时……外面还布置好了一班宪兵,荷枪实弹,如临大敌。点过名以后不久,宪兵就由看守所长带着来提人,说是‘因为南京造了大牢,趁最后一次班车,要把你们送上南京去’……对了照片以后,就要大家盖指印。开头两个同志以为这是解到南京去的公文,糊里糊涂地就盖上了指印。第三个轮到做事向来认真细心的柔石,他就在盖指印时仔细地看了一下,认出了是执行书,就高叫起来:‘同志们!这是执行书!我们不盖!’于是,审讯室里一片大乱。”⑦由于屠杀是“秘密执行”的,事件的真相没有公开,事后发表的相关报道都不确切,外界传媒对案情的叙述互不一致、自相矛盾。国民党当局对事件真相的封锁,是造成整个事件长期被“禁锢”的主要原因。
在中共方面,由于东方旅社会议是中共中央部分领导人反对王明六届四中全会决议的一次内部行动,因此,何孟雄等人被捕后,王明“并没有设法营救,也不作任何表态。”⑧1月19日上午被捕者在地方法院受审的时候:“对这案子关怀的人极少,旁听的人没几个,也都与此案无关。”⑨何孟雄等人入狱后,“监狱支部不了解四中全会的情况,接到外边的指示后,拒绝和林育南、李求实等人编在一起过组织生活。”在他们遇难后,“王明对这些烈士怀恨在心,在他们牺牲后仍写文章点名批判何孟雄同志,给这些同志扣上右倾的帽子。”⑩潘汉年当时是中央特科的情报科科长,他在东方旅社事件发生后迅速向王明作了报告,“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不愿营救被捕的同志,还幸灾乐祸地说这批人是‘反党的右派分子,进行反党活动才被捕的’,他们的被捕是‘咎由自取’。2月7日,何孟雄等24位烈士在龙华英勇就义。噩耗传来,潘汉年与许多同志都主张开追悼会,以纪念牺牲的烈士,又为王明所阻挠。”(11)由此看来,王明对整个事件的默认是造成“东方旅社事件”与“龙华二十四烈士事件”被“禁锢”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二)作为文学事件
“东方旅社事件”和“龙华二十四烈士事件”发生后,作为与该事件直接相关的革命组织,左联作出了积极的回应。为了打破政治上的“禁锢”,左联选择了以纪念五位遇难作家的方式向外界揭露事件的真相。东方旅社事件发生后第二天,时任左联文委成员的冯雪峰就从丁玲那里知道了五作家被捕的消息。五烈士牺牲后,冯雪峰以“蓝布”为笔名在3月30日的《文艺新闻》上发表“读者来信”,称“传说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等人失踪,据说他们已被枪毙云云。”这是新闻界第一次向外界透露柔石等左联作家被捕后的消息。4月13日,冯雪峰再次化名在《文艺新闻》上发表“读者来信”,披露了李伟森、柔石等左联作家已于2月7日被杀害的消息。(12)在左联内部,冯雪峰、鲁迅、茅盾等人密切合作,编辑、出版了以“纪念战死者专号”名义出刊的左联机关刊物《前哨》创刊号。在这一期杂志上,刊载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为国民党屠杀同志致各国革命文学和文化团体及一切为人类进步而工作的著作家思想家书》、鲁迅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等重要文献。在编辑《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的同时,冯雪峰、鲁迅、茅盾等还通过史沫特莱、尾崎秀实等外国友人将关于左联五作家遇难的消息发往国外,得到了世界左翼文艺界的响应和声援。(13)在“东方旅社事件”和“龙华二十四烈士事件”被封锁消息的情况下,左联对五烈士事件的宣传成为向外界透露事件真相的唯一途径。正是因为有了左联对五烈士的宣传,国民党当局对“东方旅社事件”和“龙华二十四烈士事件”的“禁锢”才没有完全奏效。
(三)作为个体事件
左联本身是党的地下组织,左联成员的活动处于地下状态,他们的社会活动受到很大的限制:“地下状态的活动空间和行为的私密性限制了‘左联’知识分子的正常社会交往。他们在上海社会没有固定的职业,没有公开的身份,也没有公开的居所。他们无法在上海建立起作为社会成员最需要的邻里关系、同事关系、朋友关系。他们不能在公开场所露面因而不能为公众所认识。大众记住的只是他们所使用的有时连‘左联’的许多成员也不能确认的笔名。”(14)据萧军回忆:“当时作为一个革命的、进步的以至‘左倾’的文化工作者、文艺工作者,他们几乎是没有一般所谓社会生活以至社交生活的。有的只是一种工作上的关系,组织上的关系。除此之外,个人间一种抒情式的交往,人与人之间所谓一般的‘友谊’是不存在的。”(15)因此不难理解,柔石等人被捕被杀后,只有他们的家属、同乡、同志、朋友关心此事,外界对此案情况既不了解,也并不关心。由此看来,冯雪峰、鲁迅、茅盾等人对遇害的五位作家的纪念不仅是出于党的利益,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个人之间的亲情与友谊。鲁迅虽参与了左联纪念五烈士的活动,但就个人而言,他对左联五烈士的纪念是以柔石为核心的。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鲁迅称柔石是“我的学生和朋友,一同绍介外国文艺的人”。在当时鲁迅所交往的青年作家中,柔石是“惟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于托他办点私事的人”。柔石的性格具有“台州式的硬气”,而且“颇有点迂”,但他为人心地善良:“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对于柔石之死,鲁迅是极为悲痛的。柔石牺牲后不久,“当《北斗》创刊时,我就想写一点关于柔石的文章,然而不能够,只得选了一幅珂勒惠支夫人的木刻,名曰《牺牲》,是一个母亲悲哀地献出她的儿子去的,算是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的柔石的记念。”在1936年4月7日的《写于深夜里》,鲁迅再次提及珂勒惠支的那幅以《牺牲》命名的木刻画,申明这幅木刻画在别人看来是对“被害的全群”的纪念,而对鲁迅而言,则是专为纪念柔石的。(16)鲁迅对柔石之死的纪念是解读“左联五烈士事件”的一个重要因素。
以上表明:“东方旅社事件”和“龙华二十四烈士事件”是一个由政治、文学、个人等多重因素构成的综合性的历史事件,鲁迅与左联同人对“左联五烈士事件”的宣传一方面是出于革命道义,一方面则是基于个人感情。显而易见的是,由于这一事件在政治上被“禁锢”,鲁迅当时并不了解“龙华二十四烈士事件”的真相,因此也并不存在许文所称的“以鲁迅为首的‘左联’”,从“龙华二十四烈士”中抽出五位青年作家,进行所谓的“左联五烈士”纪念活动的历史事实。由此看来,许文根据事后“追认”的史实对鲁迅与“左联五烈士事件”关系所作的结论是对鲁迅和左联的一种误解。
三、关于“左联五烈士”与“龙华二十四烈士”的关系
许文在对相关史料作了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最后提出了“从‘左联五烈士’向‘龙华二十四烈士’的还原”问题。许文认为:“历史地说,‘左联五烈士’之死却不在于‘反革命的文化’围剿之列,他们之被捕和枪杀并不是因为他们是革命作家,而是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干部”;“‘左联’的宣传无论如何成功,事实的真相终究是难以掩盖的。”这里,许文认为左联对作为“革命作家”的五烈士的宣传“掩盖”了作为“共产党干部”群体的“龙华二十四烈士事件”。“左联五烈士事件”本来是“龙华二十四烈士事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龙华二十四烈士事件”得不到公开报道和宣传的情况下,宣传“左联五烈士事件”也就是宣传“龙华二十四烈士”,在理论上并不存在对一方宣传的“成功”而“掩盖”了另一方的问题。退一步说,鲁迅、冯雪峰等人在当时和后来都无意于回避或隐瞒“龙华二十四烈士事件”,更无意于通过对“左联五烈士”的宣传来掩盖“龙华二十四烈士”。恰恰相反,无论从左联方面还是从个人交往方面,鲁迅、冯雪峰等人一直在关注和追究“左联五烈士事件”的历史内幕,他们是在无法获得“龙华二十四烈士事件”的确切消息的情况下选择了通过纪念左联五烈士尽可能向外界揭露事件真相。尤其应该指出的是,在当时,无论是宣传“左联五烈士”,还是宣传“龙华二十四烈士”,都需要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鲁迅当时写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并要求史沫特莱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表,史沫特莱提醒说:这篇文章如果发表出来,鲁迅有可能会被杀害。但鲁迅却坚决地说:“这几句话,是必须说的。中国总得有人出来说话!”(17)可以看出,鲁迅与左联同人宣传“左联五烈士事件”是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的。许文所谓左联宣传五烈士的“成功”掩盖了“龙华二十四烈士事件”真相的说法是荒谬的。
综上所述,从“左联五烈士事件”向“龙华二十四烈士事件”的还原不是要推翻“左联五烈士事件”及其相关的宣传和叙述,也不是简单地将二者合并同类项,而是要依据相关史实历史地确认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解读二者之间内在关系的关键步骤应该包括以下几个环节:
(一)左联对五烈士的宣传
1931年2月7日龙华司令部屠杀事件发生后,冯雪峰首先在3月30日、4月13日的《文艺新闻》上披露了柔石等人的死难消息。随后,由冯雪峰、鲁迅、茅盾等人合作编辑的《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于4月20日完成,《前哨》的信息在编成之后通过史沫特莱等人传到了国外,并在世界左翼文艺界产生了强烈反响,但《前哨》在国内的实际发行要晚一些。茅盾回忆说,虽然刊物上印的是4月25日出版,但“刊物正式发行已是七月份了”。(18)陈漱渝先生对此作了考证,证实《前哨》的真实发行时间在7月底或8月初。(19)以《前哨》的出刊为标志,左联宣传五烈士的历史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突破了国民党当局对“龙华二十四烈士事件”的封锁,有力地回击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一方面,排除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对以左联五烈士为代表的“龙华二十四烈士事件”的遇难者作了正确的报道。在这个意义上说,左联纪念五烈士是解读“东方旅社事件”和“龙华二十四烈士事件”的第一步。
(二)鲁迅的纪念
1931年2月7日龙华司令部屠杀事件发生后,鲁迅在《前哨》上发表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纪念左联五烈士,又为美国《新群众》写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在烈士遇难两周年的日子,鲁迅因为无法忘却而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烈士遇难5周年之后,鲁迅又在《写于深夜里》一文中重提左联五烈士事件,为柔石等人的“暗暗的死”而深感悲痛:“我每当朋友或学生的死,倘不知时日,不知地点,不知死法,总比知道的更悲哀和不安;由此推想那一边,在暗室中毙命于几个屠夫的手里,也一定比当众而死的更寂寞。”(20)历史表明,鲁迅的纪念文章是解读“左联五烈士事件”的重要文献。
(三)中共中央的决议
1945年4月20日,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对“龙华二十四烈士”作了历史的评价:“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21)这是中共中央对包括柔石等左联作家在内的23位烈士所做的历史结论。这一结论为评价“龙华二十四烈士”确立了历史标准。
(四)“龙华二十四烈士”纪念碑的建立
1950年4月,上海市政府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找到了“龙华二十四烈士”当年就义的地址,并挖掘出烈士们的遗骸,但由于遗骸已无法辨认,只能集体合葬在一起,并建立了纪念碑。这是对“龙华二十四烈士”的永久的纪念。
(五)学术研究的历史突破
1980年前后,以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为背景,学术界关于“东方旅社事件”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其中吴贵芳的《东方旅社与二十三烈士》(载《党史资料丛刊》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李海文、佘海宁的《东方旅社事件——记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三烈士的被捕与殉难》(载《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3期)、曹仲彬的《对东方旅社事件若干史实的辨析》(载《史学集刊》1983年第3期)等文章对“东方旅社事件”作了详细的考证,澄清了“东方旅社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被捕人数、被捕者的姓名和身份,并最终证实了1931年2月7日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屠杀事件中遇难烈士的姓名和身份。至此,包括“左联五烈士”在内的“龙华二十四烈士事件”终于尘埃落定。
以上史实证明,从“左联五烈士事件”到“龙华二十四烈士事件”的历史解蔽过程延宕半个世纪之久,这个过程中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历史史料和研究成果之间存在明显的“时间差”,对这些史料和研究成果不能仅仅依据后知的结论简单地作平面化处理,而必须依据相应的历史“时间差”作客观的分析和合理的还原。“左联五烈士事件”作为整个过程的开端和标志,其历史意义是不容置疑的,从“左联五烈士”向“龙华二十四烈士”的还原不是要否定“左联五烈士事件”,而是要从新的历史角度确立“左联五烈士事件”与“龙华二十四烈士事件”的历史关系。
注释:
①许锡强:《“‘左联’五烈士”案情新探》,《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②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79-490页。
③鲁迅:《致韦素园》,《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5-36页。
④鲁迅:《致李秉中》,《鲁迅全集》第12卷,第36-39页。
⑤夏衍:《五烈士事件》,《懒寻旧梦录》四《左翼十年》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120-132页。
⑥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下),上海: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215页。
⑦郑择魁:《柔石的生平和思想》,《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1期。
⑧罗章龙:《上海东方饭店会议前后》,丘权政记录整理,《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1期。
⑨王育和:《柔石烈士被捕、营救及牺牲经过》,《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1期。
⑩李海文、佘海宁:《东方旅社事件——记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三烈士的被捕与殉难》,《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3期。
(11)张云:《潘汉年的一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9-60页。
(12)袁成亮:《左联五作家被害内幕》,《党史纵览》2004年第9期。
(13)戈宝权:《谈在美国发表的三封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信》,《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14)许纪霖主编:《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47页。
(15)许纪霖主编:《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第247页。
(16)鲁迅:《写于深夜里》,《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北京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99-512页。
(17)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年谱》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254页。
(18)茅盾:《“左联”前期》,见《茅盾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434-480页。
(19)陈漱渝:《关于〈前哨〉的出版日期》,《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20)鲁迅:《写于深夜里》,《鲁迅全集》第6卷,第499-512页。
(21)《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52-1003页。
标签:为了忘却的记念论文; 左联五烈士论文; 红旗日报论文; 读书论文; 柔石论文; 文艺新闻论文; 冯雪峰论文; 何孟雄论文; 许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