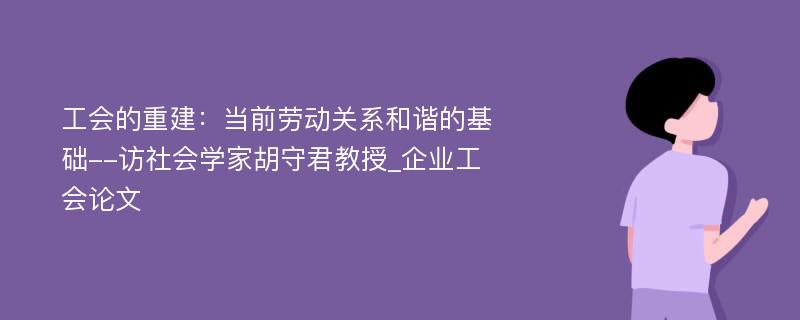
工会重建:当下劳资关系和谐的基点——社会学家胡守钧教授访谈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家论文,基点论文,劳资论文,工会论文,访谈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矿难频发。姑且不论难以准确统计的矿难数据大得有多惊人,不论某些地区“5000块钱另加500斤粮”的矿难补偿有多低廉,也不论“70多家矿山抽检中女工多达249人”有多荒唐,仅面对各大媒体披露的矿难前后相关部门的全部反应,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学术委员会主任、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胡守钧教授不无遗憾地质问:“工会在哪里?工会在干什么?”作为工人表达意愿的重要渠道,作为缓和劳资紧张关系的减压阀,一个组织健全的、功能有效发挥的工会是我们所期盼的;但显然,当下工会的存在状态和作为状态也是为我们所忧虑的。日前,记者就转型期工会的缺位、工会的不作为和工会的重建等话题,对社会学家胡守钧教授进行了专访。
为什么要在社会转型背景下谈工会
记者:胡老师您好,我们注意到,在矿难频发和矿工补偿问题的一系列声音中,您与许多媒体和学者不同,您的关注点直指工会。我们想知道,为什么您特别关注工会?在目前高分化、高流动的体制转换的社会背景下,是不是特别有必要来讨论工会的再组织问题?
胡守钧:对工会的关注确实源自我对社会转型也就是体制转换的持续关注。我想,如果充分了解当下的社会转型,特别是三大制度背景,工会问题讨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会自然凸显。
我对社会转型曾提出了专门的说法——告别计划社会。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突出的特点是国家垄断所有的资源,包括经济、文化、组织和人力资源,按计划运行,我把它叫做计划社会。在这种社会形态下,工人作为劳动力资源是属于国家的,工厂作为生产资源是属于国家的,资本作为经济资源也是属于国家的,所有资源在国家框架下进行统一配置。因此,在那个时代,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关系相对比较缓和,利益主体的分立并不明显。而到了告别计划社会的时代,出现了两个显著特征:一个显著特征是不同资本的出现,如民间资本和外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劳动力与资本开始分裂,并产生了一些变化。具体说来,一方面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民企和外企,即由于资本出现了不同形式,劳动力走向市场,劳动力和资本成了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工人希望工资最大化,老板希望利润最大化,从而导致利益纠纷时常发生;另一方面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国企,因为国企要成为市场主体,要降低生产成本,在这个过程中,国企与工人之间必然会产生矛盾。简言之,劳动力和资本形成了新的结合形式,劳动力和资本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作为劳动力代表的工人和作为资本代表的民企或外企的老板、国企的厂长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这就是第一个大的制度背景。
第二个大的制度背景是,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相对过剩。这就导致在劳动力与资本的互动中,资本处于优势,劳动力处于劣势。进而,劳动力的利益如何保障就成为一个大问题。譬如,有的工厂工作环境恶劣,工伤事故时常发生,而处理方式通常是赔点钱后就把受伤的工人解雇,工人利益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第三个大的制度背景是,面对社会转型过程中劳资关系的种种变化,政府相关部门还没有做好应对的准备。具体而言,计划社会下劳动力和资本都是属于国家的,工人的就业、工人的基本权利直接由政府提供保障,尽管一些深层次的矛盾被隐藏起来了,但至少表面比较缓和,通常通过思想工作就可以解决劳资矛盾。而到了告别计划社会的时代,劳动力和资本的关系复杂而紧张,特别是在资本相对稀缺的情形下,劳动力已经处于弱势。但是,相关的政府部门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而如果协调工作和应对措施不能很好跟上,劳动力必将被置于更加弱势的位置。
记者:看来,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如果真正意义上的工会重建不能被提上时代的议程、受到充分的重视,是否像贫富差距、劳资纠纷等社会问题就有可能越演越烈?
胡守钧:的确,这些问题之间都有着极强的相关性的。劳动力和资本的组合可以创造价值,但是如果分割价值的过程不尽合理,工人所得过少,资本所得过多,长此以往,贫富差距和劳资纠纷就可能会演化为严重的贫富分化与尖锐的劳资冲突。
因此,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就显得非常紧迫。当然,现在出现了不少维权组织,比如一些类似“讨薪组织”的亚组织形态,但我觉得这些组织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问题的关键是,工人要有从根本上维护工人利益的工会组织,因为在工人和老板的整个博弈过程中,单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只有通过组织来进行“讨价还价”才是充分有效的。
为什么工会频频缺位
记者:既然工会的位置是如此重要,2001年修改的《工会法》又明文规定“在中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中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都有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阻挠和限制”,那么为什么在矿难中却绝少看到工会?为什么沃尔玛首个在华职工工会直到今年7月底才组建起来?
胡守钧:这个问题涉及的具体细节比较复杂,特别对民企和外企而言,由于工人与老板是不同的利益主体,老板不会主动组建工会;即便他们主动组建了工会,工会的独立性也是先天不足。对于工会组建的困境,我认为,根本上还是与工人所处的弱势地位紧密相关。譬如在私人煤矿里,如果谁带头组织工会就要开除谁,那么工会基本无法组建。在此意义上,民企、外企的工会需要上级工会帮助组建,政府有关部门(如安检、工商等部门)也应该密切关注和保护工人的权益不受侵害。而不管怎样,有一条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国企、民企和外企都一样,工会是劳动力的所有者保护自己利益的基本方式,如果工人长久没有表达利益诉求的有效渠道,没有工会,对社会的稳定也是不利的。现在沃尔玛虽然建立了工会,但是目前还看不出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关键要看其具体运作的效果。不过,外资企业成立工会至少是件好事,我们应该支持和鼓励。
这里,还需提及的一点是法律的屡屡失效。虽然法律规定工人有组建工会的权利,但是没有工人去组建工会。原因很多,一部分是因为他们不谙法律,遇到了困难,根本不知道可以组织工会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记者:您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工人的权利意识和工会组建的关系问题。您能否结合非正规就业者(农民工和转制工人这两类特殊群体)的具体情况,展开来谈谈?
胡守钧:好的。我先说农民工。农民工的一大特征是他们属于处于弱势的工人群体中的弱势群体,而其中失去土地、失地补偿远远不到位的那部分农民工更是弱势中的弱势。因此,对于这些农民工来说,如何重新评估当初的失地补偿,进行相应的再补偿的问题迟早会提出来。农民工的另一大特征是他们的文化教育水平相对较低,权利意识、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自我管理意识都比较差,由他们去组建工会进行维权的难度也大得多。农民工的再一个特征是,绝大多数没有技术优势,在城市里缺乏亲朋好友,被社会边缘化的可能性非常大。农民工还有一大特征也是被许多人所忽视的,即农民工的身份转变问题。也就是说,农民工从农民变成工人,这个身份的转变过程是非常痛苦的,即使有的是自觉、自愿地转变,也是比较痛苦的。这一点从社会学、心理学上比较容易理解。换句话说,农民工以前可能非常善于种地,在播种和收获中,对自我价值有相当高的认同;但进城后却常常苦于无用武之地。怎样使农民工坦然面对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转换便成为一个大问题。
因此,对于农民工,我们首先要考虑对其失地补偿的重新评估问题,当然这更多的是一个社会工程。仅就工会组建而言,上级工会一定要给予农民工更多的关注,比如提供更多的经济资助(减免会费、增加经济补贴);办农民工夜校,让他们接受再教育,启发他们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觉悟。对于许多不是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企业,在工会组建上还必须考虑到农民工融入工人群体、完成身份转变和价值转换是一个痛苦又漫长的过程,可以在企业工会之外帮助其成立一些同乡联谊组、同乡互助组。
转制工人的问题也基本如此,因为他们也是弱势群体。一方面,如果以前对转制下岗工人的补偿不足,就需要重新评估和再补偿;另一方面,转制工人也存在一个痛苦的身份转变过程,需要工会帮助其树立新的价值认同。如告诉他们改革是一个大的发展进步,转制是改革的必然举措;教育他们学会走向市场,先就业再择业,在市场中重新定位价值。当然更要让工人懂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弃自己的神圣公民权。只有这样,才能将零散的转制工人的“人”和“心”用工会重新组织起来。
总之,这两类非正规就业者都应是工会重点进行权益保护的对象。
记者:这么说,工人的权利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还是很容易被启发的?相应地,也比较容易被组织起来?
胡守钧:是这样,工人的基本需要和想法往往现实而简单,通常就是安全地干活、拿工资、养家糊口;但是现在这个权利是否能够得到保证都很成问题。我举个小例子,广东梅山矿难前,地下渗水好多天了,工人说不能下去,但老板说不下去就全部解雇,结果工人下去后一个都没有回来。其实工人每天在第一线工作,安全不安全的问题他们最清楚,只是由于处于弱势地位,没有表达的渠道和表达的机制。一次事故、两次事故后……他们的觉悟是容易被激发的,他们期望有话语权,有自己的维权组织。说实话,看到这种报道我很震惊,但我更惊异于矿难后的许多报道没有提到“工会”两个字的,也没有提到有劳工代表参与调查的,所以我觉得工会严重缺位了。
为什么工会常常不作为
记者:胡老师,对于已经成立了工会的企业,有两类说法特别让人疑惑:一类说,国企中的工会就是个摆设,戏称“吹拉弹唱队”;另一类说,民企、外企中的工会主席整个儿就是老板的代言人。为什么工会常常会表现出不作为?您是如何理解的?
胡守钧:工会不作为,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工会缺乏独立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和工会的整体发育情况有关。比如全国总工会是个准政府组织,相应的也缺乏独立性,所以在一些特定的情境下处境比较尴尬。在国企中,不少工会主席是厂长“认可”的,自然会帮着厂长讲话;有的民企、外企的老板很聪明,他们不反对建立工会,但工会主席领着老板的工资,又怎会轻易唱“反调”?工会本应是保护工人的组织,这种种反过来的情形是可笑又可悲的。我们说,理论上,工会产生于所存在的企业,同时又应该独立于所存在的企业,应该是在真正的结社自由之下成立的自愿组织,工会干部一定要由工人选举出来。但坦白说,就目前而言,工会无法做到独立运作。
此外,工会不作为与工会干部权益保护机制的建立问题紧密相关。前面也提到,如果工会干部缺乏相应的保护,选中谁,谁就丢饭碗,那么谁也不肯当选工会主席,工会的存在也就必然依附于厂长和老板。
记者:在现实的工会运作中,许多“搭便车”的行为致使大量的集体协商和谈判制度“胎死腹中”。不知这点和您说的工会干部权益保护机制的不到位是否相关?如果是这样,您觉得在我们现有的制度框架内,工会干部的权益如何才能得到有效保护?工会又如何在独立运作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更加有所作为呢?
胡守钧:“搭便车”行为的确是致使工会不作为的另一个主要原因,也是我们俗话说的“枪打出头鸟”——你去争取,赢了大家都有好处,输了你一个人吃亏。所以,如何保护工会干部的权益便是个大问题。就此而言,首先需要建立保护工会干部合法权益的相关法律体系,至少有“厂长或老板不能因为工会干部代表工人与他们谈判而解雇他们”的明文规定,让我们的保护有法可依;其次,需要教育工人充分认识到他们和工会干部是一个“共生体”,工人的利益需要工会干部的保护,工人也要保护工会干部。而说到点子上,工会干部一定要为工人所推选,有些工会干部应该是专职的,工会应该独立于所存在的企业。当然,相应的,工会干部的工资从哪里来,工会的会费够不够,这又是需要讨论的问题。
我稍微展开点讲。我觉得在目前的制度框架内,工会完全独立不行,不独立也不行,那么相对独立至少是可能的,这也是工会有所作为的根本保证。先说说国企的工会。国企工会的组织形式比较健全,尽管缺乏独立性,但是在国企系统内工会的相对独立还是可以实现的。譬如,专职的工会干部由工人选举产生,直接接受上级工会的领导和工人的监督,他们的工资待遇也由上级工会、工人来支付;厂长无权随意解雇工会干部,企业党委也不能直接干涉工会干部的去留(我们强调工会要接受党的领导,但可操作的最好状态应该是一种垂直的、专业的领导关系);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规定企业要抽取一部分利润作为工会活动的经费。这样,工会具备了相对独立性,对改善国企与工人的关系,推动国企的发展将有很大的帮助。而民企、外企工会相对独立性的建构可能更容易做到、更快实现。因为,民企和外企与国家的关系主要是税收,不像国企本身就是国家的企业,全国总工会相对于民企和外企是独立的,可以直接加强对企业工会的领导。
由于目前工人对工会的监督机制是欠缺的,我们还要谨防工会组织官僚化的问题。我一再强调,工会干部一定要由工人选举产生,因为这样就为工人“弹劾”不合格的工会干部,“问”不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干部的“责”提供了可能。此外,上级工会要注重对工会专职人才的培养。要胜任工会工作,工会干部的素质一定得过硬,需要专业知识、实践经验和职业道德等等。
为什么要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
记者:刚刚和您讨论的工会缺位、工会不作为现象,可以说大都是在探讨劳动力所有者的权益如何不受资本所有者牵制的问题。我们想知道,劳动力所有者和资本所有者一定是以对立和冲突的形态存在的吗?有没有一种可以使双方共赢的、和谐的存在形态?工会在这方面又需要做什么呢?
胡守钧:对于这一问题,我认为首先要从多个角度把劳动力和资本的关系再看得清楚点。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工人代表劳动力,老板代表资本,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是既对立又统一的。一方面,他们存在冲突,工人的工资高了,老板的利润就低了;工人的工资低了,老板的利润就高了,双方都希望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他们相互依赖,工人离开老板没有工资,老板离开工人没有利润。他们之间的互斥性和互补性,决定了他们为了合理分割利润可以讨价还价,也只有实现合理分割,才能实现效益的最大化。从行政学的角度看,他们之间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既有对立又有统一。一方面,他们存在冲突,管理者要管束被管理者,被管理者不希望被管束。另一方面,他们也相互依赖,没有被管理者,就没有管理者;没有管理者也不行,工人的工作需要一定的秩序。他们之间的互斥性和互补性,决定了他们存在斗争和妥协,为的是合理分享权力;也只有实现合理分享,才能实现价值的最大化。当然,我们还可以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我们会发现,劳动力所有者与资本所有者的关系的根本问题就在于怎样合理分享利润、权力等,实现双方利益的最大化。当然,这一定是利益的相对最大化。
看清楚了这对关系,我们就可以继续探讨如何实现双方利益的相对最大化。这就需要工会的组建、工会的有所作为,通过工人代表与老板的讨价还价,划定双方共同认可的权限。因为这个权限如果不为双方所认可,不是和谐共生的状态,一旦过分损害一方的利益,最终也会损害另一方的利益。此外,还有一种在行业层面协商谈判的理想状态,就是工会组织与商会组织通过讨价还价,划定双方共同认可的权限,从而保证双方利益相对最大化的实现。谈到这里,其实还隐藏着一个前提,也是前面提到过的,即双方的力量要达到势均力敌,才能很好地讨价还价,划定大家都认可的权限。而当下的情况是,老板占有资源,处于优势;工人要通过工会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要有说话的分量,只有一个足以有效与老板抗衡的手段,就是不干活了。但是,如果一波人不干活了,又有一波人主动去填补这个缺口,抢着干活怎么办?很显然,这是集体而不是个人的事情,工会在此必须充分发挥协调作用。而且,我们要明确一点:不干活绝不是为了不干活而不干活,不是要把老板彻底打倒,不是要扰乱社会的秩序,而是为了作为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迫使老板能和工人站在同一个阶梯上,商讨如何合理分享利益的问题。有了这一条,我相信很多矿难可以避免。当然,工人的理智和理性也是必须提醒的,斗争哲学是不可取的,和谐共生应该成为工会组织行动的基本理念。
记者:这些应该需要整个制度环境建设的共同努力吧。如果让我们的讨论更有操作性,让和谐的劳资关系可以早日“成真”,您觉得在当前制度环境的建设中,有哪些环节是从现在起就可以着手改善的?
胡守钧:我认为首先应从政府做起。从经济学上讲,政府要正确认识各种要素在经济中的贡献,不仅要看到资本,还要看到技术和劳动力的作用,要一视同仁地对待他们。不过,这也不表示没有重点,比如在资本相对短缺时,可以着力吸纳资本。问题是,着力吸纳资本并不等于对资本所有者礼遇有加,对普通工人看不上眼。因此,在这一点上政府一定要紧扣公权力的核心——公平。老子有句话,“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管子也有句话,“政者,正也”。我们说,公权力是为了主持社会的公道,为了维护社会的秩序,为了使社会一直充满活力。因此,使用公权力者在劳动力和资本的博弈过程中,必须是一个公正的裁判者,要注意到谁是弱势,需要帮助,从而保持一个平衡。但是现在,有些地方政府的官员,因为资本短缺,就引进资金,进而发展到对老板顶礼膜拜,最后官商勾结,把工人的利益压到最低,劳资和谐无法保证,社会和谐更看不到希望。除了用权力捞取资本,官商勾结的另一种可怕的形式是公权力被资本收购,比如某个证件不全、违法开采煤矿的矿主既是老板又是地方人大代表,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指望公权力主持公道?而不管是哪一种官商勾结形式的存在,对工人来说都是莫大的灾难。
制度环境建设与媒体自律亦有关系。媒体是“无冕之王”,我们可以说它也拥有一定的公权力,特别是由于我国社会的许多媒体本身就是政府的组成部分,公权力的性质更强。那么,它的基本使用原则也应是公平,要正确对待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等。而现在不少媒体却患了拜金主义的病,大量的媒体少见有专设工人栏目的,工人要通过媒体维护自己的权益就非常困难。说得远些,现在房地产行业的调控为什么那么艰难,除了一些地方政府的官员、银行的不配合,媒体刊登大量房地产广告的不配合,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这里还有学者的问题。由于学者的话语权在社会中能够发挥一定影响,这就要求学者讲实话、有社会良知,不能老为资本讲话。我很不理解在基尼系数达到0.4以后,还有不少学者大谈“没问题、差距不大”。试问,一旦某些公权力、媒体、学者一一和资本病态结合,同声相应,工人还可能有说话的空间吗?
记者:是呀,工人和工会属于社会大系统,需要每个人的关爱。胡老师,现在有个比较流行的说法,“一次分配讲效率,二次分配讲公平,三次分配讲社会责任”,不知您可否用简单的几句话概括一下工会在这三次分配中的定位?
胡守钧:我们上面讨论的全部内容都是关于一次分配的,我们在探讨工人如何通过工会与老板讨论还价,得到合理、有效率的回报(让工人有动力,不断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为企业和社会创造价值)。对此,我不再多说。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不管多健全的市场经济都会造成贫富差距,因为如果没有差距,这个市场经济是没有活力的。现在的关键是,有了差距以后我们怎样谨防差距过大,如何把它控制在合理的度上。而由于工会代表农民工、代表转制工人,这部分工人的弱势地位非常突出,他们在医疗、教育等方面存在许多困难,就此而言,工会必须要参与到二次分配的讨论中,或者说有相应的代表参与二次分配法律的起草,能够提出自己的意见,因为,在法理公正中立法公正是基础。当然,工会在二次分配的讨价还价中也要以社会共生论为指导,树立和谐共生的理念,不能放弃应有的权利,该争取的一定要争取,但是也不能要求过多,因为,如果工人所争取到的社会保障太高了,就可能会影响其他利益群体,甚至是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这个合理的福利线的商定,还要考虑到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不过,就目前情况来说,社会保障线偏低,应该适当提高。对于第三次分配,我觉得工会在自愿、在道德感召的情况下,可以量力而行,和其他社会组织共同参与到社会救助、捐赠等公益性事业中去。应当说,工会在此方面的发展空间还相当大。
当然,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不仅需要工会,还需要商会。工会代表工人,商会代表老板,合理分享,和谐共生。关于重建商会的问题,我们可以下次讨论。
记者:谢谢您,相信广大读者会和我们一样对工会有全新而深刻的认识。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江晋参与了本文的采访和录音整理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