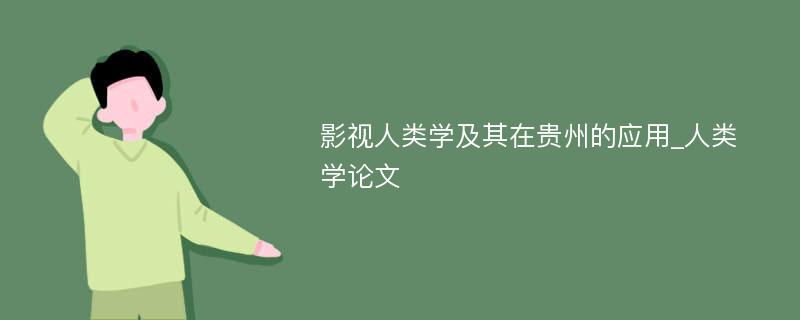
对影视人类学的认识及其在贵州的运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学论文,贵州论文,影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影视人类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在我国建国初期就开始了。1995年4月24-28日在首都北京以此为命题召开的“影视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却又属首次,这说明我们的理论研究已落后于实际。因此,这个会议就更显得十分必要和及时。
影视人类学,是以影视为手段从事人类学研究的一门学科,或以人类学影片为载体从事人类学研究的一门学科,属于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与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史前人类学、精神分析人类学等学科不同,不是以内容为界定,而是以手段、载体为界定的一门学科。它本身是一个集人类学、影视学两大综合性理论于一体的新的综合体,它又具有自己的特征。
在我国,早在本世纪50年代中期,新中国建立不久,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少数民族十分关心和重视,在向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派出数千人的庞大专业队伍进行社会历史调查的时候,就拍摄了一批人类学影片。这批人类学影片是我国的宝贵财富。当时,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正发生着迅速的变化,不少东西处于逐渐消失状态。把少数民族地区各少数民族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奴隶制社会、农奴制社会、领主制社会、封建制社会等不同时期的经济、政治状况的社会历史资料真实地、运用活动的形象化的声像手段系统地拍摄保存下来,确实具有不朽的历史功绩,为日后的人类学研究和教学提供了很有学术价值的资料和教材。这些人类学影片的拍摄 ,首先是得到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国家最高领导人指示要“抢救”这些资料,有关国家机关,如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文化部民族文化工作指导委员会等对拍摄这些影片的目的、意义、方法等都有明确、系统的指示。毛泽东主席在建国初期就指出:“对于少数民族的社会情况,应该赶快调查抢救,要求对全国少数民族正在发生急剧变化的社会制度、物质文化生活进行“抢救”。周恩来同志在谈到拍摄《少数民族科学记录片》时说,“这个工作很有意义,拍这样的片子是对世界的贡献。”①全国人大负责领导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彭真同志指出:调查的目的之一是进行科学研究,号召民族研究工作者要深入到少数民族中去,立志做当代的“摩尔根”,这里当然包括拍摄科学纪录片。拍摄的手法和内容上则“要以科技片的手法,客观地反映少数民族的生活与斗争。”②拍摄中,正确处理艺术与学术的关系、“艺术要服从科学研究的要求……要服从科学历史纪录的真实性。”对具体拍摄,“首先要真实的,其次是具有该民族特点的东西。”③同时,在这些科学记录片的拍摄中,始终有一支具有民族学科专业知识的科研人员参加。因此,使得我国的第一批人类学影片从理论到专业知识方面就站到了一个较高的起点上,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影视人类学理论体系提供了丰富多彩生动的科学资料,为我国影视人类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影视人类学既然是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应该说,它研究拍摄内容与人类学研究的内容是一致的,“是研究人类本身及其新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起源、形成、发展规律的学科”④,内容十分广泛。它包括人类的社会历史、社会组织、社会结构、人类起源、民族、部落、民族的形成、发展、消亡及社会活动,人类体质等;物质文化方面,如各种生产工具,生产形态、生产方式、饮食、居住等;精神文化方面,如民族风情、节日庆典、婚丧习俗、宗教信仰、伦理礼仪、文化艺术等等,都是影视人类学的研究内容。
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变化,向前发展着的。古代社会是什么样子?我们今天无法让历史恢复原始,只能通过口碑传说,文字记载,地下发掘的实物和历史遗物进行分析理解,研究推理,得到一些形象的认识,甚至可以根据得到的认识形象,摸拟出古代社会的情景,但毕竟时代久远、不是直接的状况。只有通过人类学影片对当今世界一些地区、一些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滞后,有的甚至还停留在原始社会等前资本主义各种社会形态的直接拍摄纪录,才能帮助我们对古代社会的文字、文物更直接的了解,把研究推向深入。人类学影片能把人类在不同环境的社会生活状况真实地纪录下来,让人们(包括以后的人们)通过活动形象更直接真实地了解,对人类学自身和社会发展的认识,运用社会发展的规律以改造社会,改造自然。同时,还可以运用人类学影片,进行相互的交流,传递信息,加深对人类自身的认识研究。
人类学影片的拍摄,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大都是由人类学研究者和影视拍摄者共同合作而制作出来的。一般来讲,需要经过选择题材、撰写提纲、现场拍摄和编辑制作这4个阶段。选择题材,这应该是由人类学研究者来完成,题材选择得好坏,这与研究人员的素质和对题材熟悉程度有关。一个素质较低、学术造诣不高的研究人员,就不可能站到一定的学术高度。反之,一个有较高素质,较高学术造诣的研究人员就能选择准题材,就能站在一定的高度。因此,每位影视人类学研究者,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学科素质和学术造诣。同时,选准选好题材,又与研究人员对题材内容的熟悉程度有关,一个素质高的研究人员,如果对题材不了解,或了解不深,也有可能对题材定得不准确。撰写提纲,在选好题材的基础上,必须撰写好拍摄提纲。从某个意义上讲,一部人类学影片拍摄的好坏,是由提纲决定的。提纲要内容明确、主题突出,脉络清晰,主次分明,便于拍摄者掌握、操作,才能达到影片拍摄的目的。现场拍摄,主要由摄影者来完成,摄影者首先要弄清楚影片拍摄目的,熟悉内容。这里,在拍摄之前,人类学研究者有必要从学术价值、内容概况、重点,拍摄内容的演进等全过程都让摄影者了解清楚,让其操作中有主动权,而人类学研究者还必须亲临现场,及时处理现场临时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或者纠正,弥补摄影者出现的偏差和不足,只有这样,才能使拍出的影片成为“用人类学家的眼光,去选择、捕捉那些能体现人类学这门学科揭示事物客观规律,探求真理的内容。使这种影片能区别于其他影片,成为具有人类学学科特征的科学影片。”⑤让研究指导拍摄,艺术服务于学术。编辑制作中,必须严格地按照拍摄提纲的要求和原则进行,审片中严格把关,和解说词是否一致、准确,整个影片编辑制作得主题突出,脉络清晰,使观看效果更佳。应当指出的是:不管是人类学影片的研究者或者摄制者,都必须深入实地,深入调查研究,这是至关重要的。只有深入实地,认真地了解和研究被拍对象,经过观察、访问和研究,方能发掘和掌握某一事件发生或存在的环境、空间和情景,乃至更深层次的内容。只有这样,才能拍摄出好的人类学影视片。
人类学影视片,具有形象语言的特征,一部成功的人类学影视片,就是一项完整的人类学研究成果,其学术价值并不亚于一篇学术论文。所不同者,学术论文是研究者用文字(有时配以照片)表述自己的学术思想,反映研究的成果,用个人的辛勤劳动就能完成。而人类学影片则不同,它必须是“人类学家的学术思想与摄影学艺术和制作技术相结合的产物”。⑥人类学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必须通过摄影家到现场拍摄,用影片的形式(包括研究者给影片配录的解说词)以图象和解说词来表现学术思想,用两者的结合(研究者和摄影者为1人完成除外)来完成,反映研究成果。但是,正因为人类学影视片有图象能让对方观看,应该说效果是学术论文一般所不能及的。
(二)
贵州省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有16个世居少数民族,其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34.69%(其65.31%为汉族),以大的杂居和小的聚居为特点分布全省各地,其中超过百万人口的有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10万人口以上的有彝族、水族、仡佬族、回族、白族等。对于人类学研究者来说,贵州既是一个神秘的地方,更是一块宝地。
贵州省建省较晚,开发也较晚,历史上被称为所谓“蛮荒”、“化外”之地。与全国比较,经济发展较慢而滞后,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省内边远少数民族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领主制经济形态,地主制经济形态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等。贵州是一个典型的高原山区,部分地区地理情况复杂,有“十里不同天”之谚,交通闭塞,即使相距不远的两个村寨,相处数百年,只要不同民族都仍传承着自己的语言、服饰、生活习俗等独自的特点。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推进,贵州农村的社会、经济、生活正发生着越来越快的变化,许多宝贵的属于人类学研究的资料正在急剧演变之中,有的濒于消失,或正在消失,或即将消失。
面对贵州的现实情况,建国以来至今,已拍摄了数十部基本属于人类学影视片的电影片或电视片。本世纪50年代进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起至70年代末,就拍摄了《苗族》、《清水江流域苗族的婚姻》、《苗族的工艺美术》、《苗族的节日》、《苗族的舞蹈》等5部电影片。其中《苗族》片,记录了台江县反排寨苗族的生产、生活,还记录了从江县加勉寨春耕生产和丧葬习俗。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这方面的工作随着整个民族研究工作的发展和活跃也随之活跃起来,不仅是从事民族研究工作者参与拍摄了一些影视片,即使没有专业民族研究工作者参与而拍摄的影视片,也为人类学的研究记录了许多宝贵的资料。如纪录西南少数民族音乐的电视系列片——《西部之乐》等,贵州就拍摄了《流动的鼓》,以贵州少数民族的木鼓和铜鼓为内容线索,反映了苗族的祖先崇拜,苗族的生存和发展。该片吸收了许多有关的研究成果,记录了各地木鼓的不同类型和功能。又如贵州电视台拍摄的《土家族薅草锣鼓》,就真实地纪录了贵州土家族的薅草锣鼓。⑦这里,特别值得提到的是: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拍摄的贵州少数民族风情史料电影片,它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1990年9月,贵州省民委决定对省内的少数民族拍摄20多部电影片,摄制的目的和作用是很明确的。在向省政府的报告中指出:拍摄的目的在于“抢救贵州民族文化的需要”和“国内外民族学专家学者文化交流和科学研究的需要”。并指出:“摄制好贵州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继承贵州优秀民族文化的作用”,“为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以及音乐、舞蹈、戏剧、美术等各门学科提供宝贵的材料,对繁荣我省乃至全国有关科学研究事业有着重要的作用”。经过4年多的努力,现已拍出了《贵州布依族》、《贵州侗族》、《贵州苗族》、《贵州土家族》、《贵州仡佬族》、《梵山乌水育土家》、《笙鼓传人》、《鼓楼情韵》、《依山傍水布依人》等电影片,彝族、水族等民族的影视片正在拍摄或积极准备拍摄之中。这些影片有这样一些特点:(1)选择了很好的时机。正是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卫生,许多属于历史遗留下的传统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东西也正在发生急剧变化的前提下,抓住时机,努力抢救。(2)拍摄工作始终坚持了从事民族研究的专业人员和本民族干部参与,在拍摄以上所列影片中,我们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的大部分人员都参与了自己研究的民族的拍摄脚本的编写工作。(3)由电影制片厂的专业摄影家负责拍摄,他们肯于学习,对拍摄对象较熟悉,如在拍摄土家族的影片前,笔者就用了两个半天向他们讲述了拍摄内容,从内容介绍到具体每一组镜头的演进过程,注意事项到学术价值,使他们拍摄中有主动权。他们无不感慨地说:“等我们把这部片子拍完以后,都成半个民族学家啦!”(4)由于有专业研究者和本民族人员的参与和把关,因此影片的内容准确可靠,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资料价值。(5)由于贵州省民委的重视和亲自主持,经费上得到了保证,也是这些影片能顺利完成的重要原因。当然,也还略显不足,主要是综合性的内容,个性内容不突出,不详细。
建国以来,贵州逐渐形成了一支较好的民族研究队伍。以贵州省民族研究所为中心,在本世纪50年代社会历史调查的基础上,于1983年开始,对贵州省内的少数民族进行多学科全方位的调查,每年进行一期,至今已有13期,参加单位除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外,还有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民族学院、贵州省教育科研所、贵州省博物馆、贵州民族文化宫等科研教学单位的数十名专业研究人员参加,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和一批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笔者从1983年起就参加调查,1986年起参与了组织领导工作,一直延续至今从未间断。
如前所述,贵州是一块人类学研究的宝地,有很丰富的内容值得研究,为影视人类学研究者提供了十分广阔而又大有作为的天地。贵州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均有自己的特点,诸如土司制度、村寨组织、寨老制度、聚族而居的特征仍然局部保留,苗族、瑶族的支系问题,苗族的“鼓社”制度,布依族的“六马”组织,亭目制度、水族的“十六水”、“棒”组织,彝族的则奚制度,侗族的洞款组织,瑶族的“油锅”组织,“石牌制度”、“爷头洞崽”问题,苗族的“议榔”、水族的“阿康”等,还有民屯、军屯及军屯中的“屯堡人”等问题。在生产方面的内容也很丰富,诸如在边远地区还残存有石犁、木犁、锄耕、木耙的耕田方式,还有刀耕火种的遗俗,有的地方“活路头”对生产仍有指挥作用,部分地方布依族还有牧童节。一般民族的吃新节在一年中只举行一次,而在土家族和水族中却要举行两次。在各民族中有求风调雨顺、粮食丰收的节日,如土家族的“祭风神”就很具特色。在习俗方面就更丰富了,各民族都有众多的节日,仅苗族就有百个以上,其中“四月八”闻名遐尔,还有姊妹节、过苗年、跳花、龙船节等。又如水族的端节、卯节,彝族的火把节等等。各民族的服饰五花十色,斑烂多彩,苗族的服饰有上百种,彝族服饰不仅优美,而且种类繁多。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纺织技术,有各式织布机和织染技术、刺绣、挑花工艺。苗族的蜡染、侗族的侗锦、侗布、土家族的织锦、水族的花椒布、布依族的纳锦、土花布等都享誉海内外。居住方面有干栏式建筑、吊脚楼,侗族独特的鼓楼,布依族的石头建筑。各民族的婚姻丧葬都独具特色,自有情趣。文化方面,贵州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创世歌,祖先歌,反映历史迁徙的迁徙歌,苗族、布依族、侗族、水族等都有芦笙,有芦笙舞。百粤族系的民族都崇尚铜鼓,水族铜鼓舞享誉国内,在侗族和苗族中都十分盛行,形成一种文化,水族的斗牛舞、土家族的茅谷斯舞、摆手舞都很有特色。贵州的傩文化享誉海内外,被称为中国戏剧的“活化石”,土家族的傩可分为傩祭、傩舞、傩戏三类,彝族的撮泰吉、布依族的地戏都属于傩文化。贵州绝大部分少数民族都有银饰,各民族传统工艺加工的各种装饰品构成了各民族的银饰文化。贵州各民族的原始宗教更是丰富多彩,各有特色,普遍都有祭山神、祭田神、祭寨神、祭石神、祭猎神等。占卜有鸡骨卜、竹卦、蛋卦米卦等构成系列,成为另一种文化现象。等等。
总之,贵州各少数民族中,值得人类学研究的东西十分丰富,值得影视人类学研究拍摄的内容异彩纷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区特色,有着十分可喜的未来,是我们影视人类学研究者大有作为施展才华的地方。
注释:
①见《光明日报》1978年2月25日《周总理的关怀鼓舞着社会科学工作者》。
②转引自李德君《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发展历程及前景展望》,1992《广西民族研究》NO.4
③转引自张江华《我国影视人类学历史发展纪事》
④见《人类学研究》P17。中国人类学会编。
⑤见《民族研究》1994年第6期。P34,P31。
⑥薅草锣鼓,是土家族生产中的一种习俗。一队人从事农业劳动时,有数人在一旁敲击锣鼓,边敲边唱以激励生产,统一进度,催促后进,以达提高劳动效益的目的。
标签:人类学论文; 苗族论文; 贵州民族论文; 贵州论文; 苗族节日论文; 苗族舞蹈论文; 苗族刺绣论文; 苗族吊脚楼论文; 文化论文; 土家族吊脚楼论文; 水族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