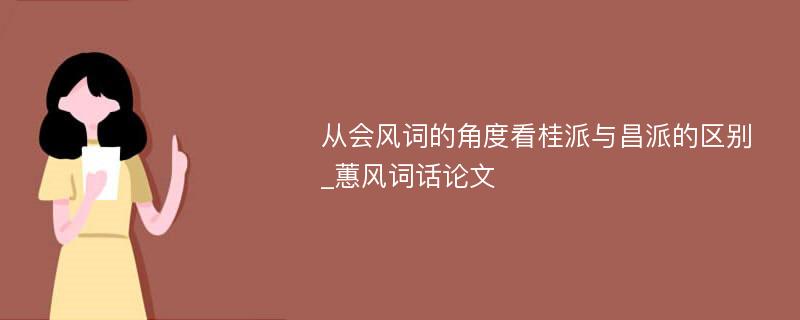
从《蕙风词话》看桂派与常派的分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词话论文,分野论文,看桂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王鹏运、朱祖谋、郑文焯和况周颐被称为晚清四大词人。这个以桂林人王鹏运为首的并在他的影响下所形成的词人群体,起始于十九世纪末,形成壮大于二十世纪前期,活跃在中国文坛达半个世纪之久,他们在清代词学史上是属于常派的延续,还是已属于另一个新词派呢?本文依据况周颐的《蕙风词话》(以下简称《词话》),对此提出一点不同的看法。
一、寄托与“即性灵,即寄托”
倡言政治寄托,是常派词学的主要标志,也是其与其他词派相区分的界别点。况书中所言“即性灵,即寄托”与“勿呆寄托”,是大相径庭的。
况书对寄托问题,有一段相对集中的论述。
词贵有寄托,所贵者流露于不自知,触发于弗克自己。身世之感,通于性灵。即性灵,即寄托,非二物相比附也。横亘一寄托于搦管之先,此物此志,千首一律,则是门面语耳,略无变化之陈言耳。于无变化中求变化,而其所谓寄托,乃益非真……夫词如唐之金荃,宋之珠玉,何尝有寄托,何尝不卓绝千古,何庸为是非真之寄托耶!(《词话》卷五,以下引况氏《词话》文,只注卷数,不写书名)
从这段话看,况氏似乎是在要求有出自性灵的真寄托,反对徒具门面的假寄托,其意是要完善寄托。但是他把性灵和寄托等同起来,实际上是否定了常派所倡导的寄托。因为常派所言的寄托,原是有特定内涵的,是限制在政治社会伦理学的范围之内,而不是依随词人兴到之处和性灵所在随意命笔的。张惠言首倡“诗人比兴”,就是要求词与“变风之义,骚人之歌”(《词选叙》)看齐。其后继者周济则进而要求所写都应是有关国事民生最重大的问题,既是词篇,又是史笔。张、周这“比兴之义”,原是从传统诗学“诗言志”中派生出来的,诗人必须先有“志”,先立意于此,然后才可以搦笔而为诗。“横亘一寄托于搦管之先”,本是常派移植“诗人比兴”于词的题中应有之义。况氏加以反对,这不但直接否定了周济的“夫词,非寄托不入”的命题,而且也动摇了“诗言志”这一古老的诗人用以安顿创作生命的神圣原则。此其一。其二,况氏高标性灵,认为寄托出自性灵,是性灵的自然流露。词中有性灵,也就有了寄托。所谓“即性灵,即寄托,非二物相比附也。”这就进而说,性灵就是寄托。性灵,是出自诗人一已之心,包括性情、气质、灵感等来自主观并含有某些先天性的因素。诗人与诗人,此性灵与彼性灵,其异如面,是各不相同的。常派寄托说所要求的寓意,是来自传统诗学中“诗言志”之“志”。“志”即理想怀抱,是要受儒家思想主导和规范的。性灵,是个体意识;“志”则属群体意识,词中的寓意,受到群体意识的规范,并能有意识的即自觉的体现在词中,就是常派所要求的寄托;任性灵的自由流露,且流露还不自知的意蕴,则是况氏所要求的真寄托,由于词人此时此地的遭际和学养的不同,这任性灵流露的意蕴,有可能是身世之感的社会政治伦理意识,更多的则不是这方面的感触。只要是真情的自然流露,都是好词。这受触发而不得不流露的身世之感,可以通于常派所言的寄托。性灵与寄托,词义交叉处在此,也仅在此。从两者立论的基本点和命题的理论性质说,性灵与寄托,个体性与群体性是不相同的。其三,况氏用温庭筠和晏殊两人词为论据。证明有性灵即有寄托。温、晏词受到张、周赞许,被推为有寄托的典范。但况氏认为,温、晏词“何尝有寄托”?意即实际上没有常派所要求的政治寄托。但两人词都是真性灵的流露,因而“何尝不卓绝千古,何庸为是非真之寄托耶!”况氏将其认为本无政治寄托的温、晏词,称赞为有“真之寄托”,这不但无限扩大了本有特定含意的寄托一词的内涵,而且也是在论证性灵可以涵盖寄托,取代寄托。从以上三点看,我们是很难把况氏的“即性灵,即寄托”,看成是常派理论体系内的延伸和发展。
况周颐对咏物词的论述,就更直接提出了反对呆寄托。
问,咏物如何始佳?答:未易言佳,先勿涉呆,一呆典故,二呆寄托,三呆刻画,呆衬托。去斯三者,能成词不易,矧复能佳,是真佳矣。题中的精蕴在,题外之远致尤佳。自性灵中出佳,从追琢中来亦佳。
以性灵语咏物,以沈著之笔达出,斯为无上上乘。(卷五)
咏物词应借物言志,因而必须有寄托,这是周济的论断。其《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评及王沂孙的咏物词言:“咏物最争托意,隶事处以意贯穿,碧山胜场也。”况氏之言,似乎正是针对周济此论而发的。如果说,况氏在专论寄托时,还力图把寄托纳入性灵之中;那么他在论咏物词时,就只谈性灵而不言寄托,并进而要求“勿呆寄托”。至于“以沈著之笔达出”云云,则是对词的体格更高层次的审美规范,此意待下文专题评述。
况周颐反对呆寄托,显然是针对常派高语寄托所带来的弊病而发的。这种弊病,也可以说是常派寄托说与生俱有的。甚至还可以说是传统诗学“比兴”说本身所固有的。常派的大师们脑子里始终绷紧寄托这根弦。写词时,一心想着寄托;读词和说词时,则戴着寄托这付眼镜。而这正是况氏所批评的呆寄托。他用性灵来代替寄托;如其说是在完善常派的寄托,不如说是从立意的基点上作了带有根本性的校正,从词意的生成,词的生命力的所在等,对此作了新的界说。况氏之论,与晚清许多评词者在总体上尊奉张、周之论,只是反对过分拘泥的是不同的。
况氏反对呆寄托,其意当然不是在反对和取消词中有真情的政治寄托。桂派的创始者以及包括况氏在内的主要词人,都受到常派重立意的影响和启示,历史的大转折与强烈的身世之感,使他们写出许多有政治寓意的词篇。况书在评析历代词作时,也曾高度评价此类作品。如言元好问“遭遇国变”,“其神州陆沉之痛,铜驼荆棘之伤,往往寄托于词。”但同时认为,遗山的故国之思,“其苦衷之万不得已,大都流露不自知。”(卷三)是日益增长并充塞于胸中的痛苦,不得不倾吐,而且多半是吐露不自知不自觉。这就是说,元好问词的寄托,是缘于他特有的性情,特有的遭际所形成的特有的性灵的自然流露。后之学词者,无此性情,无此遭遇,无此苦衷的,都不应该咿呀学舌。况氏把寄托从属于性灵。提出“即性灵,即寄托”的新命题,正是从古人的优秀词篇和他们自己创作实践中总结出来,并针对当前创作流弊而发的。
况氏的性灵说与常派的寄托说相区别,其根本之点何在呢?常派立足于“善”,“真”与“美”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善”;况氏则立论于“真”,“善”必须出自“真”,“美”也是生于“真”并能显现“真”,才有其价值。从创作论中的心物关系看,况氏的性灵说,是侧重强调心的一端,侧重于谈性情、襟怀、学养等。至于心对物的感发,特别是物对心的反作用,以及心与物的回还交往等,都论述的不够。但他对心的一端的论述,却很有理论深度。譬如说从性灵中流露出的真情和深情,其中还包括深藏于内未被作者明确认知的潜意识。这似乎是前人所未曾言的,但却是创作真谛的一重要发现。诗词意境中被读者新感知的言外之意,其中就有来自作者的潜意识,而不仅是作者的艺术安排和接受者的新创造。这些话,不是长期在创作中有深切体验并勤于思索的人,是说不出来的,这应是对创作思维认知上的新贡献。
二、“高揖温、韦”与花间词不可学
况周颐对常州词论的批评,还不仅限于寄托问题,对唐五代词的评价及词径说等,也都有其立异之处。
唐五代词并不易学,五代词尤不必学,何也?五代词人丁运会,迁流至极,燕酣成风,藻丽相尚。其所为词,即能沉至,祗在词中;艳而有骨,祗是艳骨。学之能造其域,未为斯道增重。矧徒得其似乎。其铮铮佼佼者,如李重光之性灵,韦端已之风度,冯正中之堂庑,岂操觚之士能方其万一。自余风云月露之作,本自华而不实,吾复皮相求之,则赢秦氏所云甚无谓矣。晚近某词派,其地与时,并距常州派近。为之倡者,揭橥花间,自附高格,涂饰金粉,绝无内心。与评文家所云“浮烟涨墨”曷以异。虽无本之文,不足以自行,历年垂百,衍派未广,一编之传,亦足贻误初学。尝求其故,盖天事绌、性情少者所为,曷如不为之为愈也。(卷一)
花间至不易学。其蔽也,袭其貌似,其中空空如也。所谓麒麟楦也。或取前人句中意境,而纡折变化之,而雕琢、勾勒等弊出焉。以尖为新,以纤为艳,词之风格日靡,真意尽漓。反不如国初名家本色语,或犹近于沉著、浓厚也。庸讵知花间高绝,即或词学甚深,颇能窥两宋堂奥,对于花间,犹为望尘却步耶。
词有穆之一境,静而兼厚、重、大也。淡而穆不易,浓而穆更难。知此,可以读《花间集》。(卷二)
清人首倡学花间词的,当是康熙年间的王士祯和邹祗谟。王、邹从花间词中求神韵,况周颐曾给予尖锐批评,指出清人“词格纤靡,实始于康熙中,倚声一集,有以启之。”(卷五)而《倚声集》正是王、邹编选的。但王士祯赞“花间之妙”是“蹙金结绣而无痕迹”(《花草蒙拾》),并未言其华实兼茂。而且王、邹也不是“其地与时,并距常州派近。”况氏在这里所批评的,显然不是王、邹词派。
高标唐五代词,并在以温庭筠、韦庄为代表的花间词中求深意的是张惠言,其所编《词选》及其后继者所编《续词选》,唐五代词尤其是温、韦词占有很大比例。周济也是以“深美宏约”归美温词,以“高揖温、韦”作为词中有史的验证。况氏之论与张、周之言是相对立的。
对于唐五代词,况氏既言“不易学”,更强调“不必学”,而归结点则是不要去学。所谓“不必学”,是基于对花间词在总体上评价低。认为其时“燕酣成风,藻饰相尚”,多数词都是“风云月露之作,本自华而不实”。而尤其是词的体格不高,即使“学之能造其域,未为斯道增重。”这是从词格立论,否定了向其学习的必要性。而所谓“不易学”,是指其中少数“铮铮佼佼”者,如李煜、韦庄、冯延巳(当然也包括温庭筠)各自的独造之诣。在况氏看来,这极少数名家词的高绝处,是很难学的,甚至是学不到的。即使词学造诣很高的人,“犹为望尘却步”,一般的学词者,又岂能“方其万一”。结论当然是不必去学了。所以无论从“不必学”抑或从“不易学”的角度说,提倡学花间词都是错误的。当然也有极个别的人,可以例外。即词学造诣已臻高格,并深知“淡而穆不易,浓而穆更难”的人,可以去学。“穆”,是指“静而兼厚、重、大”,而“浓”,实指艳。这也就是说,已具穆境的人,进而追求“穆”与“艳”的完美结合,就可以向花间词中学华与艳了。况周颐后期的词作,就是力图从艳词中体现厚、重、大,走的就是这条路子。况氏是自视很高的人,自认为所走的是最难的路,并取得成功。至于其他人,当然还是“不可学”,也是“不必学”的。
至于倡之者和追随者的学习效果问题,况氏的批评是异常尖锐的,“为之倡者,揭橥花间,自附高格”。而所作则是“涂饰金粉,绝无内心”,这当然无价值可言。而随之学者,出现的弊端就更多了。“其蔽也,袭其貌似,其中空空如也。”“以尖为新,以纤为艳,词之风格日靡,真意尽漓……”况氏把当日词坛上的纤靡之风,几乎全归咎于学花间词了。
况氏的论述,首先涉及到对花间词的评价问题,同时还须辨析他所批评的“某词派”,究竟何所指,对花间词,况氏的意见是得失并存的。在清代后期词坛上,把花间词与宋人词等量齐观,称之为有文有质。在一片赞美声中,况氏敢于指出其中多数人词“本是华而不实”,这是需要理论勇气的,也较为符合实际情况。但花间词以及未选入《花间集》的唐五代人词,以其很高的艺术成就,彪炳词史,形成了词体要眇宜修的特点,从而能与诗分途,确立了词体在文学史上的独立地位。它对宋人以及后代词人的创作,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况氏虽然也肯定了其中的“铮铮佼佼者”的独绝之处,但从总体上持基本否定的态度,甚至认为是后代纤靡词风的源头,学之不但无益,而且有害。这显然是不恰当的。这是他从体格一端立论所产生的偏颇。
至于况氏所尖锐指责的“其地与时并距常州派近”的“晚近某词派”,是否包括了或者就是暗示常派呢?从表层看,张惠言兄弟及周济所编的词选,地位突出,入选篇数也较多的唐五代人,也大都被况氏称之为“铮铮佼佼者”,似乎两者无太大的区别。但仔细一比较,两者的分歧还是很大的。对唐五代词,常派是从整体上加以肯定,而况氏则持基本否定态度。常派称温、韦词有寄托,因而是可学的,而且是必须学的;况氏所称许的是其中极少人的独绝处,因而是不易学的,而且也是不必学的。两者对花间词的总体评价,立论的原则和结论都不相同。两者虽有此不同,但我们还不能由此肯定况氏的批评矛头实际指向。如果能了解到况周颐对常州词派所持的基本态度,也许对弄清这个问题,以及本文所有的论题,都能有所帮助。
况周颐对常派的评价,是肯定还是否定,抑或两者兼而有之呢?翻遍况氏《词话》,却找不到答案,甚至没有一句话直接语及张惠言及常派。似乎这位在清代中后期词坛上有重大影响的人及其所创立的词派,是无足轻重,或根本不存在一样。但是我们再看他对清人词的总评价,就不难从中获得一些明确的信息。清人以及今人论词史,都是说,词盛于宋而衰于元明,至清则是中兴。况氏则认为,词不衰于元明,而衰于清,康熙中叶是分界线。他把词格的纤靡,首先归罪于王士祯,接着批评了浙派朱彝尊、厉鹗等人。其后如何呢?他没有说。再读他的《词学清义》中有关清人词的评述,就恍然大悟,原来常派词人也在他的否定之列:“清朝人词(断自康熙中叶),不必看,尤不宜看。看之未必获益,一中其病,便不可医也。且也无暇看。吾人应读之书,浩如烟海,即应读之词,亦悉数难尽。能有几许闰晷。看此浮花浪蕊,媚行烟视,灾梨祸枣之作耶!”(《词学季刊》创刊号)这里所言的“断自康熙中叶”的“不必看,尤不宜看”的“清朝人词”,难道不是已很明确的把嘉道以来的常派人词划入其内吗?蔡嵩云进而说:“清词亦只末季,王、朱、郑、况数家可以取法,余不足观也。”(《柯亭词论》)就是对况氏之言的阐发。按照况、蔡之见,清词的中兴,是始于晚清王、朱、郑、况四大词人。这当然是偏见,不足取的。这是基于体格之一端论词所带来的严重局限。但从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他对常派是持否定态度的,是自外于常派的。那么上引他所指责的“历年垂百”,“其地与时并距常州派近”的“晚近某词派”,不就是暗示常派吗!只不过是用不直接点名的点名的办法,打的是擦边球而已。对于这位对常派持激烈批评态度并自外于他们的人,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他纳入常派之内呢?
三、从学宋人词看两者词径说的分歧
学习宋人词,况周颐与常派一样,都认为必须由此入门。但学习的途径、取法之点和归宿处,都与之不同。常派的开拓者周济,有鉴于张惠言所圈定的学习范围,过于宽泛和重点不突出。将学词的取径严格限定在宋词范围内,提出一条“问途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的学词路子。这张标明了起点、中转站和终点的行程图,是用来指导和规范所有学词的人创作道路的,即所谓“余所望世之为词人者,盖如此”。(《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周济的词径说,在晚清词人中影响是很大的。况氏的词径说,却与此不同,在《蓼园词选序》中,对包括周济在内的“认筌执象”的各种词径说提出批评,进而提出不能执一以自绳的理由。
近人操觚为词,辄曰吾学五代,学北宋,学南宋。近十数年,学清真,梦窗者尤多。以是自刻绳,自表白,认筌执象,非知人之言也。词之为道,贵乎有性情,有襟抱,涉世少,读书多。平日求词词外,临时取境题外。尽素寸心,八极万仞,恢之弥广,斯按之愈深。返象外于环中,出自然于追琢,率吾性之所近……庶几神明与古人通,奚必迹象与古人合,矧乎于众古人中而龂龂祈合一古人也……晚近轻佻纤巧,饾饤叫嚣诸失,皆门径之误中之。《词话》卷一,对此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填词,智者之事,而顾认筌执象若是乎。吾有吾之性情,吾有吾之襟抱,与夫聪明才力。欲得人之力。欲得人之似,先失已之真,得其似矣,即已落斯人后,吾词格不稍降乎。
中国文士,受儒家的言必称三代的影响。倡师古,进而到复古以至泥古,以龂龂求与古人合。这在诗词文评中,几乎所在皆有,而明清尤甚。周济结合两宋词史,论述了王、吴、辛、周四家各自的特点、成就以及在宋词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不能说没有理论深度。但他却异常慎重的推出这条学词的道路,要求所有的词人都来按图索骥,这实在是很不可取,也无普遍意义可言。以周邦彦的浑化之境说,他当然不是走“向途碧山”这条路获得的。那么后人即使想臻于浑化,为什么一定要“问途碧山”云云呢。质诸周济,恐怕他也很难回答。况氏指出此路不可取,弊病很多,应该说是有道理的。
况氏反对直接取径于古人,是立论于填词一种艺术创造,非步趋模拟可成。这种创造,既是基于性情、襟抱、才能等主观质素,更有赖于平素的学养和临场时的创造性的艺术构思和表达。这创造性的艺术思维,也就必然带有个人的鲜明烙印,而不是龂龂求与古人合所能办到的。况氏所论由创作个性所主导的创作规律,除所言“涉世外,读书多”,而不太重视生活的积累对创作构思之不可少外,其精要处是深得创作真谛的,所论也深中师古者的要害。
清人浙、常之争,学南宋抑或学北宋,是其论争的一大焦点。况氏认为,这两者都是错误的。即使学之能至其域,造其境,也已落下乘,更何况也不可能完全得人之似。在清人词话的一片师古声中,读况书至此等处,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立论于创新,并不意味着放弃学习优秀传统。况氏是很强调学习宋人词的,认为两宋词人成就最高,学词者舍此无由入门。他把学词分为初学词和自为词两个不同的阶级。前者是可以而且也必须步趋古人的,但在自为词时,就应脱离师范,以吾言写吾心成吾词,而不能墨守一家之言以自绳刻。这不同阶段的不同要求,应该说是符合词人写作进程中的实际情况的。
当然,况氏对学宋人词,也有其共同的要求,这就是体格的神致。尤其是体格,更为他所瞩目。其言见《宋词三百首序》:
词学极盛于两宋,读宋人词,当于体格、神致间求之,而体格尤重于神致。以浑成之一境为学人必赴之程境,更有进于浑成者,要非可躐而至,此关系学力者也。神致由性灵出,即体格之至美,积发而为清晖芳气而不可掩者也。
《宋词三百首》系朱祖谋所编,是从选学的角度集中体现了桂派的词学宗尚。这宗尚,也就写在况《序》上。现就体格神致言。体格,体现在词中的,就是重、拙、大词格,这是桂派词学最高层次的美学宗尚。神致或神韵,即事外远致。这是指性情、襟抱、雅洁、高致及超凡脱俗等精神气质在词境中的显现。体格与神致,是相得而益彰的。学宋贤词,既要重视其“体格之至美”,也要从其神致间学习其精神品质,以完善自己的精神气质,提高精神境界。在自为词时,也就能积发而不可掩的流露,使词臻于高格胜境。这是况氏对学宋人词的最后归结之点。
况氏的词径说与周济之论相比较,不但在最后的归点上,亦即体现在审美宗尚上各不相同;在实现各自宗尚的具体途径上,也道不同不相与谋。周济的归结点是通过浑化之境表现立意上的比兴寄托。词境的浑化与寄托是对所有作家的要求,是共同的规范。况氏则在“以浑成之一境为学人必赴之程境”的基础上,进而要求体现出体格、神致之美。由于“神致由性灵出”,而“体格之至美”也是由性灵中“积发而为清晖芳气”的自然呈现。性灵是个性化的,体格和神致都从性灵中流出,也就必然带有个性的烙印。与此相联系的,是实现各自宗尚的具体途径,况氏要求遵循各自性灵、才性等特点,发挥其所长。这就是说,要重视创作个性,使词中有我。周济则要求遵循同一的创作程式,强调的是创作共性。重视创作个性与强调创作共性的不同,是立论于“真”与立论于“善”在词径说上的反映。
四、词学新宗尚:重、拙、大
重、拙、大是桂派词学的最高宗尚,也是况氏《词话》着重阐述的核心命题。以重、拙、大为权衡还是以寄托为旨归,是桂派与常派最重要的区分点。这也是蔡嵩云在《柯亭词论》中所提出的,桂派词人在创作上“以立意为体,故体格颇高”,与常派词人“以立为本”的不同处在理论倡导上的反映。
据况氏的《餐樱词自序》,这重、拙、大的提出,是缘起于王鹏运,王氏正是以此深刻地影响了朱、郑、况等人,改变了他们的词学好尚。王氏为什么要提出这一新命题,朱、郑在受到影响后在词评中有什么反映等,限于篇幅,这里只好从略。
从况氏的《自序》看,由于王氏的“规诫”和鼓励,由偏嗜轻艳一变而为宗尚气格,即所谓“体格为之一变”。创作上的变化和体会既如此深刻,理论上的认识也会很清楚和深入。这就是说,况氏的《词话》对此在理论上的阐发,是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王氏的见解,代表着桂派词学的主要意向。
况氏论词,首先高标作词“三要”。这既是想以此论题为全书的中心,独树一帜。也许还有完成王氏的遗志,反映这个创作群体词学意向的使命感。“作词有三要,曰重、拙、大,南渡诸贤不可及处在是。”(卷一)其后又补充说:“轻者重之反,巧者拙之反,纤者大之反。当知反戒矣。”(《词学讲义》)重、拙、大的反义是轻、巧、纤,那么正义是什么?况氏未直接作出简明的界定,尤其是未直接言及“大”字义。亲聆况氏教诲的蔡嵩云,对此作了相当明确的解说:“何谓重、大、拙,则人难晓。如略示其端,此三字须分别看,重谓力量,大谓气概,拙为古致。工夫火候到时,方有此境。以书喻之最易明,如汉魏六朝碑版,即重、大、拙三者俱备。”(《柯亭词论》)蔡氏之言,是从表达与显现体格的角度上谈的,与作者立论的角度和付予的内涵,应该说是相切合的。这是至今还是独一无二的解释。从立意的眼光审视一切,却是我们许多言词者的共俱只眼。
以下据况氏的词论与词评,参以蔡嵩云的提示,对三字的义界及互相关系,作一评说,以见其与常派以“立意为本”的差别。
重 何谓“重”?“重者,沉著之谓,在气格,不在字句。”(卷一)这几句话,在同书卷二又重复一次,并联系吴文英词作进一步申说:
……于梦窗词庶几见之。即其芬菲铿丽之作,中间俊字艳字,莫不有沉挚之思,灏瀚之气,挟之以流转。令人玩索而不能尽,则其中之所存者厚。沉著者,厚之发见乎外者也。欲学梦窗之致密,先学梦窗之沉著。即致密,即沉著。非出乎致密之外,超乎致密之上,别有沉著之一境。梦窗与苏、辛二公,实殊流而同源。其所为不同,则梦窗致密其外耳。其至高至精处,虽拟议形容之,未易得其神似。
近人学梦窗,辄从密处入手。梦窗密处,能令无数丽字,一一生动飞舞,如万花为春,非若雕璚蹙绣,毫无生气也。如何能运动无数丽字,恃聪明,尤恃魄力。如何能有魄力,惟厚乃有魄力,梦窗密处易学,厚处难学。
“重”即“沉著”。他还解释说:“情真理足,笔力能包举之。纯任自然,不假锤炼,则沉著二字之诠释也。”(卷一)“情真理足,笔力包举之”是“厚之发见乎外”另一种说法。“重”与“厚”的关系密切,并有赖于“厚”故又称“厚重”。但“厚”不能等同于“重”。“厚”指含意厚,意味厚,亦即“情真理足”。词的情意深厚,可以包括出自真情的讽谕寄托,但不限于此。举凡宇宙人生的思考,立身处世之道,一事一物的观感,以及乡土之思,交情的冷暖和亲情、恋情等,只要感触深,情意挚,都可称为“厚”。“厚”是“重”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厚”,就不可能有“重”。“重”是“厚之发见乎外”。也就是能把深意有力地表达出来,使人能观之,能感之。这就有赖于“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的笔力了,所以“情真理足”是“厚”,“笔力包举之”就是“重”。验之于梦窗词,“沉挚之思”是言“厚”、“灏瀚之气”则是“大”,“挟之以流转”,就是“重量”。这“重”与“大”,笔力和气概,形诸词中,是密切相连的。况氏之论与朱祖谋评吴文英词:“力破余地”,“擩染大笔何淋漓”!(《疆村老人评词》)是出自同一机枢。
至于言吴词与苏、辛词“实殊流而同源”云云,则是说,三家词都能“厚”兼“重”且“大”,这是言“同源”;但笔力和文气的表现形式则不相同,吴词在“密”,能挟无数丽字飞动,苏词在疏宕、清雄,辛词则沉郁、激扬。这就是他所言的“殊流”。况氏言三家词“同源”,是推重气格、厚重,即立论于体格所得出的结论。
况氏的“三要”,不标“厚”,而标“重”,显然他更为重视情意呈现的力度,重视力的美,并藉此以提高词的体格。虽然他也是非常强调“情真理足”。情意深厚的。
拙 何谓“拙”?《词话》卷一引王鹏运言:“宋人拙处不可及,国初诸老拙处不可及。”这“不可及”的“拙处”,应当包括同卷所言“昔贤朴厚醇至之作”及卷二赞“周、姜词朴厚”的“朴”字义。朴、质、真纯、真率、自然等,应是“朴”字的正解,而巧、矜、致饰、雕琢、勾勒以及颦眉、龋齿、楚楚作态等,都是“拙”字的反义。
况氏曾以“顽”字释“拙”,对“哀感顽艳”这一成语,作了新的解释:
问哀感顽艳“顽”字云何诠。释曰:“拙不可及,融重与大于拙之中,郁勃久之,有不得已者出乎其中,而不自知,乃至不可解,其殆庶几乎。犹有一言蔽之,若赤子之笑啼然。看似至易,而实至难者也。”(卷五)
“哀感顽艳”,出自繁钦的《与魏太子(曹丕)书》。“顽”本指愚与痴,“艳”则是美与贤。原书是言歌女所奏哀音,听之者无论贤愚美丑,都受到感发而激动。况氏从中拈出“顽”字释“拙”字,是弃原意而生新意。从况氏所付予的新意看,所谓“郁勃久之”云云,是言长期酝酿积聚在胸中的情意,愈积愈厚,无法摆脱,在无意中流露。其中还渗透了“不自知,乃至不可解”的潜意识,这是言情意深厚。而“赤子之笑啼然”,则是说形诸语言,质朴、自然、纯真、这就是“拙”。况氏以“顽”释“拙不可及”,意即指此。
从况氏这段论述看,“拙”与意厚也密切相连,是“厚”的另一种表现形态。“厚”与“重”相连为“厚重”,与“拙”相连则常称“朴厚”。“拙”与“厚”也是不能等同,不能互相替代的。“拙”是外在呈现,即所谓“若赤子之笑啼然”,是一种自然而真纯的形态。王鹏运还提出过“自然从追琢中出”的命题,强调自然是通过艺术提炼和加工而获得的,是通过雕饰而进于天然。“拙”的形成过程是很艰辛的,不是率尔命笔所能致。所以这看似平易实精纯,是很难达到的境地。
验之于其词评,况书就曾以“哀感顽艳”四字赞屈不均词,可以作为上论的注脚。屈氏为亡明的遗民,其《哀江南》词四首,流露了沧桑之感和无奈何的愁思。况氏引录其中三首,用“无限凄惋”、“哀感顽艳,亦复可泣可歌”(卷五)等语予以评赞。这“哀感顽艳”,就是言其情真语朴,有真纯朴素之美。
况书称周邦彦词朴厚,可以作为王鹏运所言“宋人拙处不可及”的例证:
沈伯时作《乐府指迷》,于清真词推许甚至,惟以“天便教人,霎时厮见何妨。”“梦魂凝想鸳侣”等句为不可学,则非真能知词者也……此等语愈朴愈厚,愈厚愈雅,至真之情,由性灵肺腑中流出,不妨说尽而愈无尽……诚如清真等句,惟有学之不能到耳。如曰不可学也,讵必颦眉搔首,作态几许,然后出之,乃为可学耶,明以来词纤艳少骨,致斯道为之不尊,未始非伯时之言阶之厉矣。窃尝以刻印比之,自六代作者以萦纡拗折为工,而两汉方正平直之气荡然无复存者”。(卷二)
这里所说的清真词的“朴厚”,就是有从肺腑中流出的“至真之情”和真率的不加装束的表达。这是“不可及”的“宋人拙处”的表现之一。如果说上引屈大均词是寄寓了故国之思,那么周词的“至真之情”,则纯系写男女之情和对情侣的思恋了。这再次说明,况氏所言意厚,并不限于君国之思,男女的恋情,也是包括在内的。他还进而言,此种情语,是“愈朴愈厚,愈厚愈雅”,“不妨说尽而愈无尽”。把沈义父指责的周词俗句,升格而为雅,许之为“拙”。比喻为两汉的“有方正平直之气”的印刻。甚至还认为,沈义父以质为俗,要对“明已来词纤艳少骨,致斯道为之不尊”负责。由此可见“拙”之所指以及在桂派所倡导的体格中的位置。
况书引王鹏运语对欧阳炯艳词《浣溪沙》的评价,似乎也是基于这一点。
《花间集》欧阳炯《浣溪沙》云:“兰麝细香闻喘息,绮罗纤缕见肌肤,此时还恨薄情无。”自有艳词以来,殆莫艳于此矣。半塘僧鹜曰:“奚翅艳而已,直是大且重”。苟无花间词笔,孰敢为斯语者。
欧阳此词是对性行为的直接描写,可等同于今日西方电影镜头的“床上戏”。桂派创始人的推许和况氏记录在案,引来了不同的评价。是之者称能以小见大,写闺房之事以喻君臣之义;非之者则直言是情趣低下的表现。言此词是以小见大的寄托,姑且不论欧阳炯是否有此用意,就是王、况二人,恐怕也无此认识。前引况书评花间词,就把包括欧阳词在内的多数词作,统归于“华而不实”之列,并批评从花间词中求寄托是“皮相求之”,他们自己当然不会再做此“甚无谓”之事了。细按王、况之意,看来还是从“愈朴愈厚”立论,肯定其情感的真诚和表达的真率,与赞赏周邦彦词意同。
况氏以意深为“厚”,以质朴、真露为“拙”,把情意的自然呈现作为体格的一端加以强调,应该说,这是符合诗词艺术的真谛的。但他过分强调真露,甚至不顾及内容的亵渎性,从这一点说,终究是不可取的。
大 何谓“大”,况书无专条诠释,论者常以“托旨甚大”为“大”,亦即以寄托君国之思为“大”,这虽有其言之成理之处,但不一定符合作者的原意。“大”的反义是“纤”,“纤”有细小柔弱意,“纤靡”,是指词的体格气质柔弱,而不是指立意上的琐屑。细小和卑微。蔡嵩云言,“大谓气概”。这是从体格立论,应是符合原意的。
“大谓气概”,近似于前人所言的文气、风骨、风格、风度、气象等,而更为强调在词中的显现,从况成评刘辰翁词,可获此消息。
须溪词,风格遒上似稼轩,情辞跌岩似遗山。有时意笔俱化,纯任天倪,竟能略似坡公。往往独到之处,能以中锋达意,以中声赴节。……如衡论全体大段,以骨干气息为主,则必举全首而言……由是推之全卷乃至口占、漫与之作,而其骨干气息具在此。须溪之所以不可及乎。(卷二)
刘辰翁为南宋末著名的爱国词人,况氏评刘词,一字未涉及到盈溢于刘词中的故国之思,而是集中笔墨赞其振起词篇的“骨干气息”。所谓似稼轩的“风格遒上”,似遗山的“情辞跌宕”,有时也能略似东坡的“意笔俱化,纯任天倪”等,也就是三家词的风格的特点和文气的表现,都可以用“大”来涵盖。刘词还有他独具的个性,即“能以中锋达意,以中声赴节”。“中锋达意”是言能集中笔墨,在关键处用突进的方式表情达意,且无过与不及之弊;“中声赴节”,指用悲伤的音调,从音序节奏上表达其来去无端的痛苦哀愁的意绪。这是刘词的文气形诸于词的一大特点,也就是刘词大处重处独具特点之所在。
况氏对元人刘因词的评价,也能看出其大处之所指,其《樵庵词跋》云:刘因词“真挚语见性情,和平语见学养……其重处大处亦不可及。”(《词籍序跋萃编》)参看其《词话》卷三中对刘因词的具体评论:“文清词以性情朴厚胜”,能“寓骚雅于冲夷,足浓郁于平淡”。并引王鹏运评语:“樵庵词朴厚深醇中,有真趣洋溢”,这“朴厚深醇”,即是“拙”与“厚”,而“寓骚雅于冲夷,足浓郁于平淡”以及“真趣洋溢”等,也就是刘因词文气的特点,亦即“大”处与“重”处之所在了。其他如言赵忠简词的“促节哀音”,梦窗词的“灏瀚之气”,党承旨词的“清劲之气”,刘秉忠词的“雄廓”,以及夏完淳、陈子龙、王夫之等人词的“含婀娜于刚健”等,都是言他们各自文气的特点、亦即言其“大”的具体表现。
如果说,“重”前提是意厚,表现在笔力;“拙”,出自真情,表现为质朴、自然;那么,“大”,则自来襟怀、抱负,也取决于才情,表现则在文气。或清雄,或遒上,或冲夷,或内刚健而外婀娜。行文或妥贴排奡,或顿挫有生气,或中锋突进,或行云流水,舒卷自如,或低徊往复,掩抑零乱等。可因人而异,各有其特色。
重、拙、大三者,虽各有规定性,但表现在词中,又是互相依存,相互作用的。其凝聚点是在“真”字上,“重”“拙”都必须出自“真”,“大”之于文气,也要有真气、生气贯注其间。“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作为佳。”(卷一)即是此意,前引况氏以“哀感顽艳”的“顽”字释“拙”,言其意是真率、真纯,而所言“融重与大于拙之中”云云,就是在说明三者的联接点在“真”字上。
“三要”作为桂派在体格上的最高宗尚,就其性质说,就是属于群体性共同性的审美规范,但况氏立论于“真”要求词中有我。失我,即失真,就是伤格或降格。所以“三要”既是共同的崇尚,又要求必须体现在各个不同的个体之中,显示出个性的特色。这就与明代前后七子所倡导的以摹拟古人为能事的格调派划清了界限。
“三要”作为体格上的要求,是在立意的基础上,进而对词格的显现作出新的美学界定,这与常派在立意本身的审美要求不同。这也就是蔡嵩云所言的“以立意为体”与“以立意为本”大别之所在。虽然对立意的内涵也有立论于“真”与立论于“善”的不同。至于两者在一些具体命题上论说的差异,则是由于基本立论点的不同所必然产生的结果。
《蕙风词话》涉及面较广,重要的论题也较多,如词心说、词经说、词笔说和声律说等,本文均没有或极少涉及。王、朱、郑的词论,特别是擅长论词的郑文焯,其论说往往与况氏有相异处,本文也未加论列。笔者仅就况氏所论体格及寄托等与常派有明显区别的问题,作了一些比较和评说。如能引起进一步的探讨,进而能给桂派词论在清代词论史以新的定位,则是笔者的奢望。误解和评析不当之处,尚祈教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