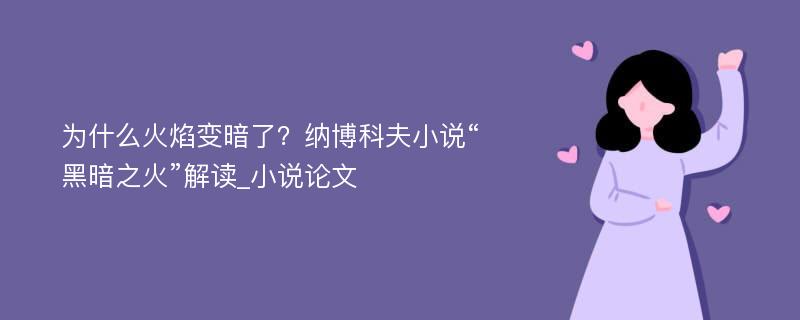
火焰为何微暗?——纳博科夫小说《微暗的火》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火焰论文,博科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微暗的火》(以下简称《微》)(注:Vladimir Nabokov,Pale Fire,New York:G.P.Putnam's Sons,A Perigee Book,1962.以下引文皆依据此版本,只在引文后括号内标明页码,不再一一作注。)出版已近四十年了。多年来,人们对它作了各种不同的诠释,可谓众说纷纭,直至今日仍不能下一断语——小说的内涵和意义显得不可穷尽。近年来,文学界对《微》的评价越来越高,学者们或用它来印证自己的新鲜理论,或用新鲜理论来诠释它,莫不感到得心应手。诚如戴维·兰普顿所说,用读者反应理论和解构主义理论等新潮理论分析这一作品,是一种有诱惑力、也很有意义的工作。(注:David Rampton,Vladimir Nabokov,Moden Novelists Series,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3,p.105,p.110; p.104.)这个现象说明小说本身具有丰富性和开放性,和当代西方文化也有某些深刻的契合之处。
下面两种观点,则是在较长时间内有影响,且为多数学者所接受的:
其一,这部小说与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的花园》相似,既有吸引人的故事情节,又有关于小说创作理论和技巧的思索。比如梅里瓦尔比较了纳博科夫和博尔赫斯的小说,并写了《纳博科夫和博尔赫斯在技巧上的招摇》一文(注:Patricia Merivale, "The Flaunting
of Artifice in Vladimir Nabokov and Jorge Louis Borges,
"in Jaime Alazrakied.,Critical Essays on Jorge Louis Borges,Boston:G.K.Hall & Co.,1987.);托尼·谭纳也在《词语之城:美国小说1950—1970》一书中探讨了纳博科夫在小说,特别是《微》中所用的镜子、象棋、游戏、迷宫、影子等意象,并且认为他和博尔赫斯有相似之处。(注:Tony Tanner, City of
Words: American Fiction 1950-1970,New York:Harper & Row,1977.)
其二,该小说主要用了学术性注释这一形式——这样的书也许不宜称作小说。难道小说真像巴思所说,已是“枯涸的文学”?难道小说创作已到了穷途末路,竟要靠古怪眩目的形式招揽读者?早在1962年,作家兼评论家德怀特·麦克唐纳就在《党派评论》上撰文对纳博科夫提出尖锐批评。(注:See Partisan Review,Summer 1962, in
NormanPage ed., Nabokov:The Critical Heritage, London:Routlege & Kegan Paul,1982,pp.138-139.)戴维·兰普顿也认为,《微》的“杂交形式”(hybrid status )甚至使人对“小说”一词的意义产生怀疑。(注: David Rampton,Vladimir Nabokov,Moden NovelistsSeries,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3,p.105,p.110;p.104.)
作为一部堪称经典的作品,《微》应当是研究现代小说和小说理论的学者的必读书。然而,该书在形式方面的试验过于大胆,和大家的阅读习惯格格不入,使大多数读者认为它晦涩难懂。最近,在研究罗兰·巴特时,我发现远在巴黎的巴特与纳博科夫在思想和写作方式上都有许多契合之处。戴着巴特的有色眼镜,我重读了《微》,发现许多问题迎刃而解。
本文将运用罗兰·巴特关于文本的理论,对小说《微》作出新的诠释。我相信,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探讨小说,可以挖掘出一些新的东西。
我认为,纳博科夫之所以用“微暗的火”一词作小说和小说中一首长诗的标题,乃是由于该词是关于现代文本和创作活动的隐喻,(注:纳博科夫还用蝴蝶、火焰、镜子等意象来隐喻小说写作。这些意象在《微》中频频出现,作者通过它们来表达自己对小说创作机制的关注。由于这些意象的存在,小说《微》便具有“自我意识性”和“自我反省性”。关于这两个术语的定义,参见Raymond Federman,Critifiction:Postmodern Essays,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3,pp.20-21。)而现代意义上的文本——无论它是一首叙事长诗,还是一部小说——也不再模仿什么绝对理念,诸如统一性、决定性和整体性这类理念的光亮已不能将文本照亮。现代文本容纳了“多种声音”,具有复调性、差异性和自娱性。相对于传统的“可读”文本,它是“可写的”。
一
从形式上看,《微》的确显得有些古怪。它由序言、999 行长诗(按:本为1,000行,最后一行未完成,因为诗人被杀害了)、注释和索引构成,用的是标准的诗歌笺注样式。长诗的名字也是《微暗的火》,其作者为著名诗人约翰·榭得,“他那嵯峨的特征和朴实的风格应当让人想到罗伯特·弗罗斯特”。(注:Donald E. Morton, Vladimir Nabokov,New York: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Co.,Inc.,1974,p.105,p.105.)而序言则是由诗歌的诠释者和作品的主人公查尔斯·金伯特所写,采用“神经兮兮的漫谈式风格,并且有不相关的感叹和明显的校对错误”。(注:Donald E.Morton,Vladimir Nabokov,New York: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Co.,Inc.,1974,p.105,p.105.)榭得的诗将由金伯特整理、作注,其结果可想而知。注释部分无论从篇幅还是重要性上看,都是全书的主干。诚如莫尔斯所言,“‘评注之文’本身也自成一种特殊的文学创作技巧……注释文本完全可以成为与所注文献并行的独立文本”。(注: A.A.Moles,"Le commentaire
comme methode de composition,"in Frank Coppieters & Didier L.Gyvaerts eds.,Functional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Ghent:E.Story-Scientia,1978,p.37.)
罗兰·巴特曾有一段关于评论(即注释)的话与我们当下的讨论相关:“怎样阅读评论?只有一种方式:既然我在此是二度读者,我就应当转变立场:评论的愉悦,并不在于成为作者的知己——这样反倒会与他失之交臂,我应当具有偷窥癖:我偷偷地观看他人的快感,我成为反常的;因而注释在我看来是一个文本,一个有裂缝的外壳。作家反常(他在写作时的快感是无功用的),评论和评论的阅读者则是双倍和三倍的反常,以此类推,以至无穷”。(注:Roland Barthes,Le plaisir du texte,Editions du Seuil,1973,p.31,p.19,p.13.)在本论文的语境中,巴特的话显得格外精辟。诗人兼作家榭得可以写出明净如弗罗斯特的篇什,但在其评注者金伯特眼中,他同样是反常的:
身体畸形,头发蓬乱成抹布似的一团,圆胖的手指,黄色的指甲,无神的双眼之下吊着眼袋。要想认出他来,惟有把这些看作从他的内在自我排出的废品;促使废品排出的是那些盼求尽善尽美的力量,这些力量同样净化和雕凿了他的诗章。他把自己删除了。
(《微》,第26页。黑体为笔者所加,下同。)
榭得的诗之所以显得纯净,是因为它早已删掉了破坏其统一性、完整性的所有因素。由于金伯特所讲的关于泽布腊国君的故事足以动摇长诗的统一性,所以该故事未能进入榭得的诗——金伯特只能从榭得废弃不用的卡片上勉强寻找到该故事的痕迹。为了维护自己思想和作品的完美,榭得宁愿把金伯特看作胡言乱语的疯子,认为“他有意剥下自己单调而不幸的过去,并杜撰出过去的辉煌。那不过是用左手翻开新的一页”。(《微》,第238页)可以看出,尽管榭得也对金伯特表示同情, 但这种同情极为有限。难怪金伯特要说:
大家知道,我曾坚定而愚蠢地相信:榭得会把泽布腊国君的故事写进诗中……但我可爱的泽布腊在哪里?……这首诗是自传性的,带有鲜明的阿巴拉契亚地区色彩,用了老一套的新蒲伯式散文体叙事……但却少了我那种特别神奇的疯狂色彩……
(《微》,第296页)
金伯特觉得,有必要为榭得的诗“重新造型”,给它加上片段的、断裂性的、恋人絮语似的注释,从整一而单纯的诗中寻出反常的东西,在那些若隐若现,意义含混的部位植入自己的欲望,因为正是在意义的显现—消失之处,即文本的断裂之处存在“滋生爱欲的区域”。(注:Roland Barthes,Le plaisir du texte,Editions du Seuil,1973,p.31,p.19,p.13.)
巴特曾把巴尔扎克的《萨拉辛》打碎成561个阅读单位,类似地, 金伯特也将榭得的长诗分割为131个阅读单位。 如果说榭得的诗是“可读的文本”,那么金伯特的注释堪称“可写的文本”。作为“可读的文本”,榭得的诗是“‘自然的’”,带有决定性的、连续的、整一的、统一的、以所指为基础的连贯整体”;作为“可写的文本”,金伯特的注乃是“无限多元,对能指的自由游戏开放,具有差异性,不受表现论约束,对于决定性、统一性、整体性意义方面的要求不屑一顾”。(注:这是巴巴拉·约翰逊在讨论巴特的《S/ Z 》时说的话, 见Barbara Johnson,The Critical Difference,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0,p.6,p.5。)
要注意的是,金伯特并未毁坏和糟蹋长诗《微暗的火》。他仅仅对它作了反建构式(de-construction)解读,并试图揭示其真实面目。 由于长诗以貌似单纯的整一形式掩盖和压制了其它声音、形式和欲望,因此确有必要分解其结构和形式,还其多声、多元、多差异的本来面目。巴巴拉·约翰逊也曾深刻地指出:
解构并非毁灭的同义词。事实上,它更接近于分析这个词最初的意义,即undo,恢复原状,解除,与de-con-struct同义。 解构文本时不能随便怀疑或任意颠覆,需要小心翼翼地引导出文本内部固有的冲突力量。如果在解构式阅读中毁坏了什么,那也不是文本,而是凌驾于其他表意方式之上并且明目张胆地实行统治的表意方式……(注:这是巴巴拉·约翰逊在讨论巴特的《S/Z》时说的话,见 BarbaraJohnson,The Critical Difference,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0,p.6,p.5。)
事实上,当巴特将《萨拉辛》分割为561个语汇时,他所做的, 不过是用解构式阅读指明该文本中固有的五种编码——情节、阐释、文化、语义和象征编码。与此相似, 当金伯特把长诗《微暗的火》分解成131个阅读单位时,他是想“讨回公道”,他喋喋不休,念念不忘要恢复长诗原有的丰富性和复调性。他说:
我更加仔细地重读了《微暗的火》……在诗中,特别是诗的异文中,我发现了我的思想零落的回响和闪光,发现了我的荣耀的涟漪。现在我对这首诗有了新的怜悯与温存。它像一个性情多变的小小尤物,一度被黑色的巨人拐走和享用,但现在安全地回到我们中间……伤疤依然存在,并引起伤痛,但现在我却怀着奇怪的感恩心情,去亲吻那些湿润而沉重的眼睑,去抚爱那被玷污了的肉体。我对这首诗的评注……代表了我的一种努力;我试图清理出那些回响和那些小小的火焰,那些微暗得如同磷火的暗示;我还要把那些多次出现的,潜在地受惠于我的地方一股脑儿地找出来……
(《微》,第297页)
可以看出,金伯特为诗歌作注,乃是为了从中找回注释者的身影,并挖掘诗中固有的异己性成分。
二
小说《微》中有两个颇具象征性的细节,它们所体现的两种异己思想或异己力量使长诗《微暗的火》和小说《微》微暗晦涩,具有未完成性——火焰的光亮因而微暗。细节之一是格雷德斯在书中的行动完全与榭得的写作同步;细节之二是金伯特具有偷窥癖,时常透过窗帘的缝隙窥视诗人的隐私。
雅各布·格雷德斯又名“杰克·德格里、德·格雷、达尔古斯、维诺格雷德斯、列宁格雷德斯,等等;此人在细碎之事上相当在行”。(《微》,第307页)这句话说明他是有代表性的普通人(Everyman), 其名字可以随意拼写,只是一种能指符号。他刺杀金伯特和最终杀害榭得的行动与榭得的诗歌创作同步:
由于一种例外的巧合(或许这种巧合为榭得的对位性诗歌艺术所固有),咱们的诗人似乎在此提到了一个人的名字(Gradual,Gray); 三周以后诗人将在一个生死关头见到此人,但在这个时候(七月二日),他还不可能知道存在这样一个人(Jacob Gradus)……他(格雷德斯)离开西欧时,心中藏着卑鄙的目的,口袋里藏着上膛的手枪。他出发这天,在一块不相干的土地上,一个不相干的诗人正在开始写他的长诗《微暗的火》的第二章。我们将在头脑里时时装着格雷德斯,随着他从遥远朦胧的泽布腊到绿色的阿巴拉契亚。他从整首诗中穿行而过,走在有韵律的路上,越过一个韵脚……一行一行荡到页脚,就像是从树枝荡向树枝;在两个词之间他躲了起来(见第596行注), 又在新的一章的开始重新出现,以抑扬格姿态越走越近,穿过街道,坐在五音步电梯里上行,手里提着行李箱,走出电梯,乘上思想的列车,走进旅馆大厅,关掉床头灯;这时,榭得正好抹掉一个词。这人睡着的时候,诗人放下笔,结束了晚上的工作。
(《微》,第77-78页)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在此无须一一列举。我们已能看出,格雷德斯乃是榭得之“对位性诗歌”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作为对位(复调中的一类)中的一种对立声音和力量,格雷德斯在诗歌的第1,000 行象征性地杀害了诗人,这标志着他所代表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谋害了诗人及其作品。这还说明,榭得的做法——“将自己关在黄色的象牙塔里冥想”(《微》,第286页)——既不可取,也不现实。 阿巴拉契亚的田园风光和淳朴风情固然可以造就弗罗斯特式的诗人,但美国的现实社会生活却绝不会因为诗人的忽略而从诗歌中引退。不承认这一点,便只能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从以上所引的文字就可看出,即使榭得不知道格雷德斯的存在,这人照样可以大摇大摆地在诗歌的每一关键部位出现。换言之,此人的存在使榭得式的诗歌创作成为不可能。
格雷德斯所体现的,则是日益支配人们一切行为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他在出场时,行头中总是有廉价小商品和报纸。如所周知,商品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垄断人们的物质生活;报纸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垄断人们的精神生活。这些东西都有能力将人变得平庸。因评论纳博科夫而出名的玛丽·麦卡锡(注:玛丽·麦卡锡为纳博科夫的前妻,后与著名学者埃德蒙·威尔逊结为夫妇——二人均以私生活不检点著称。)对此亦深有同感。她说,格雷德斯这人没有理想和追求,刺杀别人的目的不过是将枪膛中的子弹射出去。联系到他即将行使刺杀计划时突然大闹腹泻,她分析说:
贪吃的格雷德斯一到阿巴拉契亚就大闹腹泻。他曾在百老汇的一家餐馆吃了法式土豆丝,一块正宗法式火腿三明治……这些东西正在他肚里大闹天宫。他把肚肠排空这件事可怕地对应于他把自动手枪排空;他是靠自动性生活的现代人。排空枪膛时,他在行使一种“自然的”功能(按:意即其生活的全部内容是吃喝、排泄和睡觉)。小说前面的某个地方还提到,他从谋杀行为中得到的些许快感,如同一个人在捏死一只黑头鸟时得到的一点儿快感。(注:Mary McCarthy,"A Bolt
From the Blue,"New Republic,CXLVI(June 4,1962),in Norman Page ed.,Nabokov:The Critical Heritage,1982,p.133.)
格雷德斯深受现代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的毒害,变得随波逐流,思想空虚,缺乏激情。除去吃喝、排泄和睡觉,便是寻求刺激。小说还写到,他实际上是一名有精神病的罪犯,曾被金伯特的房东法官哥尔斯密送进监狱。这一点更可证明,格雷德斯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普通的美国人。像他一样,大多数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美国人也或多或少患有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
还应当指出,格雷德斯也如同消费社会(consumer society)里铺天盖地而来的用于交换的商品,缺乏内在的深度和意义,乃是和“所指”关系破裂(rupture)的“能指”符号,自由地游戏着。 金伯特和纳博科夫的写作行为因而不无游戏意味。他们的“文体”就像一颗洋葱,由一层层皮包裹着,层层剥开,里面却一无所有——终极意义并不存在。(注:Roland Barthes,"Style and It's Image,"inSeymour Chatman ed.,Literary Style:A Symposium,London:Oxford Univ.Press,1971,p.10.)
再说金伯特先生。他的偷窥癖是“在那些可怕的夜晚”养成的。辗转难眠之时,他就去“观看朋友家的窗户,希望由此得到一丝安慰……”(《微》,第96页)其实金伯特的偷窥,还远不限于夜晚从窗户观望;不拘什么时刻,若有榭得在场,他的目光就极少从诗人身上移开。他对诗人的了解也多从窥视其隐私而来。有着同性恋倾向的金伯特还一厢情愿地认为他和榭得的关系是情侣式的。他多次提到自己如何焦急地盼望榭得的妻子西比尔快些出门,他才好早些跑去和诗人约会。有一回,想见诗人的心情过于迫切,他甚至在人家洗澡时强行闯入浴室。倒是榭得宽宏大量,表示理解:“西比尔,让他进来,他不会强奸我的。”(《微》,第264页)另一次榭得过生日, 金伯特为了能赠送一件足以表达其情义的礼物而颇费心思;礼物选好后,还题上一段温情脉脉的话——其谨慎、犹豫和多情之态恰与罗兰·巴特《恋人絮语》中的描述相仿。金伯特眼中的榭得因而也是女性化了的爱恋对象,没有男儿气概。金伯特把榭得描写成“难以确定性别”(《微》,第26页)的情人,使我们联想起《萨拉辛》中的萨拉辛和赞比内拉。
巴尔扎克的《萨拉辛》讲的是雕刻家萨拉辛对意大利“女高音歌手”赞比内拉的迷恋。萨拉辛不知意大利歌剧有一传统,是用男子而不是女人演女高音角色。他在赞比内拉身上看到了完美的女性形象,却不知其为男身。巴巴拉·约翰逊在评述《S/Z》时指出,萨拉辛有自恋倾向,他从赞比内拉身上读到的其实是自己的男子汉气概。赞比内拉的柔弱成为萨拉辛性能力的镜中形象——当然,这种形象是反转的。萨拉辛爱的并非女人,而是赞比内拉这样的阉歌手,“通过这种有所缺失的形象,他感到自己依然拥有。 ”(注: Barbara Johnson,The
Critical Difference,pp.9-10.pp.7-8.)约翰逊还说:
这个有关勾引和阉割的故事的有趣之处在于,它出人意料地反映了巴特本人的批评价值体系。因为当地宣扬“主导性文本将不断被打破”时,他难道不是在私下以为:诸如阉割一类的东西要比他所谓的“整体性意识形态”优越?“如果说文本从属于一种形式”,他写道,“那么这种形式并不是单一的……;它是片段,切片,是切割或抹擦过的网络。”事实上,或许可以认为巴尔扎克提到的理想女人和阉歌手的对立,正以隐喻的方式等同于巴特提出的可读文本和可写文本的对立。像可读文本一样,迷惑着萨拉辛的赞比内拉形象是对于完美统一性和整体性的颂扬……但,如同可写文本,赞比内拉是不完整的,不自然的,性别难以确认的。(注:Barbara Johnson,The Critical Difference,pp.9-10.pp.7-8.)
金伯特对榭得的迷恋与此类似。他密切关注榭得,是因为诗人如同一面镜子,使他从中看到自己,从而确立起自我意识。当他感到诗人及其作品所代表的象征性力量约束和压制了自己时,他就决心用一种幻想的方式去颠覆这些权威力量。结果,他从诗歌和诗人身上看出了瑕疵。正因为榭得的形象亦非完美无缺(“有所缺失”),金伯特才感觉自己依然拥有自我。于是,长诗《微暗的火》被瓦解为若干充满爱欲的片断,诗人也变成性别不明的人。可以认为,金伯特对诗人的关注与他对长诗创作过程的关注是密不可分的:榭得和他的诗表面上看来完整得无懈可击,可事实上,榭得是个不完整的人,他的诗矫揉造作,刻意模仿自然,反倒成了不自然的,兼具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制性。金伯特将榭得及其诗歌作象征性阉割,恰好颠覆了榭得这类美国文人所代表的某种权威意识形态。
金伯特在“索引”中指出:“大写字母G、K、S 分别代表本书的三个主要人物”,即刺客格雷德斯、流亡贵族金伯特和诗人榭得。(《微》,第303页)这暗示G、K、S是三而一,一而三的关系,互为化身和影子。G、K、S分别代表三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 并构成三股异己力量,使长诗《微暗的火》和小说《微》朦胧晦涩,具有开放性和未完成性。
可以看出,榭得是典型的美国学院派精英。
格雷德斯身上体现出五六十年代普通美国人的特征——缺乏个性和情趣,并在一定程度上遭受资产阶级政治话语的象征性阉割。(注:对于小说中的格雷德斯究竟代表什么,大家尽可见仁见智,我在这里讨论的是他的一个主要特征。)
金伯特代表了流亡到美国的欧洲贵族,经历过十月革命,逃到美国后想要与主流社会合流,但又常有社会边缘人的感慨。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性格古怪的流亡者正是纳博科夫本人的替身(double)。
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金伯特作为作者纳博科夫的替身,渴望成为和榭得一样的学院派精英诗人和作家,但又感到自己所属的文化背景、语言和习俗使自己难以如愿;而以格雷德斯为代表的平庸之辈总是试图同化金伯特,使他与他们一样碌碌无为,饱食终日。(注:有的评论家指出,刺客格雷德斯到达纽约时迷了路,正是华兹密斯大学的一些人指点他如何找到金伯特;杰拉尔德·艾默尔德还用汽车将他送到金伯特的住所。在一定程度上,是华兹密斯大学的同事们——那些和金伯特朝夕相处的人——谋害了他。)
榭得同样是纳博科夫和金伯特的替身,代表他们的生命或人格中作为作家的一面。
格雷德斯作为众人的化身,千方百计地影响大家,像影子一样令人难以摆脱。长诗和小说显得微暗,与此人有一定的关系。
三
约瑟芬·亨丁(Josephine Hending)曾经切中肯綮地指出:
有人试图将《微》政治化,结果小说被解释为具有寓意,即现代专制杀害了诗人,但饶恕了金伯特这类微不足道的学究。然而,这部小说看来是关于纳博科夫自身艺术的一个寓言,其中艺术家、学究和掠夺者共存。榭得、格雷德斯和金伯特是同一人格的不同方面,都悬于纳博科夫那颇有些密度的感受中——他是集三者于一身的。
(注:See Daniel Hoffman ed.,Harvard Guide to Contemporary
American Literature,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Press,1979,p.268.)
要理解亨丁的这一席话,还需对纳博科夫的生平作一简介。
我们知道,纳博科夫出身贵族,财产被苏维埃政权没收后举家迁到西欧。后来父亲被俄国右翼分子刺杀,纳博科夫被迫挑起家庭的重担,过起了永久性的流亡生活。从1920年代开始,他先后在柏林、巴黎和美国波士顿等地区居住。他不仅是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博物馆的研究员,还翻译了普希金的名作《尤金·奥涅金》。大学教书生涯还让他看到了美国“学院环境里秘密而复杂的自我陶醉”(乔治·斯坦纳语)。(注:Page Stegner ed.,The Portable Nabokov,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xxxviii.Also see Julian Moynahan,"Vladimir Nabokov,"in Leonard Ungar ed.,American Writers:A Collection of Literary Biographies,Vol.Ⅲ,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74,pp.244-266.)正如小说《微》中的主人公金伯特一样, 纳博科夫的一生也充满传奇。
在某种程度上,小说《微》带有一定的自传性质。从金伯特这个为长诗作注的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翻译普希金诗作并加上批评性注释的纳博科夫的身影。从刺客格雷德斯身上,我们似乎见到了刺杀纳博科夫父亲的右翼分子的影子。像金伯特一样,纳博科夫也生活在完全不同的语言、文化和社会背景之中,被迫接受或扬弃各种意识形态。我们或许可以设想,他偶尔也会像金伯特一样幻想一下自己的帝王生涯,将自己当作某王国的流亡国君,并且发出“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感叹。他或许也会感到自己的生活带有梦幻般不真实的色彩(他写的自传性作品《说话呀,记忆!》把这种梦幻般的感受描绘得相当细腻)。小说《微》中,金伯特的精神分裂(或人格分裂)和疯狂臆想,也反映了纳博科夫与金伯特一样狂暴、骚动和迷惘的心灵,心灵中有多种声音和话语喧哗。如果说为长诗作注的人已经精神分裂,具有“三种身份……而格雷德斯之流的身份也变动不居”,(注:JulianMoynahan, "VladimirNabokov," in
Leonard
Ungared.,American Writers: ACollection of
Literary Biographies,Vol.Ⅲ,New York:CharlesScribner's Sons,1974,p.265.)那么作者纳博科夫也同样兼具三重身份或三重人格。
略微换一下角度就可发现,金伯特或作家本人的“疯狂”乃是文学创作中的一种“神经质状态”(罗兰·巴特语)。写作时——特别是想用写作来追忆逝水年华时,搞创作的人不免会染上某种轻度的神经官能症。
无论是《微》的作者纳博科夫,还是那131条注释的作者金伯特, 都有资格被称为罗兰·巴特所谓的“写手”(scriptor)。这两位写手的“神经质状态乃是一种权宜之策……神经质状态是对于本质上不可能之事的认真感悟……惟有这种权宜之策使写作成为可能。于是我们得到这个悖论:文本是在疯狂之中为抗衡神经官能症而写就的,但其本身——如果它们想被人阅读的话——还是具有引诱读者的必要的轻度神经官能症:这些可怕的文本依然是挑逗性的文本。”(注:Roland Barthes,Le plaisir du texte,Editions du Seuil,1973,p.31,p.19,p.13.)
至此,一直困扰我们的一个问题应当比较明了了。小说《微》和金伯特的注释都是在悟寐之间为抗拒神经官能症而写的,一定程度上只是作者的自娱。这样的文字,在作者看来,其实“不足为他人道也”。作者料到细心的读者在掩卷之时会责备他痴人说梦,所以预先为自己作了辩解:就我而言,写作本身的确带有一定的疯狂性,作品也难免存在艰涩难懂之处,但我已用书名《微暗的火》表示了歉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