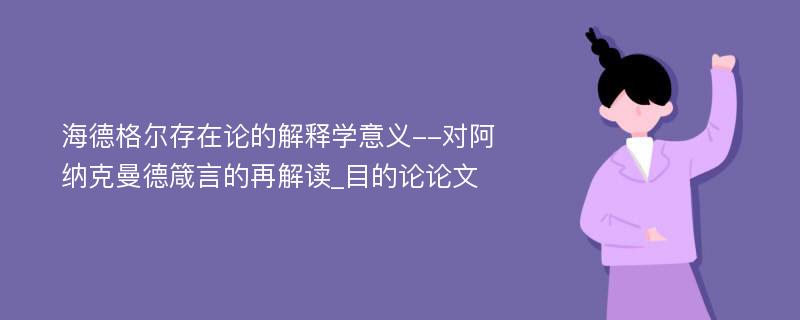
海德格尔“存在的末世论”的解释学意义——《阿那克西曼德的箴言》再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德格尔论文,解释学论文,箴言论文,曼德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副标题中的“再解读”三字,表示我对海德格尔解读阿那克西曼德箴言的一种反思和“视野融合”,并没有否定海德格尔的解读的意思,而是试图从中阐发出一种隐藏的含义。当然,这种含义也许是海德格尔自己也没有想到的,但它有可能暴露出海德格尔思想中的深刻矛盾的根源。
一
海德格尔在《阿那克西曼德的箴言》一文中,阐述了他对存在的一种“末世论”(Eschatologie)的理解:
存在者之存在把自身聚集(λεγεσθαι,λογοs)到其命运的终结之中。迄今的存在本质沉沦于它的尚被遮蔽着的真理中。存在之历史把自身聚集到这种分离之中。在这种分离中的聚集,作为对迄今之存在本质的极致(εσχατον)的聚集(λογοs),就是存在之末世论(die Eschatologie des Seins)。存在本身作为命运性的存在,在自身中就是末世论的。(Heidegger,S.323;中译本参见海德格尔,1997年,第334页。下引此文只注明中译本页码)
“末世论”,又译“来世论”、“转世论”,在基督教中,它意味着历史有一个终结(最后的审判),并且这个终结就是对开端的复归,对“正义”的恢复,从而历史主义被扬弃而绝对真理得到显现。海德格尔之所以要从阿那克西曼德的一条箴言开始进入这一讨论,就是为了回复到开端。这条箴言按照海德格尔所认可的“字面上的严格翻译”应是:
但万物是根据必然性由它产生出来的,又形成向它的消亡;因为它们根据时间次序对不正义给出正义和相互的惩罚。(第337页,译文有改动)
但海德格尔的本意决不是要对这段话重新作字面上的严格翻译,而是要从这段话里面发现永恒绝对的意义;就是说,他把这段话视为思想史的开端,而所有后来的思想史都只不过是对这段话中所包含的绝对意义的一系列遮蔽和偏离而已,直到历史终结之际这一绝对意义才得以重现。所以问题在于穿越两千多年历史去对这条箴言作出哲学上“最终的”理解。为此,他对“末世论”这个词也作了他自己的不同于基督教的解释:它并不意味着道德意义上的最后的“正义审判”,而是超越于善与恶的彼岸,类似于尼采所谓“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是早期西方思想和晚期西方思想对“同一个东西”(das Selbe)即存在者之存在的遥相呼应。(参见第340页)因此,“我们是在必须通过存在历史来思考精神现象学这一相应的意义上,来思考存在之末世论的。精神现象学本身构成存在之末世论的一个阶段,只要这个存在作为无条件的求意志之意志之绝对主体性而聚集到自己迄今由形而上学打上烙印的本质的终结中来。”(第335页,译文有改动)在这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作为通达上帝的阶梯)和尼采的“强力意志”(作为取代上帝的“超人”)都被当作了存在之末世论的一个准备阶段。
显然,从这种“终极”的立场来看,将阿那克西曼德的上述箴言翻译成人类社会的道德和法律语言就很肤浅了。在海德格尔看来,即使阿那克西曼德出于当时的局限性而不得不运用道德法律语言(“正义”、“不正义”、“惩罚”等)来表达自己的意思,我们仍然必须区分“箴言对之有所道说的那个东西”和“所道说出来的东西本身”(第337页):后者是直接说出来的语言,前者是语言所想要表达的“思想”。既然海德格尔从末世论的立场把这条箴言看作摆脱了一切语文学和历史学的系缚的“思想的箴言”,那么“思想的箴言唯有在思想与箴言之所说的对话中才能得到翻译”(第335—336页)。这种对话所需要的是一种“诗意的思”,这是一种返回到一切诗和艺术的本源的思,即“原诗”(Urdichtung);它不是为了以“神人同形同性论的表象方式”来模糊地(形象地或隐喻地)表达某种科学知识,而是由于它在它的这种诗性本质中“道说着存在之真理的口授(Diktat)”、“保持着存在之真理的运作(Walten)”,因而它在运思中体现出比语文学和历史学更为严格的约束力,甚至“必然表现为暴力性的(gewaltsam)”。(第336页)因此,海德格尔主张以尼采式的强力意志清除对希腊思想的一切“不当的先入之见”,到“形而上学之完成的极端处”,即立足于(尼采的)“晚期西方思想的晚期箴言”(第340页)去对整个西方思想进行“价值重估”,否则的话,任何字面上完全正确的翻译都“难免落入空洞和漫无边际之中”(第342页)。例如我们对希腊思想和整个西方思想的两个最基本的词语ον和ειναι、即“存在着”和“存在”(德文译作seiend和Sein)的翻译虽然是正确的,但却未经运思,因而其中“飘荡、蔓延着一种漫无边际的关于存在的闲谈”(第343页),这种纷乱不仅不能用语文学和历史学的更精确的定义来消除,反倒会由此而被掩盖起来;海德格尔则力主“不懈地关注这种纷乱,并以其顽强的力量去促成一种解决——这样的尝试有朝一日会成为一种诱因,唤起另一个存在之命运……为的是在依然持续着的那种纷乱之范围内进行一种与早期思想的对话”(同上)。总之,我们必须穿透阿那克西曼德箴言的字面含义,跨越自那以后的两千五百年西方历史对这些含义的澄明,并将其看作存在的自行遮蔽,在这个历史的最高点即“强力意志”的终点上思入“存在”,返顾历史“早先”的起点而体会“相同者的永恒轮回”。
然而,如果说,自阿那克西曼德以来的两千五百年,人类对存在者的去蔽就是对存在的遮蔽,而这一遮蔽本身又是“存在原初的自行澄明的特征”(第344页),即存在通过遮蔽自身来澄明自身,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评价人类两千五百年间的思想史呢?在这个问题上,海德格尔似乎力图保持一种“价值中立”的姿态。从他的用词来看,他无疑是对历史、历史学采取一种贬斥的态度的,他说:“迷误(Irrtum)乃是历史的本质空间。在迷误中,历史性的本质因素迷失于类似于存在的东西中。因此之故,那种历史性地出现的东西就必然被曲解(mideuten)……人之看错自身,相应于存在之澄明的自身遮蔽。”(第345页)然而与此同时,他又承认:“倘没有迷途,也就没有任何命运与命运的关系,也就没有历史。……存在隐匿自身,因为存在自行解蔽而入于存在者之中。如此,存在便随其真理而抑制自身。这种自行抑制是存在之解蔽的早期方式。”(同上)这似乎又赋予了人类思想史以不可缺少的重要意义。在此,他在与胡塞尔恰好相反的意义上使用了“存在之悬搁(εποχη)”这一术语。在胡塞尔,对存在之悬置是现象学还原的一种主观运用的思维技巧,即“在对象化过程中设定的意识行为的中止方法”(第346页),即不准存在活动(包括存在之历史)进入现象学的视野;海德格尔则把这个希腊字所蕴含的另一层意思即“划分阶段”、“划分时代”给恢复了。对存在的悬置不再只是“存而不论”或“中止判断”,而是“暂时耽搁”或“自行抑制”,以便用思想对此在的“绽出”这一命运性或历史性的东西加以思念,“向命运的要求开放我们自己”。所以海德格尔提醒我们要追问:是否“存在的闪电”楔入了我们和存在之真理的关系?是否存在的“早就消退了的雷雨的微闪,仅仅还把它的暗淡光亮带入我们关于曾在者的知识之中”?“难道还有一道闪光从οντα和ειναι在希腊文中所道说的东西出发,穿透迷途之纷乱而抵达我们吗?”(第347页,译文有改动)
但上述追问仍然有两种歧义。一种是要依据存在的自身遮蔽的两千余年历史去追溯其在早先的澄明无蔽,因而历史仍然有它自身的价值,这就是黑格尔曾经走过的历史主义之路。所以海德格尔承认“在思想上了解了思想史的唯一的一位西方思想家,乃是黑格尔”(第330页),虽然他仍然惋惜黑格尔的追溯并未达到历史的开端处即阿那克西曼德的箴言,而实际上是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起步的。另一种则是意味着这两千余年历史完全是一个错误,除了处处指出其错误之外,根本可以不加考虑,至少不必认真对待,只消直接返回到历史的开端来与之“对话”就行了。在这方面,海德格尔与黑格尔是根本不同的:黑格尔把整个哲学史看作自己哲学的形成过程,海德格尔则把自己的哲学看作对原始思想跨越式的恢复。就海德格尔自己的论述来看,他对上述第一种含义的承认是虚,对第二种含义的论证则是全力以赴。就实质而言,一种“末世论”的历史观恐怕也不能不如此,例如基督教的末世论虽然也承认,上帝让人犯罪、堕落是为了最终能让人类从罪恶中得救,但犯罪堕落毕竟是人自己的过错,是不能归咎于上帝的,言下之意,如果人类能够不犯罪,岂不是更好。同样,海德格尔也只是与阿那克西曼德对话,而不屑于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话,更不必说拉丁哲学家了:这些人的形而上学“使得存在的隐含于早期基本词语中的本质丰富性始终被掩蔽着。这样,存在才得以上升到最空洞和最普遍的概念的不幸地位上去了”(第361页)。在他看来,“追索各个思想家之间的依赖性和相互影响,这乃是思想的一种误解”(第380页);每个思想家都只是单独地和“存在之劝说”发生关系,只是早期思想家做得好些,后来的思想家做得很糟糕而已。所以海德格尔宁可引证荷马的诗句来说明阿那克西曼德,至于后来的人对阿那克西曼德的解释、因而对ον(存在着)和ειναι(存在)的解释(因为存在“承担和创造着”阿那克西曼德的“产生和消亡”[参见第351页]),他不承认有任何合理之处。他大约以为这样就可以洗刷和避免历史的罪过而返回到史前的天真状态,但果真如此,他岂不是就把自己放到了上帝的位置上了?我们凭什么能够相信他呢?
二
我们至少可以就这个问题为亚里士多德一辩。例如,当海德格尔引证荷马对先知的赞辞“他知道什么是,什么将是或者曾经是”时,他就荷马所用的“知道”(即“看”)一词的过去完成时形态大加发挥道:
唯当一个人已经看到之际,他才真正地看。看乃是“已经看到”。被看见的东西已经到达,并始终在他面前。一个先知总是已经看到了。因为事先已经有所看到,他才预见。他根据过去看见未来。如果诗人要把先知的看描述为“已经看到”,那么他就必须把“先知已经看到了”这回事以过去完成时道说出来,即:ηδη,他过去就已经看到了。先知事先看到了什么?显然只是那种在贯穿其视野的澄明光照之中在场的东西。这种看所看到的东西只能是在无蔽者中在场的东西。但什么东西在场?诗人指出一个三重的东西:既是τατεοντα,即存在着的东西,又是τατεσσομενα,即将来存在的东西,又是προτεοντα,即过去存在过的东西。(第354—355页)
海德格尔想要说的是,在荷马和阿那克西曼德那里,“在场的东西”(Anwesende)并不仅仅是指“当前的”(gegenwārtig)在场东西,连过去的东西和将来的东西也是在场者。“非当前在场的东西乃是不在场者。作为不在场者,它本质上依然关联于当前在场者”,所以“连不在场者也是在场者”,而这种“广义的在场者”“恰恰就是当前在场者和在当前在场者中起支配作用的无蔽状态,而这种无蔽状态贯穿于作为非当前在场者的不在场者的本质”。(第356页)海德格尔承认,这种理解在“希腊经验”中并不是很清晰的,它被看作是先知的一种“疯狂”,但海德格尔认为这种“疯狂”正是对存在(和非存在、无)的看守和“庇护”,因为“这种知道保持着视野。知道始终挂念着在场。知道乃是存在之回忆”(第358页)。所以先知的“看”就是本质的看:“当前在场者,出于不在场而现身成其本质。这一点恰恰必然是就真正在场者来说的”。(第359页)然而,海德格尔的这个意思其实有一个人早已经(虽然比较粗糙的方式)说过了,他就是亚里士多德。
海德格尔承认,亚里士多德并不像“四处流行的错误意见”那样仅仅“从陈述命题及其系词出发对存在者作了‘逻辑的’解释”,而是根据范畴来思考了存在者之存在,即“不是根据命题对象的对象性来思考在场者之在场性的,而是把它思为实现(ενεργεια)”。(第360页)但他还是认为亚里士多德“把存在者看作那种对于陈述来说已经现成的东西,也即看作无所遮蔽地当下逗留的在场者。……因为实体的本质,即希腊文的ονσια(在场、存在)的本质,在παρονσια(在场)意义上已经是显然的了”(同上)。这里显然有某种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亚里士多德的“实现(ενεργεια)”怎么会是“已经现成的东西”呢?其实,亚里士多德正是用“实现”来给运动下定义的,他明确说:“潜能的事物(作为潜能者)的实现即是运动”,(亚里士多德,1982年,第69页)这种实现显然不是“现成的东西”,而是在时间中运动的东西。同样,亚里士多德的“实体”(ονσια,在场)也不是“无所遮蔽地当下逗留的在场者”,而是任何一个事物(在场事物)的“怎是”(参见同上,1981年,第133页。“实体”吴寿彭译作“本体”),即το τι ην ειναι(相当于英语What it was to be,中文直译为“某物曾经是什么”,吴寿彭译作“怎是”,以表明“某物之所以成其所是者”)。该词组最使现代的研究者们困惑的是那个ον的过去式ην(即英语的was,中译为“曾经是”),以致长期以来,“学者们一直对亚里士多德为何要用过去式表示费解,名之曰‘哲学过去式’(philosophic imperfect),很少有人认为这一过去式对该术语的哲学含义有多少增加,所以在英译中,喜爱直译的学者往往忽略过去式”(余纪元,第225页)。拉丁文则把这个词组简单地译作essentia(本质)。可见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当他说第一实体就是一门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的科学的对象时(参见亚里士多德,1981年,第120页),他的意思是研究存在者是如何“在起来”(“是起来”)的,即追究任何一个存在者是何以存在的,也就是追究它“原来是什么”,那个东西就是使它得以成为它(成为该存在者)的“本质”。所以黑格尔也仿照亚里士多德,把本质规定为“过去了的存在”(黑格尔,第3页。杨一之译“存在”为“有”)。然而,如果亚里士多德真的像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把实体(ονσια)理解为“当下逗留的在场者”,他怎么会同时又把实体看作是“过去了的存在”呢?过去了的存在即“不在场”,但亚里士多德又的确同时把实体视为“在场”,这一矛盾只有用海德格尔自己提出的“广义的在场”概念才能消除:“不在场者也是在场的”。可见在这一点上,亚里士多德在当时就已达到了海德格尔的水平。
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是通过他那几乎无处不在的“目的论”,而这种目的论是海德格尔差不多完全忽视了的。这似乎可以说明,为什么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这方面的贡献视而不见。众所周知,目的论和对“目的因”(“极因”)的追寻是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最显著的特点之一,但很少有人用目的论来解释他的实体在场学说。其实,实体既在场又不在场这一矛盾正好体现了目的(τελοs)的本质特点。在一个合目的过程中,目的作为尚未实现出来的动机当然还不在场,但作为支配着整个过程并对之起作用的动机又时时处处在场;目的既是“潜在”的,又在“实现”之中,它作为这一过程所追求的“形式”就是真正的实体。既然作为结果的目的和作为原因(动机)的目的就是同一个目的,既然动机无非就是预先“看”到了的结果,它就是“目—的”(中文意为“看到的对象”),那么目的就既是在先的(过去了的),又是在后的(未来的),同时还是当下现实起作用的(ενεργεια,即“实现”)。如亚里士多德说的:“事物‘后于’发生过程的,在形式上与实体上是‘先于’,例如大人‘先于’小孩。”(亚里士多德,1982年,第182页)显然,作为动机的目的是事先建立的“过去了的存在”,但它并非现在已不存在了,而是作为事物追求的目的而使事物现实地存在,因而在实现过程中恰好是随时都在场的。实现过程也就是“存在的回忆”过程,一切事物都是向着自己先定的形式(本质)而存在的,否则根本就不会存在。所以,目的实际上就相当于海德格尔所说的那个“三重的东西”,即过去、现在、将来的统一体。目的就是“先行到将来”。但海德格尔对这个如此方便而清晰地解释了他的神秘的“三重体”的目的论却持一种不屑一顾的态度,这主要也许是由于他把目的论归于人为的制作技术而与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概念对立起来的缘故。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把亚里士多德的“目的”(τελοs)和“技术”(τεχνη)勾连在一起,并认为“有机体”这个概念“是一个纯粹现代的、机械—技术的概念,按照这个概念,生长物便被解释为一个自行制作出来的制作物”(海德格尔,2000年,第295页)。这就完全抹杀了亚里士多德以目的论超越机械论、以有机体的内在目的论超越技术主义的外在目的论的努力。其实,亚里士多德的“自然”(Φνσιs)本身就是一个内在目的论的概念,万物都以之为潜在目的而“涌现”于世,否则事物即使要“涌现”(Aufgehen,这是海德格尔对Φνσιs的翻译),也会是“涌”(gehen)而不“现”(auf),或是互相掣肘、互相抵消,那才真的会成为一个“机械论”的“盲目的”无序世界了。海德格尔把对人的机械技术的恐惧扩展到对人本身(“人本主义”)的恐惧,并进一步扩展到对有机体的恐惧,他可没料到“物极必反”。他强调“看”(“目”),但不想把“看到的东西”当作“对象”(“的”),然而无对象的看不是看,无的之目亦非目。
从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我们还可以顺利地解释阿那克西曼德的αδικια(不正义)。海德格尔问道:“何以始终逗留着的在场者就在不正义之中呢?”他认为,“如果我们撇开我们的法学—伦理的观念,如果我们坚持在箴言所说的东西那里,那么,αδικια说的就是:它运作之处,事情不对头。这意思是:某物全是裂隙。”(第363页,最后一句译文有改动)但裂隙(die Fuge)从何而来?海德格尔说:“箴言说得明白,在场者就在αδικια中,即全是裂隙。但这不可能是指在场者不再在场。但它也不仅仅是说,在场者偶然地、抑或就它的某一属性而言全是裂隙。箴言是说:在场者作为它所是的在场者全是裂隙。”(第364页,译文有改动)裂隙是在场者的本质,在场者总是要离开作为逗留者的自身,于是就造成自身内部的“裂隙”;但它离开自身还是为了去“在场”,所以它自身内部的裂隙本身就是“嵌合”(der Fug),是“非裂隙”(Un-Fuge)。于是“始终逗留者坚持于它的在场。它就这样摆脱了它的过渡性的逗留。它在坚持之固有意义中展开自身”(第365页,译文有改动)。所以,在场者的本质既是裂隙,又是非裂隙(嵌合),它保持着在裂隙中嵌合的张力。这与亚里士多德把目的当作“静止”的同时又从自身中“开启出运动”来是一致的。(参见海德格尔,2000年,第330页)目的作为动机本质上就是从自身离开(去寻求手段),因而是与自身“撕裂”;目的作为效果本质上则是使手段与动机“嵌合”而使自己“始终逗留”或“持存”。因此“裂隙”并没有分割开目的,而恰好使在场者和非在场者(使过去、现在和将来)相互归属、“相互顾视”。所以海德格尔认为对阿那克西曼德的τισιs一词也就不可译作“惩罚”,而应译作“重视”(Schtzen):“重视某物意味着:关注它,从而使受重视者在其所是中得到满足”。(第368页)更好的是译作“顾视”,但海德格尔担心“顾视”(Rcksicht)一词“对我们来说过于直露地指示着人类的特性”(第369页)而降低了自己的形而上学层次。其实这种担心大可不必,海德格尔的“重视”、“关注”、“满足”、“毫无顾忌”(同上)、“渴望”(第370页)等等,又何尝不是“指示着人类的特性”?他的这种实际上摆脱不了、口头上又不承认的拟人化,其实正是目的论的本质特征。人无法不用人的眼光来看待和思考自然。
更加拟人化的翻译是海德格尔主张用来译阿那克西曼德的το χρεων(通译作“必然性”)的那个词:“用”(der Brauch)。无论海德格尔如何辩解,这一译名也表明海德格尔无法摆脱最根本的拟人化。之所以是“最根本的”,是因为这个词在他看来“乃是思想借以把存在者之存在表达出来的一个最古老的名称”(第373页)。他认为,正是“用”,“从上而下”地“把嵌合结合起来,从而也把牵系接合起来”(同上);在“存在者之存在”这件事情中“这个词乃是第一位的”,它就是“在场本身”。但它一旦被命名,“在场本身就成了一个在场者”,而“在场之本质,以及与之相随的在场与在场者的差异,始终被遗忘了。存在之被遗忘状态乃是存在与存在者之差异的被遗忘状态”。(第374页)由此可见这个词的翻译非同小可。如他在另一处说的,“西方的命运就系于对εον一词的翻译”,即系于对存在和存在者之差异这一“存在之谜”的揭示。(第353页)“用”这个词则揭示了存在一旦成为存在者就与存在有了差异这一事实,并使存在者在与存在的差异中保持在存在的手中。如海德格尔所说的:“‘brauchen’的意思就是:让某个在场者作为在场者而在场;……把某物交给其本己的本质,并且把作为这样一个在场者的某物保持在具有保护作用的手中”,而这就是“存在本身的现身方式”(第378页)。但一切“用”都是一种合目的性的行为,所以这段引文可以用目的论的语言来解释,就是:目的一旦形成自己的手段,手段与目的就有了差异;但对手段的“用”可以使手段在与目的的差异中保持在目的手中,让某个手段作为手段而受目的支配,不至于偏离自己的本质。这是对海德格尔的翻译的再翻译,但也是完全合乎海德格尔的思想的。他所谓的“存在遗忘”,无非是把存在者当作了存在本身,把手段当作了目的本身。“人类正在贪婪地攫取整个地球及其大气层,以力量的形式夺取自然的隐蔽的管理权,并使历史进程服从统治地球的计划和安排。如此叛逆的人类没有能力轻易道说:什么存在,道说:什么是这个‘某物存在’。”(第383页,译文有改动)“用”则是回到目的,回到手段的本质和意义(如维特根斯坦所云:“一个词的意义就在于它的用法”),回到最初的没有分裂和裂隙、因而也用不着嵌合的浑然一体状态。这种状态就是阿那克西曼德的核心原则“阿派朗”(απειρον)。该词原意为“无定形”,海德格尔译作“无界限者”。“无界限而成其本质者并不是通过嵌合和牵系而接合起来的,它不是在场者,而是:‘用’”。(第379页,译文有改动)“用”本身是无定形者、无界限者,但它能把界限和形制赋予存在者或在场者(手段),而且正是由此而“成其本质”的;但正当它成其本质之际,它也就使“在场者进入了一个持续的危险之中,即,它出于逗留着的固守而僵化于单纯坚持”(同上)。因此“用”的作用就不仅在于使手段和目的相适合、相“嵌合”,而且使一切有限的手段和目的都复归于“非嵌合”(即没有任何手段能与之完全嵌合)的永恒目的,即最高的“善”。正是这一终极目的的“用”,把一切在场者都“聚集”起来了,使世界成了有意义、合目的的存在者。
于是,海德格尔把阿那克西曼德的箴言改译作:
……根据用;因为它们(在克服)非嵌合中让嵌合从而也让牵系相互归属。(第382页)
但他马上说明,这种翻译不能“科学地证明”,而“只能在箴言之思中得到思考”(同上)。这几乎是在鼓励人们对他的翻译再加改译。于是我也可以尝试将他的译文改译如下:
……(万物)服从于其目的,因为它们(在克服)不合目的性时让自己适合于目的并因而也互为目的。
严格说,这并不是我的改译,而是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我们试看他在《形而上学》中的一段话:
极因是一个“终点”,这终点不为其他什么事物,而其他一切事物却就为了这个目的;有了这末项,过程就不至于无尽地进行;要是没有这末项,这将没有极因,但这样主张无尽系列的人是在不自觉中抹掉了“善”性(可是任何人在未有定限以前他是无可措手的);世上也将失去理性;有理性的人总是符合于一个目的而后有所作为,这就是定限;终极也就是“定限”。(亚里士多德,1981年,第34—35页)
显然,亚里士多德的这段话也很符合海德格尔的意思,连细节和用词都符合。如“任何人在未有定限以前他是无可措手的”,意思是只有目的才给出了“定限”(περαs),才能够让人“措手”。海德格尔也说:“但接合着嵌合、限制着在场者的‘用’交出界线”,他还注明“界线”(Grenze)正是用来译περαs(即“定限”)的(第378页);又说“用”的意思是“我处置某物,把手伸向某物,关涉某物并帮助它”(第376页),这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谓“措手”的意思。又如“理性”一词,亚里士多德虽然用的是νονs,但他前面有交待:“不至于无尽地进行”而“抹掉了善性”。这也就可以理解为海德格尔所谓的把万物“聚集”起来的意思,νονs在这里也就相当于海德格尔所理解的λογοs(聚集),因为若“无尽地进行”则聚集不起来了;而“善性”则意味着“完全”,也是完备无缺地全部聚集在一起之意。不难看出,即使那些表面上与海德格尔相左的地方,实际上也是一致的。如亚里士多德以“有理性的人”为例来说明目的,有明显的“拟人主义”倾向,但前面已说过,海德格尔自己也摆脱不了拟人化,只不过更隐蔽而已。再就是最后一句“终极也就是定限”,看起来似乎与海德格尔所谓“‘用’同时也是το απειρον,即无界限者”(第378页)的说法相反。不过亚里士多德在批评阿那克西曼德时并没有对其“无定形”(即“无限”)全部否定,而是作了具体的分析。他认为把无限“当作一个根源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作为根源它就是不生不灭的”,而“凡产生的事物都必然达到一个完成,所有灭亡过程也都有一个终限”,所以“根源”(αρχη,又译“始基”、“本原”)这种“神圣的东西是不会灭亡的”,它只能是无限的。(亚里士多德,1982年,第77页)但他又对无限的含义作了区分,认为现实的和感性事物的无限是不可能有的,“只有潜能上的无限”,即“不是‘此外全无’,而是‘此外永有’”。(同上,第85、87页)所以亚里士多德并未完全否认终极是无限的,他承认终极潜在地具有无限可能性,但现实地则是对万物的“定限”,这两者并不矛盾,而且这比阿那克西曼德简单地以无限作为终极的始基要深刻得多,也完全符合海德格尔的“用”既是“无界线者”又能向在场者“交出界线”的观点。
但如果按照我的方式把海德格尔的“用”解释为亚里士多德的“目的”或“善”,那么το χρεων这个希腊字本来的字面含义“必然性”也就得到了恢复。因为,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开始,目的和善就是由于要探求事物的原因和必然性才引出来的。柏拉图在《斐多篇》中记述苏格拉底的话说,他早年听人说阿那克萨哥拉认为心灵把一切都安排得“最好”,便十分向往:“我以为他将能告诉我,首先这大地是平的还是圆的;而不论哪一方面是真的,他将能进一步说明其所以如此的原因和必然性,然后他将告诉我最好的东西的本性,以及指出这就是最好的……。”(《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73页)虽然苏格拉底最后失望了,但他(和柏拉图)由此起步迈向了以“善”为终极因的目的论。亚里士多德则在《物理学》中由目的论引出必然性,他把偶然碰巧的和有目的的视为“二者择一”的对立面,并说:“凡自然物都是以一定的内在根源为起点,通过不断的运动变化过程,达到一定的终结的;由任何一种根源出发的运动变化,既不会达到完全相同的终结,也不会达到完全偶然的终结,而是始终有一种竭力趋向相同终结的倾向(如果没有障碍的话)。”(亚里士多德,1982年,第64—65页)所以在凡是“含有目的的事情”里都“不能没有那种具有必然的本性的事物”。(同上,第66页)虽然这些地方所使用的“必然性”一词并非το χρεων,而是αναγκη,前者表示不可抗拒的抽象“命运”的必然,后者只是具体的某种强迫性“力量”的必然;但后一种必然一旦和最高的善(最高目的)结合起来,也能达到前一种必然的抽象性。另外,不论何种意义上的必然,当它与某种目的相联系时都可理解为“必要”、“需要”。其实海德格尔的“用”(Brauch)的动词形式brauchen的原意就是“需要”,他自己也常把这两个词看作一回事,如他说:“……brauchen和Brauch就意味着:把某物交给其本己的本质,并且把作为这样一个在场者的某物保持在具有保护作用的手中。”(第378页)所以如果我们把阿那克西曼德箴言的开头译作:“……(万物)服从(其目的之)需要”,也许不失为一个对阿那克西曼德的字面意义、海德格尔的解释性翻译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解都能兼容的办法。
我在上面极力要把海德格尔的“末世论”的形而上学引回到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和拟人论上来,是为了揭示一个问题:海德格尔到底是在哪一点上偏离了他如此称道的黑格尔的?或者说,他是在哪一点上离开了黑格尔的历史主义而走向末世论的?他深知黑格尔对亚里士多德推崇备至。黑格尔主张“要研究希腊哲学,最好的做法就是去读亚氏的《形而上学》第1卷”(转引自第330页)。海德格尔则反其道而行之,力图撇开亚里士多德去读早期希腊哲学。他尤其蓄意要悬置的是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和拟人论。然而,亚里士多德目的论的一个最重要也最有价值的特点,就是以(有机体的)内在目的论为终极目的,这就为含有历史目的论因素的末世论(如中世纪基督教的救赎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也给黑格尔扬弃末世论而确立历史主义乃至于“历史理性”提供了思路。海德格尔却想要重新确立(存在)末世论而剔除其中的历史目的论因素。但他既没有能够完全清除历史主义,也没有真正确立自己的存在末世论,而是一方面不得不经常为历史(Geschichte)的命运(Geschicke)留有余地,承认这是存在本身的必然本质,另方面在自己对末世论的“诗意的思”之外,也为他人的诗意和非诗意的思留下了极大的空间,从而使“最后的审判”无限期地推延了。海德格尔的这一两难的困境,是否仍然体现了某种“理性的狡计”,是否仍然要在某种历史主义的“思”中得到扬弃呢?且让我们对此存疑,以待来者。
标签:目的论论文; 海德格尔论文; 阿那克西曼德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读书论文; 解释学论文; 哲学家论文; 现象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