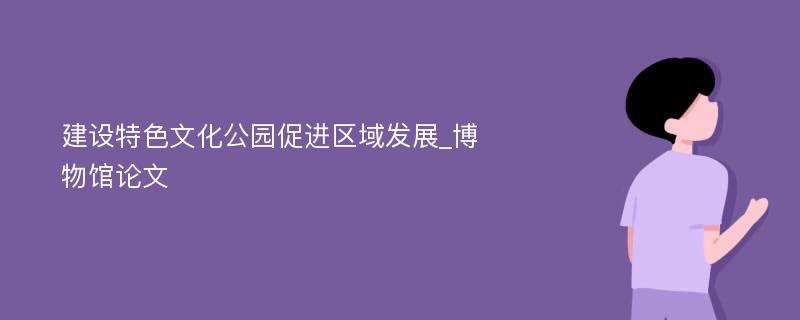
建设特色文化园区,促进区域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园区论文,区域论文,特色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全国各地各类文化(产业)园区建设中,特色文化园区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类别。木文所说的特色文化园区,重点是指近些年来在西部地区方兴未艾的生态博物馆、民族文化生态村、国家公园等建设。特色文化园区建设的共同特点是,以特定地域空间为载体,通过保护和利用文化资源,实现保育文化、改善当地居民生活的目的。特色文化园区建设已经成为促进西部区域发展的一条路径。
一、国内外特色文化园区建设概况
随着现代化、城市化进程加速,通过建设特色文化园区保护和利用文化资源,受到各国重视。20世纪70年代,以法国为代表的国际博物馆协会领导人着眼于环境保护和文化遗产保护,倡导生态博物馆(ecomuseum)理念。与传统博物馆以静态建筑为载体不同,生态博物馆强调以活态社区为载体,以社区居民为主体,保护社区各种人文资源。在欧洲,生态博物馆更多是着眼于对工业文明遗产的保护。1971——1974年,戴瓦兰以法国索勒特索煤矿区为依托,建立了生态博物馆。这是最早的工业社区生态博物馆试验。
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城市化,日本出现了农村人口流失,农业衰败的严重问题。在此背景下,日本提出了“造村运动”的理念。“造村运动”倡导依托乡村文化资源,努力形成一村一品,发展1.5级产业。一村一品要求每一个乡村培育出一个有当地特色、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1.5级产业是鼓励在传统农、林、木、副业基础上,增加其文化内涵。比如,开发编织等手工艺产品,发展特色旅游等。
受日本“造村运动”启发,上世纪90年代,台湾地区文建会在台湾乡村倡导“社区总体营造”运动。该运动有五个核心理念,即人、文、地、景、产。人,指生活在乡村中的人口;文,指乡村的文化;地,指地理特色;景,指乡村的独特风景;产,指当地特别的物产。“社区总体营造”运动旨在通过发掘地方文化内涵,提升地方竞争力。以台湾南投县埔里镇桃米社区为例。桃米社区位于台湾腹部的山地乡村。多年来,当地农民以竹笋为主要生活来源,收入微薄。年轻人流失十分严重。1999年“9.21大地震”,桃米社区毁损的房屋超过2/3,再遭重创。后来,在台湾文建会帮助下,桃米社区居民发展特色旅游,发掘地方特色餐饮业,提炼特色品牌,有效地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①
二、特色文化园区成为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路径
20世纪中叶,生态博物馆理念被引入中国。1995年,中国政府与挪威政府合作,在贵州共建苗族梭嘎生态博物馆。这是中国建立的第一个生态博物馆,也是亚洲第一家生态博物馆。梭嘎生态博物馆位于贵州省六盘水市的崇山峻岭之中,海拔1400-2200米,面积120多平方公里。梭嘎乡共有12个苗族寨子。仅有4000多人,有自己的语言。梭嘎乡的苗族以长角头饰为象征,属于苗族支系中的“长角苗”,保存和延续着古老而独特的文化。20世纪90年代,梭嘎苗族村寨基本上处于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状态,文化古朴,有丰富的婚恋、丧葬和祭祀礼仪,被称为人类工业化前生活的活化石。
1995年4月,中挪两国博物馆学家发布了一份《在贵州省梭嘎乡建立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1997年10月23日,中挪两国首脑签署了《挪威合作开发署与中国博物馆学会关于中国贵州省梭嘎生态博物馆的协议》。1998年8月和10月,中挪两国博物馆学家讨论制定了“六枝原则”,共有九条,其核心内容是强调当地居民参与,民主管理,保护文化优先,鼓励和促进社区经济发展,改善居民生活等。
梭嘎生态博物馆的成立,改变了梭嘎苗寨的境况。其一,长角苗的文化遗产得到了系统保存。1998年10月31日,梭嘎生态博物馆资料信息中心在陇嘎村建成开馆,面积420平方米,配有档案室、展览室、视听室等,濒临消失的有形和无形文化遗产被储存在这里。同时,整体维修保护了村内10幢百年以上极具特点的民居,编写了10万多字的《中国贵州六枝梭嘎生态博物馆资料汇编》。其二,提升了梭嘎苗寨的知名度。梭嘎生态博物馆的成立,使前来观光、研究的人络绎不绝。从1998年以来,梭嘎生态博物馆接待了10余万参观旅游者和专家学者。其三,当地居民生活环境有了很大改善。实现了水、电、路三通。随着旅游业的出现,当地居民也有了新的职业,如艺术表演,导游等,增加了收入。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也大大增加。1998年,当地居民人均收入不到200元,2008年达到1680元。其四,丰富、拓展了博物馆理念。梭嘎生态博物馆的核心理念是强调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这对拓展博物馆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梭嘎生态博物馆的建立产生了很大的示范效应。不仅贵州在此基础上兴办了多家生态博物馆,也带动了周边省份建设生态博物馆的热情。200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提出了“1+10工程”,即一个“龙头”博物馆——广西民族博物馆和10个民族生态博物馆的组合。广西的“1+10工程”有两个特点:其一,定位简洁明了。“1+10工程”的建设宗旨为“促进社区文化保护、传承和发展,推动社区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第二,连锁经营。根据广西多民族特点,将广西省级民族博物馆与各个民族生态博物馆建设形成一个体系,这是生态博物馆建设新的探索。不仅西部地区,东部一些地区,对建设生态博物馆也有浓厚的兴趣。如浙江安吉市积极实践生态博物馆建设。
云南以民族文化生态村、国家公园等概念探索建设特色文化园区。
上世纪80年代后期,云南有关研究机构就与美国大自然协会合作,在云南实施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经过多年探索,形成了腾冲县和顺乡、新平县南碱花腰傣村、丘北县仙人洞彝族村、景洪市巴卡基诺族山寨等一些成功试点。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与生态博物馆建设有异曲同工之处,强调专家指导,强调当地居民自我建设、自我管理,减少政府干预等。②
国家公园建设理念、旨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促进可持续发展。2009年6月,国家林业局将云南省确定为建设国家公园的试点。云南省成立了省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对《云南省国家公园发展规划纲要》以及四个试点国家公园总体规划进行了批复。丽江市老君山国家公园是其中之一。老君山国家公园是金沙江、怒江、澜沧江三江并流风景名胜区的主体部分,面积约710平方公里。有丰富奇特的自然风貌,有多姿多彩的民风民俗,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和科学考察价值。云南确立的国家公园还包括迪庆普达措国家公园,大理苍山国家地质公园等。
三、特色文化园区的价值
从目前来看,各地生态博物馆、民族文化生态村、国家公园等特色文化园区建设差异很大,有许多成功的例子,徒有虚名也不少。总体来说尚处在探索之中。但其价值和意义应予充分肯定。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特色文化园区建设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具体实践。近些年来,中央反复强调要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推动科学发展;强调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就必须找到减少物质资源消耗、可持续发展的路径。特色文化园区建设以地方特色文化资源为依托,通过对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走出一条有别于传统工业经济发展方式,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极有意义的探索。
其二,特色文化园区建设丰富了主体功能区建设思路,为西部探索出一条新的发展路径。为保护生态环境,国家“十一五”规划和中央“十二五”规划建议均提出要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按照主体功能定位,规范空间开发秩序。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大多是自然资源丰富、生态环境脆弱的西部地区。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列出了22个限制开发区和1164个禁止开发区,其中有17个限制开发区和大多数禁止开发区均位于西部地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要求要把保护生态环境作为发展前提。既要保护生态环境又要发展经济,常常是两难选择。特色文化园区建设为解决两难选择提供了路径。西部一些特色文化园区建设证明,生态资源、人文资源越是得到很好保护,地方经济越是可能做到绿色发展、差异化发展、可持续发展。
其三,特色文化园区建设为传统与当代找到了结合点。特色文化园区以其独特的自然风貌和风土人情,总是成为吸引中外游客的最佳目的地,像黄山、丽江等一些地域文化鲜明、环境优美的城市。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特色文化资源稀缺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这些特色文化园区天人合一的自然环境、闲适的生活态度与后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理念有很多契合之处。
上述现象也说明,传统文化与当代生活能够和谐相处。以前,基于历史进化论的历史观,人们认为,人类社会是由低级向高级的演变过程,文化也是由传统向现代的变迁过程。传统理念、习俗的解体,是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传统与现代是对立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商业社会势如水火。实际上,在当代商业社会我们常常看到相反的情形,传统理念与现代理念、传统习俗和时尚往往能够和谐相处,甚至常常相得益彰。比如,在拉萨的八角街,人们能看到,西藏的传统工艺品将佛教文化与时尚相结合,成为商品社会传播藏族文化的极好载体。佛教、少林武术这些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不但没有式微,相反借助商业平台如鱼得水,充分彰显其价值和影响力。这说明,就保存本土文化来说,在经济上越成功,对保存本土文化越是有强烈的自觉意识。因此,特色文化园区不仅在经济领域提供了有别于工业经济的发展路径,也在观念领域提供了有利于彰显个人价值和生活情趣的另一种方式。
其四,合理利用人文资源是对文化资源最好的保护。特色文化园区建设过程说明,合理利用人文资源是对人文资源的最好保护。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关系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一些学者赞同建设生态博物馆、民族文化生态村,但很反感利用人文资源的提法,认为文化遗产资源只能提保护,而且必须保持原貌,任何变动都是对文化遗产资源的破坏。这种观点初衷很好,但不具有可操作性。因为如果文化遗产、文化资源不能为当代社会服务、不能为当地居民服务,文化遗产保护也就失去了意义。同时,对西部许多生活在温饱线上下的当地居民来说,文化资源如果不能起到改善生活环境的作用,期望他们自觉保护文化遗产,也只是空中楼阁。在建设贵州梭戛生态博物馆时,中方专家与挪威专家就有不同观点的争论。挪威专家认为,为防止现代知识污染当地美好文化,不应该让当地长角苗女孩去读书。中方专家则认为应该让她们获得现代知识,学习更多的技能,这也有利于提高保存自己文化的自觉性。挪威专家认为,长角苗妇女由于长期背水,为保持身体平衡,有着独特的站姿与走姿,不应引入自来水,以免破坏长角苗妇女独特的走姿;而中国学者认为,不能因为要保持当地妇女的身形,而要她们长此以往地背水。上述争论的焦点是,究竟是人为文化遗产服务,还是文化遗产为人服务。实际上,只有在当地居民看到地方文化资源有利于改善当地生活环境时,才能真正激发起保护文化遗产的热情,文化的保护才能得以实现。
我们确实要正视目前文化资源利用中普遍存在的盲目开发、破坏性开发的问题。上述现象的出现,一是急功近利;二是监督不力。但因噎废食,对文化资源利用一概排斥也是不可取的。
四、特色文化园区建设的启示
一是需要重视跨区域合作。一些特色文化区域往往跨行政区划,如果仅仅着眼于本地区的规划,会出现重复建设。以酒文化为例。以赤水河为动脉,方圆500公里汇集了许多名酒,是中国著名酒乡。在该区域内的遵义仁怀镇茅台酒厂有酒文化园区,宜宾五粮液酒厂也有酒文化园区,其他酒厂都计划做酒文化园区,这就需要统筹协调,避免雷同。还有,少数民族往往分布广,具有跨行政区划的特点。在建设少数民族文化园区时,也要注意统筹协调。如苗族山寨分布在贵州、湖南云南、重庆、广西等多个省市,如何避免重复建设应该引起重视。
二是鼓励因地制宜,探索为当地居民接受的管理方式。从目前来看,特色文化园区的管理方式各有特点。有以下几种:
1、政府为管理主体。地方政府在特色文化园区建设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2、非政府组织为管理主体。贵州省黎平县地扪侗族生态博物馆就是一例。地扪侗族生态博物馆受香港明德集团资助,由中国西部文化生态工作室负责建设和运营。该工作室是一个在香港注册成立的非政府组织。
3、外来公司为管理主体。如黄山市世界文化遗产——宏村就是与北京一家旅游公司合作,由该公司负责经营。
4、当地村级组织为管理主体。如黄山市世界文化遗产——西递村就是由村办集体企业经营和管理。
各种管理模式都有优势和不足,仍需要在实践中检验。
注释:
①参见祁述裕、于国华:《两岸文化产业的比较与借鉴》,《东岳论丛》,2010年第10期。
②参见尹绍亭、乌尼尔:《生态博物馆与民族文化生态村》,《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