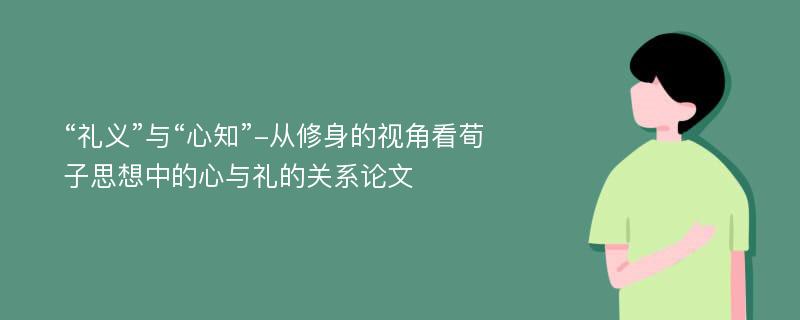
“礼义”与“心知”
——从修身的视角看荀子思想中的心与礼的关系
李健芸
(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871)
摘 要: 荀子的礼义之道内涵广泛,就其对于个人修身而言,则旨在为个人确立秩序化的行动准则。这套准则首先奠基在人群之中,群体的先在性是礼义之道实行的前提,修身就意味着在群体当中为自身确立当然之则。但这种准则不是完全外在的规范,而是能够达到疏导人情、使人的表达和行动获得最佳的节度和条理的效果。这种节度和条理所以可能的根基在于人心的洞察和创制。人通过一系列治心的功夫,使心达到无蔽的大清明状态,能够明澈洞观自身及其所属其中的事态、情境与人群,进而能够在统观自身所处的关联整体当中实现自身行动得其适宜,让自身的情欲得到适宜疏导与通畅表达,以成就此身在当时当下的身体秩序。这既是礼义之道的始基,也是礼义之道的要义。
关键词: 荀子;礼义之道;虚壹而静;大清明;修身
荀子的礼论无疑构成荀子思想架构的重要一环。在荀子思想中,“礼”不仅作为一套社会规范、政治法则运作于社会整体,同时,“礼”也是个人修身的范本,以礼修身在荀子这里正是通向理想人格、成贤成圣的必经之途。但是,在过往的研究中,不少学者将荀子的“礼”视作一套外在的规范,从而视为一种政治权威主义。如果这样,那么荀子以礼修身无疑缺失了内在于人自身的根基。但是,如果它当真只是一种外在规范,那么人何以可能与一套全然异己的东西相合?“礼”当真不是由人自身生起的一种制作吗?本文试图围绕以礼修身究竟如何可能这个问题,通过对荀子礼论的相关文段的分析,论证荀子以礼修身所以可能的根基实则在于群己关系的先在性以及在此关系整体中发挥的人的心知之用,“礼”正是由无蔽的心知之用生起的一种制作。
一、有分有义
荀子明确从“礼”的方面规定人的修身准则:
凡用血气、志意、知虑,由礼则治通,不由礼则勃乱提僈;食饮,衣服、居处、动静,由礼则和节,不由礼则触陷生疾;容貌、态度、进退、趋行,由礼则雅,不由礼则夷固僻违、庸众而野。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修身》)① 本文所引用的《荀子》原文,皆出自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下文只标注篇名,不再另作注释。
礼者,所以正身也。(《修身》)
在此,荀子指明修身必须依礼而行,而表现于外的容貌言行、举止动静也会在礼的调节下变得和谐舒缓、端庄典雅,因而礼正是个人修身的准则。在准则意义上的“礼”正是荀子所谓的“人道之极”:
先王之道,人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谓中?曰:礼义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儒效》)
礼者,人道之极也。(《礼论》)
这里荀子首先指出所谓“道”乃是“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也就是说,“道”乃是“人之所以道”之“道”和“君子之所道”之“道”,这里“所以道”和“所道”的“道”字用作动词,整句话意为“道”是众人所借以行走的“道”,是君子所行走出来的“道”。因此,君子是最初成就道的人,而民众则沿循君子所成就的道去行动即可。可见,这里的“道”正是人道。人道之极就是礼义之道,也即先王之道。但进一步的问题是:荀子所谓“礼”具有怎样的内涵使之可以作为修身的准则?上文指出,“礼者,人道之极”,故而礼的内涵就是人道。荀子对人道有如下明确界定:
人之所以为人者何已也?曰:以其有辨也……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圣王。(《非相》)
人心譬如盘水,正错而勿动,则湛浊在下,而清明在上,则足以见须眉而察理矣。微风过之,湛浊动乎下,清明乱于上,则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解蔽》)
对于“分”,荀子还有以下界说:
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王制》)
这里荀子对分的界说分两层:一是“分”是在作为群体性存在的人群中产生的;二是“分”所以能进行在于人“有义”。“群”表明荀子的人道奠基于人作为一种群体性存在,“群”作为人一切活动最初的奠基表明人从一开始就处在一个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世界中,人的活动最初就在与周边的人的互动之中展开。因此,荀子的人道不是孤立的个人之道,而是群己之道,是个人如何在人群中行动之道,更可以说是人群中的不同个体间如何互动之道。只有奠基于群体性的人之上,所谓“分”与“辨”作为一种秩序的确立才有可能实现。“群”是荀子讨论人道的基础,“义”则是实行人群之“分”的原则。
但是,所谓“义”的具体意义在上述引文中却没有得到明确的界说。既然“义”在人群之辨与分实行的过程中如此重要,就不得不对此处“义”的意义略作说明。综观《荀子》全书,荀子既多以“礼义”、“仁义”并举,也多单举“义”以为人之德行。对单举之“义”,荀子有如下界说:
夫义者,内节于人,而外节于万物者也;上安于主,而下调于民者也。内外上下节者,义之情也。(《强国》)仁,爱也,故亲;义,理也,故行(《大略》)
这里所谓的“节”和“理”,指的是节度、条理。所谓“内外上下”指:个人自身具有的情欲等内在机理和个人的行动,这是“内”;人群之间、人与天地万物之间形成的关系,这是“外”;人群之内形成的有差等的位次和序列安排,这是“上下”。在“内外上下”共属一体的关联共同体中,“义”能够使“内外上下”皆能各自有各自的节度和条理。因此,概而言之,荀子所谓“义”指的是人之行为所应有的当然之则,“义”使人的行为举止得到规范,使之无不合理、无不适宜,人有义才能“行”。同时,一个真正的君子,其行动也必定会始终以“义”为准则,而不会被其它任何外在的力量所束缚或逼迫。荀子说:
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桡,是士君子之勇也。(《荣辱》)
土壤含水量直接影响苹果栽植成活率。不同耕作方式土壤含水量存在明显差异,自然生草行间和株间土壤含水量>行间清耕>间作小麦:间作小麦20 cm土层含水量只有1. 65~3. 88%,直接影响苹果栽植成活率。
这是说真正的士君子,他一切行动都只听从“义之所在”,他不会为权势、利益等外在力量所逼迫,甚至可以为了“义”而放弃生命,这就是士君子的“勇”。因此,对于真正的君子而言,其行动之当然之则就是义之所在。所以,如荀子之论,只有以人之所行的当然之则——即“义”——为人群之辨与分所实行的根据,才能保证这样的“分”不会沦于以利益、权势为依据的强制性的等级秩序,才能使“分”能够保证人群得以“和”,得以统一为一个和谐的秩序整体,即荀子所谓:“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王制》)
B.利用SPSS进行数据分析。首先仍要将已知的加工整理数据恢复为原始数据,在“态度”变量中可进行如下编码:1—赞同,2—中立,3—反对;在“身份”变量中编码为:1—学生,2—教师,3—领导。之后依次单击菜单栏“分析”→“描述统计”→“交叉表”,在交叉表窗口中,将“态度”变量移入“行”,将“身份”变量移入“列”,如图5所示。接下来单击交叉表窗口中的“统计量”按钮,在弹出的窗口中勾选“Gamma”系数,如图6所示,单击继续。再单击“单元格”按钮,在弹出的窗口中,勾选百分比选项卡中的“行”、“列”、“总计”,如图7所示,单击继续。回到交叉表窗口,最后单击确定。运行结果如图8和图9所示。
另外,“义”作为人之异于禽兽者,自然也当属于上文所谓的“人之所以为人者”的范畴。但荀子在这里将人有义与“有气、有生、有知”放在一起讲,似乎让人以为这四者都是人在同一层次而有——生而具有。有学者据此将“义”连同“辨”一起视为人先天具有的成善的能力。① 如路德斌认为,荀子虽言人之性固无礼义,但这却不意味着人固无礼义,相反,义在荀子那里“是一种道德的属性或能力……正是这种属性和能力构成了人所以能‘伪’而成善的价值之源和内在根据。”路德斌:《荀子与儒家哲学》,济南:齐鲁书社,2010年,第115页。又如林宏星认为,“在荀子那里,‘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有义、有辨以及知、能等质具,而这种义辨、质具作为人内在本有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伪’何以可能的根据。”林宏星:《〈荀子〉精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6页。 然而,这实则是把荀子所谓“人之所以为人者”误解为对人的先天本质规定。在荀子这里,“人之所以为人者”并不是一个对人的先天本质规定的描述,而是人借由自身的力量所成就的人道。在荀子“天人之分”的视野下,“人之所以为人者”不在于属天的先天本质规定或生而具有的能力,而正在于根本上属人的成就,这正是人以自身之力所成就的人道。因此,所谓“人道”并非一个先天的被规定的“道”使得人成为人,而是人依凭自身之力所走出的道路,是人所成就的道路。这才是“人之所以为人者”“人道”的恰当含义。因此,所谓“有辨”“有义”皆是就“人之所以为人者”而言,即就人所成就出的成果而言。人所以异于禽兽在于人有义,这话其实是说人异于禽兽在于人能以人的主动性成就属于人的义道。
综上,荀子之礼存在的基础是人作为一种群体性的存在,其内涵是人群中的“分”和“辨”,而“分”和“辨”依循的原则是“义”。进一步明言之,人群之“辨”与“分”根本上正是确立一套人类社会的秩序,而这套秩序所依循的原则是“义”。“义”作为人之所行当有的应然之则,能够使人的行动得其适宜,使人群中不同的人各有其行动的节度和条理,由是而保证人群之“分”能够和谐共处以形成一个统一之秩序整体,而这个和谐统一的秩序整体表现出来就是人世之“礼”。因此,荀子言礼,最根本的内含是人类社会所得以和谐统一之秩序。此秩序既能够使个人行动在群己关系中得其当然的节度和条理,也能使整个人群的相互关系各得其宜。因此,礼的修身意义正在于让人身合于秩序。
上述对“礼”作为一种使自身得到秩序化的修身准则的含义界定,揭示出“礼”带来的秩序化意义,而这也正是荀子对善和恶的基本界说:
凡古今天下之所谓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谓恶者,偏险悖乱也。是善恶之分也矣。(《性恶》)
荀子正是以有序为善,无序为恶。因而,让人身合于秩序,不至于顺遂人之情性的自然发展而导致混乱,这当是荀子修身之学当有之义。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顺遂人之情性导致的混乱乃是人群的混乱,因而修身根本上不是修一个孤立的自我,而是在人群之中修身,在一个始终与他人共处互动的主体间性的世界中修身,通过修身让身体的情性与欲望得其应然之度,而不会扰乱与他人共处互动中的和谐秩序,这是正善平治的修身秩序当有的意趣。在修身过程中,人心作为人内外活动的主动控制力,又具有认识能力,它无疑是认识秩序和执行秩序的主体,因而心必对自身进行修治使之合于秩序,进而控制人身。因此,无论是治气养心还是化性起伪,甚或由之引发的容貌言行,都必将落实到对秩序的践行当中,才可臻于平治,亦即臻于善。
既然礼的核心内涵在于秩序的确立,因而以礼治身就必然使人身臻于平治善正,那礼义之道作为修身与成人之道的当然之则就是修身功夫的题中之义。但是,仍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值得继续追问:礼义之道作为一套人类社会的秩序,其得以确立的根基是什么?荀子固然说过礼义乃是先王“积思虑、习伪故”(《性恶》)的结果,后人只需遵循先王确立的准则而行动即可达到修身成人的目的。但是,这是否意味着礼义仅仅是人的思虑的主观构造物?抑或礼义之确立另有根基?对此追问将进一步探入荀子礼义之道与修身之道的根基。
二、礼以养情
礼义之道作为秩序化的修身准则,同时正是成善之道。荀子又有“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之论,可见礼义、善皆生于“伪”。这里的“伪”即“人为”之义② 详细考辨可参看王先谦:《荀子集解》,第487、513页。 ,而“伪”又根源于人心的思虑之功,荀子这样界定:“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正名》)又说:“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性恶》)可见礼义显然是心的创造物。但心何以能创造秩序?
梁涛教授认为,“荀子的心首先是道德直觉心”。[2]74其下此判断的理由主要依据《荀子》之中言人好善、欲善的文段:
人之所恶何也?曰:污漫、争夺、贪利是也。人之所好者何也?曰:礼义、辞让、忠信是也。(《强国》)凡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性恶》)
梁涛教授据此认为荀子之心本然地具有“好善恶恶、知善知恶和为善去恶的能力”,进而得出“荀子的心首先是道德直觉心”[2]的结论。唐君毅先生甚至认为,假使荀子从其欲善之心进一步肯定此欲善的能力为善,“则荀子亦终将谓此心为必然定然之善也。”[3]37此论可以说发现了荀子对人之欲善、好善的肯定,但问题却在于人之欲善、好善是否就是心具有的“道德直觉”?若照此说,则善之成就只需将此心之能力像孟子所说的那样“扩而充之”即可成就,那荀子又何需反复强调“积思虑、习伪故”而后成善?“扩而充之”的功夫如流水,而积习之功则如造房筑屋,必须基于对大量经验的累积才可能有所成就,而荀子所肯定的人之好善、欲善根本上就是心在反复思虑与不断实践的过程中形成的欲和好。如同荀子多次言“先王恶其乱也”① 如《礼论》篇云:“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又《乐论》篇云:“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 所暗示的那样,人在面对最初的乱象时产生的不满才让人欲求一种与之不同的有序的生活,由是而起种种思虑、反思,而这使得欲善之欲逐渐形成。正如林宏星教授指出,荀子这里对善的“欲”不是像生理欲望那般仅是对外物的直接的自然反应,而是另一种动机,这种动机表现为心在长久的顾虑后做出的“慎重的(prudential)反思、评价及其最后所作出的决断”[4]62。因此,秩序的建立的确是心的产物,但却不是道德直觉自发产生的结果,而是心之思虑与积习的成果。
分开两年,谁都没有荒着时光。方晓倩谈了一场无疾而终的恋爱,而林丹刚新婚,照他的话说,不是多爱,是时机刚刚好。
那么,如果作为秩序的善没有人的道德直觉作保障,而是产生于人心的不断思虑的积累过程,这是否可能带来外在强制的结果?人心思虑礼义所依据的是什么?不少学者喜欢援引以下文段讨论这个问题: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礼论》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先王制作礼义的起因是憎恶人群混乱,目的是为了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有学者据此认为荀子的礼论是从功利主义的立场立论② 持此观点的学者非常多,如冯友兰认为荀子论礼之必要性“从功利主义立论”,又言“荀子亦重功利,与墨子有相同处”,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重庆: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09年,第246-247页。又如牟宗三认为:“能治之礼义法度亦唯是工具之价值,而无内在之价值。此则终不免于功利之窠臼。”见牟宗三:《名家与荀子》,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第144页。 ;更有学者进一步认为荀子之礼实则是一种外在的权威,以之保证现实政治得以稳定。③ 如徐复观认为荀子之礼最终“只成为一种外铄的、带有强制性的一套组织的机栝”,见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497页。又如劳思光认为:“今荀子则据欲求立说以释礼义之产生,亦以为人怀私欲,有求遂有争,故必须制礼义以节之,使人服从一定秩序。于是礼义之源流乃归于平乱息争之要求。由此而生出荀子之权威主义理论。”见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58页。 类似的论断实则是将荀子对人世秩序的肯定误读成了功利主义和政治权威主义。上述引文的关键在于“先王恶其乱”和“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两条对礼的说明。首先,“恶其乱”让欲求秩序、建立秩序成为可能,这是上文分析过的“欲善”,对善正之序的欲求如何就能等同于功利主义呢?其次,“养人之欲,给人之求”说明了礼的目的,这分明是以人的欲求为基本满足对象,却又如何变成外在权威主义?陈来先生则认为荀子之礼是人的理性的产物,“礼制的建立和起源,本质上是人的理性面对社群生活的现实和需要所做的创制,道德则是其中的一部分。”[1]126这实则是把礼视作上文分析的纯粹心之思虑的构造物。但是,秩序如果纯是心之思虑的构造物,那这套秩序就与人之性、情、欲全然异质,其创制的根基就与其所要规范的对象本身全然无涉,而只关乎人群之基本利益,则此规范就有可能变成与人自身全然无涉的外在制约,而这正是不少学者对荀子礼论发出的质疑。
尽管如此,广州教育也面临着时代发展与城市发展的双重挑战,面临着中国教育普遍问题和广州教育特殊问题的双重压力,面临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人才成长多样化的双重需求。为有效应对挑战、充分满足需求、稳健发展教育,2011年以来,广州以“好教育”作为教育的发展目标与前进方向,不断挖掘其内涵,不断扩大其外延,不断寻找好教育的突破口与创生点,不断将对好教育的思考和实践推向纵深,广州教育由此迈上新的台阶,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交上了一份让人民满意的答卷。
然而,正如上述引文中所强调的,礼的目的在于“养人之欲,给人之求”,荀子虽然总在强调礼的规范意义,却并非认为礼仅只是一套强制人们执行的社会规范。相反,荀子认为礼对人的欲望和情感有给养、疏导的作用。荀子说:
凡语治而待去欲者,无以道欲而困于有欲者也。凡语治而待寡欲者,无以节欲而困于多欲者也。有欲
近红外光谱分析系统的设计与出现,有助于更好地检测小麦中蛋白质的含量,同时采用MPA光谱仪验证了近红外光谱分析方法用于谷物品质检测的可行性。然后利用CA-06光栅光谱分析仪建立小麦蛋白、水分的偏最小二乘法模型,使得仪器性能的稳定性和准确性大大提高。利用凯氏定氮、DA 7200和8620近红外光谱仪这三种方法研究小麦面粉蛋白质含量的快速测定方法,测定出籽粒蛋白质差异较大的60个小麦品种(系)蛋白质含量,发现可以用8620、DA 7200近红外光谱仪对育种材料进行早期测定[2]。
这里所列举的各种人心之蔽实则都是人心偏执于某一端、某一隅而给人心带来的障蔽,这些障蔽正如盘水中的湛浊之物,让人心陷溺于各种偏执的状态中而妨碍盘水之心对收容于内心的事与物予以清明的映照洞察。由这里所列举的各种人心之偏蔽可知,这些偏蔽既包括人的情欲好恶,也包括人所接受的知识。但是,盘水之心通过治心的功夫让人心中的湛浊之物得到澄清,而“澄清”不等于“清除”。“澄清”只是不以情欲好恶、已有知识等障蔽了人心的清明之用,而非对这些可能导致人心之蔽的因素加以清除。因此,上文所阐明的“虚”所表征的心的容纳力,就不仅是容纳,而且是清明地容纳,即清明地映照所容纳之物,按照所容纳之物的本来面目予以容纳,这样的容纳根本上与映鉴明照有共同的意趣。
这是认为单纯对人欲的去除或要求人们寡欲是无用的治理手段,这只是不懂得如何引导和调节人们的欲望。而在荀子看来,礼的精神恰就在于能够达到对人情、人欲的“养”:
礼者,养也。(《礼论》)
孰知夫恭敬辞让之所以养安也!孰知夫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也!(《礼论》)
护理部主任李龙倜向《中国医院院长》杂志记者补充道:“‘星星急救’旨在为广大群众培训常见意外情况的处理,以及自救、互救等知识技能,希望通过规范专业的培训,不断提升民众自救和互救技能,达到人人参与急救、人人精于急救、人人能够挽救患者生命。”
礼可以“养情”,还可以为人之情“立文”,即将人之情以恰当的形式表现出来。荀子说:
三年之丧,称情而立文,所以为至痛极也。(《礼论》)
礼者,断长续短,损有余,益不足,达爱敬之文,而滋成行义之美者也。(同上)
主持人上场就给4位导师抛出难题:“你们喜欢怎样的球员?”周杰伦说:“要花哨。”李易峰说:“要热情。”郭艾伦说:“要善良。”林书豪的答案最真诚朴实:“要技巧。”周杰伦“怼”他:“想看球技去NBA啊!”林书豪一脸认真:“我就是喜欢赢。”
凡礼……至备,情文俱尽;其次,情文代胜;其下,复情以归大一也。(同上)
礼以顺人心为本,故亡于礼经而顺于人心者,皆礼也。(《大略》)
所谓称情立文、断长续短以达于爱敬之文都是说礼作为人情的适当的表现形式,它可以充分地使人情得以通达,故而礼之中最完备的情况就是“情文俱尽”。因此,“礼以顺人心为本”,所谓“人心”,据上述引文来看当指人情。如果礼的形式恰当表达了人情,使人之情得到通达,那即便不合于古人传下来的礼经,也符合礼的精神。可见,礼并非一套单纯的外在秩序,礼之于人的作用也并非简单地强制规范。如前所论,礼之内涵根本在于“义”,“义”表现于外则是礼,而“义”是人之行动所当依循的应然之则,“义”就是“节”“理”,合于“义”的人能够在其行动中得其应然的节度和条理。“义”在人之行动中所保证的节度与条理,也正是礼以养情、礼以节欲所得以可能的保证,它能够恰当地使人情得到引导、调节和通达。但问题在于,“礼”所以能够疏导人情、为人之情欲的疏通确立适宜之度和当然之则,这样的秩序何以可能?
学者对上述文段有相当多的讨论,但大体而言多是从认识论的角度进入,认为这段文字是荀子表达心之认识何以可能的文字。无疑,荀子言心确有言及其认识的能力,这一点在前文讨论荀子心论时已经指明。但这段文字讨论的是“人何以知道”的问题,而荀子所谓“道”的核心则是礼义秩序。因而这段文字的关键在于回答心何以能成就秩序世界的问题。在已有的研究中,唐君毅先生曾敏锐指出这段话之于理解荀子人文秩序的关键意义。唐先生精当地指出,荀子虚壹而静的工夫所成就之心,“为本身能持统类秩序,以建立社会之统类秩序,以成文理之心。”[5]74但是,笔者以为此中仍有深意值得再作探讨和发掘,这即是对于如何从“虚壹而静”的工夫中成就出礼义秩序?对此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的阐明。
三、虚壹而静
在之前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知道,荀子的礼义之道也是他所要成就的人道之极,而荀子也曾肯定礼义之道是圣人“积思虑、习伪故”的成果,思虑与起伪的根源都在人心,而人之行动的能动的主宰力量也根植于人心,所以人心在成就礼义秩序和理想人格的过程中无疑是根源力量。但上文又对荀子所言之人心作为道德直觉心的观点予以了辩驳,那非道德直觉的人心如何可能在现实的人群人世中成就一套如上所述的礼义秩序?这个问题就是荀子“人何以知道”的问题。
对此问题的回答在《荀子·解蔽》篇中,荀子肯定人心莫不有所偏蔽,只有“知道”之人才能实现人心的彻底解蔽,使人心达到全体明澈的境界。兹先将荀子对此问题的回答引述如下:
(2)若不存在,则提示用户输入完整;若存在,则系统检验该用户名是否已被注册,即遍历用户表查询是否有相同信息,若不存在有相同记录则提示用户该用户名不存在,否则用户注销成功。
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心未尝不臧也,然而有所谓虚;心未尝不满也① 此处“满”字据杨倞注当为“两”,从下文来看此说当是。见王先谦:《荀子集解》,第467页。 ,然而有所谓壹;心未尝不动也,然而有所谓静。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然而有所谓虚,不以所已臧害所将受谓之虚。心生而有知,知而有异,异也者,同时兼知之。同时兼知之,两也,然而有所谓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谓之壹。心,卧则梦,偷则自行,使之则谋,故心未尝不动也。然而有所谓静,不以梦剧乱知谓之静。未得道而求道者,谓之虚壹而静。作之,则将须道者之虚则人② 据王引之注云此处“人”字当为“入”字之误,当是。见王先谦:《荀子集解》,第468页。 ,将事道者之壹则尽,尽将思道者静则察。知道察,知道行,体道者也。虚壹而静,谓之大清明。(《解蔽》)
综上所述,急性阑尾炎合并糖尿病患者实施围手术期的护理效果十分显著,且能够达到预防术后并发症和减轻疼痛感的目的,值得进一步推广与探究。
首先阐明何谓“虚壹而静”。从开头“心未尝不……然而有所谓……”的表述中可以看出,荀子这里并不是要以后者否定前者,而是在肯定心具备前者的状态的同时,还应该要有后者的状态。因而“虚壹而静”首先是作为一种治心的功夫,通过此种功夫让心达到“虚壹而静”的状态,这种状态让“心知道”得以可能。所谓“虚”,即是“不以所已臧害所将受”,这指的是心打开自身的容纳力和领受力,去接纳、领受所有进入心中的东西,不让心中已经藏纳的东西妨碍将要领受的东西。所谓“壹”,即:“心生而有知,知而有异,异也者,同时兼知之。同时兼知之,两也,然而有所谓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谓之壹。”廖名春教授认为,这里的“两”是指多种认识,“一”则是指专一于某一种知识,而“壹”则是前两者的“辩证统一”。[6]149这似乎是说所谓“壹”就是指心能在认识事物A时专心于A,而在认识事物B时专心于B的能力。这样的说法看起来很有道理,但这实则只是把“壹”解作能够专心的能力,即能够在不同事物面前专心于当前事物的能力,而非“不以夫一害此一”。何况,荀子这里所谓的“然而有所谓一”的“一”,并非专心于某一种事物的专心力,而是指两种知识各自为一的意思。唐君毅的解释颇具启发,他认为:“此整个是一对于万物万事各得其位,而通于度上,兼加以总摄贯通之心。”[5]75这说的是心的统摄力,即如何在心同时兼知多物的情况下依然能够按照它们在心中的位置加以忖度、排列,以统摄为一个整体的统摄力。而这种统摄力实际上已经暗含了荀子对秩序的寻求,即如何将各种不同加以排列,安排各自的位次,还能保证彼此不相为害,各安其位。这就需要“壹”的统摄力。所谓“静”,即:“心,卧则梦,偷则自行,使之则谋,故心未尝不动也。然而有所谓静,不以梦剧乱知谓之静。”心无处不动,这里的“静”不是让心不动,而是让心不以梦和剧的妄动扰乱了心知。所谓“静”,指的是心在动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精神专一、专注笃定的境界。
“虚壹而静”略释如上。所谓“未得道而求道者,谓之虚壹而静”,这是说对于未得道而求道的人,就告诉他们虚壹而静的治心功夫。“作之,则将须道者之虚则入,将事道者之壹则尽,尽将思道者静则察。”这是说如果按照“虚壹而静”的功夫治心就能入道、事道和思道。“道”指的正是秩序。那么,何以“虚壹而静”能成就一套秩序?下文将对此问题做出详细的分疏。
“虚”表征容纳力,“壹”表征对所容纳之物的统摄力,而“静”则表征专注力。“虚壹而静”所达到的境界就是“大清明”。所谓“大清明”在稍后的文段中荀子以盘水之喻对之做了进一步的解释,荀子说:
由此可知,“人之所以为人者”就是“人道”,其具体内涵则是“有辨”。这里以“有辨”与“饥而欲食”等人之性相对举,说明人道与人性在此截然不同。这里的“辨”以“分”为表现内容,指人类社会中的伦理、等差、位次之间的分辨,这就是“辨莫大于分”。因此,“辨”与“分”都指向了人类社会中确立的秩序。在这个意义上,荀子实则是以人之有序作为人道的内涵。陈来先生以为,荀子这里的人道是当然,“人道是人的社会生活得以成立的原理”,而人性则是自然,“人性和人道的分别,亦是自然和当然的分别。”[1]110此说可谓得当。辨与分的最佳表现形式就是“礼”,因而辨与分皆是礼的内涵。
它是一个时间段的专题组画,郑军里为求得创作的系列性,在画面的尺寸上是有所统一和控制。在不大的画面中处处皆有游迹所到。郑军里有过硬的笔头能力,造型和笔墨都如此,所以在一个新环境和新视觉里,即能爆发出信手拈来的轻松感和创造力,这种创造有很多的神来和趣味。这种神来和趣味在画甘南的这批画里依然有和畅的表现。
由这段话可以见出,经历虚壹而静之治心功夫所达到的“大清明”之心的状态,正如平静的盘水,而且是水面足够宽大的盘水。荀子在这里以盘水之喻表明,人心有湛浊的部分,而这部分需要通过治心的功夫让其不影响盘水之心的清明作用。这里所谓的湛浊实则就是《解蔽》篇中所言的人心的各种偏蔽,荀子在言人心之蔽时说:
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解蔽》)
故为蔽:欲为蔽,恶为蔽,始为蔽,终为蔽,远为蔽,近为蔽,博为蔽,浅为蔽,古为蔽,今为蔽。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同上)
无欲,异类也,生死也,非治乱也。欲之多寡,异类也,情之数也,非治乱也。(《正名》)
因此,通过“虚壹而静”的治心功夫所成就的大清明之心,首先是一明察明照之心。此心通过“虚”的功夫对人心中已有的种种偏蔽加以澄清,使人心不陷溺于其中,不为种种可能导致偏蔽的因素所妨碍,而能以此心之清明映照万事万物,即内心容受万事万物。
四、知通统类
实际上,“虚壹而静”所成就的大清明之心,就是解除心之偏蔽后的无蔽之心。而正如上文在阐释“壹”的功夫时所指出,“壹”指的是内心的统摄力,对所映鉴、所容受之万事万物的统摄力,而这种统摄力正为秩序提供了可能。但是,统摄力所成就的秩序,只有当心之清明对心所容受的万事万物映鉴出其本来面目时,这样的秩序才是“中理”的秩序。
自主学习在很多对于教育理解不深的教师眼里是一个无法完成的项目,毕竟教师的任务就是教会学生知识,如果学生都能自己学习知识那要教师还有什么用呢?其实这个想法完全是错误的,有句俗话说的好:“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作为教师这个角色的主要任务就是“领进门”——让学生学会自主学习,这对于学生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认知过程,因此能否让学生掌握自主学习的能力是评判一个教师是否达到一定境界的关键.希望广大高中物理教师都能够达到这一境界,让学生充分享受自主学习的乐趣.
对此明照之心与心之统摄力的关系,唐君毅谓之为心之能虚与心之统类的关系,唐氏云:“一方为能依类以通达之心,一方又为至虚之心,以其心能虚,故能知一类事物之理,又兼知他类事物之理,而综摄之,心乃成能统类之心。”[5]76唐先生此说颇有见地。上文已经指明,心之“壹”不同于心对某一具体物事的专一用功,而是对不同物事同时加以统摄,使之统摄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这种力量叫心之“壹”。而心的统摄力必须以心之明以照物、虚以容物为基础,在此基础上对心所照所容之物加以统摄。由于心之统摄以心之明照为基础,而上文已经分析过,心之明照就是解除内心各种陷溺于一隅之偏的偏蔽,而使内心达于无蔽的清明状态。此时的清明之心在面对其所容受、所映照的物事时,便由从前的执于一偏的有蔽之心转化为大公之心。荀子说:
公生明,偏生暗。(《不苟》)
这句话清楚地表明:裁制万物的大清明之心不是由心自己建构一套秩序去裁制万物,而是首先能“疏观万物而知其情”,这就是心之明照的功夫,心在通达万物之情后对心所容受的万物予以裁制,这就是实行心的“知通统类”之道,以通达之心行统摄之力。因此,这样的裁制依循所容受映照之物事的实情进行,可以说这是心缘物事之情实以确立其理序的过程。
这里所谓的“公生明”与大儒之“志安公”,皆是与人心之私相对而言。人心之私并不仅仅是指心之私欲,而是泛指一切由于人心陷溺于自己所执取的一偏一隅之中的状态,只要人心对其所偏向的某一端某一隅有所执取,并陷溺其中,以此有偏蔽之心评判所面对之物事和世间种种情况,就是人心有私。因此,清明之心、无蔽之心,就是大公之心,此心明照明察,因而在统摄所面对的万事万物时能“知通统类”,这就是唐君毅所谓的统类、明统之心。此明统之心在实行心之统摄力时,其所统摄之整体不会因心之偏蔽、有私而失于不当,此心由于其大公之境界,故而能在统摄之时不以己私施加于所统摄之诸部分,而能使诸部分各得其宜、各当其理,以成就和谐统一的秩序整体。因此,荀子这样描述大清明之心的效用:
疏观万物而知其情,参稽治乱而通其度,经纬天地而材官万物,制割大理而宇宙里矣。(《解蔽》)
志忍私然后能公,行忍情性然后能修,知而好问然后能才,公修而才,可谓小儒矣。志安公,行安修,知通统类,如是则可谓大儒矣。(《儒效》)
但是,在上述对心通过“虚壹而静”的功夫所成就的大清明的状态的论述中,似乎此大清明之心所成就的秩序整体乃是一套对外的秩序,这种理解固然可以从上文引述的心如盘水之喻、“疏观万物而知其情”等文段中找到依据,盘水之心的明鉴作用、心对万物之情实的观察,这些对大清明之心的描述似乎都让人以为此心所成就之秩序乃是一对外物、对心所映鉴之外物的秩序。就这个层面来说,有学者认为荀子之心是认识心,这种观点也未为不可,只是此认识心在认识事物后随即能以其统摄力而转为成就物事之秩序心,事实上唐君毅先生标举荀子之心为明统心正是此意。但是,若将荀子之心首先做这样的理解,则此心所成就之秩序整体固然仍可以首先是人世之人文统类之道、人世之礼义秩序,但此人文礼义之道则相对于心而言则为一外在之物,似乎是说心认识人世而后统摄出人世之礼义秩序,则此秩序对于心而言仍是外在之物。但是,成就人世秩序之心本就是人之心,此心此人本就是人世中人,则人世秩序怎会对于成就秩序之人心而言为一外在之物?
事实上,若照上述思路分析荀子由心成道的思想,就是对荀子思想的一大误读。固然,荀子对心作为成就人世礼义之道的根源力量多有强调,也对心作为裁制万物的能动力量多有凸显。但是,从礼义之道的始基上来看,大清明之心首先明照明察的是人自身当下所处的情境与事态,人心所最初统摄的秩序首先是此身在当时当下的事态中的行动秩序,即事态中的身体秩序。身体秩序表现着心的活动,因而大清明之心首先统摄的是自身的秩序。对此,荀子明言:
浊明外景,清明内景,圣人纵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解蔽》)
对这里的“浊明”和“清明”、“内景”和“外景”的理解,虽然不少注家都有过解释,但笔者以为俞樾所注为胜。俞樾注引《大戴记·曾子天圆篇》云:
术前所有患者均行裸眼视力、矫正视力及裂隙灯显微镜检查,非接触眼压(TX-F,日本Canon公司)及矫正眼压检查(ORA,美国Richard公司),电脑验光(kr-8800,日本Topcon公司)及散瞳后综合验光(RT-2100,日本Niderk公司),眼前节分析仪(Allegro Oculyzer,德国Oculus公司)测量角膜厚度及角膜形态,三面镜检查眼底,A超(AVISO,法国光太公司)测量眼轴长度。
2.2.2 锡伯风情农家乐。随着察布查尔县旅游业的发展,小型旅游经营实体农家乐的发展得到多方支持。察布查尔县孙扎齐乡围绕旅游景点开设了多家农家乐,大多是由当地居民经营,主要是利用当地的农产品加工出具有锡伯风味的特色小吃,同时农家乐小院具有浓郁的锡伯族特色风情,受到游客的青睐。
参尝闻之夫子曰: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圆曰明。明者,吐气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气者也,是故内景。故火日外景而金水内景。
俞樾云:“荀子‘浊明外景,清明内景’之说,即孔子之绪言也。”① 详细考辨,参看王先谦:《荀子集解》,第477页。 据此,这里所谓“浊明”当如火与日对外照明外物而自身不明,如同有浊,而“清明”则如金或水一样映照外物而自身清明。“浊明”所照之物在外呈现,是为“外景”;“清明”所明之物在自身中呈现,是为“内景”。唐君毅进一步解释道:“以浊明言人心者,盖谓人心之只专注其明于物,而限其明于物,则于其外皆无知……故人必有清明之心,内无昏浊者,然后能兼照兼见物之大形或物之全。此即清明之心。此心能见物之全,则物皆为心所映照,其影或印象观念等全在内,而物亦如在心内。”[7]257此说可谓精当。稍有欠缺处在于,唐先生以心所明之内景为外物留在心中的印象或观念,此说恐有不妥。虽然心所明之物为当时当下人所处的情境,但由于人心在经历一番治心功夫后已经达到无蔽的清明之心,且此心当体为一大公之心,因而此清明之心所映鉴之物一如其自身所容纳之物,清明之心当下全体呈现此心此身所置于其中的事态与情境,而此情境一如为心所容受,成为当时当下所呈现之心的现象,这就是清明之心所明之“内景”,实际上就是心之内景,心自身所呈现的现象。因此,大清明之心所明察明照的首先是心自身,这个“自身”不是一个孤立绝断于人世之外的精神主宰,而是始终居持在其所处所遇的情境与事态中的自身,这个自身毋宁说是一无自身的自身,心自身表现为当时当下对其置身其中的情境的洞观与朗照,这正是荀子所谓无蔽之心、大公之心、清明之心所含之真义。
因此,大清明之心首先明察明照的是自身当时当下置于其间的事态与情境,而由于大清明之心是无蔽之心、大公之心,其无自身的自身实际上是让此心消融于其所处的情境之中,由此心所发出的一举一动因而皆能与此身所处之情境相适宜,这正是大清明之心首先成就的秩序,即此身当下行动的合宜之理,即此身当下之秩序。唯有这样的秩序才能实现导欲养情的效果,因为一切情与欲的发动皆是在此身当下所处的情境之中展现,而此当下情境中的身体之动能得其适宜,则一切情与欲皆可以其应然之度而得到疏导和畅通。此身体当下之秩序才是心所成就的秩序整体的始基。
事实上,人对自身的把握必须在一个与外交接之中才可能进行。如上所论,修身之道在于治心,而治心所达到的大清明之心,实则正是对此身在与外交接中所处所遇的情境的明察明照,并通过此明照之功而让此身在其中有合宜的秩序。这里亦可称此情境为人的活动场域。事实上,人无论何时何地都必然先在地置身于某一活动场域之中,诚如海德格尔对此在的生存论分析所揭示,此在先在地“在世界之中存在”,这里的“在之中”不是空间上的某物在某个空间中,而是“依寓于”其中,人先在地生活在其所属关联的世界之中。② 关于海德格尔对“在之中”的详细阐释,可参看[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63-64页。 这个“世界”作为人的一切生存活动的奠基而存在。人世秩序之建立正是要基于人依寓于其中的生活世界而得以确立,人居持于此世界之中,并由其情欲之发动所带来的行为,由其心之发动所带来的行为,以及其他种种行为所勾连起一个活动场域,人与此中之人、事、物共属一体,结成一个意义关联体,这就是人修身的场域,也是人成就自身秩序的场域。因此,“虚壹而静”的治心功夫所以能成就身体行动的秩序,就在于其所达到的大清明之心能够极大地映鉴由自身及其所属关联的周围世界的人、事、物所结成的活动场域,此心之无蔽与大公能够对此场域中的各种情实予以明察通透的了解,因而能使人身的行动无不适宜于当时当下的活动场域。此场域不仅包括修身者周围的现成之物,在荀子那里更重要的无疑是与修身者交接互动的人群。人先在地生活于其所处的“群”当中,“群”构成了人修身活动的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活动场域。可以说,虚壹而静的功夫最初正是对这个人始终居持于其中的主体间的世界有一番明澈通达的了解,而后对收容于内心的此身之活动场域明察明照,此心之大公与无蔽能够以其无自身之自身观照此活动场域中的人、事、物各自的本来面目,而后让身体的行动得其所宜,并对此身之行动中的种种要素加以统摄为一个秩序整体,最后以专一之力持守居持于此活动场域中的此身的秩序,使之在行动中展现出秩序之所在,这就是身体秩序之成就,也是礼义之道的始基。
如上所论,大清明之心首先成就的是居持于某一活动场域中的身体秩序,是在当时当下的修身过程中做到的行动之适宜。因此,礼义修身不是固化的静态的仪节仪式,而是始终处于动态的活动中的修身过程,由于此身始终处于变动不居的活动过程中,因而其所处的活动场域亦随时变化,而大清明之心如不动之明镜一般随着修身场域之变化始终能映鉴当时当下的情境,由是而调整此身之行动,使之与当下之情境合宜。这正是荀子修身之学的精义,亦是其礼义之道所得以可能的根基。圣人深入人情,以己度人,其大清明之心运用的极致就是对整个人类社会的收容和明澈通达,甚至天地万物之情实也在理论上可以通达,但在荀子看来那也只是为了建立人类秩序世界而所需了解的物类,根本上说秩序之建立仍是人类社会的秩序。当此大清明之心臻于极致,则其所通达的活动场域就是整个人世,而其所统摄、所成就的秩序就是人世秩序,也即所以立人道之极的礼义之道,这在荀子那里正是圣王的成就。因而荀子说:
圣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以说度功,以道观尽,古今一度也。(《非相》)
这里不断“度”的过程就是圣人以身行道、以身体道,进而不断地推展出人世秩序、礼义之道的过程,其成果就是成就人类社会共同的礼义秩序,即“人道之极”。
五、余论
综上,作为人世秩序的礼义之道,其得以确立的根基既不是内在于人心的道德直觉,也非纯粹思虑的构造物,也非一套外在的现成秩序等待人去发现。它既不在主体之内,也不在主体之外,它乃是人心以其虚壹而静的治心功夫收容并明达人先在地居持于其间的活动场域之中,这一先在的活动场域包括人群所构成的主体间的世界,以及人的身体、人的心、性、情欲及一切行动置于其间的事态与情境,并进而以此心之大公明察明照其中各类的固有情实,进而让身体的行动无不适宜于此活动场域,让此身得其当然之度、行其当行之道,这也正是义之所在。正是这样的修身秩序,才使得导欲、养情、称情立文得以可能,由是而成就出一套属人的秩序世界。可以说,这套秩序正是“合内外之道”的成果。
这样的礼义秩序实际包含两方面:一是心之大清明的明察明照之功和统摄力,二是此身当下置于其中的时与位。因此,作为礼义秩序的始基的身体秩序,实则是由大清明之心与此身所处的时与位内外交互作用下产生的秩序。进而言之,由于此身所处之时与位总是处在变动不居的变化中,故而对此身的秩序安排也就总是在不停地变化中。事实上,心之大清明并非一劳永逸的成果,心必须时时在身体变换的时与位中澄清自身,以此来观照此身当下的时与位、观照当下的修身场域。因而荀子的治心之道永远在身体的动态过程中进行,贯穿始终,其修身之学也充满了艰难,心的每一次澄清自身都是一次思虑的积累,此身在每一次修身场域中展现的秩序都是一次心之伪的成果,在反复积习之中才有可能成就此身时时处处皆得其宜的修身成果。因此,荀子的修身之学不同于孟子,在孟子那里,仁义礼智根于心,心本具道德善端,只待人在道德实践中扩而充之即可得其成就。孟子的修身功夫如同幼苗生长为大树的过程,如同源泉奔涌为江河的过程;而荀子的修身功夫则要在每一次时与位所展开的修身场域中澄清其心,安排其当下身体的秩序,在此过程中逐渐积累,以其积习之功成就修身秩序,因而荀子的修身功夫则如同架房建屋,需要在反复思虑和积累中用功,以得其成就。
参考文献:
[1]陈来.从思想世界到历史世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2]梁涛.荀子人性论辨正——论荀子的性恶、心善说[J].哲学研究,2015(5).
[3]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4]东方朔.心知与心虑——兼论荀子的道德主体与人的概念[J].台湾政治大学学报,2012(1).
[5]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6]廖名春.荀子新探[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7]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中图分类号: B22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030(2019)02-0039-09
收稿日期: 2018-09-10
作者简介: 李健芸(1994—),男,贵州安顺人,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
(责任编辑:范文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