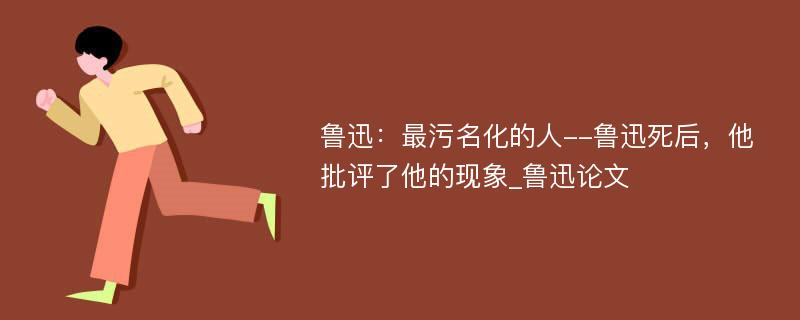
鲁迅:最受诬蔑的人——鲁迅去世后,非议鲁迅现象面面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的人论文,非议论文,最受论文,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10.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3X(2001)03-053-07
几十年来,人们非议、诬蔑鲁迅有些什么内容呢?从鲁迅不是革命家到鲁迅嫖妓,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若是单一地看,很多人也许觉得这些论客的论调不值得一驳,但倘若把各种观点摆在一起,那倒是一种十分有趣的现象,那就是,鲁迅一无是处,鲁迅什么也不是了。
从政治上看,他们认为鲁迅不是革命家。
不仅不是革命家,甚至是汉奸。郑学稼的基本论断是,鲁迅身为光复会会员,但在辛亥革命期间并无多少革命行为。接着,在辛亥革命以后,鲁迅却变成了北京军阀政府的一个小小官僚。他说,鲁迅从1912年到教育部任科长,直到1926年“三·一八”惨案以后离开,这期间的总统、执政总理走马灯似地换了不下十余人,洪宪皇帝袁世凯、贿选总统曹锟、官僚政客徐世昌、黎元洪及段祺瑞等等在任时,鲁迅都安然地做他的小京官,甚至还被提拔为“佥事”。只有张勋复辟时期,他曾愤而辞职。郑学稼阴险地说:“超过‘不惑’之年的周氏,还未曾成为一个革命者,只是北廷似苍蝇的官僚群中的一员。我们十分明白,在那样腐化的北京官场中,周树人氏能混了那么久的时间,是不容易的。他是否在那迎张送李似的生涯中,和一般官僚表演了奴颜婢膝的丑剧,只有他的同僚晓得。”郑学稼还认为,三十年代的鲁迅并没有真正从事过地下活动,如游行集会之类,因而在左派看来,他也不算是革命家。
鲁迅果真不是革命家吗?
我们看鲁迅的生平,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鲁迅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他“与旧礼教的卫道士‘国粹派’之流战,与北洋军阀刺刀庇荫下的‘正人君子’陈源之辈战,与诱劝学生进入研究室莫问国事的胡适之流战,与国民党御用文人如民族主义文学之派战”(何满子语),总之,他与专制的中国战斗,与愚昧的中国战斗,与黑暗的中国战斗……他的一生就是为了要争取一个自由的中国,一个文明的中国,一个崭新的中国,一个有声的中国,一个活的中国,一个人的中国。
思想革命算不算革命?在郑学稼看来,似乎是不算革命的。他理解的革命,大约就是上街游行,大约就是暴力行刺。鲁迅关在家中作文章,不管他作的是什么内容的文章,作者,非做也,故尔鲁迅是永远当不了革命家的。
可是,如果思想革命不算革命的话,那么,又怎么理解五四启蒙运动的革命意义呢?又怎么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大讨论的革命意义呢?《神童诗》云:“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文革”中常有人说:“拿起笔做刀枪”,总而言之,思想革命也是一种革命。既然思想革命也是一种革命,那么,从事思想革命的人自然也就是革命家了。
鲁迅在思想革命史上的意义,是有目共睹的。1918年鲁迅参加了《新青年》的工作。同年5月,他以“鲁迅”为笔名,发表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发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战斗呐喊,引起了强烈反响。《狂人日记》不仅是鲁迅第一篇用白话文写的小说,而且是中国新文学运动中的第一篇创作小说,是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个可贵的收获。同时,鲁迅把自己的思想发现借狂人的嘴说了出来:“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发现了封建制度和封建观念的“吃人”本质,同时,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唤,等等,这一切,不是具有非常深刻的革命意义吗?
不仅是《狂人日记》,鲁迅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具有不可磨灭的战斗精神,因而,也同样有着不可磨灭的革命意义。
从思想上看,他们认为鲁迅不是思想家。
李长之在《鲁迅批判》中说:
然而鲁迅不是思想家。因为他没有深邃的哲学脑筋,他所盘桓于心目中的,并没有幽远的问题。他似乎没有那样的趣味,以及那样的能力。
倘若以专门的学究气的思想论,他根底上,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常说不能确知道对不对,对于正路如何走,他也有些渺茫。
他的思想是一偏的,他往往只迸发他当前所要攻击的一方面,所以没有建设,即如对于国故的见解,便可算是一个例。[1]
李长之的结论是,鲁迅没有思想,因为他只有攻击的一方面,没有建设,所以只有零星的杂感而不成系统。
李长之关于鲁迅不是思想家的结论,实在是有悖起码的客观事实的,而且,这种见解在攻击鲁迅的阵营里,算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梁实秋就问过,鲁迅到底自己有什么见解呢?他说:“没有人能说清楚‘鲁迅思想’是什么……鲁迅思想,其实只是以尖酸刻薄的笔调表示他之‘不满于现状’的态度而已。而单单的‘不满于现状’却不能构成为一种思想。”施蛰存也说,鲁迅是没有自己思想的。他说:“鲁迅者,实在是一个思想家,独惜其思想尚未能成一体系耳。惟其思想未成一体系,故其杂感文集虽多,每集中所收文字,从全体看来,总有五角六张、驳杂不纯之病。使读者只看到他有许多批评斥责之对象,而到底不知他自己是怎样一副面目。”此外,也还有一些人所见略同。
我要说的是,有没有思想系统,最重要的是要看他的思想为现实社会解决了什么问题。什么叫思想家?怎样算有了思想体系?孔夫子有没有思想?毛泽东有没有思想?如果我们承认孔夫子和毛泽东都是思想家,那孔夫子的思想不是由许多对话组成的吗?毛泽东思想也不是由“概论”一类的书来完成的。换一句话说,毛泽东思想也是由一篇一篇的文章堆垒而成的。这些文章里面有的固然是论文,但也有杂文,也有书信,等等,等等。和孔夫子、毛泽东一样,鲁迅也有自己的思想及其体系。
针对李长之的论断,袁良骏说:
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列宁诚然是思想家,但是,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歌德、托尔斯泰难道就不是思想家吗?他们也许没有留下什么哲学讲义,但是,他们的伟大作品不都是他们伟大思想的结晶,含蕴着深刻的哲理吗?反言之,没有深刻的思想,他们能成就自己伟大的作品吗?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个伟大的作家首先就必须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鲁迅自然也不例外。姑不论鲁迅的数百万言的杂文,即使他的小说,也都是他的伟大革命思想的结晶。像他的代表作《阿Q正传》那样的作品,其思想难道还不够博大精深吗?难道我们能够离开鲁迅的创作实践去苛求什么“思想家所应有的清晰以及在理论上建设的能力’吗?实际上,鲁迅对中国历史的深刻的认识,对社会生活的熟悉洞察,对中国革命的精辟分析,几乎超过了中国当时所有的政治家、哲学家、历史家和社会学家。中国人民已经而且还将从他的遗产中撷取那些思想的精华,从而指导自己除旧布新的伟大斗争。怎么能否认鲁迅作为思想家的存在呢?如果鲁迅够不上思想家,那末,小自中国、大至世界,还有多少人可以够得上思想家呢?[2]
袁良骏认为,鲁迅是另一种类型的思想家,是以文学家的面目出现的类似于托尔斯泰的思想家。在这里,他突出了鲁迅对中国历史、中国社会的深刻洞察与全面认识。
在今天,接触过鲁迅所有作品的人,往往被鲁迅博大精深的思想魅力所深深地吸引。不少人甚至认为,鲁迅首先是思想的,其次才是文学的。现在、今后,大约不会有人再怀疑鲁迅作为伟大思想家的巨大存在了吧?
从私生活上看,鲁迅也被攻击他的人骂得一无是处。
先是有梅子以流氓的腔调对鲁迅进行恶意的攻击。读了以下这段文字,我们就不难看出梅子的堕落程度了。他写道:
……那时的鲁迅,是住在日本鬼子内山完造开设的内山书店楼上,在北四川路上可以看到的是白俄舞女的裸体跳舞,也可以看到“老伧”“瘪三”们在低低叫唤“阿要买春药”,在这样色情环境享受下的鲁迅,摇起笔杆,写几篇给黑暗的杂文,当然不是难事。如果说鲁迅的杂文好在泼辣俏皮,那么较之北四川路上“老伧”“瘪三”“娘姨”“大姐”们的当街大骂,打情骂俏,就要相形见绌,差写得多而且远了!
如此下作,这不是流氓腔调又是什么呢?梅子认为,在北四川路上可以看到白俄舞女的裸体跳舞,还有卖春药的之类(他怎么观察得这么仔细,莫非他经常前去窥视白俄舞女的精彩表演?),从而断定鲁迅是这种色情环境的享受者。这委实是上海滩上小瘪三的流氓腔调!并且,他以行家的口气,认为鲁迅的杂文较之他熟愁的“老伧”、“瘪三”、“娘姨”、“大姐”之类的当街大骂,打情骂俏,要相形见绌。这是自然的,欣赏惯了“娘姨”们的作态,鲁迅杂文与之对比,岂只是见绌不见绌的问题,简直是天上人间,有霄壤之别。梅子的逻辑是标准的流氓逻辑:内山书店在北四川路,鲁迅常去北四川路上的内山书店,北四川路上有妓院,所以鲁迅便是在享受“色情”。如此看来,经过北四川路的人,不都成嫖客了?我想,梅子是经常出入北四川路的,但是,我在没有根据之前是不会说他是老色鬼的。
再有就是苏雪林们的所谓鲁迅嫖妓说了。苏雪林对鲁迅的攻击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她说:
据最近的太阳报,有李石城所撰《鲁迅召妓引起轰动》一文,言有人在鲁迅日记发现一则小记事“某月某日,召妓发泄”,有个读者便惊叫起来,说道:“鲁迅原来是这样下流!看他外表像孔老二,居然也搞起玩妓女的事。”又有一个读者说:“鲁迅不是一个完人,因为他生活作风不正派。”[3]
李石城何许人也,不得而知。他依据“有人”的“发现”,撰文攻击鲁迅。苏雪林又拾其牙慧广为流布,用心更其阴险。对此,李允经对李石城和苏雪林进行了有力的批驳:
鲁迅日记中是否有过关于他和妓女的交往记载呢?有的。1932年2月16日,记有“往青莲阁饮茗,邀一妓略来坐,与以一元”,这原来是对于妓女的同情,可是一到李石城、苏雪林笔下,便被篡改为“召妓发泄”。莫非除此而外,李、苏等人还会在鲁迅日记中别有“发现”吗?当然决不可能。那么为什么要篡改呢?这除了粗心、无知而外,就只能是居心叵测,恶意中伤了。
同年,鲁迅还作有《所闻》一诗。诗中对妓女的同情,虽不能断言是来自2月16日的所见所闻,但也不能说绝无关连。诗中写道:“华灯照宴敞豪门,娇女严装侍玉樽。忽忆情亲焦土下,详看罗袜掩啼痕。”那时,适值上海“一·二八”战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狂轰滥炸,一些亲人死于战乱,骤然沦为孤儿的少女,不免落入酒肆,卖唱为生。在这种情况下,鲁迅邀来一谈,“与以一元”这难道就是嫖妓吗?按照这种逻辑,岂不是只要同妓女见过面,说过话的男人就都成了嫖客了吗?遗憾的是,这种荒唐的逻辑,我实在不敢苟同。我想李石城也未必就不曾与妓女见过面,说过话,久居台湾的苏雪林女士也未必就没有同嫖客见过面,说过话,但我是决不会因此就断言他们是嫖客或妓女的。[4]
苏雪林太过性急,捡到一根稻草就当作大炮,她甚至没有耐心去查一查鲁迅日记,想出鲁迅的丑,结果是谁出丑呢?我相信读者自有公论。
我想,若是用日常生活的语言来表述,我要说,鲁迅是被鬼缠上了。鲁迅的每一句话都要放到显微镜下,被放大无数倍,从中挑剔出可以攻击的内容。攻击鲁迅成了苏雪林以及苏雪林们一生生活的内容。文学史上,有劣迹有污点的是大有人在的,周作人、张资平当了汉奸,劣迹昭著,苏雪林们不吭声,现在倒有人吹捧他们的作品如何之好;郁达夫嫖了几回妓,也少有人非议,我看到有的文章甚至还把这加以渲染,说什么是真名士自风流。可是,鲁迅既不是汉奸又不曾嫖妓,但他们却非要给鲁迅以恶名不可。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呢?
鲁迅去世以后,非议、诬蔑鲁迅的,有几种情况呢?我尝试着做了归纳。不知道能不能回答鲁迅之所以遭非议与受诬蔑的原因。
在中国这样一个讲政治的国度里,我们不能不首先从政治上看问题。
说起侧重以政治的眼光来看鲁迅这一点,我以为,当首推苏雪林。苏雪林的骂鲁迅,出于文学的考虑要少,出于政治的考虑却是最主要的。鲁迅去世,与万民同悼相对立,苏雪林不择手段地发起对鲁迅的攻击。这主要表现在她1936年11月12日写的那封《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的公开信。信中称,“鲁迅病态心理将于青年心灵发生不良之影响也”,“鲁迅矛盾之人格不足为国人法也”,“左派利用鲁迅为偶像,恣意宣传,将为党国之大患也”……同时,她还致函胡适,谈了与“公开信”相似的内容。针对“新文化产业,被左派巧取豪夺”,“今日之域中,已成为‘普罗文化’之天下”的情况,也针对“鲁迅死后,左派利用之为偶像,极力宣传,准备将这个左翼巨头的印象,深深打入青年脑筋,刺激国人对共产主义之注意,以为酝酿反动势力之地”的情况,请求蔡元培、胡适站出来做所谓“取缔‘鲁迅宗教’”的工作。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苏雪林对鲁迅进行人身攻击,诽谤和谩骂。她骂鲁迅“褊狭阴险,多疑善妒”,“假左派”,“是一个刻毒残酷的刀笔吏,阴险无比,人格卑污又无耻的小人”,“睚眦必报,不近人情”,“色厉内荏,无廉无耻”,“好诌成癖”,“劣迹多端”……诬蔑鲁迅是“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她攻击鲁迅的杂文“文笔尖酸刻薄,无以伦比”,“含血喷人,无所不用其极”。更有甚者,苏雪林无中生有地诬蔑鲁迅“表面上敝衣破履,充分平民化”,其实“腰缠万贯,家私累累”。
苏雪林这样的一位作家、学者,她不可能不知道鲁迅的价值和意义。她宁可痛苦地放弃了自己曾经对鲁迅作品的偏爱,为了服从政治的需要,而不惜让自己成为一个泼妇。苏雪林如此赤膊上阵,就像一头忠实于主子的猎犬,在让人感到一定程度的感动的同时,我更多的是感叹政治竟是如此无情面地把一个有活生生思想的人异化为一种工具,一个传声筒。苏雪林不是搞政治的,却有着这么高的政治“觉悟”,这是让我莫名惊诧,又让我很是敬佩的。
第二种情况是审美情趣和价值观念的不同,也可以说是世界观的不同。
这一点,我要以闻一多对鲁迅的态度来说明问题。闻一多和鲁迅本不是一种类型的人,他们所经历的历程是不一样的。鲁迅早在留学日本时期,为了开启民智,弃医从文,决计要以文学来改变“愚弱”国民的精神。《新青年》时代,鲁迅一开始文学创作,就以呐喊者的姿态出现在中国文坛上。他的《狂人日记》,在揭露中国封建观念吃人的同时,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喊,它是黑暗中国迎来光明中国的第一声破晓的鸡啼,它是专制中国走向自由中国的第一声战斗的号角。此后,鲁迅的一切文字,都在抨击传统中国的落后、愚昧和虚伪,鲁迅一生都在批判旧中国。鲁迅是作家,是学者,是思想家,但他是战斗的作家,战斗的学者,战斗的思想家,鲁迅首先是一个不倦的战士,他一直战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闻一多则不同,他先是一个唯美的诗人,接着是一个纯粹的学者,最后,由于现实逼迫,他才成了一个民主斗士。我理解,闻一多是这样的人,他做诗人的时候心无外诱,认真地做着诗人;他做学者的时候还是心无外诱,认真地做着学者……因此,他写诗的时期,基本上不搞研究;他搞研究的时期,也就不写诗了。偌大中国,摆不下闻一多的一张书桌,他想做诗人、学者而不可得,他别无选择,他只能做战士了——作为战士的闻一多,依然是心无外诱,执著而义无返顾,甚至搭上了性命也在所不惜。
因此,1944年10月19日,闻一多在昆明文艺界举办的鲁迅逝世八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讲,回顾了他在北平时期对鲁迅的看法,认为当年他是“自命清高的人”,他说:“从前我们住在北平,我们有一些自称‘京派’的学者先生,看不起鲁迅,说他是‘海派’。就是没有跟着骂的人,反正也是不把‘海派’放在眼上的。”[5]诗人时期和学者时期的闻一多是不把鲁迅放在眼里或并不理解鲁迅的存在对于中国的意义的。
不仅如此,我还以为,若不是环境的变化引起闻一多思想上的变化,闻一多甚至可能终生都会对鲁迅怀着偏见和误解。鲁迅逝世的时候,清华大学文学研究会于当年10月24日举行了一次追悼会,会上,闻一多发表了演讲。在这样严肃的场合,闻一多仍然按捺不住地说出了他对鲁迅的带有新月色彩的偏见。他说:“鲁迅因为个性的关系,仇人很多,和他认识的人,除了那些喜爱他那种性情的人以外,十有八九都是他的仇人。”[6]
我以为,闻一多关于鲁迅“个性问题”的见解,客观上伤害了鲁迅,是对鲁迅的误解和偏见。
闻一多当时之所以对鲁迅有如此的偏见和误解,与他正专心致志地做他的教授是不无关系的,与他当时所处的环境是不无关系的。1936年前后,闻一多正沉下心研究先秦汉魏六朝诗,同时还在研究中国古代神话以及唐诗等。在优美的环境中做着关于远古的学问,确实是很难理解鲁迅以及鲁迅战斗的意义的。后来,环境变了,闻一多也变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闻一多和学生一起从北平步行到了重庆。时局动荡,生活艰苦。一个强烈的爱国者忍受着剧烈的亡国之痛,在抗战期间坚持着自己诚实而又辛勤的教育工作。但腐败的官僚却乘机发国难财,使人民原本痛苦的生活愈加痛苦。1944和1945两年,是昆明民主运动浪潮高涨的年代。中国民主同盟配合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大专院校的数千名进步师生,配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昆明分会”、“民主青年同盟”和“云南省妇女联谊会”等进步的群众团体,举行过多次的群众大会、演讲会、报告会、纪念会和文艺晚会。在这些会上,借纪念和文艺活动之名,进行反内战、反专制的宣传。在这些活动中,最后一位发言的总是闻一多。时局的恶化,不仅使闻一多无法静心于学问,甚至影响了他的日常生活。闻一多的收入,已难以维持自己的家庭开支,只好业余给人刻图章赚些钱勉强维持生计。国难家窘,他激动了,他愤怒了,他走出了书斋,他扔掉了他用惯了的笔,他投入了现实的斗争,他成了成主斗士!因为这一切,闻一多对鲁迅的斗争精神和革命行动有了新的认识,新的理解。闻一多是这样表述的:
鲁迅生前所处的环境异常危险,他是一个被“通缉”的“罪犯”!但是他无所畏惧,本着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精神,他勇敢、坚决地做他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在文化战线上打着大旗冲锋陷阵,难怪有的人为什么那么恨他!
鲁迅在日本留学,住在十里洋场的上海,他和洋人,和大官打过不少交道。但他对帝国主义,对买办大亨,对当权人物,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宁可流亡受苦,也不妥协。鲁迅之所以伟大,之所以能写出那么多伟大的作品,和他这种高尚的人格是分不开的,学习鲁迅,我想先得学习他这种高尚的人格。
有人不喜欢鲁迅,也不让别人喜欢。因为嫌他说话讨厌,所以不准提到鲁迅的名字。也有人不喜欢鲁迅,倒愿意常常提到鲁迅的名字,是为了骂骂鲁迅。因为,据说当时一旦鲁迅回骂就可以出名。现在,也可以对某些人表明自己的“忠诚”。前者可谓之反动,后者只好叫做无耻了。其实,反动和无耻本来就是分不开的。[7]
这里,鲁迅的斗争精神,鲁迅的“骂人”,已不再是与人合得来合不来的问题了,已不再十之八九是“仇人”的问题了,闻一多认识到了鲁迅是旧的时代的叛逆者,是在文化战线上“打着大旗冲锋陷阵”的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的战士。鲁迅的斗争精神是他人格高尚的表现。不仅如此,闻一多还对不喜欢鲁迅的人作了具体的分析与批判,这足以说明,闻一多的认识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而绝不是一时冲动的信口开河。
闻一多毕竟是一个真诚的人,是一个无畏的人,他在直面自己的同时,勇敢地向鲁迅忏悔。他在谈了不喜欢鲁迅的两种人以后,说除了这以外,“也还有一种自命清高的人,就像我自己这样的一批人”,闻一多为他当年的看不起鲁迅而向鲁迅忏悔。闻一多说:
现在我向鲁迅忏悔:鲁迅对,我们错了!当鲁迅受苦受害的时候,我们都正在享福,当时我们如果都有鲁迅那样的骨头,哪怕只有一点,中国也不至于这样了。[8]
接着,闻一多提出不能再当“帮闲帮凶”,要向鲁迅学习,学习鲁迅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这正是纪念鲁迅的意义所在:
骂过鲁迅或者看不起鲁迅的人,应该好好想想,我们自命清高,实际上是做了帮闲帮凶!如今,把国家弄到这步田地,实在感到痛心!现在,不是又有人在说什么闻某某在搞政治了,在和搞政治的人来往啦,以为这样就能把人吓住,不敢搞了,不敢来往了。可是时代不同了,我们有了鲁迅这样的好榜样,还怕什么?纪念鲁迅,我想应该正是这样。[9]
多几个鲁迅,就不会“把国家弄到这步田地”,中国才有救,这就是闻一多的结论。不久,闻一多为了实践他这用生命历程体验出来的结论,付出了宝贵的生命。闻一多从书斋走向了人生、社会,从与鲁迅价值观的不同,又回归到了鲁迅。
第三种情况是所谓还原一个真实的鲁迅。
周作人与鲁迅是同胞兄弟,他眼里更多的是平常的鲁迅,这似乎也可以理解。鲁迅死了几十年,远了,更远了,这期间,随着人们对他的理解的加深,鲁迅的形象大了,更大了,鲁迅的伟大已经不成问题。可是,鲁迅在周作人心目中的形象却是不变的。
周作人在六十年代初期给香港的鲍耀明的信中,对鲁迅的座像,谈了他的看法:
现在人人捧鲁迅,在上海墓上新立造像,——我只在照相上看见,是在高高的台上,一人坐椅上,虽是尊崇他,其实也是在挖苦他的一个讽刺画,即是他生前所谓思想的权威的纸糊高冠是也,恐九泉有知不免要苦笑的吧。要恭维人不过火,即不至于献丑。[10]
周作人在给曹聚仁的信中,亦有类似观点。他说:
……死后随人摆布,说是纪念其实有些实是戏弄。我从照片看见上海的坟头所设塑像,那实在可以算作最大的侮辱,高坐在椅上的人岂非即是头戴纸冠之形象乎?假使陈西滢辈画这样一张相,作为讽刺,很适当了。[11]
上海的鲁迅座像也不怎么高,从美学的角度看,正好。周作人的意思是太高了,有点儿神化鲁迅。一座雕塑,不抬到一定的高度,行吗?我们假设一座雕塑摆在地上,感觉会是怎样?那是不可思议的。
不神化鲁迅,是周作人非议鲁迅雕塑的理由。可是,鲁迅是伟人,是不是搞了伟人的雕塑就是神化了伟人呢?伟人雕塑既是对伟人一生成就的肯定,也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物化;伟人雕塑还是现代城市的一种装饰、一个景观。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伟人雕塑,丹麦有安徒生的,英国有莎士比亚的。俄国就更多了,有普希金的,托尔斯泰的,还有高尔基的,等等。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伟人,为自己的伟人树碑立传,世界皆然。鲁迅是近现代史上的伟大人物,他还是中国现代最伟大的文学家。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在他的坟上竖立一座雕塑,有什么可值得非议的?中国人为鲁迅竖立了雕像,怎么注定就是神化鲁迅呢?死后的鲁迅怎么就是“随人摆布”和“戏弄”呢?至于“最大的侮辱”,更是从何谈起!周作人说:“世无圣人,所以人总难免有缺点。”有缺点的伟人也终究是伟人,我们总不能以任何人都有“缺点”为名,从而否认了伟大的存在吧!
第四种情况是某些人为了替被鲁迅骂过的人鸣不平,扬此而不惜抑彼,他们客观上伤害了鲁迅。
1988年1月15日上海《联合时报》发表了记者黄平对新闻界知名人士、全国政协委员徐铸成的采访记,徐铸成声称“以鲁迅的只字片语给人定论是‘凡是论’的翻版”。徐铸成为林语堂鸣不平,说:“这位成就显著的爱国作家,因为早年与鲁迅有过论战,就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大陆出版的文学史上没有地位,青年人不知其人其事。”徐铸成认为,应该重新认识、重新评价林语堂,不能以三十多年前鲁迅的一句“西崽”来概括林语堂的一生。林语堂并不是什么“西崽”,按其生平,也可以说是没有一点媚骨的文学大师。徐铸成还对厦门大学建有鲁迅纪念馆,感到很奇怪。当年是林语堂建议厦大请鲁迅来校讲学的,鲁迅在该校任教三个月,而林语堂是当年陈嘉庚创办该校的得力助手,又是厦大国学研究室创办人和奠基人。在该校任教长达四年,却没有任何纪念物,徐铸成认为这很不公道。
我觉得,徐铸成对鲁迅与林语堂的关系问题,是感觉多于研究,印象代替了理性。比如,说鲁迅“骂”林语堂的所谓“西崽”问题。倘若我们细究起来,首先骂人“西崽”的,不是鲁迅,而是林语堂。他在《人间世》第二十八期(1935年5月)发表《今文八弊》,攻击别人译介波兰、捷克等被压迫民族文学,以及在文章中吸收外国语法,是“事人以颜色”,“其弊在奴”,“谈文学虽不足,当西崽颇有才”。还说:“有食洋不化之洋场孽少,也必有自欺欺人之迂腐故老。”我们知道,介绍波兰等被压迫民族的文学,始于鲁迅的《摩罗诗力说》,五四以后文学研究会也曾大力提倡。那不是“事人以颜色”,而是由于中国人同样处于被压迫的境地,译介这类作品易于心心相印之故。林语堂的肆意攻击,不能不激起鲁迅的反击,鲁迅发表了《“题未定”草(二)》予以有力的批驳。鲁迅说:“要研究西崽,只能用自己做标本,虽不过‘颇’,也够合用了。”林语堂从小吮吸着洋人和教会的乳汁,是个“西化”程度很深的知识分子,在处理中西文化、华人与洋人的关系上也有不少可议之处。鲁迅指出,他所懂得的大抵是“英文”,这是他们的吃饭家伙,专事服侍洋东家的。鲁迅说:“西崽之可厌不在他的职业,而在他的‘西崽相’。这里之所谓‘相’,非说相貌,乃是‘诚于中而形于外’的,包若‘形式’和内容而言。这‘相’,是觉得洋人势力,高于群华人,自己懂洋话,近洋人,所以也高于群华人;但自己又系出黄帝,有古文明,深通华情,胜洋鬼子,所以也胜于势力高于群华人的洋人,因此也更胜于还在洋人之下的群华人。”最后,鲁迅归纳道:“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这就是现在洋场上的‘西崽相’。”林语堂骂别人“西崽”,因为品题不切,所以粘不到别人身上;鲁迅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稍稍勾勒一下“西崽相”,他可就难以脱掉干系。这是一场遭遇战。林语堂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只能埋怨他自己,并非鲁迅存心给他“戴帽子”。
厦门大学有鲁迅纪念馆而没有林语堂的,这有什么可值得奇怪的呢?徐铸成说鲁迅在厦大只有三个月时间,而林语堂则呆了四年(林语堂1926年下半年抵厦,1927年春离开,在厦门大学也只呆了半年多。1927年离开厦大后,他到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任秘书,7月去上海,开始专事著述。可以说林语堂与鲁迅是前后脚离开厦大的。我不知道“四年”之说从何而来)。为谁建纪念馆是看谁对中国文化有更大的贡献,看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以及谁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高、对学生更有教育意义,等等,而不是呆的时间之长短。厦大为鲁迅建纪念馆是没有任何可值得非议的,至于给不给林语堂建纪念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徐铸成说,鲁迅是林语堂向校方建议从而请来教学的。他是不是要表述这样的意思:鲁迅还是林语堂请来的,林语堂没有纪念馆鲁迅却有,这不公平。倘若真是这样想,那这种思维方式就太成问题了。林语堂是林文庆请来的,假如要建纪念馆的话,是先建林语堂的还是先建林文庆的?徐铸成还认为“林语堂是当年陈嘉庚创办该校的得力助手,又是厦大国学研究室创办人和奠基人”,如果因为行政上的贡献,从而要给林语堂建纪念馆的话,徐铸成的话也未必确切。据我所知,“当年陈嘉庚创办该校的得力助手”是林文庆,而不是林语堂,若讲厦大事务谁的贡献大的话,那首要人物便是林文庆。林文庆从1921年6月至1937年6月任厦门大学校长,主持校务长达十六年之久。厦大的群贤楼等“八楼”是他主持建设的;厦大的生物学院、化学院、煤气厂、电灯厂、医院以及二十余座师生住宅等等,都是在他主持下兴建、创办的,要建也得建林文庆的纪念馆,而不是林语堂的。
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的生平业绩时说:
凡是为某种事业进行斗争的人,都不可能不树立自己的敌人,因此他也有许多敌人。在他的大部分政治生涯中,他在欧洲是一个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12]
是的,鲁迅一生,也是为着正义事业进行不倦斗争的一生,因此,他不可避免地成了现代中国最受诬蔑的人。虽然,“敌人”的概念在这里未必都是阶级或政治的对立,它更多的是指价值观念的不同与思想的冲突。
收稿日期:2001-04-23
标签:鲁迅论文; 林语堂论文; 闻一多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文学论文; 周氏兄弟论文; 读书论文; 狂人日记论文; 周作人论文; 徐铸成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