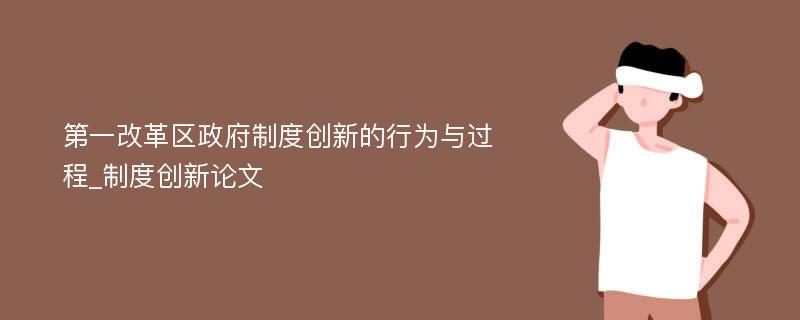
先行改革地区的政府制度创新行为与过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制度创新论文,过程论文,地区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区域性改革试验作为我国渐进改革的成功经验之一已得到了公认。解释这项区域性改革试验离不开对作为先行改革者的地方政府行为与过程研究。有关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两种观点上,一种是把改革以来地方政府的创新行为等同于商业组织中的企业家行为。Andrew G.Walder(1995)和Jean Oi(1992)对此做了较多的阐述。在他们看来,放权让利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使得“地方政府具有公司组织的特征,官员们完全像一个董事会人员那样活动”。(注:Oi,Jean,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World Politics,vol,45,no.1(October,1992),pp99-126.)更直接地说,地方政府就是厂商,地方政府官员就是企业经理。按照这种说法,探索地方政府在原有体制与实践发展发生冲突条件下,寻求制度创新的特殊性就被企业家的一般创新机制所取代了。另一种看法是借用诺斯和戴维斯(North、Davis,1991)的初级与次级行动集团理论来解释我国经济转轨中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过程(杨瑞龙,1998)。把创新行动者看成是初级行动集团,把上级部门看成是次级行动团体,通过两者的合作互动推进制度创新。问题在于,对于先行改革者来说,上级部门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可能成为诺斯所说的次级行动团体?事实上,20多年来率先突破体制约束的一些地区的变通做法已为观察先行改革者的创新策略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比如,“少说多做”;以强调试验地区特殊性的“用足政策”;打政策的“擦边球”;利用政策没有明令禁止的空间,自主制定变通政策等(孙立平,2002)。这些多样化的变通实践难以用上述的两种理论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为此,本文以环境决定策略,策略决定过程为理论框架,提出了不同于上述两种观点的一种新解释,即在我国经济转轨时期形成的制度激励与风险并存的环境要求先行改革者比一般的企业家更关注创新策略下,先行改革者如何通过信息披露实现创新策略安排,这种安排如何影响创新过程的理论观点。
二、制度激励、风险与策略需求
本文的研究范围限定在地市、县和镇等三层次率先突破体制限制的地方政府的创新行为,把这些“具有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称之为基层组织制度的先行改革者。拉巴龙巴拉(Joseph Lapalombara,2001)认为,公共组织及成员的工作是严格按照一套规范的制度化程序进行操作的,这种公共组织的制度化联系要比私营企业紧密得多,因而,公共组织的变革难度也比私有组织大得多。这就决定了公共组织的行为导向的准则是保守、不冒险。这种“组织体系内各层次政府官员的保守作风”构成了马克斯·韦伯提到的法理权力体系下的一个固有特征。虽然不排除在任何制度环境下都会出现各级政府的主要领导者因个人禀赋与能力而发生个别的创新行为,但是,从本质上说,他们是缺乏制度创新动机的。如果制度创新行为能在他们中间较多地发生,这一定与制度环境中的激励强化相关。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制度环境发生了有利于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变化。这表现在:(1)我国立法体制的调整及相应的意识形态环境的变化强化了地方政府从事创新活动的激励。将我国由一级立法体制变为两级立法体制的《地方组织法》为地方政府进行制度创新提供了直接的法律依据;(注:该法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们的常务委员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以下放行政管理自主权为主的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的调整极大地扩大了地方政府支配资源的权力与能力;以“无功就是过”取代“无过就是功”的道德评价标准等意识形态上的变更为地方政府大胆创新创造了有利的理论与思想氛围。(2)经济体制的渐进转轨扩大了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空间。面对不确定的渐进转轨,“摸着石头过河”被认为是一项有效的过渡安排。在这种过渡中,与其进行全局性摸索,不如先由个别地区进行试验。当这种试验取得了成效后,再由中央政府把这种试验中具有可行性和普遍性的经验推广到全国范围。这种通过地区试验来降低全局性的不确定性的转轨方式创造了地方政府进行制度创新的机会。(3)自主权下放和管理责任制的推行增大了地方政府创新试验的动力和压力。随着行政管理自主权的下放,上级部门改变了考核下级部门的管理方法,即由规则管理变为目标管理,干部责任制就是因应目标为本的管理方式而制定的(金山爱,2000)。这个目标管理的关键不在于上级部门制定的各项计划指标,而是本地财政收益最大化和地区间在财政收益增长指标上的竞争压力。只有本地财政收益增长了,才能保障地方政府各项职能的开展,如提供社会福利、扶持教育发展以及支援农业等,才能在各地区间业绩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然而,率先改革是有风险的。风险可分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引火烧身”。伯恩斯(Tom.R.Burns,2000)在分析制度创新者与熊彼特所论述的厂商型企业家之间的差异时指出,制度创新者以现行的“游戏规则”作为调整和更替对象,这不可避免地引起利益群体的分配格局与秩序的变化,从而“引发利益集团之间的直接冲突”。(注:伯恩斯(Tom.R.Burns)《结构主义的视野:经济与社会的变迁》,周长城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91页。)当对决策产生主导影响的利益群体收益因规则更替而受到影响时,一些从理论上说有利于整个社会福利增加的创新方案就难以推进,甚至会半途夭折。在制度创新无法实现预期收益的情况下,先行改革者不仅个人福利会受到损害,甚至晋升仕途和职业生涯都会受到影响。二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虽然一些改革试验通过上级部门的有效干预能够进行下去,并获得了新制度安排的净收益增长,但是,先行改革者却未必分享到其中的收益。因为维护原有制度安排的利益群体在无法阻止新制度安排的情况下,往往把冲突的焦点集中到这些改革者身上,如向上级部门投诉、告状、写匿名信等。上级部门为保证新制度安排的整体推进,不得不采取一些缓和冲突的妥协办法,如调离岗位等。其结果是,先行改革者付出了创新试验的各种努力与代价,而后来者分享创新所带来的预期收益。三是“率先创新,回报减少”。先行者形成的新制度方案凝结着其知识的长期积累和投入,但是,这种投入和努力是无法像技术产品取得专利一样得到法律保护的,只能通过新制度安排的实施得到实现。而新制度安排的试验往往会引起不同反应。如果实施不成功,其他群体会另辟蹊径从事创新活动,这样,先行改革者以自己的试验失败支付了其他群体创新成功的费用。如果实施成功,其他群体会免费模仿。其结果,就形成了林毅夫所说的“创新者的报酬将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报酬”。(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自R.科斯、A.阿尔钦和D.诺思等编著的《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刘守英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91页。)可见,由于存在着这些风险,先行改革者在动员和组织本地区制度创新时,不得不考虑风险规避的问题。
三、披露能力、动机与策略安排
先行改革者对创新过程中的策略安排受到披露能力与动机的影响。披露能力是先行改革者将创新信息传播出去的能力,主要取决于把握信息扩散的渠道组织和对创新活动因果关系以及成本与收益的认知。在信息渠道一定条件下,先行改革者对创新活动的认知程度对信息传播程度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而这种认知是一个由模糊到清晰、由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的过程。在创新行为初期,受到知识结构与有限理性的制约,先行改革者对创新概念、方案与结果的认知往往是有限的、模糊的。(注:Cohen,N.D and Bacdayan,P.(1994),Organizational Routines Are Stored as Procedural Memory:Evidence From a Laboratory Study,Organization Science,5:554-68.)对于外界来说,这种知识也具有明显的隐蔽性和干中学的特征,其结果,把在这种认知能力开发出来的创新信息从一个单位向另一个单位的传递就变得很困难和高成本(Teece,1982)。青木昌彦认为,“这种知识即使被外界知道了,也不太容易得到正确理解,因而对大多数参与人的预期和决策规则不发生影响”。(注:青木昌彦著《比较制度分析》,周黎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第237页。)可见,这个时期的创新信息基本上是一种不具备可传播的知识。本文把这种情况称为弱披露能力。随着创新行动的开展,先行改革者对制度创新中不确定因素的认识和把握能力逐步提高,不仅有能力对创新行动中暴露出来的各种矛盾与冲突进行相机调整,从而修正创新初期制定的方案,而且对实践已证明为行之有效的创新做法加以理论加工,并逐步将一种复杂的做法概括为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在这种情况下,概念就像数据与价格一样,其传播成本会大幅度地下降,从而这种概念性的认知会很容易地得到推广与扩展。这种情况可以看成是强披露能力。比如,广东省顺德市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率先实行产权制度创新初期,一些诸如允许经营者持股、职工获得较高的工龄补贴后可以提前离岗的改制做法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当实践证明了这些做法的有效性后,顺德人才逐步地将这些做法清晰地概括为“贴身经营”、“买断工龄”等理论概念。这个事实至少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先行改革者的披露能力是在创新实践中通过积累性学习而由弱变强的过程。
披露动机是先行改革者为实现个人和组织收益最大化而对创新信息传播方式做出安排与控制的打算。对于先行改革者来说,任何一个创新方案从意识的萌发到清晰理念的形成,再到对创新做法的提炼与概括,每个环节都凝结着知识积累、信息收集与加工和协调沟通等方面投入。在这种投入形成了一定的制度创新产品后,如变通性做法与经验等,如果它能通过契约、购买和出售等市场交易方式获取收益,如以技术专利形式进行权利的转让等,那么,先行改革者的投入可以得到相应的补偿。但是,这种制度创新产品是无法通过交换获取收益的,价格机制对这种制度创新产品转让的失效,使得先行改革者不得不寻找其它的方式从已开发的制度创新产品中获得收益,这就是通过对信息传播数量、对象与方式的控制,实现对创新产品的自我保护。因为一旦已开发出来的创新产品信息被其他的竞争对手所了解,他们就可以不用花费先行改革者的巨大投入,通过模仿很容易地推进制度创新过程,并在这个过程中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加以改良和完善,从而领先于先行改革者的创新思路。如果在这种创新尚未形成比较清晰的制度性产品时,创新信息被泄露给外界,那么,由不同利益集团构成的外界组织对创新方案所带来的预期不确定性因素会形成各种反应,诸如赞成、反对、建议和疑虑等,这都需要先行改革者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做出回应。当然,不能排除通过回应有利于清理创新思路,完善改制方案的作用,但是,更多的应对能力要放在对外界的解释、说服和沟通等方面的工作上,这不仅分散了先行改革者投入创新的精力,而且也增大了进一步创新的成本与难度。因此,无论从已成型的制度创新产品角度看,还是从尚未成型的创新过程看,先行改革者都会把控制创新信息的传播与扩散作为一种主要的策略手段,通过延长信息保密时间,尽可能长时间地给先行改革者带来制度创新所产生的“垄断租金”。
然而,控制创新信息的传播与扩散并不等于先行改革者个人在全封闭状态下创新,而是根据披露能力的增强程度和信息披露对创新活动的影响程度逐步调整信息传递范围的。可控的信息传递范围是通过选择披露对象来实现的。从创新结果来看,尽管作为披露对象的组织内成员、上级部门和公众组织最终可能都会知道先行改革者的创新方案与具体做法,但是,从创新过程来看,在什么条件下让哪一个组织知道和了解创新信息,这对降低制度创新过程的风险和减少不确定性因素将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正由于此,先行改革者将围绕着信息传递的对象选择、披露顺序与时机来制定策略。
首要的策略是把多个组织参与的博弈变为单一组织参与的博弈,以降低协调成本,增加支持的可能性。在组织内成员、上级部门和公众组织中,哪一个组织参与创新过程的博弈,这主要取决于先行改革者对该组织的信息披露。假定把信息披露看成是三类组织进入创新过程博弈的唯一通道,那么,先行改革者将信息披露给谁,谁就进入创新活动的博弈过程。如果不对该组织披露信息,它就无法进入博弈过程。如果对三个组织同时披露信息,那么,他们就同时进入博弈过程。这个博弈过程是,在先行改革者把信息披露给某一个组织后,该组织会根据自己的认知和利益做出不同的反应,如赞成、反对或怀疑等。先行改革者要争取该组织对创新活动的支持,除了赞成的情况以外,其余的两种情况都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与智慧进行沟通、解释和说服工作,以促使该组织支持创新活动,这就需要支付协调成本。对于先行改革者来说,如果应对一个组织所支付的协调成本是既定的,那么,同时面对多个组织进行解释和说服的难度就大得多,所需要的协调成本也会大幅度增加,这就是诺斯论述的随着参与人数量的减少,合作博弈的可能性增加的原因所在。诺斯指出,“在博弈中,当参与人对其他参与人的数量较少时,达到合作的结果是最有可能的。当参与人对其他参与人过去的行为不了解,并且参与人数量较多时,合作则很难达到”。(注:(美)道格拉斯·诺斯:《新制度经济学及其发展》,《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年第5期。)特别是在创新初期先行改革者处于弱披露能力条件下,该组织采取支持态度的概率往往会比反对和怀疑要小。因此,先行改革者与其同时将信息披露给多个组织,不如先披露给某一个组织,从而利用有限的协调能力,增大与单一组织合作博弈的机会。通过“分而告之”策略,分期分批地实现与多个组织合作博弈的目标。
其次是根据披露能力与创新活动的需要,确定信息披露的先后顺序,以降低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面对三个组织,先行改革者首选的披露对象是组织内成员。因为组织内成员作为新制度安排的直接行动者和试验者,新制度方案若得不到他们的充分理解和支持,就无法变为创新行动。在这种条件下,先行改革者无论花费多少精力与智慧,都要说服组织内成员,以保持与自己在创新取向上的一致性。在先行改革者处于弱披露能力条件下,先行改革者往往不会把上级部门作为信息披露的对象,这是因为在制度创新的预期收益尚未得到实践验证条件下,上级部门是不会轻易表态的。甚至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基层组织的创新意见持否定态度。据一项调查显示,上级部门对基层提出的创新意见在最初持否定态度的情况占80%。(注:张金昌等著《21世纪的企业治理结构与组织变革》,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26页。)其结果,与其遭到上级部门否定后公开对着干,不如暂时不披露真实的信息给上级部门暗着干。同样的道理,与弱披露能力相适应的有限解释力、保护动机以及既要推进创新又要应付公众反应的较高机会成本,使得先行改革者更不愿意对公众组织泄露创新信息,一方面公开披露创新信息,这等于将尚未成熟的创新打算告诉了竞争对手,其结果,会增加对创新带来的“垄断租金”的争夺。另一方面要投入较大力量应付公众机构的各种不理解、怀疑创新活动的反应,以降低来自外部舆论的阻力,但是,这会分散先行改革者的精力,使其无暇顾及创新活动中需要解决的各种问题。一些地区在创新初期采取“只做不说”的策略来推进局部性变革就是一个佐证。
随着创新试验的推进,一方面先行改革者对创新活动的因果联系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和解释力,说服上级部门支持创新活动的可能性增大了。另一方面自发创新需求与初始的制度供给不一致的矛盾会越来越多,靠先行改革者协调创新地区与整个制度结构之间的矛盾也变得越来越突出,这就越来越需要借助于上级部门的力量来增加协调能力,从而分担创新风险。特别是在作为基层组织主要领导的先行改革者基本上由上级部门任命和委派的体制下,先行改革者重视上级部门对创新业绩的评价往往超过了本地选民关注创新结果的评价。因此,在创新行为发生后,还对上级部门隐藏信息,即使制度创新取得了一定进展,先行改革者也往往承担“目无组织与领导”的责任(Levin,M.and Sanger,M.B,1994)。在这种条件下,创新信息的披露对象就由组织内成员扩展到了上级部门。但是,上级部门了解了先行改革者的创新试验后,也不愿意直接公诸于众。因为创新活动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即使看清楚了创新取向,也不一定完全把握创新过程中需要支付的成本与代价,进而无法预测创新成本与收益。特别是作为地方政府的上级部门都不愿意轻易地将不十分成熟的制度创新信息泄露出去,以防止其它地区效仿。因此,承担了一定领导责任的上级部门也会十分地谨慎对待披露问题。诺达和鲍尔(Noda,and Bower,1996)认为,“对自下而上的主动创新行动发表上级部门的公开见解非常谨慎小心……推迟宣布他们的公开承诺直到学习减少了新的商业环境中的不确定因素为止,这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因为他们关心的是保持和加强他们的权力”。(注:Noda,T.and Bower,J.L.(1996),“Strategy Making as Iterated Processes of Resource Allocation”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7(Summer special issue):159-92.)其结果,上级部门与先行改革者会在对公众机构隐匿信息的问题上形成共识,这就构成了只对上级部门,而不对公众机构披露信息的安排。
最后是把握信息披露的时机。除了把不同的利益主体排成先后顺序获得创新信息之外,把握时机对不同的利益主体披露信息也是先行改革者创新策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不同的披露时机对创新成本与收益产生着不同的影响。在先行改革者看来,在三个组织群体中,把握对上级部门和公众机构披露信息的时机是更加重要的,因为先行改革者与组织内成员之间通过信息沟通与交流达成共识的成本往往比与上级部门和公众机构要低得多。从科斯(R.Coase,1960)提出交易成本与产权关系相关联系的定理中可以引申出这样的含义,即如果达成共识所需要的成本越低,先行改革者就越不需要考虑披露的策略性问题。而达成共识需要的成本越高,选定不同的披露时机对创新成本与收益的影响程度就会越明显。当与上级部门和公众机构在创新问题上达成共识需要的成本非常高时,先行改革者才不得不考虑采用什么样的策略以降低这个成本的问题,这才使得策略安排变得越重要。因此,对上级部门与公众机构把握披露时机的策略安排也是降低创新成本的一个有效手段。那么,在什么时候对上级部门披露信息最有利于在低成本条件下达成创新共识呢?在先行改革者的披露能力由弱变强,并使得创新试验取得了一定成效条件下,对上级部门披露创新信息是最有利于得到其支持的。因为披露能力由弱变强不仅意味着先行改革者对创新的认知水平、推进思路与解释能力有了长足的提高,而且,创新试验性的行动也大大降低了人们在创新之前无法预期其结果的不确定性。如果在缺乏这种条件下对上级部门进行创新信息的披露,那么,上级部门就难以采取支持态度。这也就是我国广东、山东、浙江和江苏等一些沿海省份在自下而上的体制改革中采取“先斩后奏”方式推进制度创新的原因所在。对公众机构披露信息的时机取决于以下几个条件:(1)创新试验性的做法基本趋于成熟,进而上级部门开始有意识地将创新地区的经验向其它地区推广;(2)创新信息传递的渠道已越来越广泛,使得其它地区即使不能直接从先行改革者得到创新信息,也可以从其它渠道获得;(3)不同渠道获得的信息可能会发生误解与走样,为澄清和导正误解的信息,先行改革者有必要正面披露创新信息。这三个条件的重叠是最有利于公开披露信息的时机,缺少任何一个条件,都使得先行改革者的披露行为向后延迟。因此,披露时机的把握对创新过程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四、结语
本文通过对改革以来的制度激励与创新风险的考察,把先行改革者的策略行为引入制度创新过程。然后,解释了这种策略行为的实现机制,即以先行改革者已掌握的信息资源为策略工具,通过对信息披露环节的控制,减少外部因素对创新过程中的成本与收益等方面带来的不确定影响。最后,本文从理论层面概括了先行改革者在信息披露环节上的基本策略行为,比如,先把多个组织参与的博弈变为单一组织参与的博弈、接着确定先后顺序,最后考虑披露的时机等。从这些分析中,本文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结论,先行改革者的一系列策略行为内生于整个制度创新过程中,它是先行改革者与组织内成员、上级部门和公众机构博弈的反映。这种策略行为使得制度创新的期限与方式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从而构成了我国渐进式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与厂商型企业家的商业式创新不同,也不同于诺斯描述的初级行动团体与次级行动团体合作博弈的制度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