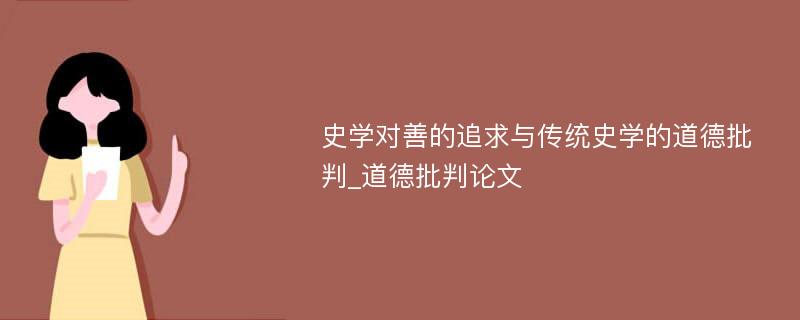
史学的求善诉求与传统史学之道德批判的省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道德论文,与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3)12-0075-07
史学本应在求真与求善二维之间的张力中展开,然而近代以来,在西方科学主义史学的影响下,史学开始向求真一维倾斜,而于史学之求善,尤其是求善诉求中的道德批判,史学工作者们则几乎无复再有人坚持,历史讨论中的道德主义甚至被认为迂腐而受到嘲弄,史学工作者亦因此推卸去了本应担在自己肩上的引领历史向善的社会责任。这种漠视史学求善功能的取向,体现于近代以来的中国,一方面是受西方科学实证主义求真的所谓价值中立影响而形成的史学家对于历史善恶的道德漠视;一方面则是沿袭晚明以来的道德批判思潮,认为传统道德已沦为恶之渊薮,并在极端情绪的批判下,形成“成王败寇”式的功利主义历史价值标尺。在对道德主义极端批判的取向下,翻案盛行,一些历史上被批判的人与事,却在功利主义的视镜下穿上了合理性合道德的外衣,美其名曰“历史”地认识——于是历史给予人们的启示或教育便是,只要能获得成功,能获得利益,不择手段乃致杀人越货都具有历史的合理性。这种可悲的事实或结果,在视追逐利益的最大化为根本目的的今天,是否应引起我们反思一下传统史学的求善诉求,反思一下其中的道德批判的价值和意义?
一、史学求善何以必要
省思史学道德批判在求善诉求中的意义,首先需要追问“史学何以要求善”,或“史学求善何以必要”的问题。这是因为,对于史学求善诉求的道德批判之存在价值的诘问,无论逻辑层面还是经验层面,其发问,最终皆会落实到这个康德式的追问,然后才有可能在问题得以解答的基础之上,依次继续追问:道德批判之于史学求善的价值何在?传统史学实践中道德批判是怎样地展开?传统史学实践之道德批判所持之价值标准是否具有其历史的合理性?而凡此等等,也是这里所试图省思之问题的起点。
先说“史学何以要求善”或“史学求善何以必要”。这实际是涉及史学终极目的的问题。按照近代科学主义史学的理解,史学的目的理所当然地指向求真,即认识历史之所以然。然而,若从人文主义的立场继续追问,则人们为什么要认识历史所以然之真,或史学求真冲动的目的何在时,问题则很自然地循此而转向了史学的求善,或历史之所应然的问题。
所谓的善(good),实际包含着有用的和好的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
关于史学之用,可以说史学之所以诞生就为了致用,否则人不会花那么大的精力去做一件无意义的活动。史学还初在萌蘖之时,其天然担负的责任是教育。其教育之用的表现有二:一是生产经验的积累与传递,一是社会经验的积累与传递,其中也包括人之为人的社会训诫。人类在这些经过筛选的、所谓有用的也是好的历史事实的积累中获取教益而不断成长,同时人类也从这些所谓有用的历史事实中完成对于自身的认识。《易·大畜·象传》称:“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按古代“德”常与“得”互训,《管子·心术》、《礼记·乐记》第十九、王弼《道德经注》三十八章等文献,皆有“德者,得也”之说。其中“出于史官”的“道家者流”,①更往往将“德”视为“人(甚至物)得之以生的根本条件”,如《庄子·天地》之“物得以生谓之德”,《韩非子·解老》之“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等等。因此,所谓“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正是通过对于历史知识的学习才完成对于知识和道德的获取。②惟因对于历史之用有如此的认识,中国的史学之父司马迁才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③只是司马迁不仅看到了史学的致用价值,也看到了史学的局限性,即“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古今“未必尽同”。但仅就认识历史所以然的目的来讲,“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关于“以史自镜”的观点,现代英国的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也指出,历史学存在的价值就在于“‘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柯林武德认为:“认识你自己就意味着,首先,认识成为一个人的是什么;第二,认识成为你那种人的是什么;认识成为你这个人而不是别的人的是什么。认识你自己就意味着认识你能做什么;而且既然没有谁在尝试之前就知道他能做什么,所以人能做什么的唯一线索就是人已经做过什么。因而历史学的价值就在于,它告诉我们人已经做过什么,因此就告诉我们人是什么。”④这也就是说,人们通过对历史的回溯,了解历史的所以然,以筹划未来的行动,也就是通过史学的求真活动,在认识历史所以然的基础上,确定历史未来走向的所应然。
那么什么是历史的所应然呢?历史所应然的指向,理应是人的目的的实现。马克思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⑤而作为类存在的人,其所追求之终极目标的指向,必将是趋于善的。按亚里士多德的话,即“一切技艺,一切规划以及一切实践和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标。因为人们都有个美好的想法,即宇宙万物都是向善的。”⑥这里所谓的“一切技艺,一切规划以及一切实践和抉择”,当然也会包括史学。史学实践的实质,是通过主体的叙述使历史获得意义:一方面将可能有用的有关生产经验、社会经验和政治经验等有关的史实纳入叙事之中;一方面是将有利于社会完善的普遍价值注入于历史的理解之中,所以史学所呈现的逻辑,是起于求真而终于求善。解释在史学的实践中可以说是无处不在。作为认识历史所以然的求真,所要解决的是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成为今天的样子,是对过去认识的问题。而作为认识历史所应然的求善,所要解决的则是我们应该怎样行动的问题,即对未来所企盼的目的。过去已往矣,认识历史的史学,根本性意义上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自己,以及自己在今天和未来将可采取的行动。史学的逻辑是始于求真而终于求善。
关于“史学何以要求善”或“史学求善何以必要”的问题,其逻辑或可以这样地展开,即:历史是人的历史,人的内在目的是历史活动的根本动力,因而人的目的也理应体现于人的史学活动之中,并内化为人之史学实践的目的与动力。即人从自己的目的出发解释历史,历史则通过人的解释而展现、说明人的目的。人的目的与史学之目的理应一致。所以我们说,“史学何以要求善”或“史学求善何以必要”,也是人追求善之目的的人性所决定的必然,史学应该是人实现其所思、所欲、所求的某种善的手段。套用《大学》之语亦可曰:史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矣。
二、史学的求善诉求与史学的道德批判
以上讨论了史学何以求善,得出了史学求善之必要性的结论。这里则讨论史学的求善诉求与史学的道德批判之关系的问题。
如前所述,所谓的“善”实际包括着有用的和好的相互联系又有一定区别的两个方面。善概念的发展,犹如作为会意字之“善”,有一个从“羊在六畜主给膳”这个最感性的口腹满足的感性感受,逐渐拓展至一切使人的欲望得以满足之感觉,又再进一步抽象为泛指一切美好事物之范畴的引申过程。这也说明所谓史学的求善,也应具有直接经世致用之求善和道德价值层面的求善(当然通过对历史的道德批判而达到指示未来行为的道德取向,也可说是史学求鉴、求用的一种形式)其中判断是否有用,因更多的是就外在的客观之物而言的价值判断,所体现的是一种工具价值;而判断是否是有道德的之好,因是就主体为目的而言的价值判断,所体现的则是内在价值。也许主体的目的具有太多的主观性的不符合近代统治学术领域的“客观”精神的原因,近代以来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界,讨论得更多的是关于“以史为鉴”层面的求善活动,但于史学求善实践中的道德批判,虽古人多有论述,但于近代以来对传统道德的社会批判逐渐成为道德知识形态主流的情况下,今人已鲜有从正面意义予以肯定了,更遑论与之理论讨论了。然而,若我们历史地理性地全面反思传统史学的求善诉求时,我们就不能漠视其中道德批判的存在,而这也就必然地引出了我们进一层追问——道德批判之于史学求善的价值何在?
我们说,史学中的道德批判事实上是一种价值评判活动,在具体的实践中,则表现为通过对过去的历史事实的是非善恶的道德评价,达到人们对于自身活动所应然的理解,告诉人们什么是道德的,人们应该怎样生活,从而建立未来将怎样行为的筹划。至于史学求善之所以有对历史予以道德批判的必要,从根本讲,是由于人性的不完善和人性发展的多向度的可能性决定。依据马克思所说:“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⑦人类本性怎样改变?即“善”之所以要“求”,乃因为道德之“善”,在人的历史实践活动中,并不一定天然地呈现。套用孟子说人性本质之善,乃“求则得之,舍则失之”者。⑧由于人的感性欲求,历史的所谓合目的与合规律的统一,只能是相对于终极意义上的理想之态而言。历史的真实呈现给我们的,更多的是历史与道德的悖离——道德意义上的恶显现为历史发展的动力。然而谁为历史立法?历史有没有起码的道德标准?有没有超越一时利害、相对恒常、相对普遍性的大是大非标准?显然历史的立法者只能是历史的主体,人之为人的基本人性,决定着历史道德诉求标准的普遍性。唐韩愈《原道》云:“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⑨这也是善之为“譱”,即众人言“善”方为之善的道理。
道德作为一种巨大的社会力量和人们内在意志力量的体现,有正义感、有求善冲动的人,是不会因历史一时的结果表现为历史的进程而宽恕其中所体现的种种行为之恶。诚如马克思在肯定资本主义之历史进步性的同时,亦对其予以了道德的鞭挞。一如康德所云,就人实现其自身目的的意志而言,经验现象的历史最终要指向本体的道德。完善的道德人的实现,才是人类历史的终极目标。没有道德批判的、短视的、只看一时结果的、实用主义的“成王败寇”式的历史观,引导的人类走向必将是社会的混乱与毁坏。
道德批判之于史学求善诉求何以必要,其经验和逻辑上的依据是:人性存在的天生的不完善性和发展可能的多向度性,以及基于普遍人性求善诉求而形成的一代代对于善之目的的不弃追求的张力,决定了人只有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对人之历史活动的道德批判,昭示其未来行为的所应然,才有可能克服人性中之恶,促进人之为人的道德升华,引领人类社会不断地趋之于善。史学从其诞生起,便天生地担负着教育的责任,即包括智识之知的教育,也包括德性之知的教育。“史家之尚论史事,贵能据德以衡史,决不可徇史以迁德……记叙史事而无是非之辨,则何贵乎有史?”饶宗颐先生如是说。⑩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就史学的价值意义讲:人的从不完善到逐渐完善的历史性,决定了人的史学求善诉求中道德批判实现的可能性、合理性和必要性。而历史也正是在人们的不断地道德批判之中理解人的所应然、不断地趋向于善。这也是道德批判之于史学求善的价值之所在。
此外,就历史认识论(知识论)来讲,近代以来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已经告诉我们,所谓的历史事实,其本身就是一种解释,任何历史事实在其被叙述的过程中,事实上就已经预设了叙述者的解释,而解释本身就包含了道德判断。因此,道德判断本身就是史学求善诉求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管你是否承认,而其重要的手段或工具就是道德批判。历史理论在经过认识论的转向和语言学转向之后,尤其是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洗礼后,一个重要的收获,就是使我们在被西方对“科学”一味追求而弄得支离破碎的史学中,重新发现道德的和美学的意义。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代表美国的海登·怀特,通过他对19世纪历史意识的研究,甚至不无激进地指出:“选择某种有关历史的看法而非选择另一种,最终的根据是美学的或道德的,而非认识论的”,并因此指出:“对于史学科学化的要求,仅仅代表着表达了对一种特殊的历史概念化形态的某种偏好,其基础要么是美学的,要么是道德的,而它在认识论上的论证仍然有待确立。”(11)进入21世纪,新兴的后-后现代主义(Post-postmodernism),则竭力尝试逃离“语言的牢笼”,“把人心的温热和心灵深处的共鸣交还给有关历史和历史写作的思考”,(12)努力在被后现代主义冲击的废墟上重建历史学赖以建立的认识论基础。于是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解构,到本世纪初出现的后后现代,整个史学理论的进程便呈现出一个理论取向的悖反——从对历史意义的质疑、历史学存在意义的质疑,到在被“科学”一味追求而弄得支离破碎的史学中,重新发现道德的和美学的意义,从一个新的认识高度,重新建立对于真、善、美的统一的历史学的追求。这也就是说,史学有必要求善,也有必要为求善而予历史以道德的批判。
三、传统史学求善诉求之道德批判的省思
回到我们省思的主题,即呈显于我们传统史学求善诉求的实践中,道德批判是个怎样的展开?其赖以批判展开的价值标准是否具有历史的合理性?抑或应该怎样认识与评价传统史学求善诉求中的道德批判?
史学中劝善惩恶的道德批判,应该说无论是在古代的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是史学的重要功能。苏格拉底所谓“知识即美德”说的建立,其逻辑前提就是建立在所谓“道德是可以教出来的。因为一切教育都要应用知识。因为人可以通过教育知道什么是善”的基础之上。(13)然而与西方比较而言,古代中国史学的道德训诫意义似乎更加突出。
在传统中国文化中,发达的历史理性和道德理性皆是钤得最深的印记,前者造就了中国发达的史学传统,后者则形成了丰富的道德学说。然而,在二者之间,因发达的历史理性而肯定人在历史中的地位,亦因强调历史是人的历史而高扬道德的意义,所以在凸显历史价值本位意识的同时,道德价值的考量也因此而被放到了一个更为优先的位置,同时也因此被视为评价历史所最优先考量的问题。即使是求真之维的“直笔”行为,如人们一直歌颂的董狐、南史之流,其史学行为背后的动力,也同样是道德的批判。即汉末史家荀悦所谓:“君举必书,善恶成败,天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德,咸在载籍。或欲显而不得,或欲隐而名彰,得失一朝,而荣辱千载。善人劝焉,淫人惧焉。”(14)北周柳虬所谓:“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记事而已,盖所以为监诫也。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彰善瘅恶,以树风声。故南史抗节,表崔杼之罪;董狐书法,明赵盾之愆。是知直笔于朝,其来久矣。”(15)唐史学理论家刘知几著《史通》,亦同样是有鉴于“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之千载”,而专立《直书》一篇。(16)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在传统史家的观念中,对于求真与求善之关系的理解——求真只是史学的手段,求善才是史学的目的,而道德批判是实现历史之善的重要手段。
中国传统史学这种富有道德批判意识的求善特点,不仅体现在中国历史理性展现的最初的曙光之时,即将道德思考置于历史的思考之中,(17)而且体现在将历史之知视为获得德性之知的重要途径,即所谓“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18)此后随着史学逐渐滋蘖成型,道德批判也进一步成为了史学求善功能得以实现的重要方式。人们对于史学功能的理解,除了包括“观成败”的政治教育价值,更包括“明是非、别善恶”的道德教化价值。当然,若从传统理性的理解看,这也是两个有联系的因素,(19)即历史成败的问题,其背后也是人心的向背,即历史行为是否具有合道德性的问题。
坚持历史合道德性的价值优先,对于传统史学来说,就是在历史评判中将义利关系的天平倾向于义的一侧。当然,对于传统史学来说,这种价值优先的历史思想,也是近代以来最为人们所诟病的思想,其批判最经常的指向,则是南宋那场“王霸义利之辨”中朱熹等坚持的“扬王黜霸”的历史思想。然而,如果我们将朱熹这种“重义”的史学观,置于理学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20)以及对北宋以来越来越专制的君权思以限制的思想语境下考量,(21)则朱熹等人坚持“王政”的政治立场之欲超越历史一时成败而为历史“立心”、引领历史向善的苦心,则未尝不可不使我们从价值的合理性和历史的合理性两个方面同情地理解或再认识传统史学家“重义”的道德批判意向。因为毕竟引领历史向善才是史学的根本目的。
传统史学求善诉求的道德批判,在史学实践中主要表现为一般意义的道德批判与社会伦理批判两个方面。
因为历史从其诞生那天起,就天然地担负着道德教化的教育功能,即教导人之为人或社会普遍认同的人的道德品质,所以就一般意义的道德批判来说,其批判的价值标准,虽然也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和社会性,但主要还是建立于普遍意义上的“人”的理解之上,因而其所秉持以批判的价值标准,至今仍然被视为揭橥。
传统史学对于人的道德批判,在传统高度发达的道德文明中占有重要地位,历代正史以及各级方志几乎皆设有诸如循(良)吏、酷吏、孝友(行)、忠义,以及佞幸、奸臣、叛臣、死节、隐逸、卓行以及列女等等类传,以期通过不同历史人物的分类叙事,展现一般道德的评判标准,以期达到“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即告知世人什么是所应该的行为。除此之外,在传统史学的一般道德批判中,对于统治者的道德批判占有重要地位。除了正史本纪的论赞之外,传统史学中更有许多涉及评议“君德”的史著,如唐代的《贞观政要》等。这种对于统治者予以道德批判的传统,可以追溯到上古殷商的“九主”之说和周代所确立的谥法制度。(22)后世儒家学者则进一步发挥,提出了道统高于治统,道德上的正义高于政治上的权力的政治思想,对后世史学道德批判的实践,提供了思想和理论上的支持,并在史学上形成鼓吹超越政治权力的道德批判意识。
由于统治者的道德行为直接关系具体的政治运作,影响社会秩序运行和人民福祉。于是对统治者的道德批判,也就上升到我们上面所说的传统史学道德批判中的社会伦理层面。
有关社会伦理方面的道德批判,孔子在所修《春秋》中表现得最突出,影响也最深远。《春秋公羊传》便有“《春秋》责备贤者”之说。按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是一个价值混乱、社会秩序遭到巨大破坏的鼎革时代。面对当时“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的社会秩序失范,“孔子惧,作《春秋》”。(23)意图通过“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等道德批判,(24)揭示历史的所应然。
孔子这里所憧憬的社会秩序,也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社会伦理或纲常礼教严正的社会。对于儒家学者提倡的纲常名教,自近代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备受诟病,然而当我们经历了近代以来对传统文化极度批判,当我们面临重建民族文化的任务之时,我们是否也应当省思一下:儒家纲常名教的提出是否具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儒家提出的纲常名教本身是否具有价值合理性?
从历史的合理性方面讲,按儒家宣扬的所谓纲常名教,其核心是礼。礼之产生在于止争,在于社会的有序,而目的则是达到社会的公平与和谐,或仁的理想在社会普遍实现。对此战国时期的思想家荀子有过精辟的论述,认为礼是因社会的发展需要而生成,亦因实现人的目的而产生。(25)
从价值的合理性方面讲,儒家提倡的纲常名教,其实质是达到社会和谐运行的伦理保证。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6)人既是社会关系的人,就必须时时面临着关系的处理,而礼作为一种社会伦理道德的规范,其实际蕴含的是一种调节社会秩序的观念,即通过对一系列社会关系亲疏远近的不同的权利界定,以使社会实现一种有序的结构而达到社会整合,其最终的目的是避免社会混乱纷争,使社会和谐有序运行。此外,人既然是生活在社会结构当中,那么每个人就必然要在社会分工中承担一定的社会角色,同时承担该角色所规定的义务。承担角色这一事实的同时也必然地要承担其相应的责任或义务。也正是社会角色与义务之关系的认识上,孔子才提出所谓“君君、臣臣、夫妇、子子”的理念,(27)按照孟子的解说,传统社会角色与相应的伦理原则应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28)而当社会角色与相应的伦理发生背离之时,也就是名实相违时,其社会角色也就失去了意义,孟子所谓由“君主”转为“独夫”而弑之可矣,即基于这样的理解而立意的。
因此,我们不能按照后来的专制君主单方面强调权利而淡化义务责任的立场,忽略其“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的价值理想。(29)毕竟对于历史大多数时期来说,稳定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和谐地运转,是有益于民众的安定生活和社会发展的福祉。任何一个稳定的常态社会,总是以拥有普遍的价值共识为其基本特征和社会保障的。儒家提倡的纲常也是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和社会有序运转的伦理保障。历史展现的事实是纲常乱则社会乱、则民受苦。对于这一点,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论道:“中国的立法者们的主要目的,是要使他们的人民能够平静地过生活。他们要人人互相尊重,要每个人时时刻刻都感到对他人负有许多义务;要每个公民在某个方面都依赖其他公民。因此,他们制定了最广泛的‘礼’的规则。”(30)惟因如此,传统史家才将“扶翊纲常”视为史学求善实践中道德评判的重要内容,而其所折射的则是史家对于正常社会秩序的愿景。回顾古代史学史,凡是纲常价值为史家所强调之时,往往也是社会失范混乱之时,也是史学家撰述历史强调纲常道德规范、展开是非批判之时。所谓“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是也。(31)至于司马光《资治通鉴》,虽非撰于乱世,但其“臣光曰”,亦同样包含着对于中唐以后藩镇割据及五代以来纲纪紊乱造成社会动荡的反思,即所谓“大抵史家之裁制不同,所以扶翊纲常,警世励俗,则一而已”。(32)即就传统史学来说,无论一般的道德批判,还是针对社会失范而进行的社会伦理的批判,其目的皆是以追求人的目的的实现,引领历史向善的努力。
美国当代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Tudt),在其《责任的重负》记述这样一件事,60多年前,法国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加缪曾质问他的左翼公共知识分子战友:“你们不觉得我们都应对价值虚无负责吗?……你们不觉得我们都应对价值虚无负责吗?……假如我们公开宣称自己犯了错,又会怎样?假如我们承认世上有道德价值存在,我们应为确立、彰显道德价值恪尽职守又如何?难道你们不觉得,或许希望会从这里萌芽吗?”(33)在加缪看来,知识分子就应当拒斥那些无原则的相对主义,拒斥一切犬儒行为。当代西方知识分子这种道德担当信念,使我想到《易传》所云:“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34)这也可说是传统史学家道德批判之求善诉求的使命意识之源吧。
注释:
①班固:《汉书》卷30《艺文志》,中华书局,第1732页。
②参见刘家和:《先秦史学传统中的致用与求真》,《史学、经学与思想》,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4-30页。
③司马迁:《史记》卷18《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中华书局,1959年,第876页。
④[德]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0-11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18-119页。
⑥《亚里士多德全集》中译本第8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2页。
⑧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第2749页。
⑨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马其旭校注,马茂元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3页。
⑩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76页。
(11)[美]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译、彭刚校,译林出版社,2004年,《序言》第4页。
(12)Frank Ankersmit,Sublime Historical Experienc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11.转引自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从“后现代”到“后-后现代”——当代西方历史哲学转型问题研究》,报告人:董立河,第54页。
(13)[德]威廉·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罗达仁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94页。
(14)《后汉书》卷62《荀韩钟陈列转》,中华书局,1965年,第2061-2062页。
(15)《北周书》卷38《柳虬传》,中华书局,1971年,第681页。
(16)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92页。
(17)参见刘家和:《论历史理性在古代中国的发生》,《史学、经学与思想》,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1-54页。
(18)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第40页。
(19)相关论点参见刘家和:《先秦史学传统中的致用与求真》,《史学、经学与思想》,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4-30页。
(20)张载:《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第376页。
(21)按关于陈亮与朱熹之间的“王霸义利之辨”,陈傅良《答陈同甫三》分析云:“‘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此老兄之说也。如此则三代圣贤枉作功夫。‘功有适成,何必有德;事有偶济,何必有理。’此朱长之说也。如此则汉祖、唐宗贤于盗贼不远。以三代圣贤枉作功夫,则人力可以独运;以汉祖、唐宗贤于盗贼不远,则天命可以偶得。谓人力可以独运,其弊上无兢畏之君;谓天命可以偶得,其弊下有觊觎之臣。二君子立论,不免于为骄君乱臣之地,窃所未安。”陈傅良从逻辑上分析了朱陈各自的观点所可能引出的政治后果:按陈亮的理论原则,很能出现完全没有任何道德敬畏心理的皇帝,即“上无兢畏之君”;而按朱熹的理论原则,则任何大臣们都可能借口皇帝行为不够道德,而起废立之心,谓“下有觊觎之臣”。如此分析,显然陈亮的观点是为君权张目,朱熹的观点则在约束君权。参见[美]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三联书店,2004年,第19-24页。
(22)《史记殷本纪集解》引刘向《别录》云“九主者,有法君、专君、授君、劳君、等君、寄君、破君、国君、三岁社君,凡九品,图画其形。”(《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94页。)“九主”的分等与谥法制度,皆是群臣对历史上的君主进行严厉而正义的事功道德评判。
(23)《孟子·滕文公下》,《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第2714页。
(24)《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7页。
(25)《荀子》曰:“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无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以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生,是礼之所以起也。”见《荀子》卷13《礼论篇》,按关于儒家学说中仁与礼的关系,按《论语·八佾》“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其详亦参见刘家和:《先秦儒家仁礼学说新探》,《古代中国与世界》,武汉出版社,1995年,第377-398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页。
(27)《论语·颜渊第十二》,《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第2503-2504页。
(28)《孟子·滕文公》上,《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第2705页。
(29)王国维:《观堂林集》卷10《殷周制度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32页。又关于礼与中国文化,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曾这样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定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详见氏著:《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7页。
(30)[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312页。
(31)《孟子·滕文公》下,《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第2714页。
(32)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2《卓行录序》,《四部丛刊》本。
(33)《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20世纪》,章乐天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
(34)《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第3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