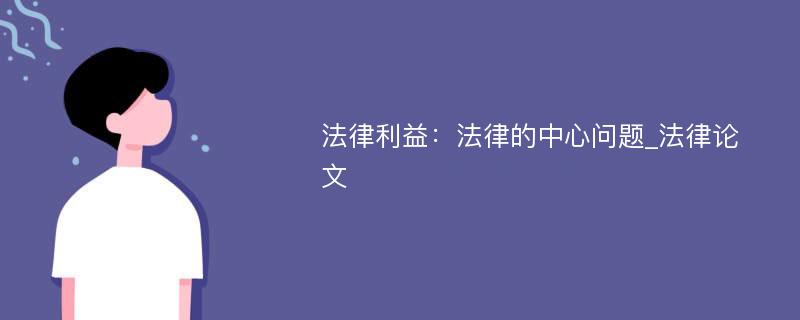
法益:法律的中心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律论文,中心论文,法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330(2008)03-0027-08
法益分析是以法益为中心的利益分析方法。法益分析将有助于法学领域利益分析的深化,提高利益分析方法和法学的亲和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刑法学家宾丁、李斯特在探讨研究犯罪的概念、犯罪的本质过程中,提出了法益范畴,并将法益提升为刑法体系的基本范畴,此后,随着法益理论的贯彻,法益理论逐步获得在德国以至在欧陆刑法学中的核心地位。二战前,法益理论由德国传到日本,战后获得较大发展。目前,我国大陆及台湾地区刑法学界均有学者对法益理论进行研究,①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学界、行政法学界在本学科研究中对法益范畴也有所探讨,②但没有像刑法学界那样将法益作为学科基本范畴进行系统化理论研究。这里笔者运用以法益为中心的利益分析方法对法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研究,以期对法学理论、法治建设有所增益。
一、法益:法的基本范畴
(一)法益的定义及特征
利益,按其是否具有法属性可界分为法益(德语das Rechtsgut,英语Legal interests)、非法利益、法外放任利益。法益,即法承认、实现、保障的利益;非法利益,即法反对、排斥的利益;法外放任利益,即法所不予干涉、由其自生自灭、放任自流的利益。其中法益是法的核心问题。在法律中有时它直接以“公共利益”“公民合法权益”等用语表现出来,大部分以“权力”“权利”等用语表现出来。法益范畴作为法学的基本范畴,在理论界一直存有争议,因而演绎出不同的法益理论派别。③如日本学者伊东研祐认为:法益是国家遵循宪法所(应当)构造的,对社会内的社会成员共同生活的存在所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且是由纯粹规范所(应当)保护的,因果上可能变更的对象。④我认为应当这样理解法益范畴:
1.法益具有法的属性
法益就是法所承认、实现、保护的利益,故法益和法密不可分。这里的法包括“法律”和“法”。关于法与法律的区别,在西方古已有之,如拉丁文的“Jus”与“Lex”,Jus是指抽象的法则、正义、权利;Lex是指具体的法律。“在他们看来,法是永恒的,普遍有效的正义原则和道德公理,而法律则是由国家机关制定和颁布的具体行为规则。法律是法的真实或虚假的表现形式。这种二元结构是西方法律文化传统特有的,是‘自然法’(理想法、正义法、应然法)与‘实在法’(现实法、国家法、实在法)对立观念的法哲学概括。这种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法律文化传统,使西方法学在方法论上呈现出对实在法的审视意识和批判精神。”⑤马克思在《论离婚法草案》中说,“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他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在有意识的现行法律之中。如果一个立法者用自己的臆想来代替事物的本质,那么我们就应该责备他极端任性”,⑥“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人的恣意横行”。⑦由此看来,前实定法益在未由立法者制定法律予以保护前已存在,立法者只是发现、表述法益,由于立法者主观意志、认识能力差异,前实定法益中可能有的上升为实定法益,有的则可能未能上升为实定法益,有的不属于前实定法益的利益可能被上升为实定法益。因此,“必须使法益概念规定中包含法益形成、确定判断的客观价值基准及其连接点。至于在现代民主主义社会的法治国家,对这种价值基准如何具体化,大体来说,可以由对现实的共同社会生活成员的必要性及宪法上的各种理念(及其适合性)来解决。”⑧法内承认、实现、保障的利益的本质属性是法,是法的人民性、公共性、公正性或正义性。在法治国家,宪法是法律的最高表现,立法者将利益上升为法益来保护,必须有宪法依据,必须符合宪法原理、法的一般原理等。
个人利益本位论的谬误之处在于它无限放大了个人利益走向了极端,它将不同属性的利益混为一谈,把个人利益范围内不属于法益的非法利益、法外放任利益混同于私法益,一同被抬上了圣尊的地位。就公共利益来说,他和私人利益一样,并不是天然具有合法性,也并不是所有的公共利益都应该受到法的保护。
2.法益具有利益属性
“所谓利益,就是指一定的社会形式中由人的活动实现的满足主体需要的一定数量的客观对象”,⑨“利益是适合社会主体存在与发展的因素或条件”。⑩主客观统一的利益范畴有如下特征:
(1)利益的主体性。需要是主体的需要,各种客观要件或因素只有适合主体生存与发展需要时,才成为利益,因此利益具有主体性。
(2)利益的客观性。首先,主体的需要是客观的。主体的需要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文化背景下产生和形成的。其次,适合主体存在与发展需要的条件或因素,也是客观的。
(3)利益的社会性。一定社会主体的利益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每一时代的一定主体的利益都具有一定的社会内容。
3.法益的因果上可变更性
法益是法所保护的利益,但并不是所有的利益都可成为法所保护的对象。法益必须是在因果关系上可能变动的因素或条件,必须具备可能的、现实的、客观的基础,亦即法益不应该由价值构成而应该由物构成,“法益必然是在现实中可能受到事实上侵害威胁的利益;如果不可能遭受侵害或者威胁,也就没有保护的必要。而所谓侵害或者侵害的危险都必然是一种事实的或因果的现象。因此,价值与价值观本身不是法益。虽然利益是具有价值的,保护利益也就保护了有价值的对象,但离开了利益的价值则是纯精神的现象,是价值观本身。”(11)法和其他社会规范区别之一在于,法是通过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而调整社会关系,保护法益,如果法律不通过规范人的行为而调整社会关系达到保护法益的目的,法律规范就无异于宗教、道德等社会规范;如果法益在因果关系上不可能由人的行为所侵害,那么法益就不具备受法保护的必要性。比如集体主义“至善”道德理想也是社会的公共利益,但就不可以作为法律和国家的目标去推动,法律关注的是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的最基本的权利,是每一个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是社会总体利益在每一个具体人之间的公正配置。集体主义“至善”道德理想就不可以作为法保护的对象,不可以确定为法保护的“法益”。
(二)法益的分类
对法益进行分类,使法益类型化,有助于立法者、法官、行政官员比较容易判断法益的位阶,在法益冲突之时予以取舍,按照“同样的事物同样对待,不同的事物不同对待”的公平原则决断何者法益予以优先保护。
1.以主体为标准的法益分类
以主体为标准的法益分类有“一元论”、“二元论”、“三元论”之别。“一元论”只承认个人法益不承认整体法益,看到了法益的特殊性而忽略了法益的普遍性;“三元论”把法益划分为个人法益、社会法益、公共法益,二者缺陷在于法益划分在外延上逻辑不能穷尽,并且“社会法益”实际上构成了一些个人或既得利益群体谋求私利的理据,甚至还会变成国家对某些既得利益群体进行保护的理据以及为他们创生新的特权的理据。(12)
“二元论”的法益分类是以主体是单个的社会成员还是社会政治组织为标准,将法益划分为个人法益和整体法益或私人法益和公共法益两类。个人法益即私人法益,是由单个社会成员基于个人生活而控制、主张的,并为法确认保障的利益。它包含两部分,即自我法益和他我法益。自我法益是一种特殊法益,是基于个人生活的自我特殊性而只能为个体所控制、主张的法益,它是个体法益中较稳定部分,不能够随意被纳入社会组织再分配领域。他我法益是一种普遍法益或共同法益中为个人所控制、主张、分享的那部分法益,是一种通过社会成员的共同生活而实现的法益。
整体法益即公共法益,是由一定社会政治组织所控制、主张的代表该社会组织全体成员或绝大多数成员的并为法所确认、保障的集合法益。整体法益是一种共同法益。只有单个社会成员相同或共同的法益,才有可能成为一种整体法益。当某社会群体尚未被组织起来时,其群体成员的共同法益存在于单个社会成员自身,这是共同法益的初级形态;当这个社会群体的成员被组织起来时,个人法益中属于共同法益的他我法益一部分脱离个人的控制,由代表这个社会群体的社会组织集合起来,就形成了一种新的高级形态的共同法益即整体法益。
整体法益的主体是拟制的抽象人格主体。整体法益脱离了单个社会成员由社会组织代表社会成员进行控制、主张,是一种相对独立的法益形态。但社会组织本身并不能消费法益,整体法益的主体是一个作为社会成员集体的代表,它可以占有、控制整体法益,却不能享用整体法益,整体法益及其主体存在的价值在于服务于单个社会成员的法益需求。整体法益在现实社会中表现为实质上或形式上的共同法益。当整体法益是全体或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共同法益时,整体法益就是一种实质上的共同法益。然而,当整体法益被少数社会成员控制或占有时,整体法益就成了一种形式上的共同法益。“整体利益之所以可能是形式上的共同利益,是因为整体利益形成(社会成员分离出整体利益)规则和分配规则的不合理,归根结底是因为私有制的形成和发展。”(13)公共法益来源于个人法益,公共法益依赖于个人法益,它以一定社会组织(公共管理机构)作为公共法益主体(社会共同体)的总代表,只具有抽象人格主体,本身并不能真正消化公共法益,最终仍需通过分配而转化还原为个人法益。法益转化之起点、终点都是个人法益,公共法益是一般化的个体法益,个体法益是公共法益的基础,公共法益如果脱离个人法益将毫无意义。“‘共同利益’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由作为‘私人’的个人造成的”,(14)历史有“事实表明,如果只注重对社会法益的保护,就会导致个人法益的丧失,保护好每一个人的法益,是保护社会法益的最佳途径”。(15)
2.以利益被法律保护的程度分类
以利益接受法律保护的层次不同分为权利、权力,弱保护法益,放任自由利益。在此有必要说明的是法益和权利不是等同的概念。关于权利的理论形形色色,有资格说、主张说、自由说、利益说、法力说、可能说、规范说、选择说等。但不管何种观点,明确的是,“权利的基本要素首先是利益,利益既是权利的基础和根本内容,又是权利的目标指向,是人们享受权利要达到的目的(以及起始动机之所在)”。(16)可以说,所有的权利都是法益,但并不能反过来说所有的法益都是权利,法益除在法律上表现为权利外,还表现为权力以及弱保护法益。利益还包括放任利益。(17)
权利是法律直接承认的私人利益或者是法律承认的私人利益主体赖以谋求利益之手段,权力则是代表公共利益,用以谋求公共利益之手段,法律对它们提供完全的法律保护。弱保护法益是已纳入法律保护范围,但法律只提供相对薄弱、不完整之保护,如反射利益、不特定多数人共享之利益、形成权利过程之利益、公序良俗所保护之利益等法律常提供相对权利、权力较低层次之保护。另外,法律内利益还涉及到一些处于自由放任状态的利益,法律对之不予干预,如公海之鱼或荒山之兽等。(18)在这三个层次中,权利、权力是法益在法律中的最主要表现形式,但我们亦不可忽视对弱保护法益之保护及实现,有时为加强弱保护法益之保护,就要把它们上升强保护法益即权利、权力之层次,予以完整、强有力的保护。
3.以法益的存在形态分类
按照法益的存在形态可以分为实定法益和前实定法益。“若由立法过程来看,立法者制定禁止规定或命令规定之前,在其想像之中,所欲保护的客体必已存在,而此客体则以人类共同生活的权益为其对象物。换言之,法益在此实具有‘前实定’性质。所谓法益的学说就是一种法益保护的学说,而不是产生法益的学说。法益保护与法益的创设是本质不相容的相对词,既言保护,那只有对于已经存在的事物,才予以法律保护;而不是对于根本尚未存在的事物的创设。”(19)它表明在法产生之前法益已存在,这种法益是前实定法益,是应然状态的法益,立法者的立法使前实定法益上升为法益,它通过具体的法律规范、法律制度表现出来。法益衡量首先必须以实定法益、以宪法和现行法律明文规定为依据,即使法律明文规定界定的利益关系有不尽合理之处,也不可以以此为由恣意妄为,否则法治的权威将丧失殆尽,这是与法治根本精神相违背的。这种以实定法益为中心的法益衡量是法益衡量的常态。即使在现行法律无明文规定之情况下,也应遵循宪法原则、宪法的基本理念、一般法理。所谓英美法系的法官“造法”,实际上是法官“找法”(Law finding),也就是遵循法的公平、正义等基本理念,在人们赖以生存、发展、共同生活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中寻找规范人们正当行为的准则,整个“找法”过程其实就是以前实定法益为中心进行法益衡量的过程。
4.以法益的内容分类
个人参与公共组织生活所应该享有的法益主要由公法调整,称为公法法益,如选举、被选举公共组织机构及其人员,监督公共组织机构及其人员活动,参与公共组织管理活动,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迁徙等方面的法益。个人进行经济生活等与公共组织生活无涉的法益主要由私法调整,称为私法法益。按照私法法益的内容,可以将其分为人格法益、身份法益、物法益、债法益、智慧法益等。人格法益又分为物质性人格法益(身体、健康、生命)和精神性人格法益(姓名、名称、肖像、名誉、隐私、贞操、婚姻等);身份法益分为亲属法益以及其他法益(荣誉、监护、著作人身法益等);物法益分为完整法益与抵押、留置、质押等法益,共有法益和相邻法益等;智慧法益分为著作法益、专利法益、商标法益等。
二、法益总量的最大化与法益结构的最优化:法律的基本目标
(一)法益总量的最大化:法律的效率价值目标
“如果说个别利益的对立使得社会的建立成为必要,那么正是这些个别利益的一致才使得社会的建立成为可能。正是这些不同利益的共同之点,才形成了社会的联系;如果所有这些利益彼此并不具有某些一致之点的话,那么就没有任何社会可能存在了。因此治理社会就应当完全根据这种共同的利益。”(20)莱昂·狄骥所谓社会连带关系就是利益一致关系。利益一致关系是法律产生、运行、发展的可能性基础。这一命题决定了法律的目标在于维护人类社会法益主体之间的法益一致,实现人类法益关系的和谐,以最终实现各法益主体的法益共同发展以及法益总和的最大化。
虽然法律及法理学并不是将所有的法益都视为处于同一承认、保护水平之上,并且在质、量的估价上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在法治的前提之下,法律为所有的法益提供一体的制度保护,我们并不能随意以各种法益价值先后位序为由而舍弃位序较低之法益。代表正义的法律意味着这样一种制度,“它意味着那样一种关系的调整和行为的安排,它能使生活物质和满足人类对享有某些东西和做某些事情的各种要求的手段,能在最少阻碍和浪费的条件下尽可能多地给以满足”。(21)亦即,法律的目标在于实现相关法益的最大化,而把法益的牺牲与摩擦降低到最低限度。这就是功利主义原则——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虽然实现法益总量的最大化这一价值追求,在实际操作中很难定量化,但不论在实际操作上会遇到何种困难,这种方法至少在逻辑上是可行的。(22)
(二)法益结构的最优化:法律的公正价值目标
马克斯·韦伯认为,利益的不一致导致了法律的产生和改革。庞德亦认为,利益冲突的广泛存在使社会控制成为必要,这种工具主要是道德、宗教和法律,在近代世界,法律成了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恩格斯认为,国家和法的产生是利益冲突关系日益尖锐化的产物。社会的利益冲突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就会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法律存在的意义就在于承认冲突并解决冲突而不是避免冲突或压制冲突。而法律就是要为人类社会利益关系提供一个调适器,为复杂的利益之间的冲突所产生的破坏性能量提供一个“出气孔”、“安全阀”,使这种能量不致于积聚太多、压力太高而致整个社会这个利益集合体崩溃。法学研究和法律制度建构应着眼于利益冲突关系,着眼于为社会提供一个健全、有效的引导不满和敌意的安全阀制度装置。法律控制利益冲突的价值标准就是公正。
在西方法学界,法律由古至今被认为是正义(公正)的同义语,正义(公正)“乃是所有法律的精神和灵魂”,(23)但离开了利益的正义是不存在的,是无法予以把握的东西,正义实质就是法益配置的标准问题,也就是法律目标的质的规定性问题,“正像双面雅努斯神的头,她向某些人呈现的一面是利益,而向另一些人呈现的一面是正义”,“说法是利益的规律和说法是正义的规律,不相抵触。利益是法所规律的目的,而正义则是法所规律的最高标准。法是利益的规律,但我们的正义感情,又要求它是利益的公正的规律”。(24)
功利主义者的国家政策目标在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无疑有它的正确性,它为法律和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思路。但是,功利主义的这种社会效益价值目标最为根本的缺陷在于,它所推论的社会主张可能不符合法律的基本的公正价值的追求。法律目标必须符合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法益总量的最大化必须以公正为前提,必须是总体法益内部结构(公法益之间,私法益之间,公法益和私法益之间)最优化配置。
(三)法益总量的最大化与法益结构的最优化:法律螺旋式价值追求
任何事物都有质和量的规定性,都是质和量的统一体,法律的目标自然也不例外。法律目标,就其质的规定性而言,就是法益的公正配置,也就是法益结构的最优化,实现公平正义为核心的人类利益关系的和谐;就其量的规定性而言,就是法益总量的最大化也就是法益配置的效率问题。法益总量的最大化、法益结构的最优化就是法律恒定不变的双螺旋价值追求。
公正和效率是法律的目标同时具有的规定性,它们相互规定,作为质的规定性的公正规定者对立面——作为量的规定性的效率;作为量的规定性的效率,规定者对立面——作为质的规定性的公正。效率和公正相互结合,相互规定,使效率和公正在一定范围内处于统一状态。公正和效率作为法律目标的同时必须具有的规定性,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可以舍弃。社会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国家任务不同,法律制度目标侧重点也就有所变化。虽然法律的公正追求和法律的效率追求始终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潜在的张力,法律目标价值取向有时是“效率优先”有时是“公正优先”,但是“效率优先”必须保证最低限度的公正,“公正优先”也必须保证最低限度的效率。法律的制度设计就是尽量避免两者发生冲突,并最大可能地同时实现法律的双重螺旋价值追求。
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及其制度设计基本是:首先,促进社会整体利益(对于法律而言是法益总量)的最大化增长,这个时期的价值取向就是“效率优先”,而后,对这种最大化的利益进行再分配,力图化解“效率优先”引起的公正、效率之间的紧张关系,由此,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由自由社会向福利社会的过渡。我国改革开放30年基本遵循的发展思路是,首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后富”,最终走向“共同富裕”。不过,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那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忽视公正的问题,使得我们现在不得不调整社会发展方向,关注社会公正问题,强调和谐发展,并把和谐发展提升到社会主义本质高度来看待。
三、权力、权利:法益配置的基础性手段
(一)法益配置手段:权力、权利
法律通过调整人们的行为进而调整人们的利益关系达到配置、确认、实现法益,控制利益冲突、维护人类社会利益一致关系,促使人类社会总体法益的最大化这一目标。法律借以配置、确认、实现法益的基础性手段就是权利和权力,权力和权利是法律中最基本的法现象。在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不同的权利(权力)的界定和分配,会带来不同效益的资源配置。有效的权利(权力)界定和分配是能使交易费用的效应减至最低的界定和分配。这些效应包括交易费用的实际发生和避免交易费用而做出的无效益的选择。科斯定理提供了根据效益原则理解法律制度的钥匙,也为实现最大效益的方面改革法律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25)
从法现象上说,权利、权力同为法律实现其目标的基础性手段。但从法深层次透视,二者又迥然相异:权利是权利主体获取自身利益的一种法律资格、一种正当化手段;权力是权力主体获取公共利益的一种法律资格、一种正当化手段。以法律生活观之,权利主体与权利载体,权利主体行为能力和权利能力有时处于同一状态,有时处于分离状态,而权力主体与权力载体,权力主体行为能力和权力能力却始终处于分离状态,只有在非法治状态之下,二者才可能走向同一。其原因在于权力的主体是个体的集合体,它是无法直接行使权力的,权力必须附着在具体的个人和组织之上方能完成法律赋予的协调私人利益实现公共利益的使命。
“上帝把天使带到人间同时也把魔鬼给放了进来”。法治之法的使命之一在于促使权利(权力)主体与载体、权利(权力)能力和行为能力的统一,统一于法益,为此法律始终要引导、规范、控制权力、权利的运作。因为权力运作总是依附在始终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和组织之身,所以权力总有被其权力载体滥用、异化的可能,而法律不懈的任务就是要防范和控制这种危险。因为人类社会私益冲突的不可调和,所以才有权力以公共利益的面貌出现进而发生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矛盾,在公益——私益关系的背后,仍是私益——私益之间的利益争夺、追逐,只是私益争夺转换了形式而已。在私益之间的利益流动中,多了个中介,即权力和公益,这个中介以共同体的面貌出现,有着强大的物质基础,从私人利益那里抽取了暴力部分,成了戴着甲胄的合法化利益,所以权力的运作相对权利的运作而言,其范围、深度和强度都是无法比拟、不可同日而语的,正因如此,法律必然以控制权力的运作为其首务。
(二)权利的至上性(绝对性)与权利的相对性
权力、权利是法益配置的手段,这在各国宪法及其他部门法中均予体现,是毋庸置疑之现实。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法律范围内,我们可以将权力、权利等量齐观。从理论上说,法律所实现、保障的法益首先是人的法益,法益以人为主体,人将自己作为手段是由于将自己视为目的的缘故,人民服从法律的统治是以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为目的和前提的,正如西塞罗所说,“为了自由,我们做了法律的奴隶”。法所反映的法益仍然是人类不平等交易的产物,但凡是选择法治的国家无论其占统治地位的为何阶级何阶层,都不能无视人的存在、人的自由与权利,它就是要企图攫取别人的利益也必须通过尊重人的自由、权利的法治之法而实现,否则那就是专制之法,人治之法。在现代社会,统治者依据专制、人治的手段已难以统治下去,任何统治者要继续统治下去,首先必须尊重人之作为人的存在的权利。台湾学者陈新民在谈到基本权利限制的目的时说:“宪法对人民基本权利,以在公共利益的需要为前提下,许可国家以订立法律方式来限制之。这种基本权利的可限制性之目的,并非因为国家可以在法律上,有概括的优于人民的优越地位,故许可国家以法律来限制权利,毋宁是以宪法肯定基本权利的存在为前提。由于基本权利保障了人民广泛的自由权利,此种自由的行使,可能会影响到宪法所要保障的公益。”(26)“宪法承认公益和私益之间,若凭人民无限制的行使基本权利,是会影响社会其他的法益,故须予以适当的限制,但绝不可任意以谋求公益为借口而牺牲私益(基本权利)。”(27)
权利的界限从本质上讲是法益,从前实定法益上讲是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从形式上讲,从实定法益讲,是法律的具体规定(而非行政法规、规章等行政规范)。具体来说,权利有其内在限制以及外在限制,权利的内在限制是指权利对权利的限制,即一种权利的行使应当以其他人同样权利行使为条件;权利的外在限制是指权利的行使受公益之限制,这是法律基于社会福利等公益目标对权利的限制,它通过权力为中介表现出来,公益具有不确定内容易为权力滥用其名义牟取私利,故它必须以法律规定界限并由权力正当合理行使之:即人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其条件为“①基于(广义的)公共利益之考虑及;②公益考虑的必要性及;③须以法律来限制等三个条件存在时,方可侵犯人民的基本权利”。(28)
(三)公共权力的工具性和公共权力权威
现代国家普遍认为公共权力是将法律整体意志付诸实现,是保障法益的工具,“国家并非像黑格尔所相信的那样,是理念的最高体现;国家也不是一个集体的超人;国家不过是一个有资格使用权力和强制力,并由公共秩序和福利方面的专家或专门人材所组成的机构,它不过是一个为人服务的工具”。(29)“对于这些官吏来说,绝不是什么订约的问题,而只是服从的问题;而且在国家所赋予他们职务时,他们只不过是在履行自己的公民义务,而并没有以任何方式来争论条件的权利。”(30)所以说,公共权力是实现法益的一个工具,是配置法益的一种手段,它本身并没有存在的独立价值,它附属于法律,是第二性的、派生的东西而非本身固有的存在物,它是实现法益的一个成本,它的价值就在于实现法益总量的最大化和法益配置的最优化。
为有效发挥公共权力的职能,对社会进行有效的管理,树立其权威是其应有之义。“麦迪森在《联邦党人文集》第五十一号中警告说:组织起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极大的困难是首先你必须使政府能控制被统治者,然后还要迫使它控制其本身。在许多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政府连第一项职能尚不能行使,何谈第二项。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在那些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恰恰缺少了权威,那里的政府不得不听任离心离德的知识分子、刚愎自用的军官和闹事的学生的摆布。”(31)
承认公共权力的权威并非说权力无边、权力无限、权力不受控制,更不是说权力在人民之上,在人民的法律之上,也不是说权力宽泛或集权就有权威,而权力范围小或分权就没有权威,“一个集权的政府,即使享有宽泛权力的政府,完全可能是一个在能力上比较软弱的政府”。(32)这也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症结,即一方面政府权力宽泛,限制较小,肆意侵扰公民自由的领域;另一方面,政府却没有权威,提高政府权威就必须要解决行政权力大而虚的问题。权威的统治必须以公众同意为政治基础,否则就失去了正当性,即使一个权威的确立起初是建立在暴力而非建立在民众合意之上,但当它获得这种权力以后也必须努力取得人民的同意,否则它就不可能统治久远。
注释:
①参见陈志龙:《法益与刑事立法》,台湾大学丛书编辑委员会1992年版;张明楷:《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②参见曾世雄:《民法总则之现在与未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蔡宗珍:《公法之比例原则初论》,载《政大法学评论》第62期。
③前引①张明楷书,第158—159页。
④前引①张明楷书,第155页。
⑤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3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2页。
⑧前引①张明楷书,第154页。
⑨苏宏章:《利益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1页。
⑩吕世伦、文正邦主编:《法哲学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页。
(11)前引①张明楷书,第163页。
(12)参见邓正来:《社会学法理学中的“社会”神》,载[美]庞德:《法律史解释》,邓正来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68—72页。
(13)叶必丰:《行政法的人文精神》,湖北人民出版1999年版,第40—41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5页。
(15)前引①张明楷书,第243页。
(16)前引⑩,第544页。
(17)参见前引②曾世雄书,第60—89页。
(18)参见前引②曾世雄书,第60—89页。
(19)前引①陈志龙书,第103页。
(20)[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5页。
(21)[美]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沈宗灵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4页。
(22)张千帆:《“公共利益”的构成——对行政法的目标以及“平衡”的意义之探讨》,载《比较法研究》2005年第5期。
(23)[英]彼得·斯坦等:《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王献平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7页。
(24)[日]美农部达吉:《法的本质》,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43页。
(25)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14—216页。
(26)陈新民:《德国公法基础理论》(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48页。
(27)前引(26),第349页。
(28)前引(26),第348页。
(29)[法]马里旦:《人和国家》,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5页。
(30)前引(20),第132页。
(31)[英]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7页。
(32)李强:《评论:国家能力与国家权力的悖论》,载张静主编:《国家与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标签:法律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 日本宪法论文; 法律主体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政治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利益最大化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