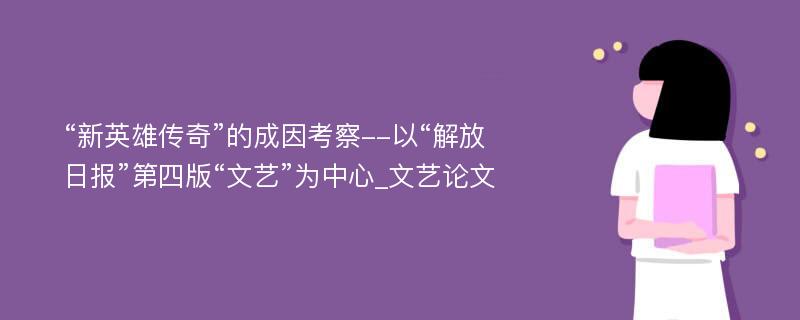
新英雄传奇的发生学考察——以《解放日报#183;文艺》第四版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解放日报论文,第四版论文,文艺论文,发生论文,英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英雄传奇是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文学乃至建国后17年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任何文学现象的出现都不是偶然和一蹴而就的,它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肇始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新英雄传奇也是如此。从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打响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新英雄传奇的基本面貌正是在这八年间逐步形成的。本文将以《解放日报·文艺》第四版为中心,详细考察新英雄传奇的发生过程。(注:《解放日报》创刊于1941年5月16日,当时文艺并未设专栏;从1941年9月16日起才开始专设《文艺》第四版。到1946年11月20日,《文艺》第四版重新并入其他版面,《解放日报》改为二版,除非特别情况,比如三八妇女节等,才会增至四版。以下引文除非特别说明,均出自《解放日报·文艺》第四版。)之所以以《解放日报·文艺》第四版为中心,并不是对解放区其他文学杂志、刊物的忽略,而是基于以下的考虑:首先是因为《解放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解放区的唯一隶属于比宣传部更高的宣传委员会的正式机关报,《文艺》第四版从文学政策以及文学写作上双方面指导、规定着作家的创作;其次,当时延安的文艺刊物并不多,1944年赴延安考察的记者赵超构曾记录延安当时的出版状况说:“全延安现在没有一种文艺刊物,只有《解放日报》第4版, 是他们的公共园地。”[1](P129);另外,由于战时条件的制约,很多杂志、刊物很难坚持办下去,即使坚持办下去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也很难保存齐全,因此以《解放日报·文艺》第四版为中心,能相对完整地看到新英雄传奇一步步发生的过程,有利于文学现象的整体考察。
抗战爆发后,大批作家知识分子走出“亭子间”,来到前线,写出大量关于前线战事的通讯、报道和文学创作。当时的抗战小说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坚持五四以来的精英式写作理念的作家知识分子创作的“通讯体”抗战小说,这是抗战小说的主流;另一类则是说书体的抗战小说。
“通讯体”的抗战小说在抗战后不久就受到批评。当时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类批评是从文学性的缺失来检讨抗战小说创作,就是讨论抗战文艺创作上的得失;另一类批评却是从文艺工作,包括文艺工作的方式和文艺工作者的身份等方面进行批评。这两种批评实际上代表了当时存在的两种写作理念、美学风格的冲突:前一种批评秉持的是五四以来的“亭子间”的写作理念,坚持从文学的角度建设文学(注:这方面的批评文章可以参看:茅盾:《八月的感想——抗战文艺一年的回顾》,载《文艺阵地》1938年8月16日,丁玲:《材料》,《解放日报》1941年9月29日,周扬:《文学与生活漫谈》,《解放日报》1941年7月17—19日。 茅盾指出抗战文艺最大的问题是“注重写‘事’而不注重写‘人’”;丁玲则在文中指出“文学家”和“新闻工作者”的不同,指出文学家要对材料进行文学上的精雕细琢;周扬则指出抗战文艺对战争的隔膜,抗战小说不能借生活本身打动人。这些批评都是从文学的标准出发对抗战文艺提出的批评。);而后一种批评则代表了抗战爆发后另一部分作家知识分子“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要求,主张文学应该“向下看”,重视广大的工农群众读者,也就是抗战的主力。(注:1938年,《文艺战线》发动作家到前方应该怎么从事文艺工作的讨论,对文艺工作的方式和作家的身份都进行了探讨,讨论的结果后来登载在《文艺战线》第1卷第4号上。参看:吴伯箫,卞之琳:《从我们在前方从事文艺工作的经验说起》,载《文艺战线》第1卷第4号,第36页;康濯、孔厥:《我们在前方从事文艺工作的经验与教训》,载《文艺战线》第1卷第4号,第38页。20世纪40年代以后对文艺工作者身份的质疑以更明确的方式提出来,批评家甚至建议文艺工作者丢弃“艺术家”的身份以更好地为抗战服务,参看默涵:《打破旧观点》,《解放日报》1942年12月4日。)
“说书体”的抗战小说就是在对“通讯体”的抗战小说的批评声中出现的,不过在抗战初期并没有形成潮流。这些作品在发表的时候往往会在小说题后附有说明,比如发表在《文艺战线》上的小说《陈二石头》,在题目后面就有括号加以说明是“讲演文学”,作者还在文章正文前特意写了一段话解释为什么是“讲演文学”:“陈二石头或者可说是一篇新鲜的东西,因为确有些四不像:说它是小说又不是小说;说它是故事,与普通所写的故事又不同。”[2] 作者在此明确区分“小说”和“故事”。“小说”指的是继承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写作经验而进行的创作,在当时应该是文学的正宗;“故事”则接近于传统的说书艺术,和民间通行的唱本、说书脚本之类比较接近,这两个概念实际上在作者的观念中代表两种不同的写作理念。《陈二石头》从文本来看确实是一篇介于“故事”和“小说”之间的带试验性质的创作,但是仍带有浓重的知识分子写作气息。《解放日报》上一系列注明是“通俗故事”的文学创作在讲故事方面则比《陈二石头》要地道得多,比如王牧的《明抗日和暗抗日》(《解放日报》1942年9月4日),何有之的《以华制华》(《解放日报》1942年12月13日),钟纪明的《赵得贵和他的枪》(《解放日报》1943年1月18日)等等。虽然它们的数量并不多,但是也代表了当时抗战小说的一个发展趋势。和当时占主流的“通讯体”的抗战小说不同,“通俗故事”的作者无意把故事扩张成“小说”,一篇文章就是一个或一系列故事,就是一个或一系列与“鬼子”斗智斗勇的过程。《以华制华》说的就是当地几个农民和“八路军”一起利用鬼子互相猜忌的弱点,将一千多“鬼子”一举歼灭的故事,语言简单、利落,利用偶然、巧合设置情节,读起来非常畅快。“通俗故事”最大的特色是语言方面通俗、易懂,一扫五四以来的“欧化气”。和“传奇总是关心着愿望和满足”[3](P87) 一样,“通俗故事”的基调是明朗的,结局也无一例外是喜剧式收场。但是作为文学创作,“通俗故事”的写作简化了很多属于文学层面的东西,包括心理、环境、细节、语言的推敲等等,技术层面显得很粗浅。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这些“通俗故事”的数量并不多,“通俗故事”的写作者也大多名不见经传,而且文章发表的时候编辑毫无例外都会在题后加括号说明是“通俗故事”。(注:这种做法也多少透露出当时文艺界的某种看法, 就是通俗故事这种迥异于新文学的创作,并不是文学的正宗,也不是文学的主流,所以编辑会在小说标题后特意加以说明是“通俗故事”。)此时“通俗故事”的写作虽然并没有形成潮流,但是作为创作上的一种倾向,已经引起了批评家的注意。
在江华一篇名为《创作上的一种倾向》[4] 的评论文章中,批评家以碧野的一篇名为《乌兰不浪的夜祭》(《文学月报》第3卷第2、3期合刊)的小说为代表,对当时文坛上出现的某种危险倾向提出批评:“我们不反对在这样徇烂的时代把握传奇式的题材,但这种传奇式的作品必须有我们时代的新的深刻的内容。……我们时代的传奇的英雄,必须是人性的真确的镜子,而不应该是仅仅表面画着脂粉的纸糊人”。[4] 这篇文章从文学的角度出发,对当时文坛在利用旧形式写作的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包括主题的选择、语言的袭用、人物的刻画等等方面提出批评,要求“传奇式”的写作应该从文学出发,尊重艺术创作的规律。
并不是只有江华一人看到了“通俗故事”写作中潜在的危机。周扬在1941年指出:“文学作品到底不只是说书,讲故事;它必须写人,写性格,写个性。”[5] 综合而言,当时的文学批评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审美标准:一方面是以“大众化”为旨归的隶属于“山顶上”的审美心态,主张作家从写作到身份都应该“大众化”;另一种则以文学性作为衡量作品好坏标准,隶属于“亭子间”的审美心态。
“亭子间”与“山顶上”的区别毛泽东早在1938年就已经指出来:“亭子间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吃,山顶上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看”[6](P13)。到底要“好看”还是“好吃”,文学家们要做出选择。1941年,作为边区文艺领导人之一的周扬发出“合流”的号召:“现在正是毛泽东同志所特别称呼的‘在山上的’和‘在亭子间的’两股洪流汇合的过程。”[7](P86) 当时一部分作家其实也有“上山”的愿望,但是因为对“山顶上”写作的陌生,也因为还没彻底放弃五四以来的精英文学理念,因此产生了一批像何其芳一样在“河边徘徊”的诗人(注:“河边徘徊”语出自何其芳的诗歌《河》,何其芳在此诗中感慨:“没有水的地方就是沙漠”,“没有声音的地方就是寂寞”。在何其芳的感叹中也可以看到诗人对延安“山顶上”的美学风格的不适应。),在理智上认识到深入群众的必要性,然而在具体创作时却无法放弃已经接受的“亭子间”的写作理念,因此无所适从。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给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一切这些同志都应该和在群众中做最低级的文学艺术普及工作的同志发生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帮助他们,指导他们,一方面又向他们学习,从他们吸收群众的养料,把自己充实起来,丰富起来,哺养起来,使自己的专门不成其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毫无内容、毫无生气的空中楼阁。”[8] 要着重指出的是,《讲话》在此所指出的解决办法是“和在群众中做最低级的文学艺术普及工作的同志发生密切的联系”,“从他们吸收群众的养料”,这和直接地“到群众中去”还有区别。所以《讲话》发表后一个很重要的文学现象,就是“大众习作”(注:延安大众出版社在1940年8月创办了一份辅导工农通讯员和初学写作者提高写作能力的刊物,即《大众习作》。一直到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作家知识分子们都是这份刊物的写作者们的文学上的指导,没有想到还可以从中学习。《解放日报》刊登此类稿件的初衷并不一定是为了给作家知识分子们一份“模范作文”,但是它在当时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作用。)的出现。以往研究多从作家角度出发研究“旧形式”在解放区大放异彩的原因,这样的研究方向并不是不对,但是忽略了当时很重要的一个文学情况。回归当时的文学情境,我们发现,影响当时作家创作的还不仅仅是他们小时候所接触到的唱本、说书,这些影响应该还是潜意识层面的,要调动潜意识的记忆还需要现实的刺激,而这现实的刺激就是当时“在群众中做最低级的文学艺术普及工作的同志”的创作,他们直接启发了来自“亭子间”的作家们的写作。换言之,“新英雄传奇”的发生不仅仅是“亭子间”的作家们自上而下的“利用旧形式”的结果,也是“自下而上”的“在群众中做最低级的文学艺术普及工作的同志”“文学启发”的结果。在考察作家的创作时,我们就注意到新英雄传奇的写作者,比如孔厥、袁静、柯蓝他们并不是从一开始就从事新英雄传奇的写作的,他们之前都曾经创作过“知识分子写作”一类的作品,后来才转向“新英雄传奇”的写作。
1942年4月《解放日报》改版, 一年后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特别说到了这次改版的成就:“《解放日报》自去年四月改版后有进步,摸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报纸材料的来源就无穷了”[9](P11)。1943年1月7日,《解放日报·文艺》第四版登载“本版征稿启事”,正式征集“工农士兵的写作及一切通俗启蒙性质的著述”[10]。1943年3月19 日《解放日报》开始增设“大众习作”专栏,发表工农士兵自己写作的作品。这些稿件分为“原作”和“改作”两种,“原作”基本上就是未经编辑之手加工的原汁原味的工农兵作品。大众习作最大的特点是明白、浅显,有什么说什么,像拉家常似的,少文学修饰。以下面这段文章为例,读者可以清晰地感受“大众习作”的特色:
贺生财今年五十六岁了。在旧社会里,他十二岁起,就给人揽工。一年赚五斗粮食,养不活家。他原是清涧穆家河人,民国五年逃难到延川,给人揽工,伙种地,安庄稼,总是短吃的。民国十三年,十八年两个荒旱年,他家过得更恓惶,家里吃荞麦花和谷知子(糠),吃树皮,十三年还把一个女子卖了。[11]
这正是作家们所不熟悉的地道的农民的语言,像说话一样明白、清楚。这篇文章在发表时编者还特意在“题后”加了“编者按”,指出:“作者是本报工农通讯员,初次写长稿”[11]。“工农通讯员”正是“在群众中做最低级的文学艺术普及工作的同志”[8]。
《解放日报》登载的大量“大众习作”,在适当的时候给了作家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如语言、人物刻画、情节设置等,起到“模范作文”的效果。
“大众习作”唤醒了作家知识分子对“传奇”的记忆。但是传奇化的写作方式要求传奇化人物的出现,因为传奇人物是达成故事传奇化的重要手段之一。传奇化写作确立的同时,文学就已经开始要求突破以往的限制,要求扩大人物在故事中的分量。但是因为初期的抗战文学并不提倡“英雄”书写,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五四以来的精英文学写作更侧重于表现生活中的普通人,哪怕是杀敌、打鬼子,也特意强调战士的普通人身份;其次可能和共产党的文艺政策有关,马列主义历史观认为是人民创造历史,英雄对于历史的发展作用不应放大;而从文学的表现来看,“英雄”的书写又很容易堕落为“个人英雄主义”的颂歌,因此“英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抗战文学中都处于不禁止也不提倡的位置。“英雄”正式合法进入延安抗战文学是大生产运动提供的契机。
随着抗战的深入,日军开始加大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国内的统一战线也显示出某种松动的迹象,“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正式对边区经济实行封锁[12]。在这样的背景下,边区政府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生产自救”运动。此时延安文艺涌现出大量的“劳动英雄”赞歌,当时的“劳动英雄”各有特色,有“农民英雄”吴满有,“工人英雄”赵占魁,“种菜英雄”黄立德,“妇女英雄”马杏儿、宋候女,还有“二流子英雄”(注:为了鼓励更多的人参加到生产运动中,当时边区政府还进行了一系列颇有成效的“二流子”改造运动,其中表现出色的被授予“二流子英雄”称号。)等等。“生产英雄”的崛起是时代、政治和经济的要求,“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是群众中的模范”,他们“使首长、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同群众联系起来了”[9](P97),这就解决了初期抗战文学中存在的“英雄”与“个人主义”的冲突问题,而且与马列主义的历史观也并不相悖。
从1942年开始,“英雄”开始频频出现于边区的报纸、杂志、刊物上,1944年《解放日报》第四版增设《英雄与模范》专栏,专门报道生产、生活中的英雄故事。这场大规模的“英雄运动”对于“新英雄传奇”的出现有双方面的影响。其一是确立了“英雄”在文学中的合法性,“新英雄”代替“传奇”里的“侠客”、“义士”成为无产阶级文学的主角。1943年,文化界举行欢迎三英雄座谈会,并表达了“笔杆与锄头、锤子结合起来”的决心[13]。当然一开始的时候文学所表现的仅止于“劳动英雄”,但是随着“纺织英雄”、“锄奸英雄”、“二流子英雄”、“识字英雄”等越来越多的英雄出现,凡在某一领域内有出色表现的都可以称之为“英雄”,英雄的含义开始扩大。这些英雄是“新”的群众的代表,和过去的旧的、个人主义的英雄区别:“这些都是新中国的新人物,真正伟大的英雄”,“他们的主要特点是只为革命,忘了自己。其次是他们永远在他们的岗位上埋头苦干着,自己以为是最平凡的人物。”[14] “新的英雄”就是人民群众,孔厥在此突出“新英雄”的群众性,纠正了过去的观念中关于“英雄”的“个人主义”倾向。(注:边区政府除了在文学中树立正确的“英雄观”外,也注意在现实生活中落实“英雄”的群众性这一观点。晋察冀根据地一级英雄李勇曾经在边区名噪一时,当时很多作家都对其事迹进行过报道(如:邵子南的《李勇大摆地雷阵》,李唯:《地雷的故事》),但是后来李勇因为骄傲脱离群众而在陕甘宁边区召开的英模大会中落选。毛泽东为此事专门致函给当时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代理书记程子华,表示对李勇的落选处理是正确的,还要注意进一步加强对英雄模范的教育工作。)
当越来越多的“英雄”进入文学,“革命英雄”,或者说“战争英雄”的书写就有点相形见绌了。朱德就很不满地指出:“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主义事迹和手创这些事迹的英雄们都被冷淡过去了,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不能说不是一个重大的损失。”[15] 战争和英雄结合,抗战小说的表现对象得以落实。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通讯体”和“说书体”抗战小说只有故事没有人物的弊端也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于是在“新英雄报道”的热潮中,一系列讲述抗日敌后武装斗争的“新英雄传奇”小说创作开始在边区出现。这些“新英雄传奇”作品的主角多为神出鬼没、艺高胆大的传奇“新英雄”,颇具民间侠客气质,同时作品表现出浓重的中国古代的英雄传奇小说的特色:一、以巧合、偶然因素推动故事发展,使故事情节传奇化。这是“传奇”式写作最经常采纳的方式;二、在人物塑造方面,不关注人物的内在性格特征,而着重讲述人物在故事中的命运,同时通过对人物能力的夸张,使人物向传奇化方向发展;三、以材料的连缀来结构情节,强调故事的有头有尾,而不讲究小说在艺术形式,比如结构、布局等方面的追求。
粗略统计1943—1946年《解放日报·文艺》第四版登载的“新英雄传奇”作品有:
张帆:《焦大海》,1943年10月5、6日连载;
江横:《山头英雄们》,1944年1月7、8、9日连载;
周而复:《小六儿的故事——晋察冀童话》,1944年7月30日;
周而复:《小英雄——晋察冀童话》,1944年7月31日;
周而复:《在一个小胡同里——晋察冀童话》,1944年8月8日;
周而复:《遛马的孩子——晋察冀童话》,1944年8月9日;
邵子南:《李勇大摆地雷阵——阜平英雄传之一》,1944年9月21日;
李果粹,小丁:《小英雄》,1944年12月7日;
周而复:《地道》,1945年4月8、9日连载;
王普:《八侠》,1945年4月11日;
武天桢,许柱:《“仙人脱衣”》,1945年4月17日;
邵子南:《阎荣堂九死一生》,1945年5月28日;
荆宇:《枪》,1945年7月17日;
孙犁:《芦花荡——白洋淀记事之二》,1945年8月31日;
李季:《老阴阳怒打“虫郎爷”——新编“古今奇观”之一段》,1945年9月12日;
罗夫:《解丑娃》,1946年2月18日;
苗康:《老子英雄儿好汉》,1946年7月15日;
马烽、西戎:《吕梁英雄传》,从1946年9月12日开始连载。
关于“新英雄传奇”,也有研究者称之为“革命英雄传奇”[16]。但是从当时的文学实际来看,“革命英雄传奇”的命名有不准确之处。虽然建国后17年文学中的“新英雄传奇”多以“革命英雄”为表现对象,但是从40年代的文学来看,“新英雄传奇”在产生之初其“革命英雄”并不是“革命战士”,更多时候他们就是生活中普通的老百姓。另外,“新英雄”的命名与当时作家、批评家们对“新的人物”、“新的群众”的期许也是一致的。至于这些“新英雄”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称之为“新”,这是另外要讨论的问题。我们在此沿用“新英雄传奇”来为这一类写作命名,是出于对当时文学环境和文学实际的尊重。作为“亭子间”和“山顶上”的两种美学思想互动的产物,“新英雄传奇”产生的时间不早于1942年,从《解放日报》来看,则是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才开始慢慢为广大作家所接受、熟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