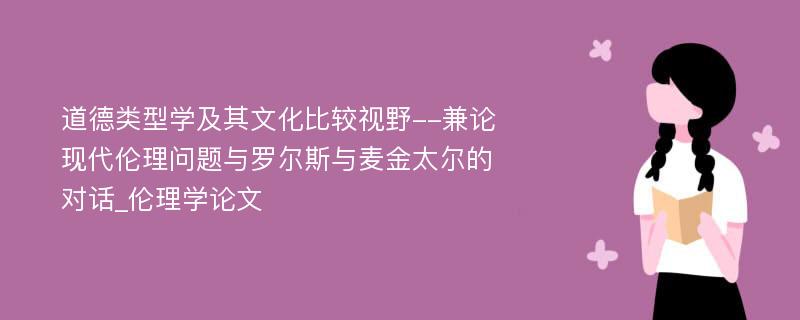
道德类型学及其文化比较视境——兼及现代伦理问题与罗尔斯和麦金太尔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道德论文,类型论文,罗尔斯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道德类型学是现代伦理学研究中日益突显的一个新的重大课题。本文从当代美国两位最著名的伦理学家罗尔斯和麦金太尔关于“规范伦理”与“美德伦理”的争论切入,在系统地梳理中西伦理学中有关道德类型学概念的基本思路之基础上,解析了罗尔斯与麦金太尔在这一课题上的理论得失。进而从文化和哲学层面阐释作者自己的道德类型学概念、并力图以此对现代社会和现代伦理问题作出原则性解释,提出“多元互补、分层贯通、共同分享”的综合性道德类型学主张。
关键词 类型学 道德 伦理 规范 美德 罗尔斯 麦金太尔
1971年,美国当代最著名的伦理学家之一约翰·罗尔斯以其扛鼎巨著《正义论》重开西方现代规范伦理学探究新风,震惊西方学界并影响了随后20多年的世界伦理学发展路向。11年后,另一位美国伦理学大家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发表了他的伦理学名著《美德的追寻》〔1〕, 从一种更广阔更深远的文化与哲学之交叉视境对罗尔斯乃至整个西方规范伦理学传统提出挑战。
在该书中,他提出了“美德伦理”(amorality of virtue)与“法则伦理”(a morality of law )两个概念,并在一种对应的意义上断定:“只有对于拥有正义美德的人来说,才可能了解如何去应用法则。”〔2 〕这一申言被西方学界普遍认为是用新的“美德伦理”替代“规则伦理”(a morality of rules )或“规范伦理”的一种不同选择。〔3 〕由此产生了一场关于“美德伦理”与“规范伦理”的学术争论。
本文不拟详尽讨论上述两位大家的伦理理论及由其所引发的这场学术争论本身,而是由他们各自对不同伦理类型主张的学理辩护和对话切入,在系统检讨西方伦理学多传统发展中有关伦理学类型的代表性观念之基础上,探究有关伦理学类型的基本问题,进而旁及我国现行伦理学和伦理文化研究的相关课题,以求为中西伦理学的比较研究探出一条新的路径。
一、道德类型学的西方概念及其流演
在我们的视野中,西方伦理是作为一个大伦理文化系统而存在的。但事实表明,在这一大伦理文化系统中,又生长着或曾经生长过多种不同的伦理文化传统。这一历史事实预制了西方伦理学类型的多样性。有一种传统的看法认为,在前现代时期,西方伦理学经过了一个由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两种伦理类型到中世纪单一伦理类型的演变过程。但麦金太尔的研究表明,这种二而一的描述并不能真实反映这一时期伦理学演进的整体图景。相反,他认为,古希腊罗马的伦理学发展所呈现出的远不只是两种类型,甚至也不只是古希腊与古罗马两种伦理学风格的递嬗,而是多种风格的交替出现。即使是在中世纪,也并不是人们通常所想象的神学一元论,至少存在“《圣经》与奥古斯丁主义”的伦理学传统与“托玛斯式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伦理学传统的内在竞争。〔4〕
麦金太尔的看法是有理由的。早在古希腊社会前期,虽然“高尚的灵魂寓于健美的体魄之中”已成为古希腊道德生活的时尚,但对于灵与肉、理与情、规则与心性、秩序与个体能动等概念的两分意识和偏颇已初露端倪。在古希腊神话中,我们甚至发现这种两分概念的原始资源。太阳神阿波罗(Apollo)象征的理性精神与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sus)象征的感性精神;众神之父宙斯(Zeus)和法律之神席米斯(Themis)象征的公正秩序与自由之神雅典娜(Athena)和爱神罗丝(Eros)象征的自由、激情和爱;无疑是这种两分意识的滥觞。而如果说,由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之伦理学命题开创的理智主义伦理学风尚贯穿了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探索的全部理路的话,那么,由智者派所代表的伦理学探究思路则是一种典型的感性主义了。但是,这种崇理与尚情的两分对应在古罗马斯多亚派的律法主义伦理探究方式中消泯了,以致于道德不再只是作为一种知识或一种情感美德,而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外在普遍的法律式约束。
古典的两分性道德思维方式是相对的。灵与肉、理性与情感、规范秩序与德性能动的分别并不具有绝对的性质。因而,道德类型的区分并不十分明显,尽管我们也不难寻找到所谓“目的论”与“义务论”或“道义论”的对应形式。但是,这种古典的两分性道德思维方式却为现代西方的道德学家们明朗化了。随着现代社会的道德生活日趋复杂和道德学家对伦理学的理论合理性追求不断强化,道德的类型化概念也越来越清晰了。这一方面当然是因为现代科学的规范化和系统性逻辑要求所致;但另一方面,在更广阔的文化意义上则是由于现代社会生活本身多元化与协同条理性特征的深层影响所导致的结果。
对于17至18世纪的西方伦理学,人们所熟知的是以英法世界为代表的感性主义目的论伦理与康德所代表的理性主义义务论伦理的两派划分方式。但麦金太尔的研究却揭示出这一方式的重大缺陷。他告诉我们,文艺复兴以后的整个西方伦理学都属于启蒙运动的现代性思想谋划的一部分,其根本特征在于它对古典美德伦理传统的抛弃和对现代性规范伦理的偏执。无论是功利主义,还是康德的理性普遍主义,都不过是对某种理想类型的规范伦理学模式的单相寻求而已。而缘于休谟的20世纪元分析伦理学的逻辑情感主义和尼采萨特式的意志情感主义,虽然表露出对这种现代性规范伦理的理论绝望,但它们并没有找到走出规范误区的途径,反倒是在逃避道德之文化历史情景解释的歧路上愈走愈远。〔5〕
麦金太尔的见解是有启发的。他高明地揭示了现代西方伦理学最具现代性的理论特征,指出了西方现代伦理与西方现代社会之间最本质的内在联系——即现代性规范伦理与现代性社会高度制度化法制化要求之间的密合性。但是,我并不认为麦金太尔的解释涵括了西方现代伦理学发展的全部内貌,至少还不足以揭示三百多年的西方现代伦理学发展所呈现出来的类型多元化特点。不错,规范合理性的寻求是整个现代西方伦理学开展的一个基本特点,但这不是全部。无论如何,功利主义伦理学的规范合理性追求与康德伦理学的规范合理性追求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前者对目的或效用的实质性价值的偏好与后者对普遍道义的理想精神价值的执着,显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道德价值取向。如果说,两者确乎共享着一种建构现代规范伦理学的理论目标,那么,这也只是在一种传统与现代的道德文化对应意义上作出的一般断言。而在道德类型学意义上,这一断言还必须有进一步的辩证。
这就涉及到我将要在本文稍后提出的道德类型学概念及其论证理据的问题。在具体谈到这一中心论题之前,我想预先指出,从一种理论意向看,现代西方伦理都应归于所谓规范伦理之列;但从道德价值取向来看,功利主义无疑是实质目的性的,而康德的伦理学则是普遍理想性的。因而,两者的规范内容和形式都有不同:前者以社会规范或某种形式的群体要求表现出来,规范的所指不是个人道德行为本身,而是行为的善性(goodness)结果,即是否能产生或有助于产生“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相反,后者却以个人或人类关系的普遍道德正当性(rightness)要求形式,来规范人的道德行为和道德关系。所以,从规范形式看,前者是社会整体型的,后者是个人自律型的;而从规范内容看,前者是善与恶的价值标准,后者是正当合理与否的道义标准。
时间进抵20世纪,功利主义与康德主义这两种最有影响的伦理学理论同时遇到了空前严重的挑战。如果说,19、20世纪之交的西季威克(更早一些甚至可以上溯到他的先驱休谟)已经意识到功利主义伦理学在规范的逻辑证明上的脆弱和严重缺陷的话,那么,1903年摩尔发表的《伦理学原理》一书则首次明确地诊断出这一缺陷的根源恰在它患有一种规范伦理学的通病——“自然主义谬误”。而如果说,19世纪晚期的叔本华、基尔凯戈尔已经预告了康德普遍主义伦理学的失败,那么,尼采的“铁榔头哲学”则彻底打击了现代规范伦理的普遍主义理论雄心。
然而,正是从这一时刻开始,西方的道德学家们形成了明晰的道德(伦理)类型学概念。从20世纪的西方伦理学发展史中,我们读到,尼采率先提出了“英雄道德”或“主人道德”与“群氓道德”或“奴隶道德”的类型区分;柏格森提出了“开放型道德”与“封闭型道德”的对立;居友提出了“确信道德”、“信仰道德”和“怀疑道德”的三重性道德类型概念。〔6〕甚至是现代元(分析)伦理学的代表人物、 “维也纳学派”的领袖石里克也在考察了西方伦理学传统后认为,在西方的道德传统中,一直存在着两类对立的道德类型和伦理学类型,这就是他谓之的“要求道德”和“放弃道德”与“欲望道德”,与之相应的是所谓“自我限制伦理学”与“自我实现伦理学”。〔7〕
石里克对道德类型的区分方式是传统的,同时也是现代的。他所区分的对象是西方已有的道德观念和伦理学理念,但其区分本身却揭示或预示了尔后为麦金太尔教授所详尽论证的西方伦理学的传统类型与现代类型的区别与对立,这就是本文开头所谈到的“美德伦理”与“规范伦理”的区分和对立。所谓“要求道德”或“自我限制伦理学”正是现代规范伦理学的本质特征,而所谓“欲望道德”或“自我实现伦理学”恰恰是“美德伦理”之目的论特质的一种较为直接的不完全表达。道德要求的基本表达形式是道德规范或伦理规则(原则),以及由此引出的一系列道德判断标准和行为戒律,而它的基本理由之一,则是普遍正当之行为规范对于整体社会秩序的必要性。道德实现的根本内涵则在于道德行为主体的内在目的和品性人格的完善,其基本理据在于:道德作为人类价值生活的基本形式之一,不仅要表达某种形式的对人类有效合作行为的普遍要求,而且必须首先是人的自我完善的内在表达。易言之,道德不仅表达人们行为的正当合理要求,也表达着、且首先表达着个人的善性达成。没有后一方面的内在支撑,就谈不上前一方面的现实可能。用麦金太尔的话说,“只有对于拥有正义美德的人来说,才可能了解如何去运用法则。”〔8〕因为诚如亚里士多德早已意识到的那样, “无论规则是多么系统周全,任何一套规则都无法给所有可能的偶然事件提供指导。”〔9 〕这正是麦金太尔给罗尔斯代表的当代新自由主义伦理学提出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二、从罗尔斯到麦金太尔:道德类型学问题的两次变换与实质
应当指出,道德类型的不同选择只是罗尔斯和麦金太尔等人产生伦理学分歧的表现形式,但它同时又涉及到两者在学理和观念上的一个根本不同,而这种差异的背后却不只是有关整个现代西方伦理学路向的根本性对立,而且涉及对现代社会与现代伦理之一般性和整体性的理解。
从一种历史的角度看,罗尔斯和麦金太尔都属于当代西方伦理学界的新潮领袖,都站在伦理学理论的转折关口,领导着一种新的理论转向。但两人所持的学术信念和选择的学理路向是不同的。罗尔斯面对的学术背景是当代美国的社会现实生活,他思维的领域是现代社会的现代性伦理建构问题。因此,他秉承的学理传统是现代的,而不是古典的或古代的;他选择的伦理学类型是现代社会规范伦理而不是其它;这一选择恰恰是基于他对现代西方自由主义价值精神的基本确信。从这一意义上说,罗尔斯本人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西方现代型规范伦理学家。与其不同,麦金太尔更像是一位带有典型地域情结的道德特殊主义( the particularism of morality)传统型伦理学家。意大利学者乔凡娜·波拉多芮在采访麦金太尔教授后感慨地谈到:“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驻足神思于一种远古过去的回忆与对美国多元论的全球性视观之间,并深深沉浸在苏格兰凯尔特人(一译“盖尔特人”)的传统世界之中,极大地丰富了当代的道德争论,使其达到了一种无与伦比的深度。他以一种全新的灵活性在历史主义的密网丛隙之间游刃有余,其辩谈(discourse)直指一种新托玛斯主义视域的极境,他并不把这一极境理解为[道德哲学]范畴重建的非常时刻,而是相反,把它理解为致达‘美德伦理’的关键点,视作全面剖析所有古典希腊文化并达到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充分系统化的一种线索。”〔10〕换而言之,麦金太尔所面对的是整个西方的伦理学历史;其所秉承的传统是西方古典的;其解释方式是历史主义的、文化学的,而不是纯哲学的或逻辑的;而他确信并坚定选择的伦理学类型则是具有强烈古典色彩的美德伦理,而不是现代西方通行的规范伦理。从这一视角看,麦金太尔的学术背景要比罗尔斯更广阔一些;其对现代西方伦理的批评性“重建”也更深远一些。但这并不代表我对罗尔斯和麦金太尔的伦理学本身的理论价值评价。一种理论本身的深刻性和创造性价值并不完全只取决于它所诉诸的理论背景和批评范围,还在于它自身的理论开掘和历史性贡献。更何况我在本文中所追求的目标不是一种简单的比较评价和两者择一式的抉择,而是一种批评性整合和创设。
在我看来,罗尔斯和麦金太尔都是承诺着某种理论关捩转折的时代性道德思想家,只是由于他们的思想背景和理论关切不同而导致了他们的理论承诺互不相同罢了。罗尔斯所关切的,是他置身其中并深有感触的60年代美国社会的道德生活,和当时与这一生活现状极不相称的伦理学理论情景。这是他关切至深却又忧心忡忡的现实情景:一方面,刚刚从太平洋战场上返回美国的罗尔斯,面对着美国社会的激烈动荡(政治危机、经济萧条、反战浪潮、黑人种族运动、女权运动……等等)揪心苦思,社会的公正秩序问题很快凝聚成他哲学思维的焦点;另一方面,二战后涌入美国的分析哲学和元伦理学风愈演愈浓,与社会现实生活的隔离越来越严重。这使得罗尔斯逐渐下决心投身于道德哲学和社会政治哲学这片充满挑战却又为他的大多数同时代学者所忽略了的理论领地,并去奋力扭转当时伦理学发展的方向。〔11〕
众所周知,20世纪前半叶的西方(包括美国)伦理学几乎完全被纳入分析哲学的研究轨道,伦理学几成逻辑和语言分析的技术性探究。道德的行为问题、规范问题、实质性价值问题,以及社会实践问题,都成了无法给予逻辑或科学证明的悬题而被束之高阁。然而,问题的复杂性还不只是这种主题的偏离,而在于元分析伦理本身所提出的伦理学的科学合理性疑问,确实是一个长期遗存于伦理学界并已突显为一个无法再回避的难题。如果人类不解释清楚“事实”或“是然”(what is orto be)与“价值”或“应然”(value or what ought to be)的逻辑沟通问题,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把道德问题作为一种有意义的理论问题来谈论,也就不能把伦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知识来研究。生活问题的重要性并不等于它本身获得科学知识特性的正当理据,一如宗教信徒不能申称自己全身信奉的信仰是一种普遍的科学一样。这就是说,现代元伦理学的研究提醒我们,在我们寻求对人类道德生活作出合理解释时,所需要的不单是一种关注人类生活意义的理论责任,而且必须持有科学的研究方式——假如我们想使自己的道德解释成为一门合理知识的话。
显然,罗尔斯致力的转变事业是一项十分复杂而艰巨的工作。为了将伦理学从纯语言纯逻辑分析的理论世界中拉回到现实生活中来,他需要重新确定一种新的伦理学探究路向;而为了完成这种方向性的理论转变,他又需要找到一种新的伦理学探究方法。否则,只能是重复现代规范伦理的老套路,像现代新功利主义伦理学那样去重弹边沁、密尔的老调。罗尔斯拒绝了17世纪至20世纪英美功利伦理和实用伦理的实利主义目的论伦理学传统,接受并改造了“由洛克、卢梭和康德所代表的传统社会契约论”,“并使之擢升到一个更高的抽象层次”,以此来重新开出一种“不仅可以替换而且优于占支配地位的传统功利主义解释”的“另一种正义的系统解释”。〔12〕在新近出版的《政治自由主义》中,罗尔斯把他自己的这种“正义的系统解释”称为康德“道德建构主义”(moral constructivism)改造基础上的“政治建构主义”(politicalconstructivism)。〔13〕而他借以达致这一理论目的的方法既不是“笛卡尔式的”道德形上学,也不是现代元伦理学家们所批评的那种“按照假定性的非道德概念来引导出道德概念定义”的“自然主义”〔14〕,而是在重建“社会基本结构”概念前提下发展出来的正义规范伦理。它是规范性的,但不是“目的论的”;它是“义务论的”,却又回避了康德对人性的“道德形上学预设”。〔15〕
罗尔斯选择了康德式的义务论规范伦理图式而不是当代英美元伦理学图式,这无疑是其伦理重建的革命性意义所在。同时,他选择康德和卢梭这样的欧洲大陆派先驱而不是英美的伦理传统,确实又使他的伦理学获得了超越英美传统规范伦理的理论视境,这同样有着理论革新的意义。如果从长期形成的所谓“英美派”与“大陆派”哲学分峙概念上看,罗尔斯在伦理学领域的这种革新显然具有一种现代整合意义。但是,罗尔斯在两个根本性的立场上并没有改变,这就是他对于“现代性”的社会确信和对于“西方世界”的现代自由主义的价值确信。这两种信念是支撑着他伦理探究的一而二、二而一的学术信念之本。作出这种判断的理由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的理由是由麦金太尔提出的,他认为,罗尔斯的正义规则伦理在根本上只是一种延伸了的现代性规范伦理变体,它的理论情结是对现代性社会的绝对信仰和绝对忠诚。因此,罗尔斯对西方传统伦理的态度是轻慢的。另一个方面的理由是我提出的。我以为,罗尔斯对现代西方自由主义价值标准的执着,限制了他的正义规范伦理的普遍意义,这与其普遍主义的规范伦理追求是相抵牾的。尽管他申言,他的“正义论本身并不偏爱这两种制度(指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引者注)中的某一种”〔16〕,但他的理论基点是西方的、甚至是“封闭性的”现代西方的。对此,我们从他在《正义论》一书中反复论证,并在其近著《政治自由主义》中仍孜孜不倦地论证着的正义论两原则中不难得出结论。罗尔斯正义论的第一个原则是“自由的平等原则”,这一原则的核心是:个人的“基本权利”必须优先考虑,不得以任何社会整体的功利或效益(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之类)的名义侵犯之(这正是罗尔斯反驳功利主义伦理学的主要理据之一)。他的第二个原则是正义的“差异原则”,这一原则的基本要求是:为了确保社会的公正和秩序,社会分配制度的安排必须以有利于惠顾社会最少数最不利者为其宗旨(与功利主义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相对)。按罗尔斯的解释,第一个原则优先于第二个原则,它们之间的顺序是一种“词典式的顺序”,不可颠倒。很明显,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仍然是自由主义至上的原则,与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核心价值观念一脉相传。而他的正义论义务规范伦理的实质,只不过是对社会的单面性公正安排的道义要求,而不是对个人的道义要求。换言之,罗尔斯的正义伦理所指,首先是且主要是对社会的规范,而非对个人行为的社会规范。无怪乎西方许多学者都把罗尔斯的正义伦理归于“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liberal individualism)之列。
与罗尔斯相比,麦金太尔的视野则要广阔得多。他更像是一位道德史家和文化思想家,也更多地钟情于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多元发展与比较,而不是现代自由主义,更不是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伦理精神。因而,他所致力于的转变事业也要比罗尔斯的更有抱负,因之更具有冒险性。因为,他不仅仅是想在西方现代的伦理学思维框架内实现一种伦理学类型的重新建构,而是要对启蒙运动以来的整个现代西方伦理作出批判性反省。所以,他所批判的不单是现代西方的元伦理学或功利主义,而是代表着现代西方整个伦理学之本质方面的规范伦理。
在麦金太尔看来,自称为西方现代生活奠定和提供基本道德观念系统的启蒙运动之思想谋划完全失败了,而且这种失败的阴影仍然笼罩着当代新自由主义伦理理念的信奉者和追随者们。这种失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道德概念的无公度性(conceptional incommensurability)使现代伦理学的普遍主义追求归于破产;伦理学上非人格性论证方式使现代伦理的规范性主张失去了通达人格内在的基础;以及现代伦理学对道德概念之广泛多元性起源的忽略所导致的非历史主义后果。〔17〕导致这一失败的基本原因有两个方面:其一,现代伦理剥夺了人类道德生活不可剥离的社会文化背景与历史背景,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人类道德的解释成了无传统无根源的主观解释,因而,看轻社会或人们生活于其间的各种形式的道德共同体和他们道德生活所展示的具体历史情景,就成了现代伦理的一个共同的必然后果。其二,现代伦理还剥夺了人类道德生活的内在目的意义和品格基础,把伦理学几乎变成了纯粹外在规范约束的设计。这不仅使伦理学或道德成了一种类似于法律的规则体系,而且也使道德规范本身失去了应有的作用和意义——因为人们无法相信,一套哪怕是再好不过的规范能够为毫无德性和品格的人接受并践行。前一个原因导致了现代伦理的个人主义后果;而后一个原因则导致了现代伦理的普遍主义规范论幻觉。
对西方现代伦理学状况的这一判断和认识,促使麦金太尔下决心摆脱现代伦理的这两种不幸命运,向传统伦理寻找新的理论资源。面对着西方世界盛行的普遍主义规范伦理的思维方式,他毅然提出“美德的追寻”之新思路。而面对在当今美国伦理学界如日中天的规范伦理学巨擘罗尔斯,他尖锐地发出“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的诘问。〔18〕
麦金太尔对上述思路和问题的解答是意味深长的。在《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一书中,他耐心地考察了自古希腊英雄时代以降的西方伦理史,疏理出在他看来是最为重要和典型的四大伦理学传统:即源于古希腊英雄史诗、中经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所完成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传统(这一传统的后继者是中世纪的托玛斯·阿奎那和他本人);《圣经》与奥古斯丁主义传统;以苏格兰启蒙运动文化为代表的奥古斯丁式的基督教与亚里士多德主义共生互容的道德传统;以及肇始于欧洲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伦理学传统(亦即当代罗尔斯等人所秉承和捍卫的现代规范伦理学传统)。进而,他提出,有多少伦理学传统,便有多少种正义和多少种合理性。〔19〕以此否认了现代规范伦理自我申言的那种唯一合法性和权威性。在《美德的追寻》一书中,他以一种更富挑战性的姿态提出了重返传统美德伦理即亚里士多德伦理的主张。
麦金太尔的理论信念是坚定而明确的:现代社会和现代道德的发展状况已经证明,人们对“现代性”(modernity)的崇尚是片面的, 其结果也是令人失望的。现代道德生活的深刻危机和现代道德理论的无公度性或不相容性事实提醒我们,一种自由个人主义的道德追求已经难以使我们获得一种对人类自我道德生活和观念的真实理解。我们必须返回到我们一直寄生其中的历史与传统,去寻找新的资源和灵感;必须求诸于我们生活其间的各种各样的和多层次的道德生活共同体(家庭、城市、群体、社团和联合体),去寻求完整的而非片面、实际的而非抽象的、具体特殊的而非普遍主义的道德理解。而重新解释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传统——即从人的道德共同体(城邦)生活与历史文化传统的复杂情景中理解人的美德生成和道德规则之间与之外,恰恰是现代伦理走出迷雾的一条有希望的道路。这也就是麦金太尔所谓之的“追寻美德”的美德伦理之路。
美国是当今西方哲学和伦理学的中心舞台。〔20〕从罗尔斯到麦金太尔,西方伦理学的发展又经历了从一种理论转向另一种理论的理路转型,并呈现出两种思维理路的对峙。就本文所论的主题而言,这两位伦理思想大家所代表的两次思维理路的转型,恰恰代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伦理学理论构成。如果说,罗尔斯所代表的是现代西方伦理从元理论分析型向社会实践规范型的转折;那么,麦金太尔则代表着从现代规范伦理向传统美德伦理的转型。如果说,罗尔斯对现代伦理的阶段性批判(现代功利主义和分析伦理学),导向了一种现代性规范伦理的重新决断和选择;那么,麦金太尔对现代伦理的全面批判,则导向了一种传统美德伦理的复归和选择。这是两种截然不同却又同样具有理论革命性的伦理类型选择。罗尔斯的选择使西方伦理学从某种形式的经院式纯理论游戏世界重返道德生活的现实世界,并用一种重释康德的方式把伦理学的理论视境凝聚在社会整体结构方面。麦金太尔的选择使(至少是力图使)西方伦理学的理论关切从单纯的现代性关切扩展到整个历史与传统的文化世界,从而使西方伦理学超越某种(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现代性的规则伦理范畴,重返真正的古典(经典)伦理学图式,即重返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图式。这才是罗尔斯和麦金太尔两次理论变革的基本意义。
三、道德类型学与现代伦理的选择:多元互补的综合解释
让我反复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进入20世纪后,西方的伦理学家们突然对道德或伦理的类型问题产生了如此广泛而浓厚的兴趣?从罗尔斯到麦金太尔短短的十余年间,西方伦理学竟出现了两次如此重大的理论转型,这究竟是何缘故?是否这也是一种世纪转型期的理论反应(这不能不让人联想起19世纪末期西方伦理发生动变的某些情形)?尽管解答这些问题已越出本文的题旨,但它们却触发了我对道德或伦理类型学与现代伦理问题的思考:现代社会条件下,人类究竟该选择什么样的道德生活样式和道德概念(理论)样式——如果确实存在着多种不同的道德生活与道德概念样式,且我们不得不作出这类选择的话——呢?在不同的道德和文化传统之间,道德或伦理的类型必然不同吗?若如此,它们是否能够求得某种公度并相互沟通呢?这是我在本文余下部分所要论及的问题,也是我对现代西方伦理学,特别是罗尔斯和麦金太尔两位大家有关道德或伦理类型问题之争的插话——在这一问题上,当代中国的伦理学者是应当也是有资格参与对话的,因为我们拥有足够丰富的道德传统资源贡献于这一课题。
从中国伦理学史和道德文化传统来看,道德或伦理的类型问题也是客观存在的。先秦时代的儒、道、墨诸子百家不仅在哲学义理上各有所旨,而且在道德伦理建构上也互有差别。孔、孟、荀等儒学宗师的仁德伦理强调的是“仁、义、礼、智”多面统合,是性情教化与礼义共达的内外贯通,是一种内在德性品格外化(“达德”)与外在礼法规则的内化(“成仁”)相统一的价值伦理类型。老、庄道学的本心自然之道德所旨,是一种摆脱社会尘世、复归自然天性的“道”得,是以无“得”而求有“德”、以“无为”而致“无不为”的守本固朴、畅达天然的自然型“心”德(得)。墨家的“功利主义”伦理是一种追求“志功合一”、“爱”“利”交融的目的论伦理,具有一种平等与平实的日常经验主义伦理风格。历史地看,儒家伦理曾在汉(经学)、宋明(理学)两个时期得到连续的扩充和发展,成为中国伦理文化传统的主脉,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道家伦理始终作为对儒家伦理过于强烈的入世主义的对应与消解因素而存在着,形成了中国伦理文化大传统中的一种内在紧张。而墨家伦理则从另一个侧面即实俗主义平民化的侧面对应和补充着儒家伦理。从道德类型学的理论角度看,儒家与道家的对应是价值目的论与本心自然论、道德理智主义或认知主义与道德反理智主义或非认知主义、道德行动主义(善达于身于性于家于国于天下)与道德自然主义(无为于世、有为于心于自然天成)的对应;而墨家与儒家的对应却反而成了社会道义论与个人目的论、或道德规范论与道德价值论的对应。所以,在一种不严格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儒家伦理归于美德伦理与规范伦理的外向混合型范畴;把道家伦理归于一种特殊的内向心得伦理(它不同于西方通常意义上的美德伦理)的范畴;把墨家伦理归于一种典型的目的论伦理范畴。
与西方伦理学发展的情形类似,道德类型学问题也是新近才为中国学者意识到的,不过比西方更晚一些罢了。就我的了解,关于道德类型的不同区分较早由王润生提出。他认为,道德历来有两种不同的类型,即“进取性道德”与“协调性道德”。前者是个人性外向性的,如“勇敢”、“自由”等等;后者是协调性、约束性的,如“仁义”等等。这种类型划分显然基于道德概念所内含的价值取向而非道德的一般理论特性或伦理学的理论探究方式。最近,在海外访学的当代著名学者李泽厚先生对道德类型问题发表了一种新的值得注意的看法,提出了“宗教性道德”与“社会性道德”的区分。他如此说道:“‘宗教性道德’和‘社会性道德’之作为道德,其相同点是,两者都是自己给行为立法,都是理性对自己的感性活动和感性存在的命令和规定,都表现为某种‘良知良能’的心理主动形式;……其区别在于,‘宗教性道德’是自己选择的终极关怀和安身立命,它是个体追求的最高价值,常与信仰相关系,好象是执行‘神’(其实是人类总体)的意志。‘社会性道德’则是某一时代社会中群体(民族、国家、集团、党派)的客观要求,而为个体所必须履行的责任、义务,常与法律、风习相关连。前者似绝对,却未必每一个人都能履行,它有关个人修养水平。后者似相对,却要求该群体的每个成员的坚决履行,而无关个体状况。对个体可以有‘宗教性道德’的期待,却不可强求;对个体必需有‘社会性道德’的规约,而不能例外。一个最高纲领,一个最低要求;一个是范导原理(RegulativePrinciple),一个是构造原理(Constructive Principle)。”〔21〕李泽厚的这种道德类型区分是一种泛文化意义上的区分,它涉及道德的功能和构造特性,进而涉及到道德的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议题,但不论道德的内在价值指向和理论路向。相反,他仍然是把道德作为一种规范形式(“命令和规定”)来看的,因而是对一种规范伦理的内部划分。
古今中外的道德类型学概念为我们进一步思考这一课题及其对理解现代伦理问题的意义提供了全面的参照。由此也使我们认识到,一方面,关于道德类型问题的多种不同概念表明,由于人们所取的角度不同,解释的方式不同,以及各自依托的文化传统与历史背景不同,对道德类型的区分方式、标准和具体表达也互不相同。这似乎印证了麦金太尔关于道德之文化传统与历史情景解释的主张。另一方面,每一个时代和每一个道德共同体都必须且必定形成自己的道德类型学概念,在这一点上,罗尔斯对现代西方自由主义规范伦理类型的忠诚与执着是有其合理性的。现在的问题是:是否存在某种确定和解释道德类型的基本原则与方式?现代社会条件下的基本伦理类型是怎样的?我们的现代道德必须在罗尔斯与麦金太尔之间进行选择吗?进而,我们的伦理学探究必须在元伦理、规范伦理、美德伦理之间作出选择吗?
答案是复杂的。让我们首先考虑道德类型学本身的基本理论问题。在我看来,无论中外伦理学的道德类型概念如何复杂多样,有几个基本的因素是共同的:第一,道德和伦理学基本领域、特性和方位的确认;第二,解释与论证的方式和标准;第三,道德的功能与意义之特定理解;第四,道德或伦理的文化背景预制和理解。第一、第二因素的作用可以从现代元伦理与规范伦理的分别中见出;而从当代美德伦理与规范伦理的对峙中,可以看到第二、第三和第四因素的作用。而“进取性道德”与“协调性道德”或“宗教性道德”与“社会性道德”的区分,主要是着眼于道德的功能本身而论的。由此可见,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或层面来进行道德和伦理的类型区分。这给我们寻找一个统一的道德类型学定义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在现代观念多元化的状况下,某种单一的道德类型学概念几乎已成为不可能企及的事情。然而,为了一种学理研究的需要,思想家个人预制某种基本概念系统仍然是允许的。因此,我们不妨尝试着给出一个道德类型学的初步定义。
所谓道德类型学(typology of morality)有两个基本意义:其一,它是一种依据某特定理论图式(这种理论图式往往带有思想家自身的理解和解释特征)来规定、区分和解释道德的特性、功能或作用,以及它作为一种特殊文化现象在人类生活中运作的特殊理解方式。这是一种文化现象学意义上的道德类型学。其二,它作为一种描述、解释、区分和论证关于道德现象之探究的理论方法论,表达着伦理学家所建构的特定道德哲学体系的样式。这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道德类型学,准确地说,它是一种伦理学类型理论。
实际上,道德类型学的两种意义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人们对道德自身特性、功能和实际运作的理解方式直接预制着他们建构自己伦理学体系的方式,后者不过是前者的理论概念化而已;两个方面实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同一码事,只是为了理论分析的需要所作的一种逻辑性划分。但是,两种理解又不能完全混同:因为,对道德的文化理解与哲学理解虽然都具有历史变化的性质,但道德的文化理解一般具有历史传统和现实直接的双重品格;而道德的哲学理解却一定程度上带有相对变化和间接的特点。也就是说,道德哲学的形成往往有着属于思想家自身时代的理论特征,这包括概念形式、语话系统、论证方式等等。柏拉图、康德、罗尔斯和麦金太尔的伦理学都有着他们各自不同的理论构建。罗尔斯所重视的正是这种理论建构方面:而麦金太尔则更重视理论与“历史事实”的同一性方面。这也就自然地推出,对人类道德现象的文化理解与哲学理解,实质上既是应当相对分开考虑又是不能截然分离的。了解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谈论现代伦理问题了。
从根本上说,罗尔斯与麦金太尔之间的争论是对现代社会与现代道德的不同理解和选择问题。罗尔斯对西方现代社会和现代道德的忠诚,表现出他对现代西方民主社会和现代西方自由主义价值精神的认可和忠诚。因此,他认定了西方现代社会的多元民主和规则法制化构成的合法性、优越性,并选择以规则伦理的形式来表达现代自由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即建立一套能够确保个人自由权利与平等发展的公正社会秩序和道德规则系统。在这里,个人的自由平等是根本的也是唯一的目的,而公正社会秩序(社会基本结构)和正义规则是保证实现这一目的的充分必要条件。没有这一条件,不仅个人的自由平等无法实现,而且甚至连人的基本正义道德感(作为最基本的个人美德)也不可能形成。但是,对于麦金太尔来说,现代社会和现代道德本身的合理性就是值得怀疑的。现代社会所呈现的严重道德分歧和现代伦理学所表现出来的概念无公度性或不相容性,使我们无法相信现代伦理本身能够给我们提供一种真正普遍的正义规则系统。因此,正如现代社会本身没有真正脱离人类固有的道德生活传统一样,现代伦理也不可能脱离传统的道德资源,否则,它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且,从更广阔的意义上看,西方现代自由主义者们所辩护和证明的所谓“现代性伦理”只是自我封闭性的,它并没有能够建立起与其它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对话,更不用说以某种亲近的姿态去承认其它文化传统的合法性了。这种姿态显然与西方现代伦理的多元性开放性主张相矛盾。
罗尔斯的学术态度和道德理论是完全西方化的、现代性的,因而也是哲学自辩性的。而麦金太尔的态度和理论则是综合性的、传统性的,因而也是文化批评的。我想再次指出的是,罗尔斯与麦金太尔的这些差异并不能成为我们对两者作出理论价值评价的全部依据甚至是基本依据。它们更应该被看成一种学理方式或风格的差异。但我们不得不说,罗尔斯理论的现代关切是对的。现代社会毕竟不同于传统社会,现代社会的道德问题毕竟不同于传统社会的道德问题。尽管我们难以描述出一幅为人们普遍公认的现代社会的特殊图景,但它特有的空前复杂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特征,决定了它必须是一种高度法制化规范化的社会,其给人所提供的自由条件、权利、机会也是任何传统社会所不能比拟的。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寻求(哪怕是通过高度技术性的重释)“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美德传统”能否满足现代人的道德生活需要?乃是令人疑虑的。然而,罗尔斯确乎忽略了两个对于其正义规则伦理(甚至是整个现代西方规范伦理)至关重要的理论问题:没有现代人自身的德性品格作为现代伦理运作的内在主体基础,道德规则(无论多么周全和系统)又如何得以实施?次之,当现代人强调自身与传统社会的脱离时,是否也有同样充足的理由宣称自身道德观念与传统道德观念的超然无关呢?人类道德观念的连续也许并不像人类对社会外部环境的改变那样可以使原有的一切面目全非,成为过眼烟云。相反,作为一种特殊的生活情感、一种文化心理的积淀、一种基本价值理念,道德的许多方面或意义却为古代人与现代人、甚至是为西方人与东方人所共享。这无需给予更多的哲学论证。它是一种文化和历史的真实,一种人类精神的存在。麦金太尔所关心的正是这些为罗尔斯所不太在意的方面,而在我看来,这又恰恰是麦氏理论的合理处。
话行至此,聪明的读者早已察出我的理论意图了。即原来我在本文中力图表达的不过是一种“调和式”的整合而已。不错,我意欲建立的道德类型学,正是某种意义上的罗尔斯与麦金太尔之论的合题。但对两种殊为不同的理论进行一种新的整合,所需要的决不只是一种意愿。它需要一种新的理论力量和一种足以通透融会两者的综合性视境。我关于罗尔斯规范伦理与麦金太尔美德伦理的合题之理据有以下四点:
首先,人类道德或伦理的一般构成与运作自身,必定且总是包括或表现为两个基本的方面:即我谓之的“道德的外化”与“道德的内化”方面。前者指“人类在文明进步中不断地通过社会文化的方式抽绎出特定的道德价值观念,并使之普遍化、客观化和社会化为一定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和相应的价值观念体系。”它表现为一种规范道德的构成形式和一种道德原则的论证过程。后者则指“人类(以个体为单位)在同一过程中不断通过自我的人性自觉和价值认同,将既定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和相应的社会价值观念系统个体化、特殊化和内在主体化。”他表现为一种美德伦理或人格品德构成形式和一种美德完善的过程。我认为:“道德之内化与外化是两个相向对应的动态过程,其间既有相互交错、相互促进的一面;又有相互抵触、相互矛盾的一面。前者表现为,道德的外化愈充分,或者说道德原则规范和相应之社会价值观念系统愈有社会合理性和客观普遍性,人们认同它们、接受它们、践行它们的可能性就愈大;反过来,一种较能为人们所认同接受和所践行的道德原则、规范、价值观念体系,就愈享有‘可普遍化性’(universalizability,黑尔语)和客观权威性。后者表现在,道德的外化程度愈高,其普遍性愈大,其客观性愈强,则其内化的过程就愈漫长、愈痛苦,所需要的主客观条件就愈高、愈复杂。这就是为什么一些人较容易认同、接受和履行家庭伦理规范,而对社会普遍性道德规范的认同和践行较为迟缓的缘故所在。”〔22〕道德的这种内在、内化和外在、外化构成形式与运作过程,是两个相互对应交会而又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若缺其内在内化方面,道德就会成为无主体基础的空洞规约,甚至于蜕变为法律和神学戒律(实际上,这也是罗尔斯本人在谈论善的“弱理论”与“充分理论”时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的〔23〕),如麦金太尔所言;若缺其外在外化方面,道德就无法获得普遍合理性证明,同样也会缺乏公度性(这对于麦金太尔来说是一个不幸的也是他所忽略了的事实),如罗尔斯所言。因此,完整的道德类型学概念必须是规范伦理与美德伦理的合题选择。
其次,现代伦理的种种教训表明,单一的规则伦理并不能真正满足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道德生活需要。“人类中心”和由此极推的“自我中心”的自由个人主义道德,造成了“现代性道德”的单面发展。规则伦理的特出,虽然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客观要求,却也是现代人无可奈何的消极承诺——过度的自由化和个人主义使道德规则和法律成了某种霍布斯式的非如此不可的强制,甚至是一种嗜好和癖性的“解毒剂”。自由无比的个人实际上不过是混身缠满规约之网的被动者。他们需要内心的平静和充实,需要找回古希腊人曾经有过的那种灵肉交融、内外统一的善生活追求。这便是规范伦理对美德伦理的现代呼唤。然则,这种现代性道德的内在求助,并不意味着规范伦理的穷途末路,它只是表明现代伦理应当重返人类道德的原始真义:心性完善的道德目的论追求与正当合理的道义规则、个人幸福与社会功利原本不可分割。
第三,综合完整的道德类型学概念将给现代科学的伦理学探究注入生机和动力。70年代以前,所谓元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和美德伦理学等等,各自为战、互不通容。这种状况极大地妨碍和伤害了现代伦理学探究的整合进程。但其后的发展逐渐显示出某种程度(尽管十分有限)的相互见纳趋势。罗尔斯的伦理学内容是规范性的,但他的方法却有着强烈的分析哲学色彩。麦金太尔的伦理选择是美德传统的,但这并不妨碍他极其老练地运用现代逻辑分析的方法来论证其伦理学主张。事实上,早在60年代像布兰特这样的新规则功利主义者,已经出现这种见纳情形。应当承认,无论是元伦理学,还是规范伦理学,抑或是美德伦理学,都反映着现代科学的伦理学探究之某一侧面,都有其合理性方面。所不同的是它们各自所取的理论视角、论证方式和理论构造。因此,没有理由在它们中间进行非此即彼的断然选择,倒是现代科学概念的进化提示我们,任何一种想获得较高合理性程度的理论,都应当具有一种综合开放的视境和外向沟通能力。一种理论类型往往有其特殊的理论发现。元伦理学的贡献是道德论证方法的严谨;规范伦理学的贡献是其对现代社会道德生活的本质把握;美德伦理学的贡献则主要在于它对人类自我的价值生活的目的论洞彻。三者(也许不止是这三者)各执千秋,若得以相互比照交融,必能相得益彰,达到多元互补。这一整合也许会历史地成为未来伦理学探究的一个共同而有益的课题。
第四,综合完整的道德类型学概念是当代世界性多元文化进行交流与对话的一个必要条件。传统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分殊并不是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特有现象。但多元的对话理解却是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特别需要的文化生存与思想交流方式。现代人视野的扩大与现代人世界的缩小,注定要把柏拉图学园式的对话和欧洲沙龙式的调侃延伸到社团、国家、民族之外,延伸到母语、传统、习惯之外。而历史表明,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着特属于自己的道德文化传统,都有着自己的话语系统和辩谈方式;因而也构成了各自不同的道德文化资源。从一种惯常的地域概念上讲,西方道德虽然有过为麦金太尔先生津津乐道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主义美德伦理传统”,但自古罗马以降,“律法主义”的道德思维方式就一直占据上风,与之相应的是规范伦理的长期主导。而以“道德文明古国”著称的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却蕴藏着丰富的美德伦理资源。尽管中西文明的进度、哲学思维方式、乃至话语系统等诸方面都存在差异,但在世界多元化交流和对话空前活跃的今天,尤其是在西方现代性伦理和中国古代传统伦理都面临挑战的今天,寻求不同类型的道德文化或伦理概念之间的对话,以分享对方有益的道德文化资源,不仅是需要的,也是可以期待的。正如麦金太尔教授在给《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一书的中译本所撰写的序言中谈到的那样:“这种对话很可能及时导向两种相互沟通的传统的一方或两方的信奉者们对他们自己迄今为止已确立的规范与标准作出一种内在批判,以便使一方或双方将对方的理智的与实践的文化规范方面和文化评价方面采纳到自己的理智的与实践的文化规范和文化评价之中。”〔24〕
不过,要实现这种跨文化的道德对话,首先必须有一种公正而全面的道德类型学概念系统,即承认各文化传统自身拥有的特殊道德类型的合法性,消除某种形式的价值优越论或道德文化上的专制主义;同时建立不同文化传统之不同道德类型间的相互平等和信任,并建立相互理解和辩谈的方式与适当语境。所以,我所预制的道德类型学概念不只是指向古典(传统)道德与现代道德之间的勾连,也要求有跨文化的沟通。这是我想就此一课题与罗尔斯和麦金太尔同时对话的用意所在。这种跨文化传统的道德对话,不仅需要有跨时空的视境超越,而且也需要有跨话语界限的相互理解。在方式上,则需要恪守多元互补、分层沟通、共同分享的原则,而不是强制统合或权威排斥。在这里,民族封闭与价值观念的霸权主义都不可取。鸣呼!
一九九五年八月中至九月初于北京大学燕北园悠斋
注释:
〔1〕本书英文原名为“After Virtue”, 该书中文版现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题为《德性之后》。以我的理解,似有不达,故译为《美德的追寻》。
〔2〕Alasdair MacIntyre.After Virtue,University of NorreDame Press,1982,the second edition,pp.150—152.
〔3〕Alasdair MacIntyre.Whose Justice? Which Rati nality?University of Norre Dame Press,1988,p.Ⅸ.
〔4 〕详见同上书及我为该书中译本所撰写的“中译本序言”——“美德伦理传统的叙述,重述与辩述”,尤其是第二部分。该书中译本由我主持译出,即将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5〕参阅After Virtue和Whose Justice? Which Rationality?两书。
〔6〕见拙著:《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上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一编,第一章第三节,第三章第三节。特别是第88—91页;第169—172页。
〔7〕见同上书,第408—410页。
〔8〕After Virtue,p.152.and also Whose Justice? WhichRationality?“Preface.”
〔9〕Whose Justice?Which Rationality?p.94.
〔10〕Giovanna Borradori,The American Philosopher,Th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p.137.
〔11〕Samuel Aybar,Joshua D.Harlan,and Won J.Lee,“JohnRawls:For The Record”in:The Harvard Review of Philosophy,Spring 1991.
〔12〕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 Mass.HarvardUniversity Press,1971,p.Ⅷ.
〔13〕John Rawls,Political Liberalism,New York,ColumbiaUniversity Press,1993.Part One,Lecture Ⅲ.
〔14〕A Theory of Justice,p.578.
〔15〕Cf.Ibid.pp.28—30.
〔16〕Ibid.p.280.
〔17〕After Virtue,pp.9—10.
〔18〕这正是麦金太尔教授在80年代撰写的两部伦理学代表作的书名。
〔19〕参见我为Whose Justic? Which Rutionality? 一书中译本所写的“中译本序言”。
〔20〕参见拙文:“美国当代社会伦理学新发展”,载《中国社会科学》(北京),1995年,第三期。
〔21〕李泽厚:“哲学探寻录(提纲之六)”,收入李中华、王守常编:《文化的回顾与展望》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第152—153页。
〔22〕见拙著:《伦理学新论——走向现代伦理》,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334—335页。
〔24〕Alasdair MacIntyre,“For Chinese Readers ”(致中国读者),见Whose Justic? Which Rationality?一书中译本,当代中国出版社即出。
标签:伦理学论文; 现代性论文; 文化论文; 道德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功利主义论文; 类型学论文; 康德哲学论文; 自由主义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