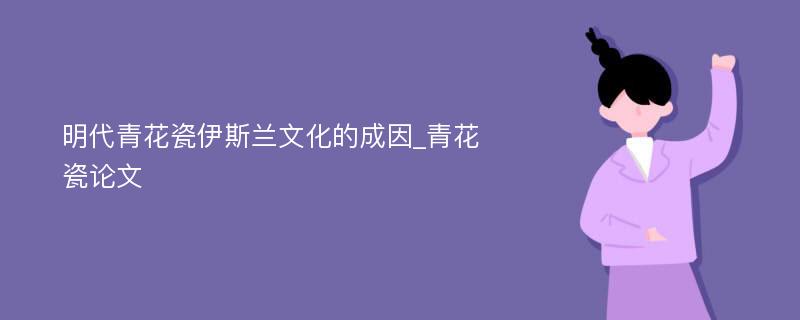
论明代青花瓷的伊斯兰文化成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论文,成因论文,明代论文,青花瓷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40(2008)05-0053-07
中外学术界对于明代青花瓷中的伊斯兰文化已有不少论述,但对明青花瓷中呈现出的伊斯兰文化的原因却叙述不清而且结论简单。①这些论述大多认为,明代宫廷,特别是明代中前期宫廷中的穆斯林宦官势力强大,他们要求御窑厂为自己生产瓷器,因而青花瓷在造型和装饰上呈现出明显的伊斯兰因素。②另一种说法源于日本著名古陶瓷学者三上次男,由于无法合理解释为什么埃及和中东地区的考古发掘中大量出现中国中世纪的青花瓷器,三上次男认为,这类瓷器“是应中东诸国的特殊要求而烧制的订货”,[1]明代官窑是为了满足外销定制的需要而烧制大量具有伊斯兰风格的瓷器。三上次男的上述观点得到国内一些学者的认同。③关于明代青花瓷的生产是为了满足外销定制还是供应内销,作者此前已有专文进行论述,结论是,明代中前期青花瓷的主要消费群体是宫廷和皇室。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主要讨论明代中前期青花瓷中伊斯兰文化的成因。
一
据史料记载,早在至元十五年(1278年),元廷即在景德镇设立了“浮梁瓷局”,相当于宋代的司务所,作为全国惟一的瓷业管理机构。④不过,除掌管烧造瓷器外,还负责漆造、马尾、棕藤、笠帽等事项,为蒙元统治者的军旅活动准备必需品,生产的瓷器比较单一,“非内廷供奉之需,而是政府机构的日用瓷。”[2]更有学者指出,元瓷尚白,青花瓷在元代并没有成为朝廷贡瓷,其理由是“现存清宫旧藏品中,既有宋代五大名瓷的贡品,也有明清两代各类御用瓷,惟独没有元代的青花瓷器。”⑤这种推论尽管有些武断,但至少可以说明,元代“浮梁瓷局”与明代景德镇御窑厂在体制和任务方面相当不同。⑥
明代景德镇御窑厂设立于洪武二年(1369年),清人蓝浦在《景德镇陶录》中记述:“洪武二年设厂于镇之珠山麓,制陶供尚方,称官窑,以别民窑。除大龙缸窑外,有青窑、色窑、风火窑……迨正德始称御器厂。”⑦景德镇官窑的瓷器烧造,多由宫廷派遣宦官或工部官员进行监督和管理,成品解送宫内或充入内府,特别是对产品的形制和纹饰有严格的规定,所谓“诸器官窑有其制”,“岁从部解式造。”[3]如,洪武六年,朱元璋严令在器皿上“不得彩画古先帝王后妃、圣贤人物、宫禁故事、日月、龙凤、狮子、麒麟、犀象等形……违者罪之。”[4]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又规定,“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样制。”[5]可见,御窑厂产品在种类、纹饰、式样和釉色等方面都要符合帝王的喜好和需要,体现他们的意旨。《明英宗实录》记,正统三年十二月丙寅“命都察院出榜,禁江西瓷器窑厂烧造官样青花白地瓷器于各地货卖及馈送官员之家。违者正犯处死,全家谪戍口外。”因此,作为“官样”的“青花白地瓷”是专为御用而生产的,并且禁止其在民间交流或作为官员间相互馈赠的礼品。
御窑厂的设立为明代青花瓷生产提供了比较稳定的生产环境和相对固定的消费群体,这就是宫廷和皇室,其中以供应宫廷需求为主,也就是说,“统治阶层集生产者和消费者于一身。”[6]所以,景德镇御窑厂集中了当时技艺一流的匠师,占用优质原料,其产品只求质量和纹饰效果,不计较工时和成本,因而烧制的瓷器品质精美。只要烧制的瓷器成品在造型、釉色效果或纹饰上不符合要求,都要被就地打碎深埋,不允许御窑厂生产的残次品和落选品流传到民间。景德镇御窑厂遗址的大面积发掘,出土了成吨的官窑瓷器碎片即是佐证。⑧不仅如此,明代帝王还禁止民窑仿制官窑的釉色纹样,禁止私自烧造“白地青花瓷器”。《明史》载,“正统元年,浮梁民进瓷器五万余,偿以钞,禁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瓷器,违者罪死。”⑨明廷禁止御窑厂生产的青花瓷器流落到民间,帝王们的这种态度值得揣摩,它意味着御窑厂烧制的青花瓷器在形制、纹饰或意旨上有其独特之处。
蒙元时期,中国与西亚中东地区有频繁的物质和文化交流,这些地区的制瓷技术和钴土颜料对于中国青花瓷在工艺上的突破具有关键性影响。但是,元青花瓷在制作技术上仍处于初步阶段,特别是元青花瓷上常常装饰有人物故事及动物图案,目前,尚未见到带有阿拉伯文或波斯文装饰的元代青花瓷。与元青花瓷相比较,明代中前期青花瓷在装饰题材上差异明显,洪武、永乐时期青花瓷没有描绘人物的纹饰,永乐、宣德时期青花瓷的动物纹饰也大量减少。⑩明青花瓷的造型式样,一开始就出现了明显的伊斯兰风格,如扁壶、抱月壶、折沿盆、天球瓶、军持、筒形花座以及穆斯林常用的执壶、盘等器物。绝大部分明初青花瓷在造型上可以溯源到西亚或中东地区古老的金属器、玻璃器或陶瓷器,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明代中期以后。(11)
同样,明初青花瓷在纹饰内容上也呈现了浓郁的伊斯兰韵味。许多永乐、宣德时期青花瓷的纹饰采用源于西亚地区的植物和花卉,通过抽象和变形成为主体纹饰。比如,“缠枝西番莲”就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图案装饰,在永宣青花瓷上广泛采用,(12)再有就是一种椭圆形的扁菊花、苜蓿花等也较常见。这些花卉和植物的枝叶在卷曲缠绕中变形,并且同时向两个或多个方向有规律地连续伸展蔓延,形成所谓“回回花”(Mohammedan Scrolls)。此外,精美的几何纹饰也常常出现在永宣青花瓷上。三上次男也认为,15世纪之后,中国在青釉瓷器方面发生了“伊朗式的变化”。[7]虽然明代中前期青花瓷的装饰风格还称不上“以伊斯兰文化为主体”,但是它们体现的伊斯兰文化倾向、借鉴伊斯兰民族的装饰方式却是明显而强烈的。最突出的莫过于从洪武到正德时期带有阿拉伯文或波斯文装饰的青花瓷器,(13)即西方学者所谓的“回回瓷器”(Mohammedan Wares)。[8]现存有碎片粘接的洪武时期的阿拉伯文青花碗,碗的内沿和外壁有类似阿拉伯文的装饰,永乐时期的青花波斯文卧足碗,宣德时期的阿拉伯文青花碗,天顺时期的青花波斯文三足炉,成化时期的青花阿拉伯文香炉,弘治时期的阿拉伯文青花盘等等。(14)
二
为什么青花瓷在明初会被指定为御用瓷?特别是明代中前期出现具有浓郁伊斯兰风格的青花瓷器?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指出,明代景德镇御窑厂由朝廷派遣宦官和工部官员驻厂监烧,其产品是用来满足宫廷、内府和皇室的需要,它们是官窑青花瓷的最终消费者,也是伊斯兰风格青花瓷器的最终拥有者。官方在推动青花瓷的生产、消费和技术发展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明代宫廷内身居高位的穆斯林宦官可能对官窑青花瓷呈现伊斯兰因素产生过影响,但这种影响至少得到了帝王们的认可或默许。青花瓷器在明初能被作为宫廷用瓷,这件事本身就值得重视。实际上,青花瓷的两种颜色即蓝、白两色并不是汉民族文化崇尚的颜色,但却是古代西域和波斯地区的流行颜色。著名伊朗裔法籍学者阿里·玛扎海里说,蓝色是“波斯和波斯血统民族的皇家颜色。”[9]因此,蓝色作为尊贵的颜色出现在波斯地区的宗教场所、王宫和丧葬仪式上。波斯各地清真寺的穹顶、门柱门楣以及外墙都不同程度地装饰着蓝色。此外,根据中国古代文献记载,西域各民族以及与之交往频繁的中亚、西亚各民族,他们对白色的认识与汉民族也存在差别,这些民族以白色为“吉色”。[10]经过长期尚蓝、尚白审美传统的积淀,蓝色和白色成为这些民族满足宗教、王权和风俗需要的色彩。这是中亚、波斯和中东地区喜爱“青白瓷器”的主要原因。三上次男的《陶瓷之路》中已经表明能够发现有大量中国青花瓷碎片的地方是宫殿废墟和清真寺遗址。伊朗阿德比尔神庙收藏的明代青花瓷除了阿巴斯大王自己的收藏外,还有一些是萨菲王朝贵族和重臣的收藏,而且他们通常在青花瓷上钻刻自己的印记,这表明,在中世纪的波斯地区,青花瓷是一种珍贵的财富。[11]与此形成对照,汉族士绅对青花瓷的审美态度曾经历过显著变化。青花瓷的色彩和釉下彩装饰技术与中国瓷器传统的单色调及刻画装饰差别很大,甚至可以说,青花瓷器的出现是与中国瓷器生产传统的一次决裂。在当时传统士人眼里,青花瓷器起初并不受欢迎,人们更喜好宋代以来流行的单色瓷器。(15)明人曹昭在成书于洪武二十年(1387年)的《格古要论》中记述“古饶瓷”时说:“御土窑者,体薄而润最好。有素折腰样、毛口者体虽薄(一作厚),色白且润,尤佳,其价低(一作抵)于定(器)。元朝烧小足印花者,内有‘枢府’字者高,新烧大者、足素者,欠润。有青色及五色花者,且俗甚矣。”英国人蒲柏认为,这是中原士人作品中最早提及青花瓷器的。(16)曹昭的描述反映了当时士人对青花瓷的态度,很显然这种新品瓷器不受汉族士绅的欢迎,他们认为,带有“青色”和“五色花”的瓷器显得非常粗俗。同样,《格古要论》对“大食窑”的评价是“以铜作身,用药烧成五色花者与拂郎嵌相似,尝见香炉花瓶合儿盏子之类,但可夫人闺阁中用,非士夫文房清玩也,又谓之鬼国窑。”(17)对“大食窑”作如是评价的士人想必不会对源自“大食窑”技术的“景泰蓝”有更好的看法,因为,此类具有浓郁异域风格的器物不符合生长于农耕文化氛围中士绅们的审美习惯。
《格古要论》中的观点是元末明初士绅们对青花瓷的代表性评价。这种评价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发生变化,到明代中期,人们已经会欣赏、喜爱青花瓷器,并对其给予较高评价了。明人张应文在《清秘藏》(1595年由其子出版)中赞誉宣德青花:“我朝宣庙窑器,质料细厚,隐隐桔皮纹起,冰裂鳝血纹者,几与官、汝窑敌。即暗花者、红花者、青花者,皆发古未有,为一代绝品。”(18)这种态度转化与宫廷皇室的推崇和喜好有很大关系。明代帝王早在明初就将青花瓷作为宫廷御用瓷,这已经突破了当时士人的审美传统。另外,明初青花瓷在烧制技术上还有相当的缺陷,远没有成熟,(19)特别是制作青花色彩的主要原料即钴土矿要从国外引进,《明会典》及《明实录》中常有“西域回夷”进贡“回回青”以供烧制御用青花瓷的记载。(20)景德镇御窑厂对进口“回青”或“苏离麻青”(Sulaimānī)的使用有严格规定。(21)然而,技术、原料和汉族士绅审美传统的限制都未能妨碍明代帝王对青花瓷器的偏爱和喜好,这其中很可能存在精神或宗教层面的推动因素。
三
苏沛权在其《青花瓷与中外文化交流》的博士论文中指出,唐三彩器物中开始出现的蓝彩釉料工艺一直到宋代“都没有在中土扎根”,蓝色彩釉在中土未能占得一席之地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内部市场需求,尤其是“皇室贵族的需求”。[12]元青花瓷虽然在制作技术上有所突破,但其伊斯兰因素并不明显,况且青花瓷在元代未被确定为宫廷用瓷。所以,探讨明代青花瓷中伊斯兰文化的形成原因,就应该深入研究明代帝王和宫廷喜好青花瓷的原因,特别是明代帝王与伊斯兰教的关系。这方面的相关史料在明代官方文献中很难寻找,《明武宗实录》只对正德十四年(1519年)明武宗以“镇国公”名义“禁民间蓄猪”事略有记载:“时上巡幸所至,禁民间蓄猪,远近屠杀殆尽,田家有产者,悉投诸水,是岁仪真丁祀,有司以羊代之。”[13]在非官方文献中有明太祖朱元璋的御制“至圣百字赞”和明成祖朱棣的名为“谕米里哈只”敕谕,它们曾被刻在多处清真礼拜寺的石碑上,作为清真寺的一种荣耀和受官方保护的象征。(22)这些材料部分佐证了明代帝王与伊斯兰教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国外文献中提供的相关史料,例如,《沙哈鲁遣使中国记》和《中国纪行》。(23)学术界对《沙哈鲁遣使中国记》的真实性比较肯定,该书记述了明代宫廷受帝王信任的穆斯林高官;皇帝在汗八里(北京)为穆斯林建造了一座清真寺;朱棣在接见使团时说:“因为他们的国王真正心向上帝,全能之主也就赐给他们大量美好的东西。”此外,朱棣每年要离开后宫,住在城外的一座“没有塑像和佛像”的“绿宫”中“礼拜上帝”。(24)《中国纪行》同样记载了中国皇帝在北京为穆斯林建造了4座清真寺,宫廷中有许多穆斯林太监,穆斯林大臣的地位比非穆斯林大臣的地位要高,特别是明武宗朱厚照曾梦见先知穆罕默德,信仰了伊斯兰教,针对大臣们的反对意见,他认为,信教是人的内心事务,不应受法律的约束。[14]该书第二章的附章“中国皇帝每年出宫的情况”还介绍了皇帝去清真寺的情形,每年在处决犯人之前,皇帝都要来到一座“朝向麦加的墙上刻有可兰经和真主名字”的清真寺礼拜,并且检查被判死刑犯人的执行情况。这座清真寺,张星烺先生认为,是北京牛街礼拜寺。[15]台湾马明道考证为现在的北京天坛,并且认为,天坛的名称就是阿拉伯国家清真寺汉文直译“天房”的转衍。[16]阿里·阿克巴尔认为,“从皇帝的某些行动看,他已转变成信奉伊斯兰教了,然而由于害怕丧失权利,他不能对此公开宣布。这是因为他的国家风俗和法规所决定的。”[17]《中国纪行》还记述了中国皇帝对穆斯林非常友好,“从穆斯林国家来的人比其他(国家)来的人得到优先照顾”,“身份也比其他人高”,宫廷内的穆斯林太监在皇帝面前集体做礼拜。[18]中国史料也有明代宫廷太监参与修建清真寺的记载,明代“四大回回官寺”之一的北京三里河清真寺,原名清真礼拜永寿寺,明万历己巳年修建,天启甲子年重修,其“重修清真寺碑记”有:“万历己巳夏,本教司礼监秉笔太监李寿,锦衣户侯董应允,协内外官庶教众各捐己资,……不饰图像,不事雕镂,……今岁次癸亥,时届朱明,钦差提督京城内外禁门地方巡城点军司礼监文书房太监金良辅,复虔诚装修,美轮美奂,烨然一新。”[19]三里河清真寺的创建人是万历年间的司礼监秉笔太监李寿,而且李寿为“本教”,可知他是位穆斯林。天启年重修的又是“钦差提督……司礼监文书房太监金良辅。”司礼监秉笔太监、文书房太监都是皇帝身边的贴身太监,手握重权,深得宠信。金良辅能出巨资“虔诚装修”清真寺,使其“美轮美奂,烨然一新”,说明他也是位虔诚的穆斯林。山西大同清真寺在明成化初年曾由钦差镇守太监谭公魏某“大恢其制,华故为新。”[20]河北大厂县北坞清真寺碑记有该寺“原系内翰侍御太监仰泉李公奋庸营造。”[21]李寿、金良辅等都是在宫廷中有相当影响的太监,他们修建清真寺的举动至少是得到了皇帝的认可,甚至是支持。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帝王对伊斯兰教的态度。
四
学术界对阿里·阿克巴尔是否亲身到过中国还存在不同观点,但无论是亲自游历或是根据传闻来写作《中国纪行》,中国皇帝倾向伊斯兰教这一点在当时中亚和波斯地区已相当流行。德国著名东方学家保尔·卡莱(Paul Kahle)教授认为,尽管在中国史料中未能找到,但阿里·阿克巴尔所记载的明代中期“有强烈伊斯兰影响这一事实是不容怀疑的。”[22]中国台湾学者林义民在研究《中国纪行》后表示,朱元璋所领导的起义军队里“大多数人是穆斯林家族的后代”,明王朝建立后,“新王朝的领导者执政期间把自己的伊斯兰信仰隐藏起来,并且开始秘密地做礼拜。”日本学者小田寿典则评价说,明武宗的离奇行为“出乎意料直率地暴露了明朝与穆斯林的亲密关系。”[23]前述法国学者阿里·玛扎海里在他的《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中详细注释了《沙哈鲁遣使中国记》和《中国纪行》,他认为,明代帝王“非常热衷于与穆斯林打交道”,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先知的宗教,这种亲伊斯兰情绪的最终目的似乎是企图使穆斯林教徒们奉大明为整个亚洲的‘算端’。”(25)“根据穆斯林教法(这是获得永久拯救的关键),穆斯林教徒们只有在中国皇帝本人也是穆斯林时才能成为他的‘臣民’。因此,为了确保其穆斯林‘臣民们’的忠诚,大明王朝曾试图以标准‘算端国’自居。”(26)
中国学者在研究明代回回瓷器时也注意到一种带“大明正德年制”6字楷款的青花《古兰经》经文瓷牌,(27)瓷牌上的经文是《古兰经》七十二章第十八、十九和二十节经文——“一切清真寺都是真主的,故你们应当祈祷真主,不要祈祷任何物”,“当真主的仆人起来祈祷他的时候,他们几乎群起而攻之”,“你说:‘我只祈祷我的主,我不以任何物配他’。”有学者认为《古兰经》七十二章十八节经文常与礼拜地点有关,因此,这种《古兰经》文瓷牌应该放在清真寺或礼拜室内,甚至是圣龛(米哈拉布)内。同时,作为正德时期官窑的产品,这种瓷牌应是“供宫廷官用或是御用”,所以,明代宫廷内很可能“备有礼拜的地方或者举行宗教仪式。”[24]此外,明代青铜器上也出现有伊斯兰装饰和阿拉伯铭文。王建平教授对美国芝加哥博物馆收藏的明代伊斯兰青铜器皿进行过研究,并且撰文介绍过其中6件。这6件青铜器皿都是美国东方学家巴托尔德·劳费尔(Berthold Laufer)于1908年至1910年期间在西安的清真寺收购的,它们都带有伊斯兰装饰或阿拉伯铭文。铭文的内容大都是伊斯兰清真言,其中一件青铜香炉底部刻有“大明宣德五年监督工部官员吴邦佐造”的铜铸阳文印文,另一件青铜香炉底部铸有“大明宣德六年工部尚书臣吴邦佐监造”的印文。[25]这种香炉应当是进献给宫廷皇室的,是供皇家使用的礼仪用品。据此,我们可以推断,至迟在宣德年间就有专门为宫廷生产伊斯兰风格器皿的御用铸铜厂。
英国著名古陶瓷学者哈里·加纳(Harty Garner)指出:“中国陶瓷史表明,在特定时期里处于支配地位的宗教能对瓷器生产施加影响。”[26]青花瓷代表了明代瓷器制作的最高水平,白地蓝花的装饰效果寓意纯洁、高尚、凝重,非常适合广大穆斯林的审美需求。明王朝建立后不久就确定青花瓷作为宫廷用瓷,通过官方垄断原料和装饰式样的景德镇御窑厂来批量生产,不惜工时和成本,产品也只供宫廷消费或内府需求。因此,明代青花瓷器中的伊斯兰文化与明廷的推动,特别是明代帝王的喜好有很大关系。虽然明代帝王与伊斯兰教的关系大多是间接的,尚不能够清晰地说明问题,但它有助于我们深入探讨明代青花瓷中的伊斯兰文化。实际上,青花瓷在古代波斯地区“不是一般民众日常生活器物,而是含有一定的政教色彩,与清真寺、陵墓、皇宫等建筑艺术风格相配套的高级瓷品。”(28)三上次男的《陶瓷之路》对此作了印证。有意思的是,《明会典》卷二零一记载,洪武二年,定祭器皆用瓷。而且从官窑瓷器的烧制品种来看,明代宫廷祭祀用瓷也主要是青花瓷。
注释:
①青花瓷,《明史·外国传》称“青花白地”或“白地青花”瓷,或“青花白瓷”、“白瓷青花”。学术界一般认为,青花瓷是以氧化钴为呈色剂,直接在瓷胎上描画装饰图案后,外罩透明釉,在1300℃左右的高温窑炉里一次烧成的釉下彩瓷器。本文所讨论的青花瓷主要是指明代官窑生产的青花瓷器。
②参见马希桂:《中国青花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173页。德国著名东方学着保尔卡莱(Paul Kahle)教授认为,明代带有阿拉伯文字装饰的瓷器首先是为宫廷中身居高位的穆斯林宦官烧制的,见阿里·阿克巴尔:《中国纪行》,张至善编译,三联书店,1988年3月版第205页。See also W.B.R.Neave-Hill,Chinese Ccramies.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75,p.120.And also Duncan Macintosh,Chinese Blue & White Porcelain(2nd edition).Rutland,Vermont:Charles E.Tuttle Company,Inc.,1977,p.49.
③王健华:《永乐、宣德朝青花瓷的独特风格》,载王春瑜主编的《明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317页。苏沛权:《青花瓷与中外文化交流》,暨南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第72页。
④(明)宋濂:《元史》百官志四,卷八十八载:“浮梁瓷局,秩正九品,至元十五年立,掌烧造瓷器,……大使、副使各一员。”
⑤陈行一:《元青花器型与胎釉特色简论》,载郭景坤主编的《02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论文集》,上海科学技本文献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第495~501页。根据考古资料,景德镇生产青花瓷的起始年代应为元延祐六年(1319),参见暨南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苏沛权:《青花瓷与中外文化交流》,第68页。
⑥清人蓝浦在《景德镇陶录》卷五“景德镇历代窑考”中记述:“元改宋监镇官为提领,至泰定(1328年)后,又以本路总管监陶。皆有命则供,否则止,税课而已,故惟民窑著胜,然亦无多传名者。”
⑦同上书,第63~64页。清乾隆七年李洊德、汪勋编纂的《浮梁县志》“建置景德镇厂署”条谓:“御器厂建于里仁都珠山之南,洪武二年设厂制陶以供尚方之用。”另外,1994年景德镇珠山东门头出土了数十件洪武官窑青花瓷。据此可以认为,洪武二年设置的御用官窑是可信的。
⑧刘新园等:《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明、清御窑遗址考古发掘或重大成果》,载中国古陶瓷学会编的《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十辑),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版,第240~248页。另参见香港艺术馆编:《景德镇朱山出土永乐宣德官窑瓷器展》,香港市政局出版社,1989版。
⑨(清)张廷玉等:《明史》食货志卷二十八,中华书局,1997年11月版。《明英宗实录》记,正统十二年十二月甲戌(1447年)“禁江西饶州府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瓷器。命都察院榜谕其处,有敢仍冒前禁者,首犯凌迟处死,籍其家赀,丁男充军边卫。知而不以告者,连坐。”
⑩带有宣德款识的青花瓷多为明代后期或清代仿品,有些也绘有人物或动物纹饰。
(11)Soame Janyns,Ming Pottery and Porcelain.London:Faber and Faber Limited,1953.See also Basil Gray,‘The Influenee of Near Eastern Metalwork on Chinese Ceramics’,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s Society,Vol.18(1940-1941).另见王健华:《明初青花瓷发展的原因及特点》,刊《故宫博物院院刊》,1998年第1期,第75~82页。
(12)西番莲即Zndian Sacred Lotus,一般以大丽花(dahlia)唤作西番莲。参见傅振伦:《〈陶说〉译注》,轻工业出版社,1984年8月第1版,第239页注。
(13)从现有的考古发掘来看,我国最早出现阿拉伯文装饰的瓷器是1980年扬州博物馆在肖家山地段发现的一件青釉绿彩扁瓷壶,壶的正面有一组绿釉彩饰的阿拉伯文,其意为“真主至大。”从胎质和工艺看,这件扁壶是我国唐代长沙铜官窑的产品,烧制年代应在中晚唐时期。参见朱江:《扬州出土的唐代阿拉伯文背水瓷壶》,载《文物》,1983年第2期,第95页。
(14)有学者认为,尽管隆庆、万历时期回青已绝,其青花质量不及嘉靖时期,但回回文装饰,仍有保留。不过笔者尚未见到实物或相关论述。参见吴仁敬,辛安潮:《中国陶瓷史》,商务印书馆发行,1936年版,第67页。
(15)元人蒋祈《陶纪略》云:“景德镇陶昔三百余座,埏埴之器,潔白不疵,故鬻於他所,皆有饶玉之称。其视真定红瓷,龙泉青秘,相竞奇矣。”可见景德镇原来主要烧制单色的白瓷,称为“饶玉”的白瓷非常受人喜爱。
(16)See Pope,op.cit.,pp.43~44.瓷器上最早写有“青花”的是阿德比尔神庙收藏的永乐时期一件青花莲草纹折沿盘,盘底有毛笔书写的43个汉字,大多数汉字难以识别,但开头“青花”二字十分清晰,这也是迄今所知“青花”称谓的最早出现。See Pope,op.cit.,Appendix,Plate 30.
(17)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十(明)曹昭:《格古要论》(三卷版)卷中“古饶器”、“大食窑”。
(18)(明)张应文:《清秘藏》,商务印书馆影印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872册,卷上。转引自冯先铭主编的《中国古陶瓷文献集释》(上),艺术家出版社(台北),2000年版,第84页。
(19)明代早期青花瓷在制作技术上存在明显缺陷,青花发色不稳定,常出现黑色条纹、黑色块纹以及由于所应用的颜料太浓稠而结晶析出引起的‘颜料堆积’也就是“晕散”现象。“这些由于技术上不成熟而引起的特点给早期青花瓷器以特色,吸引着许多收藏者。”这些特征是鉴别早期青花瓷的重要标志,也是明代后期和清代陶匠们竭力模仿的对象。“直到十五世纪后半期,在成化,陶工才能较好地控制青花的呈色,……到了正德朝,高质量的稳定的蓝色终于被人们所掌握。”参见(英)哈里·加纳:《东方的青花瓷》叶文程,罗立华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72页。
(20)一直到万历年间,明廷还命甘肃巡抚设法收购回青,以便应急烧造御用瓷器。《明神宗实录》卷301载:“万历二十四年,闰八月癸未,先是奏回青出土鲁番异域,去京师万余里,去嘉峪关数千里,而御用回青系西域回夷大小进贡,卖之甚难,因命甘肃巡抚田乐设法召买进解,以应烧造急用,不许迟误。”
(21)明人王宗沐编纂的《江西大志》(明嘉靖三十五年刻本)卷七“回青”详细叙述了“敲青”、“淘青”、“画青”、“验青”等程序以防止陶匠们“偷出回青”。
(22)刘智:《天方至圣实录》卷二十“御制至圣百字赞”“敕诰清修寺护持文”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印。
(23)1419年10月波斯国王米尔咱·沙哈鲁派遣使团出使大明王朝,1422年8月使团返回。随行画师火者·盖耶速丁记录下了这次出使经历,即《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何高济译,中华书局,2002年第1版。《中国纪行》是中亚人赛义德·阿里·阿克巴尔1516年在奥斯曼帝国都城君士坦丁堡用波斯文写的有关中国的记述,李约瑟认为《中国纪行》是“一件重要的文献”,它说明了“十六世纪初期波斯人对中国的知识。”张志善认为,阿里·阿克巴尔是某个波斯使团成员,大约在公元1500年左右来到中国,保尔·卡莱认为,阿克巴尔在中国经历了1506年明孝宗弘治与明武宗正德之间的袭位,并且“在中国度过了几个年头”。见张至善编译的《中国纪行》,三联书店,1988年3月版第1,47,202页。
(24)《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何高济译,中华书局,2002年第1版,第126~127,133页。玛扎海里在对后一件事的注释中称这座“绿宫”是“青色的楼阁”,并认为,它可以被当作“清真寺”,因为其中没有“任何画像和任何偶像”。参见(法)阿里·玛扎海里:《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耿昇译,中华书局,1993年6月第1版,第97页注118。
(25)(法)阿里·玛扎海里:《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耿昇译,中华书局,1993年6月第1版,第124~125页。该书第28~30页刊载两封大明永乐皇帝致察合台汗国沙哈鲁算端的两封国书译文,其中有:“朕以神法而治天下”,“(尔是)敬畏和尊重上天的算端,为此原因,上天匡扶尔维持王位。”
(26)同⑧,第169页注2。
(27)英国伦敦大学戴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Percival David Foundatiton of Chinese Art)收藏有一件这种瓷牌。戴维德基金会还收藏有一件带“大明弘治年制”6字款的青花盘,盘内沿一周和盘心的5个圈内装饰有阿拉伯文。蒲柏认为盘上的阿拉伯文装饰“显然是中国人写的,或者至少是不太熟悉阿拉伯文书法的人写的”,可能译为:“侯赛因是真理”或“侯赛因无人匹敌”,这是在赞美穆圣的孙子。它显示明代中期景德镇御窑厂已经有了忠诚的什叶派信徒。See Pope,op,cit,pp.55.
(28)苏沛权博士学位论文,第102页。
标签:青花瓷论文; 伊斯兰文化论文; 景德镇青花瓷论文; 中国瓷器论文; 官窑瓷器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明代青花瓷器论文; 清代瓷器论文; 陶瓷论文; 唐代瓷器论文; 明朝论文; 古兰经论文; 穆斯林论文; 瓷都论文; 波斯论文; 格古要论论文; 阿拉伯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