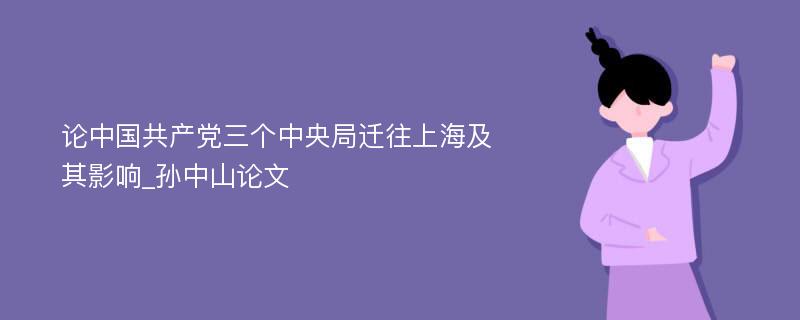
论中共三大中央局的迁往上海及其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大论文,上海论文,中共论文,迁往论文,中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1;D2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3)-11-0054-11
中国共产党在其早期的发展史上,因为革命重心及方式问题发生了许多激烈的争论。国民党一大(1924年初)前,中共党内的大范围论争围绕着与国民党的关系展开,此事在国共合作正式确立后犹有余响①。而与此直接相关的围绕中共中央驻地问题的争论,不仅关系到革命盟友的选择,也与早期中共对全国革命形势的认识相关联。再则,上海、北京、广州三城市,当日各有其政治文化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中共中央革命工作的可能方向,同时也对中共的革命思想和方式产生了一定的形塑作用。因而,欲了解早期中共的革命重心及其方式的变化,关于驻地的争论也是一个重要的认知角度。
中共三大中央局②由广州迁到上海,在党史上是个重要的事件,它反映了国共两党初步走向合作时的曲折。学界对此也不乏关注者③,对了解此事的概况做了一些工作。然而,此次中共中央迁往上海所引发的政治影响以及中共在上海的工作状况迄今尚乏专门探讨。即使是受到关注的迁沪时间和原因问题,仍值得进一步考证、探究。本文旨在考察中共三大后中央局迁往上海的前后因缘,依据各种材料分析其政治影响。笔者认为,考虑到半年后的国民党一大召开及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所产生的深远政治影响,考察中共中央局迁往上海的相关情形对认识此时两党关系是颇为重要的。中共三大后中央局驻地迁往上海并非是个偶然的事件,它与此前关于中共中央驻地问题的争论相互关联,又受到当时复杂的国共两党关系的直接影响。在复杂的情势下,中共中央驻地迁往上海是一个十分仓促的决定。或因此对上海的形势估计不足,造成了中央局迁沪后极为被动的局势。概言之,与国民党合作初步尝试的不顺利、经费的匮乏及党内的意见纷争等,使中共三大预定的许多工作陷入困境。对于鲍罗廷在广州所推动的国民党改组,中共中央局没有参与,更谈不上重视。但中共中央局在上海的这一境遇为中共知识分子独立探索中国革命之路提供了难得的机会。陈独秀等人开始尝试于国民党之外寻找新的“革命盟友”,此前设想的“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在此获得发展的良机。
一、上海与广州:关于中共中央驻地问题的持续争辩
上海这座城市,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它不仅是中国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中心,更是共产主义组织的诞生地。中共早期的几乎一切事业都与上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④。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曾指出:“上海是该处在当地全部工作的集合点”,“是朝共中央和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也集中了同日本的联系”⑤。这是与上海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有关的。有学者将上海在近代中国的地位归纳为以下几点:“全国特大城市,最大港口,对外交往基地,近代化起步最早、程度最高,多功能经济中心,全国文化中心之一”。由于外国租界的长期存在,“使得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出现了一道缝隙”,“形成反政府力量可以利用的政治空间”。⑥近代中国的各种革新力量,从维新党、同盟会到中国共产党等都极注重上海这种相对自由的政治空间,开展其革命活动。共产国际也利用其便捷的交通和国际性开展东亚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进行跟踪监视的于伦贝克总检察长说:“上海在某种程度上已开始成为一种极端主义在远东政治活动的中心”,“上海这座城市是东亚少有的可容政治上的不良分子十分顺利的找到栖息之地的几个大城市之一”⑦。马林后来到了北京,也觉得上海比北京自由得多⑧。于是,上海成为众皆认可的共产党活动中心。
但是,马林很快便看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广州的政治优势。当他到达广州,并与孙中山初步接触以后,发现“广州是唯一勿需打扰当局便可以建立常设代表处的城市”,“它对于通过香港同三个国家(中国、日本、朝鲜——引者注)联系也十分有利”⑨。共产国际代表利金和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也都持相近观点。他们认为,在孙中山占领下的广州,能为中共开展群众运动提供“合法条件”,因而都主张将中共中央驻地迁往广州⑩。这当然也与他们联合国民党的设想是分不开的。1922年3月,马林便提议“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11),还向“党的领导机关建议把驻地迁移到广州”(12)。然而,这些建议却不被中共的同事所赞许。
陈独秀综合中共的各项反对意见,写信给共产国际的维经斯基,表达了反对加入国民党的建议,也不会同意将中央迁到广州的主张(13)。达林曾建议将团中央驻地设在广州,也遭到了陈氏的当场回绝(14)。1922年6月15日,中共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15)。这是中共自身所能接受的联合方式,与马林等人的主张不同。但在莫斯科,中共的意见没有受到重视(16)。共产国际只依据马林的报告,于1922年7月18日以命令的形式要求中共中央将驻地迁往广州(17)。此时,季诺维也夫和维经斯基也都认为“把中央委员会迁到广州,那里是更适于广泛合法地开展工作的地方”(18)。但莫斯科不知道的是,广东的局势在一个多月前已经发生了变化。6月16日,陈炯明事件发生,让“迁往广州”的主张失去现实的可能性,这一命令成了一纸空文。
中共之所以反对将驻地迁往广州,一方面固然是反对马林等人提出“加入国民党”的主张,另一方面也包含着对广州复杂的军政局势的认识。比较而言,在对孙中山和广东政权的认识上,共产国际的代表们都不免有一定的误区,与事实相左(19)。陈独秀等人熟悉广东的局势,对孙中山也有多年的了解,他感到苏俄人的提议都不切实际。陈炯明事件印证了中共对广州局势的判断,也证明了陈独秀有着比马林等人更深刻的洞察力。若早依马林的见解,中共中央必定会在陈炯明事件中陷入危机,至少是进退两难的境地。
随着中共群众运动的逐步展开,上海作为中共活动的中心,也显出一些问题。中共二大后,在上海的党组织屡遭变故,先是陈独秀被捕入狱,继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又遭查封。1922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将总部迁往北京,由邓中夏任主任(20)。当年11月底,《向导》周报编辑部迁往北京(21),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似皆于此时离开上海,中共的活动中心也就转移到了北京。1923年1月下旬,苏联政府代表越飞南下上海,与孙中山会谈。越飞对上海的印象不错,但“不满意上海宣传共产主义的现状”,因而“打算从北京调12名经过训练的中国的共产主义宣传员来加强本地煽动者的力量”(22)。有意思的是,中共中央离开上海,很重要的原因可能来自越飞的要求(23)。等从北京到了上海之后,越飞才认识到上海的优势条件。然而,在此前后关于中央驻地及同国民党关系问题正在莫斯科吵得不可开交。
1922年11月,陈独秀正率领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陈独秀发言指出,中国国民党虽号称有十万党员,但多数并不在党内;在党内者,除了基层的劳动群众以外,大都是些钻营政客和官僚。这个党没有纲领,也没有章程,甚至连有形的组织也找不到,一切全靠孙中山个人的号召力和宣布的计划行事,其理论上更不相信群众,只迷信武力。(24)刘仁静也认为,“它(国民党——引者注)不对群众开展宣传运动,不试图去组织群众,它唯一的企图就是通过军事力量来达到他的目标”,而且“多数党员的本质是反动的”(25)。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代表的发言对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中国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6)。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指出:“如果说张作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附庸,因此引起中国所有民族革命分子对他的敌视,那么,一刻也不应忘记,昔日南方民主政府的首脑——孙逸仙过去和现在都在与张作霖联手合作”,“中国共产党不应屈从于中国资产阶级所建立的这些中心中的任何一个,即使这些中心的领导者具有半民主的或者甚至民粹的性质”(27)。这显然与8月指令称“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组织”(28)有所不同。共产国际四大的界定,无疑是对马林推动的联合国民党的方式进行调整(29)。或正因与中共代表团的直接接触,让维经斯基等人改变了对国民党的认识。
1922年12月下旬,马林到达莫斯科以后,中共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又引发了激烈辩论。马林报告说,中国共产党加入中国国民党的问题“没有遇到激烈反对”、党内“几乎没有遭到任何反对而被通过”(30),这当然是不符合事实的。1923年1月6日的会议上,共产国际执委会重点讨论了国共关系问题,马林与维经斯基形成了相反的意见(31)。后由布哈林进行折中,最终形成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该决议照顾了两方面的意见,但本身是充满矛盾与歧义的。它确认“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却又指出,“中国共产党特殊而重要的任务,应当是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建立工会,以便为强大的群众性组织准备基础”(32)。这样的决议为争论双方都提供了依据,直接导致中共三大上马林与张国焘的大争论。
两个月后(1923年2月7日),二七惨案的发生,造成了迥然不同的新形势。中共一年多来辛苦构筑的铁路工人组织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此前被寄予厚望的吴佩孚忽然成为最危险的仇敌,这在中共多少是有些始料未及的(33)。北京已不能容许共产党组织的存在,上海报纸上也出现了不利于共产党的言论,任何风吹草动都不免引起租界当局的注意。考虑到很快就要召集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需要一个较为安定的环境,上海已非最优的选择。3月份,国民党在广州逐渐立足,能为中共的活动暂时提供一个合法安全的政治环境,中共中央乃接受马林的建议决定将驻地迁往广州,在那里筹备并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然而,维经斯基似乎没有注意到二七惨案后的形势变化,仍继续着原有的思维。1923年3月8日,维氏告诉萨法罗夫:“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迁往广州的决定现在恰恰是不妥当的。在诸如汉口、上海、北京这样一些作为罢工运动主要据点的城市里,必须有最大数量的中央委员。总之,应该使自己永远明白,华中和华北是中国当代工人运动的主要基地”(34)。次日,在给马林的信中,又说:“看来尊意在把中国共产党全部积极分子迁至南方”,“但是就我所知,现在十分需要有一些积极性很高的同志留在汉口、上海和北京”(35)。3月24日,他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的报告中又说:“听马林说,在汉口罢工遭到破坏后,我们的人情绪非常沮丧,对今后工作的前景看得过分悲观。这是中央在几星期内作出的关于中央所在地和党的力量分布问题的自相矛盾的决定的部分原因”(36)。
其实,维经斯基信中所说“中央迁往广州”面临的问题,一直也在中共中央的考虑之中。但二七惨案对中共刚刚起步的群众工作打击太大,全国罢工的形势也远非维经斯基所认为的那样乐观。于是,中共中央在上海短暂逗留之后,便于4月中下旬迁往广州了。到了5月份,据在上海的维尔德在一封信中说:“工作重心移到了广州,这里几乎一个中国工作人员也没有留下”(37)。维氏反对将中央驻地迁往广州,主要是基于他对国民党和孙中山的判断,反对把共产党的工作纳入到国民党之下。在这一点上中共中央内部的很多人(包括陈独秀)和维氏是有相似见解的,并不因驻地迁到广州而改变。
二、希望与失望:中共三大中央局在广州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议最重要议题仍是“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虽然西湖会议上对此问题已有讨论,但反对的意见无法掩盖(38)。会议前,党内已有“陈独秀或我(马林——引者注)想解散我们的党这样一种观点”(39),会上更是唇枪舌剑。在这场激烈的争论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个人态度的转变。陈独秀与马林站在一起,旨在推动全党加入到国民党中去。这一转变或可能是在莫斯科受到狄拉克等人的影响,但根本原因当是二七惨案以后他对工人的失望(40)。他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也明明知道此种民主革命的成功诚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然而幼稚的无产阶级目前只有在此胜利之奋斗中才有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所以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合作,也是中国无产阶级目前必由之路”(41)。随着中共三大的召开,他的这一设想,也将整个党的工作带上了“国民党的马车”。
中共三大上,经过激烈的争辩,正式确认与国民党合作的策略,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议决案认为:“中国劳动阶级还在极幼稚的时代,多数劳动群众之意识,还停顿在宗法社会,非政治的倾向非常之重,只有少数产业工人已感觉国民运动之必要,真能了解共产主义及共产党组织的更是少数,因此工人运动,尚未能强大起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势力,以应目前革命之需要。”“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42)这是直接针对蔡和森等人建设工人群众政党设想的。此后,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国民革命和国民党方面。马林和陈独秀制定了国民党改组案,尝试纠正国民党忽视群众工作的问题。这些工作的展开自然是以广州为便利。这也是马林一贯的主张。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上的报告中也感慨,“我们不得不经常改换中央所在地,这使我们的工作受到了严重损失”(43)。陈独秀也是设想将中共中央长驻广州的,至少在中共三大上,尚未见有资料显示中共中央有迁上海的意向。
广州虽然也存在许多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共来讲,却是一个可以合法存在并且相对自由展开活动的城市。同时,半年多来的奔波不定使中共认识到一个稳定驻地的重要性。中共中央在广州的两个多月中,不仅成功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而且宣传事业也上了一个新台阶。除了《向导》周报外,又有《先锋》在广州创刊发行,停刊已久的《新青年》也以季刊的形式再次与读者见面。但中共三大后不久,中共中央局和马林突然又准备将驻地迁往上海(44)。其中的曲折值得注意。
实际上,自从马林到达广州后便开始专注于国民党的改组,曾和陈独秀拟定了一个详细方案(45)。但是,该方案在实际的工作中却遭遇到诸多困难。广州的形势并不稳定,故孙中山坚持先解决广州的军事困扰,然后再开展改组工作。关于军事行动和政治改组孰先孰后的问题,马林和孙中山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为此,马林先后两次会见孙中山,建议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抓紧国民党改组,但遭到了孙中山和廖仲恺的冷遇(46)。6月19日,马林再访孙中山,说“鉴于目前北京的危机,必须往上海一行,必须设法抓住反对北庭运动的领导权”。他再次碰了钉子,孙中山觉得“这并不重要”。(47)此时,新一届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也联名致函孙中山,“要求他在华南停止军事行动,到上海去,组织工、商、学的国民会议,把现有的各[农民]联合会组织成为农村自治政府”(48)。陈独秀和李大钊也曾设法同孙中山谈一次话,希望他就去上海的问题“尽快做出一个决定”(49)。中共的机关报《向导》对国民党也有连篇累牍的批评,希望扭转孙中山的态度。但这一切非但毫无结果,反而加剧了与孙中山的紧张关系。
面对孙中山的固执和愤怒,马林和中共对国民党的改组工作渐由失望至于绝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离开广州,预备在上海开展独立的工作。1923年7月2日,中共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秘书毛泽东致信共产国际,报告中共三大及其以后的活动情况,说:“此次会议后,我们决定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机关搬到上海工作,这不仅因为上海是工业最发展的中心区,而且也便于对全国工作进行指导和传达。”(50)马林则对越飞吐露:“我们的中国同志已经决定把驻地迁往上海,因为他们在广州做不了很多事情,想在北方建立新的组织,后者的任务将是:或者是国民党急剧地改变当前的看法;或者建立一个新的国民党”(51)。此外,他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声言,“中央委员会宁愿在上海处于非法地位,也不愿在广州公开活动,因为上海的意义更加重要”(52)。
总的说来,与孙中山关系的恶化,让中共中央在广州已经“做不了很多事情”。这当是中央迁往上海的主要原因。不过,在广州时马林与孙中山关系恶化、国共两党关系不和谐却也是表象,似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日本学者北村稔在其专著《第一次国共合作の研究》中指出,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国共关系的决议与1月26日发布的《孙文越飞宣言》有根本矛盾之处。前者要求中共党员在加入国民党后“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后者在开头便宣布“共产组织,甚至苏菲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否认了共产党员活动在中国的可能性。这反映了在即将建立的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共产国际、苏联政府、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四者在根本思想和立场上的不一致(53)。正是这种矛盾和差异,造成了马林、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孙中山在改组问题上的分歧以及关系的恶化。
此外,中共中央在广州还面临语言的隔阂,虽是小节,却也不可忽视。粤语和普通话之间差别巨大,有时甚至同于中、外文的隔膜。达林回忆说:“我谈了一个想法,认为把工作中心转移到广州比较适合。但是同志们不同意,于是决定把团中央仍设在上海。看来语言的障碍在这个问题上起了一定作用。过去有过这样的情况,在瞿秋白与懂英文的广东代表谈话时需要我当翻译。瞿秋白说俄文时我把它翻译成英文,然后再这样翻过来。”张国焘在广州开会时也说,“南方人听不懂我的北方话,翻译过去又歪曲了我的意思”。(54)这种情况对于广东人来说也有同样困难。广东党员梁复然回忆,中共三大上“略略谈到国共合作问题”,但“当时开会都是讲普通话,我不会听,其他就不清楚了”(55)。
三、困境与新机:中共三大中央局在上海
1923年10月6日,苏联政府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国民党的改组也随之进入实质性阶段。但正如《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中指出:“由于中共中央在三大后又移往上海,这项工作主要是在鲍罗廷和广东党组织的直接推动下进行的。”(56)此时,孙中山所指定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及候补委员中共产党员只有谭平山和李大钊(57),但二人皆非中共中央局成员。本杰明·I.史华兹在20世纪50年代研究时也指出:在“商议国民党改组问题中主要起作用的是鲍罗廷和孙逸仙”,而非中共陈独秀等人。黄埔军校的组建工作也几乎完全越过中共领导人进行。(58)那么,问题在于上海的中共中央局在国民党改组活动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秉持着怎样的态度,又为何没有直接推动?进而言之,中共中央局在上海是一个怎样的存在状态?
1923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局和马林在广州召集了最后一次会议,针对在广州所遇到的问题,对将来在上海的工作作出两个决议。首先,“必须批评国民党在政治上的无所作为和它的错误行动”,但“在批评上避免激烈词句”。其次,“必须加强国民党的宣传,在华南、华中建立国民党俱乐部”,成立“上海新闻通讯社”开展宣传工作(59)。考虑到孙中山的固执和宣传工作的重要性,马林甚至建议越飞对中共在上海的工作予以经费支持(60)。次日,中共中央局成员便准备启程去上海了,马林也要走,只有陈独秀还要留到月底(61)。许多资料显示,当时从广州赴上海,海路单程一般需要5天左右的时间(62)。以此计算,中共中央局委员(毛泽东、蔡和森、谭平山等)应在25日前后抵达(7月26日维尔德的信能证实这一推测)。除了陈独秀和马林外,“其他的大会代表已在这里”。马林的船期是在28日,陈则“比他晚到10天”(63)。徐梅坤也回忆,“大约七八月间,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来到上海”(64)。若维尔德预言不差,陈独秀抵达上海的时间当在8月7日前后。张国焘和罗章龙的回忆录都提到,在上海陈独秀和马林曾共同出席并主持中央会议(65)。马林于8月中旬离开上海(66),则至少此前陈独秀已经到达上海了。如此,中共中央局已全员抵达上海。但是,他们是否能顺利地开展预想中的工作呢?
张国焘说:“回到上海的中共中央,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也面临着不少的难题。第三次代表大会时,陈独秀先生和多数代表的主张曾得到大多数广东党员的支持,声势颇壮。可是到了上海,情势显然不同,上海、北京、湖南、湖北等主要地区的多数党员,对于第三次大会的决议却表示怀疑和责难。不少党员批评共产国际不懂中国国情,硬要将中共融化到国民党里面。”(67)当时身在北京的斯列帕克说:“最近一个时期,党的工作这里进行得很少。本来它的规模就不大,而近来由于这个倒霉的国民党奸党,工作几乎完全停止了。大家都被套在孙逸仙的马车上,对其他的一切都不屑一顾。近来在党内由此发生了重大的争吵。情况确实变得难以忍受。许多同志对我说,马林在党代会上建议完全与国民党合并,因此后来他被问得直推托。”(68)为了应付党内的这些质疑和争吵,陈独秀等人可谓煞费苦心。在11月下旬中共三大一次会议上,“中局报告”称“因同志中对于决议案有多少疑虑”,“原拟在最短期间成立北部中部各重要支部之计划遂未能实现”(69)。实际上,还有更让人忧虑的事情。
1924年元旦,陈独秀在中共与青年团的联席会议上坦承:“虽然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帮助国民党的发展,以及整个国民运动的发展,但是,几个月来党在这方面无所作为。这是因为:(1)中国共产党内对此有分歧;(2)国民党本身没有任何前进的动力”(70)。鲍罗廷到广州后观察到,“如果不算在孙的宣传委员会中的9名共产党员的工作,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两个组织之间也不存在任何实际联系”,中共三大通过的同国民党合作的决议“还是一纸空文”(71)。即使是同在上海一地,两党间也缺乏密切的联系(72)。“因同志们和国民党党员间的猜疑及政治观念不同”,两党关系甚至一度紧张。张国焘在给维经斯基的信中说:“上海的一些国民党员中出现了一股反对我们留在国民党内的情绪”。陈独秀不得不承认,“三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我们同国民党关系的政治论断,不太切合实际”。(73)
除了党内党外的不和谐因素,经费的匮乏也严重影响工作的展开。中共中央局迁到上海后,新的工作方案急需7、8、9三个月的预算经费。陈独秀致函维经斯基,请他在“这个方面采取坚决措施”(74)。但实情却恰恰相反。有学者指出,自中共三大之后,由于苏联与国民党之间的合作取得了重大进展,苏联顾问鲍罗廷等到达广州,国民党即将改组,整个联共(布)中央注意的重心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转移,尽管共产党人因为要求加入国民党而使自身的工作负担明显加重,来自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却发生了问题(75)。11月25日,斯列帕克告诉维经斯基:“说到共产党,首先应该强调一下它的财政困难情况”,“在10月、11月、12月都没有从共产国际执委会那里得到钱,而有整整6个月没有从红色工会国际那里得到钱了”(76)。中共三大一次会议,在总结“大会决议案”未能充分执行的原因时,也称“本党经济困难”(77)。在这种情形下,已有的刊物都不能正常出版,新的工作计划就更加谈不上了。这也难怪在北京的斯列帕克抱怨,中共在三大后,整个党的工作“实际上做得很少”(78)。这是实际的境遇使然。
中共中央局迁往上海,本是为了避免国共关系的进一步恶化。那时,马林、陈独秀提出的改组国民党的计划已到“向隅”的境地,不得不走。但当抵达上海后又因着上述几种因素,而陷入内外交困之中。党内反对意见的此起彼伏,经费的奇窘以及国民党的种种排斥,都让中共中央在原定的道路上寸步难行。10月中旬,鲍罗廷在广州发起的国民党改组实际上是另起炉灶,与马林、陈独秀所提出的国民党改组方案有别(79)。虽然中共中央局也在一些场合提到国民党改组的问题,但当时的种种证据表明,他们对鲍罗廷和孙中山的国民党改组案持一种颇显淡漠的观望态度。
1923年9月末,鲍罗廷曾在上海会见陈独秀和其他中共党员,并与“上海那个班子”制订了相关计划(80)。但没有资料显示,陈独秀等人对即将开始的国民党改组进行了什么样的预备。11月中旬,广州的改组工作已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身在北京的张国焘也敏锐地觉察到“现在形势起了一些变化”。他说,自“上周以来,得到这样的消息:国民党将于1924年1月15日举行全国代表大会。因此,我们必须密切注意即将召开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81)。但11月24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三大一次会议上,中央局报告对此只是泛泛点出:“此时国民党中有一派拟实行改造,并决定于明年正月十五日在广州召开大会,又一派人反对之,将来或酿成重大的变化”(82)。这是一种典型的事不关己的观望之语,显示了中共中央对此次国民党改组的真切态度。斯列帕克因之批评说:“现在广州决定于1月15日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今天已经是11月25日了,为此目的是否进行了什么组织工作?什么工作也没有做。”(83)直到12月16日,赶到上海的鲍罗廷还以此事问瞿秋白:“关于国民党改组问题,(中共)中央向上海以外的各党组织发了什么指示,或什么通知、通告没有?在北京,什么也没有收到,甚至连宣言和纲领他们都没有。”鲍氏并表示需要“起草一个通告,散发给各级组织”。(84)在他的催促下,中共中央局才发布《中央通告第十三号——国民党改组及收回海关主权问题》,正式对“国民党大会”进行回应。而此时距离国民党一大召开已不足一个月时间了。
一般认为“中共积极参与国民党改组”的学者,都会引用中共三大一次会议上通过的《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作为证据。该决议案的确提到了在各地扩大国民党组织的问题,但整个决议案并没有提及“国民党改组问题”也是不争的事实。若以之对比鲍罗廷此时对国民党的改组提出的三大任务(85),不难看出二者之间少有共同点。宣传上,鲍氏关注国民党本身的声望和影响,中共则志在“矫正其政治观念”,“促其做反帝国主义的宣传和行动”;组织上,鲍氏注重广东一地作为国民革命运动根据地的作用,而中共则专注于地方组织及新组织之创设;力量上,鲍氏强调国民党的军事建设,而中共则努力创造和参加各种人民的组织(86)。因而中共中央此处计划仍然延续马林和陈独秀所制订的改组计划,与鲍罗廷所主导的国民党改组关系似不太大。即使是这样的计划,限于经费等实际问题,实行起来也有许多的难处。实际上,中共中央局在上海常常处在多重困境中。但是,困境也孕育着新机。中共中央局和陈独秀同时进行了一些新的探索和尝试,国民革命运动开创出某些新的方向。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的设想和尝试(87)。
这个新的联合战线是在中共的《前锋》创刊号上正式提出的,它的渊源却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陈独秀与胡适发起的新文学运动。陈独秀在《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中,称胡适是“真正了解近代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人”,“适之所信的实验主义和我们所信奉的唯物史观”,“在扫荡封建宗法思想的联合战线上,实有联合之必要”(88)。这与陈独秀自二七惨案以来思想的转变有关系。胡适也注意到“仲甫近来议论,颇有变动”(89)。中共三大后,瞿秋白专程到胡适养病的杭州拜访,其间所谈涉及中共主张的变化,或即是“联合战线”的初步联络。10月初,胡适从杭州到上海,与陈独秀共处一地,为“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提供了尝试实践的机会。二人日相往还,拟定规程,商讨宗旨,计划共办《努力月刊》,以期接续《新青年》再次掀起思想界的大革命(90)。此事还引起出版界的注意,为了争夺《努力月刊》的出版权,商务印书馆和亚东图书馆几至起大冲突(91)。陈独秀以外,中共瞿秋白、恽代英、邓中夏等人都发表文章对此事进行讨论。11月24、25日,中共三大一次会议专辟“教育宣传问题”一案。该案指出:“文化思想上的问题亦当注意,这是吸取知识阶级,使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工具的入手方法。”具体宗旨有:反对东方文化派、文学的及科学的宣传主义、反对宗法社会之旧教义、反对基督教的教义及其组织、健全的唯物主义的宇宙观及社会观及“集体主义”的人生观。(92)科学与人生观问题正是此次“联合战线”所要讨论的主题。11月24日,《中国青年》刊发邓中夏的文章,将当日思想界分成东方文化派、科学方法派和唯物史观派,而后二者“结成联合战线,一致向前一派进攻,痛击”(93)。这都可以说明“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在当时进行的程度及其在党内外的影响(94)。
综上所述,中共三大中央局迁往上海后,由于党内党外的复杂形势,原定与国民党合作的决议陷入止步不前的窘境。经费问题的困扰,也让原定在上海的其他宣传工作搁浅,对于苏联政府代表鲍罗廷在广州的改组工作并不显热心。不得已之下,陈独秀等人似暂时放缓与国民党的合作,转而探索国民革命新的可能方向。与胡适的接触,让中共提出的“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理念在这段时间内进入尝试实践层面。或因工作重心的调整,国民党在广州的改组及将要召开的国民党一大并没有引起中央局的注意,直到很晚才有针对性的应对。这在某种程度上让中共中央在此次的国民党改组中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
五、余论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成功召开,在当时颇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以至于张国焘、维经斯基等素来反对中共加入国民党的人也为之欢呼。此次国民党的改组是在苏联政府代表鲍罗廷的促进下成功的。这次改组与此前马林、陈独秀所制定的国民党改组方案是有区别的,更加注意孙氏的实际需要。正如陈独秀后来所讲,孙中山之所以愿意改组,关键在于鲍罗廷的皮包里有苏联“对国民党巨量物质的援助”(95)。而仅仅在几个月前,马林和陈独秀向孙氏提出的改组计划,却遭受孙氏的冷遇甚至反感。这不仅让马林“垂头丧气”,整个中共中央的工作也因此陷入困境,以至宁愿在上海非法存在,也不愿在广州合法活动。这些在中共中央局和陈独秀都是记忆犹新的。对于鲍氏在广州的改组活动,上海的中共中央局是知情的,但鉴于此前的教训,并不很重视,对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也持同样态度。可以说,直到1923年12月中旬以前,中共中央局对国民党的改组活动是冷淡的、观望的。与此相对,中共中央局对“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反而更加重视,亦期望于此开拓国民革命的新领地、新方向。
然而,国民党改组的成功及其在近代中国的重大意义影响了人们的历史记忆。国民党一大前,中共中央局在上海的困境与探索,对鲍罗廷改组国民党的观望及对此次会议的漠然心理,多被这次会议的光芒遮掩。中共中央及陈独秀等人与胡适等自由派知识分子所推动的“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也因之淡出了人们的记忆。这些被遮掩的历史情节,恰恰真实地反映了中共知识分子在早期革命活动中的矛盾、困境与不懈的探索。只有了解这些,很多的事实才可能被后人所理解,也更能丰富我们对中共早期历史的认知。
注释:
①这一争论也较多为学界所关注,参见萧超然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1923—1926):国民革命的兴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6—58页;另请参见刘青等:《中共三大关于国共合作的争论》,《炎黄春秋》1998年第3期。
②中共三大上进行了组织机构革新,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常设机构,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由中央执行委员会议选出中共中央局成员。关于中共中央组织机构变迁,可参阅王健英:《中共中央机关历史演变考实(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
③主要有王亚春:《略述1922至1923年中共中央四次迁址的原因》,《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2期;李红喜:《一九二三年前后中共中央迁址时间考》,《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3期;王健英:《中共三大及其后的中央机关》,《上海党史与党建》2003年第5期;尚连山、苏若群:《从解密档案看中共三大的三个问题》,《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9期。
④关于中共与上海的关系可参阅齐卫平等著:《中国共产党创建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⑤《利金就在华工作情况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摘录)》(1922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82页。
⑥熊月之:《上海通史》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5、44页。
⑦《荷属印度高级法院总检察长致荷属印度总督的信》(1921年12月31日),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18页。此处“荷属印度”疑有误,应为“荷属东印度”。参见同书第39页。
⑧马林:《致加拉罕的信》(1923年2月3日),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20页。
⑨马林:《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说明》,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77页。
⑩[苏]C·A·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97页;《利金就在华工作情况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摘录)》(1922年5月2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86、82、83页。
(11)《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1922年4月6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222页。
(12)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第239页。
(13)《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1922年4月6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第222—223页。
(14)[苏]C·A·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第97页。
(1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7、45页。
(16)李玉贞:《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16页。
(17)《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命令》(1922年7月18日),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77—78页。
(18)《维经斯基给中共中央的信》(1922年8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117页。
(19)李玉贞:《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第114—115页。
(20)《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88页。
(21)斯内夫利特:《工作记录》(1922年10月14日至11月1日),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87页。
(22)《1923年孙中山与苏联特使越飞在沪会谈情况的警务报告》,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5),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9页。
(23)《越飞致马林的信》(1922年11月7日),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88、89页。
(24)《陈独秀在共产国际四大上关于中国政治形势的报告》(1922年11月),转引自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第22页。
(25)《刘仁静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1922年11月5日—12月5日),孙武霞、许俊基选编:《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32页。
(26)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第23页。
(27)《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不晚于1922年12月5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161页。
(28)《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其派驻中国南方代表的指令》(1922年8月),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80页。
(29)李颖:《陈独秀赴俄出席共产国际四大解析——在俄罗斯发现的陈独秀的两篇报告》,《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3期。
(30)《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速记记录(摘录)》(1922年12月29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179—180页。
(31)参见《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速记记录(摘录)》(1923年1月6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188—191页。
(32)《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1923年1月12日),孙武霞、许俊基选编:《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第236页。
(33)参见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11—513页。
(34)《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主任萨法罗夫的信(摘录)》(1922年3月8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227—228页。
(35)《魏金斯基致斯内夫利特的信》(1923年3月9日),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32页。
(36)《维经斯基就中国形势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的报告(摘录)》(1923年3月24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234页。
(37)《维尔德给某人的信》(1923年5月2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249—250页。
(38)李玉贞:《马林传》,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233页。
(39)《斯内夫利特笔记》(1923年6月12日—20日之间),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27页。
(40)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下,香港明报月刊出版社,1973年,第285—286页;Benjamin I.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p.47。
(41)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向导》第22期,1923年4月25日。
(42)《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编:《“二大”和“三大”:中国共产党第二、三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81—182页。
(43)《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1923年6月),《“二大”和“三大”:中国共产党第二、三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第172页。
(44)《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26页。
(45)《致越飞、达夫谦和季诺维也夫的信》(1923年5月31日),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98页。
(46)李玉贞:《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第197—198页。
(47)《致越飞和达夫谦的信》(1920年6月20日),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62页。
(48)《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会国际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远东局的报告》(1923年6月25日),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65页。
(49)《致季诺维也夫、布哈林、越飞和达夫谦同志的信》(1923年6月25日),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66页。
(50)《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126页。
(51)《致达夫谦和越飞的信》(1923年7月13日),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81页。
(52)《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3年7月15日),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88页。
(53)[日]北村稔:《第一次国共合作の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98年,第22—23页。
(54)[苏]C·A·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第97、92页。
(55)《梁复然的回忆(节录)》(1972年5月),《“二大”和“三大”:中国共产党第二、三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第607页。
(56)《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第113页。
(57)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第1711页。
(58)Benjamin I.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pp.50-51.
(59)《致达夫谦和越飞的信》(1923年7月20日),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96—297页。
(60)《致越飞和达夫谦的信》(1923年7月18日),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95页。
(61)《致达夫谦和越飞的信》(1923年7月13日),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81页。
(62)《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主任萨法罗夫的信(摘录)》(1923年3月8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228页;《荷属东印度高级法院总检察长于伦贝克致总督的信(节录)》(1922年5月12日),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40页。
(63)尚连山、苏若群:《从解密档案看中共三大的三个问题》(《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9期)一文中认为,马林到上海时间为7月21日,陈独秀也于7月底返回上海,当是出于误解。1923年7月26日,维尔德信中说:“马林同志于星期六4时8分抵达上海”。查当月日历,前后较近的星期六为7月21日、7月28日和8月4日。7月21日,马林仍在广州给廖仲恺写信(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301页),故首先排除。而马林在7月20、21日的信中都说自己很快“离穗”,此后也没有在广州的活动记录。按当时海路5日的行程,以7月28日为最合理。因此,维尔德所说当为马林的船期,为将来时态。或因翻译问题,导致时态变化,易于误解,亦在情理之中。参见《维尔德给维经斯基的信》(1923年7月26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263页。
(64)《徐梅坤回忆中共“三大”》(1980年3月),《“二大”和“三大”:中国共产党第二、三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第679页。
(65)罗章龙:《罗章龙回忆录:椿园载记》,第277页。
(66)《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斯内夫利特在华记事(1920年1月—1924年4月)》,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495页。1923年8月2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有一份证明书说明“马林同志自本年8月30日至9月14日离职赴克列缅丘区休假”,所以马林至少应该在8月29日抵达莫斯科。
(67)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下,第304页。
(68)《斯列帕克给维经斯基的信》(1923年8月25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267页。
(69)《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文件》(1923年11月24—25日),《“二大”和“三大”:中国共产党第二、三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第233页。
(70)《鲍罗廷的札记和通报(摘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442页。
(71)《鲍罗廷关于华南形势的札记》(1923年12月1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369页。
(72)《鲍罗廷的札记和通报(摘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442页。
(73)《张国焘给威金斯基、穆辛的信》(1923年11月16日),《“二大”和“三大”:中国共产党第二、三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第227、224页。
(74)《维尔德给维经斯基的信》(1923年7月26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264页。
(75)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4期。
(76)《斯列帕克给维经斯基的信》(1923年11月25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316页。
(77)《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文件》(1923年11月24—25日),《“二大”和“三大”:中国共产党第二、三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第233页。
(78)《斯列帕克给维经斯基的信》(1923年11月25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316页。
(79)鲍罗廷是作为苏联政府代表被派到广州的,莫斯科给他的指示是“服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绝对不要热衷于在中国树立共产主义的目标”,这与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马林所接受的指令是不同的。鲍罗廷在与国民党孙中山的关系上也秉持更加务实的宗旨,在国民党的改组方案上也与马林、陈独秀的主张有根本的不同。鲍氏注重国民党军队的改组,这正是马林等人极力反对的。关于鲍氏与国民党改组,可参考日本学者北村稔的《第一次国共合作の研究》和李玉贞的《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
(80)《加拉罕致鲍罗廷的信》(1923年10月6日),李玉贞译:《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25)》第1卷,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第241页。
(81)《张国焘给威金斯基、穆辛的信》(1923年11月16日),《“二大”和“三大”:中国共产党第二、三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第225页。
(82)《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文件》(1923年11月24—25日),《“二大”和“三大”:中国共产党第二、三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第234、240—241页。
(83)《斯列帕克给维经斯基的信》(1923年)11月25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316页。
(84)《鲍罗廷同瞿秋白的谈话记录》(1923年12月16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378页。
(85)1923年12月10日,鲍罗廷提出孙中山面临三个重要任务:(1)继续在全中国进行已经在广州开始的国民党改组工作。为此他必须在中国最大的城市里安排新闻事业。(2)保住广东,不是为了像此前那样时刻梦想着组织北伐,便去千方百计争取前线的胜利,而是为了在广东,建立一个发展和指导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基地。(3)改组现有的5万至10万士兵的军队并使它完全归国民党领导。为此就务必为孙中山建立军校,认真注意培养政治工作干部。参见《鲍罗廷关于华南形势的报告》(1923年12月10日),李玉贞译:《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25)》第1卷,第305—306页。
(86)《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00—201页;《鲍罗廷关于华南形势的报告》(1923年12月10日),李玉贞译:《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25)》第1卷,第305—306页。
(87)相关研究可参见罗志田:《北伐数年前胡适与中共的关系》,《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4期。
(88)独秀:《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前锋》第1期,1923年7月1日。
(89)胡适:《山中杂记》,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四),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08页。
(90)《胡适致高一涵、陶孟和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华书局,1979年,第216—217页。
(91)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四),第75—77页。
(92)《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文件》(1923年11月24—25日),《“二大”和“三大”:中国共产党第二、三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第248页。
(93)中夏:《中国现在的思想界》,《中国青年》第6期,1923年11月24日。
(94)陈独秀等中共知识分子与胡适等人尝试构建的“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在当时似有具体的内容和形式,其相关过程也颇有迹可循,《努力月刊》的筹备便是最重要的线索之一。后这一被胡适和陈独秀赋予重要使命的刊物,因各种原因,筹备一年有余终于被放弃。陈、胡二人思想上的初步共识也受到了各种因素的干扰,遂使这次联合的“尝试”归于失败。但这种整合新思想界的努力,在当时及后来都有深远的影响。此处牵涉甚多,殊难展开,详情另文再探。
(95)《告全党同志书(节录)》(1929年12月10日),《“二大”和“三大”:中国共产党第二、三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第521—522页。
标签:孙中山论文; 鲍罗廷论文; 陈独秀论文; 马林论文; 上海活动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上海论文; 历史论文; 第三国际论文; 国民党论文; 明朝历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