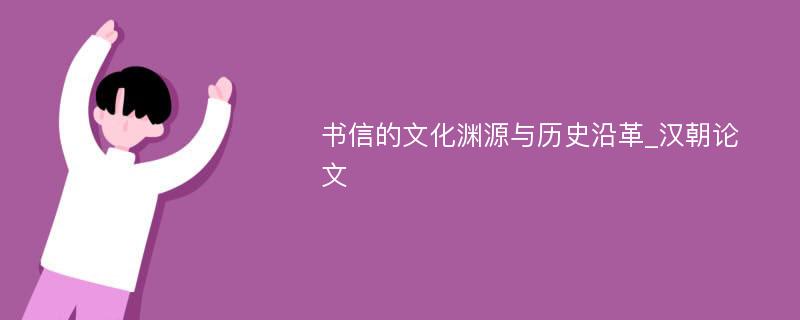
书信的文化源起与历史流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书信论文,文化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书信,是人类文明生活中出现极早、流行极广的一种实用性文体。
关于它的源起,历来说法不一,研究者们从各个方面对此作了探析,其中亦不乏真知灼见,但多未触及根本。要弄清这个问题,必须把目光投向更悠远的历史,从深厚的文化沉积中去探寻线索。
我的分析,想从这个字说起:専。
専(以下写作“专”)甲骨文像手持纺锤(原始的捻线工具),从又或从寸,示以手拨运而使之旋转。此实会意之字。《甲骨文字典》训其“为转之本字”,这是对的。因而从专之字皆有转动之义。《诗经·小雅·斯干》“载弄之瓦”,毛传云:“瓦,纺专也。”纺专即纺锤。其操作之性能在于转,因而名之。
《甲骨文编》卷三载有“专”字31例,又据《卜辞通纂》、《甲骨文字集释》、《殷虚卜辞综述》等,其字在卜辞中主要用为人名、地名。作地名之“专”,应是因人名而来。作人名之“专”,有以为侯伯名,但更多的则是贞人或卜人名。迄今所能确定的卜辞中贞人有123个, 据陈梦家考定,“专”出现于早期甲骨卜辞,为武丁晚期卜人。贞卜之人是掌卜问的史官,“祭祀占卜时代王言事,于卜辞中能‘转达’上帝鬼神之意”〔1〕。其职分十分明确:在天地神人之间转言传意, 所事类乎后之所谓“执讯”。贞人而称“专”,可谓名实相符。
《说文》解“专”字,曰:“六寸簿也。”此实为引申义。簿即笏,指手版。上古时无论贵贱皆执笏从事。《释名》:“笏,忽也。君有教令,及所启白,则书其上,备忽忘也。”又,《礼记·玉藻》“史进象笏,书思对命”,郑玄注:“思,所念思将以告君命者也。对,所以对君者也。命,所受君命者也。书之于笏,为失忘也。”笏之作用,主在告命、受命两面。据《玉藻》,其长度为二尺六寸,此当是礼制严明情况下的定规。那么,在告命、受命作为原始文明中某种需要而出现之时,就必然已有其相应粗陋而原始之“笏”。书而备忘,用为告、受,这就是“专”——转言传意之义所在。
随着先民的社会性活动日趋频繁,音讯转传以其现实之需要应运而生。郭沫若先生在《卜辞通纂》中,曾就所辑第431片、512片、513 片甲骨卜辞作过一番考释,认为这里记录的,是从千里之外的西北边境“传至殷京”(今河南安阳)的“边报”。在外来侵犯十分频仍的当时,凡有军情,则击鼓为号,借助音声程程传递消息。遇有特别紧急复杂的情况,鼓报之外,则有口头传报或诉诸文字形式的书报。这些卜文中“告曰”以下显系“边报”,并很可能就是“书之于笏”、“以告君命”的传报文字,或是对原有通讯传报文字的转述。换言之,这应该是记录或转载迄今发现最早的通讯文字,即书信,确切地说,是军事信件。在文明程度愈趋提高、“书之于笏”已不成其难的当时,书面通讯形式产生之必然是显而易见的。汉语中“音”、“讯”二字并举联义,并作为“书信”之同义语,盖因于原始背景下书信的这种独特的传递方式。
交通的发展是讯传的先决条件。甲骨文、金文中“行”像四通之路,这足以说明殷人已重视道路的建设,其时已有通衢大路。又从卜辞以及地下发掘所提供的资料来看,殷代的交通工具,除水行的舟、凡(两木相拼之木筏)而外,陆地上已大量使用车、马,并已有严格的车马制,可见其时通行之便利。所以诸如“往来”之词在卜文中已是屡见不鲜。与书信的传递同样需要有不断改善的交通条件的商业,在殷代已开始脱离实物交换的原始萌芽阶段,而进入货币贸易的实质性时期,如武丁卜辞中已有“锡(赐)贝”、“锡贝朋”(贝以十枚为一朋)的记载,晚殷金文中的“贝”也多作为赏赐这物,而河南安阳大司空村还出土了青铜贝。这说明“贝朋”作为饰物的历史已告结束。还有,当时的手工业及冶铸业均已非常进步。其原料,有的需从远地运达,这也必以交通为保证。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殷商时代,用于军旅或官政的通讯,不仅是出于实际的需要,而且已有其现实的可能。
至周代,讯传之事发展为愈趋完备的“传遽”制度。“传”为驿传之车,其字取义于“转”,为“专”之假借;“遽”为驿传之马。专置“行夫”之官掌邦国传遽之事, 特设“置邮”(驿站)以“传命”〔2〕。又据《礼记·曲礼下》、《诗经·小雅·大东》、《国语·周语中》等,可知周代在道路修建与保养方面更有规模性要求。《易·旅》中叙商人行旅,已有止宿的“处”、“所”即旅馆之便。《周礼·地官·遗人》载,“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以仓廪委积供羁旅艰厄之用。由此,可以想见当时驿制之规模。一般情况下,信件由驿道一站一站传送,遇有紧要之事,则派特使专送。《左传·文公十七年》:“郑子家传执讯而与之书,以告赵宣子。”杜注:“执讯,通讯问之官。”孔疏:“使执讯,使之行适晋也。”其讯传之便捷如此。这说明,在周代,通讯的发展已进入一个新阶段。于是,关于“书”、“简书”的文字记载亦开始见于先秦古籍。从《诗经·郑风·子衿》“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中“嗣音”(续音讯)二字,可见其时书信已同时成为民间交往的重要媒介。刘勰所谓“春秋聘繁,书介弥盛”〔3〕, 姚鼐所谓“春秋之世……列国士大夫或为书相遗”〔4〕, 显系书信发展渐盛时的情况,而并未溯及其源。
书信之“书”,《说文》释为“箸也”。凡著于简册、上报下命、往来声问之文字,原先通称为“书”。书之为休,起于实用,它一开始就显示出其固有的特征:对象性、叙诉性和传递性。
在最早的关于“书”的概念中,不分上下而惟见彼此。这一点,刘勰在《文心雕龙·书记》中说得很明白:“战国以前,君臣同书。”如乐毅《报燕王书》,实是因燕王“使人让(责备)乐毅,且谢(谢罪)之”而“使人献书报燕王”〔5〕的一封回信。 所以刘勰将“书”与“记”即奏记归为一体,给它下的定义也比较宽泛,认为“书者,舒也”,其特点在于“舒布其言”。君臣同书、书奏同源,正是由书笏的告、受二义决定了其原初的文化命运。
秦汉定制立仪,乃专以“上书”为章奏,以“赐书”为诏策。其时即便专于朝政按劾或策封制命的奏议与诏诰,往往在习惯上也还是称作“书”,如司马相如《谏猎书》、胡广《上书驳左雄察举议》、路温《舒尚德缓刑书》以及汉文帝《赐南粤王赵佗书》、汉昭帝《赐燕王玺书》等。其实,上书者,上呈之书也,赐书者,下赐之书也,在本质上无非即是书信。而邹阳《狱中上梁王书》,则纯属为个人辩诬的书信,在内容和意义上与一般朝奏自是不同,从“上书”二字使用之泛,可见书信定体之初,必然显示出书、奏同源的文化关联。
从关于“舒”的指认中,刘勰将书信的性质界定为“尽言”,他说:“详总书体,本在尽言,言以散郁陶,托风采,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也。”写信的目的,在于把“心声”传达给对方。而真正使书信从文牍中完全脱离出来,成为朋旧之间交流“心声”的工具,那是在汉代。“汉来笔札,辞气纷纭。”史迁之报任安,杨恽之酬会宗,马援之诫兄子等,或悲慨淋漓,抑扬寸心,或谆谆告诫,语重情长,已显露出书信在表情达意方面的独到之处。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陵夷,玄风大炽,士人多“越名教而任自然”,以谈议为尚。思想的解放,推动了书信体的发展。这时,涌现了一批收牍名家,有“号称翩翩”的阮瑀、“半简必录”的孔融、 “留意词翰”的应璩,还有曹丕、曹植、陈琳、嵇康等等。这些文人以自己遭逢乱世的独特体验,或议政,或论学,或谈玄,或述趣,或叙离,或记游,扩大和丰富了书信文的内容,增强了抒情的色彩。在交流思想、传达情意的同时,他们率性任气,天才艳发,往往假书信以骋才华,多情文并茂之作。六朝时骈风盛行,而如吴均、陶弘景等人的骈体小简,却全无一般骈文辞靡语滞的弊病,亦能以文藻新巧、意境超迈取胜。于是,书信又因其绚烂的艺术色彩,从单纯的应用性文体变为一种具有独立地位的文学样式。
唐宋两代崇尚古文。在新的文学风气的影响下,书牍之文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内容更切实际,笔法更趋平易,往往于议政、论学之际,叙说遭遇,慨叹人生,语多出自肺腑,出现了不少既有政治、学术价值,又十分亲切感人的书信体文学名篇。这在“八大家”中比较多见,如韩愈《答李翊书》、《答刘正夫书》,柳宗元《与友人论为文书》、《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曾巩《寄欧阳舍人书》,苏轼《答谢民师书》,欧阳修《与高司谏书》,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等。还有一些书信,则是落笔于眼前实境,即事而议,述乎小而发乎大,因情而叙,言乎志而明乎理。如柳宗元《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朋友遭火劫,家资毁于一旦,不去安慰,反为祝贺,这看似悖乎情理,然而通过透辟的分析,又句句入乎情理之中,可谓奇文奇论,妙笔惊人。韩愈《与陈给事书》、《答窦秀才书》、《应科目时与人书》等,引臂联类,情文相生,亦自气调不凡。他如王维《山中与裴秀才迪书》、王绩《答刺史杜之松书》、李翱《寄从弟正辞书》、李商隐《上河东公启》等一类书信,亦多于寻常间为文,抒怀而出,发引性灵。此外,有唐一代人才辈出,对于恃才傲世、力图逞志的唐才子们来说,最大的人生危机莫过于怀才不遇,因之,上书以行干谒,在他们实是司空见惯之举。如李白《与韩荆州书》、韩愈《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等等,旨在干谒而无意乞怜,吐辞恳切却不失清高,读此,亦可见一代之风气。在这里,书信的尽言以述怀的功能性意义,已体现为述怀以求进的功利性内容。
至明代,书信之流行更广,内容已涉乎社会人生、思想学术、个人经历、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在黄宗羲所编《明文海》中,“书”凡列为二十五目,其包罗之广,于兹可见。明代学派纷呈,文人的思想比较活跃,书信中论诗文、谈学问者颇多,如李梦阳《答周子书》、《驳何氏论文书》,何景明《与李空同论诗书》,唐顺之《与茅鹿门主事书》、《答蔡可泉书》等。笔调风格,也往往与其文学主张相应,如“前七子”中徐祯卿的《重与献吉书》,通篇作览游之叙,无一字旁迕,而字对句偶,铺张恣肆,洋洋千言,实有汉大赋之风致。李贽标举“童心”,反对“道学”,《又与焦弱候》、《答耿司寇》等书信,文字泼辣,揭露深刻,正可体现其思想。三袁出而“性灵”倡,宏道《与丘长孺书》等,可谓“任性而发”,极是真率自然。明末反清斗争中则多慷慨悲歌,夏完淳临难陈词,一封《狱中上母书》,发尽肺腑,悲壮感人。
清初开朴学之风,“则以与书一门,为辨析学问之用,洒洒千言,多半考订为多。文家沿用其体,凡意所不宣者,恒于与书中倾吐之”〔6〕。可见书至清代,其用又专与学问者相关。因此之故, 清人亦多分其类曰“书说”,说者,言谈论说之谓也。顾炎武有一组《与人书》,其中不乏此类书信。他如魏禧、袁枚、章学诚、方东树等清代学者,擅以书信谈文论学者比比皆是。而如洪亮吉《与孙季逑书》、林则徐《又复苏鳌石》等,作为友朋间的普通书信,叙如促膝对语,言必推心置腹,然所述亦必涉乎学问、时政。这当与其时“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张维屏)的风气以及清人为文之重“立言”、尚“因时”(梅曾亮)有关。而把对天下之事的关切表现为自我生命意义上的一种极致的,那就是林觉民的《与妻书》。这封信一开头便从情理关合处跌激出一个大起大落的严酷事实,从而列述四个生活片断,柔情蜜意,历历在叙,又郑重托孤,想象死后之以灵相傍、以哭相和、以梦相见。尤为感人的是,作者充一己之爱为天下之爱,将儿女情愫融于革命者的怀抱之中。与夏完淳《狱中上母书》之耿耿于“忠”、“孝”不同的是,林氏更多地表现了本世纪初清王朝全面崩溃之际,在民主思想影响下,一代新人的觉醒与坚定、乐观的革命精神,此外,以郑燮十六封“家书”为代表,所叙虽为日常琐事,但情感真挚,文字朴实,信笔所之,却往往以小及大,“言近指远”,因而亦成为清人书信文中颇为引人注目的一个部分。
作为文章一体的古代书信,有其自身的发生与发展的过程。由其原始状态就具有的实用性、对象性、叙诉性、传递性所决定,形成了它的因事随意的“尽言”特点和因机制宜的呈示方式。即以其名称而言,在“惟朋旧之间,则曰‘书’而已”的相对“近世”〔7〕,总名而外,又以所用之工具,而称为简、笺、札、牍或尺牍、尺素、尺翰、帛书,以及因传递时使用封套而称为函,陈述时跪地表敬而称为启等等。可以这么说,在古典散文中,惟有书信内容最广泛,形式最繁复,无论社会生活、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巨至君国大事,细若日常所感,皆可入书。而所谓尽言达意,说到底,全在一个“情”字。好的书信散文,往往心意真挚,情溢于辞,正如林纾所言,“大抵与书一定之体……指陈时政,抗论世局,或叙离悰,或抒积愫,所贵情挚而语驯, 能驾驭控勒,不致奔逝奋其逸足,则法程自在,会心者自能深造之也”〔8〕。所以,较诸其他一般文章,书信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更真实,体现的个人色彩更强烈。因而,读古人的书信,“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9〕。 书信在写法上极为灵活,叙事、说理、抒情无所不可,骈散长短各式俱宜,它特别讲求根据不同的对象选择不同的表达方式,这就是被刘勰肯定为“百封各意”、“亲疏得宜”的“尺牍之偏才”(一技之长)。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书信,实际上远远超越了它本身的实用性的存在价值,以其独特的光彩,成为散文园地中一枝奇葩。而在人类文明已进入电子通讯技术的今天,具有如此传统特点的书信,必然走出一段新的旅程。
注释:
〔1〕见孟世凯《甲骨学小词典》“贞人”条。
〔2〕《孟子·公孙丑上》。
〔3〕《文心雕龙·书记》。
〔4〕《古文辞类纂·序目》。
〔5〕《战国策·燕策》。
〔6〕〔8〕《古文辞类纂·书说类上》。
〔7〕吴讷《文章辨体序说》。
〔9〕鲁迅《孔另境〈当代文人尺牍钞〉序》, 见《且介亭杂文二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