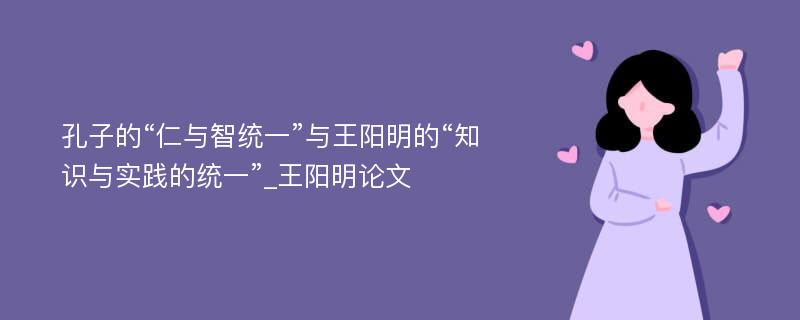
孔子的“仁智统一”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子论文,仁智统一论文,知行合一论文,王阳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公元1508年,王阳明先生于贵州龙场“大悟格物致知”之道。次年,阳明又于贵阳书院“始论知行合一”。从孔子到王阳明的2000年间,中国古代认识史上关于“知”、“行”问题的论争,经历了不断发展的曲折变化过程,不论是儒家、道家,乃至于佛家,无不对此作了详尽而艰辛的探索,经历了一个个认识发展的逻辑“圆圈”,而每一周期,都将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引向了更加深入的层次,并不断增加着对这一问题认识的真理性颗粒。
一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创立哲学体系的人,他除了对当时哲学论争的中心问题——天人之辨,提出了关于天命论的传统主张外,同时又着重考察了人道,提出了仁智统一的新学说。孔子哲学的核心概念是“仁”,而“知”的概念在他那里,紧随于“仁”,居于很重要的位置,是其哲学体系中具有全局性意义的范畴。把“知”与“仁”联系起来,赋予不可分离的性质,是其哲学的重要特征,形成了他的“仁智(知)统一”的学说。
在《论语》一书中,孔子有多处将“仁”与“知”并举。比如: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颜渊》)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雍也》)
后来,儒家学派都用“仁且智”来称道孔子的人格。孟子说:
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呼?”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孟子·公孙丑上》)
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德与周公齐,名与三王并。(《荀子·解蔽》)
在孔子和儒家看来,仁且智是理想人格(圣人)的主要特征。“仁”是伦理学的概念,“知”是认识论的范畴,在孔子哲学体系中,认识论与伦理学,达到了某种程度的统一。但是,认为中国传统哲学中认识论不占重要地位的人,大概都认为中国哲学“重人生而轻自然,长于伦理而忽视逻辑”(这话大概是胡适的)。古往今来的中国哲学家,其兴趣为伦理的而非逻辑的,往往注意“立德”、“立功”,而不重视“立言”,比如陆九渊、王阳明,都是主张不立文字的[1]。尤其是王阳明,“立德”、“立功”,可谓显赫卓著。至于孔子讲“行”,则完全是“行仁”。他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仁”被孔子视为君子必备的品德,君子之所以为君子,就在于时刻不离开“仁”,那怕是仓卒之间,颠沛流离之际,都要努力地去实行“仁”。知仁必行仁,这是孔子一贯的主张。他还对“仁”灌注了新意。在孔子以前,已经有人把“仁”从“爱亲”扩大到“爱人”。如单襄公说:“爱人能仁。”(见《国语·周语下》)孔子不仅用“爱人”来解释“仁”,强调“仁”的具体的实行,还提出“忠恕之道”,作为实行“仁”的根本途径。他说: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
《论语》又写道: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
按照冯契先生的解释,所谓忠恕之道,就是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孔子说的“仁之方”,就是用推己及人的方式实行仁。所以讲孔子“仁知且不蔽”,他的知与仁是统一起来的,而其仁,须以具体的实行仁为标准。孔子的知与行是统一的,具体表现为知仁与行仁的统一。知仁是行仁之本,行仁是知仁之用与知仁之方。这是一种在伦理道德层面上的知行统一的学说,不能不说是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的最初的理论来源。
再看孔子的说法,在“樊迟问仁”一章中,孔子把“仁”解释为“爱人”,把“知”解释为“知人”。可见他的“知”,主要是指认识人们之间的伦理关系,他的“爱人”即“仁”,则是“知”的实行。要实行仁,必先有知,他说:“曰:未知,焉得仁?”(《公冶长》)这里虽然提出“知”是实行“仁”的必要条件,即对伦理关系没有正确的认识,就不可能有自觉的仁德行为。但是,这里“知人”与“爱人”,有着时间上的先后之分,而一般理解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知”与“行”是没有时间先后之分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在时间上二者并行不悖。孔子的“仁智统一”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虽有着某种渊源关系,但又有完全的不同之处。从承继渊源关系上讲,二者又都做到了在知行问题上的伦理学与认识论的统一。关于“知”,孔子还从认识论角度上提出了不少合理的见解。如: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
这里接触到认识过程中的“知”与“不知”的矛盾。知道自己的“不知”,也是一种“知”,乃是求知的开始。这一点,王阳明大约是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未知”必不能够行,于是知就是知,不知就是不知。知,要知得真切笃实,否则就是把知行分做两截用功了。因为如果把“未知”视为知,岂不就有了未知就能够行的道理?因此知道自己有所不知,虽也是一种认识,但不能停留在这样一种认识上,须注入“行”的功夫,方能由不知转化为知,使知与行统一起来。《论语》中有一句话这样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这句话接触到了学习与思考、认识论上知与行的关系。不过这里的“行”,乃是指的意念的活动,其实这与王阳明在许多场合上对“行”的注释乃为意念活动(“一念发动”)是大致相似的。孔子说,学习而不思考则迷惘而失去方向,思考而不学习则空洞而陷于危殆。王阳明则说道:“学射则必张弓挟矢,引满中的;学书则必伸纸执笔,操觚染翰。尽天下之一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答顾东桥书》)二者所言何其相似。不过,孔子所言“学习”、“思考”之行,以及阳明所说之行,都只是一种认知活动,而不具有今日社会实践之含义。从认识论角度来讲,二者所言知与行,实际都只限于认识活动与过程之中。孔子还谈到言与行要一致的问题。《公冶长》中说:“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判断一个人是否真正有知识、才能、德性,不能只听他口头讲的,主要是看其行动。这些观点,甚至具有了唯物主义的合理成分。当孔子的“仁智统一”学说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各自不仅作为认识论命题,而且同时又与伦理学结合起来时,“行”的概念才超出认知领域,赋予了道德践履的意义。就孔子的“仁智统一”学说而言,从认识内容来说,“知”主要是“知人”;“学”主要是“学以致其道”(《子张》);“思”主要是“言思忠,事思敬,见得思义”(《季氏》)等等。认识的过程实际就成了德性培养过程。下面我们也来看看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是如何从单纯认识论命题引向认识论与伦理学相一致、相结合的结论的。
首先,从“知”与“行”的本原上看,二者皆由心所生,故知行是合一的。王阳明说:“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传习录》中)“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传习录》上)王阳明反对朱熹将“知行之所以二”,是因为朱熹把求于外物的“知”与发于内心的“行”分作了两件,所以违背了“知行合一”。在阳明看来,“知”乃是发自于内心和对本心良知的认同,而非指向外物;“行”就是复那知之本体。从那最初之根源上看,“知”与“行”简直就是一码子事,岂容将其分做上下、内外两截去用功呢?
其次,从“知”与“行”的发生过程来看,二者不仅同根同源,而且是同时存在的,不存在先后之分,所以是合一的。阳明反对朱熹的“知先行后”说,认为这种“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功夫”,实际上是“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知”与“行”是不能分开的,而是二合而一的。他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答顾东桥书》)“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他举例说:“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传习录》上)。这是说,看到好色与产生美感,既是知,也是行;闻到恶臭与产生恶感,既是知,也是行。此只是一件事,是合一的,不可分作两截去作。“知行合一”进入道德范畴时,王阳明提出了他的立言宗旨。王阳明不是不“立言”,这里其实也有一个从单纯认识论到认识论与伦理学相互结合的命题的推而广之、推而极之的过程。他说:“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传习录》下)。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的立言宗旨,就是要人在认识封建道德的同时,当即实行封建道德践履,从而把二者合而为一。正如孔子讲“知”,就是“知人”;“仁”,就是“爱人”。孔子的“仁智统一”的学说是有着值得肯定的合理因素的。一是他把“知”和“行”统一起来,强调二者不可割裂的相互关系;二是他把这种认识论上的“知行”关系学说上升到伦理学的高度,赋予了道德意义,是其理性原则与人道原则的较好的结合。如果把从孔子到王阳明关于“知”“行”关系的认识发展过程比做一个逻辑圆圈的话,孔子的“仁智统一”学说正是这一近似一逻辑圆圈的起点,即肯定的阶段。有肯定就会有否定,正是与孔子生活的时代几乎同时[2],老子和《老子》一书对哲学上的知行关系作了彼此割裂开来的论证。
二
“知”与“行”在老子那里,表现为二者毫不相干,彼此割裂与对立的关系。它的“知”是“不行而知”;它的“行”,是“无知而行”。这种认识论和它以“道”为最高实体的宇宙观是相联系的。它把“道”看作宇宙万物的本原,故而把“道”看成是认识的对象。它把人去追求具体事物的知识,称做“为学”;把认识产生宇宙万物的“道”,称做“为道”。他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认为对具体事物的认识愈多,对“道”的认识就会愈少。因此,老子采取了独断论态度,主张“绝圣弃智”、“绝学无忧”,它把知识看成是罪恶,认为必须抛弃知识,“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到了最后的一无所知,才算是知“道”和依道行事,做到“无为,而无不为”。
如果说孔子的“知”是“知人”,老子的“知”则是“一无所知”。做到了一无所知,也就知道了。老子根本反对去认识一切事物,更反对用感官去接触客观事物,干脆取消感性事物。它说:
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第五十二章》)
孔子的“仁智统一”讲的是“知人”、“爱人”,而老子的“知”不仅是空无一物,同时也是“目中无人”,《老子》说: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第五章》)
老子即使有“知”,也是“不行而知”,他说:
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第四十七章》)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不出大门,能知天下事。不望窗外,能认识天道。走得越远,知道得越少。因此,“圣人”不必经历就知道,不必亲见就明了,不必去做就成功。《老子》这里包含了两个方面重要的意思:一是它的认识方法,排除了一切感觉和经验,企图通过一种神秘直觉来体悟认识对象,所以是“不行而知”;二是它的认识对象,排除了一切客观事物而直指天道,所以他的“知”是“空无一物”和“目中无人”。《老子》的哲学思想,后被世人认为是道家的理论基础,其实佛教也大讲“体悟”,全然是超验的;王阳明于贵州龙场悟道,在某种程度上也被看成是一种神秘直觉的体验。其时,阳明先生端居澄一,以求静默,所思者惟“圣人处此,更有何道”?“格物致知”之旨乃“忽悟”而得。所以稍知中国认识发展史者,都以先秦哲学为几千年之根础。《老子》这里,不就有“众妙之门”?
《老子》的“行”,可以说是“无知而行”。他说: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第五十六章》)
其实这不是真正的“无知”,而是装作“无知”的样子,不露锋芒,以减少麻烦,超脱纠纷。他讲“大智若愚,大音希声”,就是这个意思。越是聪明的人,越要装做傻瓜;越是宣传部长,越要少说话。话说得太多,其实是无知的表现。
老子讲人不仅要装作无知,甚至要去真正地做到无知,做到“绝圣弃智”。他讲道:
智慧出,有大盗。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
民多利器,国家滋昏;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第五十七章》)
它讲了许多“不知而行”的话,其实都是一种手段,所谓“君人南面之术”。比如: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第五十七章》)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第六十三章》)
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
是以圣人,……学不学,……。
他甚至以“无知”来作为一种愚民主张,认为人民的知识多了,就不好统治,他希望老百姓越无知越好。看来,老子的认识论不仅与伦理学有关系,同时还与政治权术联系在一起。他曾经主张对人民要“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这些,历代统治者是很乐意照办的。他还说:
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第六十五章》)
所有这些,同孔子的“仁智统一”的“知人”、“爱人”的学说比较,已经完全走到反面去了。
哲学史上关于“知行”关系的论述,有种种不同的观点。有主张知先行后的,也有主张知后行先的;有主张知难行易的,也有主张知易行难的。孔子与王阳明强调知与行的统一,是知行关系的又一个方面。而《老子》在这个问题上,主张把知行关系彻底割裂开来,是很特别很典型的一派,它对知行关系的分割走向了蒙昧主义和不可知论。在西方,与老子同时,出现了一个崇尚知识,以知识为美的时代。与老子同为“隐者”的赫拉克利特(人称“晦涩哲人”的,西方有赫氏,中国有老子。他们各自成为东西方提出相反相成的辩证法、提出“道”和“逻各斯”的第一人。),充分肯定知识的作用。他认为,“爱智慧的人必须熟悉很多东西。”还说:“凡是能够看到、听到、学到的东西,都是我喜爱的。”(《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5页。)他不仅对感觉经验十分看重,还更加重视思想、智慧也即理性认识在认识中的作用。在他看来,只靠感性经验是不能得到真理的,因为“自然喜欢躲藏起来”,唯有思想、智慧才能“说出真理,并且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老子》认为,只有摒弃一切知识,才能把握住“道”,而赫拉克利特的观点则完全相反,他认为只有不仅凭借听到、看到、学到的感觉经验的东西,而且更要依赖思想、智慧等等理性认识,才能把握“逻各斯”,这个思想、智慧实际就是赫拉克利特反复强调的“逻各斯”。在他看来,认识的根本任务就在于把握这个“逻各斯”。西方哲学尽管没有知行的概念,但可以肯定地认为,知与行的观点在赫拉克利特那里,诚然表现为相互结合而不是相互分离的倾向。之所以仅仅是一种倾向,是因为在赫氏看来,能够把握“逻各斯”的,只是一部分贵族阶层的人。这符合他的身份。知与行的结合也就有了很大的局限性。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则是“人人皆可”的。
古希腊的几乎所有哲学学派,无不以追求知识、崇尚智慧为美德者,以至于出现了智者运动。在智者运动的高潮中,出现了苏格拉底的“道德知识论”,把道德归结为知识,提出“美德即知识”的著名定义。这个论断虽不能完全等同于孔子的“仁智统一”学说,但他把道德与认识、知识与行为结合起来,亦即在知行关系问题上达到了认识论与伦理学的一致性,因而与孔子、王阳明一样,一方面把道德行为知识化和科学化,另一方面又把知识判断和价值判断相联系。这种从认识论上、从科学上来了解道德本质的做法,是积极的、有启发意义的。但是他们都把道德绝对化和永恒化了。当排斥了道德的具体性、历史性和现实性时,他们不约而同走向了唯心主义。
注释:
[1] 一说认为,阳明“立德”、“立功”、“立言”皆称不朽,其实不立文字并非就是不“立言”。
[2] 老子早于孔子的说法也很流行。
标签:王阳明论文; 孔子论文; 知行论文; 认识论论文; 儒家论文; 知行合一论文; 老子论文; 国学论文; 传习录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