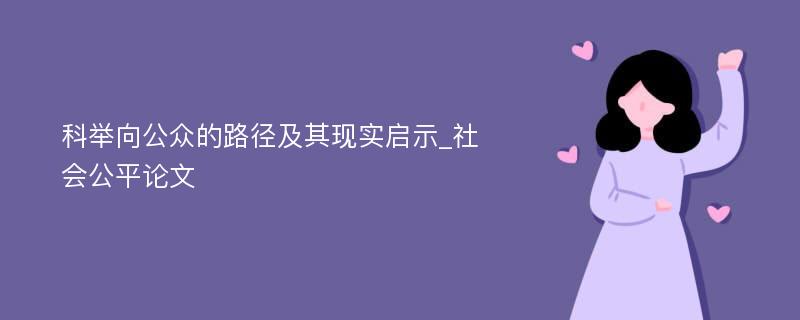
科举至公之道及其现实启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举论文,公之论文,现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0)05-0058-09
在数千年来的中国社会,考试一直是人们获取社会资源、追求上进机会的重要手段,大规模竞争性考试尤其如此。科举制度的长期运行,更将考试这一选才手段的功能发挥尽致,并极大地强化了考试选人的观念。历朝历代统治者都意识到科举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尤其是有着巨大的政治治理功能,为了使这一考试制度具有长久生命力并使其功能得到有效发挥,围绕“追求至公”这一主旨,不断完善科举制度,终将公平的重要性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科举制度的公平性可谓是科举学领域最具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以往学界对科举的公平性虽有不少探讨,但多集中于论证其为公平之制度,鲜见系统阐述科举诸方面公平建设及其得失之成果。本文拟通过梳理科举在报考资格、取士标准、考试录取、考试规制等方面的变革,探寻其变革的走向,总结考试发展的规律,并从科举的“至公之道”提炼出对当今高考改革的启思。
一、报考资格:从封闭到开放
作为竞争的起点,报考资格直接决定着取士范围的大小与考生数量的多寡,制约着取士质量的优劣,是关系到考试制度公平与否的首要环节。从隋唐到明清,科举对报考资格的限制越来越少,竞争机会也越来越公平,与科举之前各种选士制度报考资格的封闭性形成鲜明对照。
在春秋以前,选官实行世卿世禄制,用人标准是“血”而优则仕,政治体制处于全然封闭的状态,平民子弟根本没有入仕的机会,公平的理念与实践都无从谈起。汉代建立察举制后,由于“举主”具有颇大的选择权,并与被举者结成恩主与故吏的深厚关系,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与社会利益由此获得渗透的途径,察举制逐渐沦为把持权势的工具,这一良法美意也被异化为徇私舞弊、以族举德。特别是到东汉晚期,察举制度遭遇了严重危机,群僚举士“名实不相副,求贡不相称,富者乘其财力,贵者阻其势要,以钱多为贤,以刚强为上”,[1]以致当时士大夫以不应辟举为荣。在这样的环境下,无权无势、无依无靠的贫寒子弟得到举荐的机会微乎其微,他们纵有满腹经纶,也只能望“仕门”而兴叹。
到了曹魏时期,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有所松动。曹操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唯才是举”的用人原则。[2]从表面上看,“唯才是举”破除了以往“血统论”的封闭体系,“‘血’而优则仕”变成了“才高则用”,但此中的“举贤者”与前代察举制中的“举主”一样,成为一把“筛子”,将出身卑微的寒门子弟筛出“贤能之士”的圈子外,终难摆脱“血统论”之桎梏。曹丕主政时期实行的九品中正制亦难幸免于此。九品中正制成为拦截在平民与政治体系之间一道无形的高墙,“其始造也……犹有乡论余风。中间渐染,遂计资定品,使天下观望,唯以居位为贵”,[3]从而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结果。这些做法无一例外地限制了人才参选的开放性,除少数符合统治者或选拔者要求的人外,大多数人被拒之门外。
而科举与前代取士办法最大的不同,在于其给予天下读书人平等的竞争机会。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颁发的有关振兴选举和学校的诏令,便可看出其平等开放性:“诸在家及见入学者,若有笃志好古,耽悦典坟,学行优敏,堪膺时务,所在采访,具以名闻,即当随其器能,擢以不次。”[4]对“见入学者”和“在家”者一视同仁,无需出身显贵、功勋卓著或出于官学,只要“笃志好古、耽悦典坟,学行优敏、堪膺时务”,均可参与选举的竞争。但客观地说,隋制科举尚未摆脱前代选士制度之窠臼,对选举对象仍有一定的限制,如:工商者不得与考入仕,对品级不同的官员也待之有别,“文武有职事者,五品已上,宜依令十科举人。……其见任九品已上官者,不在举送之限”,[5]应选者必须由地方州县或高级官员举荐,即所谓的“州举”或“郡举”。因而,和察举制一样,隋制科举在举荐过程中也难免瞻徇私情、爱憎由己,“在外州县,仍踵弊风,选吏举人,未遵典则。……犹挟私情,不存公道。”[6]
及至唐初,科举进行了一场历史性的变革——举子可“怀牒自进”,自由报考。怀牒自进也是科举区别于前代取士制度的重要特征之一。这种做法不分贫富贵贱,基本上没有门第的限制(工商除外),将参政机会向平民开放,在人才选拔史上意义重大。也正是这种开放性,使唐代形成士人“觅举”风尚,“策第喧竞于州府,祈恩不胜于拜伏。或明制适下,试令搜扬,则驱驰府寺,请谒权贵,陈诗奏记,希咳唾之泽,摩顶至足,冀提携之恩。故俗号举人为觅举。夫觅者,自求之称,非人知我之谓也。察辞度材,则人品可见矣。故选曹授职,喧嚣于礼闱;州郡贡士,争讼于陛闼。”[7]觅举即毛遂自荐,觅举之人在当时多为无特殊社会关系的“不为人知”者,所以才需“陈诗奏记”,奔走于权贵之间,希望得到他们的赏识和提携。[8]毛遂自荐之举在隋唐之前虽偶有所见,但始终未被纳入取士制度中,更遑论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唐代的“怀牒自进”对于激发士人奔竞求仕之心、扩大取士制度的社会基础之功效,由“觅举”之风可见一斑。
唐代举子虽可“怀牒自进”,但由于在府州解试和中央省试之间存在行卷(公卷)、公荐、通榜等环节,带有明显的前代荐举痕迹,使得科举的开放性与公平性均受到一定局限。到唐代后期,声誉在录取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乃至于“先声夺人”。尤其是随着应举人数的增多,没有一定声誉者,会大大增加被“遗漏”的概率,诚如柳宗元所言:“所谓先声后实者,岂唯兵用之,虽士亦然。若今由州郡抵有司求进士者,岁数百人,咸多为文辞,道今论古,角夸丽,务富厚。有司一朝而受者几千万言,读不能十一,即偃仰疲耗,目眩而不欲视,心废而不欲营,如此而日吾能不遗土者,伪也。唯声先焉者,读至其文辞,心目必专,以故少不胜。”[9]由此而造成唐代科场请托奔竞之风盛行,“收入即少,责争第急切,交驰公卿,以求汲引,毁訾同类,用以争先”,其结果,不仅“浸以成俗,亏损国风”,[10]而且请托关节带来的权贵干扰、垄断科场也损害了科举的公平性,以致“贡举猥滥,势门子弟,交相酬酢,寒门俊造,十弃六七”。[11]出身寒微的平民子弟若无显贵相荐,则难入杏门,只能发出“空有篇章传海内,更无亲族在朝中”之愤慨。为了从制度上堵住权势干扰取士的漏洞,唐代科举不得不增设覆试环节。到了宋初,为杜绝科场“因缘挟私”,遂“诏礼部贡举人,自今朝臣不得更发公荐,违者重置其罪”,[12]宋代科举的开放性与公平性自此得以增强。自隋唐至明清,科举对报考资格的限制越来越少,宋代已允许工商、“杂类”人等报考,清代除倡优、皂隶之家与居父母丧者外,原则上所有人均可报考。
自由报考意味着报考资格从封闭走向开放,使选拔对象的范围从少数人扩大到社会各阶层,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被纳入其轨道,选拔出真才的概率自然比封闭的体制要高得多。更重要的是,自由报考使人人享有了平等竞争的机会。早在唐末五代时,就有人感叹科第之设,使有才干的草民得以出人头地,无其才的王孙公子沉迹下僚。[13]比起世卿世禄或任人唯亲的选官制度,不问阀阅、凭才取人的科举制度,可以说是在等级森严的中国封建社会中难得的一项具有公平精神的制度。[14]
二、取士标准:从主观到客观
在科举时代,取士标准直接关系到考试录取的结果与考试制度的成效,同时也与公平攸关。取士标准的划分大体上有两个维度:主观与客观。主观的取士标准难以量化,对其把握受到人为主观因素的影响,因而可能产生个体判断上的差异;客观的取士标准则可量化,便于进行刚性的衡量与取舍,不受个体主观因素的影响。中国历史上的官员选任制度,大致可划分为世袭任官、推荐选举与考试选拔三大类。其中,世袭任官的标准是单一的“‘血’而优则仕”,无所谓选拔。以察举为代表的推荐选举(荐选)和以科举为代表的考试选拔(考选)则分别与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相对应。取士标准从主观的荐选走向客观的考选,且越来越刚性,是科举制度公平诉求的必然结果。
科举建制前的官员选任办法主要是荐选,如周代的选士制度、汉代的察举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等。即使到了隋唐,科举的有些环节如“行卷”、“公荐”等,如前所述,也带有前代荐举遗风。荐选的依据主要是士人的德行、道艺与才能,如周代选士制度评选人才的标准分为三等:“德行为上,其次治事,再次言语,一律皆采取平日的素行。”[15]九品中正制也同样,人才品第的高下,主要依其资历与品德,而品德所依据的仍是人才所在地的群众舆论与公共意见。荐选固然可以将人才分为三六九等,官吏的任用黜陟表面上看好像有了客观标准,但分等的过程却难以量化,无论是德行、治事抑或言语的高下,都取决于评定者的个人判断,受制于主观因素的影响。
隋炀帝大业元年(605),置进士科,策试诸士,遂开考选之先河。其实早在北朝,已出现门资比重日益降低、才学比重越来越大、察举制逐渐朝“以文取人”方向发展的趋势,考试日渐成为察举的中心环节。但北朝的察举选士仍须先由州郡保举,然后由朝廷策试,并非自由竞争。而隋选进士,是州郡策试在前,朝廷策试在后。所以,从程序上看,后期的察举是选举与考试并行,其基本精神仍难脱选举之窠臼,科举则是纯粹地举行考试了。[16]相应地,隋朝以后,取士标准也发生了变化,“主要以考试成绩决定取舍”①,宋代以降,更是“一切以程文为去留”,[17]取士标准越来越刚性。
荐选与考选这两种办法本无所谓高下优劣,而是各有短长。荐选由于看重“平日之素行”而非一时之表现,与“选贤与能”的初衷有较高的一致性,因而,比之以单次考试来评定举子的做法有更高的效度。事实上,荐选使用之初,也确有其效。例如,中正初设,“所论惟在德行,重清议,据行实以登下其品第,以是立名教之防,使知名勇功之士,不敢有裂冠毁冕之为。”[18]然而,言采易见,德行难知;策试可凭,考察难见。荐选的流弊如前所论,由于无法量化,极易困于人情。
荐选与考选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是“人对人”,后者是“人对文”。“人对人的好处是常能看到人的全部:不仅文章、学问,还有德行、才干;也不仅一时表现,还有平日作为,乃至于家世根底,但假如推荐者私心膨胀而又外无制约,荐选也易生营私、结派、请托、谬滥的流弊。”[19]因此,荐选的效果完全取决于评选者的素质。“人对人”的主观性,容易造成荐选实践中“泥沙俱下”,与才干相关的学问、德行、能力以及与才干无关的门第、奔竞、请托,都可能影响荐选的过程及结果。荐选的目的本来在于举荐贤才,非俊莫用,但从史实来看,各种荐选制度无一例外地陷入人情的泥潭不得自拔,造成荐选结果名实不符、唯在门第。“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则荜门蓬户之俊,安得不有陆沉者哉。”[20]这种不公平极大地挫伤了广大平民上进的积极性。
荐选与考选互有短长,可相得益彰。正是由于荐选流弊重重,取士制度在隋唐有了历史性的突破,由以往“人对人”的荐选变成“人对文”的考选。考选有效地避免了荐选易羁于人情之流弊:“用一种客观的测验方法,来判断各方面所举的人是否贤能?这一作用,不独可以判断贤否,而且可以避免恩怨,就成为考试制度的精神所在了。”[21]“人对文”的考选有如当今的高考,评判者面对的是考卷而非考生本人,从而过滤了“人对人”办法中荐举者对于被荐者爱憎、好恶的私见与偏颇,有利于客观公正地选拔才俊之士。尤其到了明代,考试文体变为八股文后,衡文的刚性又迈上了新台阶,取士办法更加客观、公平、公正,“科举取人用考试的方法,完全依据客观的尺度做取舍的标准,考官丝毫不能任意出入。所以自唐代奠立科举制度以后,凡属具有真才实学的人不难有脱颖而出的机会,这是用人唯才主义的实际应用,实足以救‘乡举里选制度’之穷,防‘九品中正制度’之弊,这又是中国政治发展史上的一种大改革。”[22]
当然,考选办法采行客观、刚性的取士标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在克服荐选流弊的同时,也丢弃了荐选“重平日素行”之所长,并因此屡遭非议。千余年的科举史上,在提议改革或废止科举时,曾屡次尝试以德行荐举人才,取士标准常在“以德举人”与“以文举人”之间“拉锯”,但结果总是客观的“文才”标准胜出,主观的“德才”标准无疾而终。例如,明朝朱元璋政权建立伊始,即下诏“特设科举,务取经明行修、博通古今、名实相称者。……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但三年后,朱元璋发现“所取多后生少年,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寡”。[23]这让对科举寄予厚望、“以图至治”的朱元璋大失所望,遂诏令罢废科举,“别令有司察举贤才”,并提出“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24]的荐举标准。但由于荐举结果无法量化,“所举者多名实不称,徒应故事而已”,[25]因此,在停罢科举十年后,明政府又不得不恢复采用它。
科举考试文体的变迁也反映出取士标准的这种走向。科举考试文体在唐代重策与诗赋,宋代重策论、经义,明清只重八股制艺,放在明清科举三场考试中头场的八股文是科举的首要内容,成为举子跻身仕途的“敲门砖”。之所以如此,不仅因为文兼众体的八股文能满足科举对举子进行多方面考核和必须有相当难度与区分度等要求,而且因为它具有“规范竞争,防止作弊,客观衡文”[26]等功用,从而使作文这种主观性很强的文体变成一种标准化考试文体,以便最大限度地降低因主观评分误差而导致的结果不公平。
正是由于人的道德品质较难客观评量,以德行取士无法保障公平公正性,科举每次都旋罢旋复,最后仍不得不回到标准刚性的“以文举人”的老路上来。刚性、客观的标准有利于排除人为因素的干扰,使“‘科甲’面前人人平等”成为可能。取士标准的变革越来越朝向客观的方向发展,实在也是选才发展的规律所使然。
三、考试录取:从追求考试公平到兼顾区域公平
考试录取既是一个关系到考生竞争结果的技术问题,也是一个影响到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科举在考试录取上存在着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孰轻孰重这一千古难题。考试公平是指依据考试成绩公平录取考生,区域公平是通过区域配额来控制地区之间考中人数的悬殊差异;考试公平倚重考试结果,区域公平则偏重地域均衡。总体而言,科举录取从开始阶段单纯追求考试公平,逐渐演化为在注重考试公平的同时,兼顾到区域公平。[27]
在隋代和唐初的科举中,地方级别的州郡考试沿袭东汉以来的“均衡举额制”,按人口比例举送考生,但在全国一级考试则不分地区取中,完全奉行“自由竞争”的考试公平原则。盛唐以前,由于考试内容以经术为主,北方士子往往更守先儒训诂,质厚但不善文辞,而南方士子正好相反,好文学而轻经术,致使北方人在科场竞争中占有绝对优势。例如,唐代357名宰相中,北方人占91.3%,南方人仅占8.7%。[28]及至唐朝后期,科场开始崇尚文学性质十分突出的进士科而冷落以儒家经术为主的明经科,加之经济、文化、教育重心因战事而逐渐南移,北方士子在科场竞争的优势逐渐减弱,南方士子的优势则明显增强。
到了宋代,科场录取人数比例开始出现南北倒置现象,从北宋可考的9630名进士中4.8%为北方人、95.2%为南方人[29]这一事实便可见一斑。由此,引发了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一场分别以朝廷重臣司马光和欧阳修为代表的科举取才南北地域之争。司马光力主在考卷上“各以逐路糊名,委封弥官于试卷上题以在京师、逐路字,用印送考试官,其南省所放合格进士乞于在京、逐路以分数裁定取人”,[30]并提出逐路取人的具体比例。欧阳修则认为,科举比于前世“最号至公”的原因即在于其“不问东西南北人,尽聚诸路贡士,混合为一,而惟材是择”。而且,由于东南之士初选已精,故至省试合格者多,西北之士学业不及东南,初选已滥,故至省试不合格者多。若一律按统一比例录取,则东南之人应合格而落选者多,西北之人不合格而得者多,这样是取舍颠倒、能否混淆,会造成另一种不平等。因此,他主张“且尊旧制,但务择人,推朝廷之至公,待四方如一,惟能是选,人自无言”。[31]结果仍依成法,一初以程文定去留。这场争论既包含朝廷政治势力博弈的因素,也反映了科举录取的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之矛盾。
明初,南方举子在科场的压倒性优势依然如故,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的矛盾愈积愈深,以致爆发了充满血腥味的“南北榜事件”。明洪武三十年(1397),刘三吾主考会试,“榜发,泰和宋琮第一,北士无预者。于是诸生言三吾等南人私其乡。帝怒,命侍讲张信等覆阅,不称旨。或言信等故以陋卷呈,三吾等实属之。帝益怒,信蹈等论死,三吾以老戍边,琮亦遣戍。帝亲赐策问,更擢六十一人,皆北士。”[32]在这一事件中,刘三吾所取皆南士其实是坚持“择优录取”和“考试公平”原则的结果,而朱元璋处死或发配考官和状元、亲自主考和阅卷且所取皆为北士,则明显带有地域笼络的政治色彩。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这一问题再次被提出,仁宗认为“科举之士需南北兼取……比累科所选,北人仅得十一,非公天下之道”,[33]遂令大臣讨论具体名数。大学士杨士奇提出南北分卷的设想。两年后,南北卷制度正式实施。
到了清初,会试取中分为南卷、北卷和中卷。例如顺治九年(1652),会试取进士共400名,其中,从浙江、江西、福建等地取南卷233名,从山东、山西、河南等地取北卷153名,从四川、广西、云南等地取中卷14名,南、北、中卷的取中定额占总定额的比例分别为58%、38%、4%。但这样的划分还是比较粗糙,省区之间的录取机会仍有很大差距。所以,到了康熙五十一年(1712),“以各省取中人数多少不均,边省或致遗漏因废南、北官、民等字号,分省取中。按应试人数多寡,钦定中额。”[34]
显然,科举按区域录取且区域划分越来越细并最终被分省定额取中制度所取代,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追求区域公平的政治考虑。分省定额取中、注重区域公平的做法虽然与“唯文是论”的考试绝对公平原则有某些矛盾之处,但明显缩小了地域间人文教育水平的差距,对于调动落后地区士人的学习积极性、维护中华民族统一等都有积极意义。例如,清政府为安抚孤悬海外的台湾,于福建乡试的录取名额中专为台湾士子设立了保障名额,台湾考生的举人配额从康熙时的1名逐渐增加到咸丰以后的6名。在会试一级,从乾隆以后规定在福建省名额内专门编出“台”字号,如果台湾籍会试举人在10名以上,就至少取中1名进土。这种优待办法使台湾士子欢欣鼓舞,更加热衷于渡海来大陆参加乡、会考试,增加了台湾读书人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凝聚力的加强。[35]科举录取从追求考试公平走向兼顾区域公平,有其深远的政治意图,有利于均衡地域教育文化水平差异,扶持弱势地区的社会发展。
四、考试规制:从简疏到繁密
科举除了在报考资格、取士标准、考试录取等几个主要方面进行了划时代的公平变革外,在考试规制与防弊技术方面也日臻严密。如果说,科举在唐代主要注重“以法治考”,规制也尚显简疏,到了清代,从规制的颁行到贡院的形制则已繁密周详,对弊窦的惩处也异常凌厉,直至成为一种各环节“滴水不漏”的“至公”之制度。
为防范科举中的舞弊现象,保证科举活动的公正性和制度的严肃性,历朝历代都颁行了详略不同的考试规制。唐代颁布了“废举者”、“坐州长”等诸多法令,对考试不实者作出详细的法办规定。在《唐律疏议》、《唐六典》、《册府元龟》等典籍中均可找到有关科举的法令规制,并实行了入场搜检、考官锁院、别头试、覆试等关防弊窦的手段。宋元两代也各有不少科举条规或法令,如《宋大诏令集》便收录了35条科举诏令,在宋代编敕中也有不少关于科举的单行法,如《天圣礼部考试进士敕》、《至和贡举条制》等;《元典章》之《礼部·学校》和《大元通制条格》之《学令·科举》中,也有许多关于科举的法令,其中《科举程式条目》对元代科举的考试程序、考官选试、取中数额、科场规则等都作了详明的规定。[36]宋代创建的殿试制度、糊名法、誊录法与双复位等第法,对后世科举乃至现代考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极大地提升了科举的严密性与公平性。明代科举在考官选任、考场、阅卷以及取录各环节已形成一套严密的规制,还形成了明远楼、号舍等独特的贡院形制,从明远楼到至公堂,从外帘到内帘,贡院的所有建筑布局谨严有序,蕴含着统治者力求维护考试权威和保证考试公平的良苦用心,使明代科举赢得“天下之公”的美誉,时人亦认为“我朝二百余年公道,赖有科场一事”。[37]到了清代,由于清廷乃“部族政权”入主中原,出于稳固统治基础的考虑,将科举作为“羁縻牢笼”手段之意图格外急迫,“乡会两闱,乃国家抡才大典,必须防范周密,令肃风清,始足以遴拔真才,摒除弊窦。”[38]所以,清代不仅承袭明代的贡院规制,而且频频立法,以严防弊窦,死守公平,笼络人心。由杜受田等修、英会等撰的《钦定科场条例》便是清代考试规制的最集中体现,洋洋大观达60卷之多,对科举各层级、各环节的考试事宜以及违纪惩处都作了非常细腻的规定,可谓密于凝脂、不厌其详,而且还根据实际发展需要每十年增修一次。
明清两代尤其是清代的科举考试与防弊规制可谓集历代之大成者,“没有研究过贡院规制和科举程序的人很难想象其严密精细的程度,研究过贡院规制和科举程序的人则很难忘却其严密精细的程度。”[39]例如,为防举子夹带,对举子在试场的服式、用具等都作了严格规定:“帽用单层毡,大小衫袍褂,俱用单层,毡衣去里,裈裤绸布皮毡听用,止许单层,袜用单毡,鞋用薄底,坐具用毡片,其马褥厚褥,概不许带入,至士子考具卷袋,不许装里,砚台不许过厚,笔管镂空,水注用瓷,木炭止许长二寸,蜡台用锡,止许单盘,柱必空心通底,糕饼饽饽,各要切开。……至考篮一项,或竹或柳,编成玲珑格眼,底面如一,以便搜检。至褌裤既用单层,务令各士子开襟解袜。”[40]贡院关防之缜密、监视之严厉,“几有鸟飞不下蝇螢不入之势。”[41]
再如,明清科举阅卷环节有“搜落卷”之法,主考官除阅读分房考官的荐卷外,还对未中式的落卷尽数搜阅,以防考官“误抹佳文”甚至“挟私妄抹”,造成遗珠之憾;不仅如此,还在乡、会试开榜后,由礼部、顺天府等处出示,十日内令落第士子阅看或领回落卷,旨在令士子信服,以示至公。此举既可督促考官严谨判卷,又可平反冤案和安抚落第士子,以杜绝科场舞弊、维护科举公平。更重要的是,可以促使政府将所有阅卷过程出现的问题及制度上的漏洞在发领落卷之前尽最大努力加以解决,以保持社会稳定。[42]
除了颁行周密的规制,清朝还对科场舞弊事件刀挥斧砍,制造了一起起惊心动魄的科场案。清廷正是通过严密规制、严肃法纪和严惩舞弊,来维护科举作为“抡才大典”的公平与权威,以实现其奉为圭臬的“至公”理念。是故,清代科举“立法之周,得人之盛,远轶前代”。[43]
五、现实启思
从科举变革的历史梳理不难看出,无论政权如何更迭,帝制政府始终不遗余力地以公平为依归对选才制度进行改革,换言之,公平始终是科举变革的“关键词”。科举正是通过千余年的公平变革,最终成为一种不仅有广泛世界影响而且有深远历史影响的制度,在追求公平方面,更是一个永恒的典范。同样,在当今中国,高考改革的公平问题也可谓是一根牵动社会的“敏感神经”,高考哪怕一个小小的改革,也会经由民众的关注使其社会影响被无限放大。“公平是社会大众对高考最为关注的一个方面,也是高考制度的基本功能和精神之所在。”[44]是故,高考自建制以来的几乎每一项改革,都与“公平”二字紧紧捆绑在一起,尤其是近年来,教育部在提升高考的公平性上可谓不遗余力。
由于历史、传统、观念、文化、制度、现实国情等原因,高考改革仍存在诸多不如意与不公平,其考试形式、考试科目、考试内容、录取机会、志愿填报、高考加分、综合评价、自主招生等方面的改革,无一不在公平、科学与效率之间徘徊取舍,在各种矛盾或两难中百转千回。高考改革的一些新举措,在克服传统弊端的同时,又带来了新的不公平。因此,高考作为一项规模大、牵涉广、难度高的改革,非常需要“瞻前顾后”、放眼权衡。这就要求高考改革既要置身于宏阔的现实与国际背景,又要有辽远的历史视域。然而,在当下高考制度的公平建设过程中,有一种需要检视的现象:越来越多的人们热衷于推介“他山之石”如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先进经验,不乏“往外看”,确使改革的视域日益宽广,让人欣慰;却鲜有“回头看”,缺乏对我国考试历史与考试文化的淘沙与探寻,令人惋叹。而历史与文化对高考改革的影响力,实际上远大于域外的影响力。在我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考试历史传统与深厚考试文化积淀的国度,高考改革“回头看”尤其重要与必要。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同为大规模竞争性考试,古代科举与当今高考有许多相通、相似乃至相同之处。科举的公平理念与措施不仅在历史上具有先进性与现代性,在当今社会仍具有普适性,有些做法的公平程度至今未被超越,有相当丰厚的历史遗产值得今天的高考所继承。我们不能因为科举废止百年来社会对它“一边倒”的批判而患上“历史健忘症”。科举虽已停罢,但深含公平精神的考试选才方式却没有而且不可能被废弃。[45]
考试改革须首重公平,是科举给高考最重要的启思,也是科举留给当今社会最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历朝历代有关科举的变革与争议,无一不以“公平”为重心,正如美国学者费正清所说:“在一个我们看来特别注重私人关系的社会里,中国的科举考试却是惊人地大公无私。每当国势鼎盛、科举制度有效施行时,总是尽一切努力消除科场中的徇私舞弊。”[46]虽然从变革动机的深处看,科举制度的公平建设因与权贵的既得利益相冲突,可能并非基于改革者内心真正的公平理念和“以民为本”思想,而是出于统治者维护和稳固政权的需要,但从变革的结果看,科举的公平建设产生了实实在在的社会效益,使这一制度日臻完备,长存千余年之久,成为帝制统治秩序坚如磐石的重要支柱和中国古代文化绵延不绝的重要基石。这样的社会效益理应冲破时代与政治的藩篱,为当今中国社会所追求。作为当今中国影响最重大、最广泛的教育制度之一,高考的不公平可以说是一个潜在却不容忽视的社会安全隐患。因此,高考改革必须首重公平。这既是保护民众个体权益的需要,也是维护国家政局稳定的需要。[47]
再者,由于科举与高考有诸多惊人的相似,它的许多规制可以成为高考改革的重要参考。例如,近年来高校自主招生、保送生制度、高考加分、综合素质评价等改革,都与招生标准的取舍密切相关,改革中引发的公平争议,与科举取士标准中关于荐选与考选孰优孰劣、“德行”与“文艺”孰轻孰重之争如出一辙;高考录取的地域歧视之争,与科举录取中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之争有本质的相似,与之相关的“高考移民”则是科举“冒籍”的现代版;高考标准化考试题型僵化与内容局限等非议,与八股文(标准化试题之滥觞)考试的优劣利弊之争也有颇多共性;当今高考一些主观题阅卷的“秒杀”速度,与科举阅卷的谨严认真形成强烈反差;等等。这些问题、争议及其改革,都可以直接或间接从科举中吸取经验教训。此外,科举考试的覆试、磨勘、双复位等第法、考试立法、“搜落卷”等措施,对高考的形式改革、考试严密性、考试法制建设、高考评卷等也不无启思与借鉴。
(本文得到2007年度“福建省高等学校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的资助)
注释:
①张希清教授认为,在隋唐五代及宋初,决定科举取舍的因素有“通榜”、“公荐”等推荐的成分,举人的程文即试卷所起的作用反而甚小。直到宋仁宗庆历元年废公荐,罢公卷,程文始成为评定艺业、决定去取的唯一根据。因此,在庆历元年之前的四百多年间,均非“一切以程文为去留”,而是“主要以考试成绩决定取舍”。详见其《科举制度的定义与起源申论》,《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