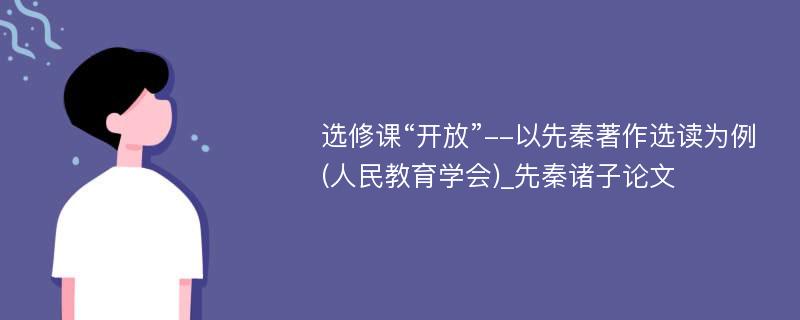
为学生“开放”的选修课——以《先秦诸子论著选读》为例(人教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诸子论文,选读论文,论著论文,先秦论文,选修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标题中我用“开放”一词的旨意,便是强调选修课不仅要让学生在选修内容上拥有绝对自由的选择权,学习过程中也要以学生自修为主,体现学习的自主性,并且还要确立重过程轻结果的多元评价体系,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下面我以文化论著研读中《先秦诸子论著选读》(人教社)为例谈谈我的设想。
一、爱我所爱,选我所选
对于选修课,课程标准规划了诗歌与散文、小说与戏剧、新闻与传记、文化论著研读、语言文字应用5个系列,并对每个系列的课程目标、教学实施、教学评价提出了具体要求,但每一系列有哪些模块,课程标准仅做了部分示范性举例,供课程开发者思考。比如文化论著研读系列有《先秦诸子论著选读》《人间词话》选读、《歌德谈话录》选读、中华文化寻根、社区文化专题。从课程安排的时间来看,高中六个学期,有三个半学期是选修课,而且课时安排在高二年级上半学期第二学段开始。在课程实施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由于硬件和软件的诸多缺陷,目前所谓的“选修课”,几乎全部由学校强行规定,一刀切,甚至干脆全省统一规定几门课,学生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另外,为了赶高考复习的进度,一般学校都将选修课压缩到高三年级上学期全部完成,甚至更早一些。这就意味着每一个系列的选修内容都必须在半个学期一个时段内完成(40节课左右),在每一个学段可供选择的同类课程模块几乎不可能超过2个,选择的空间大大缩减了,一线教师所能做的就只有在极为有限的选择空间内尽可能让学生有更多样、更丰富、更自由的选择,虽然这近乎是一个属于悖论的命题。
考虑到先秦诸子作品本身的难度和作品与学生在时空上的“隔阂”,教师在学生研读之前的导读和引导很关键,先引“登堂”,产生兴趣,才能探究研读,继而“入室”。我们可以采用影视讲座式。先秦诸子的电视讲座先有于丹、易中天、傅佩荣等教授做客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后有易中天、钱文忠等教授做客山东电视台的“新杏坛”,《孔子》电视连续剧和电影《墨攻》想必也会吸引同学们的眼球;戏剧、小说改编和漫画作品也是不错的选择。林语堂先生改编自《论语》的戏剧作品《子见南子》曾在当时引起轰动效应,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用旧瓶装新酒,以先秦诸子形象说他自己的故事和感悟,今天读来依然饶有趣味。相比之下,蔡志忠先生的系列漫画可以说是最忠于原著的,只是冠以漫画的形式,现在还有Flash动画版,不同凡响;此外我们还可以从研究学者和专家的论著引入,钱穆先生和李泽厚先生分别从史学和哲学的研究视阈来解读先秦诸子作品,鞭辟入里;而李零先生、傅佩荣先生和南怀瑾先生则旁征博引,将先秦诸子作品引入到现实生活中来解读,具有现世关怀;林语堂先生的解读则带有强烈的个性色彩,其著作《国学拾遗》代序部分有一段抒情性的文字:“孔子是一位令人心悦诚服的人,他不讲哲学,不谈神,也不论死后之事。像苏格拉底,或者像美国的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孔子只是一个聪明的、年长的、深刻的、非常机智的思想家。他只论日常的生活和如何生活。”让我们一下子亲近了原本有隔阂感的“大师”;当然我们也可以从评价我们身边的生活现象入手,从最近热热闹闹的“国学热”谈起,2008年9月,“四书”成为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实验班本科生必修课的内容,开课教授彭林表示,这种尝试是为了让学生掌握民族文化经典,背诵“四书”有可能作为考试的内容之一。从事机械制造研究的中科院院士杨叔子则要求其博士必须会背《论语》,否则不准予答辩。福州等地还出现了“汉学馆”,小朋友们开始穿汉服,读经典了。想一想,“国学热”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思考和启示?当然,任何思考和评价无疑应该建立在细心研读基础之上。
我们大可不必急急忙忙带着学生进入自修研读阶段,可以先用二周左右的时间,用上述多种导读方式让学生去感受、体验,然后再选我所选,爱我所爱。其丰富活泼的形式比较符合现今高中生的阅读接受心理,能够激发他们进一步研读和探究的兴趣。文化经典固然有它无可比拟的“魅力”,但也需要新颖生动的“包装”。我们倡导一种“主体性的阅读”模式,学生在进入真正意义上的阅读之前,要带着自己独特的感受和体验进入作品,可能这种感受很模糊、很粗糙,还不一定正确,但是有自我的感受才能融入作品。只有阅读主体主动去搅动作品客体这“一潭池水”,才会兴起波澜,发生碰撞,产生共鸣。因此,兴趣和热情才是阅读的不二法门,它是阅读主体持续探究和拓展的原动力。
学生对于研读的内容拥有绝对的选择自由,选修教材中出现的《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等内容,学生可以选择其中一部书或是某些篇章进行研读;或者选择某个“专题”研读各家对此的论述,拓展探究异同之处;也可以就导读中出现的某个场景、改编的内容、他人的评述等,对原著进行微观阅读,联系整理并加以印证和比较;甚至可以自己选择一个关于先秦诸子思想内容的“话题”,研读思考,形成自己的看法和认识。选修的内容可以多种多样,各有不同,但殊途同归,我们最终是要让学生切实掌握研读的方法,提高研读的能力,用自己获得的“金钥匙”打开文化论著宝库的大门。
作家老村回忆说,他童年生活在陕北的边远山区,没有书读,一个偶然的机缘,得到一本残缺的《道德经》,自然是看不懂。但因为没有其他书,就只得翻来覆去地读这本残书,开始是硬着头皮读,读的遍数多了,就慢慢地有所领悟,进而越读越有兴趣,读进去了,就仿佛“登堂入室”,一下子和整个民族、甚至人类的文化接通了,从此,终生受益。显然,老村的经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学生选修的课程内容和最终形成的结论往往是多样,也是可变的;而过程与方法却可能反映出带有一定普遍性和规律性的东西。只要学生注重研读的过程,掌握研读的方法,养成独立探究的能力,“文化论著研读”的教学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二、自修为主,研读质疑
新一轮课程改革的重点之一是学习方式的变革,既然选修内容由学生自己来“选”,那么“修”也应该以学生自修为主。一方面,对于必须让学生掌握学生又能理解和掌握的,如文言词语、基本句式和一些基本的文化常识等内容,可以放手让学生自己去研读;另一方面,对于学生较难理解,又是作品思想精要之处的内容,教师可以稍加提示,或者提供相关的课程资源,不做详解,留下余地,让学生自己琢磨探究。同时在阅读过程中强调问题意识和反思精神,引导学生善于探究论著中的难点和疑点,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并乐于和他人交流切磋,共同提高。
先秦诸子散文是文言体式,文本中出现的实词古今异义、使动、意动、虚词的特殊用法等语言现象,可以在必修的基础上进一步训练学生阅读古文的能力。教师建议和推荐必要的工具书和参考书目,包括疏通语言文字的《古代汉语常用词语手册》,诸子论注类的书籍,如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孟子译注》和李鍌先生的《国学基本教材》,引导学生对学习中碰到的语言现象归类整合,完成语言文字的理解和积累,同时培养学生自主阅读古文的习惯,提升阅读能力。此外,选修内容相同或有联系的同学可以组成一个学习小组,便于相互质疑、交流心得,人教版选修教材《先秦诸子论著选读》篇幅有限,尤其是《老子》《墨子》《韩非子》只选读二三篇选文,远不能满足学生选修探究的需求。一本教科书在有限的篇幅里要涵盖某一模块的全部内容是很难的,再说采用文选体式的教科书也难以满足学生多元的求知需求,更遑论只有可怜的二三篇选文了。对于选修的课程内容,学生至少要将研读的内容,结合原著通读一遍,再读几本相关论著,才有可能为下一阶段的深入探究奠定基础。因此,我们要让学生树立选修一门课程,而不是选读一本教科书或相关章节的课程意识。
选修课的一大难题,是有限的修习时间与修习内容过于丰厚之间的矛盾,解决的办法是,在学生自主修习一段时间后,针对不同学习小组提出的“研读过程中碰到的难题”,学生共同探讨、交流或者教师进行有针对性的精讲点拨,启发求思。比如《论语》中“学”这个词语有着丰富的内涵。“学”指的是“学问”,但不仅限于我们认为的满腹经纶的书本知识,还包括人格修炼、道德完善、做人道理等内容。孔子主张学习的博而广,不能偏颇、单一,他提出“文、行、忠、信”(《述而》),即文化知识,品德修养,忠诚笃厚,坚守信约,这与现代教育所强调“知识”不同,孔子认为品德行为和文化知识相比,前者更重要,“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宜学文。’”(《学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结合下面两则材料来读,我们发现其实这四者又是缺一不可的统一体,“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学而》)“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学而》)我们还看到孔子对得意弟子颜回好学的评价是:“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雍也》)孔子称赞颜渊好学,是因为他能在内心深处用功,与只注意外在才能事功者不同,求学解惑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践行真知的行为,正如《易·系辞传》的评价:“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由此看来,学习的内容要博要广,但一以贯之的其实就是对未知事物的“求真”和“践行”。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卫灵公》)孔子在回答子贡的问题时,说明自己的“多学”是相对的,在多学的基础上,我是用一个道理来贯穿自己的学说的,这个道理就是学习的根本。
“自修”环节,教师一定要强调问题意识和反思精神。引导学生在阅读过程中注重反思,探究论著中的难点和疑点,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对于那些学生自己较难把握,又是理解论著思想之精要处,教师可以展开类似的点拨示范,以期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或者给出具体的提示,让学生学会通过各种途径和课程资源自行探究,自修自得;或者提供相关的参考文献和资料,让学生自己进行联系和整理,加以印证和比较,形成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并且和其他同学或老师交流。对于那些学生一时无法理解,或这一阶段的阅读不需要他们理解的,则可略而不讲,学生也可不求甚解,囫囵吞枣。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讲有所不讲,有所学有所不学,也体现了对自修内容、修习程度的选择性。而学生能否在必修基础上有所拓展和提升的关键也正在于此。
三、个性自主,评价多元
评价是学生学业发展的激励机制,评价的最终目的,不是判定学习成绩,而是激励学业发展。选修课的评价更应该追求多元,促进个性发展。不同于必修课程“一场考试定终生”,选修课程评价内容和标准是多元的,可以是包括静态的检测,如阶段性的测试、研究总结、研读小论文等,也可以是动态的学生研读成长记录,考查学生在每个具体的时间段阅读的量与面、查找资料和收集信息的能力、综合运用研读中获得的知识和能力等。评价内容和标准的多元,意味着我们必须找到可以与之相匹配的评价形式,我们并不排除考试,可以用它来考查学生在自主修习的过程中形成和提升的古文阅读能力,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研读成长记录表”、读书笔记、专题交流心得会、研究小论文等过程性的评价形式来考核。除了教师评价和学习同伴评价外,鼓励家长和社会也参与到评价中来,使评价成为学校、教师、学生、同伴、家长、社会等多个主体共同积极参与的交互活动。评价过程体现全员参与,评价方式变得公开、开放,更好地促进竞争意识,产生激励效果。
可以尝试利用计算机和网络这一现代科学技术为我们的评价活动服务。计算机网络技术既可以打破时空界限,进行远距离的长时段的观测,又具有可重复性,便于进行大量的统计性评测,以保证评价的相对准确性;更重要的是,便于多方面人员的参与、检测,以保证评价的公平性和多元性。比如说,同一个研读学习小组的同学可以在一个共同的空间里开辟一个专栏,研读过程中出现的疑问、心得、发现,都可以在网上现场讨论,因为这个过程是在公开、开放的网络上进行的,就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参与这个讨论,同伴、老师、家长、网友,甚至还可以和国内外相关领域知名的专家和学者进行探讨。讨论和争辩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考查与评价的过程,它明显的优点在于,知识和能力的考查隐藏在“问题”的背后,不但不会使学生反感,造成心理的压力,而且能引起学生的巨大兴趣,并能激发起创造的激情,并且在相互的争辩、交流中进行自我评价与相互比较性的评价。我们所向往的“激发式”的,考查者与被考查者“共同参与式”的评价理想,在这里或许可以得到实现。
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已实施四年的选修课现状令人担忧,其中课程开发方面存在的问题最为突出。目前,选修课的课程开发基本上都被各教材出版机构的教材开发所取代,而本应该成为课程开发主力军的教师一方面由于高考的制约,另一方面由于自身知识能力所限,事实上未能担负起主角的责任和义务。语文选修课的课程开发,要求教师具备课程论层面的有关知识,同时还必须具备该门选修课程的学科知识,并且对这一学科知识的把握应当是深入、系统的,这就对语文教师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但是,在有限的时间内,让教师对至少五个系列的选修课程,有博、专、深、透的理论素养和专业知识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同一备课组老师可以分工协作,难度依然很大。如果我们采用网络评价的方式,可以适当缓解教师的压力和束缚。我们可以选择边学边做,边做边学,还可以跟学生展开互动学习,教学相长。这也恰恰印证了后现代主义教育的观点:知识具有非确定性、个人性和实践性的特点。
注释:
① 《中国教育报》2009年1月9日《关键词:四书》。
② 钱理群《语文教育门外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③ 钱穆《论语新解》,三联书店2002年9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