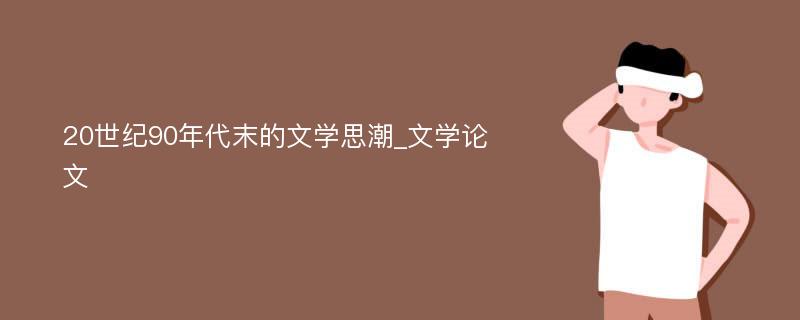
晚生代与九十年代的文学流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生论文,流向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晚生代”这个概念缘起于我数年前写的一篇关于先锋派的论文《最后的仪式》,并且在多篇文章中有所发挥。后来同行朋友时有借用,有的加以注明,有的未加注明。这个概念最初用以描述八十年代后期出现的先锋派群体,在很大程度上,这个概念是多次与先锋派作家交谈的产物。当然,更重要的是依据他们在叙事中表现出的那种态度和方式,那些意义和风格──他们是当代生活的“迟到者”,摆脱不了艺术史和生活史的“晚生感”。当然“晚生代”并不是历史最后的守灵人,文学史总是有后起之秀,更新的群体不可避免要登上历史舞台。在如此短暂的历史空档,在如此相近的历史布景面前,又一个新的群体迅速崛起,应该如何给他们命名,这确实是件令人难堪的事情。没有命名将无以描述新的历史现象,无法给出恰当的历史位置。我曾经试图用“后晚生代”来标出这个新群体的文化位置,但在这个疾“后”如仇的时期,我终究还是有所顾忌,倒不是我个人惮于那些恶意中伤,主要还是因为我不希望这个群体过于匆忙地为人们的偏见所左右。我想人们已经习惯用“先锋派”来称苏童、余华、格非和孙甘露等人,因此,用“晚生代”来指称这个后起的群体──他们主要包括张旻、毕飞宇、何顿、鲁羊、述平、韩乐、朱文、刁斗等人──也算是各得其所。
那么,在九十年代,“晚生代”到底是表征着什么样的文学事实和创作经验呢?它又预示了一个什么样的群体呈现于文学舞台上?九十年代的文学背景明显向着后个人化,向着大众化,向着商业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向欲望化的观赏性方位延伸。在某种意义上,八十年代末期的那种文学自成一体的格局已经破裂,不管“先锋派”和“新写实”多么的个人化,他们的写作终究与文学史(现实主义规范)构成对话,而九十年代才过去数年,那种反抗和挑战的姿态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彻底“零度”的写作──没有任何形而上乌托邦冲动的写作,它被历史之手推到纯粹的阅读面前。文学写作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回到个人本位,不管历史之手赋加什么样的群体意义给这种写作,它首先是以个人对文学说话的姿态进入现实语境。没有中心的时代注定了是一个多元化的不可整合的时代,当然也就注定了是一个走向“直接存在”的时代。如果我们稍加保持历史敏感性的话,我们将不难感受到在大文化转型的背景上,一种新的叙事法则正趋于形成,在某种意义上,它表征着“晚生代”的最根本的文学内涵。
当真实的历史感被取消之后,当进化论的意义遭致普遍怀疑的时候,当文化的方向感不再明确的时候,一切都变成“当代”,──没有进行时的超平面的现在──这也许就是“后当代性”的最基本含义。很久以来,我们无法设想文学写作的位置可以超出文学史语境的巨大存在之外;事实上,与传统对话的文学写作已经变得自欺欺人,它越来越被卷入更加现实的文化企图。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正在被推入一个崇尚幻象、不断把真实改造为想象性事件的文化扩张的空间,这个空间对文学写作这种古典性行业的改造同样是严重的。文学被放逐到一个更大的文化谱系中去,它被赋加了更多的象征意义──不再是古典时代的纯文学意义,也不再是意识形态充分活跃的政治隐喻,文学也变成了一种超级代码,它被不同的个人操作和使用,而变换成无穷无尽的当下性景观。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并非人们慨叹的那样萎靡不振,实际上,它是如此怪诞而奇妙,混乱而不可思议,没有什么理由不认为这是生气勃勃的转型时期。当然,从理论上来说,中心化价值解体,文化的整合功能丧失,必然迎来一个文化相对主义盛行的时期。这并不像一部分人所概叹的那样,文化的末日行将到来。这种文化情境说到底不过是过于严整的一体化的文化制度必然的后果,对绝对权威的依恋当然还构成部分人的职业爱好,但大多数的人则不再寻求共同的终极目标,乐于以个人的姿态游走于那些中间地带。人们有理由斥责这个时代机会主义盛行,但是人们同样有理由要求最低限度的文化宽容。
文学共同体解散之后,个人化的叙事置身于没有文化目标的漂移状态──正是这种漂移状态构成“晚生代”作家的存在方式,构成他们的叙事法则,他们采用的叙事视角和处理人物的方式。他们的写作不再与文学史构成直接的对话关系,也没有现实的“热点”可以与之对应,就其具体叙事而言,也难以找到那种内在性。写作者在文化中的漂移,投射到叙事上则是那种随遇而安却无所顾忌的表达方式。相对于苏童、余华、格非和孙甘露当年的对经典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挑战性,后起的这些写作者已经没有与之搏斗的风车,他们从业已形成的文学主潮中滑脱出来,游走于那些边界地带。我们可以从苏童1987年发表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中读到“祖父”“祖母”这样的意指着的莫言的文本的字句,还可以读到“我不叫苏童”这样的脱胎于马原的“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的句式,这些细节当然不会削减苏童的创新意义,它仅仅表明那个时期,或者说那个群体生逢其时,他们的写作是在文学史对话的语境中完成他们的革命意义的。显然,象张旻的《生存的意味》(1993)、何顿的《生活无罪》(1993)或《弟弟你好》(1993)、述平的《凹凸》(1993)或《晚报新闻》(1994)等作品,你看不到它们的母本,它们与即定的规范准则缺乏内在联系。这些叙事从当代文化的边际角落漂流而来,它们也没有任何内在化的文化实践功能,这些叙事主体也不再怀有特定的文化目标,这些文本不过是一些具有阅读价值的块状结构。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写作不过是偶发的行为,而叙事则是追逐那些观赏效果。这些文本在当下性的阅读情境中呈现出它的生动面目。但是我感兴趣之处在于那种叙事态度,专注于那些细微末节的纯文本态度,一种个人化的切入生活边界的偶发行为,紧凑而松驰的笔法既是一种观望,又是一种降临。究其最终的缘由,正如当年也是文学史的背景赋予一代先锋派以反叛的意义一样,这个非历史化的背景同样使张旻这样的写作具有了从整合语境中剥离出来的漂移意义。
进入九十年代,对表象的书写和表象式的书写构成了又一批作者的写作法则。那些“伟大的意义”、那些历史记忆和民族寓言式的“巨型语言”与他们无关,只有那些表象是他们存在的世界。与这个“表象化”的时代相适应,一种表征着这个时代的文化面目的“表象化叙事”应运而生。又一轮的──或者说一次更彻底的后现代浪潮正汹涌而至。表象泛滥以及对这个表象进行“泛滥式的”书写,真正构成这个时期的后人文景观。正如列奥塔德推导的后现AI写作作的基本法则:“……使得那种不可表现的事物在自己的作品中,在能指中成了具体可感之物。整个有效的叙述甚至文体操作者的区域都在与整体统称无关的情况下发挥了作用,因而新的操作者得到了考验。文学语言的语法和词汇再也不被当作既定的东西被接受了,而倒毋宁是以学术的形式出现,以在虔敬中产生的仪式(正如尼采所说)之面目出现,这种叙述使得不可表现之物不致于被显示出来。”(《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当今中国的文化现实在某些方面比列氏的激进理论走得更远,在这个全面扩张的表象背后,并没有隐藏什么“不可表现之物”,某种不可知的神秘,不可洞见的幽暗。
在那个不断膨张的当代文化表象背后,空无一物,一片虚空,一片澄静,那背后只有“无可表现之物”──对“无可表现之物的表达”,我们时代正在制作的“新表象”状态已经完成对列奥塔德的跨越。对表象的迷恋,一种自在飘流的表象,使“晚生代”的小说如释重负,毫无顾忌,真正回到了现实生活的直接存在。不管把这个时代的生活描述成分崩离析的情势,还是完美无瑕的形态,都无法否认现实本身发生的巨变,当代生活正在以夸张的姿势奔腾向前。没有人能够抓住它的本质,触摸它的精神和心灵。不管人们是欢呼还是逃避,欣喜还是恐慌,你都无法拒绝扑面而来的表象之流。“晚生代”从新时期的“巨型语言”中走出来,走向后新时期的价值解体的情境。就其美学母本而言,它是八十年代后期的“先锋小说”的叛臣贰子,在某种意义上,它还是“先锋派”和“新写实”相调和的产物。你可以看到“先锋派”的那些叙事笔法和语言风格,虽改头换面而风韵犹存;“新写实”的那些态度滋味,似曾相识却面目全非。那种反抗式的革命写作和宣言式的生活立场,业已被打碎,现在只有面对纯粹的生活本身。这是一次惊人的裂变,也是一次果敢的冲刺,而且还是一次不着边际的下降运动。
“新时期”关于情爱的主题一直是思想解放运动的注脚,八十年代中期,性爱主题显然携带着思想的力度走向文坛的中间地带。八十年代后期,中国文学(创作)已经完成了从爱情主题到性的转型,先锋派和“新写实”小说,不谈爱情,而“性”变成了叙事的原材料。它们若隐若现于故事的暧昧之处,折射出生活的死角。进入九十年代,性爱主题几乎变成小说叙事的根本动力,那些自称为“严肃文学”或“精品”的东西力不从心承担起准成人读物的重任。这股潮流迅速波及到“真正的”严肃文学,当然也就迅速抹去严肃/通俗的界线。理性的深度和思想的厚度早已在小说叙事中失去最后的领地,而欲望化的表象成为阅读的主要素材,美感/快感的等级对立也不复存在,感性解放的叙事越来越具有蛊惑人心的力量。
“晚生代”生不逢时却也恰逢其时,以他们更为单纯直露的经验闯入文坛,明显给人以超感官的震撼力。他们的兴趣在于抓住当代生活的外部形体,在同一个平面上与当代生活同流合污,真正以随波逐流的方式逃脱文学由来已久的启蒙主义梦魇。那些赤裸的生活欲望使那些粗鄙的城市街景变得更加生气勃勃,捕捉住当今为商业主义粗暴洗礼过的城市生活外形状态,就足以令人快乐,也令人惊叹不已了。他们的叙述视点几乎不带有任何先验性的观念,也不怀有发掘生活意义的明确动机,作者的兴趣仅只在表现这种生活的外形状态,纯粹的生活之流。象何顿、述平的叙事既没有复杂的文化背景,也没有那些自以为是的个人态度,他笔下的城市故事是一些真正解放的外活“原形”──原始的外形状态。那些男女凭着本能生活,只为自己生活,没有信条,不需要任何规则,我们可以指斥他们为行尸走肉,但是他们生活得很快活,潇洒走一回,过把瘾就死。在九十年代中国彻底商业化的历史背景映衬下,显得尤为真实。
这个时代的生活已经没有内在性,人们为脱贫所困扰,为暴发所怂恿,“晚生代”们抓住这个时代的趋势,把这种混乱不堪而又生气勃勃的生活性状不加雕饰呈示出来,它们是一些不加深究的表象之流。他们那种直接呈现生活表象的方式,强化了粗鄙生活的本色形状。他们热衷于去表现那些赤裸裸的欲望,这些解放的欲望四处泛滥,很显然,这些场面构成九十年代小说叙事的阅读焦点。纯粹观赏式的阅读期待,也促进了小说叙事对观赏场面的强调。他们算是参透了这个时代新的写作法则,只要制作一些具有观赏价值的欲望化的表象,就足以支撑起小说叙事,而且作为一个意外的收获,这些欲望化的表象又恰好准确概括了这个时代的生活面貌。
当然并不是说他们的叙事就不讲究形式技法,事实上,他们不过是把形式折叠到故事的内在构造中去。他们通常关注城市男女之间的暧昧情感,对他们相互诱惑和逃脱的困境刻画得淋漓尽致。那些欲望化的动机是如何以“爱”的浪漫形式为道具,它们是如何不可遏止一步步走向危险的区域,并且达到高潮。那些欲望化的观赏场景因为对个人存在的直接追问而又拥有了某种思想的力量,并且因此而具有了合法性。它们甚至经常导向对人的命运的诘难。
从总体上来看,他们的叙事笔法精细锐利,十分善于把握人物在特殊环境中的性格侧面和心理层次。这些人物都处在某种临界状态,一些细节的改变促使他们悖离预期的目标,而事实上,这又契合了他们隐藏的无意识──那些最初的欲望化的动机。在那些场景中,人的那种复杂的内心生活表现得十分深刻细致而极富有立体感,这不仅表现在人物内心活动的多侧面,同时是故事本身交织着的多种元素。可以在张旻、毕飞宇和述平的叙事中看到,他们十分注意情境和行为的互动关系,那些不断改变人物本来存在规定的选择,其实是特定的情境在起作用。那些典型的城市偷情行为,却被叙述得美好而纯真。在那些微妙的时刻人们是如何摆脱生活原有束缚,而拥有了无始无终的自在性?在述平的《凸凹》中,这是一次在报复的名义下进行的合理背叛;而对于毕飞宇的《叙事》中的主角来说,这是一次闲暇中的精神漫游。人们其实是在一些情境中偶然地作出各种选择,这些选择了的行为又如何能说明人的本质呢?事实上,这些复杂微妙的情感及生活的意味,不过是叙事的副产品,对于他们来说,对一些男人或女人的情欲和那些欲望化的场景的处理,才是叙事的原动力。然而不管如何,他们的小说在具有观赏性的同时,也具有耐人寻味的诸多意蕴。经历过八九十年代沉重的历史折叠,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突然间处在一个无比空旷的场所。这里没有方位,没有中心,没有冲撞,甚至没有真实的压力。一切都显得那么的实用而空洞,那么虚假而随意,有谁能够承受这种无根的轻松呢?事实上,人们经受住了,而且乐于分享这种轻松。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处在某种状态中──它也只能是一种状态,人们只能看到它的外形状态,而无法触摸它的内心,或许它根本就没有内在性,传统的和经典的话语无法给定它的确切含义。它总是处在某种状态中,或者说从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这样一个过渡时期,这样一个印象主义时期,文学实际处在多元化的和多方位的过渡性状态:文学在这个时期确实发生了某些实质性的变化。写作主体、表达形式、传播方式及其效果,都与八十年代相去甚远,甚至与八十年代后期,我们称之为后新时期变动的早期阶段都大相径庭。“先锋派”和“新写实”的所作的革命性举动,依然是在文学精英主义的序列之下来进行,它与经典权威话语构成紧张而持续的对话;对于九十年代后起的“晚生代”来说,他们已经完全脱离了“巨型语言”,他们的个人化立场彻底向生存的直接性倾斜,他们叙事没有文学的历史由来,更没有文化目标,历史之手也不再能强加给他们以革命性的象征意义。
没有理由认为在作品中强调欲望化的观赏价值就是低级趣味,但是所有有关欲望化场景的描写,必须精道奇妙,否则就会弄巧成拙。在另一方面,对欲望化场景的强有力的表达,无疑构成这个过渡时期的最重要的叙事法则。对情欲和暴力的巧妙书写,足可见出这个时期小说叙事的艺术水准和必要的智慧。在这样的过渡时期,某种程度上也象罗朗·巴特所做的那样:把写作比作勾引,把阅读比作色欲。当然巴特是在后结构主义式的写作的普遍象征意义上来发此惊人之论的,而对当代中国的小说叙事而言,它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填补成人读物的空缺。对这个空缺的关注,构成了这个过渡时期小说的主要叙事主题和重要的叙事策略。
事实上,对情欲的表现已经成为这个过渡时期的必要难题,欲望化的叙事已经无法拒绝成为这个多元化过渡时期的唯一有贯穿能力的文学法则;对成人读物不自量力的替代,使当代小说写作殚精竭虑,或黔驴技穷,或才情焕发。当代小说以欲望化的叙事法则当然有可能抓住这个过渡时期的生活特质。
毫无疑问文学写作是非常个人化的行为,被称为“晚生代”的这个群体当然各有特色,风格迥异,仅仅是在文学变动的历史大趋势上把他们视为一个群体。就具体创作而言,他们各个人的精神气质,价值立场和文化取向都不尽相同,甚至不无大相径庭,相互抵牾之处。例如,毕飞宇就尤为注重一种深度性的终级思考,鲁羊一直怀有绝对的形而上冲动。这都是他们在同一历史前提下所具有的非常内在的个人化体验,抹去这些个人化的东西显而易见是愚蠢的,而且对于文学写作无疑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正是这些个人化的追寻使得这个群体倔强地存在,而富有思想力度。我说过,是一种文化命运,一种不得不共同面对的文学现实,一种进入历史的机遇把他们拴在一起。
当然,“晚生代”还应该有更宽阔的视野,他们现在不过初露端倪,他们风头正健,潜力十足,不可拒绝。然而,这毕竟是一个过渡时期,他们有必要在过渡中试图超渡。因而,那些个人化的写作也有可能对当代中国的历史命运作出某些精辟的描述,对当今中国所处的文化境遇作出强有力的表现。例如,处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中国,在它走向世界和走向市场的双重步伐中,透示着这个时代极为动人的姿态。它有那么多的似是而非的场景;有那么粗犷的能指和所指脱节的话语之流;它如此偏执的本土性崇拜和狂热的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爱好;有指鹿为马的准确功能和制造文化垃圾的超常实力……等等,所有这些都表征着一个极为壮观的过渡性的后东方空间,“晚生代”的叙事法则超渡于这个空间,肯定会大有作为,一种独特的,真正扎根于直接现实之中的文本,一种毫不犹豫的直接而彻底回到个人生活的纯粹性中去的叙事,将无可争议预示着九十年代的文学向度。
一九九四年十月五日于北京望京斋
标签:文学论文; 先锋派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新时期论文; 九十年代论文; 当代论文; 毕飞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