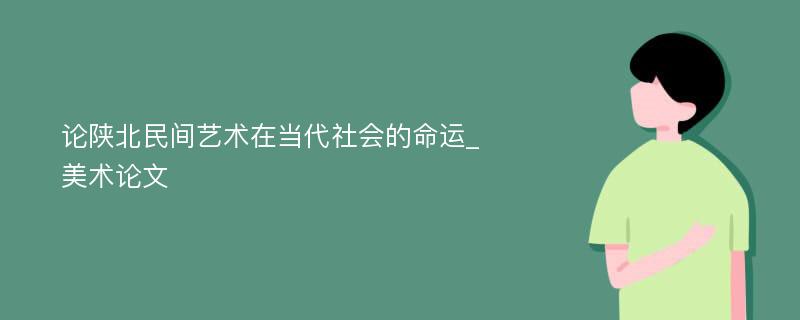
论陕北民间美术在当下社会的命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陕北论文,民间论文,命运论文,美术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传统民间美术是中华民族整个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原始文明的仰韶文化以及商周文化、秦汉文化有着密切的血缘联系。而陕北延安地区更是地处中华民族文明发祥地的黄河流域,古老的文化沉淀孕育了陕北的民间艺术,深厚的黄土养育了陕北人。陕北人以特有的顽强性格与严酷的自然环境作出抗争,他们在茫茫黄土塬生息、繁衍,他们在劳作之暇以勤劳、粗壮的双手创造了神奇的窑洞艺术,剪纸、面塑、布艺、炕围画。灿烂的陕北民间美术又以安塞县为代表。
安塞县目前是全国屈指可数的民间美术先进县,民间艺术之乡。其中安塞县文化馆在陕北民间美术的收集方面做出了积极工作。随着上世纪九十年代改革长期效益的显现,原本依赖于行政扶植的文化单位进入了十分严峻的境地,目前许多地方文化馆在民间美术与外界交流中扮演了中介者的角色。作为民间艺术创作的个体艺人,往往很难以个体形象走向市场。国内许多“民间美术之乡”因在目前市场环境中回避市场运作,文化馆与民间艺术同时偃旗息鼓。对于民间美术而言,走向市场得以生存,回避市场将走向衰弱。
安塞县文化馆目前职工十四人,财政基本与政府扶植脱钩,完全靠民间美术的自我经营运作,自筹经费建立了几千平方米的民间美术馆,内有珍藏数十万件当代所有陕北民间艺术家作品的大型豪华展厅。包括闻名遐迩的民间艺术大师曹佃祥、白凤兰、高金爱的大量原作精品。近年文化馆又自筹经费出版了《安塞民间艺术丛书》、《安塞民间剪纸精品》、《安塞民间绘画精品》、《安塞民间线描精品》、《樊小梅——安塞姑娘的剪纸故事》等书籍,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
然而就在陕北民间美术炫目辉煌的背后,民间艺术的创造者——一大批民间艺术家的生活境遇足以让亲眼所见的每个人潸然落泪。
作为陕北民间美术最杰出代表的民间艺术大师高金爱,年近八旬的她一生创作了数以万计的民间剪纸、面塑,以及布塑、农民画。她的作品曾入选法国独立沙龙美展,两次赴中央美院讲学。目前仍与七个儿孙共住在安塞县偏僻山沟中石壁裸露的窑洞中,全家年收入不足2000元,这其中主要来自于在富县开拖拉机的二孙子收入。由于种种原因,高金爱本人每年零星卖出剪纸收入不足200元,甚至在春节期间仍过着半饥不饱的生活。
同样,安塞西河口乡西河口村的民间艺术家常振芳,作为一位年愈古稀的老人,她一生生过十三个孩子,结果前十个全部夭折。虽然,后来出生的孩子最终长成了人,而这位母亲却在艰辛的环境中受到极度的精神刺激而种下了疯癫的病根。她的作品显现出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万物有灵”的思想,她是安塞大师级的民间艺人。老人目前生活状况与高金爱大致相仿,与忠实憨厚的老伴同住一孔破旧的石窑中,由于患有阵发性精神病老伴二人生活愈显艰难,除一点口粮田,两只山羊,无任何其它经济来源。到了寒冬腊月,即使花费一点柴火烧热炕头,对二位风烛残年的老人都是很奢侈的享受。家中所有的剪纸,因没有太多精力照看,大多已残破不堪。另外,陕北尚在世的民间老艺人还有高桥乡的张凤兰,并坪村的潘常旺,她们与去世的曹佃祥在艺术水准上都代表了陕北民间美术的最高境界。同样,她们在当下繁荣经济环境下都生活在一个封闭空间之中,过着坎坷的生活。
这些民间艺人为延安,为陕北乃至为全人类创造如此丰厚的精神财富之后,仍然生活在与她们的付出极不对等的物质条件之下,甚至年长的艺术家中的任何一位都没有因为自己的绝技而跨入温饱行列,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对于民间美术的关注,学者们太多地从艺术的角度去评价某位大娘的心灵手巧,如何剪的飞禽走兽具有广博的内涵,而更有为换取政治资本者粉饰太平纷纷上演民艺搭台,经济唱戏式闹剧。毫无疑问,民间美术的岌岌可危之势无论是否愿意接受,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民间美术的内涵已不仅仅再纯粹是一个美学的主题。在当下后工业社会,民间美术及其命运已泛化为社会学及人类学领域的问题。
工业革命的到来敲响了小农经济的丧钟,西方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思潮所带来的审美价值将民间美术挤到了审美趣味最边缘,时代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给世人带来了一系列全新的东西:五颜六色,光怪陆离,而民间美术那些泥、布、纸、木、竹、面等粗劣材质所映射的品质已完全不能再施展其原有吸引力。最可怕的是民间艺人在人们的淡漠中陆续谢世,后继的女儿、媳妇、姑娘们也因二十年发展带来的审美观,尤其是价值观的改变,而对民间手艺不屑一顾。在世的艺人要不观洋人、商人鼻息而动,从而被迫改变自己创作力的原汁原味,要不就自生自灭或走入旁门左道。
上世纪八十年代,“陕北民间”在中国艺术舞台上出现了戏剧性的繁荣:文学界的寻根小说、音乐界的西北风,电影界的西部片,美术界的乡土画,民间美术经过这阵少有的“辉煌”之后便静静地回归了它在社会文化中的原有位置。陕北民间美术来源于滋养它的中国几千年农耕文化和民俗文化沉淀,扎根于其形成的特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我们完全没有理由否定“陕北民间热”的积极性。但同时又不得不承认,并非经过几波“民间热”,就可随心所欲地将其推到与文人美术相提并论的文化位置。“陕北民间热”之后更多映射的是人们对都市厌恶情绪的渲泻,但这完全不足以给民间美术注上一针具有长久药效的强心剂。
一位学者曾经说过,“当民间美术的直接功能远远退出历史时,民间美术只会剩下一种观念,一种思想,一种将要彻底逝去的文化情怀”。作为一个具有良知的人,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不情愿发出这样具有悲情色彩的叹息。作为民俗产品的陕北民间美术有其产生、发展、繁荣的社会根基,这种根基的社会主干又是先民的蒙昧,是人类处于自然的必然摆布之中。民间美术创作者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满足作者本身及其所代表的社会阶层的深层次心理需求。而特定的小农经济所构筑的社会风俗及审美趣味又为其提供了良好的外在土壤,民间艺人在这些不朽之作之中不计工本,不计时间地将所有的爱与恨、欢与愁、祈祷与希望完全倾注其内,正是陕北民间美术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了它及其生产者在时过境迁的后工业社会的不祥命运。
现今,人们对民间美术的关注与偏爱更多的是一种猎奇式的怀旧情结。陕北中年民间艺人,王西安、李福爱、侯雪昭、马国玉、樊小梅前往西安、延安旅游点开设民艺摊点出卖民间艺术品。现代工业文明大步推进,民间美术在失去其功能及实用价值的前提下,在旅游品市场暂时生存,也是陕北民间美术在“存”与“亡”之间作出的一种无奈选择。
抢救和延续陕北民间美术的有效措施无非就是两种。外在式的保护:收集、宣传民间美术作品,将其纳入相应的研究范畴,并以此为基础建立改造与融入式的现代艺术创作体系。内在式的保护:改善民间艺人的社会境遇,继而继承其艺术技艺的持久力,同时进一步改善与之相伴而行的民俗文化及宏观生存土壤。而目前令人痛心的是陕北太多文化行政单位,片面地追求社会经济效益及政治影响,对民间美术的关注更多的是报喜不报忧,完全忽视民间美术内在保护,民间美术成了经济发展时穿时脱的华丽外衣。这对民间美术的长久命运而言,无异于杀鸡取卵,涸泽而渔。陕北民间美术及其艺人命运问题的改善完全是个渐进过程,因为任何事物的发展繁荣总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积累,而使其灭亡却是转眼的瞬间,民间美术这个脆弱文化尤其如此。
无论是其生产者,还是我们这样局外的旁观者,都不愿接受民间美术没落的现实,而这些辉煌灿烂文化创造者的命运,在后工业社会五颜六色的潮水中真的离我们渐行渐远。我们怀着欢欣与叹惋交织的心情,对陕北民间美术乃至中国民间美术的现实历史境遇和未来作出评估,也对它的美学意义和文化意义作出肯定。当然,未来对于陕北民间美术乃至整个中国的民间美术似乎更加难以预测,也许令人叹惋会因认识的迷误而愈来愈甚,也许由心灵深处迸发出的力量会带来让人欢欣的图景,但我们每个人都寄希望于后者。在此过程中,每一位学者是否应该在埋头苦作研究之暇,带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做更多的田野考察?是否更应以此为契机,在后工业社会冷冰冰的工作产品之后,更向社会大声呼唤那些对民间手艺关怀的暖意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