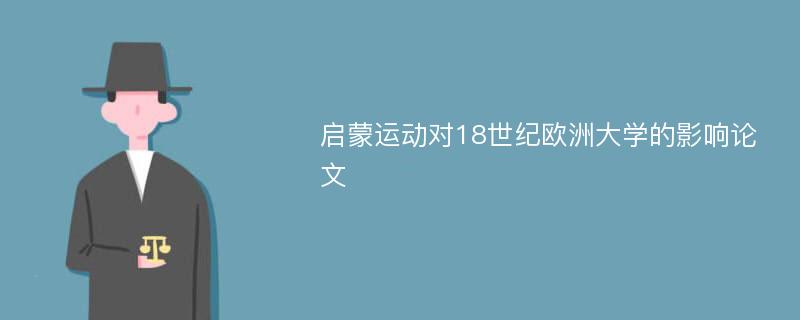
启蒙运动对18世纪欧洲大学的影响
赵 敏
摘 要: 启蒙运动为整个欧洲大陆提供了思想和行为的模式,在18 世纪对欧洲大学产生广泛的影响。这些重要的影响首先表现为科学研究的民族化,建立本国科学研究机构,减少学术领域的国际对话;其次表现为教育的实用化,注重传播实用知识,建立专门学院;再次表现为学科的世俗化,强调科学和学术脱离神学和行会精神的羁绊,神学失去独尊地位,以理性为基础的世俗学科逐步成为大学的主要系科;最后在对大学办学模式和学院改革的影响上,鉴于传统、文化及世俗政权和教会的关系差异,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大学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措施。
关键词: 启蒙运动;欧洲大学;学科地位;科学研究;实用知识
在18 世纪期间,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在其发展和改革的过程中都受到了启蒙运动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形式,但在总的趋势上没有差异。[1,2]作为社会文明、科学、学术和思想方向标的大学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启蒙运动的影响。
启蒙运动为整个欧洲大陆提供了思想和行为的模式,渗透到所有的高等教育机构。这种渗透在不同的国家和传统中差异显著,形式多样。但是,不管是在新教地区还是在天主教地区,在启蒙运动理想的实现上都极为强调:全面改善人类生活的要求以实践教育和发展智力为前提;高度重视实施人类启蒙法则的教育和实践教育;整个国家和社会必须重视教育机构发展和改革。
正如理性是人类的共性,正如契约社会必须遵循基本相同的法则,也正如大自然接受普遍规律的支配,这些都需要人类用头脑去发现,这意味着所有人都应该平等地接受启蒙的洗礼,并且都能同样产生进步的思想和行动。依靠这种启蒙,人们可以分享那些普遍的和共同的东西,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人类通过其理性能力分享世界文化。通过知识批判的训练,那些非理性的或被传统神圣化的东西就能够而且应该得到抑制,并最终完全消灭。所以,不管是政治的、科学的、宗教的,还是社会的批判,都是思想启蒙的重要课题。[3,4]
源于历史、民族、政治和宗教环境的不同,人们关于这些课题具体应包括那些内容的认识存在巨大差异,但基本的观点大体一致,其目的永远是为了改善生活,并消除现有生活和社会环境中比比皆是的各种异常现象。显然,这种基本的认识对传统秩序是一种威胁。面对这些批判的意见,是为传统秩序寻找一个新的理论基础,还是沿着批判意见所暗示的路线进行改革,人们必须做出选择。
不仅各个教会跟当时的政府面临这些选择,科学和教育机构,以及各个社会阶层也需要顺应这些思想的要求。不管这一理想是如何表达的,也不管对人类的这些祝福,如“共同幸福”、“社会满意”、“公益”、“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等能否实现,一旦这些理想被认定为人类应该追求的目标,那么通往这个理想道路上的所有障碍都面临被扫除的命运。
只是在法国大革命以后,在拉·夏洛泰(Louis René Caradeuc de La Chalotais)的领导下才颁布了《公共教育法令》,至此流行的教育制度被废除了。在1793 年,议会的一项法令取消了研究院和学会。仅仅2 年之后的1795 年10 月23 日,法国执政内阁根据热月党人的思想和准备,建立了国家科学和文学院。它的三个班级——行政—数学班级、文学—美术班级及道德—政治学班级对培训、传播和推进一种文明公民,但不是真正平等主义的科学观念有重要的意义,完成了教育和培训的完全世俗化。正如关于大学的地位逐渐明晰,虽然教会的垄断看起来已经走到了尽头,但主要的目的并未实现。
看着陆浩宇关切的眼神,温润的笑容,我心如虫噬。那女生叫绣玫,我居然跑到那女生的班上去警告了她,她淡淡地告诉我,陆浩宇是他表哥。听到她的话,我长嘘一口气,但她后面紧接的一句话,却让我的心悬了起来。
在18 世纪下半叶,这种迷漫于整个欧洲,且在某种意义上的全球性发展,日益为一些趋势所陪伴,即似乎逐渐从这些理性主义的普遍信仰中走向了它的反面。从根本上看这种表面的反向趋势并不是事实,它们实际上是启蒙运动发展的重要成果。例如,明确强调所谓重视民族特色价值的“前民族性”得到了巩固,一个民族独有的艺术、政治和语言学成就在欧洲国家竞争中的作用被夸大。孟德斯鸠(Charles de Secondat Montesquieu)所谓的民族才智为这种观点提供了最好的注释:只有那些与其传统行为模式和信仰标准相和谐的法律、教令和规范才正确,才对国家有益。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决不只是孟德斯鸠自己,神圣罗马帝国的御用宣传员,荷兰地区的某些哲学派别,穆拉托里(Lodovico Antonio Muratori)在意大利和其他地方的追随者,及与孟德斯鸠一脉相承的英国的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等人,都持有这种观点。伏尔泰(Voltaire)将历史视为文化史的历史学观念被赫德关于文化民族的观念所吸收,似乎也将“民族才智”视为对全世界的独特贡献。所有这些都在欧洲的传统知识界产生了影响。这些影响也都渗透到了大学的改革与发展中。
一、科学研究的民族化
在18 世纪的法国,大学对法国社会的智力生活及其启蒙讨论过程不再有任何显著的影响。文学院在反宗教改革的耶稣会教派的影响下,已经降低为只是颁发毕业文凭的机构。接受教会或教令管理的学院认真地承担起预备教育的任务,已变得完全僵化,根本不去发展科学知识。启蒙讨论只发生在各种沙龙和到处涌现出来的学术团体中。大学和学院仍将自己圉于执行纯粹社会性的自我复制训练功能的这种与世隔绝状态,从18 世纪中期就已经招致了日益猛烈的抨击,要求对其进行改革,在现代外语、自然科学、历史领域需要更好的教学方法,同时也需要给大学输入活力。
科学研究民族化趋势的另一个表现是作为年轻人经验之必需要素的教育旅行传统丧失了它的魅力和作用,并且几近完全消失。虽然年轻中产阶级骑士在故土之外遍游欧洲的教育旅行又一次成为时髦,并且以学术机构自己的方式延续着它的传统,但是,它与早期的教育大旅行相比显然有不同的目标和理想,其目标乃是拓宽知识面及培养年轻旅行者的职业能力。[7]
当初,有个叫韩寒的年轻人在新概念作文大赛中脱颖而出。之后,他在新浪开了博客,以大胆敢言著称。儿童文学作家郑渊洁在新浪开了博客,上天入地无所不谈。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博客的阅读量后来过亿。
二、教育的实用化
18 世纪后半期整个欧洲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是仍然对启蒙将会带来好处这种认识充满信心。人们相信,启蒙是对现有秩序的批判,并且认为通过启蒙,流行的愚蠢会被克服。在这种观点看来,有用的理论首先应该能在实际事务中解决问题。大学和类似的机构要讲授的不应是形而上学和神学,而应是经济学、技术学、医学和自然科学这类学科,实际操作的知识优于口耳相传的知识。在许多大学里,像这类学科,如法国的医学和自然科学,德国和意大利的财政学,苏格兰的道德哲学,以及许多欧洲国家的自然法学,都得到了加强或第一次开设。神学丧失了它在大学的领导地位,不再是最重要的学科。无需证明的信念和对权威的无条件顺从被放弃了,学校越来越多地教育学生自己思考。[8]
然而,不管他们怎么宣称如何具有全球性质,这些报纸、期刊及很多书籍在受众和影响范围上都常常被限定在一国之内。只有法国启蒙运动最伟大的成就——大百科全书及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著作——驰名整个欧洲。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法国的语言在许多地方是教养阶级的通用语,其次是因为当时的法国人或讲法语的人(如出生于瑞士讲法语的卢梭)的思想本身具有先进性,代表了时代的发展趋势。除了这些法语作家外,一些英国作家的作品也远近闻名,如洛克(John Locke)、休谟(David Hume)和许多自然科学家特别是牛顿(Isaac Newton)的著作。对那些不是很杰出和成功的作家来说,翻译有助于他们思想的传播。许多同时代的著作被译成了其他文字,如果不是这样做,这些作品几乎不会产生什么影响,或者甚至不为很多公众所知。在这儿我们要说,不管大学怎么说,普遍的情况是,许多大学教授及其作品的影响只限于校内。然而,由于启蒙运动的全球性目的是知识分子的殷切期望,并渗透到了他们的著作中,尽管接触到它们的受众比整个人类的范围要小,但使用“全球性”这个术语不算是不当。
那些固执的传统大学——正如那时所称呼的“经院哲学的”大学——在启蒙运动的支持者看来,似乎没有能力实现这些目标。特别是在法国、在伊比利亚半岛和意大利,人们普遍认为,大学不适合实现启蒙运动的这些雄心壮志。正是源于这种认识,欧洲国家纷纷创办医学、农业技术、军事战术和战略、工程学、财政学、美术和自然科学等领域的专门培训机构。显然,这些新建立的公共机构的中心任务是传播实用知识。同时,从18 世纪初开始建立的较早的学术机构,如伦敦皇家学会、科学院、古典和现代文学院、都柏林哲学学会、柏林莱布尼茨科学院,以及在马德里、里斯本、乌普萨拉、哥本哈根、博洛尼亚、罗马、澳洛穆茨和在斯德哥尔摩和巴勒莫之间、圣彼得堡和费城之间的其他许多地方建立的新的学术机构,也延续了不再依赖大学而发展的趋势。所以,自1764 年之后,在圣彼得堡、克拉根福、格拉茨、伽斯、维也纳、因斯布鲁克、布格豪森、策勒、曼彻斯特、伯明翰、德比、格拉斯哥、纽约、马德里、拉克鲁尼亚和70 多座西班牙和其他地方的城市都建立了一整套经济学的和爱国的学术团体。虽然其名称不同,且有不同的专门化的活动领域,但都认为他们有责任传播启蒙思想,并教授技术的和实用的知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机构都是由大学以外的人领导,因而他们主动并欢迎与其一样的团体交流。这些都体现了实用化这种普遍的趋势。[9,10]
而他采取以学术期刊搭建社会体育指导员交流平台的举措,堪称为走在时代前列;其创办的《体育研究与通讯》期刊中“通讯”栏目,每期都会刊登各县公共体育场工作人员对于社会体育指导等问题的回复,在指导提问者进行社会体育工作的同时,也为其他体育场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提供了工作问题解决范式。期刊还刊登了大量的体育基本知识、教学教法等文章,无疑也为一线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提供了范式。
这种趋势发展的结果是许多专门学院的建立,如专门的农业学院;专门的外科学院,如查利泰学院;和专门的财政学院,如柏林的蒙彼利埃学院,等等。这些专门学院对那些停滞不前的大学是一种威胁,因为后者在许多欧洲国家确实处于停滞状态。科学家和启蒙运动的支持者将希望寄托在了这些研究院、技术学校、专门学院、学术团体和学会身上。
神学院的地位——自反宗教改革时代,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时间更早的这种领导地位——跟它解释的垄断权利和检查员的作用一起被削弱继而被废除了。自此以后,文学院发现它们不用再像以前那样充当神学婢女的角色,它们现在希望为已成为领导学科的法学院提供预备教育。这一过程是在不同的时间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完成的,并且在内容和突破的深度上也不一样。尽管在具体的细节上有这么多差异,但在欧洲却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当然,有些国家的大学也主动变革,以处理各种类型的新知识并承担新任务。究竟是何种原因促使这些大学改变自身,在多大程度上是学院自身主动变革,在多大程度上是被迫与政府合作,或者说政府部门的负责人,甚至君主,在多大程度上为这些大学的改革提供了权力和必要的推动,都没有确切的材料供我们分析。但无论如何,其结果是作为皇冠学科的神学从根本上为法学所取代,大学更加世俗化,各种自然科学和科学家努力变得“谦恭”和“优雅”,并且变得更愿意接受各种疑问和现代科学。不管采取什么途径,是通过学院的内部改革,还是重新设计学科和教育培养计划,其结果都是在现有的学术界,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大学里,发生了激烈的变化。后一种类型的变革只发生在那些一直保持着活力和在智力方面保有积极性的大学里,尤其在荷兰和德语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大学。[11]
三、学科的世俗化和学科地位的变化
与前两种趋势相一致,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学科的世俗化也成为当时欧洲大学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主题。在天主教地区,这种发展主要发生在耶稣会教派。耶稣会派在1759 年被逐出葡萄牙之后,仅仅过了14 年,教皇克莱门特十四世(Clement XVI)迫于世俗的压力又将其解散了。这对教育前景特别是天主教国家的教育前景有着深远的影响,并带来了许多问题。[12]
王小东在致辞中表示,南宁市认真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展现南宁美丽形象的发力点。第十二届园博会成为南宁加强与中外城市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同时也为南宁增添了一张靓丽的名片,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生态财富。南宁将全力做好服务工作,共同把本届园博会办成引领城市绿色发展、展示城市建设成果、促进多元文化交融、服务百姓的国际园博盛会。
学科的世俗化是高等教育机构在启蒙运动时期得以生存的条件,但并不是所有大学都要追求和实现的目标。那些神学仍保持着皇冠地位的大学就没有这种学科发展上的兴趣。泛泛地说,牛津和剑桥以及许多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大学就是这种情况。偶尔在地中海地区的一些天主教国家,改革者反对耶稣会教派的斗争及其胜利有时延缓甚至避免了大学的衰落。
在那些政府与教会关系特别密切和牢固的国家对反对教会和神学持有一种激烈的对抗态度。代表启蒙力量的斗争有时没有将神学从大学中驱逐出去,那时候发生的大多数学术争论只在这些学校身边一掠而过。这使这类大学孤零零地留在了固有的正统中,不能在主要的学术争论中发挥任何重要作用,并阻止这些机构采取措施自我复兴。
大量秘密组织,特别是共济会会员,抓住时机,对这些大学进行了有力补充。他们在对科学进行补充的同时,也与传统大学在学术及与学术关系不大的问题上竞争。这些组织相信自己有责任通过从事与阶级和财产关系不密切的科学和文化活动,促进人类和科学知识进步。尽管他们在许多方面依旧唯我独尊,但他们还是愿意有一种人人都能自由参与并且没有宗教界限的启蒙运动,并希望有一个人人都将相互帮助的世界。之所以钟爱深奥而又实用的科学知识,主要是为了帮助团体成员形成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13,14,15]像“民族的”和“实践上有用的”学院、“哲学研究会”及“鼓励艺术、制造和商业”的学会等这些秘密组织,同样极力反对教会强加给知识界的专制的审查制度——特别是在那些曾经将这些权力冒称属于自己的大学及其神学院。人们认为科学和学术能够脱离神学和行会精神的羁绊。
尽管启蒙运动坚决支持的努力并不总是成功,但在限制教会和政府的审查方面的确是成功的,在有些地方后者甚至完消失了,这样出版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甚至是印刷自由在很多地方得以实现,并且在其他地方也可以容忍,尽管在各地都是法律规范的目标。出版和印刷自由是启蒙运动为确保其思想能够传播,特别是确保书面语言能被普遍理解而制定的计划的一部分。结果书籍的生产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当然,许多以科学普及、教育和娱乐为目的的期刊对书面语言的广泛传播也起到了补充作用。[16,17,18]
2)波速变化与冲击危险性的关系。大量的现场实测表明,冲击地压往往发生在高应力区和高应力梯度异常变化区。在煤矿,受煤岩地质及开采条件的影响,不同开采区域煤岩层的结构及应力集中程度都存在很大的差异,煤岩结构或应力的剧烈变化均表现出高波速梯度的异常特征。高波速异常区更容易产生应力局部化,因此也更容易发生冲击地压,且应力梯度越大,发生冲击的可能性和严重程度也越高。
学科世俗化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大学中某些学科地位的变化。首当其冲的变化是启蒙运动成功降低了神学的重要性。之前神学院是大学最主要的学院,神学教授的薪水也最高,现在都已风光不再。法学院取代了神学院的地位。最迟从18 世纪中期开始,更喜欢被人称为“人的学科”的“哲学院”,虽然非常不情愿,还是承认了它作为新的领导学科的“鹎女”的角色。进一步,哲学院开始要求与其他学科具有平等的地位和独立性,甚至要求成为真正的中心学院。这种情况发生在大学在启蒙运动的传播和移植上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地区,如在德国、苏格兰和荷兰。哲学院的一些学科在18 世纪后期已经坚决要求至少应与先前较高级的学院具有平等的地位。
降低HIV感染的发病率和病死率、减少非艾滋病相关疾病的发病率和病死率,使患者获得正常的期望寿命,提高生活质量;最大程度地抑制病毒复制使病毒载量降低至检测下限并减少病毒变异;重建或者改善免疫功能;减少异常的免疫激活;减少HIV的传播、预防母婴传播。
改革的认识、方法和实质内容对每一门学科都似乎是不可缺少的,以便能向所有学生做适当的推荐,这在一些大学是普遍的做法。被称为“第一所具有广泛科研自由和教学自由的、启蒙主义的现代大学”[19]的哥廷根大学这个18 世纪德国最受欢迎的领袖大学,远在在柏林大学建立及进行学科重组之前就提供了很好的榜样。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出现了改变科学和学术学科组织方法的新要求,对各门学科的组织和安排方式进行了改革,使教学和研究活动进行得更加有活力。强调学科的有用性和实践性,哲学院关于其学术地位至尊的新主张和神学院地位的降低,共同促使这个不怎么承认各门学科相对平等而重视科学观念的改革形成了气候。自此以后不再追求百科全书式的博学——尽管这继续是一种广泛流行的实践——而是对一些具体学科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从前的博学的学者开始转变为热衷于从事某方面研究的科学家。[20]
电源系统作为通信网络的心脏,对实现良好的室内覆盖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因此,室内覆盖网络的供电方案不仅要与通信设备相匹配,还应与网络质量的要求相适应,以满足室内覆盖网络质量的较高要求。
按科学的方法认识和掌握未知的宇宙秩序,这个在逻辑上与将世界视为世俗现象的认识相一致的任务,从法国大革命中获得了持久的动力。自美国独立战争始,人类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即如果根据科学知识自由决策,并采取合理的行动就可以改善世界。通过对世界和人类的科学研究,人们可以获得正确的认识,这就是科学知识。人们相信,以科学知识为基础,人类社会就会进步,到19 世纪这种信心在科学上变成了大家都乐于接受的自信。
(3)“氧化”时有中间产物Fe6(OH)1 2SO4生成,该物质中n[Fe(Ⅱ)]∶n[Fe(Ⅲ)]=____;该物质进一步被空气氧化成FeOOH的化学方程式为____。[注:Fe(Ⅱ)表示二价铁,Fe(Ⅲ)表示三价铁]
模具成形是采用指定的形状完成成形拥有特定的尺寸与形状模板的工具。在许多材料加工中大量的使用着各种形式的模具。比如合金成型采用的冲压成形、锻压成形、冷压成形等模具。
作物生育期的蒸散量一般包括土壤蒸发和作物蒸腾。大量研究发现土壤蒸发约占总蒸散量的30%[17]。如果进行秸秆或者地膜覆盖,土壤蒸发量会减少50%[17-18],冬小麦和春玉米总的蒸散量分别降低70 mm和75 mm,相当于一次的灌溉水量。这样冬小麦和夏玉米的灌溉水量则分别减少为200 mm和100 mm,灌溉次数也相应的较少为2~3次和1~2次。由于采用覆盖技术尤其是秸秆覆盖技术,不会增加太多生产成本,且田间操作简单,仅是将前季的作物秸秆保留在田间即可,因此可在灌区推广使用[19]。居英威也提出,在汾河灌区采用膜灌技术可节水25%~30%[16]。
需要指出的是,对理性的这种信心,事实上是对理性的过度崇拜,遭到了多种力量的反对。关于这一点要注意到,启蒙运动引起的大学学科地位的变化大多是对神学的正统、强大的教会等级、关于科学知识的行会性质的垄断和严格的社会身份界限抱有敌意。也就不难理解,反对理性主义的声音主要来自全球的自然神论、虔信主义、詹森主义、审美个人主义和创世纪信徒。前浪漫主义和早期的非理性主义的历史相对论也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加固了这一批判倾向,并为重新评价科学的内容和方法铺平了道路。在18 世纪,这些不同的思潮已经开始摆脱启蒙运动的世界观,只是看起来不那么明显。它们一起侵蚀当时的教育理想,并促使这些教育理想及其体现这种理想的教育机构发生变化。
四、对大学模式和学院改革的影响
爱国主义及在18 世纪的启蒙运动中与其共生共存的排他主义和全球主义一起,形成了自近代早期就保持的各种欧洲大学模式的区别方法。尽管科学和在整个欧洲大陆占主导地位的某种学术理论和方法,以及某些具体的教学方法存在共同的特征,但这些不同的大学继续以自己独特的途径进行发展,并且同时他们仍然只是普遍的欧洲大学模式的不同表现。这种发展是由其自身实践和认识的理论基础本身所固有的性质所决定的。
一方面,法国大学的情况存在明显的分歧,另一方面,日尔曼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荷兰和北欧社会的那些大学的情况也存在明显的差异。除此之外,牛津和剑桥这些“处于被动、防守、抵制的状态”[21]的传统大学,仍然坚持他们自己特有的模式,作为学院大学不设法学院,并坚持保留以培养未来牧师为目的的机构。同时苏格兰的大学则依照启蒙运动的精神在运行。[22]在地中海地区,启蒙运动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其领导的改革或改革的努力,改变了这些国家教育的特征。在伊比利亚半岛,遵循的是启蒙运动的法国模式,[23,24]而在意大利[25]——也像在俄国,在莫斯科大学一样——采取的是荷兰和德国大学的改革模式。与意大利改革时期的天主教有联系的亲冉森教派对非意大利国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科学研究民族化过程的一个明显征兆是欧洲各地学者和科学家积极参与国际对话活动的衰减。许多国家效仿伦敦皇家学会和法兰西科学院的做法成立了本国的科学和学术机构,因而减少了国际讨论的机会,曾在自然科学和其他领域广泛流行的国际间的知识交流削弱了。本来到国外研究就不普遍,因为自16 世纪开始,先是西班牙,然后是法国、意大利和英国,都禁止学者在外国大学从事研究。禁止到国外从事研究再一次成为许多国家专制君主政体制定的商人主义政策的一部分,学生被强制在自己国家所属的大学里学习,曾经是通用的学术语言的拉丁语被各种各样的自然的本土语所取代,甚至在神学领域也是如此。虽然拉丁语从来没有完全消失,但它作为学术王国通用语的垄断地位丧失了。虽然在18 世纪后半期书籍的产量在总体上增长迅速,但增长的主要是不同语言的出版物。
虽然自18 世纪初以后,要求教育改革的出版物的数量增加了5 倍,但宫廷和教会都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它们没有沿着启蒙运动要求的路线进行改进,甚至连杜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引入改革的努力也没有任何进展。1752 年耶稣会教令的废除的确对法国教育进而对大学的入学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挑战。然而,政府并没有承担曾经由耶稣会教会完成的任务——而且政府也缺乏必要的素质和技能,而是将他们的任务转交给了其他教派的成员,如奥拉托利会会友或本笃会修士。
本课题的多纸张缺陷一次提取算法采用Verilog HDL语言编程实现,整个算法均利用FPGA片内资源实现,算法硬件框图如图6所示。整个电路分6个阶段运行,其中分块包围盒处理部分位于图像数据流预处理主流程,随着数据流持续执行更新,其他模块处于分支流程,执行时会受到分块包围盒处理模块的控制。
也正是源于这种认识,许多受过启蒙的法国公众觉得,大学除了能满足资格证明的机会和需要之外是一种多余的东西。专业的机构如农业学院、外科学院、在1701 年进行了改革的自然科学院、医学院是仅有的促进科学发展,并进行适当的培训和教育活动的机构。这些职责是由各个教区的众多的研究院、共济会会友集会处、巴黎人的沙龙和18 世纪80 年代新建立的国立中学及博物馆来完成的。宫廷始终没有推出一种学术活动模式,由贵族和中产阶级组成的社团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了更多的影响。[26]
这种批判可能极为尖锐、激烈,并可能引起分裂,尤其在欧洲,对新的、自信的自由的可能性的觉悟就像一场美国的独立战争,引导着法国大革命去实践这些指向未来的热情批判。[5,6]这种批判,通过渐进的改善,通过和平的启蒙,通过历史发展过程中所透露出的理性,可唤起人们的正确信念,并对那些因忽视理性而丧失了活力和信誉的各种公共机构产生影响。理性的批判一定要给社会带来改善、活力和复兴,不能只是促进改革或只是改变具体的行动、决议和事务。与18 世纪上半叶相比,18 世纪下半叶似乎更令人兴奋,对自身的认识也更加不确定,并且更迫切地期盼实施更激烈的变革。
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对大学教育的重组(我们在这儿不予讨论)从法令的视角来看只赋予了高等教育机构有限的科学意义。它们被指令提供某些专门职业的培训。真正的科学和高等教育由专门的机构提供。拿破仑在颁布这一政策时做了一些符合启蒙运动支持者长期要求的事情。在更全面的预备教育之后的专门训练的法则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自17 世纪始,法国大学的持续不变的衰败(只有某些机构和学科,如巴黎大学和蒙彼利埃大学的医学是例外)几乎是不可避免地选择了这种解决方法。[27]
日尔曼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发展过程走上了完全不同的方向。大学在他们各自社会的学术生活中仍起着关键作用。在17 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根据启蒙运动的思想和某些启蒙原理进行的首次对高等教育的改革就成功地实现了——我们在这儿首先应该想到作为哲学家和法学家的教授克里斯蒂安·托马斯修斯(Christian Thomasius)和哈勒大学。然后这种运动扩展到了其他大学。1737 年建立的哥廷根大学,成了天主教会处理启蒙运动的学科和引导公开的学术讨论的榜样。(由耶稣会解散引起的问题是如何建立科学知识的新结构。)自宗教改革以来,神圣罗马帝国中有学问的人、知识分子和在学术上受过培训的人,第一次可以用单一的语言相互交谈。一旦这种事情发生了,教会的分裂就不再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意义了。[28,29]
2.运用有效方法,衔接算理和算法。处理算理与算法的关系注意:一是算理与算法是计算教学中有机统一的整体,算理和算法并重;二是算理教学需借助直观,引导学生经历自主探索、充分感悟的过程,要把握好算法提炼的时机和教学的“度”;三要防止算理与算法间出现断痕或硬性对接,必要时进行指导。
在许多大学里,在方法上已现代化了的进步的法学主宰着科学知识的结构。大学的所有学科(包括神学)都吸收了法学的成就。包括神学在内的这些学科根据启蒙运动的思想对自身进行了改革,最显著的变化是历史方法的引入。这种新的方法赢得了所有教师的参与和合作,并进行了全面的讨论。这些教师对神学的敌意比他们的法国同行少得多。神学家们在这些讨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对神学进行了现代化的改革,这是他们对大学和学科的世俗化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时,在神圣罗马帝国也出现了“爱国的”、“伦理—经济学”社团,“实用知识学会”和许多其他“学会”。此外还出现了梅森学派和一些秘密学会,但他们的目的和行为方式与那些改革后的大学没有什么差异,他们与许多学院都有广泛而深远的联系。地方性和地区性很久以来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固有特征,这与启蒙运动强调全球主义的追求并不矛盾。
自18 世纪80 年代始,在大学里和从前一样在学院之上对科学知识和精深的知识进行划分,因此学科内的学术讨论对哲学学科及其子学科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后者现在具有了与以前的“高级”学科的平等身份,事实上哲学更进一步,宣称(最后成功了)它是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即便当人们将重心放在历史和文献学科及“唯心主义”哲学的时候,也没有真正阻止四艺中的学科吸收这些学科的营养,并以自己的方式产生影响。[30,31]在荷兰,大学所起的作用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大学所起的作用类似,其改革也获得了成功。
大多数成功的改革都发生神圣罗马帝国的新教地区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这种成功常常是大学教授和那些自身在大学里接受过教育的君主的顾问合作的结果,因而这些改革主要是内部的学术创新。罗马天主教会的教育机构之所以采纳这些改革,通常源于一些教授的坚持,但更多地源于地区政府、君主的顾问和君主本人的作用。正是源于此,他们首先考虑的是政府的利害关系,而不是教会的利害关系。进一步,正是他们首先考虑政府的利益,所以,财政科学起到了“改革学科”的突出作用。这种情况在其他罗马天主教国家里表现在许多方面,在俄国也是这样。各国的君主为了使他们的社会符合当时的发展趋势,不得不将专业培训当作通向目标的可靠途径。从1760年开始,人们对帝国的这种状况日益感到悲哀。人们要求改变神学和哲学学科的落后状况。在对贵族政府的激烈批评中伴随着这些抱怨。他们的主要目标在于,为以前的哲学院和新教神学院的学生争取获得与法学院学生所享受的平等地位,并因此为他们赢得获得公共职位的权利。在大学重组以后,在对新柏林大学的效法中,这种不满的情绪在哲学院的毕业生和在读学生的身上转变成了各种优越的感觉并表现了出来。[32,33]
启蒙运动宠爱专门学院高过综合大学的趋势在总体上并没有成功地赢得德国、荷兰或北欧各国当权者的支持。的确,柏林的苗圃和矿业学院、维也纳的玛丽亚—塞丽西厄那姆和兽医学校,以及慕尼黑的财政学院等,都表明大学并非一统天下。然而,即便是星期三改革者学会,即在柏林致力于启蒙运动法则的改革者的圈子在讨论这些问题(主要在1795 年)的时候,也公然宣称,他们反对大学的“废除或彻底地转化”。将大学分成学院尽管是陈旧的和“修道士的”,但它是(有争论)对学科的一种理想的调整和改革,而不是彻底地变化才是明智的。
在西班牙和在葡萄牙一样,君主或它的首辅大臣宣布根据启蒙运动的原理对大学进行改革。改革不只是关心如何确保政府在所有公共事务中的统治,还明显地反对教会或反对耶稣会。改革者极为关心如何改善大学的荒凉状况,因为它们已没落到了为专业从业者提供预备教育的培训学院和机构的水平。首先是查尔斯三世(Charles III,1759-1788)试图对大学进行改造。他对那不勒斯的启蒙运动思想相当熟悉,并且试图通过他的大臣伯纳多·塔努奇(Bernardo Tanucci)对大学施加影响。[34,35]1753 年协定同意给予王权的职责及对耶稣会教会的驱逐,为改革提供了有利条件。从这些改革始,每所大学均设四个学院。法学院特别受到宠爱。人们相信,法学院是实现法国启蒙运动理想任务的当然机构,能提供所有改革努力的正确模式。虽然上层宣布进行这些改革,但并没有获得受教育不足的教授们的真正支持。结果,改革只停留在表面上。然而,从中也形成了一种在19 世纪才被充实内容的制度结构,并在知识分子和部分上层阶级中迷漫着亲法国政府而反对教会特权的态度。然而,这种态度的广泛程度和深入程度,都不足以确保仅仅持续了两个年代的改革活动走向成熟,并产生持久的效力。尽管如此,许多省属的学院确实使农学和技术取得了进步。正如省属学院在其他欧洲国家所起的作用一样,这些学院在共济会会员和许多秘密社团的支持下,使改革者的这种绵长的努力得到了加强。
尽管与西班牙相比需要更大的努力,卡瓦略(Sabastiao de Carvalho Pombal)候爵这位杰出的葡萄牙大臣还是试图根据他那个世纪的进步的启蒙运动颁布法令。当卡瓦略向耶稣会教派宣战的时候,约瑟夫一世(Joseph I)授予了他放手改革的权利。在约瑟夫一世加冕12 年之后,卡瓦略开始收回耶稣会教派的教育特权。他受法国启蒙运动的启发,希望将教育建立在世俗的法理之上。耶稣会教会在反宗教改革时期建立的埃武拉大学被废除了,并且将科英布拉大学变为国立大学,根据启蒙运动的原则进行管理。乔姆布诺大学的地位于1777 年得到确认,由此宣布了经院哲学的结束,也使各门科学开始转到了经验主义和实际应用的方向上。葡萄牙似乎是进步的天主教社会的先锋,启迪开始较早,并被新大陆急切地吸收,又在那儿获得进一步发展。[36]
在正式组织上,苏格兰大学与大陆大学保持着巨大差异,首先,它们没有采用大陆大学的做法将大学分成学院。不过,它们的教学和教科书影响了许多参与了欧洲启蒙运动的国家,并且对美国的教学和培训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但是,由于苏格兰大学产生了各种学术危机,而且没有聘任杰出教师的能力,在19 世纪逐渐移出了欧洲的学术圈子。
在18 世纪下半叶,整个欧洲的大学都从神学院的统治中解放了出来,这与其希望讲授有用的、实践的和易于应用的知识的想法相吻合。正如在法国不久发生的那样,这导致培训专门人才的专业成为教育的重点。这促使大学引入了新的学科,并导致已经在教授和学习的那些学科发生了变化。无论如何,对科学和学术方法及其本质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并且由于这种认识的变化,研究科学和学术的那些人的行为和自我认识也同样变化了。
欧洲不同地区和类型大学的普遍变化绘制了一副色彩极为丰富的图画。在某种程度上,法国的高等教育机构比其他欧洲国家更全面地坚持实施了启蒙运动的思想。在由拿破仑领导的法国人对欧洲部分地区的占领期间,一些被占国家接受了法国的模式,但总体上没能保持多长时间。
启蒙运动时期,西班牙、葡萄牙和俄国的改革在大学里没产生持久的效力。在紧随法国大革命的一些事件之后,来自上层的压力一旦缓和,改革的热情马上就烟消云散了。因而大多数大学保持的仅是在科学和学术命题建立过程中留给它们的那些东西,除此而外它们没有增加任何内容及变化。它们仍停留在旧的传统和稳定之中,变成了纯粹的公共培训机构。
某些学科的革新在牛津和剑桥曾出现了许多良好的开端,并且出现了对大学改革的激动人心的公开讨论,但是英国大学对其以前的组织模式及科学本质和方法的理解抱有相当忠实的信念。从根本上看,它们坚持已有的古老传统。
在意大利则相反,某些相信意大利政府的大学进行了深刻的持久的变革,将新的精力释放到了科学和学术工作中。它们以自己的方式期待在意大利半岛出现各种更广泛的运动,这些运动将导致社会和学术更具有全面的活力,国家更加统一。在波兰也是这样,大学教育和培训的革新也带来了相当明显的进步学术运动的成果。然而,国家的支离破碎使得这种努力画上了句号。[37]
苏格兰大学,特别是爱丁堡大学,经历了一个具有广泛交错影响的巨大的高潮。启蒙运动的某些思想、科学和技术的某些观念,以其最具有活力的形式出现在了苏格兰。但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大学不同,苏格兰大学的这些革新没能持续下去。
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的挑战之后,发生在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的改革,及德语国家的大学仿效它们所进行的改革,因一些重要的革新得以延续,这些革新在许多方面为大学教育和培训及理论科学和学术的应用建立了一种能够持续发展和成长的新模式。虽然柏林大学的改革在其重点上有创新,并且确实提出了一种在广泛的意义上认识研究、科学进步和科学价值的新途径,但它仍是建立在以前的发展、理论和技术之上的。自此以后,大学成了科学和学术的适当场所,为现代政府对自己的合法性和能力充满信心提供理论基础,并使人们认识到现代社会需要教育和培训。
总之,以思想和学术为追求的大学面对影响人们思想和行为方式的启蒙运动,或主动或被动,都必须面对那个时代提出的挑战。就启蒙运动和18 世纪欧洲大学的互动关系看,大学要保持持续发展的动力,一方面要积极应对外界变化带来的各种挑战,努力解决社会发展和人类生活所面临的问题,另一方面,大学应该有自己的坚守,才能始终保持教育、教学和研究的活力,并树立自己在整个大学世界的独特地位。
参考文献:
[1]Cassirer,E.Die Philosophie der Aufkla¨rung[M].Hamburg:Felix Meiner Verlag,2007.
[2]Gay,P.The Enlightenment:a comprehensive anthology[M].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73.
[3]Hazard,P.La Pensée européenne au XVIIIe siècle de Montesquieu à Lessing[M].Paris:Boivin,1946.
[4]Chaunu,P.La Civilisation de l'Europe des Lumières[M].Paris:Flammarion,1971.
[5]Palmer,R.R.The 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2.vol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9.
[6]C.Brinton,A Decade of Revolution,1789-1799[M].New York:Harper and Row,1963.
[7]希尔德·德·里德-西蒙斯.欧洲大学史第二卷:近代早期的欧洲大学(1500-1800)[M].贺国庆,等,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449-454.
[8]希尔德·德·里德-西蒙斯.欧洲大学史第二卷:近代早期的欧洲大学(1500-1800)[M].贺国庆,等,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449-454,620-624.
[9]Hammermayer,L.Akademiebewegung und Wissenschaftsorganisation.Formen,Tendenzen und Wandel in Europa wa¨hrend der zweiten Ha¨lfte des 18.Jahrhunderts[M]//Amburger,E.,Ciésla,M.,and Sziklay,L.Wissenschaftspolitik in Mittel-und Osteuropa.Wissenschaftliche Gesellschaften,Akademien und Hochschulen im 18.und beginnenden 19.Jahrhundert.Berlin:Ulrich Camen,1976:1-84.
[10]Voss,J.Die Akademien als Organisationstta¨ger der Wissenschaften im 18.Jahrhundert[J].Historische Zeitschrift,1980,231.
[11]Hammerstein,N.Zur Geschichte und Bedeutung del Universita¨ten im Heiligen R o¨ mischen Reich Deutscher Nation[J].Historische Zeitschrift,1985,241.
[12]Plongeron,B.Recherches sur l'Aufkl a¨rung catholique en Europe occidentale(1770-1830)[J].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1969,16:555-650.
[13]Barton,P.F.Maurer,Mysten,Moralisten[M].Vienna:Bohlau Verlag,1982.
[14]Hammermeyer,L.Zur Geschiche der europa¨ischen Freimaurerei und Geheimgesellschaften im 18.Jahrhundert[M]//Balazs,E'.H.Befo¨rderer der Aufkla¨rung in Mittel-und Osteuropa.Berlin:Camen,1979:9-68.
[15]Reinalter,H.Freimaurer und Geheimbünde im 18.Jahrhundert in Mitteleuropa[M].Frankfurt-on-Main:Suhrkamp,1983.
[16]Dann,O.Lesegesellschaften und bürgerliche Emanzipation[M].Munich:Arbitrium,1981.
[17]Martens,W.Die Botschaft der Tugend,2.nd edn[M].Stuttgart:Metzler,1971.
[18]Wilke,J.Literarische Zeitschriften des 18.Jahrhunderts(1688-1789),2.vols[M].Stuttgart:Metzler,1978.
[19]孙瑜.大学与18 世纪的启蒙运动[J].浙江学刊,2009,(05).
[20]Moraw,P.Aspekte und Dimensionen a¨lterer deutscher Universit a¨tsgeschichte[M]//Moraw,P.and Press,V.Academia Gissensis.Beitra¨ge zur alteren Giessener Universita¨tsgeschichte.Marburg:Elwert,1982:1-44.
[21]胡钦晓.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社会资本视角上欧洲传统大学的没落[J].江苏高教,2011,(01).
[22]Chitnis,A.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A social history[M].London:Rowman and Littlefield,1976.
[23]Sarrailh,J.L 'Espagne écLairée de La seconde moitié du XVIIIe siècle[M].Paris:Imprimerie Nationale,Libraire C.Klincksteck,1954.
[24]Herr,R.The Eighteenth-Century Revolution in Spain[M].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9.
[25]Fubini,M.La cultura illuministica in Italia,2nd edn.[M].Turin:Edizioni Radio Italiana,1964.;Venturi,F.Settecento riformatore[M].Turin:Einaudi,1969.
[26]Daniel,G.Geschichte Von Frankrech,vol.2[M].Chicago:Palala Press,2018.
[27]Brockliss,L.W.B.French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A Cultural Histor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28]Hammerstein,N.Zur Geschichte und Bedeutung der Universita¨ten im Heiligen R o¨mischen Reich Deutscher nation[J].Historische Zeitschrift,1985,241(02):287-328.
[29]Hammerstein,N.Universita¨ten und gelehrte Institutionen yon der Autkla¨rung zum Neuhumanismus und Idealismus[A].Mann,G.and Dumont,F.Samuel Thomas Soemmerring und die Gelehrten der Goethe-zeit,Soemmerring Forschungen I.Stuttgart/New York:G.Fischer,1985:309-329.
[30]Hammerstein,N.'Die deutschen Universitaten im Zeitalter del Aufkla¨rung[J].Zeitschrift für historische Forschung,1983,10:73-89.
[31]Hammermayer,L.Geschichte der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vol.I,2nd edn.[M].Munich:Beck'sche Verlagsbuch,1983.
[32]Muhlack,U.Die Universita¨ten im Zeichen von Neuhumanismus und Idealismus:Berlin[J].Wolfenbütteler Forschungen,1978,4:299-340.
[33]Nipperdey,T.Deutsche Geschichte 1800-1866.Bürgerwelt und starker Staat[M].Munich:C.H.Beck,1983:470-482.
[34]Procacci,G.Geschichte Italiens und der Italiener[M].Munich:C.H.Beck,1983:186-219.
[35]Omodeo,A.Die Erneuerung Italiens und die Geschichte Europas[M].Zürich:Artemis,1951.
[36]Ferr a¨o,A.O marquês de Pombal e as reformas dos estudos menores[M].Coimbra:Imprensa da Universidade de Coimbra,2014.
[37]Lésnodorski,B.Les universités aux siècle des Lumières[M]//Fishman,S.Les Universités européennes du XIVe au XVIIIe siècle.Aspects et problèrnes.Geneva:Librairie Droz,1967:143-159.
课题来源: 山西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社会资本视角下高校教师专业发展策略研究”(课题编号:GH-18115)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赵敏,太原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教育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教师发展。
(责任编辑:金传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