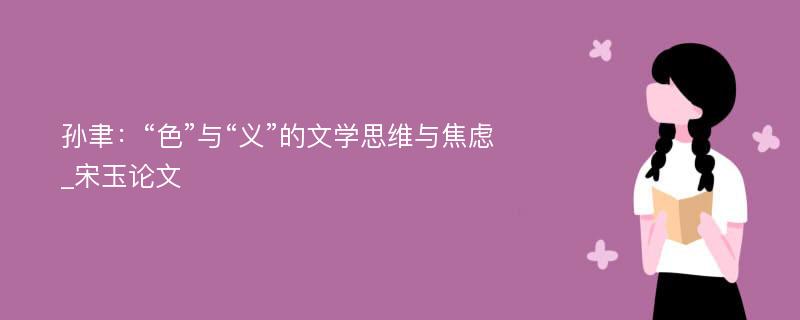
宋玉:文学思维与“色”“义”焦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焦虑论文,思维论文,文学论文,宋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荐枕席”、“迷下蔡”:女性形象的角色定位
宋玉在作品中塑造出一些美女形象。通过多样的艺术描绘,赋予她们以不同类型的美,同时,她们的情感诉求更增添了美女形象的魅力。“惑阳城,迷下蔡”是这些美女形象的意义预设。
(一)作者笔下的美女群像与美的类型。
宋玉笔下美女的身份有很大差别,女神、邻女、采桑女、逆旅主人之女等。在作品中,这些女性形象超凡之美的内涵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神秘女神的奇幻美、小家碧玉的清醇美、都会采桑女的落落大方美。
美女类型之一:女神的奇幻美。
巫山女神是宋玉塑造得最成功的,同时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的美女形象。作者在《高唐赋》、《神女赋》中多层次、多角度地表现女神的奇幻美。
巫山女神这一形象集合了超现实的神性与现实美女的魅力于一身,建构起以“奇幻美”为主色调的文学形象。
宋玉向襄王讲述朝云的仪态之美。在朦胧中,绚烂的朝云是女神仪态的幻化:她刚刚出现时,浓密如茂盛的青松。渐渐舒展,仿佛美女舞动长袖,遮蔽太阳的光辉,又似在眺望心中的恋人。形态忽然改变,仿佛驾云车疾驰,五彩羽毛的旌旗飘舞,清爽如风,凄迷如雨。风止雨霁,千姿百态的朝云也无处寻觅。女神在清晨的天空变化万端,去留无迹。
襄王向宋玉讲述梦中女神的朦胧美。她显现于恍惚仿佛中,“茂矣美矣”,“盛矣丽矣”,华美高贵,盛装艳丽,“上古既无,世所未见”。襄王对女神超凡脱俗之美给予热情礼赞。“其始来也”,“其少进也”,梦中相会,远观近察,环姿玮态的妆饰,罗纨绮缋的服采,馨香的发肤,娴静的性情,都令襄王心荡神迷。①
宋玉受命献赋,将襄王梦中所见女神的朦胧形象转化为真切生动的美女影像,他既盛赞女神“其象无双,其美无极”,具有足令毛嫱、西施相形见绌的超凡脱俗之美;又以工笔画般的手法,细致刻画她的容貌:双眸、眼神、蛾眉、朱唇,她的腰肢、体态,讴歌她的天生丽质。②
《高唐赋》、《神女赋》通过襄王、宋玉绘声绘色地讲述,塑造出一个无与伦比的女神形象。
美女类型之二:邻女的小家碧玉清醇美。
作品中的宋玉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③
作品用天下、楚国、臣里、东邻层层推进的视角,由天下之广,逐步聚焦于邻里,夸耀邻女是楚国乃至天下最美的少女。她的身材高矮胖瘦恰到好处,不需粉黛,具有天生容颜之美。她的眉目、肤色、腰肢、牙齿、笑靥,都美丽动人。作者没写她的穿着打扮。没有华贵的服饰,更显出布衣不掩国色的清醇之美。
美女类型之三:都会采桑女的落落大方美。
《登徒子好色赋》中,宋玉还描绘了爽朗多情的郑卫采桑女形象。
章华大夫是一位见多识广的人,“少曾远游,周览九土,足历五都”,见过众多美女。他发现郑卫采桑女是世上最美的女人。他认为宋玉所称赞的邻女不过是“南楚穷巷之妾”,远不能与他所见过的这些采桑女相比。郑卫在周代就被视为“淫声”、“淫乐”的产地,桑间濮上是著名的青年男女聚会、游乐之所。章华大夫特别称赞这里的美女:“此郊之姝,华色含光,体美容冶,不待饰装。”他对采桑女不需要浓妆艳抹的天生丽质赞叹有加。而在采桑女群体中,他特别赞赏其中最漂亮的少女,与她赋诗赠答。这位采桑少女:“怳若有望而不来,忽若有来而不见。意密体疏,俯仰异观,含喜微笑,窃视流眄。”④她天生丽质,含情脉脉,在与士人的交往中保持分寸,又在一颦一笑间暗送秋波,既能以礼自持,又显得落落大方。
上述三类美女的身份有很大的差异,但却都是美的化身,“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⑤都是魅力的力度。
(二)其次,宋玉作品中的美女在情感诉求方面也有明显的特点。
她们不仅有动人的美貌,而且都表现出对爱的渴望与诉求。她们的身份、处境不同,对爱情的表达也有所差异。这方面的差异也可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荐枕席”。
《高唐赋》中的巫山女神兼有神性与人性的特点。她带着飘忽的、婀娜多姿的神性,带着世间欲望的人性,出现在与楚先王相会的特殊机缘中。⑥女神求爱望幸的情愫,“愿荐枕席”的告白,将诡秘色彩和美女诱惑融合在一起,铸就了她与楚先王的旷世奇缘,成就了文学史上人神恋爱的经典传说。
宋玉笔下热切渴望爱并坦率追求幸福的美女还有《讽赋》中店主人之女。宋玉出行,人饥马疲,寻求休息处。正值主人翁夫妇外出,独有主人之女在家。她请宋玉在兰房芝室休息,自己穿上华美的衣服为客人做饭,劝饭。她对爱情的表白更坦率真诚:
以其翡翠之钗,挂臣冠缨,臣不忍仰视。为臣歌曰:“岁将暮兮日已寒,中心乱兮勿多言。”臣复援琴而鼓之,为《秋竹》《积雪》之曲。主人之女又为臣歌曰:“内怵惕兮徂玉床,横自陈兮君之傍。君不御兮妾谁怨,日将至兮下黄泉。”⑦
主人之女挑逗客人,以翡翠钗挂客人的冠缨,又在歌中述说自己玉体横陈,等待宋玉的爱怜,大胆地将自己激动不安和渴望爱情的急切内心倾诉给宋玉。这是用歌声表达了“荐枕席”愿望与心情。
第二类,“登墙窥视”。
《登徒子好色赋》中的邻女是一位痴情的少女。她爱慕作品中的宋玉,竟然“登墙窥臣三年”,对爱的表达虽不如“愿荐枕席”那样坦率,但其对男主人公的爱慕之意已表达得较为明白。这样的举动能坚持三年,足可看出她对爱情的大胆与执著。
第三类,“意密体疏”、“窃视流眄”。
《登徒子好色赋》中,章华大夫向那位最美丽的采桑女赋诗示好,又向她献花。这位美女“恍若有望而不来,忽若有来而不见。意密体疏,俯仰异观,含喜微笑,窃视流眄。”采桑女对章华大夫很有好感,微笑间暗送秋波,然而在行动上却保持一定的距离与分寸。这是爱意与好感层面的感情交流,与“愿荐枕席”的求爱望幸有本质的不同。
类似的情感在《神女赋》中也表现得较为明显。女神与襄王交往中,其感情明显不同于面对楚先王时。
时容与以微动兮,志未可乎得原。意似近而既远兮,若将来而复旋。褰余帱而请御兮,愿尽心之惓惓。怀贞亮之洁清兮,卒与我兮相难。⑧
很显然,女神并非见到每个楚王都“愿荐枕席”。襄王为会见女神,虔诚地斋戒,选择吉日良辰,又在服饰、仪仗等方面精心准备,急切地希望续写巫山传说。女神给他以希望,甚至掀起他的床帐。然而,女神的内心始终在彷徨,似乎有接受襄王之意,却又在关键时刻退缩,委婉拒绝。最后给襄王留下难以排遣的遗憾。
作者极力渲染女性形象的惊人之美,描写她们对爱的诉求,塑造出一些魅力四射的女性形象。然而,这并不是作者艺术构思的归宿。这些女性形象,包括她们的美貌,她们求爱的眼神、话语,在作品中都是展现男主人公的精神世界的外部条件,也是实现作品艺术宗旨的基础。
二 纵欲制情三境界
宋玉笔下女性的美和对爱的诉求构成男主人公必须面对的强烈的外部诱惑。在她们的魅力面前,是接受欲望的驱动,还是选择道义的皈依,成为对男主人公内心世界考量的主要依据。面对这些女性的动人之美,宋玉笔下的男主人公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程度的欲望,表现出各自的情欲观。男主人公精神世界的艺术构建主要体现在襄王、宋玉和章华大夫三个文学形象的描绘中。这些形象为人们展示出在情感、爱欲方面三种不同的境界,即贪恋女色的情欲观,以礼自防的情欲观,以义制欲的情欲观。
(一)贪恋女色的情欲观
在《高唐赋》中,宋玉生动地渲染女神的奇美、诡秘,讲述楚先王同女神的艳遇奇缘,这在襄王心中产生强大的诱惑。在传说中,楚先王与女神的高唐之会是不期而遇的缘分。而襄王却对高唐传说心驰神往。他渴望自己能续写这个传说,渴望女神能在自己的生活中重现。他对女神怀有强烈的好奇心,也怀着强烈的欲望。
为了续写高唐传说,赢得女神的芳心,襄王煞费苦心地准备这次会晤。他“先斋戒,差时择日。简舆玄服,建云旆,蜺为旌,翠为盖。风起雨止,千里而逝,盖发蒙,往自会。”他虔诚地斋戒,选择吉日良辰,服饰、仪仗等都经过精心准备,为满足内心强烈欲望竟然像祈福祭神一样诚敬。
襄王焦急地期盼与女神相会。“晡夕之后,精神怳忽,若有所喜,纷纷扰扰,未知何意。目色仿佛,乍若有记。见一妇人,状甚奇异,寐而梦之,寤不自识。罔兮不乐,怅然失志。”究竟是幻觉还是梦境,朦胧恍惚,真幻难辨。襄王对女神的追求已经到了迷失自我的程度。此后,“抚心定气,复见所梦。”
然而,对襄王来说,黄昏时如梦似幻的经历留给他的是失落,而此后“复见所梦”的追寻依然是惆怅之旅。他盛赞女神的魅力:“茂矣美矣,诸好备矣。盛矣丽矣,难测究矣。上古既无,世所未见。”他称赞女神是卓绝千古的美女。他痴迷地注视女神,“其始来也”,“其少进也”,远观近察,女神的姿容仪态,极服妙采,以及发肤性情无不精妙。他自认为如此美好的女神“宜侍旁”,正适合自己,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夙愿。然而,女神在犹豫徘徊之后,引身离去。
欢情未接,将辞而去,迁延引身,不可亲附,似逝未行,中若相首。目略微眄,精彩相授,志态横出,不可胜记。意离未绝,神心怖覆,礼不遑讫,辞不及究,原假须臾,神女称遽。徊肠伤气,颠倒失据。暗然而暝,忽不知处。情独私怀,谁者可语。惆怅垂涕,求之至曙。⑨
这次热切盼望,经过一番努力而实现的梦会,竟然在情意缠绵处戛然而止。这令襄王更加失落。他追求艳遇,但鸳鸯梦醒,反把愁添。
作品中的襄王从听说巫山女神到对梦会的追寻再到梦断高唐的失落,可以看出:贪恋女色,追求欲望的满足,这是襄王情欲观的表现。
(二)以礼自防的情欲观
作品中的宋玉形象表现出以礼自防的情欲观。这一感情倾向在《登徒子好色赋》、《讽赋》中表现得很充分。
《登徒子好色赋》中东邻的绝色美女向宋玉示爱,“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邻女虽然美丽动人,又窥墙表示爱意,但他始终未对邻女给以肯定的回应。他以漠然的态度回答少女,表现出在美女诱惑面前无所动于心,严格地保持自己道德操守,冷静地以礼自防。
《讽赋》中的宋玉形象与此相近。作品中的宋玉面对主人之女求爱的表示,先是“不忍仰视”,拒不回应;后又弹奏《秋竹》、《积雪》之曲,表现自己情操高洁;主人之女又在歌声中表示,要“横自陈兮君之傍”,宋玉却回答:“吾宁杀人之父,孤人之子,诚不忍爱主人之女。”他断然拒绝了主人之女的爱。在他看来,回应少女的爱就是比杀人之父还严重的罪行。两情相悦的爱,被解释为超越情感交流,超越道德层面的罪恶行径。
(三)以义制欲的情欲观
章华大夫对美女的态度与作品中的宋玉不同。作为文学形象的宋玉是在不同美女交往情况下实现严格的以礼自防。章华大夫则不然。他欣赏女性美,喜欢同美女交往,在交往中保持礼法准则。他自述与郑卫采桑女交往的情形:他吟诵《诗经·郑·大路》中的诗句表达对采桑女的好感,又赠少女鲜花。对方仪容端庄,也以诗回赠,彬彬有礼。“迁延而辞避,盖徒以微辞相感动,精神相依凭。”
在章华大夫看来,承认女性美并喜欢同美女交往,并不属于“好色”的毛病,“以微辞相感动”的精神交流也是正常的。关键在于当事人应把握交往的原则,这就是“目欲其颜,心顾其义,扬诗守礼”。他以自己亲身经历说明同美女交往的感受,以及由此总结出的认识,“楚王称善”。
章华大夫的行为和观点表现出更高境界的爱情观与女性观。他见美思义,不放纵情欲,严守道德修养,彬彬有礼地同美女保持精神层面的交往。
从这些作品可以看出,作者笔下的男主人公在情欲修炼方面显示出三个不同的境界,从纵欲到以礼自防,再到“目欲其颜,心顾其义”,表现出作者在精神世界所进行的探寻。
三 此“宋玉”非彼宋玉
在宋玉的作品中有一个现象值得思考,即往往有一个作为文学形象的“宋玉”出现,这些作品中的“宋玉”所表达的观点,是否可以等同于作品宗旨?是否等同于作者的观点?笔者认为,作品中人物构成关系不同,此“宋玉”同作品的宗旨也存在合与分的差异。
在《高唐赋》、《神女赋》中,楚先王仅仅出现在话语背景中,作品有襄王、“宋玉”和若隐若现的女神三个人物形象。“宋玉”是襄王的文学侍臣。他从解释高唐云气而引出女神传说。襄王则因传说而产生对女神的仰慕追求与痴迷的贪恋。
作品中“宋玉”两次献赋。前一篇描绘高唐“使人心动,无故自恐”的山水,以写女神生活的氛围,继而写祭祀、狩猎,为襄王会晤女神的前奏。作品通过这样的描写,意在突出女神超凡脱俗的神性与魅力,也在预示同女神会晤并不是容易实现的。下篇赋襄王与女神梦会之事。这次会晤,“他人莫睹,王览其状”。这是襄王梦中之事,别人自然看不到。作者根据襄王讲述的情形进行艺术显现。但襄王多赞扬女神的美,而他所说“宜侍旁”的联想,既是他一厢情愿的幻想,也流露出一些无奈和遗憾。
宋玉献赋描绘了女神异乎寻常的美,反复表现她在襄王面前的犹豫,“意似近而既远兮,若将来而复旋”,最终女神“怀贞亮之洁清兮,卒与我兮相难。”“顾女师,命太傅。欢情未接,将辞而去,迁延引身,不可亲附。”在离去之时,襄王还要挽留,“原假须臾,神女称遽”,不肯稍作耽搁。留给襄王无限的惆怅与失落。“徊肠伤气,颠倒失据。暗然而暝,忽不知处。情独私怀,谁者可语。惆怅垂涕,求之至曙。”
在宋玉受命所作的赋中,描写襄王与女神的交往,“陈嘉辞而云对兮,吐芬芳其若兰。精交接以来往兮,心凯康以乐欢。”作者以艺术方式肯定他们在精神方面的交流,至于别后的惆怅,则委婉地表现出襄王追求情欲的非现实性和失落的必然性。
作品以较多笔墨铺排渲染襄王与女神相会的情景,同时,又用委婉的方式传达出襄王与女神对这次相会的感情预期。在襄王看来,高唐之会必将是先王艳遇的再现,女神“愿荐枕席”而实现自己纵欲的快乐。而女神却以自己的神态举止表明,她与襄王的会面、交往是值得高兴的,是彬彬有礼的。作品中的“宋玉”以委婉的艺术手法表现出对女神态度的肯定。因此,作品中“宋玉”的形象与观点都是作者情欲观、审美观的直接表达。作者以这样假设问对的方式,用赋体文学将自己对情感的认识传达给“襄王”,也艺术地传达给读者。
在《登徒子好色赋》、《讽赋》的研究中,则不应简单地将作品中“宋玉”的观点等同于作者的思想。而应看到,此“宋玉”的观点只是作者思想构成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对作者思想的分析,对作品宗旨的认识,都应从文本的整体把握中得出。
在《登徒子好色赋》、《讽赋》中都有进谗言者,都以“好色”为中伤“宋玉”的主要依据,并由此提出不应让“宋玉”作为侍从出入王宫,出现在众嫔妃面前。《讽赋》的宗旨在于意在回应“出爱主人之女,入事寡人,不亦薄乎?”这是批评“宋玉”在情感方面比较放纵,随意勾引身边的女人,是浅薄轻浮的浪子。而作品中的“宋玉”在主人之女主动示爱之时,态度坚定地回绝了主人之女,传达“以礼自防”的情欲观,不近女色的人生态度。这里表现“宋玉”尽管承认女性的美,却绝不同女性交往的“以礼自防”,甚至将爱主人之女视为与杀人相类的罪恶行径。《登徒子好色赋》中的“宋玉”也表现了这样的“以礼自防”。但作品中的章华大夫则不然。他讲述自己的经历和感受,表明他喜欢同美女交往,主张在交往中坚守义。“宋玉”同章华大夫之间明显构成情欲观方面两个不同的境界。
“宋玉”与章华大夫思想观点的差异同他们的身份处境有直接关系。章华大夫出入朝廷,使于四方,其所接触的是各诸侯国的美女。这样的人即使“又性好色”,对楚王,对楚朝廷都无大碍。作品中的“宋玉”为襄王近臣侍从,随王出入宫闱。而且“玉为人体貌闲丽,口多微辞,又性好色”。这样的人经常出入王宫,必然对后宫寂寞的嫔妃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因此,进谗言者以此批评“宋玉”,同时,也要以此调动襄王的妒嫉心和猜忌心,这将使楚王产生后顾之忧。因此,对“宋玉”必须有所戒备。
“宋玉”的处境令他对这一问题非常敏感。章华大夫可以接触众多美女,可以向美女赋诗、献花。他却不能这样做。他必须防范嫌疑,要使襄王放心,表明自己对美女不感兴趣,甚至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麻木与冷漠。他要以这样的方式证明自己虽然“体貌闲丽”,却绝不会扰乱宫闱。因此可以说,“宋玉”对邻女示爱拒绝回应的“以礼自防”,只是作者思想中的一个部分,更重要的观点通过章华大夫之口表述出来。
我们在阅读这些作品时,不应将作品中的“宋玉”等同于作者,也不应将作品中“宋玉”的观点视为作者思想的真实体现。
本文强调分析文学形象“宋玉”的爱情观,是因为作品中人物的观点不能与作者的观点等同。不论作品中人物名之曰宋玉、章华大夫,还是登徒子,他们都是作品主题预设的载体,其中每个人物形象承载的意义指向可能有很大的差别。他们作为传达意义的符号出现在作品中,而作者的主题预设已经融入这些人物形象的言谈与精神中。我们只有从这样的层面分析作品中的“宋玉”形象,才能准确、客观地阐述作者的思想感情。
四 目欲其色,心顾其义
上述作品中的人物都承载着作者的审美追求,表现其爱情观中色与义的焦虑。宋玉关于女色和情欲的认识,表现在作品中“宋玉”和章华大夫的言谈中。概括地说就是:以礼自防,“目欲其颜,心顾其义”。
作者继承了周代主流文化的情欲观,在文学作品艺术营造与发挥中形成了自己的观点。
在周代文化看来,社会的纷乱与争斗源于人们欲望的恶性膨胀。人们的欲望主要来自对权力、财富、女人的追求。《左传》昭公十年引逸书云:“欲败度,纵败礼”⑩,情欲及情欲的放纵同礼的宗旨,同社会秩序的稳定是相互对立的。《国语·楚语》载楚贤臣伍举曰:“私欲弘侈,则德义鲜少”(11)。私欲和德义、情感和礼,二者不能都得发展,只能是抑此扬彼或抑彼扬此。人们在分析齐桓公能享有齐国的原因时,就指出,他“不藏贿,不从(纵)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厌,是以有国。”(12)追求礼,还是放纵欲,已经成了衡量一个人是否合于礼的定性的重要方面,也是分析其成败的重要依据。《乐记》对这一思想概括得更为透辟。其文云:“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佚作乱之事。”(13)这就极为深刻地揭示出在礼的思想原则中,情与礼在本质上的对立关系。为了礼的理想与礼的秩序,就必须压抑情感,使世俗的对物质享乐的追求停止于适当的限度之内。否则,这情感,这追求,就被视为丑恶的,罪孽的,应当受到社会的甚至是当事人自己的排斥与否定。(14)
面对这样的人生课题,先秦的哲人给出自己的理论阐述。道家主张清心寡欲,要人们衰减对物质享乐和女人的追求,从源头上解决因情欲引发的不安与争斗。儒家传承周代礼乐文明,主张以礼制欲,扼制欲望的发展与膨胀,提出了好色不淫的主张,要求人们将情欲限定在礼的规约框架内。《乐记》云:“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15)《荀子·乐论》也引用这段论述,可见这一观点在当时的流传和影响。
宋玉生活的时代,楚国贵族和士人已经较多地接受中原文化和儒家学说。从郭店楚简中的《缁衣》、《性自命出》等出土文献,可以看出当时楚国与中原文化交流的程度,可以看出儒家思想在楚国上层贵族与士人中间的传播与影响。
在中国文学史上,宋玉第一个对女性的形体美进行正面描写和艺术渲染,使之具有独特生动的美和诱惑力,并在此基础上将女性美与人们的情欲置于审美观照下。选择这样的题材就表现出作者对楚国王室的淫乐之风,对思想家禁欲主义说教的思考与挑战,而如何塑造这题材中的系列人物,如何通过作品的主题预设表现自己的审美追求,便集中体现为创作中的“色”、“义”焦虑。
先秦的儒家、道家将情和礼对立起来,否定情、欲乃是人们现实生活感情的必然,而要限制情感的滋生与发展,提倡禁欲的说教。这种脱离人们情感实际、违反两性关系合理性的说教只能成为阻碍社会发展,阻碍人们追求幸福与欢乐的桎梏,成为封建卫道士摧残人们幸福的破烂武器。在禁欲主义者看来,女性美代表了恶的根源,因此提出了“女色祸国”的命题,甚至于说“甚美必有甚恶”,将美女妖魔化,称之为“足以移人”的“尤物”。(16)
宋玉作为敏感的作家,自然不能接受卫道士的苍白说教。现实生活的感受为他提供创作的动力,而作家的审美追求——从文学角度对社会人生进行艺术的观照、解读,则使他不能无视女性美的现实存在,不能无视情欲对于人生与幸福的决定性作用。
另一方面,宋玉生活在楚国上层统治者中间。楚王室淫佚的风气乃是楚贵族和士人无不知晓的。
据《史记·楚世家》载,楚国历史上因不能正确对待美女和爱情,导致宫廷内乱或失败的事屡见不鲜。楚成王将以商臣为太子,令尹子上就极富远见地指出,楚王“多内宠,绌乃乱也。”后来,成王果然要废太子商臣而立宠姬所生的公子职,商臣以宫卫兵包围成王。成王请求食熊蹯而死也不可得。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令国中曰:“有敢谏者死无赦!”伍举入谏。庄王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钟鼓之间。楚平王使费无忌赴秦为太子建迎娶新娘。无忌对平王说:“秦女好,可自娶,为太子更求。”平王从之,卒自娶秦女,为太子另娶妇。这场父纳子妻的丑剧导致伍子胥率吴兵破楚入郢,辱平王之墓。楚怀王宠爱郑袖,袖所言无不从者,以至于在内政外交方面多听枕边风而屡屡失误。(17)
《战国策·楚三》载:张仪见楚怀王,受到冷遇。张仪便以美女为诱饵,曰:“彼郑、周之女,粉白墨黑,立于衢闾,非知而见之者以为神。”楚王曰:“楚,僻陋之国也,未尝见中国之女如此其美也,寡人之独何为不好色也?”乃资之以珠玉。(18)谈到与中原各诸侯国物质富饶的比较,楚王非常自豪,对张仪的态度也很冷淡。但张仪谈起郑、周女人之美,楚王的脸立即由阴转晴,并要张仪为自己游说。
楚君还为争夺美女而出兵征战,用将士的鲜血换取自己情欲的满足。《左传》庄公十四年载,楚文王灭息,将息夫人带回,宠爱超过后宫粉黛,立她的儿子为继嗣,这就是后来的楚成王。《左传》成公二年载,楚庄王出兵伐陈,欲纳美女夏姬于后宫。在大臣的干扰下未能得逞。(19)
楚宫之乱,多因宠幸女色而起。楚国有识之士子上、伍举等贤臣规劝君主理智地对待爱情,处理好嫔妃关系问题。这是楚国大臣的著名谏说。
很显然,在宋玉进行这组创作时,楚王室多放任纵欲无度,甚至于做出违反伦理的大逆不道之事,由此导致楚国王室乃至楚国悲剧的种种乱象,这正是引发宋玉“色”、“义”焦虑的历史依据。
由楚王室放任纵欲及其恶果的考察,很容易推导出排斥女性美,压抑情欲,进而走向禁欲主义的理论训诫。而这正是宋玉审美观照时所不能接受的思想倾向。
宋玉面临着艰难的思考,他不敢也不可能从理论上反驳儒家禁欲主义的教条,而只能对这类题材作巧妙的审美解读。因此,他的作品中出现了与作者同名的“宋玉”形象,传达出儒家禁欲主义束缚下的士人形象。他严格地以礼自防,守身如玉。他发现身边女性的美及其求爱的表示,却不敢做出回应,甚至不敢看,惟恐看一眼,就守不住感情的堤防。对美女的漠视和拒绝,成为他反驳“好色”谗言的有力证据。
然而,这仅仅是作者审美取向中较低层级的人物意蕴。他在“色”、“义”焦虑中艰难探索,在善与美的结合中寻求审美归宿。章华大夫的形象中透露出他审美追求的结晶。
章华大夫所说的“目欲其颜,心顾其义”,以及他同美女的交往,表现出作者对女性美的肯定,表现出对男女交往与情感交流的赞许。通过这一形象,女性美不再像洪水猛兽般可怕。“色”成为作品中美的重要内涵,而“义”恰是对善的追寻,“色”与“义”的平衡是作者通过章华之口传达出的审美结论。
《史记·屈原列传》云:“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20)
“终莫敢直谏”表明宋玉等人同屈原在政治品格方面的差距,表现出作家在人文关怀方面的不同。然而,宋玉对楚王室好色的遗风,对今王将巫山女神视为梦中情人的“寡人有疾”,都看得很清楚,“莫敢直谏”,遂婉而言之,借“好色”不好色为题,通过作品中宋玉、章华大夫等文学形象,传达出作者对爱情与人生的理解。《文心雕龙·谐隐》云:“楚襄宴集,而宋玉赋好色。意在微讽,有足观者。”(21)刘勰谓《登徒子好色赋》意在微讽,而非止抒发对男女之情的认识。这是这位文学理论家独具慧眼的阐释。至于《高唐赋》的宗旨,李善注曰:“此赋盖假设其事,风谏淫惑也。”(22)也强调了作品的讽喻意义。
宋玉敏锐地感受到生活中的美,感受到现实情感的合理性。“目欲其颜,心顾其义”是将美与善结合起来的审美命题。这一命题是对春秋时代视女性为祸水的女性观、文学观的一大进步。这为后来的文学正视女性美、塑造完美的女性形象、表现两性相悦的文学思想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这方面看,宋玉在这组作品中所表现的审美取向具有更深远的文学史意义。
注释:
①见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67页。
②见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68页。
③见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69页。
④见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69页。
⑤见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69页。
⑥《文选》李善注引《襄阳耆旧传》谓先王为楚怀王。笔者认为应据文本,仍作“先王”。至于其为哪一位先王,《高唐》、《神女》二赋中人与事本具虚幻性,故不必指实。
⑦见章樵新订《古文苑》,载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1页。
⑧见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68页。
⑨见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68页。
⑩《春秋左传正义》,载阮元《十三经注疏》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059页。
(11)见徐元诰:《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95页。
(12)《春秋左传正义》,载阮元《十三经注疏》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071页。
(13)《礼记正义》,载阮元《十三经注疏》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529页。
(14)参见许志刚师:《诗经艺术论》,沈阳辽海出版社,2006年,第64—65页。
(15)《礼记正义》,载阮元《十三经注疏》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536页。
(16)见《春秋左传正义》,载阮元《十三经注疏》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118页。
(17)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698—1715页。
(18)见《战国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39页。
(19)《春秋左传正义》,载阮元《十三经注疏》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771、1896页。
(20)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491页。
(21)见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文心雕龙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94页。
(22)见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6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