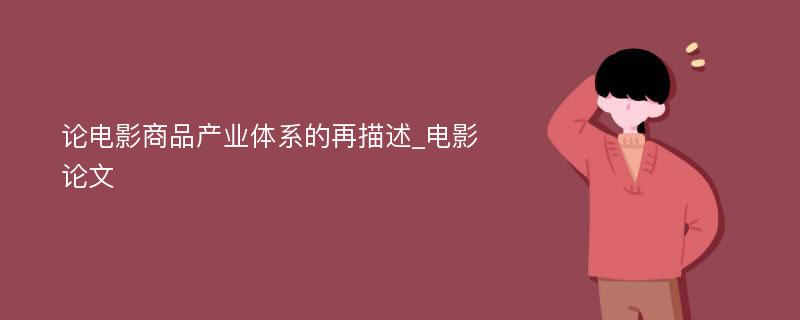
关于电影商品——工业体系的再描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业体系论文,商品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电影机制全面向市场转轨,90%的影片都来自民间投资的今天,我们又一次来讨论电影的属性问题,也许是具有讽刺意味的。80年代到90年代,我们由被动到主动、从引进到模仿地拍了那么多商业片,“观赏性”、“经济效益”越来越频繁地成为从领导讲话到导演阐述中的常用词,一个个艺术片的探索者被评论划归了好莱坞,一拨拨文化人在投资和发行的讨价还价中练成了生意人,我们甚至还有过一位主张娱乐片主体论的最高电影首长……难道,还需要再从头论证电影是一种商品吗?
十二年前,我为《电影艺术》写过一篇《关于电影商品性的再认识》,对中国电影刚刚步入市场的处境作了一番描述,说“再认识”,是就我们跟整个电影世界的认识相比而言。针对长期以来避讳经济规律所潜在的危机,我写道,“如果体制改革再进一步向前发展、制片的盈亏直接影响到创作者的饭碗,我们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局面。”
时光荏苒,鼓吹不曾有一天停止,低谷却始终没能走出。一个数十亿元经营规模的文化工业体系,一个十二亿大众精神消费中举足轻重的传播媒体,一个泱泱古国民族艺术的当代象征,捉襟见肘到这副样子,自有超越电影本身的某些原因,而从圈内同仁到报刊传媒种种关心电影的议论,常使人想起当下上海滩最时髦的一句话:“掏浆糊”,此词极多义,糊涂、装傻、瞎对付、把水搅混、莫衷一是、顾左右而言它……皆可包容。但话是这么说,有浆糊可掏总比清水一潭有趣。应编者之邀请,本着“少谈些主义,多研究点问题”精神,以如下片断描述,权作参考。
电影作为商品的窘迫
时至今日,一部影片究竟是靠什么投入制作,又是怎样进入流通领域,从市场上把成本收回的?这些关于生存的基本事实,是研究电影不可绕开的前提。
先说投资。近三五年来,每年150部的故事片, 由制片厂自有资金或加上政府资助投入拍摄的仅仅十几部,再刨去40部左右港台合拍片,其余90至100部的制片成本都来自各种各样的民间投资。 如果细算资金的额度,则社会投资所占的比例还要来得更大(几部成本上七位数的影片全部出自民营公司之手)。在当前的经济体制下,资本的性质在多大程度上实现着对产品的制约,也许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这些钱不会白白送上门来。以1995年为例,借用时下音乐界约定俗成的分类,145部影片中,严肃类作品为36部,占24%; 通俗类作品109部,占76%,正好1:3。而被我归之为严肃类的作品里,凡属民间投资的,也都具有明确的商业目标。在资金注入渠道多元化的背景下,由于市场定位和投资策略的不同,又促成了制片规模的多层次,一批高成本大制作不仅实现了创作人员的优化组合,而且打破多年“酒香不怕巷子深”的传统,从前期宣传到发行炒卖,做出许多带有鲜明商品特性的新闻。
投资格局的转型,作为电影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先声,本来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征兆。寻求投资回报率、面向大面积观众的作品成为主体,意味着这一传统媒介在文化消费市场中的重新定位,无论一二百万还是两三千万都要给老板赚回来的压力,促成了电影人从选题策划到拍摄制作前所未有的敬业精神。不幸的是,我们频频送出的秋波,老百姓居然还是不买帐,当中肯定出了什么岔子。
这就说到了发行。电影行业机制改革从发行开刀,无疑是抓到了牛鼻子的,但冷静一看,改了三年,实质性的变革只有两件局部意义的事情:一是取消了国产片发行的中影公司独家专卖,二是(由十部大片引进开始)初步实验了票房分帐发行方法。而作为流通主渠道,基本还是计划经济的省级地方垄断发行体系岿然不动,绝大多数影片由制片厂捆在一起卖给省市公司,真正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则建立适销对路、自由竞争的产供销关系还遥遥无期。这个现状,使本来可能获得巨大票房收益的影片由于中间环节的流通阻隔而大大打了折扣,而那些观众根本不需要的作品却因为得不到市场的真实惩罚还在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传媒曾经兴奋地议论过去年有几部国产片走俏影院的好消息,应该说带有相当成分的盲目乐观,所谓“三红一阳”(《红樱桃》、《红粉》、《红尘》、《阳光灿烂的日子》)的热门,首先仅限于京沪穗等几个大城市,同时又是几家民营公司独担风险地突破现行发行运作,采取全额承担宣传费用、票房分成加让利等国营厂家望尘莫及的行销方式的结果。据我所知,尽管这几部影片分别得到了国产片前所未及的回收,但由于发行规模的局限和宣传投入的超常,收支相抵也只是刚刚持平或仍有较大的亏空。同时,因为没有跟得上来的片子,城市影院和观众好不容易吊起来的一点胃口很快被噎了回去,“报春的燕子”行色匆匆,萧瑟秋风依旧。
人们又把这种窘境归咎于好莱坞大片的涌入。其实当初没有它们时国片的情形就跟现在差不多,而上述那些片子的红火又恰恰发生在引进之后;10部大片只是证明了中国电影市场存在着巨大的潜能,以人家的10部和我们的150部之比,假如国片的推出都像那样炒作, 至少不应该是现在这般寒酸。当然,制片的赖发行,发行又会把皮球踢回来——不好意思,你们的大作能跟人家相提并论吗?
这就是中国电影的怪圈:制片由于发行不畅而没有底气扩大生产,发行又因为片源不济而没有热情开拓市场,商品是商品了,未出娘胎就素质赢弱,进入流通更举步维艰。面对这个怪圈,单方面给制片输血或以行政指令控制发行行为的做法只会延续它的存在,急功近利地头疼医头、脚痛医脚,将被历史证明是徒劳的。
电影作为工业体系的困境
考察一下整个世界的电影工业,可以更清楚我们电影的境地。
以下为1994年世界主要电影国家和地区的一些重要数字:
一、年产近100部影片以上的各国制片情况
国家(地区) 影片产量(部) 投资(亿美元) 每部平均成本(万美元)
印度812
0.6814
美国420
48.9 1164
日本251
香港192
中国148
0.3121
法国115
5.38
468
意大利
95
2.63
276
俄联邦
90
0.3134
全球总计
2463
二、年发行收入3亿美元以上各国市场情况
国家(地区) 国内影院
占全球市场份额 拥有影院
发行收入(亿美元)
数(1993年)
美国 53.90
40%25737
日本 15.45
10% 1734
法国 7.945% 4397
德国 7.875% 4200
英国 6.334% 1890
意大利5.203% 3800
印度 5.05(93年) 3%13002
印度尼西亚4.98(92年) 3% 2517
墨西哥3.95(93年)2.6% 1250
西班牙3.36 2.2% 1791
澳大利亚 3.30 2.2% 940
中国近3.00(95年) 2% 2000
全球总计150.00 89625
(统计数字分别摘自《电影通讯》1995年第3期、1996年第1期)
简单的排行是:中国电影的年产量为世界第5位,电影院数是第7位,票房收入是第12位,制片投资是第14位。
更有实际意义的结论是:①我们生产着全世界6%的影片, 只分到全球市场中2%的收入, 假如在票房里再除去进口片占有的一多半份额,一个世界第一观众大国的民族电影所得是何等可怜!?②我们的制片投资总额是美国的157分之1,单片成本则为1:52,这点钱再分到几十家制片厂,生产力要发展奈何囊中羞涩,拿不出大本钱又哪里来竞争力?③12亿人口只有2000家电影院,一家平均要负担60万观众看电影;而美国一个影院老板须照顾的不到1万人,弹丸之地的香港, 人口跟大陆比是1:200,影院却达1:10,有199间。诚然,中国的众多农民也许不在电影院看电影,但近年的发行统计表明,仅有的票房收入也只是来自城市影院。一个萎缩的市场象一把双刃剑,制片和发行谁的手脚都不敢伸开。
还有一些上面没列出的数字必须补充:就美国电影而言,本土市场50多亿,海外还要赚回同样的数额,1994年好莱坞的国内外票房收入为104亿美元,占了全球影院发行总额的70%,平均每部影片卖了2470 万,即人民币2亿出头。 (而中国影片的出口除小部分港台出资片外几乎等于零。)这还不算,在目前好莱坞影片的收入总盘子中,影院票房只占到35%,大头是录象带、视盘、有线电视及其他附属产品;据最新的年度资料报表,1995年全美录象租片和销售收入为206亿美元, 几乎是影院收入的四倍。(我们的影院外销路还是一片待开垦的处女地)。合起来算,美国电影工业的经济规模对于我们可说是天文数字,财大才能气粗,在市场领域里,这话没有还价。
如此巨大的反差,不能不使人抛弃一厢情愿的幻想,离开经济规律搞点什么一蹴而就的花样。一百年来世界各国电影工业发展的成败得失就在眼前摆着,如果能从现在起,从宏观经济的视野,着手中国电影工业体系的重建,到下一个世纪出现转机或许可能。
课题(一个对于耐心的考验)
窘迫和困境,是体制不能适应产品的属性和产业的行规使然。在现行电影机制向工业化、市场化的转型中,以下课题也许是不可逾越的。
规模经营
无论制片与发行,现存机制里的经营实体规模都太小,近30家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制片厂、每个省市都有自己的发行公司,当年在计划经济模式下以行政体系建立的这套网络,早已不能适应电影现代化大工业生产和经营。经济效益让位于意识形态功利、行业利益屈从于地方区域利益、囿于生产力的低下明知不能偏要作为、大事做不了小事做不好,在改革三年来显现出种种滞后效应,更造成了生产力畏缩不前的恶性循环。以目前拍摄用摄影照明器材为例,在缺乏造血机制的情况下,各制片厂器材库存严重老化,又无力购置更新换代的先进设备,其结果是,一方面因陋就简地生产着大量制作粗糙的产品,而影象的粗劣已成为市场抵制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一批境外商家挟高档器材和周到服务乘虚而入,影圈内租用外商设备俏然成风,制片成本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拱手让“沙龙”、“先力”、“阿荣”赚走。
集约化规模经营是电影在大市场、高科技时代的必由之路。我们可以考虑的前景是:从制片业基地化(包括技术基地的专业化、创作人员的自由职业化、投资和策划的集约化)、发行业规模化(打破条块分割、收拢影院产权、推行独家代理和儿童片、艺术片等专业发行网)入手,当运作规模和财力周转达到一个相当水平后,向更完备的院线制过渡。
三年前,我作为一个制片企业的法人,曾在一次各厂领导的聚会上说:我们中的许多位也许应该以宣告自己厂子的破产来献给这次改革。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任何人也回避不了的。我现在仍持这个观点。
产供销一体化
电影规模化经营的成熟形式是制片发行一条龙的院线制。一个年产数十部影片的制片公司,在本公司所属的影院、音象制品、电视发行网络中全方位、分阶段地推出自己的产品,并通过海外子公司或跨国发行机构发生固定的供片关系,获得档期性的国际市场,再加上利用国内院线做好进口影片的发行,形成产供销一体化的电影商品—工业企业。这对目前国人的天方夜谭般的神话,却是国门外早已成就的现实。当前美国偌大一个全球市场,全部收入基本控制在10家左右的大公司中,如制片发行一体的华纳、迪斯尼(其发行公司叫布艾诺·维斯塔)、哥伦比亚/三星;制片公司联营发行的UIP (环球+派拉蒙+米高梅/联艺);超级多厅影院院线AMC等。无须否认独立制片与大公司的并存, 事实是独立制片的发行操作也与院线制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把目前我国的电影行业改造成院线制还为时尚早,但未必不能以这种合乎规律的前景来思考该做些什么。中国的足球和电影本来是一对难兄难弟,谁都敢骂、谁也不疼,三年前几乎同时开始的改革,而今足球的得宠如日中天,电影还是形影相吊,道理很简单,足球引进职业化和俱乐部制是一步到位,俱乐部从筹资建队到组织赛事,管了踢球的还管看球的,酷似我们的产供销一体。足球水平未必上去了许多,而从当年全国冠军赛都门可罗雀,到今天甲A联赛的套票提前售罄, 这不给人一份启迪?电影界也并非只在望洋兴叹,上海、北京、四川等地相继成立的发行—影院联合公司,上影的东方院线和童影厂并入中影公司,正在组建中的部分省市发行—制片联营体,已经开始了有意义的试验。以南洋、大洋、万科为代表的民营公司,也超越了独立制片小本经营的模式向规模化迈步;而负担最重的国营大中型制片厂尚无明显举措,行将成为改革的攻坚对象。
行业队伍重构
事在人为,市场竞争最终是人才的较量。多年大锅饭体制下的50万电影大军,在新的行业机制中何去何从?
已经在一些制片厂实行的准自由职业化,揭开了这场变革的序幕。文学部缩编成了策划办公室,导演要上片子得自己找钱, 演职员交够4个月合同就可自谋生路……这些过去看来不可思议的做法,正在悄悄改变着艺术家们的生存方式,也为从业队伍的重构准备了条件。
在可以预见的日程中,专业的电影策划人、制片人和经纪人是一大缺门;作为创作中心的导演,现有人数之多和素质的参差不齐必然在公平的竞争中得到优选;发行行业的宣传专门家、行销专门家和市场预测分析专门家乃至通晓国际市场的行家里手,将取代传统的行政型发行机关。企业内的人员结构和规模,应以企业的经济效益为唯一依据;而所有创作人员在成为自由职业者以后,作品的价值也就决定着他们的所得,至少,一腔热血来投身电影的民营公司老总们不大再会体尝上当的悲壮。
凡此种种,是不是一个梦?世上本没有现实,梦的人多了,也就成了现实。许多年前,一位伟人说过:多少事,从来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后来老百姓用自身的实践跟他缺席辩论说:中国的事,急是急不得的。现在的情况是,可以不许我做,但已经不能不许我明白。我想,电影的明天,将是对于我们耐心的考验。
1996.4—5.
标签:电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