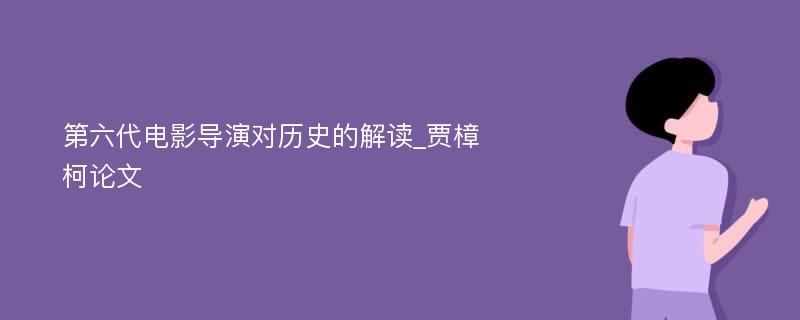
第六代电影导演对历史的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电影导演论文,第六代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97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359(2011)01-0136-05
第六代导演一般是指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90年代后开始执导电影的一批年轻的导演。代表人物及其作品有:张元《妈妈》、《北京杂种》,管虎《头发乱了》,何建军《邮差》,王小帅《冬春的日子》、《十七岁的单车》,王一持(王强)《新一年》,路学长《长大成人》,章明《巫山云雨》,娄烨《周末情人》、《苏州河》,张扬《爱情麻辣烫》、《洗澡》,贾樟柯《小武》、《站台》,王全安《月蚀》、《图雅的婚事》,宁浩《绿草地》等。
1993年《上海艺术家》第4期刊载了写作于1989年、署名为“北京电影学院‘八五’级导、摄、录、美、文全体毕业生”的文章:《中国电影的后“黄土地”现象——关于中国电影的一次谈话》。文章呼吁“中国电影需要一批新的电影制作者”,并对第五代将历史寓言化提出了质疑,认为它已成为“中国电影的重负”,“使中国人难以弄清究竟应如何拍电影”。这一檄文无疑成了“中国电影新生代在襁褓期的第一声呼号”,它“直言不讳地标示了一种自我‘命名’并自我文化定位的渴望”[1]26。1992年胡雪杨的《留守女士》上映时,他立刻宣布:“89届五个班的同学是中国电影的第六代工作者”[2]391-392,但是胡雪杨的这一告白并没有得到其他人的响应。张元就曾经明确表示:“我觉得电影还是比较个人的东西。我力求与上一代人不一样,也不与周围的人一样,像一点别人的东西就不再是你自己的。”[3]9后来的贾樟柯在谈到张元的《北京杂种》、王小帅的《冬春的日子》、章明的《巫山云雨》时也这样表示:“他们不再试图为一代人代言。其实谁也没有权力代表大多数人,你只有权力代表你自己,你也只能代表你自己。”[4]367
除了这种自我命名,第六代更多的是被他者命名。由于第六代大多采取一种体制外制片的方式以及他们对边缘题材的偏爱,他们的作品在西方的有意误读中再次变成了一幅“东方镜像”,满足了西方社会对中国当前社会的一种政治化解读。有论者曾尖刻地指出第六代影人“影片中反映的小人物的生命状态则是展现了‘东方’褪去了古代迷人的光辉而进入‘现代’成为一位‘灰姑娘’”[5]418。在西方大大小小的电影节上,素来喜欢横挑鼻子竖挑眼的西方评委一改往日的吝啬,慷慨地将一堆颂词倾倒在第六代导演头上。但是其中最多的还是认为这些作品像极了东欧巨变前的电影,这中间我们自然不难听出其言外之音。于是这些作品的命运就可想而知:在国外它们名声大噪,像张元的《北京杂种》不单在鹿特丹电影节、瑞士洛加诺电影节、新加坡国际电影节上不断获奖,甚至澳大利亚当代艺术博物馆就直接以“北京杂种”来命名;王小帅的《冬春的日子》不仅被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收藏,后来还被英国BBC评选为“电影诞生一百周年百部经典影片”。而在国内它们则寂寂无声,这些作品大部分观众也都无缘得见。一些导演甚至因此被取消了编导影片的资格。在两种意识形态的争斗中,第六代无可奈何地成为了“历史的人质”,于是“第六代”这个名字也因此被灌注了太多的意识形态的内容。在市场与意识形态的双重挤压下,第六代似乎走到了流产的边缘。但是经过十多年的磕磕碰碰,第六代的创作主体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作品无法离开中国这个生存的母体,于是在世纪末,第六代终于浮出了水面。
与第五代导演将历史寓言化、距离化不同,第六代更多的是将历史拉伸到当下现实生活。在这种对当下的冷静体察中,第六代将自己个人经验带入到电影中来。通过对边缘题材的开掘,对失语的弱势群体的关注以及对一些亚文化层面的进入,实现了个人历史记忆的银幕书写。“毕业后的他们,面临着电影业的凋零和商业消费主义观念的疯长,第六代突然发现,走出校门后他们的精英思想和精英身份已无处栖身。迷惘、焦虑、孤独、愤激、绝望的情绪开始长久地栖息于他们的精神世界之中,使他们不知不觉地偏离了主流文化,而以一种反叛、对抗的姿态出现。不再像第五代的精英们一样执著于历史和民族文化的书写。第六代抖落了历史的尘埃,疾速地奔跑在现实的刀锋之上。不再仰望巨人,而是另辟蹊径,以边缘对抗主流。这中间不乏有第六代导演渴望以标新立异的形式早日出人头地的目的,但更多的,它是一种个人情绪的宣泄。”[6]176
一、关注边缘人物
第六代对边缘题材的关注有其现实原因,黄式宪在《第六代:来自边缘的“潮汛”》一文中指出:“在历时性的坐标上,与以陈凯歌、张艺谋为主力的‘第五代’不同,这一拨新人踏上影坛之际,赶上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一方面是主流意识形态强化了宏观的控制力及其主导性、权威性;另一面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转型,大众娱乐潮兴起而精英文化衰落,正应了‘无可奈何花落去’那句话,第六代俨然成为拒绝、被隔离于秩序边缘的独行者。”[7]23-24正是这种现实的处境使得第六代导演在面对意识形态和市场的挤压以及第五代巨大辉煌的无形威逼时自然转向了边缘,他们试图通过对边缘的关注,“把一个特定的时代从连续统一的历史过程中爆破出来,把一个特定的人的生平事迹从一个时代中爆破出来,把一件特定的事情从他的整个生平事迹中爆破出来”[8]414。下面我们就几个典型文本作一番分析。
第六代导演王超的《安阳婴儿》关注的是弱势群体的生活。影片讲述的是古城安阳一个下岗工人在夜市面摊上收养了一个弃婴而引发的一系列故事。婴儿的襁褓中有一张字条,上面留有一个呼机号码,并说收养人可以与婴儿分享两百元的抚养费。工人因此结识了婴儿做妓女的母亲——冯艳丽。冯后来因为得罪了当地黑社会老大被赶出歌厅,工人与冯因此生活在了一起。白天工人在家门口摆了一个修车摊,照顾婴儿,冯则在家中继续着营生。一天,黑社会老大突然出现,他向妓女索要婴儿作为他家后代,因为他得了绝症。但冯却坚决不承认这一事实,争执之中,工人失手打死了老大,被判了死刑。冯也在一次“扫黄”活动中随手将婴儿交给了一个路人,自己也被遣送回原籍。在这里导演王超以一个影人的勇气直面了中国社会现实的一角:下岗工人、地下妓女、黑社会。它让我们窥视到了长久以来被我们漠视和阉割掉了的现实,是王超们寻找、发现了这些长期被主流社会、主流媒体和主导话语所覆盖、剪裁、压抑了的异质因素,让这些一直以来处于沉默地位的人物站出来诉说他们的遭遇。
而另一部电影《盲井》则通过对中国底层矿工生活的描绘,铺开了一幅血淋淋的画面。这是一部导演李杨用生命做赌注换回来的电影。《盲井》首先给我们的就是阴冷的一击:两个骗子唐朝阳、宋金明为了榨取矿主三万元的抚恤金,将一个盲流民工乔装成自己的亲属骗到矿井下,打死后伪装成矿难事故,向矿主索赔。三万元,一条人命。难怪霸道的矿主要说:“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当少年元凤鸣出现在这两个骗子的面前时,两个人的联盟出现了裂痕。从元凤鸣的身上,宋金明想到了自己读书的儿子。正是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让宋迟迟不肯下手,宋甚至招来小姐满足元的第一次。宋的举动招致了唐的杀机,最后两个人自相残杀在矿井下,凤鸣得到了六万元的抚恤金。影片中有对非法采矿、无视民工生命的揭露,有对公安人员上下其手的间接呈现,也有对色情泛滥召妓做爱的曝光,更有对人性裂变、堕落的直面。影片有如一道幽光,透出了地底下的一点黑暗,披露了社会的某些阴暗面。
对边缘的关注是第六代导演一个普遍特征,除以上几部影片外,还有张元的《妈妈》写患有幽闭症的儿童,《儿子》写长期酗酒的父亲,《东宫西宫》写一段同性恋情,《过年回家》写重刑犯人,《金星档案》写变性人,王小帅的《极度寒冷》写前卫的行为艺术家,《扁担·姑娘》写民工、歌厅小姐,贾樟柯的《小武》写小偷,《站台》写底层文工团员,张扬的《昨天》写吸毒人员等等。第六代正是通过对边缘人物的这种描写使长期以来处于中心的各种话语露出破绽,使主流意识形态的深层基础显出裂隙,扩张了影视文学的题材范围。
二、历史的个体化书写
中国第六代导演大多出生于上世纪60-70年代,基本上没有受过“文革”的影响,即使受到一些,也只是孩提时代的印象性记忆。中学时代至长大成人时期正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重大变革时期,旧体制、旧观念的消融与崩溃,各种新潮思想、艺术观念的发生与建立,伴随着他们成长历程,这就决定了他们习惯于站在怀疑和审视的立场上看待当前社会。他们遭遇了20世纪80-90年代经济转轨给社会带来的阵痛,同时也经历了电影从所谓神圣的艺术走入日常生活,最终还原为一种文化消费产品的无奈。贾樟柯在《贾樟柯谈〈站台〉》一文中曾说:“在中国,官方制作了大量的历史片,而在这些官方的制作中,历史作为官方的记忆被书写。我想从《站台》开始将个人的记忆书写于银幕,而记忆历史不再是官方的特权,作为一个普通知识分子,我坚信我们的文化中应该充满着民间记忆。”[4]370在《站台》里,贾樟柯通过对山西汾阳县城20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初底层文工团工作人员以及文工团本身的兴衰际遇的倾情观照,从个人独特的视角展示了一种演进在现实中的历史。
《站台》是一部半自传性的作品,也是一部有野心的作品。在这部作品里,贾樟柯完成了一个人十年的历史记忆。影片首先呈现的是文工团表演的节目《火车向着韶山跑》,这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典型的文艺节目,文工团在县城以及各乡镇轮回演出,它的表演也明显表现为对主流话语的宣传。随着80年代经济大潮的到来,文工团开始承包。一位牛高马大的汉子取代了文质彬彬的团长,剧团开始在周边地区走穴,但演唱的节目仍然是《我们的家乡》、《我的中国心》等代表主流意识话语的歌曲。但是当电视节目铺天盖地席卷而来时,剧团被迫更名为“深圳太空霹雳柔姿乐团”,成为一个闯荡江湖、挑逗欲望的卖艺群体。最终,剧团还是没有逃脱破产的命运,剧团的变迁清晰地显现出历史车轮碾过后的印痕。
美国影评家肯特·琼斯在《不合时宜》一文中曾说:“当世界电影沉溺于安伯逊式的悼念远去时光的哀婉史诗调子的时候,以贾樟柯和他姐姐的霹雳舞手经历为蓝本的《站台》却直接抓到了时间流逝的过程本身,并挟带着一种梦里不知花落去的感伤。与慢慢转型的中国社会相应,那些人物自身的变化有时也是如此渐进,以至于他们几乎是不知不觉地就告别了青春期的稚嫩,迎来了被生命消耗掉的世俗。”[9]4《站台》对时间的捕捉是通过一系列的背景元素来暗示的。最鲜明的就是背景音的设置。这些背景音时刻都弥漫在影片中,有军队操练的声音,有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报道,有国庆大阅兵邓小平的讲话,有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动员,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流行音乐的贯穿:从偷听宝岛台湾邓丽君的《美酒加咖啡》到《秘密》、《成吉思汗》、《站台》、《路灯下的小姑娘》,再到《是否》,再到《渴望》的主题曲《好人一生平安》,时光随着这些岁月的符号在悄悄流逝,80年代的历史也隐隐地浮现了出来。而且作为一种民间记忆,这些流行音乐表明并不是只有官方才有记忆历史的能力,民间同样也有记忆历史的可能。贾樟柯曾说:“1979年之前中国只有所谓革命的文艺,人民缺少娱乐,更没有个人生活,大家都生活在集体之中。到80年代,人们开始寻找自我的意义,流行文化开始产生,人们开始能享受世俗的生活。最早是来自港台的流行音乐,是流行音乐打破了革命文艺的专制,使文化出现了多元的状态,流行音乐在中国的产生意味着中国人挣脱了集体的束缚,获得了个人生活。”[4]370可以说,流行音乐作为80年代一个特殊的符号,它打开了一扇扇记忆的阀门,成功地在许多人心中复活了一个时代的记忆,开拓了另外一条描述生活的途径。
三、混杂多种叙事手法
第六代导演中关于个人成长的讨论重心,给业界获得了一次将电影创作和个人生命表达高度结合的契机,但是由于主流文化倾向和个人表达的呈现水平等多种原因,使得这些作品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其实早在贾樟柯之前,第六代另一位重量级人物姜文在他仅有的三部片子中就已经体现出了一种历史个体化书写的倾向,并运用了多种叙事手法。“文革”在许多中国人心中曾经是一段血泪斑斑的历史,在第五代仅有的三部直接书写“文革”的影片中,就充满了对“文革”的无情控诉。但在姜文的力作《阳光灿烂的日子》,影片却一扫“文革”天空的阴霾,呈现为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影片的序幕是一段旁白:“北京,变得这么快!20年的功夫它已经成为了一个现代化的城市,我几乎从中找不到任何记忆里的东西。事实上,这种变化已经破坏了我的记忆,使我分不清幻觉和真实。我的故事总是发生在夏天,炎热的气候使人们裸露得更多,也更难以掩饰心中的欲望。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太阳总是有空伴随着我,阳光充足,太亮,使我眼前一阵阵发黑……”这段旁白一开始就为影片奠定了一个个人式的叙述基调,它只不过是叙述人或者说是马小军的一段混淆了幻觉与真实的记忆。70年代初,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是生命中最黑暗的一段日子,可是对马小军和他的伙伴们来说却无疑是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大人们忙着“闹革命”,无暇他顾。孩子们到处撒野,无法无天。青春的野性无人修剪,疯长得一塌糊涂。逃学、打架、钓女孩子成了他们的主要功课。“文革”好像根本没有进入这群野孩子的生活,在影片中“文革”最多也就是作为一种叙境而存在的互文本的显影。这种对“文革”的记忆显然不同于第五代,也与大多数中国人心中的“文革”记忆存在出入。难怪戴锦华曾指出:“《阳光灿烂的日子》并非一部试图取悦于中国公众的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不时流露出对主流叙事、公众‘常识’及其‘共同梦’的冒犯。事实上,无保留地认同这部影片的,多为马小军或王朔的同代人,他们在其中找到了自己始终被权威叙事所遮没的岁月与记忆之痕,影片使他们远处置放与附着的‘想象的怀旧’之感获得了发露与表达。而此外,‘马小军’的长辈或晚辈们,却多少对影片感到不适。”[2]449学者王德胜就曾委婉地指责姜文将一群无法无天的少年冲动制作成“文化大革命史”,他认为:“在淡忘了自己的生存证明而洋溢着感性渴望的大众身体里,荷尔蒙的存储由于裸浴、撒尿的敞开性,并且随着马小军的视线不断上移到米兰健壮的腿、丰满的胸脯、细腻平坦的腰腹,一次又一次地发酵着、宣泄着,对人性痛苦的历史记忆一点点地被挤出视觉流畅的观影空间,电影使人们在‘阳光灿烂’下尽情实现了感觉的自由运动。”[10]433但姜文在建构自己关于“文革”的“小历史”时,并没有对它深信不疑,而是不断将其解构。如在马小军与刘忆苦的生日晚会上,马小军对米兰醋意大发,并用啤酒瓶猛戳刘忆苦。正当我们惊愕不已的时候,叙述人却哈哈大笑一声:“千万别相信这个……我不能发誓要人老老实实讲故事,可是说真话的愿望有多么强烈,受到的干扰就有多么大。我悲哀地发现,根本就无法还原真实,记忆总是被我的情感改头换面,并随时捉弄我,背叛我,把我搞得头脑混乱,真伪难辨。”其实姜文们又何尝不知道历史真实是无法还原的,他们建构出自己心中的“文革”史,并不是要取代其他人讲述的关于“文革”的历史,而只不过是要寻找自己曾经被权威叙事遮蔽的岁月痕迹,以置放自己那段无处附着的情感。在姜文执导的影片中,混杂了多种叙事手法,既有现实主义的,又有浪漫主义的,还有现代主义的,但都结合的比较完美,显示出他的编导才华。
《鬼子来了》同样充满了对历史的个人化书写,它是一部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抗战电影。姜文曾经表示拍这部电影是为了改变以往抗战电影可能会给人、尤其是日本人造成中国“全民皆兵”的印象。在这部电影里,姜文讲述了农民马大山被命运从平静的生活中一下子推向了悬崖:在他忙着繁衍下一代的时候,一个叫“我”的将装有一个日本鬼子和一个汉奸的麻袋扔进了他家的窗户,并叮嘱:“一个都不能少,少一样要你命。”此后,马大山陷入了巨大的困扰之中:怎样处置那两个人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难题。马大山和村人相信“以德报怨”,在养活了俘虏半年之久后,答应了日本人以粮食换自由的要求。结果换来的却是日本人的大屠杀。这部电影思索了中日两种文化的不同导致了民族悲剧,其价值观也出现了复杂的评判标准。在商业时代,姜文这种对战争的思索无疑是深刻而独到的。
就艺术营养而言,第六代导演所继承和借鉴的文学、美术、音乐、电影作品要比以前的电影工作者大大丰富。这是因为,中国的社会处在一个逐步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的思想文化处在与世界逐步的交流、融合过程中。而世界几千年的文化创造和思想潮流在二十几年的时间里涌入中国后,对中国影视界的冲击是十分巨大的。历史的个体化书写难免会存在片面和有失偏颇的地方,但是集体记忆却又不免掩盖、遮蔽一部分历史的真实存在,所以第六代导演对历史的个体化书写在质疑、颠覆由集体构建的官方历史的同时,无疑起到了丰富和补充官方历史的作用,对中国影视文学与影视艺术的发展也做出了自己独有的贡献。
标签:贾樟柯论文; 第六代导演论文; 阳光灿烂的日子论文; 中国电影导演论文; 电影节论文; 冬春的日子论文; 北京杂种论文; 剧情片论文; 伦理电影论文; 中国电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