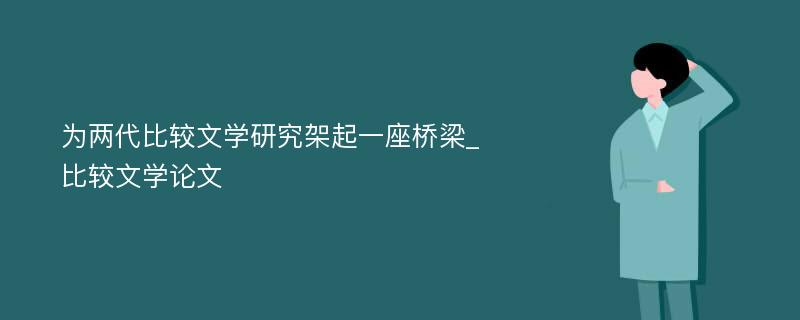
搭起两代比较文学研究之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比较文学论文,两代论文,搭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十几年,自比较文学研究在中国大陆复兴与重建以来,也曾经是风风火火,很有过声势的。但如今回头评估这一新兴学科近些年来的进展与成果,应该说,目前中国的比较文学,大体上还是处在一种教材多于研究性论著,专题性研究相对滞后于教学的状况。眼下比较文学研究的这样一种现况,其实既合情也合理,并不难理解。因为,当初中国文化和文学界刚刚从“十年动乱”的封闭和停滞状态中挣脱出来,并试图与连同以前“十七年”的偏狭与僵硬一起决裂的时候,人们特别是青年学子们发现了,在惯常和习见的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之外,还有所谓“比较文学”的学科和研究方法,因此,最急迫、最切实的需求,当然首先是普及性的知识介绍,以及尽可能地广泛地开展这方面的教学。于是,专为大学生们编写与出版的各类各样、格局纷呈的比较文学教材,在短短几年中层出不穷,本是顺理成章的事。如实而言,这些介绍比较文学框架知识的书或是比较文学的教材,在开拓比较文学研究的过程中,也确是有过开风气之先的功绩的。
不过,若是严格地推敲与区分,则应该明白,比较文学教材与研究性比较文学著作,虽然二者之间有着无庸置疑的内在关联,也可说本属于“一家人”,但它们还是有所不同,甚至是有相当差异的。这就好比是:岸上练好姿势,下河去游泳自然可能有好处,然而真正意义的游泳,毕竟应指下水后的行动,总不能只是对“旱鸭子”们的在岸上的讲解或是操练。同理,想深化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显示出这一研究的实绩,归根结底还得靠那些具体切入中外文学关系,生动而深刻地揭示出中国文学与其他国别文学之间的影响、流传、共通以及互动等等多种因缘的研究性论著。从这个角度来看,前些年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著作,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已经够多了。
自然,这种如俗话所说的“光说不练是假把式,又说又练才是真把式”的浅显道理,其实说来容易做起来也难。在近代以来世界各国文学与文化相互沟通和融合的历史情态之下而逐步成型的比较文学研究,其与传统古老的本国文学研究的根本区别,在于它要求研究者不只要有超越一国文化界限的广阔文化视野,还得有对本国和外国文学都具有相应的学养做基础,二者若缺一,便如同残疾了一条腿,是走不好比较文学这条新路的。明于此,也就不难于理解,为什么前些年,在文坛上争“说”比较文学,却尚少有人真正能“下水”在比较研究上实际“练”得像样子,本早已在这个领域里自成大家如钱钟书等先生,竟不愿承认自己是研究比较文学的。以后来者的妄测,这种被某些人视为有些“怪”的态度,其中既有作为历尽沧桑的老学者,对曾因执着于比较文学而几乎被置于死地的痛苦经历至今还难以释怀的激愤,而最主要的,大约还是担心那些比较文学的初学者,由于忽视这一新的文学研究路径的艰难,可能轻易变成名不符实却要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因此才故意置身这一当今“显学”之外。
与此相反,像钱钟书这样堪为后代风范的比较文学学者,对自己的学术前辈,却是相当敬重的。因为中国老一代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差不多都曾亲受过那些为开辟中国比较文学园地而荜路蓝缕的先驱们的教诲。他们深知,个人的学业并非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仅靠着天资聪颖与勤奋便可成就的。读《管锥篇》这样的皇皇巨著,人们既能看出钱钟书研究的独特性,但也不难从中发现那些与开创中国近代比较文学研究的前贤们形似,乃至一脉相通的地方。例如,曾被钱钟书尊为“恩师”的吴宓,就是对钱钟书的比较文学研究有较大影响的一位。翻看吴宓20年代在《清华周刊》上登载的众多《余生随笔》,会不由得让人们联想到后来钱钟书所热衷的那种札记短章式的研究体例。其实,还不只是在形式方面,更内在地说,钱钟书在《吴宓诗集》出版时所赠的《题词》中,说吴师“意欲兼”中外文化,并“以学人而为诗人,又通天人之故”等等,何尝不也是为自己后来的比较文学之路,树立起了一个学术指标呢。如果后人能够细致地条分缕析,认真回顾前一个时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之间的承传关系,也许当今的比较文学研究,再不至于有“说”与“练”脱节或错位,甚至竟自以为是闯入了一块从来无人下锄和播种的处女地。只有计真看清前人已走过的路径,才能懂得自己究竟应该从哪一个阶梯上起步。那样,就既可以在比较文学论坛上少见些数典忘祖的枉言,也可以少做些前辈已着过力的无用功。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领域这个早该有人着手的课题,如今果真有了起步和开端。由大陆的杨义与陈圣生两位学者合著、最近在台湾出版的《中国比较文学批评史纲》一书,便是这样一本回顾中国近代以来比较文学发展脉络,亟应受当今比较文学研究者重视的著作。虽然如书名所示,这本新著着眼的“中国比较文学批评”,与一般讲的“比较文学研究”,还是有些差异,但这样的切入点,却正是认识近代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历程的一个很好的视角。因为从比较文学批评的角度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历程做“百年回眸”,这既符合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生成与发展的实际情况,也是一条颇有助于新一代研究者突出中国比较文学特色的有益思路。
如两位作者在书中所说,所谓“中国批评史”,就是指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的结合点,意即:
它著重考察的是批评形态的比较文学,以及跨国度、跨文化比较的文学批评。它的基本思路,是认为比较文学不应该是一门玄学,一门不顾丰富多彩的文学批评传统的玄学;而应该是一门实学,一门具有世界性开阔视野和比较思维的实学。它以大量的原始资料为立论根据,梳理了20世纪初的梁启超、王国维,到五四时期的鲁迅、胡适、周作人、梁实秋、茅盾、郭沫若、吴宓、朱自清,以及三四十年代的梁宗岱、朱光潜、李健吾、李广田、钱钟书,直至八九十年代的一批翻译家、比较诗学研究者,换言之,梳理了几乎整个20世纪比较文学批评的历史行程、思维脉络和方法论的变化,前以导言明其宗旨,后以研究类型之传播学、主题学、比较诗学述其关键。对于比较文学学者和批评家的典型分析中,著重考察其显在或潜在的中外古今文学比较的纵横坐标系统,其独具慧心慧眼的学术发现和多种多样的方法论探索。在类型研究中,则著重分析文化传播中的过滤、变形、转化、融合和创制,以呼应多元性总体文学的旨趣。
中国近代以来的比较文学研究,基本是以批评的形态起步的。这乃由中国传统文学向近现代文学转变的时代潮流所左右。当长期以源远流长的民族传统自豪的中国文人,在近代接触到和面对着蓬勃多姿的外来文化的时候,他们最迫切与最热衷的,首先是要以从前所知、所感与所见甚少的欧美文学风格,来对照与检点本国文学的得失利弊,以扬长避短,来求得民族文化传统焕发青春,起死回生。在那样的情势下,超脱地输入或是专注于西方比较文学的抽象理论,势必显得太空洞和浮泛。这种务实性的文学批评,也许不过只是迈入比较文学研究宏大堂奥的一个门坎。然而,前几代学贯中西的中国学者们的这些批评实践,实在是于今有志于比较文学事业的后人不可缺少的“前车之鉴”。没有这种铺垫,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历史毫无所知,便无从谈起所谓“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创立。这就如《中国比较文学批评史纲》的合著者所说的:“中国比较文学批评史之所以值得研究,在于它以丰富的批评实践,提供了切入整体研究的不少新视点,为多重多向的张力系统提供一些切实的思想资料。比较文学之中国学派之所以值得提倡,在于它携带著数千年的中国文学和文化智慧,足以在实质意义和巨大幅度上校正固有比较文学研究的西方视野。”
基于中国近代以来比较文学学者们这种以小见大、以实带虚的特点,也是得益于《史纲》合著者们的别具匠心,该书中确实有不少经过点拨,真能使后来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在前人遗产中“沙里淘金”,时时有豁然开朗的论述。像书里在谈王国维以《红楼梦评论》开中国近代比较文学研究的先河,认为他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的中国文学材料互相参证,这种中西文学思想和艺术经验双向的斡旋与化合的特点,其结果可在新认识高度上解说和评价中国的文学现象。如此名为“批评”,实质上毫不逊于“研究”之价值的中国早期比较文学方式,确实是中国比较文学曾有过的独特之处,后人是不该轻易忘记的。还有,许多人已经觉察到的钱钟书与吴宓的承继关系,《史纲》也深入到了少有人论及的二人都着意开发文字的“声”与“义”为本体的诗论,并在此基本结构上附著“神韵”新标志的深层问题,也称得上是高屋建瓴的阐发。这些例子表明,中国比较文学批评史这个“富矿”,是非常值得后人开掘的。而《中国比较文学批评史纲》的合著者,则是有胆有识,实际推动当今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深化与发展的有心人。
另外值得称道的是,合著者们的这种尝试与努力,得到了台湾学术界和出版界的全力支持,使这种以前少见的中国比较文学批评史论著得以问世。台湾出版商肯印这种书,大约是无大利可赚的,其动机只能以对中国人文学术的关心与执着来解释。其中两位作者的文字,还分别以两种字体排印,使读者可以分辨得出他们见解的相同与不同。论著中这种别具一格的“比较”特色,也是台湾出版界带给内地的新意之一。这都可视为海峡两岸文化人士共同推动中国融入世界文化潮流的创新与努力。即使这本书还有诸多不成熟的地方,比如其中对当今比较文学领域新人新作的筛选和讨论,尚有些欠妥之处等等,我们也仍然应该为这本难得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著作的面世感到欣喜。
但愿这是中国比较文学兴旺的一个好兆头。
(杨义、陈圣生著《中国比较文学批评史纲》,业强出版社,1998年6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