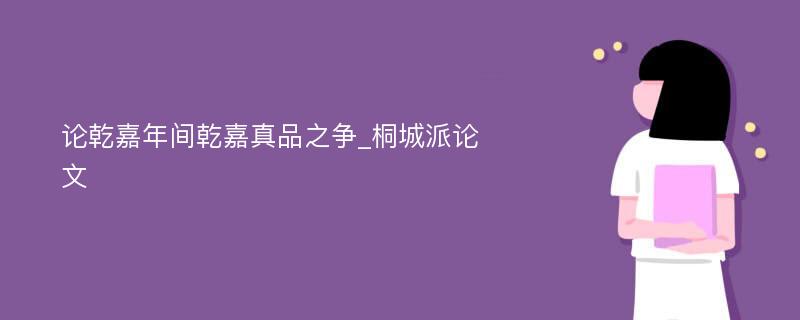
论乾嘉年间的文章正宗之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争论文,正宗论文,年间论文,文章论文,论乾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代诗坛有神韵派、格调派、性灵派、肌理派之争,清代词坛有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之争,与之对应,清代文章领域的汉学派、史学派、桐城派、骈文派之争亦颇为壮观。乾嘉年间,戴震、章学诚、姚鼐、阮元等纷起为某一类“文”争正宗地位,一方面表明对文章美感特征的界定尚存争议,另一方面也是特定作者群不同文化宗旨的体现。
乾嘉汉学的极盛标志着一个重知识而轻思想的时代。这样一种时代风气,既与政治生活氛围有关,也与思想文化自身发展的逻辑吻合。在偏重思想的16世纪,已经出现了博学的杨慎。17世纪的顾炎武等,虽为经学家,却同时以博学见长。但是,应该指出,以知识吞并思想,毕竟是乾嘉时期的时代特征。文章领域的汉学派、诗坛的肌理派、小说创作中的“以小说见才学”等,俱见祈向所在。纪昀和他主编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常以调侃的语气提到明人的理论兴趣,此中意味亦颇为深长。乾嘉汉学包括两大流派,一曰吴派,以惠栋为开山祖师;一曰皖派,以戴震为开山祖师。两派的治学风格有所不同,但都注重名物、制度的训释,其治学方法与汉代的郑玄等经学家相同而与宋代注重体系建构的朱熹等理学家迥异。根据这一特点,人们顺理成章地称这些擅长考据的学者为汉学派。严格地说,汉学只是一个学术流派,不应与文学世界瓜葛太深。但是,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其一,中国古代文章范围的划分一向存在争议,不仅骈文作家、古文作家在谁为主导一事上相持不下,哲学家、考据学者也时以文章作者自居。其二,当汉学派已毫无疑义地称雄于学界后,他们的雄心进一步膨胀。他们不满足于以知识吞并思想,还热心于以知识吞并辞章。从这样的角度看,汉学派试图在文章领域争霸是乾嘉年间考据学臻于鼎盛时一桩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戴震《与方希原书》可视为汉学派的文章宣言:
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义理,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注:戴震:《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89页。)
南宋朱熹、吕祖谦合撰之《近思录》卷二引程颐语云:“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学道,舍儒者之学不可。”“训诂之学”属于“事于制数”的考证,“儒者之学”即“事于义理”,“文章之学”即“事于文章”。戴震对“古今学问”的分类略同于程颐,但褒贬显然不同。程颐视“儒者之学”为最高等级,而戴震虽然承认义理(思想)是“考核、文章二者之源”(见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却又强调:探求义理的可靠途径是实证,“巨细毕究,本末兼察”(《与姚孝廉姬传书》);并批评理学家忽视训诂,凿空立论,“是犹渡江河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见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注:戴震:《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55页。)。至于斥“事于文章”的古文为“等而末者”,则因为在他看来古文家对“义理”的阐发不及宋儒,对“制数”的考订不及汉儒,“大本”不立,不值得推重。他是将学术性放在第一位的。钱大昕、段玉裁更明确地提出以文献学为学问之“本”,即以考据为文章本体。如段玉裁《戴东原集序》说:
玉裁窃以谓义理、文章未有不由考核而得者……先生之治经,凡故训、音声、算数、天文、地理、制度、名物,人事之善恶是非以及阴阳气化、道德性命,莫不究乎其实。盖由考核以通乎性与天道。既通乎性与天道矣,而考核益精,文章益盛,用则施政利民,舍则垂世立教而无弊。浅者乃求先生于一名一物一字一句之间,惑矣。(注:戴震:《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52页。)
段玉裁所阐发的是一种治学理论,也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文章理论。“义理、文章未有不由考核而得者”,其实就是以考据为文章之“本”。事实上,以考据为门径,难以臻于“文章益盛”之境,甚至于文章有碍(注:晚清何绍基《与汪菊士论诗》(《东洲草堂文抄》卷五)指出:“考据之学,往往于文笔有妨,因不从道理识见上用心,而徒务钩稽琐碎,索前人瘢垢,用心既隘且刻,则圣贤真意不出,自家灵光亦闭矣。故读经不可不考据,而门径宜自审处。”(据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7页)。刘师培《论近世文学之变迁》在指出语录之作不算文章的同时,也指出考据之作亦非文章:“至宋儒立‘义理’之名,然后以语录为文,而词多鄙倍……至近儒立‘考据’之名,然后以注疏为文,而文无性灵。夫以语录为文,可宣于口,而不可笔之于书,以其多方言俚语也;以注疏为文,可笔于书,而不可宣之于口,以其无抗堕抑扬也。综此二派,咸不可目之为文……乃近世以来,学派有二:一曰宋学,一曰汉学。治宋学者,从语录入门;治汉学者,以注疏入门。由是以语录为文,以注疏为文,及其编辑文集也,则义理考订之作,均列入集部之中,目之为文。学者互相因袭,以为文能如是,是亦已足,不复措意于文词,由是学日进而文日退……故近世之学人,其对于词章也,所持之说有二:一曰鄙词章为小道,视为雕虫小技,薄而不为;一曰以考证有妨于词章,为学日益,则为文日损(如袁枚之箴孙星衍是)。是文学之衰,不仅于科举之业也,且由于实学之昌明。”(刘师培《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0-272页。)何绍基、刘师培的断语,并未厚诬汉学派诸人。)。由于汉学家注重考据,他们对汉儒的文章格外推崇,而对六朝骈文和唐宋八大家的古文并不看重,其结果,如刘师培《论近世文学之变迁》所说,汉学家所造成的后果是增强文章的学术性,而减弱了文章的文学意味。汉学派目考据文为文章正宗,试图以考据学家主盟“文”坛,这种妄自尊大的盟主意识乃特殊时代的学术氛围使然。
与汉学派抗争的一支是史学派,代表人物为章学诚。乾嘉考据学风盛行,能不受其牢笼者极少。据我所知,有两位格外值得表彰。一位是性灵诗人袁枚,另一位便是浙东学派的史学大师章学诚。时人多热心于“考订名物”、“小学音画”,章学诚则独立于风气之外,大量撰写综合性的史论,必欲自成一家言。何以要为举世所不为呢?无非因为他在综合性的史论方面确有心得。章学诚注重的是创见而非博学。
乾嘉时期的理学家、汉学家与古文家之争,其分歧一目了然。理学家以义理为中心,汉学家以考据为中心,古文家以辞章为中心。其中汉学家声势最大。他们的策略是倚仗儒家经典。汉学家以儒家经典为训释对象,所以又是经学家。所谓由训诂而求义理,即将汉学与经学融为一体。章学诚锋芒所向,直指经学家或汉学家。其核心论点即“六经皆史”,意在否定六经对时代和社会具体处境的超越性,否定六经的特殊经典地位。“六经皆史”的命题,并非章学诚首次提出,明代的王阳明(《传习录》上)、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一四四)、李贽(《焚书》卷五《经史相为表里篇》)等已有类似的说法。但章学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提这一命题,一方面使之更具系统性,另一方面也赋予了它有着特殊针对性的理论蕴涵。简洁地说,章学诚旨在强调具体的“事”比抽象的“理”更值得关注。“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文史通义》内篇一《易教》上)(注: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页。),“夫子之述《六经》,皆取先王典章,未尝离事而著理”(《文史通义》内第一《经解》中)(注: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02页。),将六经视为历史著作,这就使汉学家(经学家)失去了夸口的资本,“由考核以通乎性与天道”的标榜不再具有说服力和震慑读者的效果。
章学诚在与汉学派对垒的同时也和桐城派存在巨大分歧。古文本有议论和叙事二体,但古文家对叙事几乎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半回避的态度。何以回避呢?大约是因为修史向来被认为非文人之能事,同时,小传统中的叙事文学如传奇小说的兴盛又使叙事之作易与小说结下因缘,所以,正宗古文家往往偏重义理而较为忽略“事”,韩愈视古文为载道之文,姚鼐在古文三要素中给了“义理”一席之地而未给“事”安排位置,都足以见出这一症结。与这种轻“事”而重“理”的倾向形成对照,章学诚倡论“六经皆史”,重“事”而轻“理”,认定史家之文才是古文正宗。他指出:
古文必推叙事,叙事实出史学。其源本于《春秋》“比事属辞”,《左》、《史》、班、陈,家学渊源,甚于汉廷经师之授受……而昌黎之于史学,实无所解,即其叙事之文,亦出辞章之善,而非有“比事属辞”、“心知其意”之遗法也。其列叙古人,若屈、孟、马、扬之流,直以太史百三十篇与相如、扬雄辞赋同观,以至规矩方圆如孟坚,卓识别裁如承祚,而不屑一顾盼焉,安在可以言史学哉……然则推《春秋》“比事属辞”之教,虽谓古文由昌黎而衰,未为不可。(《上朱大司马论文》)(注:《章氏遗书》补遗,文物出版社1982年覆吴兴嘉业堂刊本。)
左丘明古文之祖也,司马因之而极其变,班、陈以降,真古文辞之大宗。至六朝,古文中断。韩子文起八代之衰,而古文失传亦始韩子。盖韩子之学宗经而不宗史,经之流变必入于史,又韩子之所未喻也。近世文宗八家,以为正轨,而八家莫不步趋韩子。虽欧阳手修《唐书》与《五代史》,其实不脱学究《春秋》与《文选》史论习气,而于《春秋》马、班诸家相传所谓比事属辞宗旨,则概未有闻也。八家且然,况他人远不八家若乎!(《与汪龙庄书》)(注:《章氏遗书》卷九。)
中国古代本有“文人不能修史”的说法。唐刘知几在《史通》卷九《核才》中举例说:“以张衡之文,而不闲于史;以陈寿之史,而不习于文。其有赋述《两都》、诗裁《八咏》而能编次汉册,勒成宋典,若斯人者,其流几何?”文人修史,往往在史传中逞弄文人习气,“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史通》卷六《叙事》下),造成文不像文、史不像史的弊端。表面看来,刘知几“文人不能修史”的命题与章学诚一致,但实际上大有区别。刘知几所说的“文人”,主要是骈文作者;章学诚所批评的“八家”,则是通常意义上的古文作者。骈文作者修史,缺点是“轻事雕彩”、“体兼赋颂”,追求一种辞藻宏丽、情灵摇荡的效果。“八家”之作则名为古文,实短于叙事;即使偶有叙事之作,也不免沾染辞章习气,并非“本于《春秋》”的古文。章学诚还指出,就义理、学问、文辞三者的融合而言,史家也胜过韩、柳一脉的古文家:“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孟子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义则夫子自谓窃取之矣。’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三者固各有所近也,其中固有似之而非者也。”(《文史通义》内第三《史德》)(注: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19页。)提倡以史为宗,主张用史来规范古文的写作,实际上是将唐宋八大家所忽视的叙事文抬到比议论文更高的位置上。重“事”而轻“义理”,或者更准确地说,希望经由对事实的描述揭示出“义理”,这是史学派的基本特征。章学诚以此为依据建立了新的古文统系:上溯《左》、《史》、班、陈,而将韩、柳搁到一边(注:明代的何景明曾在《与李空同论诗书》中说:“夫文靡于隋,韩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于韩;诗弱于陶,谢力振之,然古诗之法,亦亡于谢。”此论颇遭非议,而站在章学诚的立场看,何氏之说堪称真知灼见。因为,韩愈“宗经而不宗史”,于史学实无所解,而“古文必推叙事,叙事实出史学”,韩愈古文算不得正宗古文。史学派的古文统系大别于桐城派。又,在章学诚之前,方苞的朋友万斯同已有古文以史学为中心之论。他曾对方苞说:“史之难为久矣,非事信而言文,其传不显……子诚欲以古文为事,则愿一意于斯。”(见方苞《万季野墓表》,《方苞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33页。)章学诚之后,晚清黎庶昌亦在“文以载道”的旗帜下高倡马、班之文,与之遥相呼应。其《答赵仲莹书》(《拙尊园丛稿》卷二)云:“惟独文章一事,余意以为尚留未尽之境以待后人。而因文见道之说,仆尤笃信不惑。何也?盖文以载道,周子固尝言之也。古之善为文,莫盛于司马迁、班固、韩愈、欧阳修。韩、欧之文,世颇以道归之矣,而马、班则未也。独苏明允称之曰:迁、固虽以辞胜,然亦兼道与法而有之,时得仲尼遗意焉。望溪方氏推尊子长,曾文正公则兼及班氏,谓其经世之典、六义之旨、文字之源、幽明之情状粲然大备,是岂逐世俗为毁誉哉!故仆近者妄有《古文辞类纂》之续,于《史》、《汉》所选独多,欲以踵姚氏义法后。阁下苟无意于文则已,苟有志于此,异日取吾书而读之,以求合乎桐城之法与宋儒者不悖之言,其于因文见道之说,将深造而有得也。夫道与文并至者,孔、孟是也,下此见道有浅深,言道有醇驳,而皆由文字悟入,则自汉、唐以来无或异也。”黎庶昌折中理学派和史学派的古文理论,欲纳入桐城派的框架中,表明桐城派理论本身具有折中性质,至少潜在地具有折中性质。)。
与汉学派、史学派鼎立的是桐城派。其古文统系脉络清晰:唐代的韩、柳,宋代的欧、苏、王、曾,明代的唐宋派。桐城派以辞章为依凭(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近世之学术》第二节《乾嘉间》(《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一册)说:“其时与惠戴学树敌者曰桐城派。方东树著《汉学商兑》,抨击不遗余力。其文辞斐然,论锋敏锐,所攻者间亦中症结。虽然,汉学固可议,顾桐城一派,非能议汉学之人,其学亦非惠戴敌,故往而辄败也。桐城派钜子,曰方望溪、姚姬传。方、姚固文人,而自谓尸程、朱之传,其实所自得者至浅薄。姬传与东原论学数抵牾,故经学家与文学家始交恶云。自宋欧阳庐陵有因文见道之说,厥后文士,往往自托于道学。平心论之,惠、戴之学,与方、姚之文,等无用也。而百年以往,国学史上之位置,方、姚视惠、戴何如哉。”在梁启超看来,桐城派在“义理”方面的造诣不高,方、姚只是以“辞章”见长的“文人”。),自会将“文人之能事”摆在首位。它的第一任盟主方苞曾以“义法”论文。从顺序来看,方苞置“义”于“法”之前,似乎更重作品的义理(注:刘熙载即将“义”理解为“理”,其《艺概》卷一《文概》云:“长于理则言有物,长于法则言有序。”“文之尚理法者,不大胜亦不大败;尚才气者,非大胜则大败。”在刘熙载的表述中,“理”所取代的正是“义”。(刘熙载《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41页。)),其实,他心里看重的还是“法”,还是文体对写作的规定和限制。徐珂《散体文家之分派》云:“苞尝与宸英论行身祈向,曰:‘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故其论文严于义法。今约举其大旨如下:一、非阐道翼教,有关人伦风化,不苟作。二、凡所涉笔,皆有六籍之精华。三、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注:徐珂编《清稗类钞选》(文学、艺术、戏剧、音乐),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第35页。)三点“大旨”中,第一点属于“义”,但视为“法”也未尝不可,因为这仍属制约古文题材选择的体裁规范。二、三两点更只能作为“法”来理解。
桐城派的第二任盟主刘大櫆将方苞潜在的重“法”意图明确地表达了出来。他在《论文偶记》中以“神为主”取代了“理为主”的习惯说法(注:《论文偶记》云:“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见刘大櫆《论文偶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页。)。“理为主”,那是理学派的基本思想;“神为主”才真是桐城派的心得所在,且已偏于对一种韵味的感受,显然与诗论相通。桐城派以前,韵味论大体属于诗学的范畴,何以将之纳入古文理论中来?我想这是受到理学派和史学派挤压的缘故。当“义理”和“事”这两个古文要素被理学派、史学派攫取之后,留给桐城派的便只有辞章了。以辞章为焦点,他论“神”、“气”、“势”,格外注重音节。按照通常的看法,语言有两种基本类型,一是讲述性语言,一是歌唱性语言。讲述性语言旨在表意,故较为朴实、明了,发音平缓,声调变化幅度不大;歌唱性语言旨在抒情,故注重声音的高下抑扬、轻重缓急、顿挫起伏,音调变化幅度大,同时以规则性的旋律一以贯之。身为古文作者的刘大櫆,他本应青睐讲述性语言,何以会对歌唱性语言一往情深呢?这与桐城派自方苞开始的注重“情辞”的传统有关。“情辞”是与音乐性密不可分的(注: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1768-1834)的意见可以参看。他把语言的功能分为两种:音乐性的声音和逻辑性的意义。诗歌首先是声音,是“谐音的总体”,施莱尔马赫设想这种谐音类似音乐,是表现自我认识之流,“存在的内部多变性”,“内在心境的主观性”。同时诗歌又利用语言的意义,因为它迫使通常表现共相的语言代表殊相。诗人唤起一种殊相化的,全然单整的、明确的意象。诗歌因而是双重性的:它是造型性的,体现“形象的客观性”,又是音乐性的,体现内在心境。德国早期浪漫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弗·威·约·谢林(1775-1854)的体裁理论也值得重视。他认为,在抒情诗中,有限——即主体,诗人的自我——占了上风。抒情诗是主观性最强、个性化最强的体裁,最有特殊性,在谢林的分类法里最接近于音乐,音乐也是表现主观感受的。比较而言,柯勒律治和雪莱的看法与刘大櫆的见解更为接近。雪莱对节奏在诗里的作用抱有强烈感受:和柯勒律治一样,他试图缩小韵律性的诗歌与节奏性的富于想象的散文之间的界限。柏拉图和培根依他看都是诗人,不仅是从诗人、哲人兼于一身这个广义来说,而且是从他们节奏性的语言和意象的角度来看。他的语言特性感极强,因此他否定译诗的可能性(参见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二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56-157页,第370页,第96-97页)。)。故刘大櫆此论一出,得到桐城派后学的纷纷赞同(注:曾国藩:《复吴南屏》(《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五):“姚惜抱氏谓诗文宜从声音证入,尝有取于大历及明七子之风。”明确揭示出桐城派古文理论与诗学的渊源关系。钱钟书《管锥编》第四册全宋文卷一五“文笔皆有声律”条则云:“散文虽不押韵脚,亦自有宫商清浊;后世论文愈精,遂注意及之,桐城家言所标‘因声求气’者是,张裕钊《濂亭文集》卷四《答吴至甫书》阐说颇详。刘大櫆《海峰文集》卷一《论文偶记》:‘音节者,神气之迹也,字句之矩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姚范《援鹑堂笔记》卷四四:‘朱子云“韩昌黎、苏明允作文,敝一生之精力,皆从古人声响处学”,此真知文之深者。(《朱文公集》卷七四《沧州精舍谕学者》:‘老苏但为学古人说话声响,极为细事,乃肯用功如此’);吴汝纶《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卷一《答张廉卿》:‘承示姚氏论文,未能究极声音之道……近世作者如方姚之徒,可谓能矣,顾诵之不能成声’;均指散文之音节,即别于‘文韵’之‘笔韵’矣。古罗马文家谓‘言词中隐伏歌调’,善于体会,亦言散文不废声音之道也。”(《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78页。)钱氏以倡“破体”著称,故并不认为“声音之道”乃诗之专利。但毋庸置疑,桐城派注重“声音之道”的特征是明显的。而在我们看来,这一特征是受到诗学影响的结果。)。
桐城派的第三任盟主姚鼐在理论建构方面以提倡义理、考据、辞章的统一著称。强调义理,意在防御理学派;强调考证,意在防御汉学派;而强调辞章,实为桐城派的看家法宝。姚鼐指斥理学派之作“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考证派之作“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述庵文钞序》)(注:姚鼐:《惜抱轩全集》,广智书局1959年版,第46页。),正是以桐城派之长形理学派、考证派之短。“文章”(或说“辞章”)是桐城派的关注焦点。
方苞论“义法”,目光所注实在“情辞”;刘大櫆论“文法”,目光所注实在“神”、“气”;姚鼐论辞章,目光注于何处?概括地说,姚鼐的关注重心是意境和风格。
姚鼐所崇尚的意境是“风韵疏淡”。这显然受到其老师刘大櫆的影响。而刘、姚二氏又都取资于诗中的神韵说。故方宗诚《桐城文录序》云:“惜抱先生文,以神韵为宗,虽受文法于海峰、南青,而独有心得。”(注:舒芜等编《中国近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96页。)朱庭珍《筱园诗话》卷四也说:“近来古文,天下盛宗桐城一派。其持法最严,工于修饰字句,以清雅简净为主。大旨不外乎神韵之说,亦如王阮翁论诗,专主神韵,宗王、孟、韦、柳之意也。”(注: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2页。还可参看施补华《复陈子余论韩文书》(《泽雅堂文集》卷二):“桐城自方灵皋以下皆知推重退之,然桐城一派实导源于欧、曾,托之退之以取重耳,其笔其气其词固不类也。魏冰叔有言:韩公是山分文字,峰峦峻峭,欧公是水分文字,波澜动宕。为持论最平。”韩愈古文风格雄健,欧、曾之作却以风神淡远见长,与神韵相通。)而从具体的操作来看,“风韵疏淡”的特征之一是“每写一二无关系之事”(注:关于“有关系”与“无关系”的内涵,参见拙著《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3页。)。方苞在理论上拘于“有关系”之说,在创作实践上便不免矜持一些;姚鼐则在理论和实践上同时摆脱了“有关系”之说的束缚,高揭“无关系”之帜,并以神韵说来消释古文作者对时政的热情。他的古文成就较高颇得益于此。
姚鼐标举风格,首先是针对乾嘉时期偏重考据的风尚而言的。考据家的通病是无识,对风格缺少领悟能力即其症候之一。故姚鼐《尚书辨伪序》虽肯定考证以确凿的证据说话,“利以应敌,使护之者若不能出一辞”,但又强调,“然使学者意会神得,觉犁然当乎人心者,反更在义理、文章之事也”(注:姚鼐:《惜抱轩全集》,广智书局1959年版,第193页。)。风格在一定的场合比证据更重要。
无论是风格论还是意境论,都属于审美范畴。姚鼐以风格和意境为支柱来构建其古文理论体系,表明他刻意与理学派和考据派划清界限,以凸显其“文人”风范。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主要包括抒情诗和一部分以抒情写景为主旨的骈文,据萧绎《金楼子·立言》的描述,其特征有三:一是“流连哀思”、“情灵摇荡”,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和强烈的感染力;二是“绮縠纷披”,讲求藻饰、辞采;三是“宫徵靡曼,唇吻遒会”,即声律和谐。比照魏晋南北朝对纯文学(“文”)美感特征的这种认识,我们发现,桐城派(尤其是刘大櫆、姚鼐)的宗旨是视古文为纯文学,所以他们讲求“情辞”、音节、神韵、风格,即不仅与学术著作(指理学派、考据派的作品)划清界限,而且与杂文学(如史学派的作品)划清界限。姚鼐钟情于“文人”风范,实即以纯文学作家自期和自许。
然而,正是在古文有无资格算“文”(纯文学)的问题上,桐城派遇到了来自骈文派的强有力挑战。
自从唐代的韩、柳确立古文在文章领域的正宗地位以来,骈文一直处于弱势状态。随着清代朴学的兴起,知识阶层的古典文化素养日渐提高,以驱遣典实、藻采绚烂为特征的骈文获得了开阔的发展空间。陈维崧、毛奇龄、胡天游、汪中、邵齐焘、孔广森、洪亮吉、孙星衍、彭兆荪等皆为清代的骈文名家。在这种背景下,骈文家欲与古文家争纯文学正宗,便是一桩自然不过的事(注:蒋伯潜、蒋祖怡《骈文与散文》说:“文体之中,有‘文’的本义的,只有后世的骈文,它有着排比藻饰的字句、叶协宫商的声调,而散文虽以单行的文辞,有随意发挥的自由,但它也着重于声调的抑扬和文字的情采的,不过不及骈文那么专重罢了。”(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骈文在六朝时已是正宗的纯文学,清代骈文家与古文家争正宗,站在他们自己的角度看,乃是名正言顺的事。)。
早在清初,陈维崧即在《诗选序》中为骈文家受歧视鸣不平。在他提到的几部名著中,《庄子》是子书的代表,《离骚》是抒情诗的代表,《史记》、《汉书》是史书的代表。陈维崧以庾信的骈文名作与之并列,表明了将《哀江南赋》等视为经典的态度。他没有贬抑古文,但如此推重骈文已足以显示出骈文家的自信。不久,毛际可作《陈其年文集序》,热情洋溢地称道陈维崧的骈文说:“言情则歌泣忽生,叙事则本末皆见;至于路尽思穷,忽开一境,如凿山,如坠壑,如惊兕乍起,鸷鸟复击,而神龙夭矫于雨雹交集之中。”二十四年后,毛际可又作《汪蓉洲骈体序》,致力于把握骈文的基本美感特征,即“遥情远致”,“言情则歌泣忽生”;神秀骨清,而又灏气盎然。这样的描述,都是暗指着古文的不足说的,虽然并未明确向古文叫板。袁枚《胡稚威骈体文序》(《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一)则公然将骈文和古文放在一起比较:
散行可蹈空,而骈文必征典;骈文废则悦学者少,为文者多,文乃日敝。(注:袁枚:《袁枚全集》第二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98页。)
“散行”指古文。写骈文必须铺排典实,没有“满腔书卷”便不能胜任,这有助于克服空疏不学、陈陈相因之弊。袁枚傲然宣称,这是骈文胜过古文之处。其《答友人论文第二书》(《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九)驳“散文多适用,骈体多无用,《文选》不足学”之论(注:袁枚:《袁枚全集》第二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22页。),辞气酣畅淋漓。古文家所赖以自高身价的理由是古文乃“载道”之文,“有关系”,“有用”,而袁枚一针见血地指出:一、“文之佳恶,实不系乎有用与无用也。”二、所谓“明道”或“文以载道”云云,“直是文章家习气如此”,不过是为了“挟持以占地步”而已。这样说来,以藻采面向读者的骈文是胜过名为“明道”而实陈陈相因的古文的。袁枚之外,李兆洛编《骈体文抄》,意在取代桐城派的《古文辞类纂》;其《骈体文抄序》奇偶兼用,骈散俱重,也体现了为骈文争地盘的用意。
与毛际可、李兆洛等人虽推重骈文,但仍不否定古文的正宗地位有别,乾嘉时期的阮元,以骈文派健将的身份,不容置疑地宣称,古文不配称为“文”,只有骈文才具有“文”的资格。其理论依据是六朝时期的文笔说,而他所擎的大旗则是他称之为“千古文章之祖”、相传为孔子所作的《文言》(注:阮元从训诂入手论“文”,章太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从训诂入手,指出了他的一个疏忽:“阮芸台妄谓古人有文、有辞,辞即散体,文即骈体,举孔子《文言》以证文必骈体。不悟《系辞》称‘辞’,亦骈体也。”见章太炎《国学略说》,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05-206页。不过,阮元的这一疏忽,并不妨碍他的正面立论。)。他从训诂人手,推断“文”必须具备两个特征:一、必须有韵:“古人歌、诗、箴、铭、谚语,凡有韵之文,皆此道也。”(阮元《文言说》)所谓“有韵”,并不一定指押脚韵,还兼指句中的平仄协调(注:近代视“韵”为“句中声律”的,以阮元和黄侃为代表。阮元的意见见其子阮福的《文笔对》。黄侃的意见见其《〈文心雕龙〉札记》。阮元《文韵说》亦云:
福问曰:“《文心雕龙》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据此,则梁时恒言有韵者乃可谓之文,而昭明《文选》所选之文,不押脚韵甚多,何也?”曰:“梁时恒言所谓韵者,固指押脚韵,亦兼谓章句中之音韵,即古人所言之宫羽,今人所言之平仄也。”福曰:“唐人四六之平仄,似非所论于梁以前。”曰:“此不然。八代不押韵之文,其中奇偶相生,顿挫抑扬,咏叹声情,皆有合乎音韵宫羽者;《诗》、《骚》而后,莫不皆然。而沈约矜为创获,故于《谢灵运传论》曰:‘夫五色相宜,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又曰:‘自灵均以来,此秘未睹,至于高言妙句,音韵天成,皆暗于理合,匪由思至。’又沈约《答陆厥书》云:‘韵与不韵,复有精粗,轮扁不能言之,老夫亦不尽辨。’休文此说,乃指各文章句之内,有音韵宫羽而言,非谓句末之押脚韵也(原注:即如“雌霓连蜷”,霓字必读仄声是也)。是以声韵流变,而成四六,亦只论章句中之平仄,不复有押脚韵也。四六乃有韵文之极致,不得谓之为无韵之文也。昭明所选不押韵脚之文,本皆奇偶相生有声音者,所谓韵也。”(郭绍虞主编《中国历史文论选》第三册,第592页)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秉承阮元之意,确信“有韵为文之说,托始范(晔)谢(庄)而成于永明,所谓文者,即指句中声律而言”。又说:
愚谓文笔之分,不关体制,苟惬声律,皆可名文,音节粗疏,通谓之笔。此永明以后声韵大行时之说,与专指某体为文、某体为笔之说,又自不同,然则以有韵为押脚韵者隘矣(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总术第四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12页)。
按照阮元、黄侃的说法,无论押韵还是不押韵,只要声律和谐,整练含蓄,均可归入“文”的范围。)。二、文必“多用偶”:“凡偶,皆文也。于物两色相偶而交错之,乃得名曰文,文即象其形也。”(阮元《文言说》)用上述两个标准来衡量古代作品,其结论是:
昌黎之文,矫《文选》之流弊而已……《选序》之法,于经、子、史三家,不加甄录,为其以立意纪事为本,非沉思翰藻之比也。今之为古文者,以彼所弃,为我所取,立意之外,惟有纪事,是乃子、史正流,终与文章有别。(阮元《与友人论古文书》)
然则今人所作之古文,当名之为何?曰:凡说经讲学,皆经派也;传志记事,皆史派也;立意为宗,皆子派也。惟沉思翰藻,乃可名之为文也。非文者,尚不可名为文,况名之为古文乎!(阮元《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注:舒芜等编《中国近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07页。)
“说经讲学”、“立意为宗”属于学术著作,“传志记事”属于杂文学,骈文属于纯文学。理学派、汉学派的作品可归入学术著作,史学派的作品可归入杂文学,骈文派的作品可归入纯文学。那么桐城派呢?桐城派主张义理、考据、辞章合一,阮元却将“义理”、“考据”还给“说经讲学”、“立意为宗”的“经派”、“子派”,将“辞章”还给“沉思翰藻”的骈文派,一点依凭也不给桐城派留下。这可真算得釜底抽薪了。桐城派的尴尬处境由此可见。
清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结时期。其流派竞争的特点与前代有所不同。以明代为例,茶陵派、七子派和公安派前后相续,大体上是一个历时态的演变过程。而清代的格调派、性灵派和肌理派,则同时并起。乾嘉年间,汉学派、史学派、桐城派、骈文派纷起争夺文章正宗的地位,更堪称典型的共时态竞争。一个严肃的作者,在共时态竞争中会努力避免意气用事,理论本身的说服力因而得到高度重视。我们注意到一个事实,清代的诗、文流派,其理论主张一般都有前人提出过,但比之前人的阐释往往更为深入、更为系统。研究清代的文学流派,由此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意义。
标签:桐城派论文; 文化论文; 春秋论文; 读书论文; 中国传统文化论文; 章学诚论文; 中国古代文学论文; 论文偶记论文; 古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