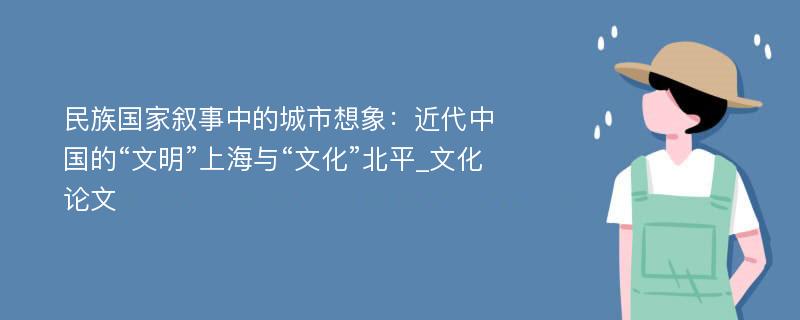
民族国家叙事中的都市想象——近代中国的“文明”上海与“文化”北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平论文,上海论文,近代中国论文,民族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73(2012)05-0012-07
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在谈到大城市的兴起时,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世界上大都市的兴起,主要依靠两个因素:一个大帝国或政治单位,将其行政机构集中在一个杰出的中心地点(罗马、伦敦、北京);一个高度整体化和专业化的经济体制,将其建立在拥有低成本、容量大的运载工具的基础上的贸易和工业制造,集中在一个显著的都市化的地点(纽约、鹿特丹、大阪)。[1]2
近代中国的上海与北京正是这两种城市的典型。如姚公鹤所言:“上海与北京,一为社会中心点,一为政治中心点,各有其挟持之具,恒处对峙地位”。[2]50城市绝非仅仅是个人或社会设施的聚合体;城市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是这些礼俗中所包含,并随传统而流传的那些统一思想和感情所构成的整体。[3]1在整个现代化时期,城市发展不仅仅是空间意义上的,而且是根据文化意义而构成的领土,城市也以此方式被理解,被展现出来。[4]17420世纪的中国城市注定要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中进行艰难、痛苦的转型。以往有关上海与北京的城市文化史研究尽管对这一南北遥相呼应的双城分别被看做“文明”与“文化”的都市想象有所涉及,但均未从将对方作为“他者”的互构角度考察这一问题。近年来,已有学者运用此类建构主义式的方法做思想与文化层面的研究。李欧梵从张爱玲的文本及1930年代的上海电影出发,将上海与香港置于互为“他者”的解读下,考察其文化建构。[5]刘禾引用“理论旅行”理论,注重思想史层面的近代中国引入西方的关键词所涉及的中西互释互译等问题。[6]然而,尚无人从建构主义角度考察近代中国的北京与上海是如何在以对方为“他者”的参照中建构出自身的都市想象。都市景观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可供繁复解读的文本,而对都市景观的充分理解必须建立在景观本身并不生产意义,只有通过人类的阐释与想象,某一时期的景观才与主体产生关系的认识基础之上。[7]城市并不能言说自己,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表述及想象,赋予城市以意义。而城市一旦被赋予意义后,也就不断地循环与再生产这种意义。基于此,本文拟结合观念史层面对“文明”与“文化”在近代中国被赋予的意涵,在建构主义视角下,考察近代中国的上海与北京是如何被赋予了“文明”与“文化”的城市想象。
一、民族国家叙事中的“文明”与“文化”
“文明”与“文化”是社会文化史研究中无法回避的两个概念。然而,这两个概念几乎自诞生以来,就处于一种混用状态,其内涵与定义众说纷纭。英语中“文化”的定义有260多种,据说它是英语词汇中意义最丰富的二、三个词之一。现代意义上、扩展了的“文化”和“文明”的概念则产生于18世纪下半叶。19世纪后,culture的意义发生了变化。“文化本身变成了某种东西。它首先是用来指‘心灵的某种状态或习惯’,与人类完善的思想具有密切的关系。其后又用来指‘一个社会整体中知识发展的一般状态’。再后是表示‘各类艺术的总体’。最后,到19世纪末,文化开始意指‘一种物质上、知识上和精神上的整体生活方式’。”
汉语中“文化”一词最早可分解为“文”与“化”。在金文和甲骨文中,“文”字象征一个人前胸被纹以图案或挂了一串贝壳;[8]2857-2858“化”字象征人一正一倒之形,表示变动、变化和转化。其本义为生成化育,可引申为教化之意。“文化”一词的连用最早见于刘向《说苑》:“圣人之治天下,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这里“文德”与“武力”相对,使“文化”具有明显的“以文化之”之意。“文明”一词在汉语中出于《易经》。《易·乾文言》:“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在注易时的解释为“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文明也。”从这里看,文明应指一种人类社会的气象,“文章”教化之后的一种整体风貌。可见在汉语中,文化与文明最早并不是一回事。一个是指一种有意的意识推行改造过程;一是指特定意识、价值观念下所显现的气象。从孔颖达的注释来看,“文明”还应该含有物质层面的内容。[9]
19世纪末期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使传统“天朝”观与“华夷秩序”受到冲击。在“文明”、“文化”概念流行之前,帝国晚期多半使用“声明文物”、“政教修明”、“文艺”、“文教”、“教化”、“开化”等词表达与欧洲近代文明相近之含义。[10]洋务运动的失败,使维新之士开始在对传统文化价值观展开愈来愈强烈的批判反思同时,将西方现代文明视为一个整体,对其持赞赏态度。戊戌时期,现代“文明”的概念及其传播实践,已开始较为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的政治变革运动,逐渐有力地改变着人们的部分价值观念,并已初步显示出必将进一步影响人们社会生活的前景和力量。[11]尽管现代“文明”的引入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在物质层面的渗透,但当近代知识分子意识到冯桂芬所谓的“四不如夷”后,他们有别于19世纪至20世纪的西方思想家将“精神文化”与“物质文明”皆然二分,在肯定物质层面的“文明”时,更体现出一种精神层面的价值观意涵。梁启超认为:
文明者,有形质焉,有精神焉。求形质之文明易,求精神之文明难。精神既具,则形质自生。精神不存,则形质无附。然则真文明者,只有精神而已。……求文明而从精神入,如导大川,一清其源,则千里直泻,沛然莫之能御也。[12]61-62
康有为更注重“文明”一词的教化功能:“国之文明,全视教化。无教之国,即为野蛮无教之人,近于禽兽”。[13]9鲁迅认为,物质生活“不足尽人生之本”,由“客观的物质世界”转向“主观之内面精神”,才是“将来新思想之朕兆,亦新生活之先驱”。[14]27-31
从词源上比较,将“文”与“明”的组合与欧洲思想史中的重要概念enlightenment(英语:启蒙)、aufklaerung(德语:启蒙)的相通之处,也许是维新之士青睐“文明”的一个重要原因。[10]在维新之士眼里,西方近现代文明所造就的新式文化,已将老中国文化排除在外。“文明”一词作为一个内涵广阔的整体象征着近代西方“富强”的总体现,在知识界中广泛流行并被纳入民族国家的叙事结构中。“夫泰西之民,人怀国家思想,文明程度若甚高矣。”[15]118这一“文明”与进化论及线性历史发展观相联系,意味着运动、变化和进步;自己的传统不仅一无是处,更成了发展民族国家的障碍,是一个必须要推翻的堕落退化社会的残障。通过“广开学会”、建立现代市政及公共设施等手段,借西方现代“文明”之诸方式以扫除中华滞后之“文化”,使传统中华帝国变为现代民族国家,成为晚清知识分子信奉的圭臬。“敝国应筑铁路,又采列国各种文明之利器,以更新中国,是盖有抒胸臆之语”。[16]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下,现代“文明”概念首次提供了一个融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整体综合的社会价值目标和观念基础。能将现实努力的整体价值目标和进化论的理论逻辑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也是现代“文明”观念在变革功能上涵括“进化论”而又超越单纯“进化论”理念的地方所在。[11]梁启超在肯定世界“渐进于文明大同之域”的趋势,把文明看作一个进化过程的同时,对中国实现“文明”赶超西方的前途充满信心:
西人百年以来,民气大伸,遂尔渤兴。中国苟自今日昌明斯义,则数十年其强亦与西国同,在此百年之内进于文明耳。故就今日视之,则泰西与支那诚有天渊之异,其实只有先后,并无低昂。而此先后之差,自地球视之,犹旦暮也。地球既入文明之运,则蒸蒸相逼,不得不变。[17]72
一战爆发导致的灾难暴露出资本主义产生的严重弊端,使19世纪欧洲人的历史进化观受到了真正打击。对经济技术和物质发展之优越性的怀疑与日俱增,西方知识界陷入一片“世纪末”的悲观论中。他们认为这场愚蠢的破坏是一种物质和科学文明的结果。[18]330如果说此前对西方文明失去信心只是个别人的观点行为,此时则“成为了西方思潮、大学,甚至宗教生活的主流”[19]98。欧游的梁启超写道:
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功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三千年所得还要加几倍。我们人类不唯没有得着幸福,反倒带来许多灾害。……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当前世界思想的一个转折点。[2]127
就在这个时候,原本同义的“文明”与“文化”开始分裂:德语中原有的对“kultur文化”的青睐越发明显并慢慢在欧洲普及,成了“zivilisation文明”的反命题。“文化”和“文明”有了高低之分,“文化”更具有精神与道德涵义。伴随对自身历史发展的失望,西方知识界出现了一股告别过去、拥抱东方文化的“东方文化救世论”思潮,对儒家文化表现出高度向往。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于1919年致泰戈尔的信中写道:
大战之惨祸,已明白昭示欧洲文化弊病深重,非吸取东方文化之精髓,融东西文化于一炉,不足以言自存。[21]
中国现代“文化”概念的形成产生于保守主义对现代西方文明挑战的迎战过程中。[22]随着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知识界认识到了西方对“文明”与“文化”的区分,注意到了斯宾格勒等人的多种文化形态的独立性立场。1925年的五卅运动,使上海的这场危机演变成了一个质疑中央政府执政能力和外国驻京使团的全国性危机。[23]158随之而来的是席卷全国的反帝运动,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周作人用愤慨的笔调写道:
文明人有枪炮,野蛮人没有枪炮。西洋人有枪炮,所以是文明;中国人没有枪炮,所以是野蛮。请大家先要摸一摸腰边有无机关枪,倘若你想去同文明国人去说话。[24]512-513
在民族主义情绪的感染下,周作人一面将“文明”与野蛮、征服相联系;一面流露出再造中国精神文明的希望。
1928年后,“文化”被国民政府赋予了新的民族主义色彩,这一来自官方的倡导为北方知识界所接受。“文化”终于在那个民族危机的阴云日益密布的时期,逐渐取代更多象征着侵略、欲望与物质的“文明”,成为一个流行的概念。
二、“文明”——上海的都市想象与北京“他者”
现代“文明”概念主要指人类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一种不断进化着的社会综合状态,一种相对而言的当下较高发展水平。当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致力于对“文明”做精神教化层面解读之时,他们无法回避日常生活中作为物质层面的“文明”在中国的渗透过程。西方的现代性是资本主义发达的产物,而资本主义文明则是在现代性的大都会中产生的。19世纪西方的“文明”概念,更多与城市及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相联系。资本主义工商业是上海的经济基础与经济命脉。殖民主义者必然把他们的物质文明带到他们经营贸易和长期生活的地方。[25]23作为近代开埠以来的首批通商口岸之一,上海注定要成为一个“文明”的象征。
明清以来的上海中心为上海县城,范围在今南市区北部。在近代上海开埠后的十年里,西方人在上海县城北郊设立了租界。“租界马路四通,城内道途狭隘;租界异常清洁,车不扬尘,居之者几以为乐土,城内虽有清道局,然城河之水,秽气触鼻,僻静之区,坑厕接踵,较之租界,几有天壤之别”。[25]42上海的新式建筑、现代交通工具与城市空间均给时人留下深刻印象,是当时的人们了解西方文明的窗口:
今有人焉,游踪所至,忽抵上海,耳目之所接触,不啻身入欧美都市也,楼阁之巍峨,道路之平坦,旅店俱乐部之伟丽,游览之处,则公园及大桥在焉,交通之具,则汽车电车及公共汽车备焉,洋商林立,电炬烁烂,凡此皆在欧美所习见者。[26]1
梁得所在《上海的鸟瞰》中指出,来自外地的旅客“对于上海的感触,印象最深的应该是黄浦滩。因为我们旅客无论来自太平洋、大西洋、长江、珠江,或渤海,大多数由黄埔滩的码头,踏上上海的土地。……黄埔滩的景象,足以代表上海,使我们知道她是一个现代化物质文明的都会,同时是情调深长的地方”。[27]45-46
伴随市政建设及日常生活中物质文明的引入,知识分子与民众的眼光也在发生变化。对于输入上海的西方物质文明与生活方式,经历了一个从惊诧到理解再到崇尚的过程。在上海都市民谣竹枝词中,讴歌“洋场”的竹枝词在19世纪70—80年代形成一个创作高峰期,刊于《申报》,或收入私家刊印文集。[28]340到19世纪90年代以后,上海人的崇洋心理已相当普遍,对西洋器物大都崇尚并拿来为我所用,各大报刊争相刊登广告。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昂的知识分子看来,上海开始被视作一个象征现代“文明”的城市,起着引领全国风气之先的作用:
报馆者一切文明之导线也,上海者又吾国文明之导线也。……上海既为吾国文明之导线,则欲内地文明者,非上海莫与属也。[29]
但在上海城市空间内部,“文明”的符号象征并非铁板一块。当英国统治的公共租界忙于通过摩天大楼、豪华公寓和百货公司展示商业文明时,法租界却在回顾文化的芬芳,高等的或低等的,但永远是法国情调,比英美更有异域风味。道路两旁的法国梧桐与各种风格精致的花园洋房搭配,显得静谧雅致。如果说外滩的雄伟空间展示的是西方的权力意志和嚣张气焰,是“意识形态”化的话语空间,那么,霞飞路给出的主要是生活化的租界空间,是被审美化的日常浪漫空间。[30]在张若谷看来,霞飞路有“是一条富于异国情调的街道,是东方的尼古拉路,也是新兴的神秘之路”[31]。尽管如此,城市空间内部公共租界的商业“文明”象征与法租界的异域“文化”展示,丝毫没有影响到上海作为一个整体的“文明”象征。
而同一时期作为帝都的北京,则正在努力摆脱被视作传统与守旧形象的烙印,迈向“文明”的时代坐标。清末新政至北洋时期的北京,力图用割断作为“帝国首都”象征的方式打造一个现代化的文明城市。在民国初年的政治混乱时期,北京城保持了作为一个新城市中心的史无前例的稳定性,开始采取市政管理与空间规划的新举措,实现由一个帝制时期的首都向共和时期的现代城市的转变。政府致力于勘测地图、命名街巷胡同、构建交通设施及开放公园茶社之类的公共空间诸举措以规训市民,提高民众素质水平,与现代文明市民相匹配。1914年,因改社稷坛为公园而募捐的公告上声明:
窃以京都首善之地,人文骈萃……向无公共之园林,堪备四民之游息。……果能因地拓建,仿公园之规制,俾都中人士休沐余暇眺览其间,荡涤俗情,怡养心性,小之足以俾益卫生,大之足以转移风俗,消息至微,影响实巨。[32]2
可以看出,修建此公园尽管有“怡养心性”之类好处,但其长远目的仍在“转移风俗”,朝向开化与文明。北京正在变得现代和“文明”,但为此也不得不因此而隐匿在“文明”上海的阴影之下。1891年3月31日《申报》的一篇文章通过对比京沪两地街道的差异,喻示现代“文明”带来的好处:
京师“天气晴朗,飞沙铺面,污及衣履。凡客入厅,事先命奴仆扑尘,然后入座叙茶。”……上海洋场土质也是沙土,与京师无异,但经租界建设,现在“天雨无淖没之虞,天晴亦无飞扬之患,行人过此,几不知其本为沙地矣。[33]
晚清人对京沪两城市的比较,认为一个比较洋化、开放、文明,但崇洋、浅薄;一个比较土气、守旧,但有学究名士气习。汇聚近代上的知识分子大都来自内地。当他们脱离了乡土,来到这个五方杂处的都市,也就意味着切断了自身与传统血缘纽带、邻里关系和世袭生活等传统情感的关系,成为都市中无根的“陌生人”。他们是都市中的乡下人,在现代“文明”面前感到自身的传统“乡土”落差。故此,尽管对上海的都市“文明”弊端也有着诸多感触与批判,但他们通过将北京描述成象征传统的、落后的、不文明的城市来反衬生活在其中的上海的现代“文明”。一方面,平衡其内心面对都市“文明”时的“乡土”落差;另一方面,逐渐建构起自身与这个城市的文化认同。“文明”上海的都市想象开始被建构出来。伴随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将“文明”看作标志民族国家富强崛起的象征,上海也自然成了中国的“文明”中心。
一部分作家极力讴歌声光化电的机械文明,将其看做一种生命力的象征。茅盾指出了现代都市生活与机械文明不可分割的关联:
都市里的人们生活在机械的“速”和“力”的漩涡中,一旦机械突然停止,都市人的生活便简直没有法子继续。交通停顿了,马达不动了,电灯不亮了,三百万人口的大都市上海便将成为死的黑暗的都市了。机械这东西本身是力强的,创造的,美的。我们不应该抹煞机械本身的伟大。[34]402
然而,伴随机械带来的喧嚣、摩天大楼造成的视觉挤压、生活节奏的加快等都市生活弊端,科技发展带来的负面价值开始显现。到20、30年代,对机械化的上海、商业消费的上海批判的声浪愈发高涨,尤其是对声光化电等机械文明的态度。[35]89
当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把“文明”纳入民族国家叙事话语中时,所有“文明”的能指都带上了工具论的价值色彩,都必须服务于民族国家的最高利益。一旦不被纳入民族国家的发展需要时,这些“文明”器物立刻带上了贬义的色彩。1930年代,知识分子眼里的上海,已经蜕变为一个不断负面化的城市。高植认为上海有三个特点:
一、商业化:近代文明使一切东西都商业化,……你有钱,你可买小姐的青睐,若是没有钱,烧饼店的芝麻也莫想吃一粒;……二、洋化:物质方面固然洋化,在文化上,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全是跟外国人脚后跟打转,……三、最新式的恶源:绑票是一例,政治争斗及谋害又是一例。[36]
然而,尽管在道德与价值层面对“文明”批判之声不绝于耳,仍有许多知识分子对上海的物质文明给城市生活带来的好处心向往之。上海的“现代派”则因过于贪恋“文明”的物质幻像,终未能发展出与他们同时代的西方一代知识分子的现代性批判。上海在生活方式的整体建构过程中混合了新与旧、中与西。尽管对上海体现出的现代“文明”的态度褒贬不一,但知识分子对上海象征着一个现代“文明”城市这一点则没有分歧。
三、“文化”——北平的都市想象与上海“他者”
老辈学人邓云乡在《文化古城旧事》一书中,对民国时期的北京城被看做“文化古城”的缘由有一番说明:
“文化古城”这一词语,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是在一个历史时期中人们对北京的一种侧重称谓。其时间上限是1928年6月初,……其时间下限是1937年7月“77”事变之后,……这期间,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等中心均已移到江南,北京只剩下明、清两代五百多年的宫殿、陵墓和一大群教员、教授、文化人,以及一大群代表封建传统文化老先生们,另外就是许多所大、中、小学,以及公园、图书馆、名胜古迹、琉璃厂的书肆、古玩铺等等,这些对中外人士、全国学子,还有强大的吸引力…凡此等等,这就是“文化古城”得名的特征。[37]1
邓云乡勾勒出北京作为“文化”象征的概貌。而纵观清末至1930年代的北京,必须看到,北京的城市符号在1928年前后这个分水岭发生了从“文明”到“文化”的明显转变。
清末民初的北京还保留帝都时代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城市风格。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改直隶省为河北省,北京为北平。这一更名意味着北平失去了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退至边缘。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伴随上海作为经济中心地位的确立,现代银行纷纷将其总部移往南方。北平的经济命脉、城市秩序及社会格局均呈恶化趋势。就连素来最具特色的古玩业,也不免萧条之况:“自首都南迁,市况顿减。一般古董之肆或携其宝藏,远走津沪;或迁地为良,另图别计。去岁倒闭休业者,不下二十余家”[38]。
新的执政者赋予这个颓败中的城市以“文化”象征。伴随上海“文明”的不断负面化,北平承载的传统负荷终于摆脱了负面含义。如果1928年前的城市转型是与过去划清界限,努力迈向现代与文明的方向;1928年后的北平则重新建构城市的过去,并将这个城市的过去与民族的历史相联系。国民政府将北平打造为“文化中心”的举措得到了知识分子的认同。现代民族国家是一个政治单位,通过共同的价值、历史和象征性行为表达集体的自我意识。[39]401928年后,“文化”被国民政府赋予了新的民族主义色彩。这一来自官方的倡导因被北方知识界所接受,终于在那个民族危机的阴云日益密布的时期,逐渐取代更多象征着侵略、欲望与物质的“文明”,成为一个流行的概念。1930年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高涨。其特征之一,在思想文化方面,从原来的反省、批判传统文化转变为对传统文化的发掘和弘扬。知识界弥漫着关于中华民族复兴的讨论,并出现了一个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热潮。知识分子在“发现传统”的过程中“发现”了北平。
知识分子认同北平的“文化”象征也标志着1930年代的知识分子开始形成自身的阶层认同感。1930年代伊始,左翼倾向的知识分子留守上海,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移居北平。已有论著描绘出在上海,受商品经济影响的知识分子基于生计的忙碌生活;以及在北平,学院派知识分子闲雅淡泊的日常生活两者之间的差异。当国民政府颁布了教师待遇法规后,知识分子的收入有了明显提高和保障,改变了北洋时期因政府拖欠薪金而拮据的生活。抗战前的北平大学教师群体中,更是出现了一个“万元户”的知识阶层,其时教师月入多在200圆以上(一圆约为今50元)。[40]当知识分子变得有钱又有闲时,他们就成为凡勃伦笔下的悠闲阶级。
北平的学院派知识分子多在国家建制化的最高学府任职。他们可在一个知识与体制相结合的制高点上体现个体价值和发挥群体影响。故相较于依托体制外发达的出版传媒市场的上海知识分子,他们拥有充足的文化资本,得以有相应的从事文化生产与交流的空间。他们通过对基于保守主义立场的“文化”的标榜,同象征着声色犬马的上海“文明”相区隔,构建自身的阶层认同感。
当“文化”终于摆脱了晚清时期象征着守旧及传统的负担,在1930年代被赋予正面色彩并在北平完成其地域化过程的时候,北平也因此真正摆脱了“文明”上海的阴影,并与其正面对峙。在1930年代弘扬传统文化以实现民族复兴的思潮中,北平被看做民族文化的象征。在随后的长期战争中,北平负载的“文化”更是被知识分子看作民族存亡的关键加以捍卫;上海则被北平知识分子投射为一个崇洋媚外,导致民族文化濒临危机的腐朽之城。当知识分子酣畅淋漓地痛斥着上海“文明”的罪恶时,他们也是在缓解自己即将远离象征故乡之根的乡土,在精神上即将流离失所的恐惧与无助感。
四、结语
“文明”与“文化”在近代中国经历了一个彼此建构的地域化过程。“文明”在上海的地域化过程,缘于晚清西方物质层面的输入。近代上海自开埠以来,在渐进引入西方物质文明的过程中被自然地赋予了“文明”的城市符号。清末民初,上海的“文明”象征被视作崛起的民族国家步入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而在此期间,北京则正在努力摆脱被视作传统与守旧形象的烙印,在迈向“文明”的时代坐标时,不得不隐匿在“文明”上海的阴影之下。知识分子通过将北京描述成象征传统的、落后的、不文明的城市来反衬生活在其中的上海的现代“文明”。一方面,平衡其内心面对都市“文明”时的“乡土”落差;另一方面,逐渐建构起自身与这个城市的文化认同。到了1920年代末期,伴随民族危机的阴影加之“文明”带来的负面影响,上海的“文明”逐渐被视作应当远离的罪恶贪婪和声色犬马的欲望载体,上海“文明”也因此让位于北平“文化”。1928年后的北京被国民政府赋予了“文化”的城市符号,这一符号得到了知识分子的认同。在将北平视作“文化”的象征以同“文明”上海相区隔的过程中,知识分子也在形成属于自身的阶层认同感。近代北京与上海通过将对方视作“他者”的互构,形成各自的都市想象。
当人们基于都市特质及自身生活经验赋予都市以特定的文化符号时,这种符号能指就被都市持续复制与再生产,从而更加巩固与丰富了都市想象的过程,城市成为一种再呈现。这就是近代中国京沪双城分别被赋予不同的文化意涵并得到广泛认同的原因。然而,历史的发展使得这种都市想象因必须服从所处时代的主流叙事的需要而与真实再现渐行渐远。1930年代的北平无疑比清末帝都更为现代,然而,却在都市想象的过程中被赋予了“文化古城”的象征。1930年代的上海依旧车水马龙夜未央,但此时象征道德低下与颓败的“文明”已非清末时在历史进化论阳光照射下的那个“文明”。近代中国北京与上海的都市想象最终因镶嵌在民族国家叙事的话语中而改变。
[收稿日期]2012-08-16
标签:文化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华夏文明论文; 现代文明论文; 1930年论文; 上海论文; 人类文明论文; 政治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读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