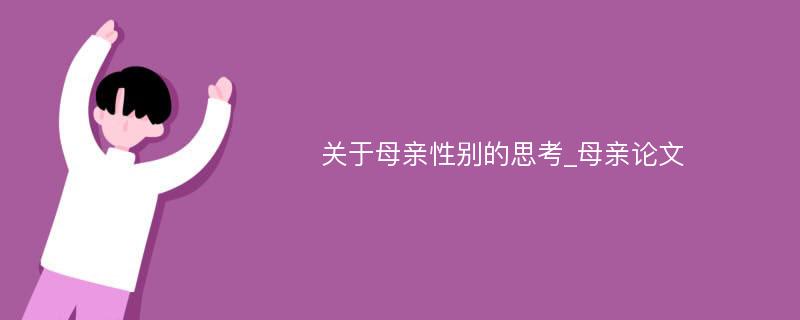
对母亲社会性别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性论文,母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研究者注意到,在中国历史上,母亲曾拥有权力。如,杜芳琴教授(1996)对中国历代女主和女主政治的研究,又如玛杰里·伍尔芙(Margery Wolf 1972 )对台湾农村妇女与家庭的研究。 前者指出, 在2300年的封建社会中,女主统治或女主参与统治的约600年, 但母后执政并不是妇女社会地位高的标志; 后者提出了“子宫家庭”(uterinefamily)概念,认为妇女通过生育特别是生儿子从而取得了在父权制家庭中的母亲权力,这种权力巧妙地挑战了男性统治,同时也巩固了男性统治的传统。这些研究提示了“母亲”与“妇女”在历史上被分离的迹象。
中国现代作家林语堂意识到了母亲权力,但他因母亲的权力而否认女人受压迫。他在《中国人》一书中说:“人们对中国人的生活了解越多,越会发现所谓的妇女的压迫是西方人的看法,似乎并不是仔细观察研究中国人生活之后得出的结论。这个批评肯定不适用于中国的母亲这个家庭的最高主宰。”林语堂把母亲拥有的地位和权力当成了女人的地位和权力,这是人们常见的一种混淆,乃至是一种有意把“母亲”和“女人”混为一谈的混淆。实际上,主流话语一直竭力分离“母亲”和“女人”,如果我们不首先认清这种分离,就很难识别那种有意的混淆。本文尝试分析主流话语对“母亲”和“女人”所做的分离,这一分析基于社会性别概念,目的在于指出:母亲是被社会性别话语制造的。
一
这里,首先要提及“妇女”概念。
李小江(1997)认为,不同的意识形态为我们思考女人提供了不同的话语。关于中国女人有三种截然不同的话语世界——传统的、社会主义的和女性的。属于传统话语的如“小女子”、“老妇人”之类完全由男人制造并直接服务于男性中心社会;而“妇女”这一称谓与革命相联,毛泽东称自己队伍中的女人为“妇女”或“妇女同志”,“妇女”话语塑造了“非性化”时代,它在官方文件中是女人的统称。依李小江对“妇女”特有的历史文化内涵——已婚的、成年的、老态的、旧式的——的解释,“妇女”这一语言符号包含“母亲”,内涵又较“母亲”更宽。我们在阅读中,对“妇女”和“母亲”所指的这种差别也并不陌生,如“青提夫人所遭受的苦难和目连救母过程中的曲折艰辛,便具有了感动作为女性和母亲的妇女听众内心的震撼力量。”这句话中,“妇女”就包含了“女性”和“母亲”。
“母亲”在传统话语中具有明确含义,李小江(1989)在《性沟》中写道:“父权社会中的妇女,也仅仅是在母亲的意义上,才能得到家庭的认可和社会的尊重。”就是说,“母亲”是被社会承认的妇女,是有德妇女;在社会主义的话语中,“母亲”被淹没在“妇女”中,即使在高生育率的年代,“母亲”也没能脱离“妇女”而独立表达。倒是传统话语中的“贤妻良母”在近20年中重新获得了表达机会,虽然此时,“贤妻”已失去传统话语的所指,因为“妻”是“爱人”;“妻”参加社会生产,有工作,是职业妇女,不再是被供养者;婚后有自己的姓氏。中国妇女曾由此获得了西方妇女的羡慕。从传统话语中捡出“贤妻良母”是因为“良母”,即女人必须为母,优生优育,生育儿女,独生子女政策,因子女而来的家务,因生育而荒废的学业和失去的机会,双重角色,……在社会主义的话语中,“妇女”不仅会因“母亲”受到尊重,也可能会因为不是“良母”而遭到实实在在的否定。“母亲”得到赞扬较“职业妇女”多,社会最需要的是“母亲”——为男性中心社会生育、教育接班人。所以,尽管看起来“母亲”被“妇女同志”或“女劳模”、“女代表”等掩盖了,但传统话语的“母亲”仍暗含在“妇女”所指中,并且伺机独立表达。
1980年,《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全文刊登了周恩来在1942 年11 月20日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的、题为“论‘贤妻良母’与母职”的文章。文中写道:“母职,是妇女在人类社会中最光荣的天职。我觉得,泛论起来,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任务,再比母职光荣和永恒的了。为着人类绵延,民族繁荣,尤其是为着目前健强我们中华民族的后代子孙,我们亟须尊重母职,提倡母职。…至于妻职问题,是应当与夫职通道开地和相提并论的。我们非空口反对‘贤妻良母’,而是主张以尊重母职提倡母职为中心的新概念来代替‘贤妻良母’的旧概念的。”学报为此文加的编者按认为,周恩来的观点对破除旧的道德规范具有指导意义。这至少说明,时至80年代,社会主义话语尚未能发现代替“良母”的对妇女生存形式的另一种表达。
除了用“革命”外衣包装了的“妇女”,就是含义确定的“贤妻良母”,无论哪一个,“母亲”都是其中的主要内涵,社会性别话语一直在塑造母亲。
二
在传统话语里,“女子”是小的、弱的、可以被轻贱的、可生灾祸和需要驯服的,最为著名的有,孔子言“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论语·阳货》);“母亲”是慈祥的、勤劳的、牺牲的、伟大的。依刘向《列女传》,母者,应如周太姒“思媚太姜、太任,旦夕勤劳以尽妇道。生十男……诲十子,自少及长,未尝见邪僻之事。十子之中,武王、周公成圣。”母之功绩在教子,母亲生育、养育后代的辛劳终有回报,那就是“孝”。孔子主张“事亲孝”(《论语·学而》),“亲”即父母双亲。“孝”主要包括听从母亲、成人成才和赡养母亲。所以,“女人”与“女子”、“妇人”的所指相同,是在特别提示女性生物性别时使用的,在对“母亲”塑造的过程中,“女人”逐渐地被置于“母亲”的对立面上。
在解释女主政治的文化原因时,杜芳琴(1996)明确指出:在中国,既有贱视妇女的偏见,又有尊母的传统。中国没有女权、妻权而有“母权”。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数“家”在“尊母”上取得了共识:道家尊母,是从道的本体立论;法家重母,是从功利实用出发;儒家尊母,则是从伦理道德着眼。在民间流传甚广的佛教故事“目连救母”,也宣扬了一种尊母思想。
当一方面是“尊母”,另一方面是“小女人”时,传统话语便分离了“母亲”与“女人”。
这种分离还体现在“女”特别与“色”相关,而“母”只与“家”相联。在传统话语中,“色”主要表示“女色”、“女性魅力”(江晓原1995)。先后儒家均有“好德”与“好色”的讨论,“色”具有很强的对象化特征,“好色”非人(包括男女)之本性,而仅是男人对“女”(物化对象)的追逐,或是“女”对男人的迷惑。“女”即“性”,她不是另一性(人),而是洪水猛兽,是可怕之“物”。“好色”则是“毁德”,所以,“坐怀不乱”、不近女色在后儒就是不毁掉自己的“德行”。与“女色”有毁男人的德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尊母则使男人具有“德行”。研究者(中国伙伴关系研究小组1995)发现,在汉代孝行的例子中,以孝敬母亲者居多。孝子得到官方和民间的一致赞扬,是一个男人在朝在家取得地位的必备品德。
传统话语对“母亲”与“女人”的分离一直延续下来。近20年,我们几度讨论“贤妻良母”的角色冲突,但无论论者说什么,女人们还是被要求做或要做贤妻良母。为什么?是因为“母亲”被社会接受、赞扬,她是确定的、完整的、幸福的;而脱离“贤妻良母”的女人则是孤独的、不确定的、不完整、不幸的,此外,如果她们是“三陪女”、“妓女”,那她们就是卑鄙的、下流的、无耻的、肮脏的,甚至非人的。
三
现代史上,“男性思想家们一致借用女权主义为利器,反对封建主义;却未等女权主义与女人见面,便将她窒息在民族主义和社会革命大潮中。”(李小江 1997)窒息女权主义的行动之一, 就是利用传统话语分离“母亲”与“女人”。
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十分重视母性之于家庭的意义,他(1928)以为,女子之中,有母性特别强者,有平庸者,也有特别薄弱者。他说:“今从事于女权运动者果为何种女子乎?曰,大多数为母性甚薄弱之女子。”他批评那些母性薄弱之女子宣传其他女子加入社会事业,而影响母性平庸者专心于家庭生活,所以,在他看来,“最初之妇女问题为如何安插此少数母性特薄而才力特厚之女子;今天之妇女问题则为如何使大多数妇女恢复其适当之家庭生活。”十分明显,潘先生相信,大多数妇女应是“家庭”中的“母亲”。对于少数女子背离母性去从事社会事业,他虽表现出宽容,但对其对母性的背离是持否认态度的。这里,“女子”与“母亲”的对立显而易见。
再举现代作家林语堂为例。他在《理想中的女性》中的这段文字则明白地分离着“母亲”和“女人”:“由中国人看来,西洋社会之最大的罪恶为充斥众多之独身女子,这些独身女子本身无过失而言,除非她们愚昧地真欲留驻娇媚的青春;她们其实无法自我发抒其情愫耳。许多这一类的女子,倒是大人物,象女教育家,女优伶,但她们倘做了母亲,她们的人格当更为伟大。一个女子倘若爱上了一个无价值的男子而跟他结了婚,那她或许会跌入造物的陷井,造物的最大关心,固只要她维系种族的传殖而已;可是妇女有时也可以受造物主的赏赐而获得一卷发秀美的婴孩,那时她的胜利,她的快乐,比之她写了一部最伟大的著作尤为不可思议;她所蒙受的幸福,比她在舞台上获得隆盛的荣誉时尤为真实。”
从这里我们清晰地读出了“女”较之“母”的不足,林先生借助造物主对比了“女”幸福之有限和“母”幸福之无限与绝对。
“女”不仅不如“母”幸福, 也不如“母”伟大。 有一本出版于1993年名为《母亲》的散文集,编者在序中写道:“母亲的伟大,不仅仅在于她生养了我们,不仅仅在于她为生养我们所承受的巨大痛苦与磨难;母亲的伟大,也不仅仅在于她对我们比海洋更为深远的爱,也不仅仅在于她为爱我们所进行的拼死抗争,所付出的血泪的代价。母亲的伟大还在于,她既要在家庭中扮演好贤妻良母的角色,又须在社会生活中同男人一样地去争得一席之地,去谋求事业上的成功。……所以,母亲的伟大还在于,她们在实际上是并不自由的生活中,承受着沉重的社会积习的压力,却仍能够向社会播撒着爱与美的种子,向人间奉献出鲜花与微笑。”这里写出了是谁伟大、为什么赢得了“伟大”:作者肯定不允许也难以将“母亲”换成“女人”,因为不仅此间作者强调的是为人母者而不是某一性别群体,并且,如要赞美女人,须用另一套话语。
“母亲”的牺牲精神是母亲塑造中惯用的。尽管,母亲因为什么富于牺牲精神需要专门分析,但人们还来不及询问就已经习惯于相信:母亲应该具有牺牲精神。古时,寡母含辛茹苦抚养子女被人传诵,今天,传媒中不乏“为筹措儿子大学学费——寡母挨户跪了49家”(《北京晚报》1997年10月22日)之类的报道。
李慧英(1997)曾在《中国妇女报》上撰文,评论电视剧《渴望》和《风雨丽人》中两类反差极大、对比强烈的女性形象:一类是母亲,一类是女强人。她说:“作家们不约而同把喜爱献给了母亲,将反感留给了女强人。”她指出,也许这并不是出于编剧们的自觉。的确,这恰是传统话语对“妇女”话语的渗透,是“尊母”与“小女人”的继续。
显然,传统话语对“母亲”的塑造及其与“女人”的分离还在继续。
为什么社会主义话语在“妇女”中没能消除“母亲”与“女人”的对立?原因在于,中国文化是重生育、重人伦的。李银河(1994)指出:“中国文化之有幸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绵延数千年不曾断绝的文化之一,崇尚生殖应当说是功不可没的。”母亲因其是生育者在中国文化中是具有特殊意味的。从位置上看,她属于“家庭”,拥有教育子女、管理家庭的权力。她是家庭等级和制度的坚强维护者,家是她发挥才能的天地;从经历上看,她经由“女孩”“女子”达成。“母亲”不只因生育自然成就,而是由生命的一个又一个的疑问和梦想的不断破灭而实现的。李小江(1989)描述了它达成的过程:“当女儿的急于出阁,希冀嫁一个好夫婿,结束寄人篱下的娘家生活;做了妻子,又盼望早日生儿育女,获得主持家庭的权力;一旦做了母亲,就意味着她完成了女性生活的全部经历,本来就淡薄的自我意识完全消失,融化在忘我的母爱中。”“母亲”是在对“女人”的否定中获得的,因此,她十分珍视自己最终获得的位置;从功绩上看,“母亲”承担人类社会延续,甚至被赋予神圣的意义。如土地和祖国。由此,当我们说“祖国,母亲!”时,不能想象“女人”能够承担此种神圣。
所以,可以认为,“母亲”在以往的话语中从“女人”中被异化出来,而这种异化过程正是“母亲”概念不断远离其生物性的过程。
用社会性别看母亲时,我们会发现,当母亲站在男人一边反对女人(如婆媳冲突中,婆婆往往代表家族的、传统的、男权的势力压迫媳妇)时,她们较男人更强烈,更彻底;当她以“妇女”的面目出现时,它又是男权统治的受害者;就其根本的立场而言,母亲维护家庭和子女的利益,较少关注社会政治,缺乏平等观念。在中国历史上,是男性通过母亲的生活,感受和理解了妇女的苦难,进而为了反封建而疾呼妇女解放,而不是母亲首先意识到自己因性别的缘故而受的压迫,进而进行解放斗争。
四
由于传统话语对“母亲”与“女人”的分离,女性话语在“母亲是谁?或,女人是谁?”这一根本问题上遇到了困难,也就是说,寻找女性“自我”的路途因此倍加艰难了。
目前,研究者试图通过让女性自己说话的办法来发现,是谁在做?为什么要做?比如,塞西莱、刘犁(1997)在对中国城市生育意愿的研究中,让多位母亲说话:一位天津的妇女(母亲)说:“现在国家实行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我觉得要第一胎就生一个男孩,这是很大的压力。我丈夫是他们家的独子,在我们结婚后,我就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只能生一个男孩,我怀孕后,我就希望自己能生一个儿子。后来,我生了一个男孩,我觉得我这是为我丈夫家生了一个儿子。这种传统的思想似乎是无法改变的。”这就是母亲!在“我希望自己能生一个儿子”和“我觉得我为丈夫家生了一个儿子”之间,母亲不知道“我”的真实愿望,因为,母亲的“我”不确定——离开了“家庭的、丈夫的”,还有没有母亲的愿望?
研究母亲是一条寻找女性自我的路。我想,关于母亲性别的思考与如下问题相关:(1)母性是女性本身固有还是被塑造的品性? “母亲”与男权文化有无冲突?若有,冲突在哪儿?母亲是否能够自己意识到与男权文化的矛盾冲突?回答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中国女性的群体意识及其自我意识觉醒的问题。中国女性是否因是“母亲”而缺乏主体意识?所谓“中国妇女运动总是汇入中华民族运动”是否也与此有关?
(2)“母亲”是否限制了女性的多样性存在与发展? 某些女性能在男权文化中获得某种实惠,那么这些既得利益者的生活方式是否就会成为男性中心社会否定女性多样性生存发展的借口?这些既得利益者是否会如同传统社会中的婆婆一样转而成为男性中心社会的帮凶(或可名曰合作),直接压迫另一些女性?
(3)关于“母亲”的美德。 今天我们最难抗争的就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比如,一边对“贤妻良母”提出质疑,另一方面,视“贤妻良母”为女性之美德。如,《中国女子与女子教育》一书的作者写道:“在中国几千年的反复实践、积累中所形成的贤妻良母相夫教子的优良传统,对于通过家庭来协调男女两性关系、教育子女,为社会提供一种和谐、安定的环境,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满足于这些美德,也以为“母亲”的性别模糊是两性友好、两性合作的原因,那么,我国的女性研究将出现方向迷失;反之,如果将母亲美德视作是女性异化的证据,那么,我们就可以迈开寻找女性理想的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