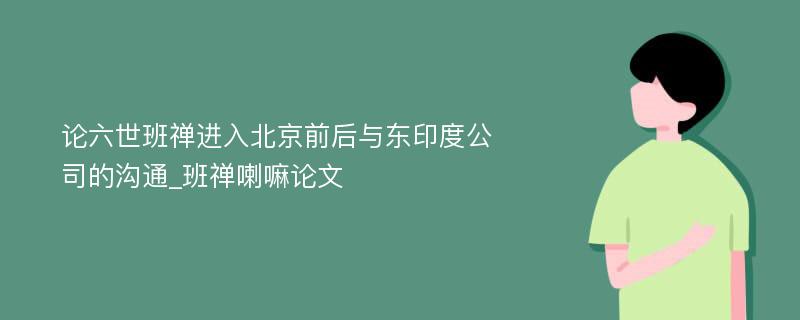
论六世班禅进京前后与东印度公司的交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印度公司论文,班禅论文,论六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K24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57(x)(2013)01-0101-08
对六世班禅罗桑巴丹益喜(blo bzang dpal ldan ye shes,1738—1780)进京这一历史事件,不少中国学者早已作过研究。不过,这些研究大都着眼于清廷如何以藏传佛教为纽带来加强和西藏的紧密关系,尤其是立足于班禅的宗教影响和清朝治理多民族帝国的政策而展开。这种以巩固多民族的大清帝国的统治为视角的说法既非有误,亦非偏离史实,可是历来的研究忽略了这一历史事件背后牵涉到的班禅和当时驻加尔各答的东印度公司的交往。对这一跨喜马拉雅山的交往,先后有几位西方学者利用东印度公司的史料,尤其是其派员留下的旅行记录,深入地研究了乔治·波格尔(George Bogle,1746—1781)和六世班禅的交往、萨姆尔·特纳(Samuel Turner,1759—1802)访问扎什伦布寺的经历以及东印度公司从喜马拉雅山的另一边打开西藏,乃至大清帝国的大门的计划所做的诸多努力。
本文在综合中外学者现有的研究成果之余,把六世班禅和东印度公司之间的交往这一重要历史事件放到18世纪后期跨国界交流的背景下来审视,意在突破原有的清朝大一统的理论框架,为分析六世班禅时期西藏与外界的交往提供一个新的视角。研究六世班禅和东印度公司交往的重点不仅在于梳理与这一事件有关的多语种的史料,而且至关紧要的是需要对班禅进京的历史事件加以全面的分析。从史料看清朝和西藏的关系的同时,我们尚需突破固有的视角和观念,还要从喜马拉雅山的另一边来看西藏在18世纪与周边地区的交流。
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六世班禅进京前后西藏与东印公司的相互交往及其牵涉到的诸多错综复杂的关系。第一、18世纪后半期跨国界交流为我们留下了多语种的史料,各种史料具有不同侧重点,其中清朝满文史料可能会为我们研究这一事件提供突破性的解释。第二、以印度游方僧普林格尔(Gosain Purangir)为信使和中介,六世班禅和东印度公司有过频繁的交往。普林格尔是六世班禅与东印度公司维持交往不可或缺的中介人物。借此,我们利用现有的史料来看六世班禅东行期间,普林格尔为东印度公司起的是什么样的作用。第三,18世纪后半叶东印度公司对西藏的了解非常肤浅,对清廷也所知甚少,而对西藏和清廷之间的微妙关系更是不了解。虽经百般努力,东印度公司最终未能实现通过西藏打开中国市场的愿望。这或许为后来清廷和英国的关系,尤其是鸦片战争的发生埋下了一个伏笔。
一、各种史料对六世班禅和东印度公司交往的记载
汉文、藏文、英文和满文等语种的史料对六世班禅和东印度公司交往的这段历史都有所记载。每一语种的历史资料有着不同的视角,因而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和特点。汉文和藏文的资料比较简洁,东印度公司的英文资料颇为丰富,而满文的资料除了业已出版的《六世班禅朝觐档案选编》收集的目录之外,还有待学者作进一步的研究。
1.汉文
六世班禅应邀进京,可谓清廷治理藏区的一件盛事。在章嘉国师若必多吉(lcang skya rol pavi rdo rje)的协调和安排下,六世班禅应邀动身东行,于1780年即乾隆皇帝70岁寿辰之年,朝觐清廷。正如五世达赖喇嘛进京会见顺治皇帝,六世班禅进京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充分显示乾隆皇帝亲近和敬拜藏传佛教领袖,竭尽努力团结藏族上层人士而达安治多民族帝国的目的。出于这一历史背景和意义,我们本该想当然地认为清朝官史该会对此事件作一翔实的记载。但是从现有的汉文史料来看,并非如此。
汉文史料对班禅进京的过程作了一些记录,罗列了班禅及其随从拜见乾隆皇帝的隆重礼仪,让人自然而然记起五世达赖喇嘛觐见顺治皇帝的场面。《清实录》、《清宫热河档案》和《清宫普宁寺档案》等清朝官史记录的都是诸多朝廷礼仪和冗长的赠礼单子,却没有记录任何有关六世班禅和乾隆皇帝直接接触和交往。《清宫热河档案》中收录的文档与六世班禅进京相关的寥寥无几。至于究竟是没有收录进去,还是根本就没有这一事件的详细记录,我们就不得而知。①即便是直接记载六世班禅进京的诸多仪式和活动,汉文史料也仅作轻描淡写。比如,六世班禅圆寂以后,在乾隆四十五年七月丁酉(1780.8.20)《清实录》记载:“班禅额尔德尼自后藏入觐。上御依清旷殿召见,赐座,慰问,赐茶。”②诸如此类的记载还有几处,但都是简单之至。只是在乾隆四十六年正月癸未(1781.2.2)给八世达赖喇嘛的上谕中详细道出六世班禅来京觐见,染病、圆寂以及圆寂之后扎什伦布寺内事务的安排。③这是《清实录》中有关六世班禅来京这一历史事件记载得最为详细的官史记录。
日本学者石滨裕美子曾对现有的有关六世班禅进京朝觐的汉文和藏文史料作了非常透彻和精细的对比和研究,罗列了班禅进京参加的各类政教活动和会面仪式的时间,地点和相关的事件的细节。④但是,文中根本没有涉及东印度公司和六世班禅在那一时期的交往。
因此,汉文史料就六世班禅的记录大多集中在他东行进京一事,并没有记录他和东印度公司的交往,更何况提及东印度公司的人员曾随同六世班禅来京造访。
2.藏文
藏文史料对此未能提供多大帮助。意大利藏学者毕达克于1949年发表在《通报》的短文对和东印度公司派员相关的所有藏文史料作了一个总结。⑤他仔细查阅了六世班禅自传中提及的有关波格尔来访扎什伦布寺的内容。⑥根据他的解读,自传中几处提到波格尔来访以及会见班禅事宜,但除此以外,既没有有关波格尔来访的翔实的记录,也不见有关随班禅进京的印度游方僧普林格尔的记录。⑦有关普林格尔这一人物,下文将会详细叙述。
最近陈庆英和王晓晶两位学者对六世班禅的传记的藏文和汉译本进行了仔细的研读。他们注意到六世班禅传记中曾提到班禅东行时有两位印度的瑜伽师陪同,而班禅大师圆寂之时曾提到想和两位印度瑜伽大师见一面。以下是陈庆英和王晓晶对藏文相关的段落的翻译:“尔后,大师派人去叫两位印度瑜伽师。可是一位不在,而另一位叫浦南吉尔(即普林格尔)的到了。大师高兴地向他用印度语赐教。”⑧
据笔者所知,这是藏文史料中提到普林格尔的唯一的记录。《六世班禅全集》(第一卷·年谱)和《章嘉国师若比多吉传》中都没有提到普林格尔这一人物。虽然贡觉·晋美旺布在《传记》中并没有对细节作任何记录,但是我们从中至少能确定,普林格尔不仅随从班禅进京,而且能算得上是他的一位贴身近侍。这是藏文史料有关班禅进京朝觐中涉及的东印度公司人员的非常珍贵的一则信息,确实是对汉文史料的一个很好的补充。
3.满文
清史和边疆史领域的学者迄今都未能参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满文史料。我们最多只能猜测,尚未公开的满文史料或许能有助于我们了解普林格尔在京的活动,或者至少能为学者的一些推断提供佐证的史料。值得庆幸的是1996年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的《六世班禅朝觐档案选编》列出诸多现存于一史馆的满文史料。由于列出的满文资料涉及的事务是其他文种的史料所奇缺的,与本论文议题相关的条目,都一一选录其下。
这些条目共9条,即福隆安寄信谕伍弥泰等询明班禅带往热河人众实数、福隆安等奏与章嘉呼图克图酌定于依清旷会见班禅时陪同入见人员名单折、福隆安等奏紫浮念经人数不需增加折、乾隆御避暑山庄接见班禅、乾隆首次于依清旷殿会见班禅赏单、福隆安等奏班禅谢准从徒众内再选一人入宴情形折、乾隆初宴班禅及其徒弟并赏单、随班禅到热河之僧众从人名单、乾隆帝于保和殿赐宴班禅,分别摘自军机处班禅寄信档、军机处班禅议复档和军机处班禅档以及军机处录副包内。⑨
从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清廷对六世班禅朝觐时参加殿会,赴宴和念经的人员和人数是非常仔细的,所有的人员和人数都得经过一一核实。或许印度游方僧普林格尔曾加入班禅的随从僧人而赴宴。
4.英文
东印度公司保存了齐整的史料,因此有关波格尔和特纳以及东印度公司和六世班禅之间来往的英文资料都非常齐全。⑩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东印度公司的官方文件使用的是英文,但是实际上个人之间的对话和书信来往使用的是波斯语和兴都斯坦语。(11)
英文史料不仅存有有关事件的前因后果的具体记录,而且还记载了有诸多妙趣横生的个人感受和实地观察。我们不仅有波格尔和特纳的游记以及经由马克姆编辑的记录,还有附录中普林格尔的两封书信记录了他随同六世班禅进京,朝觐清廷的细节,其中竟然还包括对班禅和乾隆皇帝间的多次对话。总之,英文材料非常注重东印度公司通过西藏建立和清朝的贸易关系的诸多努力,比如多次派员前往日喀则拜访班禅,如何建立跨越喜马拉雅山的贸易关系,如何利用西藏的地理位置来达到打开中国市场的目的。
中国学者长期以来难以直接接触到这些英文史料,一些西方学者得便曾对这些英文资料作过深入透彻的研究。最早的有卡门(Schuyler Cammann)出版于1951年的博士论文。(12)卡门主要采用英文史料来分析东印度公司在18世纪通过西藏打开中国贸易市场的百般努力以及由此带来的结果。他关注到,普林格尔这位游方僧曾在六世班禅和东印公司交往期间起到了的关键的作用,并且指出学者对这一关键人物的关注远远不够。(13)
时隔半个世纪之后,似乎这一议题重又得到学者的青睐。特尔彻(Kate Teltsher)利用东印度公司的档案,对东印公司总督哈斯汀士(Warren Hastings)和派员的个人背景和生活经历作了翔实的研究,还对东印度公司派员和班禅的个人交往以及普林格尔这一人物作了详细的追述,于2006年出版了《通往中国的崎岖山路》。(14)马世嘉(Matthew W.Mosca)则于2008年向哈佛大学东亚系递交的博士论文以一个世纪内清廷对印度的接触和了解为题,对现有的史料进行了非常透彻的研究和分析。(15)虽然他的博士论文的要点是清廷在18世纪后半期和19世纪前半期(1750—1847)对印度的了解,但论文的第四章着重论述18世纪后期西藏,尤其是班禅在清廷对印度的了解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他对六世班禅进京以及普林格尔参与会谈的记录也作了详尽而又深入的分析,得出的基本观点与卡门的相呼应。他认为,乾隆中期清廷对印度的了解微乎其微,甚至对东印度公司和扎什伦布寺建立的交往关系也是一无所知。
东印度公司和六世班禅的交往和六世班禅启程东行发生在同一历史时期,其重要性显然值得学者们关注。而从现存的史料来看,能连接这两起历史事件的只有来自东印度公司的普林格尔的笔记。(16)普林格尔的笔记以书信的形式被收存入特纳游记中,量少且并不可靠,但是由于其他语种的材料极度缺乏这方面的记载,学者们仍然频频引用。
虽然我们知道确实有普林格尔这么一位受用于东印度公司的游方僧,但是这些史料如何能帮我们进一步了解普林格尔这一人物呢?他真的随同班禅去了北京,并且步入朝廷而亲闻目睹班禅和乾隆皇帝的会谈吗?18世纪晚期这位印度游方僧的出现能说明什么呢?
二、印度游方僧普林格尔(Gosain Purangir)
由于普林格尔的这个人物的出现与那个时代紧密相连,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执掌扎什伦布寺的六世班禅出众的个性和修养。因此在讨论普林格尔这一人物之前,需要先对六世班禅作一简单介绍。
六世班禅法名丹巴益喜(1738—1780),是后藏南木林宗扎西则谿卡人,是18世纪西藏一位至关重要的宗教和政治领袖。1774年,六世班禅曾写信给东印度公司总督哈斯汀士,调节不丹和印度孟加拉之间的纠纷。哈斯汀士收到班禅的书信之后,不仅缓和了与不丹的紧张关系,而且还利用班禅来信的机会,派波格尔前往扎什伦布,亲自拜见班禅,了解西藏的各方情况。波格尔来到扎什伦布寺,在那里一住就是整整4个月。这一来访未能马上到达预期的目的。波格尔既不能继续前往拉萨,也难以和达赖喇嘛取得联系,更不能当下通过班禅和清廷建立任何关系。虽则如此,但是波格尔的到来和逗留生活使东印公司和六世班禅的关系得以进一步加深。往后10年里,双方维持着密切的交往关系。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波格尔启程回加尔各答之时和六世班禅的一段对话。波格尔提出:“哈斯汀士总督将遣其臣仆不时致书班禅,是否同意?”班禅答以:“余愿总督此时暂勿派遣英人,余愿总督遣一印人来也。”后来哈斯汀士遣派普林格尔前往扎什伦布寺,就当然是他对六世班禅的要求的最好的回应。
有关六世班禅的描述多处可见,如“(班禅)年近四十,赋性豁达坦率而慷爽,外貌愉悦和善。其谈话时尤令人欢乐愉快,常以无限之幽默与滑稽述谈有趣之故事。”(17)这可在藏文文献中得到印证。比如,多仁丹津班珠尔著的《多仁家族纪实》中多次对六世班禅作过生动而又富有个性的描述。(18)
因此,在六世班禅执政期间,扎什伦布寺和东印度公司能建立密切的交往关系并非偶然。除了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外,六世班禅所具的佛教领袖品格和丰富个性无疑是这种跨喜马拉雅的关系的行程不可或缺的因素。与此相关的还有那一时期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和东印公司在印度面临的濒临崩溃的金融危机。
虽然六世班禅擅长与外界接触和交往,但他与东印度公司和与清廷的交往还是得完全依靠信使和派员,以他们为中介进行交流。与东印度公司总督的交往,他得依赖于普林格尔;而与乾隆皇帝的来往,章嘉国师是他得力的中介。对章嘉国师若必多吉的身世及宗教和政治地位和作用,王湘云曾作过透彻的研究。(19)而普林格尔是谁?他到底在班禅和东印度公司的交往中起何等作用?难道他真的如自己的笔记中所写,陪同班禅,不仅亲眼见到乾隆皇帝,并向大清皇上介绍印度斯坦(东印度公司)及其总督?
对游方僧普林格尔的关注和研究早在百萨克(Gaur Das Bysack)发表于1890年的论文中就有较为详尽的阐述。(20)卡门和马世嘉都曾引用。卡门于1950年代初的专著充分利用英文史料,对普林格尔这一人物作了较为仔细的研究,并特别提出,这一人物的重要性非常值得学者们关注。而马世嘉于200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再次对普林格尔这一议题作了深入的分析。2006年出版的特尔彻的著作进一步充分利用现有的英文资料,对六世班禅和普林格尔的交往加入了诸多富有文学性的描述。总结他们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肯定普林格尔确实在六世班禅和东印度公司在18世纪后半期的交往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具体而言,有关普林格尔,我们可以确定与本文相关的两个要点。第一,作为东印度公司和六世班禅得以建立密切关系的中介人物,普林格尔不仅多年来游走于喜马拉雅山区,而且还曾千里迢迢随同六世班禅东行进京,朝觐清廷;第二,对他在京的角色和活动,我们依然一无所知。
根据收录在特纳旅行笔记中的普林格尔写给东印度公司的两封书信,我们还得知他还曾多次出现在乾隆皇帝和六世班禅会面、对话的现场。不少学者对这些记录的真实性或多或少产生怀疑,可是汉文或藏文史料中难以找到相关的佐证资料。卡门认为,即便班禅和乾隆皇帝之间进行的那场有关东印度公司的对话确实发生过的话,其实就当时的场景看来,应该只是一场无关大体的交谈。(21)对此,马世嘉也持有类似的看法,认为这场对话仅是不经意的茶间对话。
这是长期以来学者对普林格尔在京城的活动所知的少有的一点信息,而他随从六世班禅东行,进京朝觐乾隆皇帝,参加各类佛事活动时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亲自参加了何等仪式,哪类会面等等,一概不得而知。
特纳笔记的附录中普林格尔本人的信件能进一步说明普林格尔确实曾陪同班禅前往北京之外,依然无法证明普林格尔随员进京的身份会重要到能亲临班禅、章嘉国师和乾隆皇帝会面的场合。根据现有的历史资料,难以解释普林格尔亲自参加这一对话的可能性。其中有几大问题:一是礼仪上并不可能;二是语言交流上的困难;三者,当时会面的场景注定普林格尔几乎逐字逐句记下这场对话是非常不切实的。
从礼仪上来看,普林格尔不大可能会受邀正式参加乾隆皇帝和六世班禅的会面。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著的《章嘉国师若必多吉》多次重复记述:“班禅大师所到之处,章嘉国师都亲自陪同。”1780年十月初三日在保和殿会面的记载,尤其显示出皇帝对会见班禅的礼仪和随员的极度注重。“大皇帝在历代皇帝举行登基大典的保和殿会见班禅大师,盛宴款待,章嘉国师也参加宴会。大皇帝传谕:‘班禅大师可以乘轿到此殿的第三道台阶,章嘉国师可以坐轿到第二道台阶。’”紧接着,确吉尼玛还写道:“保和殿系历代皇上举行登基大典之殿,休说有天下其他哪个贵人坐轿进殿,他们不经召见连进入院内也不可能。”(22)
我们从满文档案目录中提及的内容中可以看出,清廷非常重视班禅随员身份以及人数的清点。在清廷主持的仪式和宴请等场合,不管是随从人员的身份,还是确切的人数,清廷都派专人负责,逐一清点,并落实。而满文档案中也多次提到清点召见和赴宴人数,确保无误等事宜。对照《六世班禅传》以及清廷对入宫人员的严格控制和清点,他所描述的自己身临其境的经历实在有太大的出入。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当时在承德避暑山庄的万树园内,普林格尔很可能会被当作六世班禅的侍从,被招来回话。
语言交流上的困难则是通过推理而得出的。作为清朝皇家的子弟,乾隆皇帝自小通满文和蒙文。在六世班禅来京师之前,乾隆帝随章嘉国师学会了简易的藏语日常对话。《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记录了乾隆帝对六世班禅说的一段话:“朕以前不会说藏话,为了你的到来,朕赶紧向(章嘉)胡图克图努力学习日常用语,但是不够熟练,有关教法的词语,可请胡图克图担任翻译。”(23)章嘉国师通藏文和蒙文,因此,班禅和乾隆皇帝见面,每次都有章嘉国师在旁陪同,他们的对话几乎全得由章嘉国师用藏语或是蒙语释义。
如若普林格尔真的被招来答话,他也许说的是兴都斯坦语,经班禅翻译成藏文,而由章嘉国师译成蒙文,然后传达给乾隆皇帝。或者,普灵林格尔也很可能懂藏语,因为他毕竟在西藏生活了很长时间,不过这同样得由章嘉国师帮忙翻译,给乾隆帝解释。不管怎样,当时在热河万树园看戏的大场景中,实在难以想象整个对话过程是怎么进行的。
根据班禅在热河的行程的安排,并对照六世班禅的传记对这次重要会面的描述和普林格尔本人的记录,陈庆英和王晓晶提出这么一个疑问,即“当时乾隆帝与(班禅)大师的宝座有三个阶梯高,浦南吉尔(即普林格尔)作为无头衔的大师随从,只能排在较后位置,再加上当时的表演声音,是如何听清大师与乾隆帝交谈的内容的?”(24)如何亲自介入这场有关印度斯坦的对话确实成了一个大问题。不管是从清宫礼仪和语言交流的角度,还是从当时场面的设置,对这场听起来妙趣横生的对话,我们不能不产生疑问。
由此看来,普林格尔在班禅和乾隆会见的场所就座的真实度并不高。乾隆皇帝问询有关兴都斯坦的问题时,章嘉国师在座。有可能是班禅招呼普林格尔过来,作一简短的回答,仅此而已。总之,班禅进京一行不仅没有引起清廷对印度的兴趣,也没有增进双方的相互了解。兴都斯坦的存在并没有引起清廷官方的起码的关注。(25)这或许能解释为何普林格尔紧随班禅进京朝觐,而官史缺乏记载的原因。
正如六世班禅和清廷的交往得完全通过章嘉呼图克图颇具外交手腕和文化背景的周旋和协调一样,六世班禅进京之际,来自东印度公司的普林格尔终未发挥东印公司总督所期望的作用。而一向开放、擅长政治和外交策略的六世班禅也不幸在京城病死于天花。即使普林格尔书信中有关乾隆帝会让班禅捎信给东印总督的所言所记为实,终将无法兑现。
凭借六世班禅这一宗教领袖的巨大影响,以西藏为桥梁来和清廷建立关系是18世纪后期东印度公司在东亚的计划。由于双方缺乏起码的了解,这看似一个合情合理的外交和贸易举措却只能成为一厢情愿的计划,而到头来不了了之。这一结果归根结底并不归咎于六世班禅或是普林格尔。真正的问题出在东印总督哈斯汀士,在缺乏起码的了解和交流的情况下,对自己的宏大计划过于乐观,期望过高,并且觉得有班禅帮忙,事成肯定有望。因此也就难怪作为东印公司的信使和派员,普林格尔会写下如此这般栩栩如生的记录而载入特纳的游记。
三、东印度公司对西藏和清廷的了解
根据现有的史料,我们可以肯定的是18世纪后半期六世班禅和清廷保持密切的关系的同时,他也曾通过书信来往和人员互访与东印度公司有过相当频繁的交往。与清廷交流时,六世班禅以章嘉国师为中介,而与东印度公司的联系,他则离不开普林格尔的效忠。
对东印度公司来讲,这种来往目的相当明确,即通过西藏来打开中国的商贸市场,以解救濒临破产的东印度公司。而对六世班禅来讲,西藏和印度宗教文化本就同源,而他的个性,教养和独立而又强大的政治地位都促成了他和周边地区的密切联系。
从波格尔写给哈斯汀士的报告中,我们可以知道,波格尔在扎什伦布寺的所见所闻所感大大充实了原来仅仅从书信中得到的信息。原来他一直认为,八世达赖喇嘛尚幼,六世班禅总管西藏的政教决策。而到了扎什伦布寺之后,他不仅了解到摄政在拉萨执掌西藏政事,而且当他从班禅那里得知外邦人士进入西藏尚需通报清朝皇帝时,颇觉惊奇。后来从班禅的言谈中,他才渐渐明白西藏的行政体制隶属于清廷。
虽则如此,波格尔依然认为,班禅在西藏的政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还写到,班禅曾对波格尔提到通过章嘉国师的中间关系,他们帮哈斯汀士和乾隆皇帝取得联系,并能准许波格尔进京。这一承诺似乎在普林格尔的笔记里乐观、积极的语调和内容中得到印证。因此,波格尔认为,虽然班禅实际上并不统领西藏,而且诸事均得上报清廷,但是凭借他的势力和影响,他可以帮我们达到和西藏和清朝建立商贸关系的目的。这就不难解释为何在所有的史料中,唯有普林格尔写下了班禅和乾隆皇帝之间如此详尽和生动的对话。无疑,他想传达的是他随班禅东行朝觐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建立东印度公司和清廷之间的关系。
当然,这些记录都是经由中介转达的,或多或少夹杂着个人的主观臆想和猜测,还有含有相当的夸张的成分在内。六世班禅深知驻藏大臣和拉萨的摄政对外邦人入藏的顾忌,所以对英文史料中提到的他曾答应波格尔把哈斯廷士介绍给乾隆皇帝的说法,我们不能不产生怀疑。同样,我们难以完全相信普林格尔记录在案的他亲自介入其中的乾隆皇帝和六世班禅那场有关印度斯坦和东印度公司总督的对话。
从现有的史料来看,东印度公司的动因和想法显而易见,但是对班禅处理前后事宜的意向,我们实在不得而知,也不能妄加揣测。虽然受东印公司之托,班禅趁进京的机会为东印度公司出面和乾隆皇帝商谈此事最合适不过,但是东印度公司对班禅此行的期望实在过高,远远超越了六世班禅的宗教角色和这次进京朝觐的历史背景和目的所有容纳的范围。通过章嘉国师帮忙来建立乾隆皇帝和东印度公司总督的交往关系都只是一厢情愿的事情。正如马世嘉提出的,“如若真有的有过这场对话,那么这只是宴会或是茶歇之际的一场闲聊而已,远远不足以在清朝的官史或是藏文的传记上记录在案。”(26)
四、结语
18世纪后半期,班禅和东印度公司的派员虽有过跨国界、跨区域、跨文化和跨语言的交流,但是他们之间的相互了解毕竟才刚刚起步。要说起东印度公司对西藏的了解,其实充其量只是来往的书信和波格尔在扎什伦布寺寓居的经历,而他们对清廷的了解就更是微乎其微了,更何况是有关西藏和清廷之间微妙而又复杂的关系。汉文资料、英文资料和藏文资料对这一事件或多或少作过介绍,但是却未能详细地反映18世纪末西藏和周边地区交往的总体的画面。这种史料上的断裂或许正是这种相互了解和交流的断裂的一种反映。当时跨喜马拉雅山脉的这种接触和交流毕竟只能算是“早期全球化”的一个侧面。(27)
值得学者们关注的是18世纪末史无前例的跨国和跨地区之间交往在很多区域产生。为了走出财政困境,打通东亚的贸易渠道,东印度公司从印度向周边的地区发展,喜马拉雅山脉都挡不住他们要打开西藏和中国市场的迫切愿望。无独有偶,在东边,我们有朝鲜使团频频来访北京,朝鲜学者和汉学家之间的密切交往和学术交流是从未有过的,(28)更有英国访华使团和西藏喇嘛贵族进京的记载。以葛兆光的话来说,这无疑说明这一时期已形成了一种“早期全球化”的现象,为19世纪的暴力冲突和正面接触埋下了一个深深的伏笔。
在这么一股“早期全球化”的潮流中,诸多事件和各种交流的契机也把西藏纳入了这种开放的、流动的商贸和外交关系之中。其实,18世纪后半期的西藏并非与世隔绝,具有开放眼光的六世班禅和清朝的盛世使这种交往成为可能。可是,1788—1792年间尼泊尔和西藏之间的两次大规模的廓尔喀战争促使清廷紧紧地关闭了西藏的西大门。从此,这种封闭的状态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
即便诸多历史细节和一些记载的准确性仍然值得我们继续证实和研究,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细节和历史事件所反映的18世纪末的那种“早期全球化”的大趋势。英国不仅打开了印度的门户,而且垄断了印度与邻国的贸易。作为近邻,西藏也被纳入了东印度公司开发市场的大计划之中。从18世纪后半期东印公司企图通过西藏打开中国市场的历史事件来分析当时西藏和清廷在跨国界交流中的互动,我们会对当时西藏和清廷的关系有更深的理解。
18世纪后半期,东印公司与西藏进而与清廷的交往刚刚开始,彼此的了解自然都非常有限。而随着90年代西藏大门的关闭,东印度公司穿越喜马拉雅山脉的宏大计划终未能实现,这一地区的“早期全球化”的交流自此也告一段落。东印度公司从此放弃了从西藏进入中国内地,而后打开庞大的中国市场的初衷。他们转而以广州的通商口岸为基地,用坚船利炮从沿海地区打开中国的贸易大门。六世班禅和东印公司的短暂交往或许还能从一侧面解释鸦片战争在东部沿海爆发的部分历史缘由。
注释:
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承德市文物馆合编:《清宫热河档案》[Z](4)和《清宫普宁寺档案》[Z](1),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丛刊。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
②《清史录》[Z],卷1111,页4上。
③《清实录》卷1122,页9上—10下。《西藏研究》编辑部编:《清实录藏族史料》[Z],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991—2992页。
④石滨裕美子:《1780年班禅喇嘛和乾隆皇帝会见的本质的意义》,《西藏佛教世界的历史的研究》(日文原版),东京东方书店,2001年,第321—361页。
⑤Luciano Petech,The Missions of Bogle and Turner according to the Tibetan Texts in T’oung Pao,XXXIX,1949,pp.330—346.
⑥毕达克在文章的脚注中指出,说是自传,其实并不准确。其实这是六世班禅著作全集的第一卷,记录和罗列了喇嘛一生参加的重大宗教和世俗事务。同上,第332页。
⑦同上,第341—342页。
⑧陈庆英、王晓晶:《蒲南吉尔考—从〈六世班禅传〉解读》,“八世纪至十五世纪中部和西部西藏艺术和文化史会议”论文,维也纳,2011年4月5日—9日。贡觉·晋美旺布:《六世班禅白丹益喜传》[M](藏文),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第1090页。
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六世班禅朝觐档案选编》[Z],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第192页、212页、221页、230—231页、233—34页、241—43页、289—90页和第292页。
⑩Clements Markham,Narratives of the Mission of Goerge Bogle to Tibet,and of the Journey of Thomas Manning to Lhasa,London:Trübrier and Co.,1876.克莱门茨·马克姆编著,张皓,姚乐野等译,石硕,王启龙校:《叩响雪域高原的门扉:乔治·波格尔西藏见闻及托马斯·曼宁拉萨之行纪实》[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Samuel turner,An Account of an Embassy to the Court of the Teshoo Lama in Tibet,New Dehli:Asian Educational Services,1991.
(11) 六世班禅和哈斯汀士的通信通常用的是波斯语。笔者手头没有六世班禅被译成波斯文的通信,但是廓尔喀战争期间他们之间的通信尚存完好无损。见迪斯卡尔卡的论文,曾被中外学者广为引用。D.B.Diskalkar,“Tibeto-Nepalese War,1788—1793”,in Journal of the Bihar and Orissa Research Society,Vol.XIX-IV (1933),pp.355—398.
(12)Schuyler Cammann,Trade through the Himalayas:The Early British Attempts to Open Tibet.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1.
(13)同上,第145—146页。
(14)Kate Teltsher,The High Road to China:Goerge Bogle,the Panchen Lama and the First British expedition to Tibet,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06.
(15)Matthew W.Mosca,Qing China’s Perspectives on India,1750—1847,Harvard University Ph.D.Dissertation,2008.
(16)Samuel Turner,An Account of an Embassy to the Court of the Teshoo Lama in Tibet,New Dehli:Asian Educational Services,1991,pp.457—473.
(17)Clements Markham,Narratives of the Mission of Goerge Bogle to Tibet,and of the Journey of Thomas Manning to Lhasa,London :Trübner and Co.,1876.
(18)丹津班珠尔著,汤池安译:《多仁班智达传—噶锡世家纪实》[M],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年。其中曾记载了六世班禅来访噶锡庄园时和多仁班智达有关儿子教育的一场妙趣横生的对话。见第63页。书中此类例子多处可见。
(19)Wang Xiangyun(王湘云),Tibetan Buddhism at the Court of Qing :The life and work of lCang-skya Rol-pa’i-rdo-rje,1717—86,Harvard University Ph.D.dissertation,1995.“The Qing Court’s Tibet Connection:Lcang skya Rol pa’i rdo rje and the Qianlong Emperor,i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60,No.1,pp.125—163.
(20)Gaur Das Bysack,“Notes on a Buddhist Monastery at Bbot Bagan in Howrah”in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1890,Vol.59.No.1,pp.50—99.
(21)Schuyler Cammann,Trade through the Himalayas:The Early British Attempts to Open Tibet.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1,p.74.
(22)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著,陈庆英和马连龙译:《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348页。
(23)同上,第39—350页。
(24)陈庆英、王晓晶:《蒲南吉尔考—从<六世班禅传)解读》,第10—12页。
(25)Matthew W,Mosca(马世嘉),Harvard University Ph.D.Dissertation,2008,p.209.原文如下:“There is evidence of other Hindu priests or other Indians in the Qing Empire in the 1700s,but they seem to have had virtually no influence on contemporary understandings of India.”
(26)Matthew W.Mosca ( 马世嘉),Harvard University Ph.D.Dissertation,2008,p.516.原文如下 :“Tibetan records were more detailed,especially about spiritual matters,but as Puringar made clear both alleged discussions took place during moments of idleness,at a banquet and over‘ refreshment of fruit’.It is plausible that this‘table talk’,neither formal court business nor spiritual exercise,did not merit notice by either Qing or Tibetan chronicles.”
(27)葛兆光:《文史研究新视野》[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第34页。
(28)孙卫国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演讲,"Collecting,Annotating,and Analyzing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Chinese and Korean Scholars in the Qing Period",2010年8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