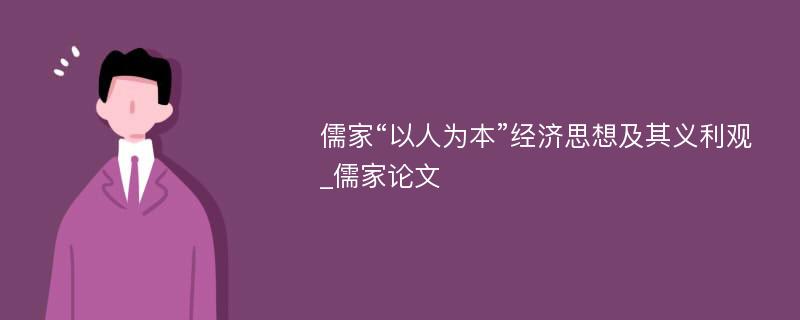
儒家“民本”经济思想及其义利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义利论文,民本论文,思想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 —5117(2000)04—0083—03
儒家“言义”,也“言利”,因而在儒家学说中,既包括伦理道德方面的内容,也包括社会经济思想方面的内容。然而,与其它学派不同的是,儒家经济思想不是从财富增值或理财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而是以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定和谐为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惟其如此,儒家经济思想也就更具生命力,值得我们去探讨与思考。
一
在君、国、民的关系问题上,儒家主张以民为本、以国家社会为重。孟子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1](《孟子·离娄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而为大夫。[1](《孟子·尽心下》)这里, 孟子提出了一条十分简单而又深刻的道理,即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而要得民心,最主要最根本的就在于解决人民的生计,满足人民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基本需要。“若民……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1](《孟子·梁惠王上》)因此,统治者“政之急者, 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2](《孔子家语·贤君》)
儒家强调以民为本,主张“富民”,表面看来,与统治者的利益是大相径庭的。对此,孔子的看法是,只有人民富裕,国家才会富强,君主的统治才会得到巩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3](《论语·颜渊》)荀子直接了当地说:“下贫则上贫, 下富则上富”[4](《荀子·富国》)统治者应“因民之所利而利之”[3](《论语·尧曰》),而不可与民争利。儒家甚至将那些能为统治者聚敛财富的“良臣”斥为“民贼”。“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工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1](《孟子·告子下》)如果统治者不顾人民利益, 任意搜刮社会财富以充实府库,追求所谓的“富国兵强”,其结果必然会导致统治地位的丧失,就必然使百姓“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饥年不免于死亡。”[1] (《孟子·梁惠王上》)而统治者本身“暴其民甚,则身杀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1] (《孟子·离娄上》)从而将民之贫富与国之衰强、君之危安有机地辨证统一地结合在一起,也更容易为统治者所接受。
那么,统治者应该如何使人民富裕呢?首先,儒家认为君主应施“仁政”,“正经界”让百姓有田可耕。“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1](《孟子·滕文公上》)也就是说, 既要使百姓服务于统治者,为统治者创造财富,同时又要给他们一定数量的生产生活资料,使百姓家家拥有“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则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1] (《孟子·尽心上》)“方里而井”与“百亩而田”,表面看来似乎是儒家为了恢复西周王朝时期的旧制,是一种不合时宜的理想模式,但实际上其实质在于使人人有田耕、户户足饱暖,而不在于形式。其次,统治者应“以政裕民”,省刑罚、薄税赋。荀子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为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余若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藏之。夫君子奚患乎无余。故知节用裕民,则必有仁义圣良之名,而且富厚丘山之积矣。此无他故焉,生于节用裕民也。不知节用裕民则民贫,民贫则田瘠以秽,田瘠以秽则出实不半。上虽好取侵夺,犹将寡获也。”“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勿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夫是之谓以政裕民。”[4] (《荀子·富国》)但是,儒家也不是认为赋税越轻越好,而应有一定的标准,因为赋税是“养君子”所必需的。而这个标准,在儒家看来以十取一最为合适。“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5] (《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1] (《孟子·告子下》)赋税过轻,不能够维持国家财政支出,无以“养君子”;而赋税过重,则是夏桀的暴政。可见,儒家的上述主张,不是主观提出来的,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二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封建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勃兴,社会贫富分化也日趋严重。董仲舒说:
“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民财内足以养老尽孝,外足以事上共税,下足以畜妻子极爱,故民悦从上。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又颛山川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6](《汉书·食货志》)
不仅如此,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和解体,也对社会政治秩序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和破坏,形成了“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同乐”的社会俗尚。在沧桑巨变之中,儒家一方面举起“周礼”的大旗,呼吁“克己复礼”另一方面,又从解决社会财富的分配入手,提出了其经济均平思想。
孔子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3] (《论语·季氏》)董仲舒对此解释说:“故有所积重,则有所空虚矣。大富则骄,大贫则忧。骄则为暴,忧则为盗,此众人之情也。圣者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之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7] 因此,在儒家看来,只有解决了人民的生计问题,消除大富大贫现象,才会使社会安定和睦。
其实,儒家的经济均平思想并非是以往人们所认为的绝对平均主义,而是在维护“礼”——等级秩序前提下的一种经济分配主张。“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也。……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8](《礼记·中庸》)“礼”体现在对土地的占有上, 即“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8] (《礼记·王制》)体现在爵禄上,即“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禄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禄,君十卿禄。”[8] (礼记·《王制》)体现在消费上,就是“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4](《荀子·王制》)由此我们不难看出, “礼”在儒家的心目中,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政治伦理概念,而且也是其社会经济均平思想的重要体现。
三
“重义轻利”是儒家经济思想中最具影响力的道德伦理准则。孔子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3] (《论语·里仁》)“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3] (《论语·述而》)也就是说,追求富贵是人的一种本能,实无可厚非,但追求富贵必须遵守道义,必须合乎一定的道德伦理规范。否则,“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3](《论语·述而》)可见, 在义和利的关系问题上,儒家主张义是第一位的,利是第二位的;义对利具有普遍性的制约和限制作用。
儒家主张人们追求经济利益的行为必须要符合道义,无论是国君、官吏还是平民,都不例外。然而,在具体要求上,却不完全一致。就国君而言,儒家要求只言义而不言利。因为,国君乃天下财富的最高所有者,“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滨,莫非王臣。”[9] (《小雅·北风》)因此国君应以道义治国,即行“仁政”。因而《礼记·大学》主张:“为人君,止于仁。”“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国君的利就是义,就是“仁”。孟子则结合当时的社会实际,从君主对义利的态度趋向及由此而引起的一系列严重后果,阐述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则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1] (《孟子·梁惠王上》)其中,“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一语,足令君王们闻之心惊而望利却步。
对于各级官吏,儒家则不仅言义,而且也言利。因为,官吏主要是依靠君主的俸禄来养家糊口的,因此,“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地。”[1](《孟子·滕文公下》)“仕非为贫也,有时乎为贫。”[1](《孟子·万章下》)然而,官吏求“利”也必须要合乎道义,即“不食于力,不动于末”。因为,在儒家看来,官可以享受俸禄,农可以耕种土地,商获取利润,工匠获得工费,应该各有所得而各养其家,而不可夺他人之利。所以,孔子才说:“君子不尽利以遗民。诗云:‘彼有遗秉,此有不敛,伊寡妇之利。’故君子仕则不稼,田则不渔。”[8] (《礼记·坊记》)董仲舒解释说:“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缚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者,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有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6](《汉书·董仲舒传》)
对于一般的社会平民,儒家主张要求利、致富,但同时又要为他人着想,“富而好礼”,富而好仁。孔子与弟子子贡有过这样一段对话:“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3] (《论语·学而》)可见,在孔子看来,“贫而乐,富而好礼”才是人们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前提下应达到的精神境界。但是,孔子也深知“利”对人的诱惑力是十分强烈的,即使有较高修养的人也难免在“利”的诱惑下而丧失理智和道德,故孔子不仅选择了贫穷一生却“乐道”的颜回为其弟子的表率,而且也尽量不“言利”。对此,朱熹倒有比较深刻的理解,他说:“这‘利’字是个监界鏖糟的物事。
若说全不要利,又不成特地去利而就害;若才说著利,少间便使人生计较,又不成模样……缘他是个理外牵连底物事,才牵着这一边,便动那一边,所以这字难说……利最难言。利不是不好,但圣人方要言,恐人一向去趋利;方不言,不应教人去就害,故罕言耳。”[10]可见,孔子“罕言利”非真“罕言利”,而是一种无奈中的“难言”。
儒家的“富民”主张和社会经济均平思想,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儒家的社会政治主张和理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的要求和愿望。儒家企图依靠道德的约束力来制约人们的贪欲,进而实现“大同”的社会,显然是行不通的。但是,儒家社会经济思想及其义利观,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今天,对我们进行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却也不乏一定的借鉴意义。
收稿日期:1998—12—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