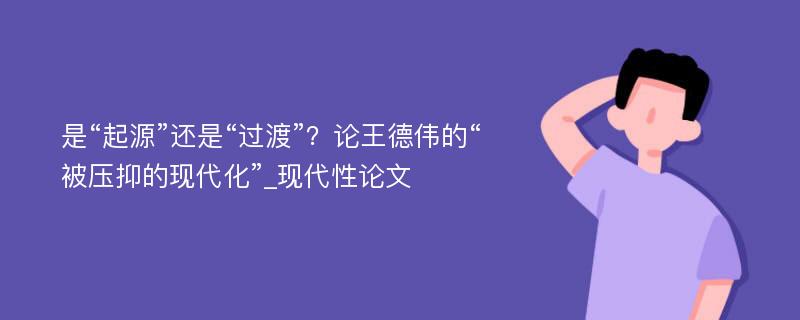
是“起源”,还是“过渡”?——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刍议论文,现代性论文,起源论文,王德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文学创作景象与文学史书写的混淆 第一次见到“被压抑的现代性”的说法,还是读王德威教授的《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一书。该书是王德威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本学术著作。时隔七年,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在大陆出版。王德威在书中详细阐释了“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缘由。从此开始“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说法,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传播流行起来,至今仍余音未绝。 在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界通常是把“五四”文学革命作为“新文学”的正式开端。尽管在晚近出版的一些文学史中,已经在强调“五四”新文学在“变革”中国文学中起决定性作用,也开始注意到“五四”新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之间的关系了,“文学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又存在着紧密的承续关系,所谓古典与现代、新与旧,难于做一刀切的划分”①。但是,这种“温和”地对待“五四”与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的做法,显然是不能令王德威满意的。他不能认同我们只是把晚清的文学看作是从传统文学到现代文学的“过渡”。在他看来,中国“新文学”的起源在“晚清”而不是在“五四”,“晚清时期的重要,及其先于甚至或超过‘五四’的开创性。”② 其实,在王德威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之前,就已经有学者开始重视晚清文学对“新文学”的重要意义了。陈平原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中就将“新小说”作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开端。在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等人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中,也包含了将“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贯通的努力尝试。但是,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中,他们的重点并不在于贯通“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他们关注的是“由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走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它关注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世界向度”,它更注重中国现代文学向“世界文学”融入的“现代化”努力,它把晚清或近代文学看作是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过渡”;而在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的相关论述中,瞩目的则是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中的“传统向度”,把晚清视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起源”。 “注重进程,消解大家”是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中所采取的一种文学史叙述策略,只不过是他将关注的目光转向了“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向度”——晚清文学。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一书中,借用丰富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知识,对晚清小说的四大文类进行了精彩的解读与分析。但是,我们看到,王德威的分析论述的焦点,主要并不在这些晚清小说是如何体现了“现代性”审美的要求上。他更在意的或者更想说明的是在“五四”新文学的理论倡导以及此后的文学史书写中,是如何完成了从“众声喧哗”的晚清到“五四”以后的唯写实主义独尊的转化。他在揭示这种“转化”完成过程时,将造成“窄化”了多元共生的晚清文学的原因,归结为“五四”以后日益“激进”的社会政治。正是在这种激进政治的规训之下,“‘五四’文学革命已缩小成‘革命文学’的紧箍咒了。我们的确见到了一种新形态的文学,但这种文学多半围绕着意识形态打转,没有什么革命精神可言”④。激进的政治还通过各种论争、批评乃至批判运动,将各种写实主义之外的文学题材和文学实验,都规训到写实主义的旗帜之下。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王德威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就是对以写实主义为文学典律的新文学史的一次颠覆与重构,它也是一次“重写文学史”的实践。 王德威的这次“重写”,将中国新文学的源头移至晚清,颠覆了“五四”作为中国新文学“开端”的历史地位。为此,一些学者也表达了与王德威的不同意见,在他们看来,“五四”作为新文学“伟大开端”的地位是不能动摇的。“五四”是新文学的“开端”,而不是“收煞”。在笔者看来,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命题,是从两个层面而言的,一个层面是从文学创作论,一个层面则是从文学史书分析。王德威的文风恣意,夹叙夹议,从文学创作到文学史编撰辗转回旋,其论述的两个层面的问题不知不觉间就被纠缠起来了,混淆了文学现象与文学史书写之间的界限。就文学创作而言,“五四”没有压抑晚清,王德威所言的晚清小说的四大文类,在“五四”以后仍然“兴盛不衰”⑤。仅就文学的受众而言,通俗文学作家并不逊色于新文学作家,甚至他们的读者比新文学的读者还多。但是,与新文学倡导者相比,通俗作家就缺少话语权罢了。所以,刘纳就指出:“如今问责‘五四’者……往往混淆了文学史与文学史叙述,将窄化了的文学史叙述作为批评链条原点——‘五四’的依据。《被压抑的现代性》指认‘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愈趋僵化’,透露出其对‘五四’的反思也肇于逆向关照的运思逻辑。”⑥在笔者看来,王德威在此论述的重点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是论及了晚清文学的丰富与多元,但是他的重点似乎不在晚清的创作,而在晚清以来的尤其是所谓唯写实主义独尊的“文学史书写”。在王德威看来,“五四”新文学为“写实主义”独尊,现代中国作家也多肩负着沉重的历史使命。这种强烈的人道主义和写实主义情怀,让现代中国作家对于那些“启蒙”文学之外的文学形式失去了兴趣。这也极大地削弱和窄化了晚清以来形成的“众声喧哗”的文学趣味和文学景观。正因为此,王德威才说:“如今端详新文学的主流‘传统’,我们不能不有独沽一味之叹。所谓的‘感时忧国’,不脱文以载道之志;而当国家叙述与文学叙述渐行渐近,文学革命变为革命文学,主体创作意识也成为群体机器的附庸。文学与政治的紧密结合,是现代中国文学的主要表征,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却不必化约成如此狭隘的路径。”⑦在此王德威委婉地把晚清以来文学窄化的原因,与“感时忧国”的政治使命与情怀连接起来了。我们都知道,历史就是一种叙述,而叙述的背后是隐含着权力、政治相关的历史观及价值观等因素。王德威批评“五四”以来的“写实主义”窄化了晚清的“丰富”,其实质还是批评主宰文学史书写的政治与权力。由此可见,王德威是通过对“五四”以来的文学史书写的否定性批评,来否定“五四”以来的文学创作。 二、被“先锋”理论放大的晚清文学“现代性” 王德威关于晚清文学现代性的相关论述,是受到了“在中国发现历史”思维的影响,他反复辩难“五四”确立起来的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是如何受到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但是,王德威在反驳“五四”奉行的“西方中心论”的同时,“他针对于此建立起来的新的叙事”亦不能免除“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⑧我们在上文中已经指出,与钱理群等人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中对新文学的“世界向度”瞩目不同,王德威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其瞩目的是新文学的“传统向度”,套用一个说法也可以说王德威在意的是新文学的“中国向度”。但是,无论是钱理群等人对于“世界向度”的关心,还是王德威对于“中国向度”的在意,他们关心的问题仍是共同的,即现代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他们的差异,只是表现在他们的思维方式和问题的聚焦点上。一般认为,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分为两种类型,即“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和“后发外生型现代化”。⑨普遍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模式是属于“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也称为“冲突—反应”模式。钱理群等人关心的“世界向度”,其思维的基础就是“冲突—反应”模式,而王德威强调的“中国向度”,其思维基础并不完全来自于“早发内生型现代化”模式的启发,更多地倒是可以看作是对“冲突—反应”模式的一种修正,即对于“现代性”的抵抗也可以产生一种有别于“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性”,这与柯文所言的“在中国发现历史”是存在着一致性的。 王德威有着深厚的理论素养,他借助大量的理论资源,对于晚清小说做出了细致分析。在这些分析中尽显其肆意飞扬的文采,雄辩的理论阐释,纵横古今的文学史视野。王德威在分析晚清小说时,使用了大量的理论资源,这其中不乏一些“先锋”理论。尽管他的文本分析解读非常精彩,但是他得出的一些结论,恐怕还是很难为一些晚清小说文本所“承受”。比如他在谈及民国时期欲望化政治时说:“民初女作家借写作抒发对爱欲的追求,曾经震骇多少卫道士,而她们也被视作放荡女子也就不足为奇了。富于反讽意味的是,尽管狭邪小说中的女性角色多是一些花柳之人,但她们依然间接预示了‘新女性’感情与行为的先进姿态。”⑩从烟花柳巷中看到了“五四”新女性的“雏形”,排除道德上的“偏见”,王德威的这样解释实在是牵强过分。在王德威的书中,类似这样的类比、对比仍有许多。在王德威看来,从梁启超的“新小说”中蕴含了“不可思议之力”(11)开始,一直到鲁迅的“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12),他们都无疑是地道的“文以载道”的信徒,他们秉持的都是启蒙主义的文学立场。他们一面将文学看得很“重”,一面又将文学看得很“轻”。“重”与“轻”是同一话题的一体两面。“重”着眼在他们用文学改造人心,变革社会,将历史的重任放置在了文学的肩上;“轻”就表现在他们对小说的拥护仅止于变化一般大众的气质心态。(13)但是,将文学看得如此之重,可能是这些启蒙主义者的一厢情愿。作者与读者,精英与大众之间的鸿沟与歧途,一再重现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之中。而“新小说”的创作则是步履维艰,从开始严肃探讨家国大事的道德文章,滑落至描绘诲淫诲盗的轻薄戏文。这也难怪梁启超在《告小说家》中会发出这样的感慨: 然则今后社会之命脉,操于小说家之手者泰半,抑章章明甚也。而还观今之所谓小说文学者何如?呜呼!吾安忍言!吾安忍言!其什九则诲盗与诲淫而已,或则尖酸轻薄毫无取义之游戏文也,于以煽诱举国青年子弟,使其桀黯者濡染于险诐钩距作奸犯科,而摹拟某种侦探小说中之节目。其柔靡者浸淫于目成魂与窬墙钻穴,而自比于某种艳情小孩所之主人者。于是其思想习于污贱龌龊,其行谊习于邪曲放荡,其言论习于诡随尖刻。近十年来,社会风习,一落千丈,何一非所谓新小说者阶之厉?(14) 然而,就是从晚清“新小说”的衰败所带来的文学创作的“乱象”中,王德威发现了晚清小说的“现代性”。王德威将晚清小说中大量存在的“腐败”、“腐朽”、低迷之象,与晚清政府的昏聩无能、摇摇欲坠的政治统治并置在一起进行解读。通过这种互文式的文本解读,他发现了晚清小说带给我们的“启蒙”——现代性。晚清小说的“启蒙”与“五四”新文学的启蒙,是截然不同的。在王德威看来:“晚清小说的现代性既不表现于严复心目中的载道理论,也不表现于梁启超的末世想象;它其实是由严复及梁启超所贬抑的‘颓废’气质中迂回而生的。”(15)这种颓废的文学观不仅表征了晚清社会的乱象与败局,而且也以戏谑的方式对晚清的时局展开了反讽性的批评。在王德威看来,梁启超等人将“无用”的小说,赋予了“大用”的使命之后,文学审美与社会启蒙之间的界限已然被打破了,这种对文学自身功用缺少自制的理解,构成了颓废文学观的一个标志。除了颓废的文学观以外,王德威还认为,晚清作家在文学叙述形式上所采取的“放肆”的态度,他们用戏仿、戏谑等方式对中国传统文学的主题进行“改写”。这种“放肆”的改写,也构成了王德威所言的“现代性”。所以,王德威才会对晚清文学中的狭邪小说,给予较高的评价。他一反鲁迅等人对于晚清狭邪小说内容“不道德”的批评,认为这些狭邪小说中表现的才子、妓女、身体、性别问题(同性之恋,异性之恋),以“无所顾忌的欲望潜能可以被用为反抗权威的激素(而未必是反抗权威的行动本身)。个体的解放可以被视为集体解放的前提(而未必是集体解放的结果)。”(16) 王德威之所以会对晚清小说做出“超文本”的“过渡阐释”,其主要目的还是想通过各种理论的“丰富意义”在晚清小说中得到验证,从而列举出晚清小说的“丰富性”与“现代性”。这种思维方式,与其说是发现晚清小说的“理论意义”,还不如说是借助对晚清小说的演绎分析,来验证某些理论的正确性与可适性。这实在是以“理论之思”骇文学之义了。 三、从“晚清”看“五四”:一种新的“二元对立” 以上的诸多论辩,都是从“五四”新文学的“起源”与王德威展开争论的。他们之间的分歧,就在于到底“五四”是中国新文学的开端,还是“晚清”是中国新文学的开端。然而,在有的学者看来,王德威提出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学术命题,已经超越了单一的“重写文学史”的“二元对立”思维。王德威是从“后现代”的批评立场出发,他消解的不仅仅是“五四”,“挑战的不是‘五四起源论’,而是‘起源论’本身。”(17)据说王德威是中文世界中,翻译福柯的“第一人”,他率先翻译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王德威将此书译为《知识的考掘》)。在王德威的字里行间,我们确实可以感受到福柯的影响。比如他对于“文学谱系”的强调,对于历史“连续性”的疑虑、对“主流”与“边缘”关系的辩证等等。但是,就此是否就可以像李扬那样认为,“被压抑的现代性”这个命题,不是一个“建构性”命题,而是一个“解构性”命题呢?在我们看来,王德威确实是用“晚清”解构了“五四”,在这个意义上,“被压抑的现代性”是一个“解构性”命题。他是“通过解构‘晚清’与‘五四’的二元对立来进一步解构‘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并进而质疑历史的进化论、发展论和方向感”(18)。王德威确实不像我们主流文学史所叙述的那样,把“晚清”看成是“五四”发展中的一个“过渡”,把“晚清”到“五四”看作是文学的进步与发展。这种进化论、进步论的文学史观,是他一直要进行质疑和致力拆解、解构的重要部分。然而,王德威提出“被压抑的现代性”的命题,远非止于李扬所言的“解构”。他是要通过对线性文学史观的质疑,进而对于“五四”文学的现代性“标准”提出质疑。在质疑“五四”文学的现代性“标准”的同时,他通过对晚清小说的解读,发现了开启于晚清的“另一种现代性的努力”。这也正与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不谋而合了。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德威并非像他所译介的福柯那样,是一个彻底的“解构主义”者,他的“被压抑的现代性”命题,也并不如李扬所言的那样,是要消解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是要消解文学的“起源论”。如果说,此前的文学史叙述是从“五四”看“晚清”,形成了一种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那么,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则是从“晚清”看“五四”,形成了一种“现代”与“狭隘现代”新的二元对立。在此,李扬与王德威一样,都有对文本的“过渡诠释”之虞。 ①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页。 ②④⑦⑩(13)(15)(16)[美]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宋伟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页,第37页,第5页,第72页,第31页,第32页,第73页。 ③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页。 ⑤范伯群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中指出,对通俗文学作家而言,“当务之急,不是去争领导权、争作中心、争当主流,而是争取读者。对职业作家来说,读者是上帝,是衣食父母,只要有广大的读者群,这些中国第一代职业作家就能在与知识精英作家的‘相克’中‘相生’……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通俗文学现代化‘百花齐放’的10年,是他们在知识精英作家的‘相克’中求得‘相生’的艰难与辉煌的历程。”见范伯群:《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绪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7页。 ⑥刘纳:《也谈晚清和“五四”》,《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2期;刘纳在另一篇文章中也指出,“讨论五四是否压抑了其后几十年间中国文学的多种可能性,必须区分文学史写作、文学史本身以及话语权与行政权。”她还指出“五四新文学不是空洞的概念,它由一个个作家一部部作品构成。每一个体认了新文学写作者身份的人分别作出关联着人生选择的文学选择。毕竟,那个时代的文学界并无行政管理者,没有什么权力机构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规定写什么和不许写什么,这样写和不许那样写。”见刘纳:《五四能压抑谁?》,《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1期。 ⑧冷露:《评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2期。 ⑨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00-1949),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3页。 (11)(14)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陈平原、夏晓红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0页,第510页。 (12)鲁迅:《域外小说集序》,《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76页。 (17)(18)李杨:《“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两种读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1期。标签:现代性论文; 晚清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王德威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