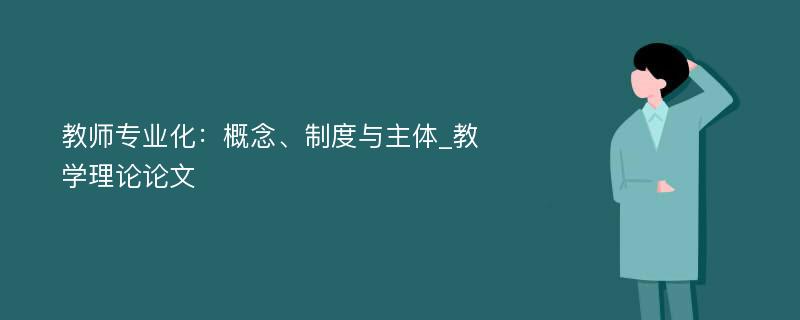
教师“专业化”:理念、制度、课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课题论文,理念论文,制度论文,教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国际教育界的教师“专业化”探索
学校教育的成功取决于三个要件:“硬件、软件、人件”。所谓“人件”就是教师的专业素养、教师的专业化程度。这是教育改革的重大主题之一,也是教师教育研究的核心课题。
(一)从历史发展看,教师教育体现了从“专业化”走向“反专业化”再到“专业化”的趋势。可以说,教育学的科学化与师资培育的“专业化”是18世纪启蒙运动与19世纪科学发展的产物。赫尔巴特科学教育学的确立和国民学校提升教师专业地位的努力,成为尔后美、法等国师法之典范。20世纪60年代以来,现代化运动席卷全球,社会科学中的实证主义主宰教育研究的各个领域,成为教育研究的主流。教师教育的“专业化”因而转向“技术化”。行为目标、能力本位、系统管理的课程设计与评估,教学技术的训练成为教师教育的核心焦点。“工具理性”主导了欧美各国的教师教育。20世纪7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过去现代化理性主义的科层管理转型为“小即巧”、“小即美”的后福特主义管理模式;过去专业主义所赖以发展的“基础主义”面临挑战。传统的课程受到“小班小校”、“微型课程”等等的冲击,基础学科衰落,注重现场经验。要求教师角色冲破学校与学科的框架,能够适应学生的需求与能力。教师教育从“技术化”迈向彻底的“反专业化”。面对提升教师素质的社会压力和“反专业化”的挑战,世纪之交欧美各国都在寻求教师专业理念与制度的重建。“全美教学与美国未来委员会”相继发表的两份报告书——《什么最重要:为美国未来而教》和《做什么最重要:投资于优质教学》就是一个信号。这些报告书勾画了美国21世纪新型的“卓越教师”的形象,强调“重新设计教师的专业发展”,“重建学校使之成为学生和教师的真正的学习型组织。”(注:[日]永井圣二:《教师专业职论再考》,《教育社会学研究》第43集,1988年第54页。)可以说,这些教师教育政策也许意味着在更高的层面上寻求更高程度的“专业化”。
(二)国际教育界关于教师“专业化”的探索交织着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撞,或者说,交织着这两种话语体系的解读。我国教育界更多关注的是现代主义(技术主义)范畴的“教师形象”,但后现代主义的“教师形象”也需要关注。
一般说来,教师“专业化”探索的主要方式是,从理论上界定什么是“专业”,给出衡量“专业”的标准,然后对于教师职业所具备的专业条件的情况作出理论性、实证性的探讨。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专业化”的发展成为时代“充满希望的信号”(注:陈永明:《现代教师论》(当代教师进修丛书之一),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70页。),教师“专业化”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绝不是孤立的现象,它受到整个社会职业的“专业化”浪潮的推动。据说,弗莱克斯纳(A.Flexner)是最早设定衡量专业程度指标的学者之一。(注:[日]奥田真丈主编:《现代学校教育大事典》,行政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398页。)在国际教育界广泛运用的,是利伯曼(M.Lieberman)定义的“专业”概念。他指出了所谓“专业”,应当满足如下的基本条件:(1)范围明确,垄断地从事于社会不可缺少的工作;(2)运用高度的理智性技术;(3)需要长期的专业教育;(4)从事者无论个人、集体均具有广泛的自律性;(5)专业的自律性范围内,直接负有作出判断、采取行为的责任;(6)非营利,以服务为动机;(7)形成了综合性的自治组织;(8)拥有应用方式具体化了的伦理纲领。(注:筑波大学教育学研究会编、钟启泉译:《现代教育学基础》,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442页。)可以说,这是一种结构一功能主义的界定,这个界定明示了作为“专业”的理想模型。
不过,围绕教师的专业属性问题的讨论,亦即教师职业究竟是“专业”还是“半专业”,主要有下列论点。第一个论点,构成教师专业属性的核心是教育的科学原理与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构成专业属性制核心的“学科教学法”的学术水准尽管不同学科有所差异,但总体说来低于其他专业的科学原理与技术。第二个论点,教师职务范围的明确化与合理化问题。教师的职业范围同其他专业相比,并不明确。亦即学校的教育服务同家庭、社区的教育分工不明确。第三个论点是自律性的问题。由于来自学校教育的公共性这一社会性质的制约和支配现实社会体制的公共政治、行政权力的压力,以及教师专业能力等种种因素的交织,在这些权力关系之中,“自律性”的范围是有限的。基干教师工作的这种复杂性、混沌性、不确凿性等等,不能像医生、律师、大学教师那样有确凿的专业领域的“知识基础”。就是说,只能把教师职业视为一种“半专业”、“准专业”(Semi-Profession),或是“中位专业”(Middle-Status Profession)。(注:[日]奥田真丈主编:《现代学校教育大事典》,行政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399页。)到了20世纪60年代,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于教师地位的建议》,描述了这种专业的特点:“教师工作应被视为一种专门职业。它要求具备经过严格而持续不断的研究才能获得并维持专业知识与专门技能的公共业务;它要求对所辖学生的教育与福利拥有个人的及共同的责任感。”(注:筑波大学教育学研究会编、钟启泉译:《现代教育学基础》,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443页。)不管怎样,教师职业同别的专门职业比较起来,成熟程度还是一个问题,需要紧扣教师工作特殊性作出教师专业属性的论证。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教师“专业化”的探索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在美国,围绕教师“专业化”的教师教育改革兴起了两大浪潮,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各国的教师专业化探索。(注:参见钟启泉:《教师“专业化”:涵意与课题》,《教育参考》1999年第4期,第36~38页。)第一浪潮以《国家处于危险之中》为起点,是自上而下推行的。其目标是追求教育的“卓越性”,实施教师“职能测验”,视学生的成绩支付相应的工资,由教育行政部门实施职务升迁制度。第二浪潮是以《准备就绪的国家——21世纪的教师》为起点,是自下而上推行的。其目标是追求教师的“专业化”,以教师的自律性为基础从学校内部推进有创意的改革。在这两次浪潮中,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意识到教育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教师。
美国卡内基财团组织的“全美教师专业标准委员会”倡导《教师专业化标准大纲》,这是一份迄今为止最明确地界定了教师“专业化”标准的文件,它明示了如下制定专业化量表的基本准则(注:[日]佐藤学:《教师:两难问题》,世织书房1997年版,第66~67页。):(1)教师接受社会的委托负责教育学生,照料他们的学习——认识学生的个别差异并作出相应的措施;理解学生的发展与学习的方法;公平对待学生;教师的使命不停留于学生认知能力的发展。(2)教师了解学科内容与学科的教学方法——理解学科的知识是如何创造的、如何组织、如何同其他领域的知识整合的;能够运用专业知识把学科内容传递给学生;形成达于知识的多种途径。(3)教师负有管理学生的学习并作出建议的责任——探讨适于目标的多种方法;注意集体化情境中的个别化学习;鼓励学生的学习作业;定期评价学生的进步;重视第一义目标。(4)教师系统地反思自身的实践并从自身的经验中学到知识——验证自身的判断,不断作出困难的选择;征求他人的建议以改进自身的实践;参与教育研究,丰富学识。(5)教师是学习共同体的成员——同其他专家合作提高学校的教育效果;同家长合作推进教育工作;运用社区的资源与人才。当然,也有人批评这些准则,突出了文化实践的属性,却淡化了社会实践、伦理实践、政治实践的属性,容易陷入心理学主义或是“教育中立性”。(注:[日]佐藤学:《教师:两难问题》,世织书房1997年版,第68~69页。)尽管这些局限终究以更广的视野界定了教师的专业属性,为形成教师“专业化”的社会共识和相应政策提供了基础。
不过,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倾听另一套话语系统——后现代主义的若干主张。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基于产业社会的学校教育不过是把人当作“工具”来塑造的冷冰冰的甚至是毁灭人性的装置,是以技术主义、操作主义、功利主义为特征的;而教师的“专业化”不过是应试产业中单纯的甄别调整的装置罢了。(注:[日]浅沼茂:《21世纪的教师形象》,《教育展望》2000年第1、2期合刊号,第19页。)21世纪的教育则是高举“人性”旗帜的教育,是一种充满爱心、平等对话的过程。它要求打破狭隘的教师“专业化”概念,强调教师作为“教育专家”的创造性侧面。教师不再是知识权威的代表,不再是以一种权威的姿态在课堂中“传道、授业、解惑”。知识权威不过是一种权力控制,必须解构。后现代的教师教育必须使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参与解构各种教育理论、教学理论政策报告、研究报告。就是说,后现代教师不再是权威的代表,而是一个解构者。在解构过程中与学生共同参与知识文化的建构与再建构。这样,过去教师教育课程所依据的教育理论、教学理论学生发展理论、学校制度理论,都必须重新探讨。
(三)从制度层面看,教师“专业化”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奋争过程。如果说美国教师“专业化”的观念与制度的确立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那么,日本也是同样。从战前绝对效忠天皇的“圣职论”,战后维护教师权益的“劳动者论”,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得到教育界公认的“专业职责论”,也经历了一个多世纪。在日本,从“专业化”观念的确立到制度的落实,又经历了20年的岁月。一般认为,1997年日本教员养成审议会的审议报告就是教师“专业化”观念在教育制度上的体现。这个文件突出了作为现代教师的使命感:保障学生的学习权。教师作为学生学习的指导者与建议者,只有立足于保障作为人权的学生的学习权与发展权的视点,才具有价值。就是说,教师专业成长的基础在于学生的权利——发展,学生不是教师专业属性的附属物。该文件还突出了造就现代“教师能力”的若干要点:作为教育者的使命感;深刻理解学生的成长、发展;对于儿童的教育爱;关于学科的专业知识;广泛丰富的教养;以及基于上述的教学能力——顺应种种教学方式的能力,适应个性差异的能力,从实践中学会教学的能力。(注:[日]八尾坂修:《当今所求的教师形象、所期待的教师形象》,《学校经营》2001年第6期,第10~11页。)这个思路值得我们借鉴。
不过,教育理念和教师教育制度的创新不过是实现教师“专业化”的一种机制、一种保障。教师职业要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专业”,尚待教育科学的发展。
二、我国教师“专业化”面临的挑战与课题
从国际教师“专业化”探索过程的大体回顾,可以看出,教师“专业化”的问题是既老又新的问题。何谓教师?教师应当怎样?必须怎样?——这些问题是任何时代普遍存在的永恒的课题,但另一方面,教师毕竟是社会的存在,往往是与社会同步发展的。因此,离开了现实社会停留于抽象层面,是难以把握我们所求的教师形象的。前者是教师的主体条件,后者是教师的社会条件。主体条件是理想的,社会条件是现实的。我们需要洞察当今中国所需要的理想的教师形象,把握教师队伍的现实水准,并求得从现实水准迈向理想境界的策略。这是一篇大文童,不是本文能够回答的。下面,仅从我国教师教育的现状,围绕教师“专业化”需要满足的三个条件——理性的教师形象的确立、教师教育制度的创新、教育科学的改造与发展,探讨我国教师“专业化”面临的挑战与课题。
第一个课题,教师教育理念尚待进一步到位。这表现在如何看待教师的“专业化”,什么叫“专业化”的问题上。教师的“专业化”存在两种模式。(注:[日]佐藤学:《教育方法学》,岩波书店1996年版,第137~139页。)一种模式是,技能熟练模式——一主张教师职业同其他专业职务一样,把专业属性置于专业领域的科学知识与技术的成熟度。认为教师的专业能力是受学科内容的专业知识、教育学、心理学的科学原理与技术所制约的。在这种模式中,“教学实践”被视为学科内容的知识与教育学、心理学原理与技术的合理运用。教师的专业程度就是凭借这些专业知识、原理技术的熟练程度来保障的。这样,教师进修的课程开发就是确定并组织有关教师职业的理论、原理、技术的“知识基础”。现行的教师教育的制度、内容、方法,可以说就是以这种现代主义的“专业化”为思想背景形成的。另一种模式是,反思性实践模式——认为“教学实践”是一种囊括了政治、经济、伦理、文化、社会的实践活动。这种模式中的教师的专业程度是凭借“实践性知识”来加以保障的。这里所谓教师的“实践性知识”,有这样五个特点。其一,它是依存于有限情境的经验性知识,比起理论知识来说缺乏严密性和普遍性,却是一种鲜活的知识、功能灵活的知识;其二,它是作为一种“案例知识”而积累并传承的;其三,它是以实践性问题的解决为中心的综合多学科的知识;其四,它是作为一种隐性知识发挥作用的;其五,它是一种拥有个性性格的“个体性知识”。这些知识是通过日常教育实践的创造与反思过程才得以形成的。同其他专业相比,教师工作的最大特点是不确凿性(混沌性),情境性,要求针对情境作出灵活应变的决策。是不是可以说,这是以后现代主义的“专业化”为思想背景形成的。
这两种模式反映了两种不同的话语系统及其所勾画的两种不同的“教师形象”,各有其合理性,因此构成了塑造未来“教师形象”的两难问题。问题在于,我们在探讨教师“专业化”的时候,缺乏对后一种“教师形象”的勾勒和后一种话语系统的支撑。多年来教师进修的内容大多停留于教育学、心理学基本原理的灌输,脱离了教师自身的教学实践的问题。教育界倡导“学者型教师”,这当然是不错的。但教育报刊的舆论不是去引导教师反思自身的教育实践,许多优秀教师却纷纷以树立某某教育理论为追逐目标,这无异于“缘木求鱼”。教育理论家所追求、所拥有的理论知识,并不就是要求于中小学教师创造的理论知识。作为教师的实践性知识,有其特定的含意。我们要求于教师的,是建立在对教师自身的实践的反思基础上,特别是借助于教育理论观照下的案例解读,逐渐积累而成的富有个性的教育实践的见解与创意。
第二个课题,教师教育制度尚待进一步完善。近年来教育部出台了包括《园丁工程》在内的一系列教师教育的政策,标志着我国的教师教育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不过,许多制度需要进一步明确和完善,举例来说:(1)“一体化”(职前教育与在职教育)教师教育体制的确立。迄今为止我国教师教育中的“职前教育”与“在职教育”分别由师范大学和教育学院实施,但是后者的专业水准与教育学术水准远远落后于前者,不仅无力承担教师研修的重任,而且往往误导了教师的专业成长。取消教育学院的建制,由师范大学统一规划并承担职前职后的教师教育,是势在必行了。(2)教师“资格制度”的完善。教育部明确规定要全面实施教师“资格制度”,引进竞争机制,完善教师聘任制,破除教师职业“终身制”和“身份制”,开通“下岗”、“分流”的渠道,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能进能出”、“能上能下”的用人机制。教师资格制度作为国家对教师实行的特定的职业许可制度,旨在保障教师队伍达到基本的素质要求,对新世纪的教师在师德、文化素质、教学水准等各个方面,提出了更高更具体的要求。不过,在教师资格制度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几乎所有在职教师都“自然过渡”了。而面向社会认定教师资格,吸收非师范类优秀人才从事教师工作,打破了师范院校“专营”教师教育的格局,这也是世界教师教育发展的共同趋势。问题的实质在于“择优上岗”,因此“门槛”设置不宜过低,防止资格认定流于形式。(3)在职“研修制度”的改进。传统的教师研修目标存在强调理论知识特别是专业学科理论知识而忽视教学实践能力的偏差,这种取向不能适应素质教育对教师素质的要求。作为在职教师的“研修制度”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可以考虑增加教师参与课程实验、课程开发的机会;加强课程与教学的研修课程;倡导教师开展“行动研究”,等等。
第三个课题,教育科学尚待改造与发展。我国作为教育学科之核心学科的“教育学”非但不能成为教育改革的助力,而且往往成为一种阻力。教育学的话语系统基本上还是凯洛夫的一套。教育学的“研究”重思辨,轻实证;重宏观,轻微观;重高教,轻基教。即便高教研究也是重总体规划、行政体制的研究,轻专业课程、学科建设的探讨,远远不能适应教育市场的需求。师范大学面临生存危机,需要反思,需要变革,需要确立自身的优势。在这方面,我们面临诸多课题。
例一,如何解决学科生态的失衡与“学科教育学”的重建的课题。我国师范大学教育学学科点的布局沿袭前苏联的一套,几十年一贯制,造成了严重的“学科生态失衡”。一方面是传统的教育学科游离于生气勃勃的教育改革实践之外,另一方面是紧贴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前沿的学科教育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师范大学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活动缺乏时代气息与生命活力。事实上,现代知识的生产方式已经转型。英国著名知识社会学家吉本斯(M.Gibbons)(注:[英]M.Gibbons编著,[日]小林信一主译:《现代社会与知识的创造》(1994年版),丸善股份公司1997年日文版,第19~47页。)从学术研究与现实社会之关系的角度,严格地区分了两种知识生产模式。模式Ⅰ是传统的近代型知识生产模式,其特点是脱离现实问题高度抽象化的学术探讨,是学科内的、学科社区的、线性的、阶层性的、僵化的。模式Ⅱ是现代型知识生产方式,其特点是直面现实社会问题,是跨学科的、非线性的、网络式的、平等对话的、流动鲜活的。同样,现代教育科学知识的生产方式也需要转型。亦即我们需要有广阔的国际学术视野,直面教育改革实践,调整和改造教育学科,发展模式Ⅱ的教育科学研究。最近,教育部师范司部署了师范专科学校层次的教育学科课程改革,相信会给教育界带来一股冲击波。华东师范大学集中了一批学科教育的专家,目前正在编撰一套“学科教育展望”丛书,期望能够为打破学科教育研究的死气沉沉的局面,尽一份力量。
例二,如何主动介入基础教育的课程开发与“学校文化”重建的课题。师范大学对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反应迟钝,这本身就是师范大学生存危机的一种表现。《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引导我们把课程与的改革作为切入口,围绕课堂教学层面深入基础教育的改革。这不仅为广大教师的专业化提高提供了机遇,也为师范大学的改革和教育学科的改造提供了机遇。《纲要》着力于从课程政策层面、课程理论层面、课堂教学层面(包括教学规范、评价制度乃至教材生产方式)的转型,体现了教育思维方式的根本变革。基础教育的目标是为每一个学生奠定人格与学力发展的基础,奠定终身学习、终身发展的基础。《纲要》倡导把学生当作一个完整的人而不是作为工具(标准件)来培养,因此,我们的课程教学应当摆脱分科主义、操作主义、工具主义的束缚,不能灌输被肢解成一大堆支离破碎的知识技能;不能仅仅满足于传统的3R(读写算),还要体现3C(关爱、关切、关联)。倡导学科的综合化,倡导“综合实践活动”(包括“研究性学习”)。这样,我们不仅需要“基于学科知识系统的课程开发”,也需要“基于主题(课题、专题)的课程开发”。这种课程开发要求跨学科、跨学校、跨行业,跨地区甚至跨国界的对话与协作。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从本质上说,是铲除“应试型文化”、建构“发展型文化”的过程,是“学校文化”的重建。因此,我们迫切需要现代教育科学知识生产的基地,需要研究型师范大学的重点建设,这是教师教育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大凡改革,总是包含了理念、观念层面的改革和制度、体制层面的改革。教师教育的改革也是同样。我们应当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确立适应新时代需要的理想的“教师形象”,二是确立相应于理想的“教师形象”的教师教育体制。这两者是统一的、不可或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