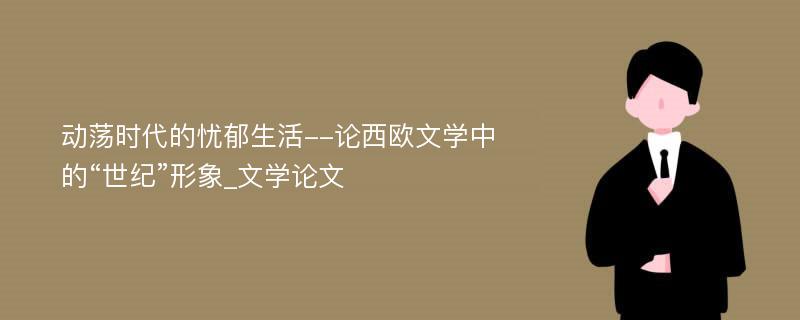
动荡时代的忧郁人生——论西欧文学中的“世纪儿”形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欧论文,动荡论文,忧郁论文,形象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的西欧文学史上,出现了一批描写“世纪儿”的作品,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夏多布里昂的《勒内》、塞南古的《奥培曼》、贡斯当的《阿道尔夫》、缪塞的《一个世纪儿的忏悔》以及拜伦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等。这些作品的主人公有着相似的病态性格,他们往往被忧郁迷惘的情绪所困扰而难以自拔。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曾经指出:“十九世纪早期的忧郁是一种病,这种病不是哪一个人或哪一个国家所独有的,它是一场由一个民族传到另一个民族的瘟疫,就象中世纪常常传遍整个欧洲的那次宗教狂热一样。”〔1〕他把“世纪儿”形象的出现看作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内的带有普遍性的文学现象。事实上“世纪儿”形象不仅在当时有其代表性,而且在以后的世界文学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因而对这种文学现象进行一番考察是很有必要的。
一
西欧文学中众多的“世纪儿”形象产生于不同国度、不同作家的笔下,他们的经历和个性不尽相同;但是,从总体上看,他们的精神世界是相通的,他们有着苦闷彷徨、孤独忧郁的性格。法国作家缪塞把这种精神状态称为“世纪病”,他对“世纪病”的具体描绘是:“一种无可名状的苦恼感觉。”这些“世纪病”无不是由个人理想与客观现实的矛盾所造成的。“世纪儿”们在生活中往往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幻想,然而他们身处的现实社会又总是无情地粉碎了这些幻想。他们的内心世界痛苦万分,孤独、忧郁、冷漠、麻木的情感便油然而生。
这类形象比较集中在法国。十九世纪第一个十年,法国文学史上就出现了塞南古的《奥培曼》和夏多布里昂的《勒内》两部描写“世纪儿”的名篇。《奥培曼》的主人公奥培曼在社会上始终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总是在抑郁中度日。“我需要幸福,我生来却注定要受苦受难。”在无法摆脱自我追求与现实环境的矛盾时,他只觉得生活便是无涯际的痛苦。《勒内》中的主人公勒内也是患有“世纪病”的典型。这个破落贵族子弟自幼在忧郁孤寂中长大,成人后到处漫游,无论在何处,他都感到像在沙漠中一样寂寞。“唉!我孤零零,孤零零活在人间!”人生无常的慨叹伴随着他度过一生。在这两部小说问世后不久,贡斯当创作了《阿道尔夫》,又一个“世纪儿”形象出现于法国文坛。阿道尔夫傲视平庸的环境,甚至觉得“我没有发现任何足以吸引我注意力的东西。”这样他就由卓然不群进一步形成对任何事物都漠不关心的厌世态度,从而显示出“世纪病”的特征。缪塞的《一个世纪儿的忏悔》出现于文坛已到了三十年代,但主人公沃达夫与上述的勒内、奥培曼、阿道尔夫一样,也是以孤独烦闷、消极厌世为其主要特征。
在法国以外,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中的维特应是德国文学中的“世纪儿”形象。这部小说描写的是维特和绿蒂的不幸的爱情故事,但着重表现的却是维特孤独的感情和痛苦的心情。维特的苦闷也来自环境,他生活在那个腐朽、庸俗、鄙陋的社会,感到难以忍受的压抑。所以他的烦恼的内涵实际超出了恋爱的范围,而体现出个人理想与环境之间的不协调性。英国著名诗人拜伦创作的诗体小说《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描写了一个英国的“世纪儿”形象。哈洛尔德出生于英国的破落贵族家庭,他过着纸醉金迷的享乐生活,感到空虚无聊便离开祖国,似一个“忧愁的流浪者”前往欧洲大陆旅行。作品重点写的是哈洛尔德在欧洲各国的絮飘萍泊的体会。他的游历虽然包含着对新生活的追求:“宁可遭些灾祸,但求变换情调,落入地狱也不妨。”但他又常常悲叹:“现在我是孑然一身,在这辽阔的海上飘零。”孤独感伤的情调一直笼罩着他。
既然“世纪病”源于“世纪儿”自我与环境的不协调性,那么在这种以苦闷忧郁为特征的病态中势必包含着程度不同的对环境的叛逆意识。这一群人才智过人,又有着自己的追求,但在现实中老是碰壁。然而,他们碰壁后无论是自沉于消极颓唐的状态还是采取了玩世不恭的态度,都决不向社会妥协。否定现实的精神始终是“世纪儿”性格中的闪光之点。最能显示这一点的是他们对社会的愤怒诅咒。维特对于他所处的环境就深恶痛绝,他憎恶一切束缚个性发展的清规戒律。在他看来现实社会像是一座监牢,生活中的一堵堵墙就像是牢房的墙,把人与人隔离开来。可见他对社会本质有着颇为清醒的看法。缪塞《一个世纪儿的忏悔》对拿破仑帝国覆灭后的现实的诅咒通过沃达夫的感受尽情倾泻出来,其中对于时代的抨击是尖锐的,而且分析也有一定的深度。“世纪儿”对现实的否定虽然体现出明显的反叛意识,但他们毕竟没有能力改变现实。因而他们的叛逆性显得苍白无力。在种种幻想破灭后,等待着他们的只能是悲剧的结局。维特最后在对生活彻底无望后走上了自杀的道路。勒内在现实生活中感受到的痛苦同样深重,他为摆脱愁闷的心境出国游历,去了遥远的美洲。奥培曼对社会也极为反感,于是他追求一种孤独的生活,觉得再孤独也不过分,以至于忘却了人类、忘却了时间。阿道尔夫和沃达夫采取的亦是超然物外、平淡冷漠的生活态度。哈洛尔德在厌倦了周围的一切后,也悲愤地离开祖国,到处漂流,他与勒内有点相像,都希望在异国风光和大自然中寻找安慰。这些世纪儿所选择的道路各有特色,而且似乎都那么消极,但他们不与世同流合污的精神是一致的。从个人命运上讲,他们的结局是悲剧;但从对抗现实的角度看,他们的选择仍不失为一种抗争。
对于爱情生活的描写是“世纪儿”作品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这方面的内容实际上还是为刻划主人公的“世纪病”服务的。当苦闷感、忧郁感向“世纪儿”袭来时,他们常会希望从爱情生活中寻求慰藉和解脱。然而由于各式各样客观的和主观的原因,他们总是得不到幸福的爱情生活;或者难觅知音,或者情场失意,或者徘徊游移,结果则是加重了自身的苦闷和忧郁。爱情生活不但没有治好世纪病,反而使病态加剧,人物的悲剧性也因此而加深。
在《少年维特的烦恼》中维特与绿蒂的恋爱并不是一般少男少女的恋情。在维特眼里,贤淑善良的绿蒂乃是美好的化身。维特遇上了她仿佛在丑恶的现实中发现了光明,他对她倾注了全部热情。然而绿蒂却表现得那么平庸,她宁肯服从礼俗而牺牲爱情。维特失望极了,他的“烦恼”非但未从爱情中得到减轻,反而愈加严重。在《一个世纪儿的忏悔》中,沃达夫也希望用爱情来治疗“世纪病”。他与比莉斯·比埃松夫人的爱情也曾使他兴奋异常,以至觉得爱情可以填补自己空虚的心灵。但是他又特别敏感,常常自寻烦恼地寻找比莉斯的不贞,从而妒火中烧。这种变态的恋爱心理折磨了情人,也折磨了自身,最终爱情生活没有治愈沃达夫的“世纪病”,他的精神堕入了更痛苦的深渊。
如果说《少年维特的烦恼》描写了一对本该结合的恋人终究未能结合的悲剧,那么《阿道尔夫》写的恰恰是一对已经结合的恋人却又分离的故事。当阿道尔夫爱上了比他大十岁的爱蕾诺尔,爱蕾诺尔也报之以热烈的爱情时,他曾有过一种征服感和幸福感。只是这种感觉太短暂了,不久他就感受到两方面的压力:一是社会的压迫。来自父亲和亲友的非难,使阿道尔夫不堪重负;二是爱蕾诺尔对他的强烈的爱。她要充分占有阿道尔夫的全部感情,连片刻的分离都难以忍受,阿道尔夫觉得自己追求自由的个性受到了束缚。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对爱情感到了厌倦,在感情上抛弃了爱蕾诺尔。然而,一种难以自拔的自责自怨的情感又随之而来。阿道尔夫既不愿继续发展爱情生活,又在心灵上不断责备自己的忘恩负义。爱情生活同样把他推向了绝境。
二
“世纪儿”产生于十八世纪与十九世纪相交时期并非偶然,他们的出现有着特定的文化背景。
那是一个剧烈动荡和变革的时代,欧洲正处于一个历史的转折时期。1789年法国大革命在本土对封建制度给予摧毁性的打击,同时也震撼了整个欧洲。然而,大革命后大资产阶级的专制统治替代了封建的专制统治,人民群众参加了革命却未能从革命中得到利益。在大革命后的几十年,法国一直处于侵略与反侵略、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中。而各种专制统治中又夹杂着十分复杂的因素:革新与守旧、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都相互交错,令人难解难分。革命前有些先进的启蒙思想家曾预言一旦打倒了封建制度,将会实现以理性、真理和正义为主宰的制度,革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们都没有得到真正的理性、真理和正义。此种情形就如恩格斯所说:“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2〕在这样的社会政治背景下,一代知识分子受到了不断的希望和失望的困忧。旧的时代无论是好还是不好都已逝去,新的时代又处处暴露出令人难以忍受的问题,未来的前途更显得渺茫和无望。他们就成了那个特定时代的“世纪儿”,他们的忧郁苦闷的“世纪病”实际上也就是在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是非抉择上陷入迷惘的必然反映。
《少年维特的烦恼》出版的时间在法国大革命前四年,那时启蒙思想已深入到新兴的市民阶层中。尤其是青年一代,他们对自己政治上无地位并处处受到歧视深感不满,渴望着打破等级制度,建立符合自然的社会秩序和平等的人际关系,维特就是这样的青年。但在法国大革命前,欧洲封建贵族势力仍很坚固,资产阶级在与它的较量中还难以取胜,德国尤其如此。一方面是强大的社会势力,另一方面是维特的愤懑和失望,这反映出欧洲在法国革命前夕的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夏多布里昂笔下的勒内是法国大革命后最早出现的世纪儿之一。他与维特之间隔着一场曾给欧洲封建势力以沉重打击的大革命,但为什么他也与维特一样患上了世纪病呢?那是因为巨大的社会变革带来的实际情况与人们所期望的相距甚远,新的专制政权未能给人权斗争带来美好的结果。如果说维特的苦恼是“世纪儿”革命前对现实的不满,勒内的抑郁则是“世纪儿”革命后对现实的不满。
沃达夫的出现比维特与勒内稍后一些,他属于出生在拿破仑时代的人。“母亲们在战争的空隙怀了他们,他们在隆隆的战鼓声中成长。”在拿破仑时代,尽管空气中弥漫着火药味儿,但法国青年倒曾感到过兴奋,拿破仑确乎创造过一种给予青年的机遇,即让他们通过个人奋斗、自由竞争去取得成功。沃达夫就有一种“生来就要参加那些大搏斗”的感觉。然而波旁王朝的复辟结束了光荣的拿破仑帝国时代,法国青年的幻想遭到沉重的打击,他们成了新的历史背景下的“世纪儿”。缪塞在他的作品中写道:“过去的一切已不值得留恋,因为信心已经丧尽了,未来嘛,他们是喜爱的,但是,怎样的未来呢!”对过去、未来和现在全然无望这便是沃达夫当时对社会历史的直觉。可见他的“世纪病”也是在新旧交替时代迅速变化的社会现实面前所形成的。
当然,产生“世纪儿”的文化背景并不单纯是社会政治的,它还包括那个时代的思想意识、价值标准、道德观念乃至审美情趣。事实上随着法国大革命带来的社会体制的变化,社会意识形态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大革命前,法国先进的启蒙思想家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封建制度,提出了资产阶级社会秩序应该建立在“理性”之上。伏尔泰、孟德斯鸠是启蒙思想的鼻祖,他们有力地抨击了贵族僧侣的特权,代表第三等级喊出自由、平等的呼声。卢梭是比他们更为激进的思想家,他提出了“天赋人权”的理论,提出了建立共和国的要求,提出了政权属于人民本身和人民有永远的革命权的学说。这些思想家的“理性王国”的学说启迪过人们,并为法国大革命作了思想的准备。问题是大革命后的现实却使这些思想黯然失色,而十九世纪那些伟大的思想尚未形成科学的理论,整个意识形态呈现出凌乱不堪的局面,人们无所适从,于是道德观念、价值标准、审美意识都显得十分混乱。绝大多数“世纪儿”从小受到过启蒙思想的哺育,并经历了革命,故而有着自由、平等、博爱的愿望,有着个性解放的要求。但革命后的新的专制统治,尤其是拿破仑的军事独裁统治压制了他们的愿望和要求,他们在对启蒙思想所形成的人生观感到失望之后就形成了一种虚无主义人生观。整个社会在他们的眼里都是丑恶的,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制度,他们一概反对。这种混乱的意识导致了“世纪病”的形成。
另外,“世纪儿”自身的经历也是他们产生病态的原因之一。“世纪儿”大多是出身于贵族的知识分子,从小受到过良好的文化教养,先天和后天都使他们自视甚高。他们看不起周围平庸的人们,有一种孤芳自赏的高傲性格,因而也就脱离了现实,找不到真正的出路。十八世纪启蒙思想虽然带给他们民主意识,但实际上他们对于自由、平等的要求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哈洛尔德在欧洲游历时面对意大利、西班牙、希腊的斗争始终是一个旁观者。沃达夫对王政复辟的谴责是尖锐的,但同时他又悲观地远离社会实际,钻进个人生活的小天地中。这类人物自身的性格特点造成了他们既厌恶现实又无能为力,从而显得感情脆弱,沉湎于无边无际的孤独苦闷的愁绪中。而这特点也是与他们所处的文化背景相关的。
三
西欧的“世纪儿”形象不但在当时社会上有很大影响,而且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有很重要的地位。《少年维特的烦恼》是最早描写“世纪儿”的作品,小说一问世就风靡了整个欧洲,它拨动了千万读者的心弦。到十八世纪末,它已有了十几种译本,在各国流传。维特虽然活动于法国大革命前,但他的悲观失望、郁郁寡欢的精神世界引起了大革命后的许多人的共鸣。事实上,后来描写“世纪儿”的作品几乎没有不受到它的影响的。夏多布里昂自己就强调过他的思想受到过维特和圣·普勒(卢梭的《新爱洛伊丝》中的人物)的影响。他笔下的勒内的性格与维特有着惊人的相似。塞南古的奥培曼也是如此,他的愤世嫉俗的议论也令人很容易联想到维特。直到贡斯当、缪塞笔下的人物,整个法国文学中的“世纪儿”形象都有着维特的影子。
当然,维特仅是法国“世纪儿”的先声,及至法国一批描写此类人物的作品出现,方始形成一种文学现象,而且这一现象产生后就占据了十九世纪初西欧文坛的主要地位。法国的这些“世纪儿”小说基本上都是属于浪漫主义的作品,作者自我情绪的倾泻是它们的主要内容。由于作家本身受个性解放思想影响,对社会极度愤慨,因而他们的自我表现充满了积极的社会意义,他们所塑造的“世纪儿”形象也就具备了某种典型意义。从这个角度讲,它们与西欧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也可算“心有灵犀一点通。”斯丹达尔、巴尔扎克等小说家所表现的也是以个性解放为思想武器的个人与现实的矛盾,从而批判揭露了社会的黑暗。《红与黑》中的于连、《幻灭》中的吕西安等人物就是追求个性自由发展的典型,他们也都因上流社会阻碍和打击而成为不幸的悲剧人物。这一点与“世纪儿”形象是完全一致的。
随着时间空间的转移,与“世纪儿”相类似的艺术形象越来越多地出现于世界文学史上。比西欧“世纪儿”形象稍迟,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俄国文学史上出现了“多余人”画廊,主要有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奥涅金、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皮却林、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中的奥勃洛摩夫等。“多余人”形象与“世纪儿”形象在性格上如出一辙。他们也是在丑恶的现实中幻想破灭,从而在精神上堕入苦闷忧郁的。如果究其根源,他们与各自身处的俄国社会文化背景也是密切相关的。还必须指出的是俄国的“多余人”形象在创作过程中与西欧的“世纪儿”有着直接的继承性。普希金就是拜伦的崇拜者,长诗《恰尔德·哈洛尔德》是他非常喜爱的作品,主人公孤独傲世的性格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描写的奥涅金也十分崇拜拜伦和拿破仑,拜伦的肖像和拿破仑的铁铸像一直是他的随身之物。拜伦的诗篇也激荡于他的心中。作品还写道:“他出现在各家的客厅中,象恰尔德·哈洛尔德一样:阴郁、懒散。”显而易见,奥涅金形象中渗透了拜伦诗篇的精神。
翻开“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史,不难发现西方文学给予中国现代作家深刻的影响,其中也包括了“世纪儿”和“多余人”的影响。郁达夫的小说就描写了一系列他自己称之为“零余者”的形象。中国的“五四”时代也是新旧交替的时代,西方的进步思潮冲击着中国传统文化,“五四”先驱者认为给腐朽的封建制度敲响丧钟的时刻已经来临。然而封建制度却并未像他们预言的那样迅速退出历史舞台。在幻想和现实的矛盾、希望和失望的冲突下,一代知识分子的苦闷从心田出土。“零余者”的苦闷中既包含了时代的特征,也有着自身的因素,这些与“世纪儿”、“多余人”都极其相似。甚至他们身上的变态的性苦闷,其内涵与“世纪儿”爱情悲剧的实质也异曲同工。郁达夫自己明确地说过他所受到的“多余人”作品的影响:“在许多古今大小的外国作家里面,我觉得最可爱、最熟悉,同他的作品交往得最久而不会生厌的,便是屠格涅夫。”〔3〕郁达夫的小说,不仅是主人公的忧郁症, 就连整个作品的情调、风格,都与“世纪儿”、“多余人”的作品相仿。由此可见郁达夫艺术创作渊源的一方面。鲁迅笔下也出现过带有中国特色的“世纪儿”形象。《在酒楼上》里的吕纬甫和《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便是两个代表。这两人都是活动于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知识分子,作者表现了他们在大变革时代中的升降浮沉,着重刻划的也是他们的颓唐徘徊的心态。鲁迅其他作品中描写的知识分子,例如《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伤逝》中的子君、涓生等也都有孤独、彷徨的特征。他说自己写小说(《狂人日记》):“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4〕这“百来篇”中既有东欧文学也有西欧文学。而且,鲁迅早在1907年写的文言论文《摩罗诗力说》中就全面分析过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他大力颂扬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裴多菲等人的作品,尤其对拜伦推崇备至。他之所以在小说中写出了中国的“世纪儿”形象,原因之一正是欧洲文学对他的影响。
显然,“世纪儿”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了。无论是“世纪儿”还是“多余人”、“零余者”(在日本,这类形象还被称为“畸零者”,紫式部和二叶亭四迷笔下就写过这类人),它们名称虽然不同,却有着共同的审美特征。他们跨越了时代和国度,影响之深远,共鸣之强烈,且愈来愈得到人们的理解和同情。这确是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
注释:
〔1〕勃兰克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分册:《流亡文学》)。
〔2〕恩格斯:《反杜林论》。
〔3〕郁达夫:《屠格涅夫的(罗亭)问世以前》。
〔4〕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标签:文学论文; 小说论文; 一个世纪儿的忏悔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