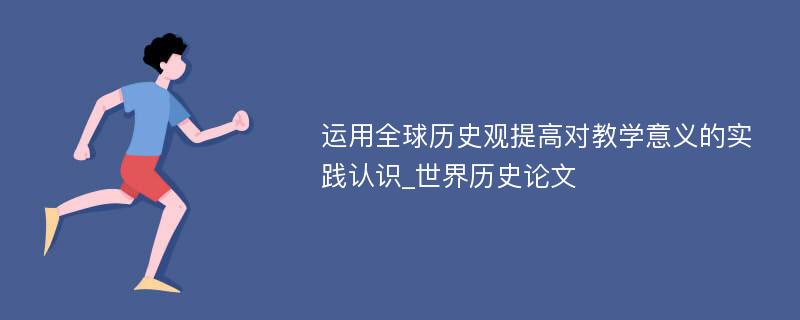
运用全球史观提升教学意义的实践性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义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就中学历史课程而言,初中阶段先讲中国史,再讲世界史;高中阶段虽然按照模块划分为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形式上是中国史和世界史混编为一本书,但中国史和世界史分属不同章节,课与课的内容缺乏内在联系。换言之,世界史是排除了中国史的各国历史的相加与汇总,中国史则主要是以王朝兴衰和社会变迁为线索的断代史和专题史的分解与整合。所以,即使完成了历史课程学习,并不一定能使学生形成开阔的历史观,即从中国的角度看世界,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这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既不利于学生形成一种广阔的视野,也会影响学生思考事物的角度。视野狭窄、角度单一,会导致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形成开放的世界意识的目标流于空谈。因此,无论是世界史教学还是中国史教学,如何培养学生具有一种全球史观的眼界显得尤为重要。下面就中学历史教学如何运用全球史观谈谈自己的实践性认识,以期为中学历史的教学与改革提供一些不成熟的想法。 一、破除“中国中心观” 全球史(Global History)兴起于20世纪下半叶,全球史观旨在突破传统历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建立一种超越狭隘民族和国家界限、公正地评价各个时代和各个地区的一切民族的建树的整体历史观。全球史观的提出者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Geoffery Barraclough)认为:“世界上每个地区的各个民族和各个文明都处在平等的地位上,都有权利要求对自己进行同等的思考和考察,不允许将任何民族或任何文明的经历只当作边缘的无意义的东西加以排斥。”[1]经过半个多世纪以来各国学者的共同努力,“欧洲中心论”基本上已经从学理上彻底颠覆。但是,伴随着二战以后亚非拉各国民族独立运动的蓬勃开展,世界上又兴起了一种狭隘的民族国家中心观。 由于中国从近代以来就饱受西方列强的侵略与蹂躏,所以当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和民族的自豪感空前高涨,反映在学术研究中,就是在否定“欧洲中心论”和批判“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非常浓厚的“中国中心观”。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国内持续高涨的“李约瑟热”与对美国学者柯文撰写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的热捧,就是这种思维的反映。具体到中国古代史教学,教师通常会在不经意间运用这种史观解读历史。例如,过分强调中华文明的独立发展道路和在东亚文明的中心地位,陶醉于中国古代的各种发明创造和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动辄以“我们古已有之”来回应世界新生事物的诞生与出现,忽视域外文明的存在及其影响。在讲中国古代的科技发明成果时,特别强调有多少个世界第一。在讲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时,反复强调四大发明对西方文明的影响有多么重要和深刻——如果没有指南针的西传,西方就没有地理大发现;如果没有印刷术和造纸术的西传,就没有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如果没有火药的西传,封建堡垒就不能攻破,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就不可能成功。这样的历史课堂教学,容易给学生造成一种中国是天下“救世主”的印象和“中华文明优越论”的感觉,也会导致学生形成盲目排外与妄自尊大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 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样的“中国中心观”历史上早已有之。先秦时期,中国就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天下观”,这种“天下观”对世界的认识是建立在“华夏居中,蛮、夷、戎、狄居四方”的“华夷”五方格局基础之上的,它强调的是以中原王朝(或曰正统王朝)为中心向边缘扩散的差序格局,也可以称之为“华夷秩序”[2]。这样就构成了当时人们眼中的“四夷”环绕“中华”的世界图景。这种“华夷观”强调华夏文化的优越正统地位、蛮夷文化的落后附属地位。“华夏”和“夷狄”之分既非建立在征服的基础之上,亦非在于种族之分,而是文化优劣的区别。不仅“夷狄”接受了“华夏”文化就是“华夏”,而且“华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也会沦为“夷狄”。由此还形成了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贵中华、贱夷狄”的思维范式,也成为古代中国史书编撰的基本标准。著名全球史学家皮特·N.斯特恩斯(Peter N.Steams)曾说:“几千年来中国人把中国内地以西和以北大草原上放牧牛羊的游牧民族看作与自己不同的蛮族。对于中国人来说,文明开化与否是从文化上来看的,而不是从生理或种族角度来看。如果蛮族学会了中国的语言,采用了中国的衣着和食物等生活方式,那么他们就被认为是文明人了……(20世纪以来),中国人越来越欣赏自己的文明成就,在判断谁是文明的和谁是不文明的社会理论中保持着一种民族优越感。”[3]例如,在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中,我们往往津津乐道于少数民族(“四夷”)的汉化,即华夏文化“和合”与“同化”周边“四夷”的模式(北魏孝文帝的改革、辽金元清的汉化),无意之中就会流露出少数民族学习汉族就是进步的,从语言文字、服饰打扮,到礼仪制度的汉化措施代表进步的发展方向,否则就是落后。虽然“汉化”与“胡化”不能一概而论,但往往因为片面强调一个方面,从而忽视了“汉化”与“胡化”的双向交流互动而产生的对历史发展的推动力,所以这种历史观是不全面、不客观的。 在世界史教学中,由于某种原因,我们往往又不由自主地运用了“欧洲中心论”这一早已被全球史学者批判的历史观。尤其是高中历史教学,世界古代史相当于希腊罗马史,世界近代史相当于欧美史,而对其他国家的历史和文明视而不见。似乎除了欧美以外,其他国家的历史不值得借鉴,忽视了世界各地区之间的文明互动。 其实,无论是“欧洲中心论”,还是“中国中心观”,都是有失偏颇的狭隘历史观。笔者认为,中国史教学只有将中国历史放在全球史的大背景之下来把握,才能更好地理解不同时期中国历史进程和世界其他地区历史进程的相互联系和区别,也才能更为正确地理解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世界史教学,我们不应该将世界史讲成国别史,除了讲世界各国历史发展的特点以外,更应该重视世界各地区文明的互动交流和相互借鉴。 二、贯彻“互动”理念 “互动”是全球史观的核心理念。全球史观认为,“互动”是人类社会组织的存在形式,任何人类社会组织都不是封闭和孤立的,它们必然存在于与外界的交往当中,彼此形成一个互相关联的体系或网络,并在该体系和网络内部相互影响。“互动”也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全球史观的研究者借鉴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认为社会发展源自变化,而变化的起点是接触外来新事物;对新事物的取舍过程就是传统的蜕变过程,尽管社会对新事物通常并不抱欢迎态度,但抵制新事物的结果同样导致社会变化。正因为如此,全球史观主张,历史学家应对不同文化的“相遇”(encounter)保持足够的敏感[4]。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互动”也是中国社会发生变化与进步的动力。长期以来,我们在中国史的教学中较多地强调东亚地理环境的相对封闭和中华文明的独立发展道路,以致给学生造成一个只有在汉代张骞通西域之后中国才和世界发生联系的错觉。著名全球史学家杰里·本特利(Jerry Bentley)指出:“尽管在中国和印度、西南亚之间存在高山和沙漠的阻隔,贸易网络还是早在公元前3千纪的时候就把中国与西方和南方的大陆连接起来了……古代中国也是在一个彼此影响、彼此交流的世界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贸易、移民和中国农业社会的扩大,促进了东亚和中亚各民族彼此之间正常关系的发展。”[5]也就是说,中华文明早在五千年前就与世界上的其他文明发生了联系,张骞通西域只不过是古代中国开始大规模探索与了解世界的一大壮举。 其实,在世界古代文明史上,张骞通西域并不是一件完全孤立的历史事件。在此之前约二百年,希腊一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发动的东征就到达了中亚的巴克特里亚(大夏)和南亚的印度河流域——这些地区是张骞后来才到达的。也就是说,“就丝绸之路的全线贯通而言,亚历山大东征和张骞通西域都发挥了同样的历史作用”[6]。假如我们在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中能够将张骞通西域与亚历山大东征联系起来,就能让学生更好地理解这一时期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不同人群之间渴望“相遇”以及“相遇”对人类文化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这也正是全球史学家所要表达的一种“互动模式”。 在世界文明史中,佛教的产生与传播体现了世界各地区之间文明的交流与互动。佛教在公元前六世纪诞生于古代印度,大约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是那个时期中国的“新事物”。由于佛教是一种外来的异质文化,在其传入中国时曾经产生过严重的水土不服现象,受到本土文化的强力排拒,甚至酿成“三武一宗灭佛”(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灭佛事件)的激烈冲突。尽管中国社会对佛教这一外来的“新事物”并不完全持欢迎态度,但抵制的结果同样导致中国社会发生了变化。我们知道,佛教为了尽快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开始了中国化(本土化)的过程。经过与本土文化的排拒、吸纳、依附、融汇,最终演化为中国化的佛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唐宋巨变中,理学的兴起与道教的变化就都受到佛教的影响。因此,中国社会对佛教这一外来“新事物”的吸收、取舍的过程本身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蜕变过程。如果我们不从全球史观的文明互动角度来解释这一文化传播现象,也就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 另外,在中国古代史教学中,还有一个非常容易被忽视的现象,那就是“胡化”问题。在中学历史教学中,一提到少数民族的“汉化”问题,通常就会大讲特讲,认为这是一种社会进步的现象;反之,一提到“胡化”问题,就会与历史的“倒退”、野蛮,甚至落后相联系,因而有意回避或者干脆不讲。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与偏见。全球史学家认为,文明的“互动”是相互的和双向的,世界上每个地区的各个民族和各个文明都处在平等的地位上,都有平等对话和互相交流的权利。在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汉化”固然是历史发展的主旋律,但“胡化”也不容忽视,它曾经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产生过重大影响,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汉唐社会胡气氤氲——胡服、胡食、胡音、胡乐、胡舞、胡骑、胡俗——盛极一时。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胡化”现象甚至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还有反映。假如我们在中国古代史教学中能够从文明互动的视角将“汉化”与“胡化”现象结合起来讲授,就能让学生更好地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共生共存的包容格局。 全球史观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视野开阔、思维开放地看待历史的全新视角与方法,不仅如此,全球史观致力于通过跨学科、长时段、全方位地探讨和关注人类生活层面的相互联系与互动,尤其是关注跨越地域和种族的互动与交流,诸如对人口的迁移、疾病的传播、帝国的扩张、生物的交流、技术的转移、思想观念和信仰的传播以及自然生态环境的变迁等的全方位、多视角的观察与解读,既能为我们历史课堂处理相关内容提供教学素材,还能为我们培养学生的历史意识、文化素质和人文素养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