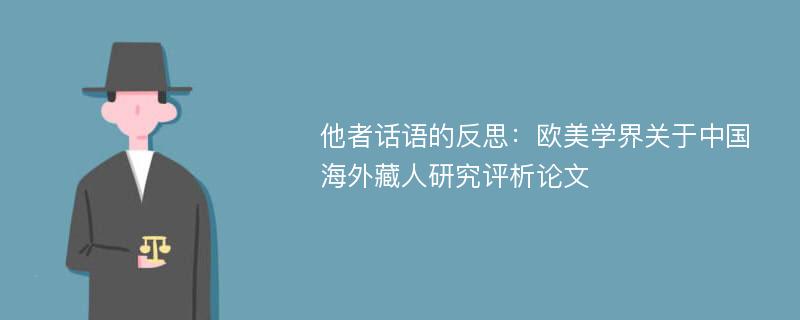
他者话语的反思:欧美学界关于中国海外藏人研究评析
李志农 高云松
[摘要] “西藏问题”,尤其是中国海外藏人问题,是我国党和政府始终关切的重要问题。自1959年西藏叛乱以后,中国海外藏人问题在一些西方国家备受关注,也成为欧美学者们竞相展开调查研究的重要领域,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涉及了国际关系、人口迁移、国际援助、难民政策、身份政治、文化传播等诸多领域。本文将在对大量欧美学者的相关专著与论文进行整体把握的基础上,厘清欧美学界海外藏人研究的基本特点,对欧美学界的相关研究状况进行分析,并重点分析了欧美学者对中国海外藏人社区的实地研究,指出许多研究过分服务于政治目的,或研究中情绪色彩过重,或关注点过于集中于中国海外藏人的处境状况。因此,国内的相关研究应发挥本土优势,关注中国海外藏人生活境遇,将海外藏人研究与国内藏族研究相结合,构建起更加完整的藏族研究体系。
[关键词] 欧美;中国海外藏人;研究综述
1959年,达赖集团挟持一些不明真相的藏人逃往海外,在印度大肆进行分裂国家的活动,成立学术研究机构,并出版刊物、丛书等①,影响很大。同时,随同出逃的藏人沦为难民,他们的命运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一些上层喇嘛和官员,受英、法、日、意、美、西德等国的聘请,到有关机构协助进行学术研究工作;而西方的藏学家及关注“西藏问题”的其他学科研究者,也积极开展对于西藏与藏人的研究。这使得西方的藏学研究队伍空前扩大,若干国家相继出现了藏学研究中心。几十年来,欧美学界对中国海外藏人研究发展迅猛、成果颇丰。我们认为,全面了解欧美学界关于中国海外藏人的研究现状,并努力开展中国视角下的中国海外藏人研究,有助于打破西方在“西藏问题”上的话语霸权,是维护国家主权、抵御境外势力和解决“西藏问题”的重要一步。
一、欧美海外藏人研究的总体分析
下面我们将从海外研究成果的学科分布、研究主题、研究内容、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出发,对欧美的中国海外藏人研究进行总体分析。
首先,从研究成果的学科分布上看,研究涵盖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宗教学、语言学等多种不同学科,涉及范围十分广泛,也因此几乎囊括了有关中国海外藏人的宏观国际背景和微观生活状况。其中,对中国海外藏人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多采用实地调查方法,主要关注藏人社区的社会问题、藏人的民族认同和社会适应等问题,旨在全面展示中国海外藏人的生存现状,如Saklani的《印度的西藏难民:对一个背井离乡的社区的社会学研究》[1]一文。对中国海外藏人的心理学研究则从对难民的人道主义关怀出发,运用多种心理学方法测量藏人难民的创伤后心理问题以及离散生活的心理健康状况,如Crescenzi等学者的《政治监禁和创伤史对近期在印度的西藏难民的影响》[2]。政治学主要将中国海外藏人视为国际性的政治问题,既从宏观层面讨论不同国家围绕中国海外藏人问题所提出的不同外交政策、由藏人迁徙带来的国际关系变化、各难民接受国的难民立法和政策、达兰萨拉“流亡政府”的行政治理等重要政治问题,如McConnell的文章《治理作为国家实践?构建流亡藏人群体》[3];也从微观层面上探讨中国海外藏人的政治认同、身份政治、权益保障等方面的状况,如Subba的《一条或多条道路:应对印度的西藏难民》[4]。有关中国海外藏人的经济学研究则聚焦于生计方式和社会发展上,分析他们的生活水平及其变化,如O’Neill的《地毯、市场和制造商:藏人地毯行业的文化与企业家精神》[5]一文。另外,还有宗教学等其他学科从文化入手,探讨藏人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变迁,以Moran的《佛教观察:加德满都的旅行者、流亡者和西藏佛法》[6]为代表。欧美学界运用不同学科范式从不同领域出发深入了解海外藏人的生存背景与生活实践,取得了丰厚的研究成果。
第二,从研究主题上看,欧美学界对中国海外藏人的研究建立在认同其为难民身份的基础上,这种难民研究具有较强的问题意识,主要从身份认同、社会适应、权益保障、身心健康等方面进行探讨。如Feller在《庇护、移徙和难民保护:现实、神话和对未来事物的承诺》[7]一文中,探讨了庇护、移民和难民保护的发展、挑战和未来,并认为各国不应阻止移徙,而应集中精力更好地管理移徙。她讨论了庇护问题以及与维护这一问题有关的挑战。在解决庇护的合法性问题的同时,还试图将个人的合法权利与国家的关切进行调解。更重要的是,Feller强调了错误分类的危险:难民不是移民,因此将他们归类就会危及他们的权利。她接着给难民下了定义,并概述了与难民地位相关的权利。尽管承认并非所有国家都有难民法,也不是所有国家都是保护难民的国际努力的一部分,但Feller指出,世界人权宣言第14条概述了寻求和享受庇护的权利。
中国海外藏人的身份问题是难民研究最常关注的问题之一,Yeh在《西藏侨民的身份政治》[8]一文中,回顾了藏族身份的标志,以及他们在不同的藏族群体中的差异。在较小的程度上,她还谈到了印度、西藏和中国的其他藏区的藏族身份的文化政治比较目的。她探索了作为藏人标志的种族和身体特征、语言和方言以及社区归属。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她关于藏人社区内部和整个地区的真实性问题,以及每个地区是如何定义藏人身份的。作者试图用相对较短的篇幅来讨论广泛而复杂的问题,而这篇文章如果能延长篇幅,以便有更多的细节和解释,将会更有帮助。此外,由于她只关注中国西藏、印度和加利福尼亚的藏族社区,所以她的研究范围有限。但她的研究得到了学界的广泛支持,这也体现了欧美学界对中国海外藏人身份政治问题的研究兴趣。
在其早期意义上,“拙”与动作、行为等有关。就文献看来,从行为、语言的缺乏技巧、不顺畅等较早义开始,“拙”的语义主要向着三个方面发展:
欧美学者强烈的问题意识也体现在一篇名叫《传染及其伪装:印度流亡藏人的不平等和疾病》[9]文章中。作者Prost以藏人“流亡社区”为例,分析了“流亡社区”的健康和社会不平等状况。在这项工作中,她认为健康差距反映了更广泛的社会不平等,并建议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探讨“移徙阶段”。另外,通过成功地区分印度达兰萨拉的新难民和已定居的难民,Prost也让人们得以一窥“流亡社区”的内部斗争。尽管普罗斯特的文章是针对医学界的,但她还是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个可读的西藏难民经历的描述,其中鲜明地表现出作者对藏人难民问题的强烈关注。
一项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献研究是Falcone等人的《“我们不在家”:二十一世纪在印度的西藏难民》[13]一文。Falcone和Wangchuk通过使用证词、公共话语、媒体、中国西藏和印度文献来探讨西藏难民的无国籍状态,重点是藏人流亡社区与印度政府之间的关系。他们还讨论了具体的法律概念,如公民身份和印度移民制度的参数,以及哲学思想,家庭作为庇护所的重要作用——这些是对难民社区充分融入印度社会的能力的参考。尽管涉及一系列问题,但作者的陈述是全面和客观的。此外,尽管这篇文章依赖于匿名线人的证词,但由于使用了大量的消息来源,这篇文章明显具有可靠性。虽然这不是一篇关于这一主题的介绍性文章,但它迎合了广泛的读者,是那些对印度西藏难民人口感兴趣的人的必读文献。
欧美相关难民机构的调查获取的大量有关中国海外藏人的调查资料,但也受限于各种原因,存在有失全面性和客观性等问题。加拿大移民和难民局发布的一篇名为《印度:1)西藏难民的法律地位;2)藏人取得印度国籍的权利》②的报告提供了关于在印度的西藏难民的法律地位和他们获得印度公民身份的权利的基本和简要的信息。报告回顾了印度政府如何在1959年给予西藏难民政治庇护,并在全国范围内为他们提供了众多的定居点。尽管如此,西藏难民仍须遵守居留许可条例,即使出生在印度,也无权获得印度国籍。报告没有区分1959年第一批难民的地位和权利以及1979年第二批难民期间和之后抵达的难民的地位和权利。此外,关于藏人获得印度公民身份的权利也存在着报告中没有讨论的争论。总体而言,所提供的信息虽然来源充足,但非常不全面。另一篇名为《印度:西藏难民和不被承认为难民的人的状况;包括合法权利和生活条件》③的报告提供了截至1999年印度藏人的生活条件和合法权利的信息。它包括在印藏人的重要统计数据,以及印度政府为难民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就业机会情况。报告简要介绍了藏人与当地居民的关系、身份和公民身份要求,以及对藏人行动自由、政治参与和抗议的限制。该报告利用各种来源提供了较为全面和公正的介绍。它在一份相对简短的报告中包含了许多深入的问题,形成了内容丰富而却浅显易懂的报道。虽然有些过时,但这份报告反映了在印度的新藏人难民所面临的困难,并概述了法律问题。加拿大移民和难民局的又一篇名为《中国/印度:居住在印度的藏人的居住权;藏人在印度获得和保留永久居留权的要求》④的报告论述了藏人在印度的居住权问题,并概述了在印度获得和保留永久居留权的要求。报告强调了“登记证书”在确定难民生活条件方面的重要性。然而,除了1979年以前抵达的难民在印度出生的子女外,“登记证书”不再自动授予难民。尽管“西藏流亡政府”声称拥有一个“登记证书”可以给予他们和印度公民一样的权利,除了选举权和在政府内工作的权利,但其他人则持相反的观点。通过使用各种来源,其中一些甚至相互矛盾,报告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多方面的主题概述,并成功地说明新的藏人难民在永久居留方面所面临的挑战。
美国公民和移民局同样提供了丰富的调查资料。2003年报告《印度:关于西藏难民和定居点的信息》以简洁的方式介绍了西藏难民在前往印度达兰萨拉途中遇到的许多重要过程,并特别强调尼泊尔和印度的移民系统。总的来说,报告通过一个较为宏观的法律和人权的观点,提供了一种管窥西藏难民的方式。虽然受到其篇幅的限制,但该报告提出了合理的研究,并参考了各种其他资料以获得更详细的信息。然而,一个明显的弱点使得最终的结论并不完善,就是它没有提到藏人被印度视为外国人,因此没有被赋予平等的法律地位。⑤2007年世界难民调查提供了印度难民状况的概览。《2007年世界难民调查——印度》提供了关于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在该国的人数和原籍以及他们获得公共服务和援助的情况的统计数字。尽管调查没有把重点放在一个特定的难民群体上,但调查确实指出,一些人口,如斯里兰卡泰米尔人和藏人,比其他人口享有更多的权利。与大多数此类报告一样,其内容大多是介绍性的,不应被视作对印度难民状况的全景展示。⑥
首先,许多研究受到西方固有价值观的束缚,没能够保持研究自身的科学性,反而服务于某些政治目的。赵光锐在《历史追溯与现实关切:德国学界西藏研究的新进展》一文中犀利地指出,国外的西藏研究也有其“政治正确”,并非是绝对的学术自由,并认为德国的这些研究从其著作体现的立场来看并未超出一般西方学者在“西藏问题”上的“政治共识”。[26]在当今国际社会,西方国家对于“西藏问题”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话语权,而中国则由于对这一问题缺少详细和充分的了解,导致了在这一问题上的失声。努力开展中国视角下的中国海外藏人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发出自己的声音,有助于打破西方在“西藏问题”上的话语霸权,也是维护国家主权、抵御境外势力和解决“西藏问题”的重要一步。
除基于难民机构的调查资料外,欧美学者们也尝试对“流亡”的亲历者们进行口述史研究,以期建构那段历史。发表于《西藏评论》的《流亡在外,这不是家》[11]一文,是一篇基于一位西藏难民Amchok口述资料的文章,为印度的西藏难民所经历的无国籍状态提供了一个简短而又有启发性的叙述。他描述了西藏难民在与他们的收容社区,特别是在印度,认同方面所面临的许多困难。他进一步揭示了达兰萨拉的藏人和印度人之间的关系,详细描述了过去和最近的冲突最明显的是,难民及其子女缺乏获得公民身份的途径。Amchok详细介绍了在印度的西藏难民缺乏有效的公民身份制度是如何导致该社区的无国籍感的。他推测,解决藏人流亡者无国籍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让他们返回中国西藏。尽管作者对无国籍问题提出了有疑问的解决办法,但这篇文章对藏人无国籍问题的描述对任何对此问题感兴趣的人来说都是有价值的。
第四,从研究视角上看,文章多以西方发达国家固有价值观为主导,多站在西方人权观的立场来讨论问题。这一人权观同样体现在同情藏人“流亡”生活和关注他们精神状况的研究中,这些科学研究事实上也确认了一种固有的价值判断。如《步入流亡:抵达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难民的创伤、心理健康和应对》[12]一文作者Sachs等人以到达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难民的精神状况为研究焦点。与以前的相关报告相比,这项研究结果显示出了更低的精神创伤比率。报告详细讨论了比率降低的可能原因,其中包括:其他研究对重度贫困者进行了过度抽样;招募调查对象的时间不同;以及新抵达难民特有的若干因素,从而导致作者所谓的“和谐时期”。该研究还探讨了难民使用的各种应对机制以及他们处理心理痛苦的能力。不幸的是,在大量的统计分析和心理学术语的遮蔽中,这些结果的重要性被忽略了。
子带内误差源于系统的非理想特性,发射机发射的信号经过接收机后,信号不再是理想的,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失真,图2是单子带定标信号脉冲压缩结果。从图中可以看出信号出现了明显的畸变,旁瓣很高且不对称,必须进行补偿。
第五,从研究方法上看,文献研究、定量研究、实地调查、口述史等多种方法都被用于对藏人的难民研究中。
近年来随着医疗系统电子化与可穿戴监测设备的流行,可利用的医疗数据呈指数增长,与此同时数据科学和大数据分析方法快速发展,心力衰竭的研究迎来新的机遇。目前有关心力衰竭的大数据分析研究,主要基于患者的病史资料、查体特征、辅助检查、治疗方案等数据,使用算法建立模型,进行诊断、分类和预测预后方面的研究分析。笔者使用“心力衰竭”、“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聚类分析”、“神经网络”等关键词在PubMed、Web of Science、Scopus、ScienceDirect、EMBASE数据库进行文献检索并汇总如下。
第三,从研究内容上看,一方面,欧美相关难民机构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关于中国海外藏人调查资料,描述了藏人难民生活的基本状况;另一方面,学者们通过对事件亲历者的访谈也获取了大量口述资料,用于建构出这些难民的“流亡”生命史。
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给自然环境带来了很大影响。近年来,太阳能作为一种创新、高效的清洁能源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并网光伏逆变器作为并网发电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件,对整个光伏并网发电系统的电气效率与电能质量将产生很大影响。
藏人旅居海外必定面临如何适应和融入当地社会的问题,这也是中国海外藏人研究的一个重点。《逃亡与适应:大吉岭-锡金喜马拉雅地区的西藏难民》[21]一书即是关于这一主题的代表作之一,是对生活在印度边界内的西藏难民进行的研究。作者不仅梳理了大吉岭-锡金喜马拉雅地区藏人的“逃亡”过程以及定居点的状况,而且从经济适应、社会适应等方面分析了藏人对于当地社会的融入状况。正是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和变化性,社会适应与融入研究必然成为海外藏人研究的一个热点。
另外,如前所述,欧美学者对中国海外藏人进行了大量的口述史研究,极大补充了其“流亡”背景的历史文献。实地研究可以说是欧美相关研究中成果最丰、贡献最大、科学性最强的研究方式。欧美学者对中国海外藏人社区的实地调查,是更加深入了解该群体生计活动、政治实践和文化认同的重要方法。本文将在下一部分针对欧美学者的实地研究状况进行梳理,以求对其学术贡献有一个较深刻的把握。
二、欧美学者对中国海外藏人社区的实地研究现状
实地研究是欧美学者的中国海外藏人研究中最具价值的研究方法。通过这种方法,欧美的藏人研究不仅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文献资料,全面而深入地了解了中国海外藏人的生活状态,而且推动了欧美学界完成了从对中国西藏的东方主义式想象到更具科学性的学术研究之间的飞跃。欧美学者在实地研究中,关注了包括中国海外藏人生存困境与问题、民族认同与身份、社会适应与融入、生计与发展、宗教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主题。本节即从这五个方面的研究主题入手进行梳理和分析。
(一)生存困境与问题研究
欧美的中国海外藏人研究,作为一种难民研究,以探索藏人的生存困境与社会问题、寻求解决之道为核心。藏人的生存困境与问题研究也只有借由学者的实地调查研究,才能获得更加准确、客观的结论,这是欧美对海外藏人社区进行研究的一个基本方向。
《危险的旅程:记录西藏难民的经历》[15]一文作者Dolma等人介绍了一项在尼泊尔进行的关于西藏难民的研究。作者认为,这些难民在流亡旅途中所经历的困难,可能对他们的长期身心健康产生影响。作者强调了尼泊尔边防军对难民的不人道待遇,并强调难民所经历的大多数苦难是可以预防的。他们认为需要更有效的国际压力,以确保边境国家遵守国际法和人权。作者还坚持认为,“西藏流亡政府”必须制定方案,解决难民的身心健康需要,但他们没有具体说明哪些方案结构或内容可能有用。尽管缺乏广度,而且只专注于尼泊尔的旅程,而尼泊尔并不总是西藏难民的最终目的地,研究描绘了移民过程中所面临的障碍。
对于“中国海外藏人”来说,居住在一个异文化的社会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与当地人口之间关系:一方面,藏人的迁入必然会压缩当地人口的生存空间,并与其争夺当地资源,给迁入地的社会和族群关系造成一定的紧张状态;另一方面,藏人群体也会努力融入当地社会,缓和与当地族群间的资源竞争关系,从而形成一种张力。美国著名藏学家梅·戈尔斯坦就在《南印度藏族难民的族群生成与资源竞争》[16]一文中以在迈索尔州的一个农业计划中定居的藏族难民为例,研究了这一族群生成的动态过程。作者在文中所采取的立场是,这些难民人口之间以及他们与印度人口之间对资源的竞争,是藏人与其他族群的民族边界的确立和强化以及藏人群体内部民族认同强化的关键因素之一。
(二)民族认同与身份研究
对于藏人民族认同与身份的研究也始终是欧美海外藏人相关研究的重要话题。中国海外藏人的身份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于藏人自身的本民族认同的研究,二是对于藏人作为难民的身份认同的研究。
对于那些已经成为难民的人来说,保持难民身份通常不是一个选择。在这些国家,很少有难民群体选择继续保持这种地位,因为非公民的经验比较不利。例如,在印度,作为非公民或“外国人”的难民无法购买土地或住房,只能在得到特别警察授权的情况下在国内旅行,可能难以在难民社区以外获得就业。因此,由于明确的功利性理由,大多数难民更喜欢加入东道国的国籍。然而,在当代,有几个难民团体在至少20年里故意维持难民地位,例如巴勒斯坦人和藏人。Dorsh Marie de Voe的《保持难民身份:西藏视角》[17]一文,是关于在印度的藏人是如何在逃离家园25年后仍然保持着难民身份的。文章是根据作者于1977-78年和1980-82年在印度几个西藏难民地区进行的实地工作写作而成的。文章在简要介绍藏人作为难民的情况后,作者将关注的重点放在:(1)藏人与东道国印度的关系;(2)重新安置的经济组织。作者认为,由于藏人社会与印度社会之间存在鲜明的族群文化差异,因此藏人的身份在流亡期间得到了加强。此外,难民环境为藏人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体验到自己的独特性,并观察到这些文化之外的人对他们的产品和文化遗产的兴趣。作为长期的难民,在印度的藏人有着越来越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这种民族主义立场,加上对未来的方向,为难民的经历提供了哲学基础。保持难民身份被视为捍卫宗教信仰的一种行为,而获得印度公民身份将使藏人变得面目全非。
在《塑造和重塑西藏侨民身份》[18]一文中,作者Houston与Wright认为可以把藏人的离散作为一个条件和过程来分析。离散藏人的状况强调流亡人口的结构特征,如种族、性别、阶级和宗教。在这一过程中,离散藏人引起了人们对难民生活经历的关注——离散藏人身份的形成和重塑。在离散的藏人中,达赖喇嘛的形象占据着中心地位。通过他的全球形象和跨国民族主义的政治结构,他创造了“藏人”的形象。在这种民族主义的框架下,藏人的身份呈现出一种单一性、统一性和同质性的特点。
1.2.6 观察胎膜情况通过肛门指诊或阴道检查明确胎膜情况,多于第一产程末自然破裂。如胎膜未破,可在先露部前触及前羊水囊;如胎膜已破,则可直接触及先露部,推动先露部,会有羊水于阴道流出[6]。当胎膜破裂后,应及时听胎心,并详细记录破膜时间、胎心率、羊水的色、量、性状等,正常羊水呈现无色、无味、略混浊的不透明液体状,同时观察有无脐带脱垂的征象。破膜后,应嘱产妇卧床休息,应用消毒会阴垫,并注意外阴保持干净,如破膜超过12 h扔未分娩者,应给予抗生素,防治感染。
在海外藏人身份的塑造过程中,民族主义发挥了重要影响,一些学者也将关注点聚焦于此。文章《想象民族主义:南亚散居的藏人的身份和代表性》[19]关注塑造今天藏人身份的各种具体和内在的叙事,特别是生活在南亚的西藏侨民。有人认为,不仅仅是西方人将西藏和藏人推向了海外;西藏的侨民也为他们自己的战术目的在这种(新)东方主义代表战略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作者认为,尽管藏民身份是一种想象出来的、有争议的概念,但它对那些自认为是藏民的人有自己的影响。藏民族认同是几个相互关联的、物质上的因素不断协商和重新协商的产物。跨国因素与本土因素一样,都是藏人民族主义演变话语的一部分。“流亡”在外的人中的“藏民性”,既是流散在外的人的归属感(对一个独特民族的归属感),也是流散在外的结果。同时,作者也对藏族单一话语假设提出了质疑。《西藏民族主义:宗教政治》[20]一文则认为,是藏传佛教而不是世俗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为“西藏独立”的政治话语提供了重要的习惯用语。
奖优罚劣就是要让教师对学校的管理制度有敬畏之心,才会收到应有的效果。要按照依法治校、依法治教的原则,把握好奖优罚劣的尺度,才能激励先进、鞭策后进,促进学校的长足发展。
(三)社会适应与融入研究
定量分析也被大量运用到对中国海外藏人的人口研究中,《对印度的西藏难民的社会和人口研究》[14]即是一例。本定量研究描述了在印度的西藏难民的人口、社会和健康特征。这些结果说明:西藏难民人口经历着从较不发达社会的贫困特征向中等收入社会的较高社会经济水平特征的过渡过程。教育程度的提高、劳动人口的增加、出生率的下降和预期寿命的增加只是表明这种转变的几个表现。尽管这项研究无疑会引起人道主义援助人员,特别是保健人员的兴趣,但必须清楚,这些数据是在1994年至1996年期间收集的,因此可能不能说明目前印度难民的生活条件。
《在南亚流亡35年的西藏难民的社会经济适应》[22]一文指出了在具有另一种气候和文化的国家重新安置的难民一般来说会经历适应新环境的三个阶段:1)物质生存;2)种族生存;3)经济和社会融合。第一阶段以强烈的“群体”取向和与东道国社会环境的分离为主导。许多难民仍然希望尽快返回祖国,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援助计划。如果流离失所者不愿意适应流亡生活中发生的变化,他们将终生成为难民。但总的来说,在流亡几年之后,第二阶段首先是积极的适应进程,主要是在经济领域。同时,难民培养自己的传统民族特征,普遍拒绝某些形式的文化融合,如通婚或东道国公民身份。第三阶段始于新一代在流亡中成长。只有通过老年难民的口头故事,或在某些情况下,在制度化的环境中传播对一个人的族裔和语言过去的更正式的理解,才能获得关于原家园的民间知识。随着新一代开始接受永远无法返回家园的可能性,经济和社会融合的障碍逐渐被容纳和改变所取代。在“西藏问题”上,同样存在类似的三阶段。在第一阶段,藏人背井离乡,依赖外国援助,许多人死于健康问题。在3至10年的时间里,他们生活在过渡营中,在喜马拉雅山从事道路工人的工作,或不得不在分散的小社区生存。在第二阶段,许多难民被康复方案吸收。他们被转移到自己的定居点,获得了某种程度上安全的经济基础,以便逐步发展流亡中的社会凝聚力。第三阶段的特点是,藏人越来越多地参与印度和尼泊尔各地的私营商业企业。这使他们的生活水平比当地的平均人口要高。作者从社会经济适应的角度,展开了藏人融入南亚社会的具体过程,也为适应理论提供了重要的个案资源。
针对中国海外藏人如何适应和融入当地社会的问题,Adams在《在印度的西藏难民:通过发展社会传统、文化传统和精神传统以获得的融合机会》[23]一文中指出,在印度的“西藏流亡社区行政当局”似乎对难民的需要做出了很大的反应,虽然它可能能够满足他们的基本需要,但并不能保证他们更广泛的社会福利和融入现有社区。然而对西藏难民来说,通过利用他们自己不同的传统,似乎确实有很大的潜在利益,这可能会恢复和增加社会资本,随后成功地使新来的难民融入已建立的流亡社区。
拓展性课程评价应该遵循“诊断,促进,提高”这个发展性评价的价值取向,主要做好三方面的评价工作:一是对课程评价,即学校考核组对每门拓展性课程实施效果的综合评定;二是教学评价,就是学校对教学成果的价值进行评定;三是学业评价,即任课教师对学生的学习表现进行鉴定。评价方式可以灵活多样,一般可以采用量化评价和质性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方式,做到评价指标全面、评价方法灵活、信息收集多元、评价反馈及时。
在一项更加微观的研究中,《从那时到现在的桥梁:旅居海外的藏族老人》[24]一文的作者将关注点放在了藏人中的年长者上,展示了年长的西藏难民如何适应印度不断变化的社会和经济条件。研究结果显示,在不得不放弃熟悉的环境后,这些参与者在印度经历了艰难的时期,但已经很好地适应了。他们为自己争取到了有意义的生活。提供的儿童教育机构资源已证明对老年人有利。有孩子的参与者认为他们得到了很好的照顾,这增加了他们对目前环境的满意度。然而,那些没有孩子的人没有任何资助来源,他们感到不满。这些发现有助于推动难民老龄化和社会适应等领域的研究,对如何对待和接受全世界的难民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生计与发展研究
有关中国海外藏人的生计与海外藏人社区的发展的研究,虽然并没有成为欧美学界关注的主流,但也积累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在中国海外藏人群体的诸多生计方式中,地毯业是其中较为突出的部分,受到了一些学者们的关注。O’Neill的《地毯、市场和制造商:藏人地毯行业的文化与企业家精神》[5]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专著。这篇民族志论文对三百多个地毯厂的概况和民族志资料进行了分析,研究对象是尼泊尔加德满都Boudha和Jorpati两个地区开发委员会的当地西藏—尼泊尔地毯业的企业家,主要关注在这一产业因为虐待童工问题常常遭到国际舆论批评时期的企业家。在欧洲地毯商人与离散藏人的出口商合作,利用藏人的地毯编织技术并结合欧洲的设计研制出一种混合型的“西藏”地毯之后,该产业在过去的十年中获得了惊人的发展。因此,成千名藏人企业家和尼泊尔企业家获得了商业全球化带来的新的经济岗位。同时,地毯业也出现了不合法的大量雇佣童工的现象。作者认为,童工现象更主要是欧洲市场需求的产物,而不是由传统剥削行为所造成的。
其次,许多欧美学者在对所谓“流亡者”的口述材料的应用上未加辨别,研究中带有较强的情绪色彩。许多藏人出于某些身份策略,通过话语来博取国际社会的同情,这种本身具有强烈政治目的性的文本是不能不加甄别就全盘使用的。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欧美学者的这种身份促使了中国海外藏人去建构自己的历史故事,以期获得西方社会更多的关注和经济援助。
(五)宗教与文化研究
关于中国海外藏人的宗教文化研究,以Moran的《佛教观察:加德满都的旅行者、流亡者和西藏佛法》[6]为代表。这项人类学研究考察了西方旅游者和藏人流亡者在尼泊尔加德满都郊区的Bodhanath的遭遇,并分析了佛教在政治、文化和宗教认同讨论中的重要性。Moran考察了藏人和藏传佛教是如何在Bodhanath的遭遇中被“创造”的,以及西方佛教徒是如何把他们想象中的文化和宗教具体化的。藏传佛教已经成为Bodhanath卓越的文化产品,它不仅是外国游客的奇观,也提醒了流离失所的藏人铭记民族文化。在这里,作者特别关注的是,藏传佛教是如何被西方游客当作一个要观察、思考和内在化的对象来呈现的。这项研究指出,构成西方世界对藏传佛教的认知的通常基于一种对异文化的想象。
三、关于国内外中国海外藏人研究的几点思考
(一)对国外研究的批判性思考
在对中国海外藏人生活现状的实证研究中,欧美学者走在了前列,不仅在研究成果的学科构成、研究主题上具有广泛性,而且在运用的研究方法上十分多样,尤其是在深入开展实地研究上,值得我们中国学者学习和借鉴。欧美学界对于中国海外藏人的研究是成体系的,无论是在理论的运用上还是在经验调查的开展上,都具备较高的学术水准。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欧美相关研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对其进行批判和反思是拓展我国对境外藏人研究应迈出的第一步。
麻石水电站于1970年6月开始动工建设,1971年9月截流,1972年底第1台机试运行发电,1973年5月正式投产。2号机和3号机分别于1976年4月和9月投产,建成时装机容量为1.0×105kW。后于2006年和2011年对3台机组进行技术改造后,装机容量为1.085×105kW,最大发电引用流量708.9m3/s,多年平均发电量 4.5361×108kW·h,装机年利用小时数4143h。
由律师William Vela向旧金山移民法院提交的报告《藏人印度公民身份分析》[10],简要探讨了西藏难民印度公民身份的法律问题。虽然这一简短的说明涉及到在美国寻求庇护的西藏难民个人,但它对更多的人有用,因为它规定西藏难民被印度法律列为外国人,因此不享有与印度公民相同的权利和特权。维拉以一系列的证据支持他的主张,包括与不同官员的通信、政府文件和其他法律案件的摘要。尽管仅仅这一简要说明可能不足以支持西藏难民不是也不可能成为印度公民的论点,但它肯定是一份强有力的支持文件。
第三,出于对藏人群体的“西方式”的解读,欧美学者主要关注藏人难民的权益保障、经济与医疗援助等问题上,而在其他一些主题的研究上则略显不足。如今,由于大部分中国海外藏人的生活或多或少适应并融入了当地社会,西方舆论界也不再像前几十年那样热切关注这些藏人,因而欧美学界对于中国海外藏人研究的热度也逐渐趋于平淡,对于中国海外藏人的当前生活状况的研究略显不足。
另一篇名为《“富难民”的赞助、资金和西藏难民的非正规经济问题》[25]的文章则探讨了印度达兰萨拉(Dharamsala)藏族难民社区“非正式”经济交流和赞助关系的发展问题。作者首先回顾了对西藏难民现代性的调查所带来的理论和方法上的挑战,然后关注“流亡者”非正式经济中一种特殊的交换形式:rogs ram,即外国人对藏人的赞助。文章认为,在经济资本稀缺的社区中,象征性资本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实际上它是经济资本的附带条件。象征资本高度不稳定的特点意味着,对西藏难民和其他社区来说,它的经济资本转换是艰巨的,并导致赞助者和受惠者之间的紧张谈判。这样的研究揭示了海外藏人社区同西方赞助者之间的重要经济关系,以及海外藏人社区的发展机制。
内浮顶储罐主要部件有:浮盘、内浮筒、骨架、梯子、浮顶人孔、周边密封装置、安全通气阀、量油孔、浮盘支腿、浮盘防转装置、导静电线、雷达液位导波管导向装置等组成。浮盘材质主要选用铝及铝合金、不锈钢,浮盘与储罐间加装弹性密封装置来达到对浮盘下油品、油气的密封。浮盘在储罐安全液位范围内上下移动,通过浮盘下安装的浮筒来起伏浮盘运行,同时浮盘上的安全通气阀、支腿在浮盘下落时起到对浮盘的保护和支撑。
(二)对国内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西藏问题”尤其是中国海外藏人问题,是我国党和政府始终关切的重要问题。然而,在有关中国海外藏人的学术研究方面,相较于欧美学者的研究,国内的相关研究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
一方面,我国学界对欧美学者有关中国海外藏人研究成果的梳理和分析不足,使得国内学者对国外藏学发展状况了解不足。评述类成果仅有苏发祥的《论海外藏人社区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及其特点》[27]一文,简要回顾和总结近年来中国海外藏人社区人类学研究的历程及其特点;刘志扬的《海外藏人的人类学研究:围绕北美藏学博士学位论文的评析》[28]一文,将研究对象圈定在北美藏学博士论文,分别梳理了印度、尼泊尔境内藏人居住区的文化适应研究和藏人移居西方国家后的生活与“藏族认同”研究,对这些北美学位论文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给出了客观的评价。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对国外的藏学研究机构也有过一些介绍,索珍的《美国主要涉藏研究机构和藏学研究人员现状及其分析》[29]《奥地利主要涉藏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现状分析》[30]《德国主要涉藏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现状分析》[31]三篇文章,分别围绕美国、奥地利、德国的涉藏研究机构和藏学研究者的现状进行了跟踪和研究,并就这几个欧美国家藏学的趋势及特点做出了分析。但显然,国内学者对欧美关于中国海外藏人研究的了解仍然不足。
另一方面,国内的中国海外藏人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显不足。现有研究成果包括马林的《第二代流亡藏胞状况及达赖集团对他们的影响和控制》[32]、游祥飞的《国外藏人近况探析》[33]、李明欢的《海外藏胞的发展状况与多元分化》[34]等。总体来看,国内的研究成果十分有限,研究主题也较为局限,对海外藏人现状的掌握也不够全面深入。中国海外藏人这一特殊而庞大的群体作为关涉今日中国“西藏问题”变化的兼具内外因素的重要力量,其内外联动的方式一直深刻地影响着“西藏问题”的走向。但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以往我们对这个特殊群体只是有所闻而不知其详,尤其是缺乏中国学者自己身历其境的第一手田野调查资料和数据,根据他者传言与文献资料形成的判断往往难以让我们做出准确的战略判断与政策决断,更难以在国际社会确立本国对于“西藏问题”的话语权。因此,关注中国海外藏人的生活境遇、着力开展我国海外藏人的研究乃是目前学术界的当务之急。
1.5.1 单因素分析 将血药浓度检测结果定义为“因变量”,对应的“自变量”为性别、年龄、体表面积(BSA)、白蛋白水平、肝功能水平、N-乙酰化酶2(NAT2)*4位点基因型、NAT2*15位点基因型和有无合并基础疾病。对于部分更适合作为分类资料处理的自变量进行赋值量化 (肝功能异常为ALT或AST>40 U·L-1),量化结果见表 1。使用 SPSS 20.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治疗2个月后,两组流脓涕、鼻塞、头闷痛、耳胀痛评分较治疗前均显著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两组治疗前、后嗅觉不灵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鼻塞、头闷痛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流脓涕、耳胀痛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我们也要认识到,国内海外藏人研究前景可观。尤其在研究的客观性与全面性上,中国学者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国海外藏人与国内藏民族在民族情感、宗教文化、地域等方面的高度认同性,使中国海外藏人问题与国内的“西藏问题”有高度的关联性和联动性。因而,将中国海外藏人研究与国内的藏族研究相结合,构建起更加完整的藏族研究体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通过基于中国视角的中国海外藏人研究,构建基于中国人研究的话语概念、话语体系,以及涉藏问题理论,有助于应对西方政治势力和价值观的挑战,促进与国际藏学界相关学者进行平等的对话和交流。同时,依托第一手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资料历史、全面、动态地了解、认识中国海外藏人群体,可对治藏、稳藏、安藏及应对复杂的“西藏问题”提供基础性研究成果。
注释:
①十四世达赖喇嘛成立“西藏文献与档案图书馆”,用于保存从西藏带出的文献与档案,并充当对外学术交流机构。该机构还以藏语、英语和印地语出版书籍和杂志,包括英文刊物《西藏季刊》和《藏药》,以及在大吉岭创刊的《西藏之声》(后更名为《西藏评论》),还出版了250本英文和印地文撰写的关于佛教哲学和其他西藏文化方面的书籍。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立学术机构、发行刊物、出版著作是达赖集团向国际社会宣传“藏独”的重要方式。
水泵控制均为变频调速恒压变量供水。集中显示、管理、分散控制。系统各部分相对独立,分散了危险性,增加了整个系统的可靠性。具有良好的扩展能力,利用网络技术完成系统的纵向扩展和横向扩展。管理维护方便,可维护性好,系统中的任一部分因故脱离系统,不会影响系统其他部分正常运行。
②Immigration and Refugee Board of Canada. 1992. “India: 1) Legal Status of Tibetan Refugees; 2) Rights of Tibetans to Indian Nationality.” Available online: http://www.unhcr.org/refworld/docid/3ae6aab124.html.
③Immigration and Refugee Board of Canada. 1999. “India: Situation of Tibetan Refugees and Those Not Recognized as Refugees; Including Legal Rights and Living Conditions.” Available online: http://www.unhcr.org/cgi-bin/texis/vtx/refworld/rwmain?docid=3ae6ad4124.
④Immigration and Refugee Board of Canada. 2009. “China/India: Residency Rights of Tibetans Residing in India; Requirements for Tibetans to Obtain and Retain Permanent Residence in India.” Available online: http://www.unhcr.org/cgibin/texis/vtx/refworld/rwmainpage=country&docid=4a7040b81c&skip=0&coi=IND&rid=4562d8cf2&querysi=tibetans&searchin=title&display=10&sort=date.
⑤United States Bureau of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 2003. “India: Information on Tibetan Refugees and Settlements.” Available online: http://www.unhcr.org/cgibin/texis/vtx/refworld/rwmain?docid=3f51f90821.
⑥United States Committee for Refugees and Immigrants. 2007. “World Refugee Survey 2007 -India.” Available online: http://www.refugees.org/countryreports.aspx?id=2000.
参考文献:
[1]Saklani G. Tibetan Refugees in India: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an uprooted community[J]. The Tibet Journal, 1978, 3(4): 41-46.
[2]Crescenzi A, Ketzer E, Van Ommeren M, et al. Effect of political imprisonment and trauma history on recent Tibetan refugees in India[J].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Official Public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raumatic Stress Studies, 2002, 15(5): 369-375.
[3]McConnell F. Governmentality to practise the state? Constructing a Tibetan population in exile[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012, 30(1): 78-95.
[4]Subba T B. One or many paths: coping with the Tibetan refugees in India[J]. New Delhi: Regency,2002.
[5]O’Neill T. Carpets, Markets and Makers: Culture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TibetoNepalese Carpet Industry[D]. Canada: MC Master University, 1997.
[6]Moran P. Buddhism observed: travellers, exiles and Tibetan Dharma in Kathmandu[M]. Routledge, 2003.
[7]Feller, Erika. Asylum, Migration and Refugee Protection: Realities, Myths and the Promise of Things to Com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fugee Law, 2006, 18 (3): 509-536.
[8]Yeh, Emily. 2002. “Will the Real Tibetan Please Stand Up!: Identity Politics in the Tibetan Diaspora”. In Klieger, P.C. (ed.), Tibet, Self, and the Tibetan Diaspora : Voices of Difference ; PIATS 2000: Tibetan Studies: Proceedings of the Nin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Boston: Brill.
[9]Prost, Audrey. Contagion and its Guises: Inequalities and Disease among Tibetan Exiles in India.[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2008,46 (5):55-70.
[10]Vela, William. Analysis of Indian Citizenship for Tibetans.[C]// San Francisco: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Executive Office of Immigration Review,2003.
[11]Amchok, Jamyang Tashi. In Exile, It’s Not Home.[C]// Tibetan Review: The Monthly Magazine on all Aspects of Tibet, 2010:25-26.
[12]Sachs, Emily, Barry Rosenfeld, Dechen Lhewa, Andrew Rasmussen, and Allen Keller. Entering Exile: Trauma, Mental Health, and Coping among Tibetan Refugees Arriving in Dharamsala, India.[J].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2008, 21 (2):199-208.
[13]Falcone, Jessica, and Tsering Wangchuk. We’re Not Home: Tibetan Refugees in Ind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J]. India Review ,2008,7 (3): 164-199.
[14]Bhatia, Shushum, Tsegyal Dranyi, and Derrick Rowley. A Social and Demographic Study of Tibetan Refugees in India.[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2002,54: 411 - 422.
[15]Dolma, Sonam, Sonal Singh, Lynne Lohfeld, James J. Orbinski, and Edward J. Mills. Dangerous Journey: Documenting the Experience of Tibetan Refugees.[J].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2006, 96 (11): 2061-2064.
[16]Goldstein M C. Ethnogenesis and resource competition among Tibetan refugees in South India[J]. Ethnicity and resource competition in plural societies, 1975: 159-186.
[17]De Voe D M. Keeping refugee status: a Tibetan perspective[J]. Center for Migration Studies Special issues,1987.
[18]Houston S, Wright R. Making and remaking Tibetan diasporic identities[J].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2003, 4(2): 217-232.
[19]Anand D. (Re) imagining nationalism: Identity and representation in the Tibetan diaspora of South Asia [J]. Contemporary South Asia, 2000, 9(3): 271-287.
[20]Kolas A. Tibetan nationalism: the politics of religion[J].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1996, 33(1): 51-66.
[21]Subba T B. Flight and adaptation: Tibetan refugees in the Darjeeling-Sikkim Himalaya[M]. 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 2000.
[22]Methfessel T. Socioeconomic adaptation of Tibetan refugees in South Asia over 35 years in exile[C]//KOROM Frank J., Tibetan Culture in the Diaspora. Papers presented at a panel of the 7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Tibetan Studies, Graz. 1995: 13-24.
[23]Adams W F. Tibetan refugees in India: integration opportunities through development of social, cultural and spiritual traditions[J].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2005, 40(2).
[24]Wangmo T, Teaster P B. The bridge from then to now: Tibetan elders living in diaspora[J]. Journal of Applied Gerontology, 2010, 29(4): 434-454.
[25]Prost A. The problem with ‘rich refugees’ sponsorship, capital, and the informal economy of Tibetan refugees[J]. Modern Asian Studies, 2006, 40(1): 233-253.
[26]赵光锐.历史追溯与现实关切:德国学界西藏研究的新进展[J].国际政治研究,2014(6).
[27]苏发祥.论海外藏人社区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及其特点[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
[28]刘志扬.海外藏人的人类学研究:围绕北美藏学博士学位论文的评析[J].思想战线,2012(6).
[29]索珍.美国主要涉藏研究机构和藏学研究人员现状及其分析[J].中国藏学,2006(2).
[30]索珍.奥地利主要涉藏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现状分析[J].中国藏学,2007(3).
[31]索珍.德国主要涉藏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现状分析[J].中国藏学,2008(2).
[32]马林.第二代流亡藏胞状况及达赖集团对他们的影响和控制[J].青海社会科学,2000(5).
[33]游祥飞.国外藏人近况探析[D].中央民族大学,2005.
[34]李明欢.海外藏胞的发展状况与多元分化[J].世界民族,2014(6).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391(2019)04-0037-10
DOI: 10.3969/j.issn.1674-9391.2019.04.00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活”项目“尼泊尔中国海外藏人的历史与现状研究”(2018VJX09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李志农( 1969-),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藏学研究;高云松( 1993-),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藏区民族关系研究。云南 昆明 650091
收稿日期: 2019-03-19
责任编辑:许巧云
标签:欧美论文; 中国海外藏人论文; 研究综述论文;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论文;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论文;
